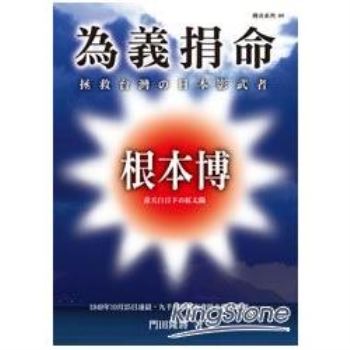寫在前面:六十年如白駒過隙 門田隆將
強風穿越了台灣海峽,在海面上掀起了無數的白色波濤,飛濺起來的水沫和映照在水面的陽光,鋪陳出一片令人為之目眩的白色景象。一陣陣的波濤聲,似乎在哀悼在這裏喪失生命的年輕英靈。
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古寧頭大捷屆滿六十年的日子裡,我站在金門的一座小山上,遠眺著對岸的中國大陸。作為兩岸的分界點,這個地方在十五年前還不許外國人進入,就連台灣人自己也不能隨意進出。
這座小島曾經是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就在這裡,幾十萬發的砲彈隔空互射;就在這裡,數以萬計的年輕戰士浩浩蕩蕩地渡海進攻,卻再也回不了家鄉。
我之所以從日本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是想要了解六十年前來這裡參戰的日本人,心裡到底在想什麼?當時數以萬計的年輕戰士又抱持何種態度?那些不幸在戰爭中喪生者,心中是否殘留什麼樣的悔恨?
金門距離中國大陸只有短短兩公里,簡直就像附著在大陸沿岸一樣,其主權卻屬於遠在一百八十公里外的台灣;是什麼樣的因素阻隔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更密切往來?難道是橫亙其間的台灣海峽嗎?
時間要拉回到六十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在全球各地展開拉鋸、爭霸戰,其中衝突最大的要數位在中國境內的「國共內戰」。當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展開好幾場激烈血戰,最後在金門這個小島劃上休止符。那時誰都沒有想到,在這之前幾乎每一場關鍵戰役都落敗的國民黨,竟然會在差不多已經崩潰的情況下,於金門古寧頭獲得大勝。
更少人知道,在這場奇蹟般的勝利背後,竟有一位日本人大力協助。這個人是誰?他為什麼要在日本戰敗後的一九四九年,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全、進駐金門最前線?而且隱身幕後,殫精竭慮,功成而不居?
那就是前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陸軍中將根本博。
時序再往前推,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時還有四萬名日本軍民滯留在中國內蒙。八月二十日蘇聯軍隊趁中華民國政府鞭長莫及之際,打算強行接收。根本博為了保護部下與僑民的安全,毅然決然悍然抵抗,與蘇軍周旋到底;最後終於獲得國民政府傾全力調派可用車船接應,將全部的日本僑民與將士安全遣返,之後他才懷抱著無限感恩之心搭船回國。
豈料後來國民政府在內戰中一敗再敗,幾乎一籌莫展;這位日軍司令官於是以報恩之心再度來華,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此種義舉連當時的主政者也覺得不可思議,完全想像不到。
這就是根本博的「以義報義」,甚至不惜「為義捐命」!
他是個貫徹人道主義思想的軍人與戰略家,他對「義」這個原則的堅持,讓他的所作所為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但他為了貫徹這些想法,確實也犧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本書所要敘述的,就是這麼一個不怕犧牲生命,以「義」為生存原則的日本人,以及一群跨越國界而支持他的人,他們那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二○一○年春筆者
序幕:我感到非常遺憾---- 根本博拜訪明石家的第一句話 明石元紹
時間是一九五二年秋天,地點在日本新宿御苑附近,內藤町一號的一棟兩層樓洋房裡,漫溢著一種幾乎要令人窒息的沉重氣氛,一個留著灰白頭髮,穿著灰色西裝,臉上掛著一副圓形黑框眼鏡的男士來到這裡,朝著先父的靈位上香。
雖然這個具有獨特氣氛的人出現,讓我們(明石)家人感到訝異,不知其所為何來。但母親似乎早就有預感,還把他帶到供奉先父靈位的房間裡。從母親恭敬的態度中,我感覺到這位應該是個重要的客人。
他點燃了自己帶來的線香,拜了幾下後就插在香爐中,雙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詞,好似在對先父報告著什麼事情。他的一舉一動都展露出一種無形的威嚴,給人一種無形的壓迫感,就好像他曾經在修羅場中打滾過一樣;(後來才知道,來人確實走過槍林彈雨,過去都在戰場上拼搏。)
雖然我那時已經讀大一,也算是個成人,卻被那種壓迫氣氛所感染,緊張得不敢作聲。家母、祖母和小我一歲的妹妹似乎也是如此,只能默默注視他的背影。時間就在一片靜默中慢慢流逝,而這個陌生人的背影似乎越看越覺得巨大。
靜默讓人感覺時間過得特別緩慢,好像過了很久很久之後(至少也有四、五分鐘,實際上也許只有一分鐘,甚至更短,只有幾十秒而已),來人終於拜完了。
我們都等著他開口。
再過一會兒,他終於以嘶啞的聲音說:「我感到非常遺憾!」在說這句話時,眼中還透露出十分惋惜的神情。一個像巨人般給人壓迫感的人,卻突然冒出充滿感性的語言,好像為家父的英年早逝致歉一樣,讓我們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回應。
來人也不再多說,只是深深地向我們行禮,之後就站起來,跟來的時候一樣,慢慢地走出去。
雖然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有滿肚子的話要問,例如:父親為什麼抑鬱以終?死前那段時間他到底在做什麼?但我們都開不了口,他也沒有再說什麼。
當時明石家中只有我(元紹)是男性,按理必須代替父親成為家中的支柱,一肩擔起守護家庭的責任。但直到陌生人突然來訪這一刻,我依然無法理解父親的想法與作為;到底在生命日薄崦嵫之際,他是在努力推動什麼計劃呢?其所作所為又有什麼秘密?
雖然滿腹狐疑,但就一個剛從學習院高等科畢業,才進入慶應大學經濟學系就讀的十九歲學生而言,我實在太嫩(太年輕)且見識不足,不夠格質問眼前這位威嚴外露的男性。直到後來才從母親口中得知,來人名叫根本博,當時六十一歲,是前陸軍中將,曾擔任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他是在回到日本後,得知家父明石元長已經過世,才特地前來弔唁。其實那時父親已經過世三年,就習俗而言,過世三年後才來上香總讓人覺得有點詫異。
據說父親明石元長就是為了護送根本博到台灣,不眠不休地到處奔走,結果因積勞成疾而過世。我雖然對此說將信將疑,但既然母親認同,那麼在沒有更確實的資訊出現前,我們也只能估且相信。
明石家和台灣有難以切割的情分 門田隆將
明石元紹是第七任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上任)之孫,他父親明石元長則是元二郎的長子。
明石家和台灣,有著難以切斷的緣分。
元紹的祖父明石元二郎,在日本軍界中擁有非常多的傳說,但其赫赫功績並不是在戰場上,而是見不得光的情報戰與謀略戰。比如說在日俄戰爭期間(一九○四到一九○五年),明石元二郎就在歐洲籌措資金,暗中支持俄國境內的反政府運動,製造敵國內部不穩的情勢。由於他把這個當時號稱「日本陸軍的最大任務」做得非常漂亮,使得他不但成為傳說中的人物,其所作所為也成為戰前日本陸軍情報學校的重要教材。
明石元二郎一生中的最後一項職務,就是一九一八年就任第七任台灣總督。在短短一年半中,他做出了許多貢獻,比如設立台灣電力公司,積極推展水力發電事業,開譬道路等許多基本城市建設;而且建構台灣的金融、教育與司法制度等等,奠定了未來的發展基礎。
也許正因為太過勞累,以至於在返回日本後不久,即於故鄉福岡猝逝。他生前遺言「死後要葬在台灣」,所以家屬特地將其棺木從福岡移葬於台北市。(編按:明石元二郎的遺體運來台灣後,就葬在台北市南京東路與林森北路口的日本人公墓中。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拆除附近及公墓上的違章建築,將所有遺骸遷葬台北縣三芝鄉,原址改建為大安森林公園。)
明石元二郎過世時,長子明石元長還在台灣唸小學,直到畢業才回到日本,後來成為貴族院議員。(編按:戰前的日本國會稱為「帝國議會」,分為「貴族院」和「眾議院」兩院;戰後廢除「貴族院」,改為「參議院」。)
明石元長過世如一場噩夢
明石元紹還記得父親過世那天的情景。
就在根本博到他家弔唁的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四十二歲的明石元長剛從九州回家。當時他們位在中野的住家已遭二次大戰時的美軍炸毀,而暫住在母親內藤和子娘家。由於內藤家的祖先為江戶時代信州(現在的長野縣)高遠藩藩主,在東京新宿一帶擁有佔地廣大的宅邸,因而特別撥出旁邊一棟原本留給下一代居住的兩層樓洋房,讓明石家棲身。那時明石元紹還是高中生,雖然不知道父親到底去做了什麼事,但從其疲憊不堪的神情看來,顯然剛完成了一件大事。
明石元長回到家後,第三天就覺得身體有些不對勁,接著突然說「胃好痛!」
才剛說完就開始痛苦呻吟,痛得額頭冒出冷汗。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應該是過度勞累引起,所以元紹的母親命他趕快去請附近內科診所的森戶醫生前來,立刻給病人打一針止痛劑,之後患者就不再喊痛,慢慢地睡著了。
但這種情況沒有維持多久,大約晚上十一點多時,他父親不斷叫痛,大聲呻吟,家人再度請醫生前來打止痛劑。不料完全沒效,患者叫痛的聲音越來越大,還難過得滿地打滾,接著聲音越來越微弱,最後唉叫一聲就再也不動了。醫生看到這種景象也嚇得臉色發白,家人更是張惶失措。
「爸爸!」元紹就像要喚父親回來一樣地脫口而出。明石一家四人(包括祖母在內)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病人痛苦死去,一時之間都說不出話來。
森戶醫生則鐵青著一張臉,一語不發,不知道過了多久才鼓起勇氣、確認病人的脈搏,然後以一句「很遺憾」宣告死亡。
還在唸高一的元紹雖然外表像個大人,其實還是個孩子,他眼看昨天還好好的父親,就這麼突然死了,現在躺在床上、變成一具冰冷的遺體,簡直無法接受這個現實;還在唸初二的妹妹更不用說了。然而元紹的母親還不放棄;雖然送走森戶醫生時已經半夜,她還是決定請住在附近、慶應大學醫學系第一代教授川添正道醫師過來看看。
川添醫師看在鄰居份上趕過來,仔細檢查患者的脈博與瞳孔後,不好意思地說:「很遺憾,已經過世了。」
這時大家都忍不住叫了一聲:「爸爸……」,但沒有哭。任何人在遭到這種強烈衝擊時,可能當下都沒有辦法適切反應吧!包括感情在內。
幾天後明石元紹才從媽媽口中得知,父親在猝逝前曾經透露片斷消息,據說為了協助一位將軍「到台灣去」,不惜違反國家禁令,到處奔走籌措資金、張羅船隻,包括送出去的途徑與方式等,都親自參與,最後終於完成心願。
從此之後大約三年時間裡,元紹為了升學和維持家計而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再去想這件事,一直到那個嚴肅的人:前陸軍中將根本博出現,才讓他的內心再度波濤洶湧;心想:父親不就是為了把這個人送到台灣去,才力盡而亡的嗎?而他在台灣的那幾年又做了什麼呢?
遺憾的是,從短暫接觸的那一天之後,明石元紹再也沒見過根本博。如此千載難逢、可以問清楚一切的機會就那樣失去了,以致他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裡,一直為這件事情感到懊悔。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流逝,明石元紹已經過了父親猝逝的四十二歲,兩個女兒也都各自結婚生子,現在已經七十五歲,垂垂老矣,但隨著年歲增加,他追尋父親當年奮鬥的真相之心反而愈加強烈。如今回想當時父親痛得在地上打滾、大聲呻吟,連主治醫師的臉也嚇得發白的景象,對於那時還在讀高一,被炎炎夏日曬得頭部發昏的明石元紹來說,就好像做了一場噩夢一樣。
第一章 搭小船偷渡
宮崎縣日向灣沿岸氣候溫暖、景觀秀麗,尤其是被稱為「日豐海岸」的大分線南部至宮崎縣北部一帶,半島與海灣彼此交錯,閃閃發光的白砂、青松和高峻的斷崖交互輝映,整個景色如同里昂式海岸般富於變化,觀光客往往流連忘返。這裡還盛產青花魚、竹筴魚、河豚等,漁業資源豐富,不僅吸引許多漁民前來捕撈,釣客也趨之若鶩。
但這是現在的景致,我們若把時間推移到西元一九四九年,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不久,聯合國委託的美軍總部(GHQ)正統治著日本,百廢待興,當時人人努力奮鬥,只希望能生存下去;直到二十年後才有觀光客出現。
就在GHQ嚴格管制日本船艦的情況下,這裡卻出現了極不尋常的情況。
先搭小船再接泊「捷信號」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從清早開始就吹帶有濕氣、且比平常還大的風,到了下午果然下起雨來。這是南部地區梅雨季節的常見現象,海水就像與梅雨相呼應一樣,每次一降雨,海面上就波濤洶湧,而且越接近傍晚,風雨越強波濤也越洶湧。
強風穿越了台灣海峽,在海面上掀起了無數的白色波濤,飛濺起來的水沫和映照在水面的陽光,鋪陳出一片令人為之目眩的白色景象。一陣陣的波濤聲,似乎在哀悼在這裏喪失生命的年輕英靈。
二○○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古寧頭大捷屆滿六十年的日子裡,我站在金門的一座小山上,遠眺著對岸的中國大陸。作為兩岸的分界點,這個地方在十五年前還不許外國人進入,就連台灣人自己也不能隨意進出。
這座小島曾經是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就在這裡,幾十萬發的砲彈隔空互射;就在這裡,數以萬計的年輕戰士浩浩蕩蕩地渡海進攻,卻再也回不了家鄉。
我之所以從日本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是想要了解六十年前來這裡參戰的日本人,心裡到底在想什麼?當時數以萬計的年輕戰士又抱持何種態度?那些不幸在戰爭中喪生者,心中是否殘留什麼樣的悔恨?
金門距離中國大陸只有短短兩公里,簡直就像附著在大陸沿岸一樣,其主權卻屬於遠在一百八十公里外的台灣;是什麼樣的因素阻隔台灣與大陸之間的更密切往來?難道是橫亙其間的台灣海峽嗎?
時間要拉回到六十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在全球各地展開拉鋸、爭霸戰,其中衝突最大的要數位在中國境內的「國共內戰」。當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和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在這片廣袤的大地上展開好幾場激烈血戰,最後在金門這個小島劃上休止符。那時誰都沒有想到,在這之前幾乎每一場關鍵戰役都落敗的國民黨,竟然會在差不多已經崩潰的情況下,於金門古寧頭獲得大勝。
更少人知道,在這場奇蹟般的勝利背後,竟有一位日本人大力協助。這個人是誰?他為什麼要在日本戰敗後的一九四九年,不顧自己的生命安全、進駐金門最前線?而且隱身幕後,殫精竭慮,功成而不居?
那就是前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陸軍中將根本博。
時序再往前推,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時還有四萬名日本軍民滯留在中國內蒙。八月二十日蘇聯軍隊趁中華民國政府鞭長莫及之際,打算強行接收。根本博為了保護部下與僑民的安全,毅然決然悍然抵抗,與蘇軍周旋到底;最後終於獲得國民政府傾全力調派可用車船接應,將全部的日本僑民與將士安全遣返,之後他才懷抱著無限感恩之心搭船回國。
豈料後來國民政府在內戰中一敗再敗,幾乎一籌莫展;這位日軍司令官於是以報恩之心再度來華,希望能助一臂之力。此種義舉連當時的主政者也覺得不可思議,完全想像不到。
這就是根本博的「以義報義」,甚至不惜「為義捐命」!
他是個貫徹人道主義思想的軍人與戰略家,他對「義」這個原則的堅持,讓他的所作所為至今仍讓人印象深刻;但他為了貫徹這些想法,確實也犧牲了很多人的生命。
本書所要敘述的,就是這麼一個不怕犧牲生命,以「義」為生存原則的日本人,以及一群跨越國界而支持他的人,他們那段不為人知的過去。
二○一○年春筆者
序幕:我感到非常遺憾---- 根本博拜訪明石家的第一句話 明石元紹
時間是一九五二年秋天,地點在日本新宿御苑附近,內藤町一號的一棟兩層樓洋房裡,漫溢著一種幾乎要令人窒息的沉重氣氛,一個留著灰白頭髮,穿著灰色西裝,臉上掛著一副圓形黑框眼鏡的男士來到這裡,朝著先父的靈位上香。
雖然這個具有獨特氣氛的人出現,讓我們(明石)家人感到訝異,不知其所為何來。但母親似乎早就有預感,還把他帶到供奉先父靈位的房間裡。從母親恭敬的態度中,我感覺到這位應該是個重要的客人。
他點燃了自己帶來的線香,拜了幾下後就插在香爐中,雙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詞,好似在對先父報告著什麼事情。他的一舉一動都展露出一種無形的威嚴,給人一種無形的壓迫感,就好像他曾經在修羅場中打滾過一樣;(後來才知道,來人確實走過槍林彈雨,過去都在戰場上拼搏。)
雖然我那時已經讀大一,也算是個成人,卻被那種壓迫氣氛所感染,緊張得不敢作聲。家母、祖母和小我一歲的妹妹似乎也是如此,只能默默注視他的背影。時間就在一片靜默中慢慢流逝,而這個陌生人的背影似乎越看越覺得巨大。
靜默讓人感覺時間過得特別緩慢,好像過了很久很久之後(至少也有四、五分鐘,實際上也許只有一分鐘,甚至更短,只有幾十秒而已),來人終於拜完了。
我們都等著他開口。
再過一會兒,他終於以嘶啞的聲音說:「我感到非常遺憾!」在說這句話時,眼中還透露出十分惋惜的神情。一個像巨人般給人壓迫感的人,卻突然冒出充滿感性的語言,好像為家父的英年早逝致歉一樣,讓我們一時之間也不知該如何回應。
來人也不再多說,只是深深地向我們行禮,之後就站起來,跟來的時候一樣,慢慢地走出去。
雖然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有滿肚子的話要問,例如:父親為什麼抑鬱以終?死前那段時間他到底在做什麼?但我們都開不了口,他也沒有再說什麼。
當時明石家中只有我(元紹)是男性,按理必須代替父親成為家中的支柱,一肩擔起守護家庭的責任。但直到陌生人突然來訪這一刻,我依然無法理解父親的想法與作為;到底在生命日薄崦嵫之際,他是在努力推動什麼計劃呢?其所作所為又有什麼秘密?
雖然滿腹狐疑,但就一個剛從學習院高等科畢業,才進入慶應大學經濟學系就讀的十九歲學生而言,我實在太嫩(太年輕)且見識不足,不夠格質問眼前這位威嚴外露的男性。直到後來才從母親口中得知,來人名叫根本博,當時六十一歲,是前陸軍中將,曾擔任中國派遣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他是在回到日本後,得知家父明石元長已經過世,才特地前來弔唁。其實那時父親已經過世三年,就習俗而言,過世三年後才來上香總讓人覺得有點詫異。
據說父親明石元長就是為了護送根本博到台灣,不眠不休地到處奔走,結果因積勞成疾而過世。我雖然對此說將信將疑,但既然母親認同,那麼在沒有更確實的資訊出現前,我們也只能估且相信。
明石家和台灣有難以切割的情分 門田隆將
明石元紹是第七任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到一九一九年十月上任)之孫,他父親明石元長則是元二郎的長子。
明石家和台灣,有著難以切斷的緣分。
元紹的祖父明石元二郎,在日本軍界中擁有非常多的傳說,但其赫赫功績並不是在戰場上,而是見不得光的情報戰與謀略戰。比如說在日俄戰爭期間(一九○四到一九○五年),明石元二郎就在歐洲籌措資金,暗中支持俄國境內的反政府運動,製造敵國內部不穩的情勢。由於他把這個當時號稱「日本陸軍的最大任務」做得非常漂亮,使得他不但成為傳說中的人物,其所作所為也成為戰前日本陸軍情報學校的重要教材。
明石元二郎一生中的最後一項職務,就是一九一八年就任第七任台灣總督。在短短一年半中,他做出了許多貢獻,比如設立台灣電力公司,積極推展水力發電事業,開譬道路等許多基本城市建設;而且建構台灣的金融、教育與司法制度等等,奠定了未來的發展基礎。
也許正因為太過勞累,以至於在返回日本後不久,即於故鄉福岡猝逝。他生前遺言「死後要葬在台灣」,所以家屬特地將其棺木從福岡移葬於台北市。(編按:明石元二郎的遺體運來台灣後,就葬在台北市南京東路與林森北路口的日本人公墓中。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拆除附近及公墓上的違章建築,將所有遺骸遷葬台北縣三芝鄉,原址改建為大安森林公園。)
明石元二郎過世時,長子明石元長還在台灣唸小學,直到畢業才回到日本,後來成為貴族院議員。(編按:戰前的日本國會稱為「帝國議會」,分為「貴族院」和「眾議院」兩院;戰後廢除「貴族院」,改為「參議院」。)
明石元長過世如一場噩夢
明石元紹還記得父親過世那天的情景。
就在根本博到他家弔唁的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四十二歲的明石元長剛從九州回家。當時他們位在中野的住家已遭二次大戰時的美軍炸毀,而暫住在母親內藤和子娘家。由於內藤家的祖先為江戶時代信州(現在的長野縣)高遠藩藩主,在東京新宿一帶擁有佔地廣大的宅邸,因而特別撥出旁邊一棟原本留給下一代居住的兩層樓洋房,讓明石家棲身。那時明石元紹還是高中生,雖然不知道父親到底去做了什麼事,但從其疲憊不堪的神情看來,顯然剛完成了一件大事。
明石元長回到家後,第三天就覺得身體有些不對勁,接著突然說「胃好痛!」
才剛說完就開始痛苦呻吟,痛得額頭冒出冷汗。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應該是過度勞累引起,所以元紹的母親命他趕快去請附近內科診所的森戶醫生前來,立刻給病人打一針止痛劑,之後患者就不再喊痛,慢慢地睡著了。
但這種情況沒有維持多久,大約晚上十一點多時,他父親不斷叫痛,大聲呻吟,家人再度請醫生前來打止痛劑。不料完全沒效,患者叫痛的聲音越來越大,還難過得滿地打滾,接著聲音越來越微弱,最後唉叫一聲就再也不動了。醫生看到這種景象也嚇得臉色發白,家人更是張惶失措。
「爸爸!」元紹就像要喚父親回來一樣地脫口而出。明石一家四人(包括祖母在內)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病人痛苦死去,一時之間都說不出話來。
森戶醫生則鐵青著一張臉,一語不發,不知道過了多久才鼓起勇氣、確認病人的脈搏,然後以一句「很遺憾」宣告死亡。
還在唸高一的元紹雖然外表像個大人,其實還是個孩子,他眼看昨天還好好的父親,就這麼突然死了,現在躺在床上、變成一具冰冷的遺體,簡直無法接受這個現實;還在唸初二的妹妹更不用說了。然而元紹的母親還不放棄;雖然送走森戶醫生時已經半夜,她還是決定請住在附近、慶應大學醫學系第一代教授川添正道醫師過來看看。
川添醫師看在鄰居份上趕過來,仔細檢查患者的脈博與瞳孔後,不好意思地說:「很遺憾,已經過世了。」
這時大家都忍不住叫了一聲:「爸爸……」,但沒有哭。任何人在遭到這種強烈衝擊時,可能當下都沒有辦法適切反應吧!包括感情在內。
幾天後明石元紹才從媽媽口中得知,父親在猝逝前曾經透露片斷消息,據說為了協助一位將軍「到台灣去」,不惜違反國家禁令,到處奔走籌措資金、張羅船隻,包括送出去的途徑與方式等,都親自參與,最後終於完成心願。
從此之後大約三年時間裡,元紹為了升學和維持家計而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再去想這件事,一直到那個嚴肅的人:前陸軍中將根本博出現,才讓他的內心再度波濤洶湧;心想:父親不就是為了把這個人送到台灣去,才力盡而亡的嗎?而他在台灣的那幾年又做了什麼呢?
遺憾的是,從短暫接觸的那一天之後,明石元紹再也沒見過根本博。如此千載難逢、可以問清楚一切的機會就那樣失去了,以致他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歲月裡,一直為這件事情感到懊悔。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流逝,明石元紹已經過了父親猝逝的四十二歲,兩個女兒也都各自結婚生子,現在已經七十五歲,垂垂老矣,但隨著年歲增加,他追尋父親當年奮鬥的真相之心反而愈加強烈。如今回想當時父親痛得在地上打滾、大聲呻吟,連主治醫師的臉也嚇得發白的景象,對於那時還在讀高一,被炎炎夏日曬得頭部發昏的明石元紹來說,就好像做了一場噩夢一樣。
第一章 搭小船偷渡
宮崎縣日向灣沿岸氣候溫暖、景觀秀麗,尤其是被稱為「日豐海岸」的大分線南部至宮崎縣北部一帶,半島與海灣彼此交錯,閃閃發光的白砂、青松和高峻的斷崖交互輝映,整個景色如同里昂式海岸般富於變化,觀光客往往流連忘返。這裡還盛產青花魚、竹筴魚、河豚等,漁業資源豐富,不僅吸引許多漁民前來捕撈,釣客也趨之若鶩。
但這是現在的景致,我們若把時間推移到西元一九四九年,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不久,聯合國委託的美軍總部(GHQ)正統治著日本,百廢待興,當時人人努力奮鬥,只希望能生存下去;直到二十年後才有觀光客出現。
就在GHQ嚴格管制日本船艦的情況下,這裡卻出現了極不尋常的情況。
先搭小船再接泊「捷信號」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從清早開始就吹帶有濕氣、且比平常還大的風,到了下午果然下起雨來。這是南部地區梅雨季節的常見現象,海水就像與梅雨相呼應一樣,每次一降雨,海面上就波濤洶湧,而且越接近傍晚,風雨越強波濤也越洶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