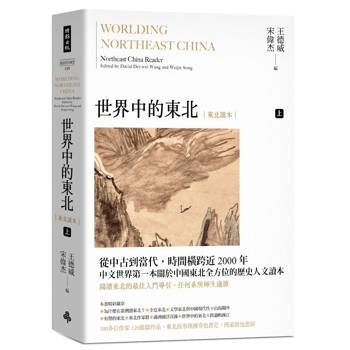導論
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王德威
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
──傅斯年,《東北史綱》
「東北」作為中國現代經驗的輻輳點,具有多重意義。狹義的東北指代東北三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以及內蒙古東部。這塊土地面積一百六十二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一億。廣義的東北則指涉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時的規劃,包括外興安嶺以南、烏蘇里江以東、庫頁島在內的大片土地。東北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夏官.職方氏》,《尚書.禹貢》、《山海經》均有記載。1907年清廷於東北設置三省,正式使用「東三省」一名。「東北」、「關東」或「關外」為中國一般習稱,而「滿洲」一詞則為近現代日本及西方所沿用。
東北歷史源遠流長,卻從來被視為中原文化與政治的外圍。「關外」意味政治地理和文化傳統的邊緣。但在中國近現代史脈絡中,東北的地位無可比擬。1644年,雄據山海關外的滿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開啟所謂「華夷變態」──華與夷地位顛倒──的契機。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不僅關乎東北的歸屬,更牽動歐亞霸權博弈。1931年九一八事變,導致日後偽滿洲國的建立以及第二次中日戰爭。1946年後的國共內戰,東北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最早易幟。1949年後,東北以其戰略位置、自然資源以及重工業基礎,成為「共和國的長子」。
然而曾幾何時,東北遭遇種種挑戰,不僅產業下滑,民氣積弱,甚至人口不斷外流,成為亟待「振興」的區域。事實上,從毛澤東時代以「三線建設」為名開發西北、西南,到江澤民時代倡導「西部大開發」,東北總是瞠乎其後。近年「一帶一路」計劃再次強調西北與西南,相形之下,東北又錯過了大勢之所趨。從偏見的眼光看來,東北是落後與落寞的。
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振興」東北?方法之一,是重新講述東北故事。所謂故事,當然不只是虛構的起承轉合,而更關乎一個社會如何經由各種對話、傳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體。換句話說,就是給出一個新的說法,重啟大敘事。目前東北文學與文化研究往往囿於邊緣意識,成為主流論述的對應或從屬,因此難以凸現特色。而在海外,滿洲或偽滿洲國研究獨樹一幟,又遮蔽了東北文化的來龍去脈。我們必須借助敘事的力量為這一地區的過去與當下重新定位,也為未來打造願景。
東北是個有「故事」的地方。在東北,清代流人寫下困蹇蹉跎的詩詞,闖關東的移民口耳相傳墾荒冒險的傳奇。《呼蘭河傳》(1940)、〈松花江上〉(1944)、《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巨流河》(2009)等當代文人創作見證這塊土地的魅力與情懷,電視劇《闖關東》(2008)、紀錄片《鐵西區》(2004)演繹一個世紀東北創業史的希望與悵惘。《八月的鄉村》(1935)、《林海雪原》(1957)傳頌革命歷史的豪情壯志,《杜晚香》(1978)、《北荒草》則銘記一代革命人的激情與創傷。
在東北,白俄、猶太難民引進歐洲摩登,日本、臺灣、朝鮮移民勉力落地生根。滿鐵、中東鐵路快車奔馳著,紅鬍子神出鬼沒,薩滿大神遊盪四方。張作霖、張學良、愛新覺羅.溥儀、馬占山、楊靖宇、趙一曼、安重根、川島芳子、李香蘭出入歷史舞臺。另一時空裏,王進喜、雷鋒以生命證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樣板;劉賓雁、劉曉波以生命捍衛個人的理想與信仰。東北蒼莽沉鬱,卻絕不乏世俗的生命力甚至自嘲嘲人的韌性和痞性。上個世紀末「二人轉」突然發揚光大,「忽悠」文化傳染全國,〈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歡唱一時。
這林林總總的線索如何能匯集成有關東北的敘事?相對於海外方興未艾的滿洲和偽滿洲國研究,以「東北學」為名的論述是否有其可能?
「東北」的定義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第一,一個地理所在,包容獨特的社會人文與風土自然生態;第二,一個流動的文化、族群、政經脈絡,啟動關內與關外各種關係運作;第三,一個「時空座標」(chronotope),投射、建構有關「東北」的想像、言說、論述、演繹。如上所述,文學所指不僅限於書面文章,也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象徵活動。「東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感覺結構」──因器物、事件、風景、情懷、行動所體現的「人同此心」的想像、信念、甚至意識形態的結晶。
本章將從四個角度切入,說明文學對東北研究的意義。第一,東北的(文學)現代性與空間政治的關聯;第二,「東北」與「滿洲」敘事線索的辯證;第三,東北的跨區域及跨文化屬性;第四,講好東北故事的方法。
地理就是歷史
儘管東北文明可以上溯八千年前或更早,東北的文學與文化卻必須與近現代掛鉤。和關內傳統相比──不論是江南還是巴蜀,關中還是荊楚──東北都顯得瞠乎其後。清代以前東北漁獵、游牧、農耕文化夾雜,不利文風滋長;清代以來東北被視為龍興之地,嚴禁移民,更難以形成氣候。反倒是貶官囚徒如楊賓、吳兆騫、方式濟等以血淚書寫謫民背井離鄉之痛,形成獨特「流人文學」傳統。十九世紀下半葉東北解禁,大批墾殖者湧進,繼之以殖民勢力入侵,每每因時因地激發出歌謠傳奇,形式則未必能登大雅之堂。
如果東北缺乏傳統文學史的譜系,這一地區文學文化就必須從不同方面?眼。我以為與其刻意追蹤歷史脈絡,東北文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興起,從無到有,本身恰恰就是現代經驗的表徵。「現代」的意義源出多端,歸根結底,在於歷史主體置於前無來者的情境下,對時空絕續的深刻體會,對文明板塊位移的巨大警醒,對種種生命可能與不可能的決絕演練。「東三省」的設立在二十世紀之初(1907),恰恰是甲午與日俄戰爭後,中國與東洋、西洋,封建王朝與革命勢力衝突的「核心現場」。「東北」此時浮出歷史地表,宛如一場關鍵詞的命名式,是帝國命運急轉直下的標記,也是新世界發生的起源。因為東北,「現代」有了地理意義,進入文學視野。
相對於中原各個文學區域所根植的歷史譜系學(genealogy)傳承,我強調文學東北最重要的依歸是對地理拓撲學(topography)──空間的符號學──的指認和銘刻。現代文學濫觴時刻,東北已經是重要座標。「新小說」發起人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2)即是以兩位留歐青年革命者搭乘西伯利亞鐵路,經過山海關回到中國。黃克強主張立憲,李去病號召革命。他們激烈辯論新中國的未來時,放眼望去是殖民者蠶食鯨吞的東北大地。
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王德威
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
──傅斯年,《東北史綱》
「東北」作為中國現代經驗的輻輳點,具有多重意義。狹義的東北指代東北三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以及內蒙古東部。這塊土地面積一百六十二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一億。廣義的東北則指涉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時的規劃,包括外興安嶺以南、烏蘇里江以東、庫頁島在內的大片土地。東北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夏官.職方氏》,《尚書.禹貢》、《山海經》均有記載。1907年清廷於東北設置三省,正式使用「東三省」一名。「東北」、「關東」或「關外」為中國一般習稱,而「滿洲」一詞則為近現代日本及西方所沿用。
東北歷史源遠流長,卻從來被視為中原文化與政治的外圍。「關外」意味政治地理和文化傳統的邊緣。但在中國近現代史脈絡中,東北的地位無可比擬。1644年,雄據山海關外的滿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開啟所謂「華夷變態」──華與夷地位顛倒──的契機。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不僅關乎東北的歸屬,更牽動歐亞霸權博弈。1931年九一八事變,導致日後偽滿洲國的建立以及第二次中日戰爭。1946年後的國共內戰,東北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最早易幟。1949年後,東北以其戰略位置、自然資源以及重工業基礎,成為「共和國的長子」。
然而曾幾何時,東北遭遇種種挑戰,不僅產業下滑,民氣積弱,甚至人口不斷外流,成為亟待「振興」的區域。事實上,從毛澤東時代以「三線建設」為名開發西北、西南,到江澤民時代倡導「西部大開發」,東北總是瞠乎其後。近年「一帶一路」計劃再次強調西北與西南,相形之下,東北又錯過了大勢之所趨。從偏見的眼光看來,東北是落後與落寞的。
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振興」東北?方法之一,是重新講述東北故事。所謂故事,當然不只是虛構的起承轉合,而更關乎一個社會如何經由各種對話、傳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體。換句話說,就是給出一個新的說法,重啟大敘事。目前東北文學與文化研究往往囿於邊緣意識,成為主流論述的對應或從屬,因此難以凸現特色。而在海外,滿洲或偽滿洲國研究獨樹一幟,又遮蔽了東北文化的來龍去脈。我們必須借助敘事的力量為這一地區的過去與當下重新定位,也為未來打造願景。
東北是個有「故事」的地方。在東北,清代流人寫下困蹇蹉跎的詩詞,闖關東的移民口耳相傳墾荒冒險的傳奇。《呼蘭河傳》(1940)、〈松花江上〉(1944)、《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巨流河》(2009)等當代文人創作見證這塊土地的魅力與情懷,電視劇《闖關東》(2008)、紀錄片《鐵西區》(2004)演繹一個世紀東北創業史的希望與悵惘。《八月的鄉村》(1935)、《林海雪原》(1957)傳頌革命歷史的豪情壯志,《杜晚香》(1978)、《北荒草》則銘記一代革命人的激情與創傷。
在東北,白俄、猶太難民引進歐洲摩登,日本、臺灣、朝鮮移民勉力落地生根。滿鐵、中東鐵路快車奔馳著,紅鬍子神出鬼沒,薩滿大神遊盪四方。張作霖、張學良、愛新覺羅.溥儀、馬占山、楊靖宇、趙一曼、安重根、川島芳子、李香蘭出入歷史舞臺。另一時空裏,王進喜、雷鋒以生命證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樣板;劉賓雁、劉曉波以生命捍衛個人的理想與信仰。東北蒼莽沉鬱,卻絕不乏世俗的生命力甚至自嘲嘲人的韌性和痞性。上個世紀末「二人轉」突然發揚光大,「忽悠」文化傳染全國,〈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歡唱一時。
這林林總總的線索如何能匯集成有關東北的敘事?相對於海外方興未艾的滿洲和偽滿洲國研究,以「東北學」為名的論述是否有其可能?
「東北」的定義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第一,一個地理所在,包容獨特的社會人文與風土自然生態;第二,一個流動的文化、族群、政經脈絡,啟動關內與關外各種關係運作;第三,一個「時空座標」(chronotope),投射、建構有關「東北」的想像、言說、論述、演繹。如上所述,文學所指不僅限於書面文章,也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象徵活動。「東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感覺結構」──因器物、事件、風景、情懷、行動所體現的「人同此心」的想像、信念、甚至意識形態的結晶。
本章將從四個角度切入,說明文學對東北研究的意義。第一,東北的(文學)現代性與空間政治的關聯;第二,「東北」與「滿洲」敘事線索的辯證;第三,東北的跨區域及跨文化屬性;第四,講好東北故事的方法。
地理就是歷史
儘管東北文明可以上溯八千年前或更早,東北的文學與文化卻必須與近現代掛鉤。和關內傳統相比──不論是江南還是巴蜀,關中還是荊楚──東北都顯得瞠乎其後。清代以前東北漁獵、游牧、農耕文化夾雜,不利文風滋長;清代以來東北被視為龍興之地,嚴禁移民,更難以形成氣候。反倒是貶官囚徒如楊賓、吳兆騫、方式濟等以血淚書寫謫民背井離鄉之痛,形成獨特「流人文學」傳統。十九世紀下半葉東北解禁,大批墾殖者湧進,繼之以殖民勢力入侵,每每因時因地激發出歌謠傳奇,形式則未必能登大雅之堂。
如果東北缺乏傳統文學史的譜系,這一地區文學文化就必須從不同方面?眼。我以為與其刻意追蹤歷史脈絡,東北文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興起,從無到有,本身恰恰就是現代經驗的表徵。「現代」的意義源出多端,歸根結底,在於歷史主體置於前無來者的情境下,對時空絕續的深刻體會,對文明板塊位移的巨大警醒,對種種生命可能與不可能的決絕演練。「東三省」的設立在二十世紀之初(1907),恰恰是甲午與日俄戰爭後,中國與東洋、西洋,封建王朝與革命勢力衝突的「核心現場」。「東北」此時浮出歷史地表,宛如一場關鍵詞的命名式,是帝國命運急轉直下的標記,也是新世界發生的起源。因為東北,「現代」有了地理意義,進入文學視野。
相對於中原各個文學區域所根植的歷史譜系學(genealogy)傳承,我強調文學東北最重要的依歸是對地理拓撲學(topography)──空間的符號學──的指認和銘刻。現代文學濫觴時刻,東北已經是重要座標。「新小說」發起人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2)即是以兩位留歐青年革命者搭乘西伯利亞鐵路,經過山海關回到中國。黃克強主張立憲,李去病號召革命。他們激烈辯論新中國的未來時,放眼望去是殖民者蠶食鯨吞的東北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