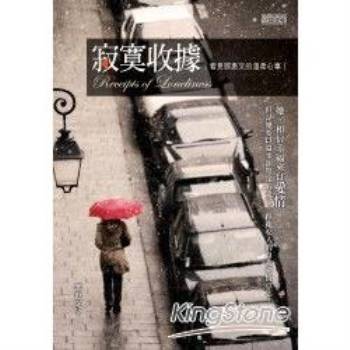〈爸爸〉
她的記憶有一道斷層,她不知道父親是怎麼不見的。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明白的。明白他走了。
「那麼,就談到這裡。」
她抬頭看了時鐘。長針已經經過12,斜倚在2的上方。
還是超過了時間。穿上外套的時候,她看著K,想從他臉上多找到一些線索,關於她自己的線索。
但是K的臉上並沒有特別的表情。如果有,也只能說是一貫的疲累樣子。他起身走在前面,替她打開門,沒有說下週見,只是微微地點頭,視線似乎望進她的瞳孔,但又穿透過去,飄向遠方。
K是她的心理治療師。每個星期一晚上,她從工作的地方坐兩段票公車去找他。一小時後或者更晚一點,再走一段路搭捷運回家。這樣過了一年。到目前為止,她仍然沒有辦法把K對她的所有詮釋整合起來。
上車以後,她試著回想過去一年內和K的談話,卻覺得疲倦不堪。
她首先想起K捲菸的手。他會用三根手指從有浮雕的鐵盒中捏出菸草,在白色的薄紙上鋪成一線,然後從一側捲起,熟練地壓緊菸草,細長的紙捲在他修長的指間滾動著。然後她聞到點燃的菸草味道,沈厚中透著辛辣的氣味。
視覺和嗅覺都非常清晰,但語言的記憶卻成團糾結。此刻她想不起任何談過的話。列車進站後上來了一個穿深色西裝的男人,木香調的古龍水氣味漫過她的臉龐。
她突然覺得在K指間滾動的瘦長紙菸有點像蠶。
小學的時候她養過蠶,那時候大家都養。第一次在國小後門的文具店買蠶,老闆把牠們放在紅白條紋的塑膠袋裡交給她。一路上她頻頻察看,總覺得牠們在袋子裡一動也不動。她擔心老闆抓蠶的時候傷了牠們。到家後,她小心翼翼地把牠們移進一只鞋盒,盯著看了很久,直到確定每一隻都活著。漸漸地,她瞭解蠶並不是有趣的寵物,除了調整姿勢以便齧咬桑葉之外,牠們很少如預期地爬來爬去。她花了一些時間注視頂蓋打了洞洞的紙盒,主要是為了確定牠們活著,其次是嘗試跟牠們互動,但她很快就明白沒有什麼可為之處。幾週後,蠶的身軀變胖、變黃,然後就開始吐絲。
有一天放學回家,她發現所有的蠶都不見了,紙盒裡是十個淡黃色的繭。她知道牠們在裡面,但感覺卻是消失了。她拿起其中一個,很輕,輕得像會被呼吸吹走。透著燈光檢視,沒有什麼影子,搖起來像是空無一物。她的蠶們消失了,吃掉了桑葉和她的零用錢,自始至終面無表情,然後集體消失了。她試著想像書上描繪的蛻變生長圖,但卻無法在心中發現任何一絲期待。
她不太想看牠們出來以後的樣子,一點也不想。
她覺得一切都結束了。
那天晚上她一直聞到指頭上沾染的蠶繭味道,洗了許多次還是聞得到。她躺在外婆身邊,張著眼睛過了一夜,牆上不時飄過大大小小的黑影,伴隨著窗外車輛疾駛而過的聲音。一輛車的遠燈照亮前面的車,投射出移動的黑影,後面的車燈又照著這輛,形成層層疊疊深深淺淺的黑影,走馬燈似地投射在她四周的牆上。外婆熟睡著發出規律的鼾聲。她第一次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沒有辦法呼喊誰、只剩下自己的存在。
走出K的治療室時,她也有這種感覺,彷彿又回到無底的孤寂之中。在開始治療之前,她的工作中止了,她從早上到晚上都保持著大同小異的姿態,偶爾必須移動的時候也極其緩慢。她一向非常地瘦,但那一陣子更加厲害,她只喝流體,一小塊雞肉都會使她嘔吐。
蠶並不是她養的第一種動物。五歲的春天,她得到一隻鸚鵡作為慰病的禮物。那時候她父親還會來,一個星期兩次或三次,穿深色西裝,提著黑色的硬殼公事包。父親帶鸚鵡來的時候,她患了胃炎,不斷地嘔吐,躺在沙發上,出診打針的護士剛剛離開。父親放下公事包,蹲下來仔細看了她的臉和她的手。她歪著頭,看見他的視線隨著扎在她手背上的細長軟管一路往上,停在另一端連接的點滴瓶上。他的頭稍微向後仰著,眼球也往上看,額頭的皮膚皺起了紋路,她看到他下巴一些黑色的鬍渣,比上次來時多些。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聞到一些菸草和古龍水混合的味道。
他舉起一個鳥籠讓她看。綠色的鳥站在一根橫桿上,同她一般歪著頭。鳥並沒有叫,也沒有發出其他聲音。
她跟鸚鵡相處的時間不算長。牠沒有學過她說話,她甚至不記得自己有沒有餵過牠。鳥籠通常被懸掛在後陽台,在廚房外面。下一次她生病的時候,又連續幾天不斷地嘔吐。等到她好不容易退燒以後,終於有人想起了後陽台的綠鸚鵡。她們沒讓她看見僵掉的鳥。之後很久,她都沒有到後陽台去過。
她長大後還是經常這樣生病。胃裡漲滿酸液起起落落地翻攪,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衝上來。櫥櫃的氣味、特殊食物的氣味、鄰家裝潢的揮發溶劑都會啟動這樣的翻攪。她頭昏眼花,飄盪在模糊的意識之間,望著似乎永遠滴不完的點滴,用發燙的手指觸摸冰涼的細長軟管。她想念菸草混合古龍水的味道。但是她父親在鸚鵡還活著的時候就已經不再來了。
二十七歲的夏天,她在另一個男人身上嗅到菸草混合古龍水的味道。那個午後她靜靜地躺著,覺得非常虛弱。
「點滴順著細細的管子流進妳的身體,這樣很erotic。」來看她的男人逗留了五分鐘,笑著這樣說。他不戴手錶,卻總能準時地離開她回家。她沒有力氣抬頭看他,只是望著他放在地上的公事包,一個陳舊但質地堅韌的牛皮手提包。許多年沒有出現過的孤寂感一下子擴散開來。她突然覺悟,這個男人永遠無法瞭解她是如何地害怕嘔吐,而這是她吐過最嚴重的一次。那個下午說再見的時候,她決定了他將不會知道,曾經有六個星期,她的身體裡有另一個心跳。
她說話的時候,K多半只是靜靜地聽。她花了很多時間敘述關於生病和嘔吐的事。K第一次打斷她,問她是否能想起任何喜歡的食物。她沒有回答。之後的下一次,她依約進入治療室,坐下來一整個小時都沒有說話。她們沉默地對坐,K捲了一支又一支的菸。時針接近12的時候,她才抬起頭。
「我把所有的繭都丟掉。」她看著治療室牆上的風景月曆,成千上萬的蝴蝶佈滿狹長的谷道。
「丟掉。」他重複。
「事實上,」她緊閉雙唇,彷彿說話是艱難的。
「我把一個剪破了。」
她在二十七歲生日的前一天去做手術。出門前她把胎兒的超音波相片放進皮包夾層。護士為她打上點滴,她再度躺著,伸出手指觸摸細管,一如預期的冰涼。護士對她微笑,將裝有麻醉藥的針筒扎進線上的橡皮支管。她很快就發現自己漂浮起來,幾星期以來的噁心欲吐全部消失了。自有記憶開始,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她想哭,舒服得好想哭。
K打開菸盒,卻發現裡面只有一些散落的碎屑。他把盒子蓋上放回原處,在紙片上寫了一個字。
「Leitmotif」,她看著紙片,再看著他。
「不斷重複的、主旋律。」他說。開始捲一根新的菸。
她沒有學過樂器,但她記起迴盪在舞蹈社裡的探戈樂曲。她的母親是一個社交舞老師。她不確定父親跳不跳舞。她在記憶中搜尋,沒有任何父親和母親跳舞的畫面,也沒有任何父親和母親相互擁抱、或者並肩而立的記憶。她看到的是父親修長的手指熟練地捲動包裹口香糖的錫箔紙,捏成一個漂亮的高腳杯,她和父親假裝著對飲,隨探戈樂曲的節奏搖晃酒杯。她聽見探戈的主旋律,手風琴的響聲膨脹延伸,再重重落下,父親和她重複著乾杯往覆的動作。
「Cheers,Cheers,」他們一遍一遍地說。這可能是她第一個學會的英文字。
在K那裡,她試過許多次,但完全沒有辦法把父親離開之前和離開之後的記憶銜接起來。她的記憶有一道斷層,她不知道父親是怎麼不見的。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明白的。
明白他走了。
從母親這邊的親戚口中,她努力拼湊了一個故事。父親認識母親的時候已經有了妻子和一個女兒。在她五歲之前,父親會在上班時間來,多半是接近中午的時候。他們一起吃午餐,和她玩藏在公事包裡帶來的新玩具。睡午覺之後,他淋浴,然後回去上班。
她自己不記得睡午覺的事。她存放在午後的記憶是他在她的頭髮上吹煙圈,一邊喊著火了,著火了。她尖叫,拼命想掙脫他的臂膀,但他緊緊地抱著她。她清楚地感覺到他呼出煙圈的氣息在她的頭皮上暖暖麻麻的。
五歲那年的夏天,父親帶著他的妻子和女兒移民澳洲。之後再也沒有聯絡。
母親說她被告知的時候,父親已經決定了。她連一句話都沒有問。
「母親是堅強的人。」K說。
她不願去想自己對母親的評語。父親走後,有很長一陣子母親很少回家。偶爾回來的時候,她會聞到酒味。她向她報告考試和各種比賽的名次,但母親心不在焉。外婆說母親忙著工作,她需要更多的錢。她學會挑無關緊要的話對母親說,而母親給予她大量的零用錢。高中三年級的某一天,母親在路口撞見一個男孩摟著她的肩膀。她們激烈地爭吵,她沒有辦法叫喊得比母親更大聲。她衝向窗口,用頭撞擊玻璃。外婆哭著攔她。
她母親停止謾罵。
「讓她死。」
她回頭,確定她的母親這麼說。
母親拿了皮包,頭也不回地走出去。
很多時候,她對母親的乾脆感到氣憤。大學修心理學時,她相信自己潛意識中怨恨母親弄丟了父親。她經常想,在過去的某一天,父親是否就像這樣頭也不回地走出去。她可能在睡覺,自己在玩,完全不知道他要走了。而她的母親看著父親離開,一句話也沒有問。
她不斷榨取記憶的汁液,他沒有向她道別嗎?他有沒有對她解釋過--或者像所有大人對小孩說的--爸爸要去很遠的地方,妳要乖乖聽媽媽的話?
她並未擁有這樣的記憶。他消失了。
她翻閱不到記載痛楚的一頁。在她的生命書裡,那一頁被膠黏起來,標示的頁數突兀地被跳過,無法翻閱,但卻未曾撕去,祕密地被保存下來。她的流產手術也是這樣。她沉沉睡著,任由冰冷的器械在她的子宮裡刮攪,她的小嬰兒只有二點一公分,比她看過的任何一個蠶繭更小,更輕,半透明的心臟和蟬翼一般的血管網絡生澀地輸送著來自她的血液。不鏽鋼的刮匙邊緣有鋸尺狀的突起,但她不會疼痛。她不在那裡,藥水把她帶到身體很舒服的天堂,在那兒,探戈手風琴的主旋律一遍一遍地迴旋,在她翠綠的蕾絲蓬裙旁邊,有一整排銀色的錫箔高腳杯。
醒來後她以為身體裡面已經沒有東西了。第二天她看著醫生從她體內取出好幾個浸著血漬的紗布團時,非常地訝異。但她沒有太多時間思考,沒有麻醉的內部清理過程十分疼痛。她哀求醫生,但他沒有回應。起來穿衣服的時候,她看著還沒有被收拾的紗布團,散發著浸漬血液的氣味。她想起自己剪破的繭緩緩流出液體,沾濕了她的手指。
她停下來。K把金黃色的茶水注滿她的紙杯。
終於她想起一種曾經喜愛的食物。
金黃色的蘋果汁。
她乾涸的口腔逐漸被唾液濕潤,舌上的味蕾紛紛膨脹起來。蘋果清香的甜味和縷縷酸味,掀開了她的祕密扉頁。
她記起蘋果的珍貴,小時候蘋果並不像現在的輕易可得,她吃的都是父親從日本特地買回來的富士蘋果。咬蘋果時,鬆搔的聲音會使她全身顫抖,所以外婆總是親手磨蘋果泥,再用雪白的紗布濾出果汁給她。她想起了許多早餐時刻,桌上有兩杯蘋果汁。一杯是她的,一杯是母親的。
她曾經看著母親喝蘋果汁,是母親住院的時候。外婆帶她到病房門口,要她提菜飯進去給母親。病房小而昏暗,她母親在被單裡,整個人好像小了一圈。
「媽咪,吃飯。」
母親接過她手上的圓形提籃,把每一層打開後,都只看了一眼就蓋上。打開底層的時候,她們的眼光同時落在一杯半滿的、金黃色的蘋果汁上。母親緩緩地端起杯子,移近嘴唇。母親的嘴唇很白,使她覺得有些陌生。她看著母親輕輕啜著蘋果汁,彷彿不是在喝,只是以嘴唇和舌尖蘸著。沒有開燈,她覺得媽媽好像在哭。她穿著薄長袖外衣,時節是夏季的末尾。她明白了那是什麼。
母親是去拿掉孩子的。在老房子對街的婦產科診所。
她想著母親對父親唯一的描述。
父親告訴她要走的時候,已經是決定了的。所以她一句話也沒說。
一句話也沒說。就像她自己懷孕的時候,默默望著男人的牛皮公事包的那一天。
她下車,回家。撥了母親的電話號碼。
「妳什麼時候回來?幫我帶講更年期的書好不好。」電話那端傳來嘈雜的水聲。
她許久不知該說什麼。
「喂?」
她的腦海中只出現一句話。她自言自語的說著。
「媽,妳是堅強的人。」
「喂?聽不清楚啊,妳打手機是不是?」
「我明天給妳買書回去,順便帶蘋果給妳。」
掛上電話,她感受到許久未有的飢餓。她打開冰箱,找到一包過期的泡麵。她換了熱水瓶的水,插上插頭。
在沙發上坐了一會之後,她猶疑著站起來,到床底下摸索了許久。她取出所有小時候母親不用而給她玩耍的鑲珠包包,一個一個打開。在翠綠色的那一個裡面,她拉開拉鍊夾層,找到一張泛黃但是仍然清晰的照片。她穿著蓬裙和跳舞鞋,笑得非常燦爛。父親和母親站在她身後,母親的頭朝父親偏著。她在母親另一側的腰間看見父親修長的手。
她的記憶有一道斷層,她不知道父親是怎麼不見的。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明白的。明白他走了。
「那麼,就談到這裡。」
她抬頭看了時鐘。長針已經經過12,斜倚在2的上方。
還是超過了時間。穿上外套的時候,她看著K,想從他臉上多找到一些線索,關於她自己的線索。
但是K的臉上並沒有特別的表情。如果有,也只能說是一貫的疲累樣子。他起身走在前面,替她打開門,沒有說下週見,只是微微地點頭,視線似乎望進她的瞳孔,但又穿透過去,飄向遠方。
K是她的心理治療師。每個星期一晚上,她從工作的地方坐兩段票公車去找他。一小時後或者更晚一點,再走一段路搭捷運回家。這樣過了一年。到目前為止,她仍然沒有辦法把K對她的所有詮釋整合起來。
上車以後,她試著回想過去一年內和K的談話,卻覺得疲倦不堪。
她首先想起K捲菸的手。他會用三根手指從有浮雕的鐵盒中捏出菸草,在白色的薄紙上鋪成一線,然後從一側捲起,熟練地壓緊菸草,細長的紙捲在他修長的指間滾動著。然後她聞到點燃的菸草味道,沈厚中透著辛辣的氣味。
視覺和嗅覺都非常清晰,但語言的記憶卻成團糾結。此刻她想不起任何談過的話。列車進站後上來了一個穿深色西裝的男人,木香調的古龍水氣味漫過她的臉龐。
她突然覺得在K指間滾動的瘦長紙菸有點像蠶。
小學的時候她養過蠶,那時候大家都養。第一次在國小後門的文具店買蠶,老闆把牠們放在紅白條紋的塑膠袋裡交給她。一路上她頻頻察看,總覺得牠們在袋子裡一動也不動。她擔心老闆抓蠶的時候傷了牠們。到家後,她小心翼翼地把牠們移進一只鞋盒,盯著看了很久,直到確定每一隻都活著。漸漸地,她瞭解蠶並不是有趣的寵物,除了調整姿勢以便齧咬桑葉之外,牠們很少如預期地爬來爬去。她花了一些時間注視頂蓋打了洞洞的紙盒,主要是為了確定牠們活著,其次是嘗試跟牠們互動,但她很快就明白沒有什麼可為之處。幾週後,蠶的身軀變胖、變黃,然後就開始吐絲。
有一天放學回家,她發現所有的蠶都不見了,紙盒裡是十個淡黃色的繭。她知道牠們在裡面,但感覺卻是消失了。她拿起其中一個,很輕,輕得像會被呼吸吹走。透著燈光檢視,沒有什麼影子,搖起來像是空無一物。她的蠶們消失了,吃掉了桑葉和她的零用錢,自始至終面無表情,然後集體消失了。她試著想像書上描繪的蛻變生長圖,但卻無法在心中發現任何一絲期待。
她不太想看牠們出來以後的樣子,一點也不想。
她覺得一切都結束了。
那天晚上她一直聞到指頭上沾染的蠶繭味道,洗了許多次還是聞得到。她躺在外婆身邊,張著眼睛過了一夜,牆上不時飄過大大小小的黑影,伴隨著窗外車輛疾駛而過的聲音。一輛車的遠燈照亮前面的車,投射出移動的黑影,後面的車燈又照著這輛,形成層層疊疊深深淺淺的黑影,走馬燈似地投射在她四周的牆上。外婆熟睡著發出規律的鼾聲。她第一次清楚地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沒有辦法呼喊誰、只剩下自己的存在。
走出K的治療室時,她也有這種感覺,彷彿又回到無底的孤寂之中。在開始治療之前,她的工作中止了,她從早上到晚上都保持著大同小異的姿態,偶爾必須移動的時候也極其緩慢。她一向非常地瘦,但那一陣子更加厲害,她只喝流體,一小塊雞肉都會使她嘔吐。
蠶並不是她養的第一種動物。五歲的春天,她得到一隻鸚鵡作為慰病的禮物。那時候她父親還會來,一個星期兩次或三次,穿深色西裝,提著黑色的硬殼公事包。父親帶鸚鵡來的時候,她患了胃炎,不斷地嘔吐,躺在沙發上,出診打針的護士剛剛離開。父親放下公事包,蹲下來仔細看了她的臉和她的手。她歪著頭,看見他的視線隨著扎在她手背上的細長軟管一路往上,停在另一端連接的點滴瓶上。他的頭稍微向後仰著,眼球也往上看,額頭的皮膚皺起了紋路,她看到他下巴一些黑色的鬍渣,比上次來時多些。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聞到一些菸草和古龍水混合的味道。
他舉起一個鳥籠讓她看。綠色的鳥站在一根橫桿上,同她一般歪著頭。鳥並沒有叫,也沒有發出其他聲音。
她跟鸚鵡相處的時間不算長。牠沒有學過她說話,她甚至不記得自己有沒有餵過牠。鳥籠通常被懸掛在後陽台,在廚房外面。下一次她生病的時候,又連續幾天不斷地嘔吐。等到她好不容易退燒以後,終於有人想起了後陽台的綠鸚鵡。她們沒讓她看見僵掉的鳥。之後很久,她都沒有到後陽台去過。
她長大後還是經常這樣生病。胃裡漲滿酸液起起落落地翻攪,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衝上來。櫥櫃的氣味、特殊食物的氣味、鄰家裝潢的揮發溶劑都會啟動這樣的翻攪。她頭昏眼花,飄盪在模糊的意識之間,望著似乎永遠滴不完的點滴,用發燙的手指觸摸冰涼的細長軟管。她想念菸草混合古龍水的味道。但是她父親在鸚鵡還活著的時候就已經不再來了。
二十七歲的夏天,她在另一個男人身上嗅到菸草混合古龍水的味道。那個午後她靜靜地躺著,覺得非常虛弱。
「點滴順著細細的管子流進妳的身體,這樣很erotic。」來看她的男人逗留了五分鐘,笑著這樣說。他不戴手錶,卻總能準時地離開她回家。她沒有力氣抬頭看他,只是望著他放在地上的公事包,一個陳舊但質地堅韌的牛皮手提包。許多年沒有出現過的孤寂感一下子擴散開來。她突然覺悟,這個男人永遠無法瞭解她是如何地害怕嘔吐,而這是她吐過最嚴重的一次。那個下午說再見的時候,她決定了他將不會知道,曾經有六個星期,她的身體裡有另一個心跳。
她說話的時候,K多半只是靜靜地聽。她花了很多時間敘述關於生病和嘔吐的事。K第一次打斷她,問她是否能想起任何喜歡的食物。她沒有回答。之後的下一次,她依約進入治療室,坐下來一整個小時都沒有說話。她們沉默地對坐,K捲了一支又一支的菸。時針接近12的時候,她才抬起頭。
「我把所有的繭都丟掉。」她看著治療室牆上的風景月曆,成千上萬的蝴蝶佈滿狹長的谷道。
「丟掉。」他重複。
「事實上,」她緊閉雙唇,彷彿說話是艱難的。
「我把一個剪破了。」
她在二十七歲生日的前一天去做手術。出門前她把胎兒的超音波相片放進皮包夾層。護士為她打上點滴,她再度躺著,伸出手指觸摸細管,一如預期的冰涼。護士對她微笑,將裝有麻醉藥的針筒扎進線上的橡皮支管。她很快就發現自己漂浮起來,幾星期以來的噁心欲吐全部消失了。自有記憶開始,從來沒有這麼舒服過。她想哭,舒服得好想哭。
K打開菸盒,卻發現裡面只有一些散落的碎屑。他把盒子蓋上放回原處,在紙片上寫了一個字。
「Leitmotif」,她看著紙片,再看著他。
「不斷重複的、主旋律。」他說。開始捲一根新的菸。
她沒有學過樂器,但她記起迴盪在舞蹈社裡的探戈樂曲。她的母親是一個社交舞老師。她不確定父親跳不跳舞。她在記憶中搜尋,沒有任何父親和母親跳舞的畫面,也沒有任何父親和母親相互擁抱、或者並肩而立的記憶。她看到的是父親修長的手指熟練地捲動包裹口香糖的錫箔紙,捏成一個漂亮的高腳杯,她和父親假裝著對飲,隨探戈樂曲的節奏搖晃酒杯。她聽見探戈的主旋律,手風琴的響聲膨脹延伸,再重重落下,父親和她重複著乾杯往覆的動作。
「Cheers,Cheers,」他們一遍一遍地說。這可能是她第一個學會的英文字。
在K那裡,她試過許多次,但完全沒有辦法把父親離開之前和離開之後的記憶銜接起來。她的記憶有一道斷層,她不知道父親是怎麼不見的。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明白的。
明白他走了。
從母親這邊的親戚口中,她努力拼湊了一個故事。父親認識母親的時候已經有了妻子和一個女兒。在她五歲之前,父親會在上班時間來,多半是接近中午的時候。他們一起吃午餐,和她玩藏在公事包裡帶來的新玩具。睡午覺之後,他淋浴,然後回去上班。
她自己不記得睡午覺的事。她存放在午後的記憶是他在她的頭髮上吹煙圈,一邊喊著火了,著火了。她尖叫,拼命想掙脫他的臂膀,但他緊緊地抱著她。她清楚地感覺到他呼出煙圈的氣息在她的頭皮上暖暖麻麻的。
五歲那年的夏天,父親帶著他的妻子和女兒移民澳洲。之後再也沒有聯絡。
母親說她被告知的時候,父親已經決定了。她連一句話都沒有問。
「母親是堅強的人。」K說。
她不願去想自己對母親的評語。父親走後,有很長一陣子母親很少回家。偶爾回來的時候,她會聞到酒味。她向她報告考試和各種比賽的名次,但母親心不在焉。外婆說母親忙著工作,她需要更多的錢。她學會挑無關緊要的話對母親說,而母親給予她大量的零用錢。高中三年級的某一天,母親在路口撞見一個男孩摟著她的肩膀。她們激烈地爭吵,她沒有辦法叫喊得比母親更大聲。她衝向窗口,用頭撞擊玻璃。外婆哭著攔她。
她母親停止謾罵。
「讓她死。」
她回頭,確定她的母親這麼說。
母親拿了皮包,頭也不回地走出去。
很多時候,她對母親的乾脆感到氣憤。大學修心理學時,她相信自己潛意識中怨恨母親弄丟了父親。她經常想,在過去的某一天,父親是否就像這樣頭也不回地走出去。她可能在睡覺,自己在玩,完全不知道他要走了。而她的母親看著父親離開,一句話也沒有問。
她不斷榨取記憶的汁液,他沒有向她道別嗎?他有沒有對她解釋過--或者像所有大人對小孩說的--爸爸要去很遠的地方,妳要乖乖聽媽媽的話?
她並未擁有這樣的記憶。他消失了。
她翻閱不到記載痛楚的一頁。在她的生命書裡,那一頁被膠黏起來,標示的頁數突兀地被跳過,無法翻閱,但卻未曾撕去,祕密地被保存下來。她的流產手術也是這樣。她沉沉睡著,任由冰冷的器械在她的子宮裡刮攪,她的小嬰兒只有二點一公分,比她看過的任何一個蠶繭更小,更輕,半透明的心臟和蟬翼一般的血管網絡生澀地輸送著來自她的血液。不鏽鋼的刮匙邊緣有鋸尺狀的突起,但她不會疼痛。她不在那裡,藥水把她帶到身體很舒服的天堂,在那兒,探戈手風琴的主旋律一遍一遍地迴旋,在她翠綠的蕾絲蓬裙旁邊,有一整排銀色的錫箔高腳杯。
醒來後她以為身體裡面已經沒有東西了。第二天她看著醫生從她體內取出好幾個浸著血漬的紗布團時,非常地訝異。但她沒有太多時間思考,沒有麻醉的內部清理過程十分疼痛。她哀求醫生,但他沒有回應。起來穿衣服的時候,她看著還沒有被收拾的紗布團,散發著浸漬血液的氣味。她想起自己剪破的繭緩緩流出液體,沾濕了她的手指。
她停下來。K把金黃色的茶水注滿她的紙杯。
終於她想起一種曾經喜愛的食物。
金黃色的蘋果汁。
她乾涸的口腔逐漸被唾液濕潤,舌上的味蕾紛紛膨脹起來。蘋果清香的甜味和縷縷酸味,掀開了她的祕密扉頁。
她記起蘋果的珍貴,小時候蘋果並不像現在的輕易可得,她吃的都是父親從日本特地買回來的富士蘋果。咬蘋果時,鬆搔的聲音會使她全身顫抖,所以外婆總是親手磨蘋果泥,再用雪白的紗布濾出果汁給她。她想起了許多早餐時刻,桌上有兩杯蘋果汁。一杯是她的,一杯是母親的。
她曾經看著母親喝蘋果汁,是母親住院的時候。外婆帶她到病房門口,要她提菜飯進去給母親。病房小而昏暗,她母親在被單裡,整個人好像小了一圈。
「媽咪,吃飯。」
母親接過她手上的圓形提籃,把每一層打開後,都只看了一眼就蓋上。打開底層的時候,她們的眼光同時落在一杯半滿的、金黃色的蘋果汁上。母親緩緩地端起杯子,移近嘴唇。母親的嘴唇很白,使她覺得有些陌生。她看著母親輕輕啜著蘋果汁,彷彿不是在喝,只是以嘴唇和舌尖蘸著。沒有開燈,她覺得媽媽好像在哭。她穿著薄長袖外衣,時節是夏季的末尾。她明白了那是什麼。
母親是去拿掉孩子的。在老房子對街的婦產科診所。
她想著母親對父親唯一的描述。
父親告訴她要走的時候,已經是決定了的。所以她一句話也沒說。
一句話也沒說。就像她自己懷孕的時候,默默望著男人的牛皮公事包的那一天。
她下車,回家。撥了母親的電話號碼。
「妳什麼時候回來?幫我帶講更年期的書好不好。」電話那端傳來嘈雜的水聲。
她許久不知該說什麼。
「喂?」
她的腦海中只出現一句話。她自言自語的說著。
「媽,妳是堅強的人。」
「喂?聽不清楚啊,妳打手機是不是?」
「我明天給妳買書回去,順便帶蘋果給妳。」
掛上電話,她感受到許久未有的飢餓。她打開冰箱,找到一包過期的泡麵。她換了熱水瓶的水,插上插頭。
在沙發上坐了一會之後,她猶疑著站起來,到床底下摸索了許久。她取出所有小時候母親不用而給她玩耍的鑲珠包包,一個一個打開。在翠綠色的那一個裡面,她拉開拉鍊夾層,找到一張泛黃但是仍然清晰的照片。她穿著蓬裙和跳舞鞋,笑得非常燦爛。父親和母親站在她身後,母親的頭朝父親偏著。她在母親另一側的腰間看見父親修長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