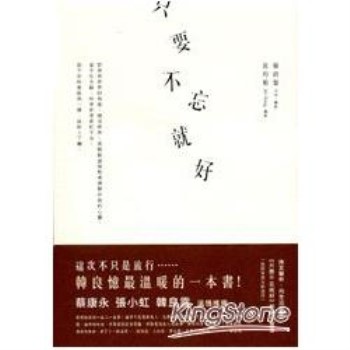母親的風衣
這是件款式傳統保守的風衣,卡其色,雙排扣,後擺開叉;褐色方格的內裡襯布則讓熟悉品牌的人,一望即知它是倫敦的老牌子。
它原來不是我的衣服,雖然的確是我多年以前在香港買的。當年我還挺年輕,卻已有了穩定且收入不低的工作,因此也像當年許多愛趕時髦的台灣白領女性,老愛往香港跑,香港當時可是時尚之地呢。
有年冬天,趁著春節假期,又到香港。港島的氣候一般和台灣差不多,冬天不怎麼冷,可那一回偏巧碰上冷鋒過境,亞熱帶的香港竟然涼颼颼。抵埠那天傍晚,我從港島搭地鐵過海到九龍,一出地鐵站,就被風吹颳得直打哆嗦,身上那件羊毛薄外套根本不擋寒,乾脆拐進購物中心,逛街兼取暖。
就這樣瞎逛到精品店,一眼看見這件Aquascutum風衣,我知道母親一直想要一件英國老牌風衣,卻嫌貴,捨不得買。在那之前幾年,家裡經濟出了問題,母親頗吃了點苦,那會兒難關雖已過了,但她心有餘悸,對錢仍很小心。
我考慮了半晌,毅然花了近半個月的薪水,買下了這件風衣。記得當時安慰自己,不貴不貴,這風衣不但可以孝敬母親,我在香港這幾天還可以「借穿」一下,藉以抵擋來自西伯利亞的北風,疼惜女兒的母親想來不會介意的。
母親果然一點也不介意,而且很喜歡這件禮物。台灣難得天冷,但只要一有寒意,母親就會穿上,旁人倘若稱讚兩句,母親就會說:「是良憶買給我的。」
SARS那一年,母親因病猝逝。整理遺物時,姊姊說:「風衣是妳送給媽媽的,妳拿走吧。」我默默收下,沒有多說什麼。這風衣算來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卻保養得很好,像是簇新的,母親顯然很珍惜。
我帶著風衣回到荷蘭,碰到下雨又起風的日子,出門總愛披上。不知有多少個蕭颯的秋日,多虧了這件風衣替我擋風遮雨,給了我一點溫暖,可是每逢這時,我卻又總是希望,那一刻穿著這風衣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母親。(待續)二姊
我的二姊良雯,我們都叫她阿雯。
她喜歡港式茶樓的廣州炒麵、台北遠企地下樓的生菜沙拉、麥當勞的冰咖啡和薯條;喜歡聽鄧麗君唱的〈虹彩妹妹〉;喜歡跟人聊天,問人家的爸爸或媽媽在那裡;喜歡玩大門的鎖鏈;最喜歡去「心路社區家園」上學。
她因為出生時腦部缺氧,有極重度智能障礙,台灣人稱之為「憨兒」,用美式英語的講法,則是「心智受挑戰者」(mentally challenged)。
我每個週末都從荷蘭打電話回家,向爸爸問好,並和從頭到尾拿著另一支分機傾聽對話的阿雯,談上兩句。姊妹間的對話常常是這樣的:
「阿雯,妳有沒有乖?」
「有。」
「有沒有吵把拔(爸爸)?」
「沒有。」(這時我爸會在分機上插嘴說:「阿雯現在好乖,都不吵。」)
「有沒有去麥當勞?」
「還沒有。」
「哦,那去的時候,不要吃太多薯條喔,太胖了會得高血壓。」然後,我常常就想不出來要講什麼,只好說:「阿雯,還有沒有事要對良憶妹妹說?」
電話那頭遲疑了一秒鐘,我可以想像一頭削薄短髮的阿雯,嘴巴正微微一開一閤,似在考慮下頭要聊些什麼。緊接著,一般有兩種版本。
第一版本:
「良憶美沒(妹妹),約柏呢?」約柏是我的丈夫,荷蘭人,基本上不會講中文。
「約柏在忙。」
「忙什麼?」
「忙打電腦(或整理照片、看報紙…等等)。」
「約柏馬麻(媽媽)呢?」
「在她家。」
「阿雯跟約柏講話。」
「好,等一下。」我這方於是換人。
阿雯在那一頭說:「哈嘍,約柏,鼓摸你。」
約柏回答:「Good morning,A-Wen。」
阿雯咯咯笑了。「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接著下來,只聽見阿雯大聲講:「三Q,拜拜。」然後又是一陣吃吃笑。
第二版本:
「良憶妹妹,荷蘭幾度?」
「xx度。」我會隨便講個數字。
「冷不冷?」
「不大冷。」
「有沒有下雨?」
「沒有。」
「好,」阿雯說,「拜拜。」
朋友聽說阿雯的情況,總愛問我她的心智年齡有多少,我的標準答案是多年前醫生講的,「三、四歲吧」。可是,三、四歲的孩子會跟她一樣,數數兒只能數到八或九,老是分不清楚三角形、四方形,然而接到我高中老同學的電話,不必問人家,光聽聲音,就能清楚地喊出對方的名字嗎?
三、四歲的孩子又會不會在我們的母親過世後,偶爾自問自答,說:「阿雯馬麻呢?」然後根據阿姨給她的答案,答稱:「上天堂去耶穌那裡了。」繼而嚎啕大哭,嚷道:「馬麻死了。」非得等旁邊的人再三保證,媽媽被上帝接走了,才會揉揉紅紅的眼睛,破渧為笑。
我也始終不明白,阿雯為什麼在沒有見到金髮藍眼的約柏以前,就曉得要跟他講 “How are you”,而不是「你好嗎」,三、四歲的孩子是這樣的嗎?
去年春節和中秋節,我兩度回台北探望老父和家人。阿雯週末從她住讀的「心路」回家,看到我,總是一下子迸出了笑顏,伸手摸摸我的臉,好像想確認她的妹妹果真又回到眼前。摸完,叫了聲「良憶美沒」,她盤腿坐在沙發上,上半身開始左右慢慢搖晃,嘴裡偶爾發出輕微的「喀喀」聲。阿雯只要覺得高興,就會這樣搖啊晃的,很自得其樂。
我常常在想,藏在這樣一副逐漸邁入中年,終將垂垂老矣的軀體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靈魂?是個比孩童還純真清澈的靈魂?還是個歷經多次輪迴,已閱盡滄桑哀樂,索性轉目不觀人世的老靈魂?
每個生命,都是個謎,而阿雯的生命,尤其是個謎。(待續)持叉舉杯,向人生致敬
從還有點悶熱的亞熱帶島嶼飛回秋涼的北溫帶低地國,算天公賞臉,陽光溫熙,正適合到公園散步,對抗時差。草地上一片落葉,還掛在樹梢的黃葉和紅葉被午間的陽光照得一樹金燦,秋意真的濃了。我隨手拾起一片金黃夾紽紅的落葉,放進羊毛外套口袋裡。秋天雖好,總嫌短暫,留下一片黃葉,算是見證自己有過一個絢麗璀璨的秋季。
果然,隔不了幾天,荷蘭吹起晚秋常見的暴風,樹木剎時禿了頭,寒風颼颼,彷彿刺入骨髓,我把輕薄的棉衣統統收進五斗櫃,風衣送洗,取出羽絨衣和喀什米爾羊毛圍巾,掛在玄關,每回出外以前總要把自己全身包裹得暖呼呼的,才敢踏出家門。
節氣剛過「小雪」後不久,鹿特丹飄起今年第一場雪,我戴上氈帽,在鹽粒般的細雪中,搭電車到市區,有兩位朋友晚上要來家裡吃飯,九月底初感秋涼時,我們一起在普羅旺斯度假,說好回荷後要約個時間交換照片看,轉眼秋已經深了。
天氣一冷,就想吃點熱騰騰的東西,我打算上中國城的肉店買火鍋肉片,做日式壽喜燒或中式涮鍋,給兩位荷蘭朋友嚐點東方味。興沖沖地進店裡,一問,肉片居然「賣哂」(粵語賣完了之意),難不成今晚鹿城有一半華人都要打邊爐?看來火鍋是做不成了,三位大男人都是肉食主義者,沒肉,可就怠慢了客人。
好吧,只好改弦易張,回頭做洋食,做什麼呢?原本一心想吃鍋物,菜單都盤算好了,這會兒一下子沒了主張,轉往有機小超市一看,菜架上儘是包心菜、大蘿蔔、胡蘿蔔、韭蔥、苦苣、抱子甘藍等較耐寒的蔬菜,還有馬鈴薯、南瓜與各種蕈菇,夏季時盛產的菠菜、生菜萵苣、彩椒和茄子等,不但數量上少了許多,價格也貴,想是溫室產品。水果攤上呢,不同品種的蘋果、梨和柳橙、蜜柑堆積如小山,難得還有西班牙來的脆柿,金的紅的,喜氣洋洋。
在店裡繞了一圈,繽紛的色彩看得人心情飛揚,靈感也來了,決定了,就準備四道菜:生蠔、柿子佐義大利風乾火腿、南瓜湯、白酒燉橄欖雞,甜點煮個紅酒梨好了。這一頓晚餐的材料有海裡採來的(生蠔),地裡種的(柿子、南瓜、橄欖和梨子),山上熟成的(火腿)、農場裡養的(有機放養雞),算得上「山珍海味」,而且是很適合秋季食用的養生晚餐。
不加任何中藥材,如何說是「養生」餐?可話說回來,誰規定養生一定得靠藥材?
先說生蠔吧。生蠔雖生雖涼,卻是秋冬滋補聖品。西方人傳統上講究只在英文拼音裡帶R的月份吃蠔,換言之,陽曆五至八月不宜食用。據說在不對的季節吃生蠔,小則鬧腸胃,大則會讓人痛不欲生。這種說法雖嫌誇大其詞,背後卻有其道理,因為五至八月正是牡蠣產卵季節,如果大夥在這時仍大啖生蠔,不就剝奪了牡蠣繁殖的機會,此一食蠔禁忌,其實反映了永續漁業的精神。
再者,生蠔本身自古來便被視為壯陽食品,這跟蠔肉的形狀長得像雄性器官應該有關,不過倘若換以科學角度來看,蠔肉含豐富的鋅,而男性要是缺鋅,精子數量就會不足,影響生殖功能,但不知先民是如何察覺這巧妙的連繫。
至於柿子,是我家秋季果盤上必備的水果,我從小愛吃柿子,可是礙於民間相傳的柿與蟹不可同食的禁忌,一直以為柿子是「不好的」水果,直到近幾年來對食材的天然療效產生興趣,翻閱中醫相關資料才發覺,原來柿子味甘性寒,可養肺、清燥火、補虛、止咳、利腸和除熱,特別適合在乾燥的季節食用。
原來老天爺自有其安排,從食補的角度來看,當令的農產往往是最適合那個季節攝取的食物。好比說,秋冬天乾地燥,芒果、漿果和西瓜等水果退場,取而代之的柿、梨、蘋果和柑橘類水果,不是有生津、潤肺之效,就是可以清熱降火、化痰止咳,正是秋冬餐桌上的聖品。
這一天買的柿子來自西班牙,我拿來搭配鄰國比利時的風乾火腿。這靈感來自南歐一帶的夏季開胃菜─甜瓜火腿,是有一年秋天在甜瓜下市後,靈機一動想出的主意。我改用與甜瓜色澤相似的柿子,除了取其色美之外,也想以柿之清脆甘甜,對比火腿之陳香鹹潤,結果頗受好評,從此成為我秋季宴客常做的小菜。
南瓜湯更用不著說,有什麼比這道滋味樸實悠長的湯品,更有歐洲秋日的顏色和味道呢?根據中醫觀點,南瓜有防燥之效,可平喘、消腫、預防哮喘和支氣管炎。前一陣子咳嗽得難過,煮了一大湯鍋南瓜湯,喝了兩三天,咳嗽果然好了,南瓜應該佔有一部分功勞吧。
當主菜的燉雞乍看與秋天無關,卻大有關聯。賦予整道菜特殊風味的橄欖,正是深秋的果子,在南歐產橄欖油的地區,看到青白色的橄欖色澤逐漸轉深,人們便明白一年快到盡頭,得趕緊採收橄欖來榨油,來年才有好油可食。橄欖雖是地中海一帶的農產,但也可應用於漢方醫療,有清熱解毒,化痰潤肺的功效。
收尾的紅酒梨更是秋冬絕妙甜品,梨對肺「好」不曉得算不算華人常識,記得小時天寒地凍時節,先母上粵菜館子吃飯,常愛點上一盅冰糖川貝燉梨,說是可以清心降火、生津潤燥,以致我如今一到秋季,只要呼吸器官稍有點不適,第一個念頭就是該燉梨子來吃了。
這一晚的餐桌上,在座四個人中有一位明年要滿六十了,即將走入人生中最圓融的冬季,其餘三位則仍在享受生命最成熟的秋季時分,初冬也好,深秋也罷,每個季節都各有各的美好,且讓大夥持叉舉杯,以美食佳釀與溫暖的友情,向季節、向人生致敬。(待續)我的記憶密碼
常覺得人的腦袋像密封的魔法寶盒,裡頭藏著無數的奇思幻想,有當下這一刻的念頭、對明日的憧憬和期待,還有對昨日的記憶,其中往事的回憶恐怕占了很大一部分,畢竟人的一生是以珍貴卻短暫的今天、未知的明天和許許多多的昨天所組成的。然而昨日一天天過去,久而久之,累積的往事多到數不清,有些往事塵封已久,記憶漸漸模糊,到頭來索性整個遺忘。
所幸,我們還有啟動記憶的「密碼」,輸入了密碼,密封的寶盒便打開了,幽渺的往事也就隨著慢慢恢復的記憶,一件件回到眼前。這個密碼往往不是一組數字,更可能是一首歌(聽覺)、一個畫面(視覺)或一種氣味(嗅覺),也有人的記憶密碼是一種味道,好比說,法國文豪普魯斯特。
說到味覺召喚往事的力量,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應是文學上最著名的例子。一口椴花茶和貝殼形瑪德蓮蛋糕,讓他冷不防想起童年往事,回憶如潮水般湧來,文豪逆著時間的洪流而上,爬梳過往的種種,寫成了這一部文學巨構。
我的才華當然不及文豪的千百分之一,和他唯一相通之處,或許只有味覺這個密碼吧。對我這個饞人而言,食物不單只是維持生命的事物與感官的享受,它更是喚起回憶的密碼,常讓我不期然憶及往昔時光,並感到生命因林林總總、或苦或甜的往事而更加充實。
最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食物,是一種六芒星形的甜餅,如今推算回去,吃到那餅時我才四、五歲。當時我們全家從新北投去台北市西門町逛街、上館子時,爸爸只要一看到那位臉孔黑黑的攤販立在騎樓下,便會買上好幾個,爸爸告訴我們,這餅叫做「金剛蹄」,是江蘇老家的特產,他在台灣其他地方都沒見過,恐怕就只有這位小販會做吧。(晚近,我上網搜尋,發現它的真名應該是「京江臍」,只是給爸爸的鄉音一唸,變成了金剛的蹄子,倒是呼應了上海人的叫法──「老虎腳爪」。)
金剛蹄(或京江臍、老虎腳爪)的外殼金黃略硬,內裡是發酵的白麵,帶股甜香,我第一次吃,覺得有點像媽媽拿來擦臉的「雪花膏」,聽爸爸解說才明白那其實是桂花香,來自糖漬桂花。爸爸買完餅,多半會跟那小販聊個一會兒,他們用家鄉話交談,我似懂非懂,只知爸爸捧著那一大包甜餅,帶著一家大小在前往餐館的路上,常會搖搖頭,不捨地對媽媽說:「這老鄉也可憐,糊里糊塗來台灣,沒手藝,就會做這個。」
年幼的我自然不能理解爸爸的言外之意,成年後,台灣的政治環境大不同於肅殺的戒嚴時代,我閱讀文史資料後方逐漸明白,那位與父親同鄉的攤販,應是退伍的國軍低階士兵,正是俗稱的「老芋仔」。他或許是在國共內戰時期被拉伕渡海來台,更說不定是農家子弟,大字不識幾個,除種地耕田外別的都不會,只好憑著昔日看母親烤餅的記憶,做出了家鄉味,賺點小錢維持生活。當時也剛從軍中退伍不久的爸爸經常關照他的生意,一方面是憐惜老鄉在台舉目無親,二方面或也是想重溫兒時滋味吧。
幼時的我有點偏食,一般不喜甜食,那桂花餅不很甜,我吃著香,是少數我會主動索求的點心。後來不知怎的,有好一陣子沒再吃到,有一回我吵著想吃,爸爸乾脆帶我專程到西門町,父女倆在小販原本固定出現的幾處騎樓找來找去,就是不見其人蹤影,爸爸不死心,跟附近商家打聽,都說好久沒見到,「該不會已經不在了」。記得當時我很失望,可是看到爸爸臉上凝重的表情,很乖覺地並未吵鬧。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嚐到金剛蹄,但是它那股濃濃的桂花香和淡淡的甜味,卻彷彿始終留在我的舌尖,以後我只要一嚐到糖漬桂花的味道,就會想起那些仍吃得到金剛蹄的時光,還有爸爸帶著我大街小巷尋找金剛蹄的那個下午。他的大手緊緊牽著我的小手,力量如此堅定,他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藉由溫暖的手心,把慈父的愛默默傳遞給年幼的小女兒,讓她感受到一種確切而深邃的安全感。
金剛蹄雖已成絕響,所幸還有記憶留存在寶盒中,只要味覺密碼稍加提示,盒蓋便應聲而開,中年的我便立刻回到那早已消逝的童年。(待續)給姊姊的信
良露:
收信平安!
接到來信時,正準備出門買菜,今天去的是鹿特丹市中心的有機超市。這家超市是個體經營,並非財團經營的連鎖企業,它不賣鮮魚生肉,除了乾糧雜貨,就只供應中小型農場生產的蔬果,價格雖不是最低,卻也不很貴,尤其每週都有的兩三樣促銷果菜,甚至比一般超市的慣行農法產品還便宜。它們可不是因為快枯萎凋縮了才賤賣,而全是當令的農作,由於盛產,數量一多,價錢就低了。好比這一週,我和約柏都愛吃的櫛瓜就特別划算,我一口氣買了一公斤。
買完菜回家的路上,想起四月待在台灣的最後一天,一大早在爸爸家附近的菜場,也居然看見有位歐巴桑在賣櫛瓜,那可是我頭一回在台北的傳統市場看到這種洋蔬菜,一問之下,不是進口貨,而是本土宜蘭的產品。
我當場買了一大袋,打算當天中午加點蒜末炒上兩條,我想我們那生性好奇的雙子座爸爸看到這陌生的蔬菜,一定會下箸嘗鮮,說不定還會喜歡。果然,他一個人就吃掉大半盤。爸爸吃得香,其實不是因為我的廚藝有多高明,燒出來的櫛瓜有多好吃,而只是這幾年每逢春秋二季回台北陪爸爸住上幾星期,差不多天天做飯或教阿莉燒菜給他吃,久而久之,也就越來越抓得住爸爸的胃口。
老實講,爸爸的口味不難拿捏,妳每星期都至少陪他吃飯一次,這一點應也早已明暸。簡單講,他愛吃的東西,質地須軟爛,千萬不可有嚼勁,味道亦宜濃重而不可清淡,記得我小時家裡餐桌鮮少出現茄子,這兩年爸爸卻以乎愛吃醬燒茄子了,我問他怎麼胃口變了,他輕輕嘆口氣說:「牙齒越來越糟,只要是軟的東西,我都吃了。」所以,那天的櫛瓜片我又炒又燜,非要它質地軟爛得幾乎入口即化才行,起鍋前還不忘嗆點酒,淋點蠔油,讓節瓜味道重一點,投其所好。
這兩年,我還學會一件事,可別買什麼養生粗食孝敬爸爸,那些他是不吃的。記得我有一回買了兩種素食全麥包子,心想這包子內餡全是天然蔬食,麵皮又富含纖維質,給爸爸當早餐吃,可比他平日一早起來的那一大杯特甜的牛奶咖啡加麥片健康多了。
第二天早上,我興沖沖地請阿莉蒸了甜、鹹各一只給他,他各嘗了一口,說沒味道就擱在一邊,我不信,嘗了一點,覺得不會呀,紅豆南瓜餡不很甜膩,香菇豆腐味噌餡也不會死鹹,帶點甘甜,挺好吃的。
「有味道呀,怎麼會沒味道?」我勸爸爸多吃兩口,「這是養生食品,對身體好,你老吃那些甜不拉嘰的東西,不行的。年紀大的人吃東西要注意!」
「妳年輕,吃著有味道,我老了,味覺退化了,吃來真的沒味道。」他又將盤子推開。
我一時無語,只覺得有點難過又有點內疚。我們的爸爸一輩子嘴饞,盛年時講究吃,為吃一擲千金在所不惜,這會兒年紀大了,身體機能大不如從前,就連「吃」這人生最大的樂趣也被剝奪了大半,他也只能臣服於歲月之下,向生命妥協,吃起那些從前嫌棄的東西,而我竟還振振有詞「教訓」老父,我真是太粗心又太自以為是了。孝順二字,我做的遠不如妳,我連「孝」都做得有形無體,更別說「順」了。所謂孝道,顯然仍是我邁入中年後亟需學習的人生課程。
歐洲的夏日天氣溫和,前一陣子早晚出門仍需披上薄外套。這兩天總算轉為炎熱,有點夏天的樣子,今天雲多,濕度稍高,我買完菜回家,下了公車走不過五、六分鐘路,竟微微出汗。這令我想起台北的春天,在六張犁買到櫛瓜的那天,似也正是這樣的天氣。
立秋了,再過一陣子秋天就要來臨,我也又要回台灣了,很期待。
良憶(待續)學舌記
前兩天有人問我,有沒有在異國生活分外痛苦的經驗。我呢,說好聽點是生性樂觀,說難聽點則是神經大條,一時竟想不出這些年以來有什麼特別不愉快的經歷,後來左思右想,終於記起來,移居低地國後的第一個冬天,真有過一段苦不堪言的時光,而那一切痛苦全是學荷蘭語造成的。
其實僑居荷蘭,就算你不會講荷語,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方面,也不會因語言不通而產生嚴重的問題,因為英語在這裡相當流通,全國有八成以上的人口英語尚稱流利,還有很多人也會講德語、法語。所以,只打算在荷蘭工作或就學三、四年的外國人,多半都覺得沒有學荷語的必要。
我卻是一搬來這裡,就認清現實,於私於公,我都沒有不學荷語的權利。
於私,我的另一半是土生土長的荷蘭人,英語雖然講得不錯,但他的親戚朋友未必人人都講得口好英語,而我總不能一輩子都仰仗約柏替我把荷蘭語翻譯成英語,真要那樣,他不累,我也會慚愧。
再者,我生來好奇,對不同的文化也一直有興趣。說到底,語言是文化的根基,不懂荷蘭的語言,卻想要深入觀察、進而領會荷蘭文化的幽微和精髓之處,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一早就明白,自己就算沒辦法學會講一口標準道地的荷語,也一定要加強聽力和閱讀,這樣才能豎直我的耳朵,「偷聽」街談巷議,睜大我的眼睛,觀看芸芸眾生,閱讀書報雜誌。
於公,由於我是以伴侶身分依親來荷,算是移民。按照荷蘭政府當時規定,為了讓移民及早融入荷蘭社會,新到移民必須上政府委託民間教育機構辦的荷語班,一般至少得上課六百個小時,課程結束後,並須通過語文測驗,學習期間,學費全免。(相關規定這幾年已有所改變,但大同小異,總之就是要鼓勵且敦促新移民學習荷語。)
這個免費課程用意良善,我後來卻沒上,而在移居鹿特丹的一個多月後,自費改上政府也認可的台夫特科技大學(TU Delft)語言班。這一來是因為政府免費課程通常得等上好幾個月才排到名額,我卻想儘早學習,儘快在語言上自立自強。二來是由於約柏就在這所大學擔任研究工作,對它的教學品質很有信心。
於是,我就報名參加台夫特的荷語密集班,開始學舌講荷語,殊不知,這正是我人生最拚命也最痛苦的學習生涯的開始,因為這個語言課程是有名的魔鬼訓練班,嚴格的不得了,而約柏跟我講了它的一大堆成功例證,唯獨沒提這一點,據他自稱是出自善意,怕我還沒上就氣餒了。
那年冬天,總共有兩個多月時間,我一禮拜有四天,天沒亮即出門上課(冬天早上八點多才東方大白),直到夜幕既將低垂才返抵家門,立刻開始K書,聽輔助錄音帶,直至三更半夜,就連不必上學的禮拜三和週末也不能偷懶,照樣得溫書、作功課,不然隔天準跟不上進度。
我的一切嗜好,散步也好,聽音樂或看書、看電影也好,統統都不得不割捨,連平日賴以暫時忘憂的烹飪之樂,常也得讓給約柏去享受(雖然他覺得那比較像是工作)。簡單的講,幾乎一整個冬天,我根本就沒有生活可言,世界只繞著學習荷語這件事轉。至於學舌過程中的難關和挫折,更是罄竹難書,日後有機會再談。
總之,算我運氣好,痛苦了兩個多月,終有了收穫,我在兩次進階考試中,都拿到接近滿分的好成績。發表分數時,我比當年大學聯考放榜考上第一志願還高興,苦盡甘來的滋味,畢竟不同凡響,而我在那段期間確實可比年少時準備聯考還拚。
所謂學海無涯,研習荷語的經歷讓我這句老掉牙的話格外有感觸,因為直到現在,我仍然在學舌,離精通荷語,雖然還有一大段距離,不過起碼這會兒,我搭火車時,聽得懂鄰座在八卦什麼,翻閱報刊時,只要多查兩次字典,便看得懂一篇篇的長篇大論,而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天談南北、講笑話時,也能會心一笑,而不光是呵呵跟著傻笑,卻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在笑啥。謝天謝地,那個冬天已成飄渺的回憶了。
這是件款式傳統保守的風衣,卡其色,雙排扣,後擺開叉;褐色方格的內裡襯布則讓熟悉品牌的人,一望即知它是倫敦的老牌子。
它原來不是我的衣服,雖然的確是我多年以前在香港買的。當年我還挺年輕,卻已有了穩定且收入不低的工作,因此也像當年許多愛趕時髦的台灣白領女性,老愛往香港跑,香港當時可是時尚之地呢。
有年冬天,趁著春節假期,又到香港。港島的氣候一般和台灣差不多,冬天不怎麼冷,可那一回偏巧碰上冷鋒過境,亞熱帶的香港竟然涼颼颼。抵埠那天傍晚,我從港島搭地鐵過海到九龍,一出地鐵站,就被風吹颳得直打哆嗦,身上那件羊毛薄外套根本不擋寒,乾脆拐進購物中心,逛街兼取暖。
就這樣瞎逛到精品店,一眼看見這件Aquascutum風衣,我知道母親一直想要一件英國老牌風衣,卻嫌貴,捨不得買。在那之前幾年,家裡經濟出了問題,母親頗吃了點苦,那會兒難關雖已過了,但她心有餘悸,對錢仍很小心。
我考慮了半晌,毅然花了近半個月的薪水,買下了這件風衣。記得當時安慰自己,不貴不貴,這風衣不但可以孝敬母親,我在香港這幾天還可以「借穿」一下,藉以抵擋來自西伯利亞的北風,疼惜女兒的母親想來不會介意的。
母親果然一點也不介意,而且很喜歡這件禮物。台灣難得天冷,但只要一有寒意,母親就會穿上,旁人倘若稱讚兩句,母親就會說:「是良憶買給我的。」
SARS那一年,母親因病猝逝。整理遺物時,姊姊說:「風衣是妳送給媽媽的,妳拿走吧。」我默默收下,沒有多說什麼。這風衣算來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卻保養得很好,像是簇新的,母親顯然很珍惜。
我帶著風衣回到荷蘭,碰到下雨又起風的日子,出門總愛披上。不知有多少個蕭颯的秋日,多虧了這件風衣替我擋風遮雨,給了我一點溫暖,可是每逢這時,我卻又總是希望,那一刻穿著這風衣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母親。(待續)二姊
我的二姊良雯,我們都叫她阿雯。
她喜歡港式茶樓的廣州炒麵、台北遠企地下樓的生菜沙拉、麥當勞的冰咖啡和薯條;喜歡聽鄧麗君唱的〈虹彩妹妹〉;喜歡跟人聊天,問人家的爸爸或媽媽在那裡;喜歡玩大門的鎖鏈;最喜歡去「心路社區家園」上學。
她因為出生時腦部缺氧,有極重度智能障礙,台灣人稱之為「憨兒」,用美式英語的講法,則是「心智受挑戰者」(mentally challenged)。
我每個週末都從荷蘭打電話回家,向爸爸問好,並和從頭到尾拿著另一支分機傾聽對話的阿雯,談上兩句。姊妹間的對話常常是這樣的:
「阿雯,妳有沒有乖?」
「有。」
「有沒有吵把拔(爸爸)?」
「沒有。」(這時我爸會在分機上插嘴說:「阿雯現在好乖,都不吵。」)
「有沒有去麥當勞?」
「還沒有。」
「哦,那去的時候,不要吃太多薯條喔,太胖了會得高血壓。」然後,我常常就想不出來要講什麼,只好說:「阿雯,還有沒有事要對良憶妹妹說?」
電話那頭遲疑了一秒鐘,我可以想像一頭削薄短髮的阿雯,嘴巴正微微一開一閤,似在考慮下頭要聊些什麼。緊接著,一般有兩種版本。
第一版本:
「良憶美沒(妹妹),約柏呢?」約柏是我的丈夫,荷蘭人,基本上不會講中文。
「約柏在忙。」
「忙什麼?」
「忙打電腦(或整理照片、看報紙…等等)。」
「約柏馬麻(媽媽)呢?」
「在她家。」
「阿雯跟約柏講話。」
「好,等一下。」我這方於是換人。
阿雯在那一頭說:「哈嘍,約柏,鼓摸你。」
約柏回答:「Good morning,A-Wen。」
阿雯咯咯笑了。「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接著下來,只聽見阿雯大聲講:「三Q,拜拜。」然後又是一陣吃吃笑。
第二版本:
「良憶妹妹,荷蘭幾度?」
「xx度。」我會隨便講個數字。
「冷不冷?」
「不大冷。」
「有沒有下雨?」
「沒有。」
「好,」阿雯說,「拜拜。」
朋友聽說阿雯的情況,總愛問我她的心智年齡有多少,我的標準答案是多年前醫生講的,「三、四歲吧」。可是,三、四歲的孩子會跟她一樣,數數兒只能數到八或九,老是分不清楚三角形、四方形,然而接到我高中老同學的電話,不必問人家,光聽聲音,就能清楚地喊出對方的名字嗎?
三、四歲的孩子又會不會在我們的母親過世後,偶爾自問自答,說:「阿雯馬麻呢?」然後根據阿姨給她的答案,答稱:「上天堂去耶穌那裡了。」繼而嚎啕大哭,嚷道:「馬麻死了。」非得等旁邊的人再三保證,媽媽被上帝接走了,才會揉揉紅紅的眼睛,破渧為笑。
我也始終不明白,阿雯為什麼在沒有見到金髮藍眼的約柏以前,就曉得要跟他講 “How are you”,而不是「你好嗎」,三、四歲的孩子是這樣的嗎?
去年春節和中秋節,我兩度回台北探望老父和家人。阿雯週末從她住讀的「心路」回家,看到我,總是一下子迸出了笑顏,伸手摸摸我的臉,好像想確認她的妹妹果真又回到眼前。摸完,叫了聲「良憶美沒」,她盤腿坐在沙發上,上半身開始左右慢慢搖晃,嘴裡偶爾發出輕微的「喀喀」聲。阿雯只要覺得高興,就會這樣搖啊晃的,很自得其樂。
我常常在想,藏在這樣一副逐漸邁入中年,終將垂垂老矣的軀體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靈魂?是個比孩童還純真清澈的靈魂?還是個歷經多次輪迴,已閱盡滄桑哀樂,索性轉目不觀人世的老靈魂?
每個生命,都是個謎,而阿雯的生命,尤其是個謎。(待續)持叉舉杯,向人生致敬
從還有點悶熱的亞熱帶島嶼飛回秋涼的北溫帶低地國,算天公賞臉,陽光溫熙,正適合到公園散步,對抗時差。草地上一片落葉,還掛在樹梢的黃葉和紅葉被午間的陽光照得一樹金燦,秋意真的濃了。我隨手拾起一片金黃夾紽紅的落葉,放進羊毛外套口袋裡。秋天雖好,總嫌短暫,留下一片黃葉,算是見證自己有過一個絢麗璀璨的秋季。
果然,隔不了幾天,荷蘭吹起晚秋常見的暴風,樹木剎時禿了頭,寒風颼颼,彷彿刺入骨髓,我把輕薄的棉衣統統收進五斗櫃,風衣送洗,取出羽絨衣和喀什米爾羊毛圍巾,掛在玄關,每回出外以前總要把自己全身包裹得暖呼呼的,才敢踏出家門。
節氣剛過「小雪」後不久,鹿特丹飄起今年第一場雪,我戴上氈帽,在鹽粒般的細雪中,搭電車到市區,有兩位朋友晚上要來家裡吃飯,九月底初感秋涼時,我們一起在普羅旺斯度假,說好回荷後要約個時間交換照片看,轉眼秋已經深了。
天氣一冷,就想吃點熱騰騰的東西,我打算上中國城的肉店買火鍋肉片,做日式壽喜燒或中式涮鍋,給兩位荷蘭朋友嚐點東方味。興沖沖地進店裡,一問,肉片居然「賣哂」(粵語賣完了之意),難不成今晚鹿城有一半華人都要打邊爐?看來火鍋是做不成了,三位大男人都是肉食主義者,沒肉,可就怠慢了客人。
好吧,只好改弦易張,回頭做洋食,做什麼呢?原本一心想吃鍋物,菜單都盤算好了,這會兒一下子沒了主張,轉往有機小超市一看,菜架上儘是包心菜、大蘿蔔、胡蘿蔔、韭蔥、苦苣、抱子甘藍等較耐寒的蔬菜,還有馬鈴薯、南瓜與各種蕈菇,夏季時盛產的菠菜、生菜萵苣、彩椒和茄子等,不但數量上少了許多,價格也貴,想是溫室產品。水果攤上呢,不同品種的蘋果、梨和柳橙、蜜柑堆積如小山,難得還有西班牙來的脆柿,金的紅的,喜氣洋洋。
在店裡繞了一圈,繽紛的色彩看得人心情飛揚,靈感也來了,決定了,就準備四道菜:生蠔、柿子佐義大利風乾火腿、南瓜湯、白酒燉橄欖雞,甜點煮個紅酒梨好了。這一頓晚餐的材料有海裡採來的(生蠔),地裡種的(柿子、南瓜、橄欖和梨子),山上熟成的(火腿)、農場裡養的(有機放養雞),算得上「山珍海味」,而且是很適合秋季食用的養生晚餐。
不加任何中藥材,如何說是「養生」餐?可話說回來,誰規定養生一定得靠藥材?
先說生蠔吧。生蠔雖生雖涼,卻是秋冬滋補聖品。西方人傳統上講究只在英文拼音裡帶R的月份吃蠔,換言之,陽曆五至八月不宜食用。據說在不對的季節吃生蠔,小則鬧腸胃,大則會讓人痛不欲生。這種說法雖嫌誇大其詞,背後卻有其道理,因為五至八月正是牡蠣產卵季節,如果大夥在這時仍大啖生蠔,不就剝奪了牡蠣繁殖的機會,此一食蠔禁忌,其實反映了永續漁業的精神。
再者,生蠔本身自古來便被視為壯陽食品,這跟蠔肉的形狀長得像雄性器官應該有關,不過倘若換以科學角度來看,蠔肉含豐富的鋅,而男性要是缺鋅,精子數量就會不足,影響生殖功能,但不知先民是如何察覺這巧妙的連繫。
至於柿子,是我家秋季果盤上必備的水果,我從小愛吃柿子,可是礙於民間相傳的柿與蟹不可同食的禁忌,一直以為柿子是「不好的」水果,直到近幾年來對食材的天然療效產生興趣,翻閱中醫相關資料才發覺,原來柿子味甘性寒,可養肺、清燥火、補虛、止咳、利腸和除熱,特別適合在乾燥的季節食用。
原來老天爺自有其安排,從食補的角度來看,當令的農產往往是最適合那個季節攝取的食物。好比說,秋冬天乾地燥,芒果、漿果和西瓜等水果退場,取而代之的柿、梨、蘋果和柑橘類水果,不是有生津、潤肺之效,就是可以清熱降火、化痰止咳,正是秋冬餐桌上的聖品。
這一天買的柿子來自西班牙,我拿來搭配鄰國比利時的風乾火腿。這靈感來自南歐一帶的夏季開胃菜─甜瓜火腿,是有一年秋天在甜瓜下市後,靈機一動想出的主意。我改用與甜瓜色澤相似的柿子,除了取其色美之外,也想以柿之清脆甘甜,對比火腿之陳香鹹潤,結果頗受好評,從此成為我秋季宴客常做的小菜。
南瓜湯更用不著說,有什麼比這道滋味樸實悠長的湯品,更有歐洲秋日的顏色和味道呢?根據中醫觀點,南瓜有防燥之效,可平喘、消腫、預防哮喘和支氣管炎。前一陣子咳嗽得難過,煮了一大湯鍋南瓜湯,喝了兩三天,咳嗽果然好了,南瓜應該佔有一部分功勞吧。
當主菜的燉雞乍看與秋天無關,卻大有關聯。賦予整道菜特殊風味的橄欖,正是深秋的果子,在南歐產橄欖油的地區,看到青白色的橄欖色澤逐漸轉深,人們便明白一年快到盡頭,得趕緊採收橄欖來榨油,來年才有好油可食。橄欖雖是地中海一帶的農產,但也可應用於漢方醫療,有清熱解毒,化痰潤肺的功效。
收尾的紅酒梨更是秋冬絕妙甜品,梨對肺「好」不曉得算不算華人常識,記得小時天寒地凍時節,先母上粵菜館子吃飯,常愛點上一盅冰糖川貝燉梨,說是可以清心降火、生津潤燥,以致我如今一到秋季,只要呼吸器官稍有點不適,第一個念頭就是該燉梨子來吃了。
這一晚的餐桌上,在座四個人中有一位明年要滿六十了,即將走入人生中最圓融的冬季,其餘三位則仍在享受生命最成熟的秋季時分,初冬也好,深秋也罷,每個季節都各有各的美好,且讓大夥持叉舉杯,以美食佳釀與溫暖的友情,向季節、向人生致敬。(待續)我的記憶密碼
常覺得人的腦袋像密封的魔法寶盒,裡頭藏著無數的奇思幻想,有當下這一刻的念頭、對明日的憧憬和期待,還有對昨日的記憶,其中往事的回憶恐怕占了很大一部分,畢竟人的一生是以珍貴卻短暫的今天、未知的明天和許許多多的昨天所組成的。然而昨日一天天過去,久而久之,累積的往事多到數不清,有些往事塵封已久,記憶漸漸模糊,到頭來索性整個遺忘。
所幸,我們還有啟動記憶的「密碼」,輸入了密碼,密封的寶盒便打開了,幽渺的往事也就隨著慢慢恢復的記憶,一件件回到眼前。這個密碼往往不是一組數字,更可能是一首歌(聽覺)、一個畫面(視覺)或一種氣味(嗅覺),也有人的記憶密碼是一種味道,好比說,法國文豪普魯斯特。
說到味覺召喚往事的力量,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應是文學上最著名的例子。一口椴花茶和貝殼形瑪德蓮蛋糕,讓他冷不防想起童年往事,回憶如潮水般湧來,文豪逆著時間的洪流而上,爬梳過往的種種,寫成了這一部文學巨構。
我的才華當然不及文豪的千百分之一,和他唯一相通之處,或許只有味覺這個密碼吧。對我這個饞人而言,食物不單只是維持生命的事物與感官的享受,它更是喚起回憶的密碼,常讓我不期然憶及往昔時光,並感到生命因林林總總、或苦或甜的往事而更加充實。
最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食物,是一種六芒星形的甜餅,如今推算回去,吃到那餅時我才四、五歲。當時我們全家從新北投去台北市西門町逛街、上館子時,爸爸只要一看到那位臉孔黑黑的攤販立在騎樓下,便會買上好幾個,爸爸告訴我們,這餅叫做「金剛蹄」,是江蘇老家的特產,他在台灣其他地方都沒見過,恐怕就只有這位小販會做吧。(晚近,我上網搜尋,發現它的真名應該是「京江臍」,只是給爸爸的鄉音一唸,變成了金剛的蹄子,倒是呼應了上海人的叫法──「老虎腳爪」。)
金剛蹄(或京江臍、老虎腳爪)的外殼金黃略硬,內裡是發酵的白麵,帶股甜香,我第一次吃,覺得有點像媽媽拿來擦臉的「雪花膏」,聽爸爸解說才明白那其實是桂花香,來自糖漬桂花。爸爸買完餅,多半會跟那小販聊個一會兒,他們用家鄉話交談,我似懂非懂,只知爸爸捧著那一大包甜餅,帶著一家大小在前往餐館的路上,常會搖搖頭,不捨地對媽媽說:「這老鄉也可憐,糊里糊塗來台灣,沒手藝,就會做這個。」
年幼的我自然不能理解爸爸的言外之意,成年後,台灣的政治環境大不同於肅殺的戒嚴時代,我閱讀文史資料後方逐漸明白,那位與父親同鄉的攤販,應是退伍的國軍低階士兵,正是俗稱的「老芋仔」。他或許是在國共內戰時期被拉伕渡海來台,更說不定是農家子弟,大字不識幾個,除種地耕田外別的都不會,只好憑著昔日看母親烤餅的記憶,做出了家鄉味,賺點小錢維持生活。當時也剛從軍中退伍不久的爸爸經常關照他的生意,一方面是憐惜老鄉在台舉目無親,二方面或也是想重溫兒時滋味吧。
幼時的我有點偏食,一般不喜甜食,那桂花餅不很甜,我吃著香,是少數我會主動索求的點心。後來不知怎的,有好一陣子沒再吃到,有一回我吵著想吃,爸爸乾脆帶我專程到西門町,父女倆在小販原本固定出現的幾處騎樓找來找去,就是不見其人蹤影,爸爸不死心,跟附近商家打聽,都說好久沒見到,「該不會已經不在了」。記得當時我很失望,可是看到爸爸臉上凝重的表情,很乖覺地並未吵鬧。
從此以後,我再也沒嚐到金剛蹄,但是它那股濃濃的桂花香和淡淡的甜味,卻彷彿始終留在我的舌尖,以後我只要一嚐到糖漬桂花的味道,就會想起那些仍吃得到金剛蹄的時光,還有爸爸帶著我大街小巷尋找金剛蹄的那個下午。他的大手緊緊牽著我的小手,力量如此堅定,他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藉由溫暖的手心,把慈父的愛默默傳遞給年幼的小女兒,讓她感受到一種確切而深邃的安全感。
金剛蹄雖已成絕響,所幸還有記憶留存在寶盒中,只要味覺密碼稍加提示,盒蓋便應聲而開,中年的我便立刻回到那早已消逝的童年。(待續)給姊姊的信
良露:
收信平安!
接到來信時,正準備出門買菜,今天去的是鹿特丹市中心的有機超市。這家超市是個體經營,並非財團經營的連鎖企業,它不賣鮮魚生肉,除了乾糧雜貨,就只供應中小型農場生產的蔬果,價格雖不是最低,卻也不很貴,尤其每週都有的兩三樣促銷果菜,甚至比一般超市的慣行農法產品還便宜。它們可不是因為快枯萎凋縮了才賤賣,而全是當令的農作,由於盛產,數量一多,價錢就低了。好比這一週,我和約柏都愛吃的櫛瓜就特別划算,我一口氣買了一公斤。
買完菜回家的路上,想起四月待在台灣的最後一天,一大早在爸爸家附近的菜場,也居然看見有位歐巴桑在賣櫛瓜,那可是我頭一回在台北的傳統市場看到這種洋蔬菜,一問之下,不是進口貨,而是本土宜蘭的產品。
我當場買了一大袋,打算當天中午加點蒜末炒上兩條,我想我們那生性好奇的雙子座爸爸看到這陌生的蔬菜,一定會下箸嘗鮮,說不定還會喜歡。果然,他一個人就吃掉大半盤。爸爸吃得香,其實不是因為我的廚藝有多高明,燒出來的櫛瓜有多好吃,而只是這幾年每逢春秋二季回台北陪爸爸住上幾星期,差不多天天做飯或教阿莉燒菜給他吃,久而久之,也就越來越抓得住爸爸的胃口。
老實講,爸爸的口味不難拿捏,妳每星期都至少陪他吃飯一次,這一點應也早已明暸。簡單講,他愛吃的東西,質地須軟爛,千萬不可有嚼勁,味道亦宜濃重而不可清淡,記得我小時家裡餐桌鮮少出現茄子,這兩年爸爸卻以乎愛吃醬燒茄子了,我問他怎麼胃口變了,他輕輕嘆口氣說:「牙齒越來越糟,只要是軟的東西,我都吃了。」所以,那天的櫛瓜片我又炒又燜,非要它質地軟爛得幾乎入口即化才行,起鍋前還不忘嗆點酒,淋點蠔油,讓節瓜味道重一點,投其所好。
這兩年,我還學會一件事,可別買什麼養生粗食孝敬爸爸,那些他是不吃的。記得我有一回買了兩種素食全麥包子,心想這包子內餡全是天然蔬食,麵皮又富含纖維質,給爸爸當早餐吃,可比他平日一早起來的那一大杯特甜的牛奶咖啡加麥片健康多了。
第二天早上,我興沖沖地請阿莉蒸了甜、鹹各一只給他,他各嘗了一口,說沒味道就擱在一邊,我不信,嘗了一點,覺得不會呀,紅豆南瓜餡不很甜膩,香菇豆腐味噌餡也不會死鹹,帶點甘甜,挺好吃的。
「有味道呀,怎麼會沒味道?」我勸爸爸多吃兩口,「這是養生食品,對身體好,你老吃那些甜不拉嘰的東西,不行的。年紀大的人吃東西要注意!」
「妳年輕,吃著有味道,我老了,味覺退化了,吃來真的沒味道。」他又將盤子推開。
我一時無語,只覺得有點難過又有點內疚。我們的爸爸一輩子嘴饞,盛年時講究吃,為吃一擲千金在所不惜,這會兒年紀大了,身體機能大不如從前,就連「吃」這人生最大的樂趣也被剝奪了大半,他也只能臣服於歲月之下,向生命妥協,吃起那些從前嫌棄的東西,而我竟還振振有詞「教訓」老父,我真是太粗心又太自以為是了。孝順二字,我做的遠不如妳,我連「孝」都做得有形無體,更別說「順」了。所謂孝道,顯然仍是我邁入中年後亟需學習的人生課程。
歐洲的夏日天氣溫和,前一陣子早晚出門仍需披上薄外套。這兩天總算轉為炎熱,有點夏天的樣子,今天雲多,濕度稍高,我買完菜回家,下了公車走不過五、六分鐘路,竟微微出汗。這令我想起台北的春天,在六張犁買到櫛瓜的那天,似也正是這樣的天氣。
立秋了,再過一陣子秋天就要來臨,我也又要回台灣了,很期待。
良憶(待續)學舌記
前兩天有人問我,有沒有在異國生活分外痛苦的經驗。我呢,說好聽點是生性樂觀,說難聽點則是神經大條,一時竟想不出這些年以來有什麼特別不愉快的經歷,後來左思右想,終於記起來,移居低地國後的第一個冬天,真有過一段苦不堪言的時光,而那一切痛苦全是學荷蘭語造成的。
其實僑居荷蘭,就算你不會講荷語,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方面,也不會因語言不通而產生嚴重的問題,因為英語在這裡相當流通,全國有八成以上的人口英語尚稱流利,還有很多人也會講德語、法語。所以,只打算在荷蘭工作或就學三、四年的外國人,多半都覺得沒有學荷語的必要。
我卻是一搬來這裡,就認清現實,於私於公,我都沒有不學荷語的權利。
於私,我的另一半是土生土長的荷蘭人,英語雖然講得不錯,但他的親戚朋友未必人人都講得口好英語,而我總不能一輩子都仰仗約柏替我把荷蘭語翻譯成英語,真要那樣,他不累,我也會慚愧。
再者,我生來好奇,對不同的文化也一直有興趣。說到底,語言是文化的根基,不懂荷蘭的語言,卻想要深入觀察、進而領會荷蘭文化的幽微和精髓之處,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一早就明白,自己就算沒辦法學會講一口標準道地的荷語,也一定要加強聽力和閱讀,這樣才能豎直我的耳朵,「偷聽」街談巷議,睜大我的眼睛,觀看芸芸眾生,閱讀書報雜誌。
於公,由於我是以伴侶身分依親來荷,算是移民。按照荷蘭政府當時規定,為了讓移民及早融入荷蘭社會,新到移民必須上政府委託民間教育機構辦的荷語班,一般至少得上課六百個小時,課程結束後,並須通過語文測驗,學習期間,學費全免。(相關規定這幾年已有所改變,但大同小異,總之就是要鼓勵且敦促新移民學習荷語。)
這個免費課程用意良善,我後來卻沒上,而在移居鹿特丹的一個多月後,自費改上政府也認可的台夫特科技大學(TU Delft)語言班。這一來是因為政府免費課程通常得等上好幾個月才排到名額,我卻想儘早學習,儘快在語言上自立自強。二來是由於約柏就在這所大學擔任研究工作,對它的教學品質很有信心。
於是,我就報名參加台夫特的荷語密集班,開始學舌講荷語,殊不知,這正是我人生最拚命也最痛苦的學習生涯的開始,因為這個語言課程是有名的魔鬼訓練班,嚴格的不得了,而約柏跟我講了它的一大堆成功例證,唯獨沒提這一點,據他自稱是出自善意,怕我還沒上就氣餒了。
那年冬天,總共有兩個多月時間,我一禮拜有四天,天沒亮即出門上課(冬天早上八點多才東方大白),直到夜幕既將低垂才返抵家門,立刻開始K書,聽輔助錄音帶,直至三更半夜,就連不必上學的禮拜三和週末也不能偷懶,照樣得溫書、作功課,不然隔天準跟不上進度。
我的一切嗜好,散步也好,聽音樂或看書、看電影也好,統統都不得不割捨,連平日賴以暫時忘憂的烹飪之樂,常也得讓給約柏去享受(雖然他覺得那比較像是工作)。簡單的講,幾乎一整個冬天,我根本就沒有生活可言,世界只繞著學習荷語這件事轉。至於學舌過程中的難關和挫折,更是罄竹難書,日後有機會再談。
總之,算我運氣好,痛苦了兩個多月,終有了收穫,我在兩次進階考試中,都拿到接近滿分的好成績。發表分數時,我比當年大學聯考放榜考上第一志願還高興,苦盡甘來的滋味,畢竟不同凡響,而我在那段期間確實可比年少時準備聯考還拚。
所謂學海無涯,研習荷語的經歷讓我這句老掉牙的話格外有感觸,因為直到現在,我仍然在學舌,離精通荷語,雖然還有一大段距離,不過起碼這會兒,我搭火車時,聽得懂鄰座在八卦什麼,翻閱報刊時,只要多查兩次字典,便看得懂一篇篇的長篇大論,而親朋好友聚在一起天談南北、講笑話時,也能會心一笑,而不光是呵呵跟著傻笑,卻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在笑啥。謝天謝地,那個冬天已成飄渺的回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