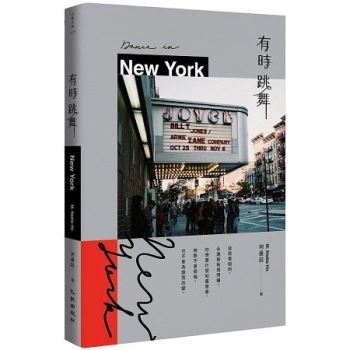男舞者教我的事
舞蹈教室是一個女多男少的世界,然而舞團總監卻經常都是男的。
先不管舞蹈總監界的性別比例,在紐約的芭蕾世界裡,有一個男人的名字是鑽石級閃耀、無法動搖的,那就是喬治‧巴蘭欽(1904-1983)。
巴蘭欽出生在聖彼得堡藝術世家,是他的父親是聲樂家兼作曲家,當過喬治亞(當時是沙皇屬國,後來獨立一下又加入了蘇聯)的文化部長,家族成員不是軍人,就是藝術家──蘇聯的藝術家也是軍人。大師一生到底編過多少支作品呢?粗略估計約在四百部左右,可能有些人不情願,但這個俄國人確實重新定義了美國芭蕾,他創辦美國芭蕾學校(American Ballet School)、長期培訓舞者,開創出一套適合美國舞者、充滿力量與速度的「巴蘭欽技巧」。
巴蘭欽生在今天的話一定會變網紅,因為他不但是花美男,而且名言很多:例如「舞者是花,花本來就美,而不是因為花有甚麼了不起的故事要表達」;他還說「舞者只是樂器,應該把編舞家的音樂給演奏出來」,他引用喬治亞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話自稱「我不是人,只是一朵穿褲子的雲。」說明了他有多自戀。他以軍人般的鐵血紀律要求自我,也嚴格要求他的舞者;「你是在對自己客氣甚麼?你幹嘛退縮?你現在保留實力---下次用?沒有下次了,只有現在,現、在。」他連自己的貓都抓來訓練,他的貓Mourka出過自傳,能正確的做出大跳跟擊腿。
穿褲子的雲還致力於跟美麗舞者結婚,而且要最優秀的舞者,他一生結婚五次(其中一次無法律效用),每一任妻子都是舞台上的超級巨星, 他最後一任妻子是女神級的芭蕾舞者Tanaquil Le Clercq (暱稱泰妮),一九五六年,小兒麻痺疫苗才剛發明兩年,沒有接種過疫苗的泰妮,在北歐巡演的途中發病,隨即被送進當時的治療器材『鐵肺』這種很像太空艙、沉重冰冷的密閉金屬體,以幫浦抽吸空氣,幫助肌肉萎縮的病人被動呼吸。當時泰妮二十七歲,她人生最後一場表演跳的是「天鵝湖」。在小兒麻痺還會致死的年代,她保住了性命,但進食等生活起居都需要護士幫忙,她漸漸接受了事實:她不但不能跳舞,連走路都不可能了。這場疾病據說讓巴蘭欽的心又回到妻子身邊,也他因此開始思考新的舞蹈方法,並認識了彼拉提斯先生(Pilates瑜珈發明人)本人,編出了Agon這支雙人舞裡面,女舞者本身並不動作,由男舞者把她的身體「擺成」不同的姿勢與位置,被認為是巴蘭欽面對肌肉萎縮的妻子想做的嘗試,雖然過程非常艱難,但泰妮後來成為一名坐輪椅的舞蹈老師,她用手跟上半身教舞。巴蘭欽在照顧妻子九年之後,為了另一位美麗舞者Suzanne Farrell 而提出離婚。
每年到了十一月初,日光節約時間一結束,一夕之間紐約的白天就短得令人沮喪,宣告漫長的冬天要開始了,全市開始掛燈結彩、室內的暖氣、櫥窗上的霧氣、低沉溫柔的爵士樂,都在努力溫暖路人的心。為了準備過年,美國各地芭蕾舞團也開始把《胡桃鉗》拿出來排練,巴蘭欽版的胡桃鉗,為美國人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節慶文化,從一九五五年推出新版以來每年都上演。
二○一五年的胡桃鉗照常有好多小朋友觀眾,節目單的第一頁是寫給小觀眾的觀賞須知,除了戲院禮節之外,還教他們如何欣賞舞蹈:記下自己喜歡的服裝、喜歡的角色,或者看看交響樂團裡面你最喜歡的樂器。節目進入下半場,巧克力仙子、茶仙子、咖啡仙子一一出場,坐我旁邊的小女孩躍躍欲試,壓軸的糖梅仙子終於降臨,穿著粉紅色的大紗裙,連續不停地做出完美的旋轉,小女孩忍不住跟著音樂扭起來了!
每一場芭蕾舞的觀眾席裡,都會有幾個這樣坐不住的小孩,也許未來的芭蕾舞巨星就在其中──然而一百位從小立志要跳公主仙子主角的女孩,有九十九個大概跳不到,但光是能在舞團裡得到一個位置,得耗上十幾年學習,外加無重大傷病的運氣:反過來說,若你是萬中選一的優秀舞者,跳王子公主的角色對你來說還可能不夠有趣,你會想跳壞蛋角色,你會想當黑天鵝、當魔王、或是當一隻巨大而活躍的老鼠。
萬物也許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就是令人生理上無法接受,老鼠的賣相真的很差,牠的顏色、牠的體型、牠發出的吱吱與喳喳、牠鬼祟的行為以及身上夾帶的十一種常見疾病,都讓人不敢直視。但你知道嗎?老鼠其實眼睛看不見,他們在城市黑暗的地底,靠著感覺行走,是天生的盲舞者。這世界上有屬於老鼠的浪漫嗎?有的。《胡桃鉗》的原著原題就叫做《胡桃鉗與老鼠王》,是德國浪漫主義劇作家E•T•A霍夫曼的作品。在這個聖誕夜故事裡,老鼠是重要的反派群,當午夜的鐘聲一響,老鼠就從那放滿聖誕禮物結滿彩燈的樹下一隻隻地鑽進瑪莉小妹妹一家人溫暖的屋裡,我這個人從小看童話故事都會偏心反派,可能是因為他們都比主角有個性、有風格吧,而在《胡桃鉗》裡面,老鼠王真的超有風格,牠有七個頭——當然包含了七張老鼠臉了。同情反派是浪漫者的特質之一,霍夫曼的原著裡,老鼠王也有牠自己的辛酸,人類的小孩放置捕鼠器殺死了老鼠王的孩子,悲憤的老鼠王率領鼠軍誓死一戰,而下巴掉了的胡桃鉗將軍,被瑪莉小妹修好之後為了報恩,帶領胡桃鉗大軍擊退鼠軍,人類獲勝,得到聖誕夜的安寧與平靜,但老鼠王卻是家破人亡,仔細一想,這個故事根本就不溫馨。老鼠的形象在卡通普及後,變得可愛許多。在一張波士頓芭蕾舞團彩排的舊照中,老鼠王正在糾正部下的老鼠芭蕾,我這才發現,原來各地的老鼠芭蕾也有不同的風格:波士頓鼠王鼠兵毫無殺氣,上下身一比一,毛皮蓬鬆,穿著遊樂園吉祥物的連身服,加上露兩齒的呆萌喜感,很適合放在Hello Kitty旁邊;舊金山芭蕾的鼠王特色,是尖嘴裡一整排衝到下巴的尖牙,指甲也銳利如刀,是標準的壞溝鼠扮相;紐約市立芭蕾的鼠王與老鼠就跟地鐵老鼠一樣,在城市日夜堆積的惡性油紙餵養下,下盤肥大,但四肢細長——如此方便逃跑——,鼠兵們一跳躍,灰色的屁股就上下左右咚咚咚地擺盪;再看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鼠王造型,灰階多層次的襤褸服飾,有一種狄更斯式悲慘遇上Alexander McQueen的暗黑華麗,想當年童工被虐棲身於下水道時,身邊也只有嚇人的老鼠竄流:以上種種顯示,英美工業發展過程中,都會居民內心累積了不少對抗老鼠的創傷,那麼特產是戰鬥民族與芭蕾巨星的俄羅斯又是如何呢?莫斯科芭蕾的鼠王挽救了浪漫之名,牠玉樹臨風、黑衣倜儻、腳尖筆直、迴旋跳躍無懈可擊,能跳鼠王的舞者必須技巧高超、經驗豐富,因為這個角色必須穿著那麼重的道具服展現輕盈,而更困難的是,當他帶著鼠頭跳舞時,頭套幾乎完全阻擋了視線,他的視野比戴上眼罩的賽馬更加狹窄,看不見地板、也看不見旁邊的舞者、甚至看不見觀眾席,只能看著觀眾席後方一個小紅點確定方位。
搬離曼哈頓之後,因為路遠,我越來越少去林肯中心,除了實際距離的影響,我與大師經典的心理距離也越來越遠;我清楚記得最後一次看巴蘭欽作品《黑與白》那天,走出劇院,心想「巴蘭欽這個沙文主義者真無聊」──巴蘭欽沒有變,是我變了,巴蘭欽六十年前新創的風格,放到現在也變得老土。
巴蘭欽制霸林肯中心數十年,在這段期間,有一位同為俄羅斯天才男舞者也曾經空降林肯中心,那人在舞蹈界外的觀眾眼中,是欲望城市裡那個「演過凱莉前男友的藝術家」,而在舞蹈世界裡,他是演、視、歌、舞,永遠追求突破、無與倫比的 "Misha"先生──巴瑞辛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巴瑞辛尼可夫在一九七四年加拿大巡演中脫隊,要求政治庇護,之後歸化美國,關於他的動機有許多說法:民主浪漫人士說他衝破鐵幕投奔民主,自由派藝術人士說他厭倦蘇聯僵化的創作體制,還有人說他被情治單位盯上了, 這個疑問當時可能很難解,然而四十年後回看他到紐約後豐沛的創作與成就,誰還需要問他為何要跳機呢?以紐約為中心的創作生命自由奔放、充滿可能性,連他「投奔自由」這件事本身,都在隔年馬上拍成了一部跳舞電影,《白夜》(White Nights, 1985),這可能是愛國電影中最帥的一部了,如今蘇聯也早已解體,記憶中只剩跳舞,尤其是那段著名的「十一圈」打賭。
「十一圈」是這樣開始的:無論在電梯裡、小屋裡,或是一間有窗的芭蕾教室裡,幾個人被圍困到最後,大概都會開始賭博,一名俄國芭蕾舞星(巴瑞辛尼可夫)跟一名美國踢躂舞者(Gregory Hines)被關在一起能賭什麼呢?Pirouettes ——轉圈圈——,賺一圈贏一盧布,連轉七圈,七盧布。
「等等,要是你輸了我得到什麼呢?你又沒錢。」踢躂舞者問。
「我的手錶嘍。」俄國舞者說。
「哦,不,我要這個。」踢躂舞者用下巴指了一下那台手提音響。
對圍困中的舞者來,輸掉手提音響是多麼嚴重的事情!這時踢躂舞者又挖著口袋說:「等等,我還有,你看……十一盧布,十一圈。」
巴瑞辛尼可夫(脫外套!)說:「你來得及數嗎?」(一秒如風般早就超過十一圈)。
巴瑞辛尼可夫現在依然住在紐約,跳舞早就已經無法滿足他,他喜歡演戲,喜歡挑戰怪異的角色,而且不怕展現自己的年邁蒼老的模樣,以他為名的表演藝術中心(Baryshnikov Arts Center,BAC),提供表演場地及駐村機會給跨界表演作品。
無論是忠實觀眾,或是芭蕾群英,來到林肯中心是為了一睹經典風采,但若要在藝術的路是繼續前進,恐怕還是得離開林肯中心。巴瑞辛尼可夫離開美國芭蕾劇場之後,才展開了他最有實驗性的創作旅程,紐約市立芭蕾依然定期寄送印刷精美的舞者型錄到我家,每頁標明舞者穿著服裝的品牌與價錢,內容完全可以預料的舞碼適合攜家帶眷前往同樂,但我想要更多,想要有意外驚喜、想被舞者嚇到、想頭皮發麻、想為舞者走火入魔感到憂心。
然而沒想到另一位男舞者鄭宗龍先生把我喚回了中城劇院區的City Center──2016年秋天,雲門二回紐約了。紐約秋季舞蹈藝術節(Fall for Dance at New York City Center),被舞評直接稱之「拼盤(Sample platter)」──幸好不是人人都有一副貴族腸胃,拼盤性價比高,是許多人嘗試觀賞新舞種的契機。不太清楚國際舞蹈藝術風格的一般民眾,或是世界各國跑去紐約學跳舞的窮孩子們,Fall for Dance 舞蹈節一張票均一價15美金,一晚可以看到看四團──就跟去有Coldplay跟The Rolling Stones音樂節一樣──,真是又划算又補,所以一開賣當天幾小時內就會賣光,幸好我早就記好時間,開賣當天在網上排隊一小時後終於購得。
第二次到紐約演出的雲門二被放在整個節的最後兩天壓軸檔,而且還被放在三位明星編舞家的後面,開場是一名歐洲長大的印度女舞者ShantalaShivalingappa帶著三個老樂師的印度傳統Kuchipudi獨舞;荷蘭舞蹈劇場(NederlandsDans Theater, NDT)演出有如極限運動般的Marko Geoko作品;第三個是退休後復出的ABT明星芭蕾舞者Alessandra Ferri演出MacGregor──這個人是上過TED、幫Radiohead的Thom Yorke編過舞的那麼有名)的新作品首演, 中場休息之後,最後一首是雲門2藝術總監鄭宗龍的作品「來」,好像在說你就是下一個明星編舞家。
在City Center看雲門2那天,至今記憶猶新,那是我睽違兩年首次回到中城劇院區去看戲,傍晚一場豪雨之後,開演前下著細雨,門口擠滿人,大廳裡此起彼落聽得見台灣腔國語,印度大叔應援團,與巨人般的荷蘭粉絲團在走道上擦身而過。一口氣看完三段風格迥異的舞之後腦力有點不支,中場休息之後,雲門2飄著七彩衣襬出場,他們的重心那麼低卻那麼輕盈,流動像水卻充滿力量,我心想果然要練太極啊,髖骨好放鬆看得真愉快,但四周的觀眾依舊肩膀僵硬,正經而木訥,可能是場地太拘謹了。在這新摩爾式建築風格的藝術殿堂裡,抬頭還可見到新近修復的古蹟陶瓦圓頂,不過在我右後方,罕見地一次坐著二十名左右非裔美國人小學生,出於不明原因他們整團被帶進了劇院,湊巧地看到了《來》。有好幾次,當雲2舞者開始搖擺起來──為了方便理解就先稱它為「廟會搖」──小孩們就忍不住格格發笑,又互相噓說不要吵,噓著噓著台上又搖起來,他們又笑了,我心想好久沒見到這麼捧場的觀眾。就在這小朋友強忍的笑聲中,迎接到「來」的高潮,也是這場舞蹈節的完美句點,正如Dance Magazine所說 :Fall For Dance Ends on a High。演完收工,舞者們還沒卸完妝就蹦蹦跳跳地跟到酒吧慶功,查證件的門衛非常驚訝這些少年少女竟然已超過21歲,路人好奇地看著這些「聶隱娘們」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每一次謝幕過後,人們想要延續那股難得的興奮,於是劇院旁的酒吧在散場後生意總是特別好,在劇場裡一晚上的表演,平日得花多少年月準備,而下一次見面又得等多久呢?想到這裡,眾人更不願意就這樣道別了,往往在散場之後還要喝上好幾杯,直到過了午夜、甚至凌晨兩、三點,走出酒吧的封閉環境,迎面而來的是從街道上吹來車尾的熱風,這個時間的紐約依然燈光燦爛得刺眼,當你走到第七大道,朝著時代廣場方向走,午夜過後的時代廣場人潮已經變得稀疏,每個人玩到這時都快要投降,但是時代廣場絕對不會閉眼,你站在廣場正中央,自帶一圈旋轉,幾百支股票、產品、時尚、劇院一次入眼,這就是紐約,永遠無恥而閃耀,你想要什麼就盡管拿,她既不會受傷,也不會為誰而改變。
舞蹈教室是一個女多男少的世界,然而舞團總監卻經常都是男的。
先不管舞蹈總監界的性別比例,在紐約的芭蕾世界裡,有一個男人的名字是鑽石級閃耀、無法動搖的,那就是喬治‧巴蘭欽(1904-1983)。
巴蘭欽出生在聖彼得堡藝術世家,是他的父親是聲樂家兼作曲家,當過喬治亞(當時是沙皇屬國,後來獨立一下又加入了蘇聯)的文化部長,家族成員不是軍人,就是藝術家──蘇聯的藝術家也是軍人。大師一生到底編過多少支作品呢?粗略估計約在四百部左右,可能有些人不情願,但這個俄國人確實重新定義了美國芭蕾,他創辦美國芭蕾學校(American Ballet School)、長期培訓舞者,開創出一套適合美國舞者、充滿力量與速度的「巴蘭欽技巧」。
巴蘭欽生在今天的話一定會變網紅,因為他不但是花美男,而且名言很多:例如「舞者是花,花本來就美,而不是因為花有甚麼了不起的故事要表達」;他還說「舞者只是樂器,應該把編舞家的音樂給演奏出來」,他引用喬治亞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話自稱「我不是人,只是一朵穿褲子的雲。」說明了他有多自戀。他以軍人般的鐵血紀律要求自我,也嚴格要求他的舞者;「你是在對自己客氣甚麼?你幹嘛退縮?你現在保留實力---下次用?沒有下次了,只有現在,現、在。」他連自己的貓都抓來訓練,他的貓Mourka出過自傳,能正確的做出大跳跟擊腿。
穿褲子的雲還致力於跟美麗舞者結婚,而且要最優秀的舞者,他一生結婚五次(其中一次無法律效用),每一任妻子都是舞台上的超級巨星, 他最後一任妻子是女神級的芭蕾舞者Tanaquil Le Clercq (暱稱泰妮),一九五六年,小兒麻痺疫苗才剛發明兩年,沒有接種過疫苗的泰妮,在北歐巡演的途中發病,隨即被送進當時的治療器材『鐵肺』這種很像太空艙、沉重冰冷的密閉金屬體,以幫浦抽吸空氣,幫助肌肉萎縮的病人被動呼吸。當時泰妮二十七歲,她人生最後一場表演跳的是「天鵝湖」。在小兒麻痺還會致死的年代,她保住了性命,但進食等生活起居都需要護士幫忙,她漸漸接受了事實:她不但不能跳舞,連走路都不可能了。這場疾病據說讓巴蘭欽的心又回到妻子身邊,也他因此開始思考新的舞蹈方法,並認識了彼拉提斯先生(Pilates瑜珈發明人)本人,編出了Agon這支雙人舞裡面,女舞者本身並不動作,由男舞者把她的身體「擺成」不同的姿勢與位置,被認為是巴蘭欽面對肌肉萎縮的妻子想做的嘗試,雖然過程非常艱難,但泰妮後來成為一名坐輪椅的舞蹈老師,她用手跟上半身教舞。巴蘭欽在照顧妻子九年之後,為了另一位美麗舞者Suzanne Farrell 而提出離婚。
每年到了十一月初,日光節約時間一結束,一夕之間紐約的白天就短得令人沮喪,宣告漫長的冬天要開始了,全市開始掛燈結彩、室內的暖氣、櫥窗上的霧氣、低沉溫柔的爵士樂,都在努力溫暖路人的心。為了準備過年,美國各地芭蕾舞團也開始把《胡桃鉗》拿出來排練,巴蘭欽版的胡桃鉗,為美國人開創了一種全新的節慶文化,從一九五五年推出新版以來每年都上演。
二○一五年的胡桃鉗照常有好多小朋友觀眾,節目單的第一頁是寫給小觀眾的觀賞須知,除了戲院禮節之外,還教他們如何欣賞舞蹈:記下自己喜歡的服裝、喜歡的角色,或者看看交響樂團裡面你最喜歡的樂器。節目進入下半場,巧克力仙子、茶仙子、咖啡仙子一一出場,坐我旁邊的小女孩躍躍欲試,壓軸的糖梅仙子終於降臨,穿著粉紅色的大紗裙,連續不停地做出完美的旋轉,小女孩忍不住跟著音樂扭起來了!
每一場芭蕾舞的觀眾席裡,都會有幾個這樣坐不住的小孩,也許未來的芭蕾舞巨星就在其中──然而一百位從小立志要跳公主仙子主角的女孩,有九十九個大概跳不到,但光是能在舞團裡得到一個位置,得耗上十幾年學習,外加無重大傷病的運氣:反過來說,若你是萬中選一的優秀舞者,跳王子公主的角色對你來說還可能不夠有趣,你會想跳壞蛋角色,你會想當黑天鵝、當魔王、或是當一隻巨大而活躍的老鼠。
萬物也許生而平等,但有些動物就是令人生理上無法接受,老鼠的賣相真的很差,牠的顏色、牠的體型、牠發出的吱吱與喳喳、牠鬼祟的行為以及身上夾帶的十一種常見疾病,都讓人不敢直視。但你知道嗎?老鼠其實眼睛看不見,他們在城市黑暗的地底,靠著感覺行走,是天生的盲舞者。這世界上有屬於老鼠的浪漫嗎?有的。《胡桃鉗》的原著原題就叫做《胡桃鉗與老鼠王》,是德國浪漫主義劇作家E•T•A霍夫曼的作品。在這個聖誕夜故事裡,老鼠是重要的反派群,當午夜的鐘聲一響,老鼠就從那放滿聖誕禮物結滿彩燈的樹下一隻隻地鑽進瑪莉小妹妹一家人溫暖的屋裡,我這個人從小看童話故事都會偏心反派,可能是因為他們都比主角有個性、有風格吧,而在《胡桃鉗》裡面,老鼠王真的超有風格,牠有七個頭——當然包含了七張老鼠臉了。同情反派是浪漫者的特質之一,霍夫曼的原著裡,老鼠王也有牠自己的辛酸,人類的小孩放置捕鼠器殺死了老鼠王的孩子,悲憤的老鼠王率領鼠軍誓死一戰,而下巴掉了的胡桃鉗將軍,被瑪莉小妹修好之後為了報恩,帶領胡桃鉗大軍擊退鼠軍,人類獲勝,得到聖誕夜的安寧與平靜,但老鼠王卻是家破人亡,仔細一想,這個故事根本就不溫馨。老鼠的形象在卡通普及後,變得可愛許多。在一張波士頓芭蕾舞團彩排的舊照中,老鼠王正在糾正部下的老鼠芭蕾,我這才發現,原來各地的老鼠芭蕾也有不同的風格:波士頓鼠王鼠兵毫無殺氣,上下身一比一,毛皮蓬鬆,穿著遊樂園吉祥物的連身服,加上露兩齒的呆萌喜感,很適合放在Hello Kitty旁邊;舊金山芭蕾的鼠王特色,是尖嘴裡一整排衝到下巴的尖牙,指甲也銳利如刀,是標準的壞溝鼠扮相;紐約市立芭蕾的鼠王與老鼠就跟地鐵老鼠一樣,在城市日夜堆積的惡性油紙餵養下,下盤肥大,但四肢細長——如此方便逃跑——,鼠兵們一跳躍,灰色的屁股就上下左右咚咚咚地擺盪;再看英國皇家芭蕾舞團的鼠王造型,灰階多層次的襤褸服飾,有一種狄更斯式悲慘遇上Alexander McQueen的暗黑華麗,想當年童工被虐棲身於下水道時,身邊也只有嚇人的老鼠竄流:以上種種顯示,英美工業發展過程中,都會居民內心累積了不少對抗老鼠的創傷,那麼特產是戰鬥民族與芭蕾巨星的俄羅斯又是如何呢?莫斯科芭蕾的鼠王挽救了浪漫之名,牠玉樹臨風、黑衣倜儻、腳尖筆直、迴旋跳躍無懈可擊,能跳鼠王的舞者必須技巧高超、經驗豐富,因為這個角色必須穿著那麼重的道具服展現輕盈,而更困難的是,當他帶著鼠頭跳舞時,頭套幾乎完全阻擋了視線,他的視野比戴上眼罩的賽馬更加狹窄,看不見地板、也看不見旁邊的舞者、甚至看不見觀眾席,只能看著觀眾席後方一個小紅點確定方位。
搬離曼哈頓之後,因為路遠,我越來越少去林肯中心,除了實際距離的影響,我與大師經典的心理距離也越來越遠;我清楚記得最後一次看巴蘭欽作品《黑與白》那天,走出劇院,心想「巴蘭欽這個沙文主義者真無聊」──巴蘭欽沒有變,是我變了,巴蘭欽六十年前新創的風格,放到現在也變得老土。
巴蘭欽制霸林肯中心數十年,在這段期間,有一位同為俄羅斯天才男舞者也曾經空降林肯中心,那人在舞蹈界外的觀眾眼中,是欲望城市裡那個「演過凱莉前男友的藝術家」,而在舞蹈世界裡,他是演、視、歌、舞,永遠追求突破、無與倫比的 "Misha"先生──巴瑞辛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巴瑞辛尼可夫在一九七四年加拿大巡演中脫隊,要求政治庇護,之後歸化美國,關於他的動機有許多說法:民主浪漫人士說他衝破鐵幕投奔民主,自由派藝術人士說他厭倦蘇聯僵化的創作體制,還有人說他被情治單位盯上了, 這個疑問當時可能很難解,然而四十年後回看他到紐約後豐沛的創作與成就,誰還需要問他為何要跳機呢?以紐約為中心的創作生命自由奔放、充滿可能性,連他「投奔自由」這件事本身,都在隔年馬上拍成了一部跳舞電影,《白夜》(White Nights, 1985),這可能是愛國電影中最帥的一部了,如今蘇聯也早已解體,記憶中只剩跳舞,尤其是那段著名的「十一圈」打賭。
「十一圈」是這樣開始的:無論在電梯裡、小屋裡,或是一間有窗的芭蕾教室裡,幾個人被圍困到最後,大概都會開始賭博,一名俄國芭蕾舞星(巴瑞辛尼可夫)跟一名美國踢躂舞者(Gregory Hines)被關在一起能賭什麼呢?Pirouettes ——轉圈圈——,賺一圈贏一盧布,連轉七圈,七盧布。
「等等,要是你輸了我得到什麼呢?你又沒錢。」踢躂舞者問。
「我的手錶嘍。」俄國舞者說。
「哦,不,我要這個。」踢躂舞者用下巴指了一下那台手提音響。
對圍困中的舞者來,輸掉手提音響是多麼嚴重的事情!這時踢躂舞者又挖著口袋說:「等等,我還有,你看……十一盧布,十一圈。」
巴瑞辛尼可夫(脫外套!)說:「你來得及數嗎?」(一秒如風般早就超過十一圈)。
巴瑞辛尼可夫現在依然住在紐約,跳舞早就已經無法滿足他,他喜歡演戲,喜歡挑戰怪異的角色,而且不怕展現自己的年邁蒼老的模樣,以他為名的表演藝術中心(Baryshnikov Arts Center,BAC),提供表演場地及駐村機會給跨界表演作品。
無論是忠實觀眾,或是芭蕾群英,來到林肯中心是為了一睹經典風采,但若要在藝術的路是繼續前進,恐怕還是得離開林肯中心。巴瑞辛尼可夫離開美國芭蕾劇場之後,才展開了他最有實驗性的創作旅程,紐約市立芭蕾依然定期寄送印刷精美的舞者型錄到我家,每頁標明舞者穿著服裝的品牌與價錢,內容完全可以預料的舞碼適合攜家帶眷前往同樂,但我想要更多,想要有意外驚喜、想被舞者嚇到、想頭皮發麻、想為舞者走火入魔感到憂心。
然而沒想到另一位男舞者鄭宗龍先生把我喚回了中城劇院區的City Center──2016年秋天,雲門二回紐約了。紐約秋季舞蹈藝術節(Fall for Dance at New York City Center),被舞評直接稱之「拼盤(Sample platter)」──幸好不是人人都有一副貴族腸胃,拼盤性價比高,是許多人嘗試觀賞新舞種的契機。不太清楚國際舞蹈藝術風格的一般民眾,或是世界各國跑去紐約學跳舞的窮孩子們,Fall for Dance 舞蹈節一張票均一價15美金,一晚可以看到看四團──就跟去有Coldplay跟The Rolling Stones音樂節一樣──,真是又划算又補,所以一開賣當天幾小時內就會賣光,幸好我早就記好時間,開賣當天在網上排隊一小時後終於購得。
第二次到紐約演出的雲門二被放在整個節的最後兩天壓軸檔,而且還被放在三位明星編舞家的後面,開場是一名歐洲長大的印度女舞者ShantalaShivalingappa帶著三個老樂師的印度傳統Kuchipudi獨舞;荷蘭舞蹈劇場(NederlandsDans Theater, NDT)演出有如極限運動般的Marko Geoko作品;第三個是退休後復出的ABT明星芭蕾舞者Alessandra Ferri演出MacGregor──這個人是上過TED、幫Radiohead的Thom Yorke編過舞的那麼有名)的新作品首演, 中場休息之後,最後一首是雲門2藝術總監鄭宗龍的作品「來」,好像在說你就是下一個明星編舞家。
在City Center看雲門2那天,至今記憶猶新,那是我睽違兩年首次回到中城劇院區去看戲,傍晚一場豪雨之後,開演前下著細雨,門口擠滿人,大廳裡此起彼落聽得見台灣腔國語,印度大叔應援團,與巨人般的荷蘭粉絲團在走道上擦身而過。一口氣看完三段風格迥異的舞之後腦力有點不支,中場休息之後,雲門2飄著七彩衣襬出場,他們的重心那麼低卻那麼輕盈,流動像水卻充滿力量,我心想果然要練太極啊,髖骨好放鬆看得真愉快,但四周的觀眾依舊肩膀僵硬,正經而木訥,可能是場地太拘謹了。在這新摩爾式建築風格的藝術殿堂裡,抬頭還可見到新近修復的古蹟陶瓦圓頂,不過在我右後方,罕見地一次坐著二十名左右非裔美國人小學生,出於不明原因他們整團被帶進了劇院,湊巧地看到了《來》。有好幾次,當雲2舞者開始搖擺起來──為了方便理解就先稱它為「廟會搖」──小孩們就忍不住格格發笑,又互相噓說不要吵,噓著噓著台上又搖起來,他們又笑了,我心想好久沒見到這麼捧場的觀眾。就在這小朋友強忍的笑聲中,迎接到「來」的高潮,也是這場舞蹈節的完美句點,正如Dance Magazine所說 :Fall For Dance Ends on a High。演完收工,舞者們還沒卸完妝就蹦蹦跳跳地跟到酒吧慶功,查證件的門衛非常驚訝這些少年少女竟然已超過21歲,路人好奇地看著這些「聶隱娘們」到底是哪裡來的呢?
每一次謝幕過後,人們想要延續那股難得的興奮,於是劇院旁的酒吧在散場後生意總是特別好,在劇場裡一晚上的表演,平日得花多少年月準備,而下一次見面又得等多久呢?想到這裡,眾人更不願意就這樣道別了,往往在散場之後還要喝上好幾杯,直到過了午夜、甚至凌晨兩、三點,走出酒吧的封閉環境,迎面而來的是從街道上吹來車尾的熱風,這個時間的紐約依然燈光燦爛得刺眼,當你走到第七大道,朝著時代廣場方向走,午夜過後的時代廣場人潮已經變得稀疏,每個人玩到這時都快要投降,但是時代廣場絕對不會閉眼,你站在廣場正中央,自帶一圈旋轉,幾百支股票、產品、時尚、劇院一次入眼,這就是紐約,永遠無恥而閃耀,你想要什麼就盡管拿,她既不會受傷,也不會為誰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