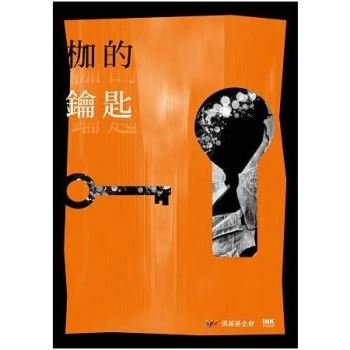楊澤評語──
〈台北車站偶見〉寫假日蜂集在此的外傭群像,是一首令人驚豔的新詩。標題說「偶見」,其實是作者掩人耳目的話語策略,因為從一開始,此詩即充滿「直擊」的速度感與現場感,爆發力十足。我們讀者因此有幸目睹了,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台北車站,不單廻蕩「叫拜樓的回音」,且海風鹹腥味陣陣襲人。而第二段畫面的視覺能量尤其驚人:「她們把車站大廳/漆成了拜占庭的巴剎/希賈布染滿色彩熾烈的告白……」不可思議的是,透過揮灑大量西洋藝文典故(東方主義及其他),年輕詩人竟能穩穩的將此詩,始終維持在某種意象與思想強度、高度上,直至最後而不墜,委實令人贊嘆不已。
結尾處,年輕詩人果敢站出來現身說法,堪稱是,針對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城市,一記又狠又準的回馬槍:「以直視那些面紗之下/眼睛裡的光/裡頭映著的是這座城巿的美麗與猙獰/那些我自己看不見的地方」年輕詩人既能穿透(真理的)面紗,清楚看見資本主義的美麗與猙獰(結構性暴力),而最終又將一切歸結於某種「看不見」,這份未明言的吊詭與(自我)反諷,也許正是此作最難及之處。
李維菁評語──
〈枷的鑰匙〉這篇作品應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最引人矚目的一篇,作者澎湃的情感、迷惘與憤怒交雜,還有那份訴說的渴望的激切,都讓人感動。
而作品中涉及的性別問題、家庭內部的剝削,作者將家與囚禁的意象連結,特別是那份性的暴力緊張,瀰漫在祖母、母親、父親與主人翁之間,家早已非提供安全庇護之所,而是隱密幽微的暴力的展演所,倒是父親的外遇對象,反而提供了一種平等的釋放感。
作者展現的情感能量與企圖心,令人期待他未來更多的表現。
童偉格評語──
〈子宮的樓上〉開啟一個夢魅般的啟蒙敘事,或者,一個少女版的「性的人間」。在血與肉嘎吱互絞,羊水與精液相處融洽的快感修辭底,作者安藏一位不無詩意的主體「我」,而藉「我」的表述,將許多後製成「我」的時空碎片,織寫為姊姊「妳」(或許是「我」以想像和實感,去「亂七八糟」扮裝、或再「生回來」——這個意象,及對「共同生活」的描摹,明確亦是大江晚期作品的典故延異——的代體)獨自的,既莊嚴又滑稽的逃生路徑。這或許,正是〈子宮的樓上〉篇章命名的深意,及其視域不免會受啟蒙敘事模組規訓的原因:將「女孩經常被告知」的,重塑為女孩對世界的告知;從最古老的過往,到最近切的親者,一切條理與意義,如今,皆可由「我」,在一個觀測定點重新編排,而所有這些輯成,內向指涉了「我」在話語世界中,自我主體化的完成。簡單說:「我」複寫「我」自己,終爾將「子宮」,這生理與啟蒙模組中的過渡場域,自我重置為詩學意義上的「我」之起源。自「我」作祖,如小說所言,「媽媽生出我的時候,我的子宮也跟著拉出一串的人」。〈子宮的樓上〉企圖實踐的這次複寫,及其所動支的書寫技藝,在本屆作品中無疑是最特出的,因此獲選為首獎。
〈台北車站偶見〉寫假日蜂集在此的外傭群像,是一首令人驚豔的新詩。標題說「偶見」,其實是作者掩人耳目的話語策略,因為從一開始,此詩即充滿「直擊」的速度感與現場感,爆發力十足。我們讀者因此有幸目睹了,一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台北車站,不單廻蕩「叫拜樓的回音」,且海風鹹腥味陣陣襲人。而第二段畫面的視覺能量尤其驚人:「她們把車站大廳/漆成了拜占庭的巴剎/希賈布染滿色彩熾烈的告白……」不可思議的是,透過揮灑大量西洋藝文典故(東方主義及其他),年輕詩人竟能穩穩的將此詩,始終維持在某種意象與思想強度、高度上,直至最後而不墜,委實令人贊嘆不已。
結尾處,年輕詩人果敢站出來現身說法,堪稱是,針對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城市,一記又狠又準的回馬槍:「以直視那些面紗之下/眼睛裡的光/裡頭映著的是這座城巿的美麗與猙獰/那些我自己看不見的地方」年輕詩人既能穿透(真理的)面紗,清楚看見資本主義的美麗與猙獰(結構性暴力),而最終又將一切歸結於某種「看不見」,這份未明言的吊詭與(自我)反諷,也許正是此作最難及之處。
李維菁評語──
〈枷的鑰匙〉這篇作品應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最引人矚目的一篇,作者澎湃的情感、迷惘與憤怒交雜,還有那份訴說的渴望的激切,都讓人感動。
而作品中涉及的性別問題、家庭內部的剝削,作者將家與囚禁的意象連結,特別是那份性的暴力緊張,瀰漫在祖母、母親、父親與主人翁之間,家早已非提供安全庇護之所,而是隱密幽微的暴力的展演所,倒是父親的外遇對象,反而提供了一種平等的釋放感。
作者展現的情感能量與企圖心,令人期待他未來更多的表現。
童偉格評語──
〈子宮的樓上〉開啟一個夢魅般的啟蒙敘事,或者,一個少女版的「性的人間」。在血與肉嘎吱互絞,羊水與精液相處融洽的快感修辭底,作者安藏一位不無詩意的主體「我」,而藉「我」的表述,將許多後製成「我」的時空碎片,織寫為姊姊「妳」(或許是「我」以想像和實感,去「亂七八糟」扮裝、或再「生回來」——這個意象,及對「共同生活」的描摹,明確亦是大江晚期作品的典故延異——的代體)獨自的,既莊嚴又滑稽的逃生路徑。這或許,正是〈子宮的樓上〉篇章命名的深意,及其視域不免會受啟蒙敘事模組規訓的原因:將「女孩經常被告知」的,重塑為女孩對世界的告知;從最古老的過往,到最近切的親者,一切條理與意義,如今,皆可由「我」,在一個觀測定點重新編排,而所有這些輯成,內向指涉了「我」在話語世界中,自我主體化的完成。簡單說:「我」複寫「我」自己,終爾將「子宮」,這生理與啟蒙模組中的過渡場域,自我重置為詩學意義上的「我」之起源。自「我」作祖,如小說所言,「媽媽生出我的時候,我的子宮也跟著拉出一串的人」。〈子宮的樓上〉企圖實踐的這次複寫,及其所動支的書寫技藝,在本屆作品中無疑是最特出的,因此獲選為首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