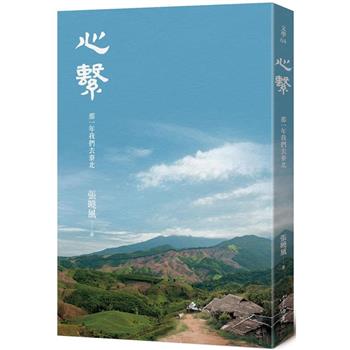行行重行行
「沒有藥,啊——沒有關係。」
女孩大約十四、五歲,長的樣子我已經忘了,卻記得她的一句話。
那是八月初,我們的醫療隊在泰北一個山村看病,病人從早到晚走動不 停,我們吃飯的時候,周圍的走廊上也站着病人,使人一面吃,一面很有罪疚感,恨不得自己能不吃不睡才好。
從台灣帶來的藥,有一部份已經用完了,村子裏有個雜貨店兼賣藥,卻供不上我們的需求。
而那女孩剛好是拿不到藥的一個,山村裏看病,和我們在台北不同,病人很可能是走了三個小時山路才到的,沒有藥給他們使我們很不安。
「你下個禮拜再來,那時候牙醫來看病,順便會帶第二批的藥來,今天沒有藥了。」
說那樣的話,使我的心很疼,在台北,藥像米、麵一樣,大家簡直是濫吃,而這小女孩,翻山越嶺而來,只因來遲了,竟沒有一顆藥。
「沒有藥了?」她詫異中有平靜,「啊──沒有關係。」
說完,她匆匆走了,像是不敢耽擱下一個病人的樣子。她那副恭謹莊矜、不想麻煩別人的表情,使我疼惜到了暗自憤怒起來。
我跑到迴廊上,只見人如潮湧,我心中衝動,只想大聲叫出來: 「老鄉親啊!在西方,那塊幸福的土地上,曾經有人說,人有免於飢餓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對你們而言,願你們有『免於無醫療的自由』吧!求求你們不要用那樣感謝的眼光看着我們吧!要知道這根本就是你們的權利啊!你們的身體本來就該有人來照顧的啊!」
如果那天那女孩用抱怨的口吻說:
「哼!怎麼偏偏好輪到我就沒有藥了?」
或者:
「什麼?我從上個禮拜就來親戚家借住,今天早起又走了三個鐘頭的路,居然沒有藥?」
如果她生氣,如果她怨嘆,我都會一邊向她解釋一邊覺得好過一點,可是,為什麼她偏用那麼卑微細小的聲音說:
「啊──沒有關係。」
「有哩──」
在泰北行醫,問病是相當大的困難,文明世界裏的病人每每可以把自己的病形容得生動活潑、鉅細靡遺,山裏的難民卻辦不到。
「大娘,」掛號部的工作人員,打起雲南腔問話,「你哪裏不好過?」
「不好過啊!」大娘慢悠悠地應了一句,她很老了,一副一輩子劬勞的樣子,但和我們說話的時候卻是無限信任如見神醫。
「哪裏不好過?」掛號處急了,不知該把她分給哪一位醫生,「頭痛不痛?」
「有哩──」(這兩個字他們說得很慢,都讀作第一聲。)
「胃痛嗎?」
「有哩──」
「關節痛?」
「有哩──」
「心痛?」
「有哩──」
「手膀痛?」
「有哩──」
不敢再問下去了,總之,她全身都痛,她如此高年,如此勞苦又如此營養不良,全身都難過倒也不是不可解的。
我獨自跑開去看山色,不遠的地方有大河日夜繞流,是什麼使我悲痛?
是眼前這麼無處不痛的老婦人,還是那位讓我無端想起的、另一個全身無處不病的叫做「中國」的老母親?
「不是她丈夫──是全村」
團裏的化驗師把結果公佈,那女人的病是瘧疾。我看他簡直有點興奮,竟對着顯微鏡大叫:「快來看啊,台灣看不到這種東西!」
大夫緊張兮兮地透過翻譯問那女病人:
「她家裏還有什麼人?」
「有丈夫。」
「去把她丈夫也叫來──」
「她生病,為什麼叫她丈夫來?」翻譯問。
「通常一個人有這種病,一家人都會有的,叫她丈夫也來看病,否則她病好了,她丈夫還病着,治了等於白治,她丈夫是不是也跟她一樣發冷發熱、臉色黃黃的?」
「是啊!是啊!」旁觀的人熱心地插起嘴來,「不過不是她丈夫──是全村,他們那個村子的人全都發冷發熱,又黃又瘦。」
我們一時全噤住了!
在某個小山頭,有一村的人,全都是瘧疾病人。
我們或許可以到那個村子去出診,一一發給他們奎寧丸,但是,那有什麼用呢?除非我們先消滅他們的瘧蚊,而要消滅瘧蚊,除非整理整個環境……。
「我起先只懷疑她丈夫──我沒有想到全村……。」
大夫喃喃說着,一副被擊中什麼而要崩潰的樣子。
醫生所能作的,是多麼少的一部份,我們每想起那個不知名的村子,大家心裏總有一陣抽痛。
獨臂人
車從山路下來,顛得人七葷八素,車到半途,終於不去理會尊嚴,大聲叫停。
停下來以後,我和何大夫跑到路邊去大吐,吐完了,用土掩好,繼續上路。
終於到了巴山,一個類似三叉路的地方,我跳下車來去買冰汽水喝,自己覺得自己只剩三分像人了。
正在這時候,迎面走來一個男子,他顯然已經站在那裏等了很久。
「姐姐,」他叫了我一聲,「你們就是從台北來,過兩天要上老象堂去看病的人嗎?」
我當時被那樣親切的聲音一驚,整個人醒了過來。
在台北也常被人叫姐姐,但習慣上叫的人只叫「張姐姐」,叫開了連老一輩的朋友如王藍也這樣叫我。
但忽然在荒山野嶺的小驛站上被陌生人那樣親切地叫一聲姐姐,心裏的感覺竟是驚動。其實,「姐姐」一稱在這個地區很流行,不一定指比自己年
齡大的女子,只是一種尊稱,我曾聽一個女病人叫何大夫姐姐,請她為自己裝樂普,當時也聽得耳熱心酸。
「你怎麼知道是我們?」
「我昨天就來等了,我想你們車子一定從這裏過,你們要多少被子、褥子?要不要我們替你們準備伙食,伙食要多少錢一天的?」他一一細問。
「我們有二十四個人,伙食要麻煩你們,七百銖一天(約台幣一千二百元),好嗎?」
這一帶窮鄉僻壤,根本沒飯店旅館,我們一路總是睡民房,委託別人辦食,當然,偶然也會接受招待。
「好,那我就去準備了。」
喝完汽水我們上車──我這才敢好好看他一眼,他是個獨臂人,一隻袖子空盪盪的,袖口塞在腰帶裏,剛剛我不敢注視他,怕傷了他的自尊。
以後熟了,才知道斷臂的由來。
小時他曾經胳臂受傷,有人教他們一個土方,把活雞連毛帶血斬成醬,趁熱敷上包好,一個禮拜取下,不料患部卻格外紅腫潰爛,病毒侵入骨中,醫生要他鋸斷手臂……。
誰來幫助遠方的同胞有「免於無知的自由」呢?
苗孩的酷刑
那天早上我們到苗人村去採血液,想知道瘧疾散佈的情形。
在路上,我們碰到那苗人小孩。他差不多八、九歲,是個清秀的小男孩,眼光卻是呆滯畏葸的。
走近了,馬教士上去和大人打招呼,小孩低頭垂眉,一言不發。
「他兩隻腳全燙爛了,你看!」
「怎麼啦?」大家雖然只看到一小角,卻也大驚失色。
「他其實本來只是打擺子(即瘧疾),他們苗人有個土法子,聽說是把一大鍋水燒得滾滾的,然後再燒紅烙鐵,並且把鐵往水裏一丟,就會冒起一 陣很熱的蒸氣,把小孩拿棉被包了,薰這蒸氣,擺子就會好。」
可是這孩子被太強的蒸氣所傷,下半身的皮全爛了,上身和手也燙傷了好幾塊,他整個的皮膚變成難看而難受的紅疤。
小孩忍耐着由我們看他的疤,並且那位帶着他的大人(似乎是他叔叔) 答應下午來讓大夫為他還未結疤的傷口擦藥。
擦上消毒藥,發現我們所能做的也就這麼多了,如果真要治的話需要一流的醫院,在隔離無菌的地方慢慢進行整形手術,不是我們這種奔波千里的醫療隊所能做的。
本來幾顆奎寧就可以解決的事,如今那孩子卻失去了全身一半的表皮。 如果他有幸適時碰到一位醫生……。不能想下去了,一年有多少苗人死於這 種治療,有多少小孩傷於這種治療,在文明的觸角伸不到的地方,活着,是一件艱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