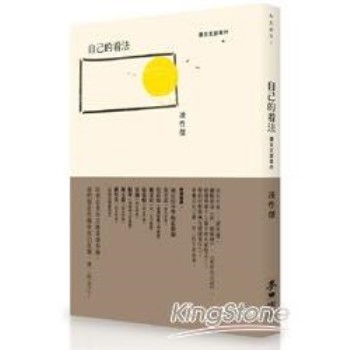一個有故事的人——〈方山子傳〉(節選).宋.蘇軾
才氣縱橫的蘇東坡
蘇軾(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文學家,文章詩詞書畫皆所擅長,唐宋八大家之一,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考中進士。他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三蘇」。
神宗時,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為杭州通判,又改任密州等地。元豐二年(一○七九),御史臺以「訕謗朝政」罪名將他逮捕入獄,即所謂「烏臺詩案」。之後死裡逃生,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後,他擔任翰林學士、充任侍讀。哲宗紹聖元年(一○九四),蘇軾以譏刺先朝罪被貶英州,未至貶所又貶居惠州(今廣東惠陽),後來更遠謫到儋州(海南島)。徽宗繼位,他才遇赦北還,於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今江蘇常州)。
他認為作文的藝術境界是:「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方山子傳(節選)
獨念方山子1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2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3,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4,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5見之歟?
【註釋】
1 方山子:姓陳,名慥,字季常,宋眉州青神(四川省今縣)人,自號龍丘居士。晚年棄第宅,庵居蔬食,戴方形高冠,人稱方山子。
2 怒馬:快馬。
3 勳閥:勳,功勳;閥,功績、功勞。舊時有功勳的臣子,皆書有功狀,榜於門左,故稱「勳閥」。引申為名門望族。
4 佯狂垢污:假裝癲狂不潔之人。佯,假裝。
5 儻:或者、倘若。
【語譯】
回想起方山子年少的時候,縱情任性地喝酒弄劍,揮霍無度,視金錢如糞土。十九年前,我在岐山,曾見方山子帶著兩名騎馬的隨從,挾藏兩副弓箭,在西山遊獵。見到前方有鵲鳥飛起,方山子便命令隨從追趕射擊,然而未能射中。方山子於是快馬加鞭,獨自向前,一箭便射中。意氣昂揚的他騎在馬上,與我談論用兵之道以及古今成敗的事理,自認為是一代的豪傑。至今不過短短的時日,那股英氣精悍的神色,依舊顯現於眉宇之間,我疑惑著,他哪裡會是一位蟄居山中的隱士呢?
方山子出身於功勳世家,循例應可做官。假如他投身官場,現在早就顯達有名望了。他家在洛陽,園林宅第富麗,與公侯之家不相上下。在河北也有田產,每年可得千匹絲綢收入,這也足以使得生活富樂了。然而他拋開這些,獨自來到窮山荒野中,這難道是因為心中無所領悟才這樣嗎?
我聽說光州、黃州一帶頗多奇人,常常佯裝瘋癲、外表髒汙,但是無法遇見。方山子或許才能夠遇見他們這樣的人吧。
〈方山子傳〉全文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歧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我讀我思
透過事件強調個性
傳,是古代文體之一,用來記載人物事蹟。我們如今多把此類作品統稱為傳記。〈方山子傳〉是一篇佈局奇特的人物傳記,長僅四百多字。透過這裡節錄的兩百餘字可以看出方山子的形象,也可以隱約揣測蘇東坡為何要如此描寫一個好朋友。蘇東坡寫這篇〈方山子傳〉,重點不在詳細交代身形外貌,而是要揭示一種生命態度。這篇文章精彩的地方,是透過事件來強調個性。我們看見了方山子的精彩,其實也就看見了蘇東坡這個書寫者的價值判斷。
從裝扮形塑個人風格
在篇章的開頭,蘇東坡不作尋常起筆。一般人物傳記裡慣有的家世、籍貫、姓名,這裡全都略去不談,反倒是告訴我們這個主角人物的綽號,以及他崇拜的對象,進一步說明綽號從何而來。方山子少年時或許血氣方剛,想要行俠仗義,特別嚮往朱家、郭解的為人。他的這兩個偶像,是漢朝著名的俠客,喜歡挺身而出為人解憂。方山子稍長才折節讀書,希望實現政治抱負。然而他一直未受賞識,無法馳騁才華。年紀老大了,便隱居光州、黃州,往來山中。因為總戴著一頂方山冠(方形古帽),就被稱為方山子了。
從裝扮可以看出個性,從裝扮也可以形塑個人風格。在古代社會,男生的帽子標誌著年紀或身份,年滿二十歲叫做弱冠,因著身份官位不同,帽子的樣式也有差異。這種方山冠,原本是漢代宗廟祭祀時樂舞者所戴的,到了唐宋兩代仍有一些隱士喜歡做這種裝扮。於是,帽子便成為了象徵。
短句簡潔順暢,俐落而昂揚
次段,記述蘇東坡因為被貶黃州,才在岐亭巧遇方山子。透過蘇東坡的對答,順勢點出方山子姓甚名誰。對於這不期然的相見,東坡說:「這是我的老朋友陳慥(季常)啊,怎麼會在這裡呢?」方山子也驚訝地問東坡為何會到此地。知道了原因後,方山子先是低頭不語,接著仰天大笑,邀請東坡到家中作客。方山子家裡環堵蕭然,一貧如洗,即便如此,妻兒奴僕卻都怡然自樂。(妻子奴僕尚且如此,方山子想必也能自樂的。)這時,蘇東坡對這樣的景象感到驚奇了。久別重逢之際互問遭遇,陳季常低頭不語然後仰天大笑,這動作本身就饒富意味。我們或可推敲:低頭不語是若有所思的感傷?仰天而笑是在自嘲彼此都不遇於世?於是只能在這場合裡交換困頓的消息?
交代了重逢景況,文章接著就是蘇東坡印象中,幾件足以代表方山子氣質神采的事件了。蘇東坡筆鋒一轉,將場景迅速切換到十九年前。初見陳慥的狀況,考驗著蘇東坡的敘事功力。他究竟要怎樣將畫面鮮明的帶出來呢?人際交往,第一印象是至關重要的。從第一印象,我們辨識對方是否值得交遊往來,思量言語交談的深度。從第一印象,決定了彼此往後的關連或不關連。
蘇軾三言兩語,就召喚出十九年前的記憶。短句簡潔順暢,俐落而昂揚。先寫當下之重逢再寫過去的初見,情境的跳接毫不生澀,方山子年少時的意氣風發,正好與當下的隱遁貧窶形成強烈對比。身為讀者當然好奇,這中間究竟發生什麼事?蘇東坡沒有明說。沒有明說的部份,或許也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從異於常人之處寫起
方山子這個人物的形象,蘇東坡只用四百多字便勾畫得清晰深刻,讀來如在眼前。蘇東坡從他異於常人之處寫起,那些看似怪異的行為,一下子就吸引住讀者的目光。少年飛揚跋扈、一身俠義,「怒馬獨出」就能彎弓射鵲,可說是武功高強了。他與蘇東坡談論兵法,分析古今成敗,想必是氣度恢弘,展現了無比的自信,自認為是豪士。俗語說物以類聚,年輕的陳季常如此自負,蘇東坡怕也不遑多讓吧。初見任俠不羈的青年陳季常,言語投機才能結為好友。陳季常家世顯赫,在洛陽擁有豪宅,在河北的田產收入頗為豐厚。憑他的家世與才華,想要出仕做官應當不是難事。然而他捨棄一切,隱居在荒僻的鄉野。這樣的作為,更顯出方山子的特別。背後的原因,也更加引人尋思。
凸顯對方,對照自我
這位帽子先生,曾經扮演過「俠」與「士」,最後選擇的卻是「隱」。這是衷心嚮往還是不得不然?其中有許多思考的空間。「俠」、「士」、「隱」三種人格特質,在陳季常身上顯現,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風采。人在面對環境的時候,自己的態度可能改變環境,也可能被環境所改變。想要馳騁當世的人,「不遇」(沒有出路、無法施展)或許才是做出人生抉擇的關鍵。選擇隱居的陳季常,與捲入政治紛爭而遭受貶謫的蘇東坡相遇了。這樣的「遇」,更加深刻的對映出各自的「不遇」。宋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李定、舒亶等人誣陷蘇東坡詩文訕謗朝廷,下獄治罪,史稱「烏臺詩案」。蘇東坡死裡逃生,被貶黃州團練副史。已經年過四十的蘇東坡遭此挫折,內心當然有深切的感觸。寫陳季常的時候,不斷凸顯對方,其實也正在不斷的對照自我。他對陳季常的理解,往往也是自我理解的一部份。
最後一段裡,蘇東坡說光州、黃州間多「異人」,這些特異份子往往佯狂垢汙,氣質張狂非理性,美化一點的說法或許是不修邊幅的瀟灑。蘇東坡說他們不可得而見,於是要問問方山子或許見過了吧。「佯狂垢汙」的「光、黃異人」是誰?不正是方山子嗎?不正是中年被貶謫的蘇東坡自己嗎?寫他人的同時,也暗示了自己的心境,蘇東坡確實高明啊。
順帶一提,陳季常的軼聞奇事不只這一樁。蘇軾〈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中寫著:「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陳慥之妻柳氏凶悍善妒,蘇東坡寫詩將陳妻比為河東獅,形象亦極為鮮明。〈方山子傳〉裡陳季常的英雄形象,在另一篇作品中竟成了怕老婆俱樂部的會員了。「河東獅吼」、「季常之癖」後來變成成語典故,蘇東坡摹狀人物的功力可見一斑。
【以古觀今】
傳記作品的書寫重點:寫人物必須從經驗出發
傳記類型的作品,往往要介紹人物的姓氏籍貫、生卒年月、生平行事,以平鋪直敘為主。這樣的寫法固然平易翔實,但卻容易讓人讀了覺得千人一面。就像許多小學生寫自己的爸媽,和別人的爸媽沒什麼不一樣,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人物描寫若是淪於這種境地,或許是因為書寫者本身感官的遲鈍、思想情感的貧乏。
經驗的單調與貧乏,是我們現代生活中最可怕的現象。不管是求學或就業,每一個現代社會體制下的心靈,往往欠缺了創造的勇氣與能力。在人與我何其相像的世界裡,我們不免懷疑,自己的生命還有故事好說嗎?自己的面目,真的和他人不一樣嗎?張愛玲說過:「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欠缺生活體驗,沒有故事好說的人生,我以為是不值得活的。
蘇東坡〈方山子傳〉提醒我們,寫人物必須從經驗出發。擺開俗套,另闢蹊徑。試圖挖掘故事,才能把人物寫得奕奕有神。有時自己的心事說不出口,那麼不妨說說他人的故事。
延伸閱讀
陳芳明,《昨夜雪深幾許》,印刻
劉強,《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麥田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印刻
保羅莫朗,《我沒時間討厭你》,麥田
才氣縱橫的蘇東坡
蘇軾(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文學家,文章詩詞書畫皆所擅長,唐宋八大家之一,仁宗嘉祐二年(一○五七)考中進士。他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三蘇」。
神宗時,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為杭州通判,又改任密州等地。元豐二年(一○七九),御史臺以「訕謗朝政」罪名將他逮捕入獄,即所謂「烏臺詩案」。之後死裡逃生,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後,他擔任翰林學士、充任侍讀。哲宗紹聖元年(一○九四),蘇軾以譏刺先朝罪被貶英州,未至貶所又貶居惠州(今廣東惠陽),後來更遠謫到儋州(海南島)。徽宗繼位,他才遇赦北還,於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今江蘇常州)。
他認為作文的藝術境界是:「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方山子傳(節選)
獨念方山子1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2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3,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4,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5見之歟?
【註釋】
1 方山子:姓陳,名慥,字季常,宋眉州青神(四川省今縣)人,自號龍丘居士。晚年棄第宅,庵居蔬食,戴方形高冠,人稱方山子。
2 怒馬:快馬。
3 勳閥:勳,功勳;閥,功績、功勞。舊時有功勳的臣子,皆書有功狀,榜於門左,故稱「勳閥」。引申為名門望族。
4 佯狂垢污:假裝癲狂不潔之人。佯,假裝。
5 儻:或者、倘若。
【語譯】
回想起方山子年少的時候,縱情任性地喝酒弄劍,揮霍無度,視金錢如糞土。十九年前,我在岐山,曾見方山子帶著兩名騎馬的隨從,挾藏兩副弓箭,在西山遊獵。見到前方有鵲鳥飛起,方山子便命令隨從追趕射擊,然而未能射中。方山子於是快馬加鞭,獨自向前,一箭便射中。意氣昂揚的他騎在馬上,與我談論用兵之道以及古今成敗的事理,自認為是一代的豪傑。至今不過短短的時日,那股英氣精悍的神色,依舊顯現於眉宇之間,我疑惑著,他哪裡會是一位蟄居山中的隱士呢?
方山子出身於功勳世家,循例應可做官。假如他投身官場,現在早就顯達有名望了。他家在洛陽,園林宅第富麗,與公侯之家不相上下。在河北也有田產,每年可得千匹絲綢收入,這也足以使得生活富樂了。然而他拋開這些,獨自來到窮山荒野中,這難道是因為心中無所領悟才這樣嗎?
我聽說光州、黃州一帶頗多奇人,常常佯裝瘋癲、外表髒汙,但是無法遇見。方山子或許才能夠遇見他們這樣的人吧。
〈方山子傳〉全文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歧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我讀我思
透過事件強調個性
傳,是古代文體之一,用來記載人物事蹟。我們如今多把此類作品統稱為傳記。〈方山子傳〉是一篇佈局奇特的人物傳記,長僅四百多字。透過這裡節錄的兩百餘字可以看出方山子的形象,也可以隱約揣測蘇東坡為何要如此描寫一個好朋友。蘇東坡寫這篇〈方山子傳〉,重點不在詳細交代身形外貌,而是要揭示一種生命態度。這篇文章精彩的地方,是透過事件來強調個性。我們看見了方山子的精彩,其實也就看見了蘇東坡這個書寫者的價值判斷。
從裝扮形塑個人風格
在篇章的開頭,蘇東坡不作尋常起筆。一般人物傳記裡慣有的家世、籍貫、姓名,這裡全都略去不談,反倒是告訴我們這個主角人物的綽號,以及他崇拜的對象,進一步說明綽號從何而來。方山子少年時或許血氣方剛,想要行俠仗義,特別嚮往朱家、郭解的為人。他的這兩個偶像,是漢朝著名的俠客,喜歡挺身而出為人解憂。方山子稍長才折節讀書,希望實現政治抱負。然而他一直未受賞識,無法馳騁才華。年紀老大了,便隱居光州、黃州,往來山中。因為總戴著一頂方山冠(方形古帽),就被稱為方山子了。
從裝扮可以看出個性,從裝扮也可以形塑個人風格。在古代社會,男生的帽子標誌著年紀或身份,年滿二十歲叫做弱冠,因著身份官位不同,帽子的樣式也有差異。這種方山冠,原本是漢代宗廟祭祀時樂舞者所戴的,到了唐宋兩代仍有一些隱士喜歡做這種裝扮。於是,帽子便成為了象徵。
短句簡潔順暢,俐落而昂揚
次段,記述蘇東坡因為被貶黃州,才在岐亭巧遇方山子。透過蘇東坡的對答,順勢點出方山子姓甚名誰。對於這不期然的相見,東坡說:「這是我的老朋友陳慥(季常)啊,怎麼會在這裡呢?」方山子也驚訝地問東坡為何會到此地。知道了原因後,方山子先是低頭不語,接著仰天大笑,邀請東坡到家中作客。方山子家裡環堵蕭然,一貧如洗,即便如此,妻兒奴僕卻都怡然自樂。(妻子奴僕尚且如此,方山子想必也能自樂的。)這時,蘇東坡對這樣的景象感到驚奇了。久別重逢之際互問遭遇,陳季常低頭不語然後仰天大笑,這動作本身就饒富意味。我們或可推敲:低頭不語是若有所思的感傷?仰天而笑是在自嘲彼此都不遇於世?於是只能在這場合裡交換困頓的消息?
交代了重逢景況,文章接著就是蘇東坡印象中,幾件足以代表方山子氣質神采的事件了。蘇東坡筆鋒一轉,將場景迅速切換到十九年前。初見陳慥的狀況,考驗著蘇東坡的敘事功力。他究竟要怎樣將畫面鮮明的帶出來呢?人際交往,第一印象是至關重要的。從第一印象,我們辨識對方是否值得交遊往來,思量言語交談的深度。從第一印象,決定了彼此往後的關連或不關連。
蘇軾三言兩語,就召喚出十九年前的記憶。短句簡潔順暢,俐落而昂揚。先寫當下之重逢再寫過去的初見,情境的跳接毫不生澀,方山子年少時的意氣風發,正好與當下的隱遁貧窶形成強烈對比。身為讀者當然好奇,這中間究竟發生什麼事?蘇東坡沒有明說。沒有明說的部份,或許也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從異於常人之處寫起
方山子這個人物的形象,蘇東坡只用四百多字便勾畫得清晰深刻,讀來如在眼前。蘇東坡從他異於常人之處寫起,那些看似怪異的行為,一下子就吸引住讀者的目光。少年飛揚跋扈、一身俠義,「怒馬獨出」就能彎弓射鵲,可說是武功高強了。他與蘇東坡談論兵法,分析古今成敗,想必是氣度恢弘,展現了無比的自信,自認為是豪士。俗語說物以類聚,年輕的陳季常如此自負,蘇東坡怕也不遑多讓吧。初見任俠不羈的青年陳季常,言語投機才能結為好友。陳季常家世顯赫,在洛陽擁有豪宅,在河北的田產收入頗為豐厚。憑他的家世與才華,想要出仕做官應當不是難事。然而他捨棄一切,隱居在荒僻的鄉野。這樣的作為,更顯出方山子的特別。背後的原因,也更加引人尋思。
凸顯對方,對照自我
這位帽子先生,曾經扮演過「俠」與「士」,最後選擇的卻是「隱」。這是衷心嚮往還是不得不然?其中有許多思考的空間。「俠」、「士」、「隱」三種人格特質,在陳季常身上顯現,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風采。人在面對環境的時候,自己的態度可能改變環境,也可能被環境所改變。想要馳騁當世的人,「不遇」(沒有出路、無法施展)或許才是做出人生抉擇的關鍵。選擇隱居的陳季常,與捲入政治紛爭而遭受貶謫的蘇東坡相遇了。這樣的「遇」,更加深刻的對映出各自的「不遇」。宋神宗元豐二年(一○七九),李定、舒亶等人誣陷蘇東坡詩文訕謗朝廷,下獄治罪,史稱「烏臺詩案」。蘇東坡死裡逃生,被貶黃州團練副史。已經年過四十的蘇東坡遭此挫折,內心當然有深切的感觸。寫陳季常的時候,不斷凸顯對方,其實也正在不斷的對照自我。他對陳季常的理解,往往也是自我理解的一部份。
最後一段裡,蘇東坡說光州、黃州間多「異人」,這些特異份子往往佯狂垢汙,氣質張狂非理性,美化一點的說法或許是不修邊幅的瀟灑。蘇東坡說他們不可得而見,於是要問問方山子或許見過了吧。「佯狂垢汙」的「光、黃異人」是誰?不正是方山子嗎?不正是中年被貶謫的蘇東坡自己嗎?寫他人的同時,也暗示了自己的心境,蘇東坡確實高明啊。
順帶一提,陳季常的軼聞奇事不只這一樁。蘇軾〈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中寫著:「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陳慥之妻柳氏凶悍善妒,蘇東坡寫詩將陳妻比為河東獅,形象亦極為鮮明。〈方山子傳〉裡陳季常的英雄形象,在另一篇作品中竟成了怕老婆俱樂部的會員了。「河東獅吼」、「季常之癖」後來變成成語典故,蘇東坡摹狀人物的功力可見一斑。
【以古觀今】
傳記作品的書寫重點:寫人物必須從經驗出發
傳記類型的作品,往往要介紹人物的姓氏籍貫、生卒年月、生平行事,以平鋪直敘為主。這樣的寫法固然平易翔實,但卻容易讓人讀了覺得千人一面。就像許多小學生寫自己的爸媽,和別人的爸媽沒什麼不一樣,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人物描寫若是淪於這種境地,或許是因為書寫者本身感官的遲鈍、思想情感的貧乏。
經驗的單調與貧乏,是我們現代生活中最可怕的現象。不管是求學或就業,每一個現代社會體制下的心靈,往往欠缺了創造的勇氣與能力。在人與我何其相像的世界裡,我們不免懷疑,自己的生命還有故事好說嗎?自己的面目,真的和他人不一樣嗎?張愛玲說過:「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欠缺生活體驗,沒有故事好說的人生,我以為是不值得活的。
蘇東坡〈方山子傳〉提醒我們,寫人物必須從經驗出發。擺開俗套,另闢蹊徑。試圖挖掘故事,才能把人物寫得奕奕有神。有時自己的心事說不出口,那麼不妨說說他人的故事。
延伸閱讀
陳芳明,《昨夜雪深幾許》,印刻
劉強,《一種風流吾最愛:世說新語今讀》,麥田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印刻
保羅莫朗,《我沒時間討厭你》,麥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