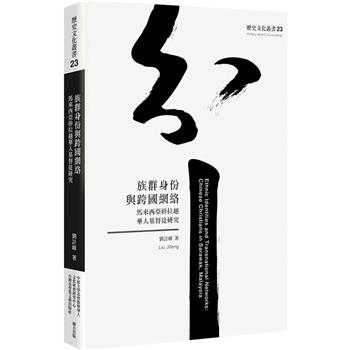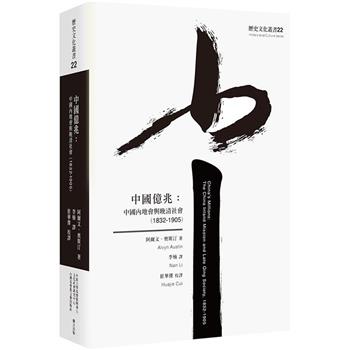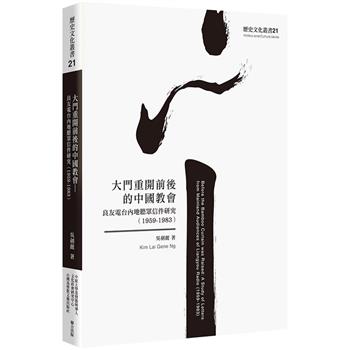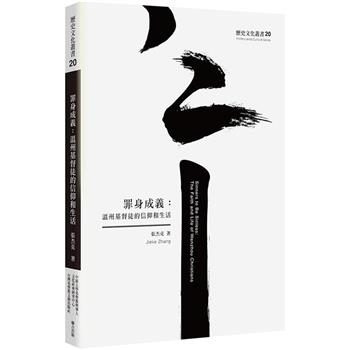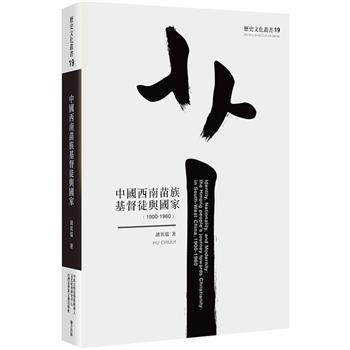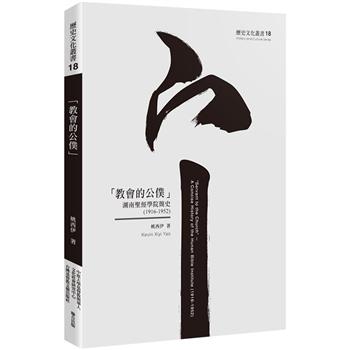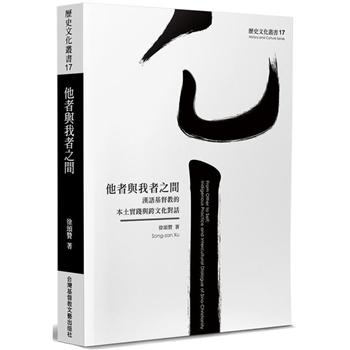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
反智主義是深刻影響中國教會的「原罪性」問題,但至今未有專門討論這一重要課題的著作。作為第一本研究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之專著,本書在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缺。《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首先對中國教會語境中的「反智主義」作出定義並分析了其核心特徵,接著在追溯其歷史淵源時考察了上個世紀對中國教會影響至深的三位教會領袖——倪柝聲、王明道和宋尚節——思想中的反智傾向,然後對中國教會的反智主義作出神學探源,從上帝論、基督論、創造論和人論等幾個方面分析了反智主義的神學根源,最後對中國教會提出建設性提議。本書雖然涉及中國教會歷史,但更多是一本關於神學思想的著作,即對中國教會某個重大問題所作出的神學反思,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是為構建中國教會處境化神學而作的一次努力。
從「滅教」運動到「中國的耶路撒冷」的誕生
中國基督教歷史的研究中,在有意無意間會出現一個斷層,即自1957年至1979年的歷史。筆者從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教會作為一個縮影,追溯被作為「無宗教區試點」的區域,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經歷無情的逼迫,在被稱為「三無」(無教堂、無教牧、無聖經)的時期中,靈活轉型,引來教會的大復興? 本書向我們展示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城市,如何引來全面的關注,幾十年的「溫州熱」,展現教會中的「溫州模式」。在傳統意義上的政策便利、差會支持、教牧領導、經濟支撐等因素盡失時,溫州教會卻能夠在「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之下進行宗教活動,在無數宗教逼迫中堅守信仰立場,在各教會之間實行聯合派單。同時,溫州教會建立了具有溫州特色的牧區管理體制。藉由本書,幫助我們瞭解今日溫州教會諸多現象的根源。
潛存教會的本色語言:周聯華《易的神學》重構
《易》內蘊於中華文化深層,許多成語、典故皆從易經而來。然而,易經的卜筮體裁難免令基督徒有所抗拒。周聯華牧師 (1920-2016) 所撰《易的神學》嘗試以易經的語言素材,對教會闡釋基督教的神學概念,期望能建構本色化的神學;然而以文本批判理論所謂「理想讀者」而言,不熟悉易經文本的建制教會會眾恐怕並非首選。因此本書將既有的易經讀者,即《易》的詮釋群體,視作田立克 (Paul Tillich) 所謂「潛存的教會」(latent church),運用此群體累積的易學知識與概念體系,重構「易的神學」,期望能實現周聯華牧師在中華文化背景下寫作《易的神學》初衷,並能對精神文化的跨界域傳播工作者有所啟發。
族群身份與跨國網絡
東南亞華人基督徒身處高度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情境。馬來西亞是以馬來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華人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處於被動地位,基督教亦是少數派宗教,華人基督徒因此是被雙重邊緣化的群體。然而,華人基督徒群體不必然服從制度性安排,相反,他們積極回應現實困境,大力拓展主體性空間。本書聚焦於處在「邊緣」位置的馬來西亞砂拉越華人基督徒群體,動態地呈現在國家主導的伊斯蘭化背景下,他們如何保持其宗教信仰與族群身份,並拓展跨國網絡,進而理解這一邊緣群體的主體性與能動性。本書是在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接觸區理解華人,但絕非以此去思考「文化中國」的象徵世界。本書指出,以基督教為重要維繫手段的華人社會並非中華文化的海外「延續」,他們雖然身處「邊緣」,卻致力於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中心」。
中國億兆:中國內地會與晚清社會(1832-1905)
奧斯汀所著《中國億兆》一方面在宏觀上展示以中國內地會為代表的基要主義團體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發展歷程,在微觀上聚焦戴德生的傳教助手群體,展示他們身上鮮明的個性和時代特性;另一方面聚焦於該時期基要派基督教在中國本土化乃至變成中國人的基督教的歷程,展示了該過程中,中國內地會鮮為人知的一面。整體而言,《中國億兆》展現了中國某種民間基督教的發展歷史,這種歷史在當今仍有故事在發生,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品格與面貌。
大門重開前後的中國教會
本書旨在以1959 年至1983 年間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信件為基礎,嘗試整理中國教會在大門重開前後處於歷史巨變中的面貌。 早於1949年初,遠東廣播公司以「良友電台」之名,開始藉大氣電波向中國大陸傳送福音節目,成為迄今面向中國廣播最久的福音廣播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教會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在「極左」路線下,連串政治運動開展,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教會在政治風潮下幾至沒頂。數十年之久,中國教會一直隱蔽於竹幕背後,外間無從得知教會及信徒的情況。期間,製作中心設於香港的良友電台從未停止向中國大陸廣播;惟基於種種因素,廣播對象幾乎完全靜默。直至1979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宗教政策亦有所調整,中國教會的大門終得以重開。至此,寄自中國各地的聽眾信件數量陸續增加。這批珍貴的信件,記錄了竹幕低垂期間中國教會的處境及信徒的心聲。本書以1959年至1983年間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信件為基礎,整理大門重開前後中國教會處於巨變中的面貌,在歷史大論述以外提供另一個民間角度。
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1900-1960)
這是一本探討中國西南苗族皈信基督教的專書,論述中國西南苗族在時局的影響下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由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與在來世尋求千禧年的永恆盼望。而這樣的企求又可視為是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所以本書也將這段歷史置於「現代性」(modernity)探討之中。這個身份尋覓的過程,就算到了當代依然可見,在今日中國西南苗族的社群中,基督教依然發揮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力。正如曾在中國西南傳教多年的英國傳教士王樹德所言,基督教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傳播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故事,就像一塊石頭丟入了湖心,激起了層層的漣漪,至今仍然餘波蕩漾。
教會的公僕:湖南聖經學院簡史(1916-1952)
自拙作《為真道爭辯:在華基督新教傳教士基要主義運動(1920-1937)》(香港:宣道出版社)於2008 年問世之後,我一直希望整理和研究1949 年之前中國基督新教基要主義運動的相關機構和人物。這本小書就是沿著這個思路努力的結果。之所以選定湖南聖經學院(湖聖)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對於基要主義運動來說,聖經學校是其最重要的活動平台之一。而湖聖則是一個典型個案。它不僅是基要派的一個神學教育機構,更是基要派事工與活動的一個綜合體。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福音佈道等事工影響之大與其華人教授團隊實力之強都相當突出,比當時號稱基要派神學教育大本營的華北神學院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二,近十年前,我得以在洛杉磯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 圖書館找到了較為完整和系統的相關英文檔案,其中多為當時湖聖與洛杉磯聖經學院(BIOLA) 領導層的英文通信。這項研究雖然醞釀和起步較早,但由於我轉換工作,教學和行政事務繁忙,健康狀況等原因,進展遲緩,時斷時續,中文材料的發掘整理尤為不易。其間我雖然也曾發表了三篇相關論文,但直到2019 年,蒙我所任教的歌頓—康維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批給學術假期,我才得以進一步充實材料,最終定稿。在這本小書中,我希望能夠勾勒出湖聖歷史的粗線條,並把湖聖置於國際基要派聖經學校運動的大背景下略作考察與評價。本書的大標題「教會的公僕」經常出現於1930 年代《佈道》雜誌所刊載的「湖南聖經學院工作概況」及「招生廣告」, 能表達該院的身份和使命。正如我在導論中所言,在我看來,此書只能說是這個課題研究的第一步。切盼此書的問世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引起學界同仁,尤其是華語學者們對中國基督新教史上眾多基要派聖經學校的關注,一同把此領域的研究推向深入。這也是為什麼我特意選定以中文發表此書的主要原因之一。湖聖自1916 年正式在長沙建校,到1952 年關閉。它的歷史正好涵蓋了中國基督新教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時期。就教會的外部大環境來說,中國社會歷經晚清、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南京十年、日本侵華,到國共內戰,見證了十分動盪不安的時代。就教會自身的發展和演變而言,則是本土教會的成熟和自立,從傳教到教育、醫療等各項的事工的成長,多數都可圈可點。尤其是這個時期教會的神學和事工明顯呈現多樣化的趨勢。本土復興運動風起雲湧,新宗派紛紛出現。隨著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在華傳教運動的演變,以及北美教會內基要主義與自由主義(現代主義)鬥爭的激化,中國教會和在華西教士群體在二十世紀初也大致分化為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陣營。雙方圍繞著聖經權威等教義問題和傳教運動方向與重心等議題發生了明顯對立。可以說,湖聖的歷史從多方面反映了中國教會這個時期的一些主要發展趨勢。
他者與我者之間:漢語基督教的本土實踐與跨文化對話
本書是徐頌贊的學術論文集,收錄了從2013 年到2019年創作和發表的學術文章,以及主題相關的報刊文章、演講稿和紀念文。總體而言,這些文字都是圍繞「漢語基督教的本土實踐和跨文化對話」這一核心議題而展開。雖然,這些文章的論述風格和研究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內在的關懷是相通的。這份相通的關懷,就是將基督教與中華文化與社會的關係,視為「他者」與「我者」的關係。它們同時是彼此的「他者」,各從對方身上汲取經驗和他者視角,展開融「他者」入「我者」的交涉過程,進而形塑出新的實踐主體──「漢語基督教」。圍繞「漢語基督教的本土實踐和跨文化對話」這個核心,作者試圖從中國與西方、本土與全球、傳統與現代等角度,來分析基督教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中的本土生成與演變,包括跨文化交流、融合民間生活、塑造知識階層、參與公共社會等方面的經驗,並且從歷史、文學、宗教學、人類學的跨學科維度,分為四個部分來反思基督教的中國社會處境和跨文化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