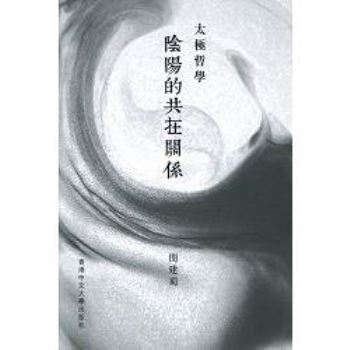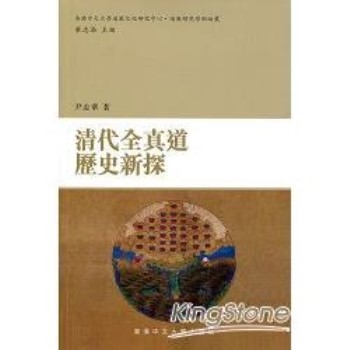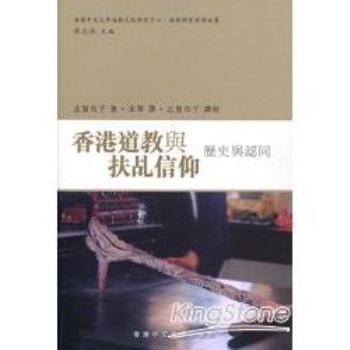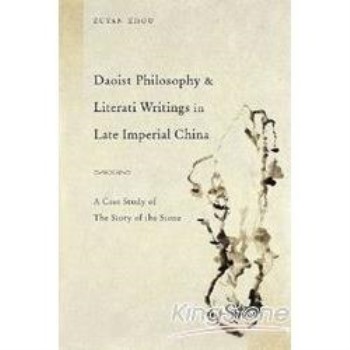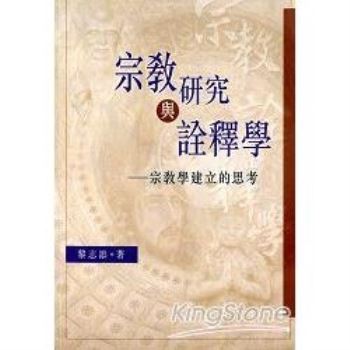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電子書】太極哲學:陰陽的共在關係
在人生的旅途上,人所作出的行動選擇是「對」或「錯」往往乃視自己能否適當的調整與本身有關的「共在」關係而定,這些共在關係例如有個人與群體,理性與感性,物質與精神,善與惡,有與無,表與裏,正與不正,私利與公利,精明與單純,進與退,動與靜,合與分,剛與柔,損與益,得與失,中與偏,我與真我,對政治、經濟與社會境況的應對等。人的行為例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進退有度」,「剛柔轉化」,「剛柔配對」,「外柔內剛」,「外剛內柔」,「剛柔相濟」,「以柔制剛」,「以剛制柔」,「向善去惡」,「堅持與靈活」等等都需要具有「適時」、「適位」與「適中」的判斷力與適應力。而要提高人的認識能力就必需具有辯證力與推演力,才能引導出適當的判斷力。《易經》的太極思維就是辯證思維,易卦與太極陰陽圖像是辯證思維的分析工具,能提高人對境況與情景變動的辨識力。人的行為可從太極思維的角度來觀察與分析,太極思維包含了陰陽思維。當觀察的對象是一個整體時,就是整體思維「一」的觀念。當對觀察的對象作深層的分析時就轉化為「一分二」的多角性陰陽思維。通過太極與陰陽思維的分析,就能對人的行為與有關的共在關係具有較深層的認識,人有了對共在關係的認識,就會在「做人」與「做事」方面有了原則,有助於自身行為的適當抉擇。這是一本談論辯證力、變通力與修養的書,也是一本談思考方法的書。
【電子書】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
全真道興起於金朝,從元代至今為道教的兩大主流教派之一。學術界對全真道的研究成果,過去多集中在金元時期,而明清時期全真道的研究則比較薄弱。本書作者充分利用地方志、道教名山宮觀志、碑刻、清人文集、教內宗譜等文獻,對清代全真道的發展歷史作了全面系統的考察,資料翔實,論述謹嚴。
【電子書】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
在香港市區林立的唐樓中,分布著一批俗稱「道堂」或「道壇」的宗教組織,從事「扶乩」這一中國古老的降神術以及誦經活動。這類屬於道教系統的宗教團體,由於並沒有十分明顯的外部特徵,歷來不太為人所知。本書作者前往道堂實地參與觀察、訪談調查,結合道堂發行的刊物以及在香港、廣東、日本所收集的地方志、文 史資料、筆記、善書等文獻資料,從信仰、功能、歷史背景與展開過程四個層面描述道堂的全貌。本書通過具有歷史視域的民族志的?述方式,揭示出香港道堂和近現代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宗教、社會、歷史等各種因素間的錯綜關係。
【電子書】Daoist Philosophy and Literati Writings in Late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his volume firs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Daoism in late imperial period through the writings of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s. In such a cultural context, it then launche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aoist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narrative masterpie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the inscriptions of Quanzhen Daoism in the infrastructure of its religious framework, the ideolog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Daoist concepts of chaos, purity, and the natural, as well as the Daoist images of the gourd, fish, and bird. Zhou presents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Daoist philosophy both in th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Stone, and the literati culture that engenders it.
【電子書】宗教研究與詮釋學:宗教學建立的思考
十九世紀西方的啟蒙運動與科學理性主義,為其後的宗教研究提供了研究範圍、對象及方法,俾使它成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其中一們學科。 但是,把理性作為宗教研究的工具,結果不是錯誤理解宗教,便只是觸及宗教的表面。 當代西方學者以重新思考宗教研究的方法,並嘗試採用詮釋學(Hermeneutics)的理論探索宗教現象。 詮釋學是強調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哲學。 透過理解,世界、社會、文化和宗教就能夠建立一種互相尊重的意義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