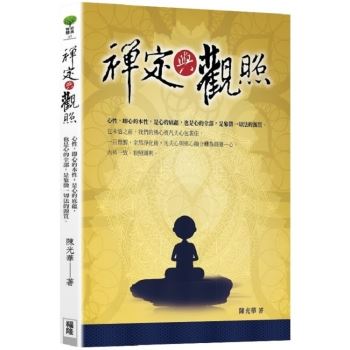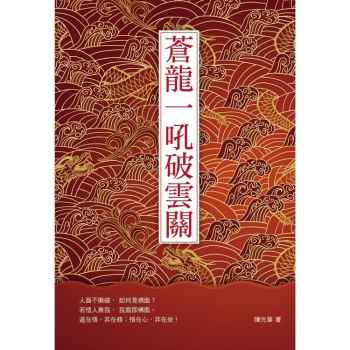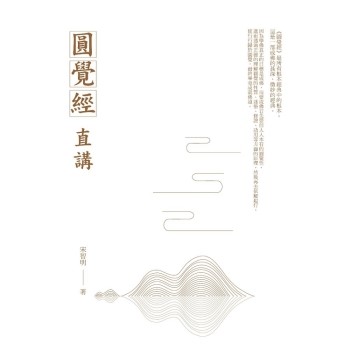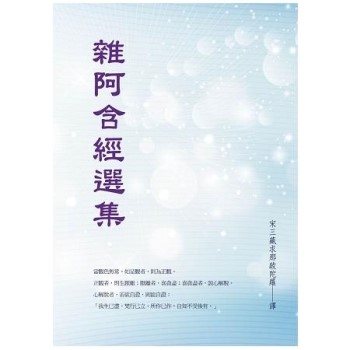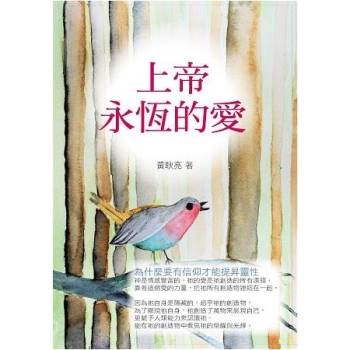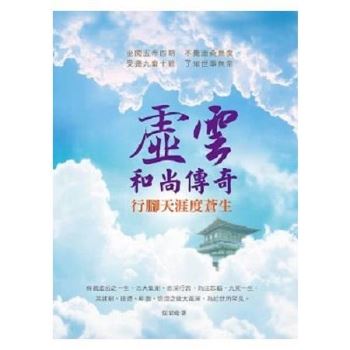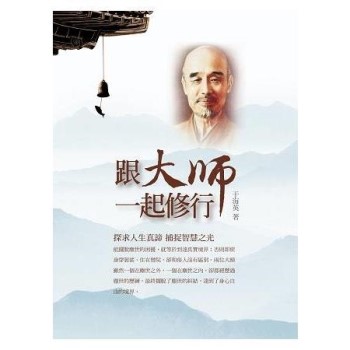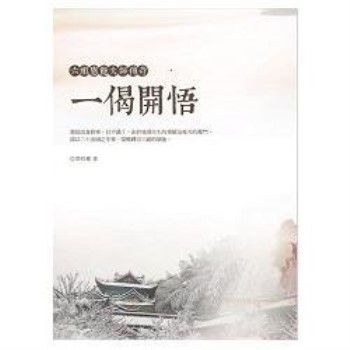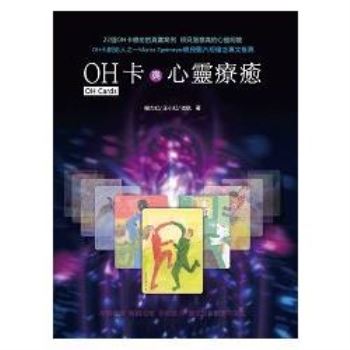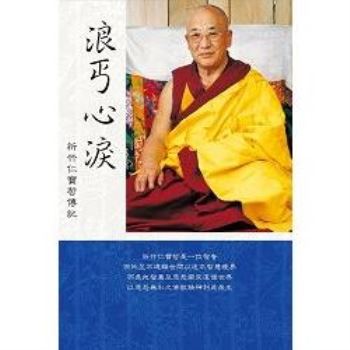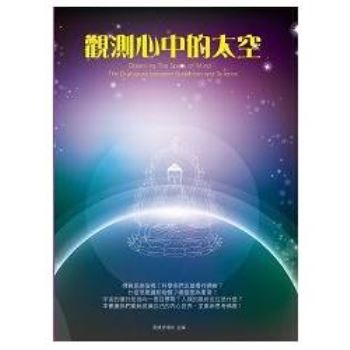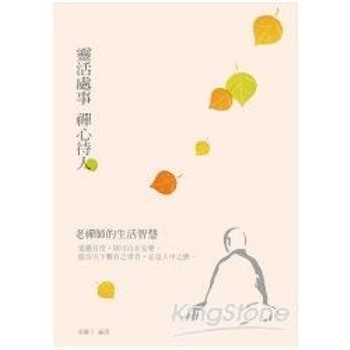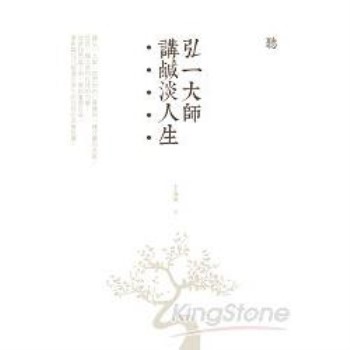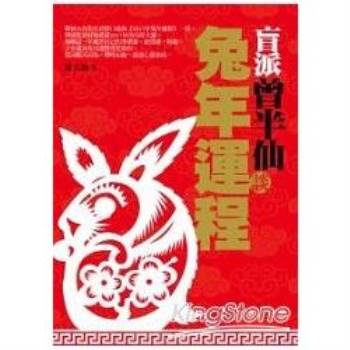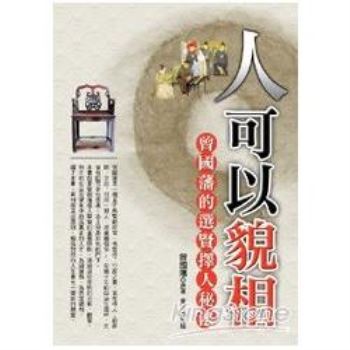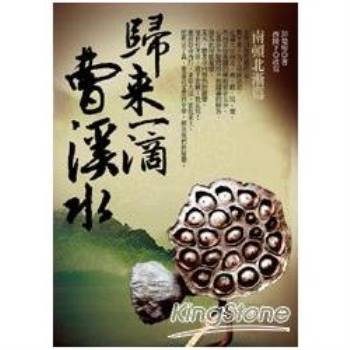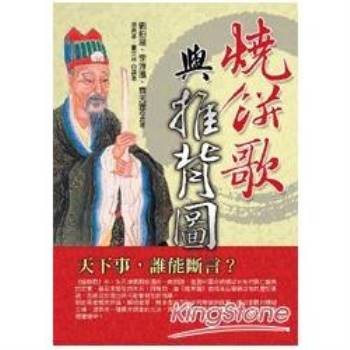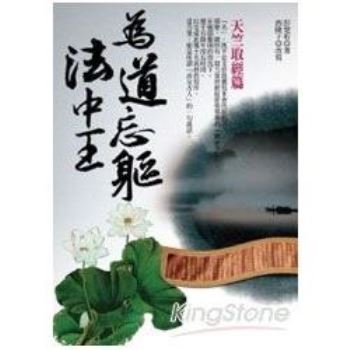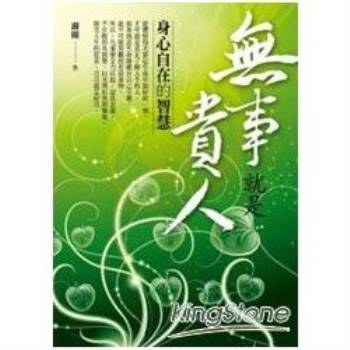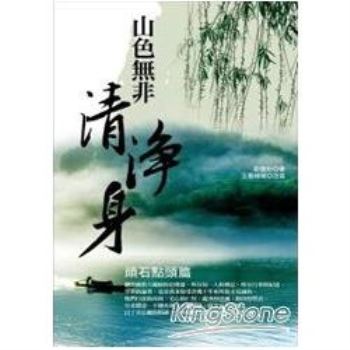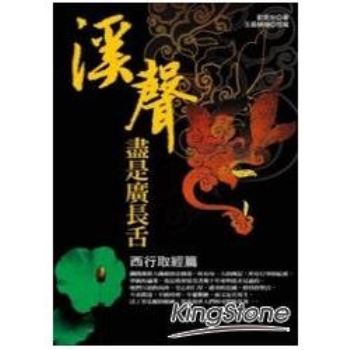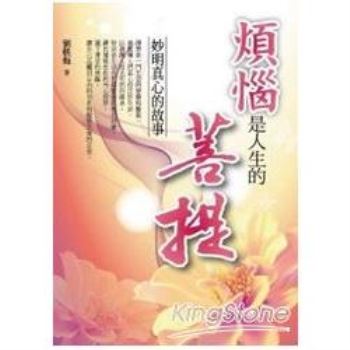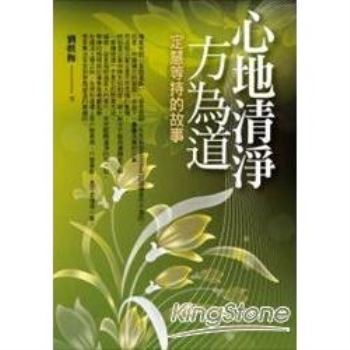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電子書】禪定與觀照
心性,即心的本性,是心的底蘊,也是心的全部,是象徵一切法的源質。在未悟之前,我們的佛心被凡夫心包裹住,一旦覺醒、全然淨化後,凡夫心與佛心融合轉為圓覺一心,內外一致、寂照圓明。生活的規律如同鐘擺一般,每天都有瑣碎的事,雖是固定,總是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未解的問題,一件接一件,讓你忙個不停。每一次我們都可讓自己的心開放或封閉,當自己覺得已經無法處理任何狀況時,其實此刻正是探索內心最好的機會。若情況實在太糟了,沒有辦法掌控局勢,無法全身而退,所有努力都白費了,真的動彈不得了……,此時照著鏡子,看看自己,是一隻狗熊?還是一條龍?不論你怎麼把鏡子翻來翻去,狗熊還是狗熊,龍還是龍!要不就接受眼前事實,要不就推開不看。
【電子書】蒼龍一吼破雲關
人面不撕破, 如何見佛面?若悟人無我, 我面即佛面。道在悟,非在修;悟在心,非在坐!生活,只是要你如何保持,每一個當下的心地清明。而非拼個你死我活,或詩歌無病呻吟,或描繪出虛擬幻境。生命,只是要你如何開啟,眼前展示每一個現量的智慧覺醒。破除這VR投影的境。活的自在,無拘無束,但盡凡心,別具聖解。勿加入個人意識註解!使命乎?天命乎?
【電子書】蒼龍一吼破雲關
人面不撕破, 如何見佛面?若悟人無我, 我面即佛面。道在悟,非在修;悟在心,非在坐!生活,只是要你如何保持,每一個當下的心地清明。而非拼個你死我活,或詩歌無病呻吟,或描繪出虛擬幻境。生命,只是要你如何開啟,眼前展示每一個現量的智慧覺醒。破除這VR投影的境。活的自在,無拘無束,但盡凡心,別具聖解。勿加入個人意識註解!使命乎?天命乎?
【電子書】圓覺經直講
《圓覺經》是所有根本經典中的根本,這是一部成佛的甚深、微妙的經典。 因為學佛真正的目標是成佛,而要成佛首先要信人人本有的圓覺性,進而透過正確的理解圓覺的性質、迷悟、修證、功用等方面的原理,然後再去依解起行,使行行歸於圓覺,最終畢竟成就佛道。 這部經是無上的微妙佛法,是佛果覺的全體流露,是稱性之談,所以聽聞的人應當離開一切知見,所謂凡夫貪著的知見、外道心外求法的知見、二乘偏空狹劣的知見、菩薩著相行法的知見,以及宗派與法門的知見等等,應放下一切知見,無心而聽,無為而入,自然與佛義打成一片而相應。因此,對於過去的人生經驗、各種的知識、虛妄的觀念、修持的體會,都不能執著而成對比,或者牽強附會,比量佛義,產生自以為是的妄覺,應在不執著、不比量的情況下,善用一切經驗與知識,深入佛智,一一化解,而成為有力的法種,助成佛道之行。
【電子書】雜阿含經選集
《雜阿含經》為南朝劉宋求那跋陀羅在元嘉二十年(443年)於楊都祇洹寺口述,寶雲傳譯漢文,慧觀筆錄,共五十卷。其原本來源不明,《開元釋教錄》記載,此本就是法顯由錫蘭取回的雜阿含梵本;也有可能是求那跋陀羅由天竺或錫蘭帶來中國。現代在高昌及於闐發現梵文片斷,與現存《雜阿含經》一致,因此可以推斷它是由梵文本譯出,屬於根本說一切有部。(維基百科) 《雜阿含經》是禪修的經典,文章精簡雜錄,現存一千三百五十九篇經文,乃佛陀在世時對弟子所說的重要教理,以「五蘊」、「六入處」、「十八界」為禪觀,對「緣起」、「四聖締」的闡釋,了知一切法是「無常」、「苦」、「空」、「無我」,從而獲得真正的解脫。現代學者根據《瑜伽師地論》有關記載將其歸納為七誦:「五陰誦」、「六入處誦」、「雜因誦」、「道品誦」、「佛所說誦」、「弟子所說誦」和「八眾誦」。(維基百科)
【電子書】上帝永恆的愛
1. 信仰 信仰不應該是堅持於教義、教條、形式或儀式。不應該像蒙著面紗、模糊不清或盲從。今日的信仰,應該是直接、正向、沒有被懷疑的空間及模糊性。信仰超越於僅承認並知道我們與上帝(創造主)間的一種關係,或意識到上帝對宇宙萬物的統權,信仰應該是我們藉由上帝所派遣的聖者,對他們的認同所建立的盟約。也就是說我們接受聖者及祂的教導,也就等於認可上帝並接受上帝的教導。盟約是一種接受上帝對我們今生的計畫、並且願意遵守祂的計畫,活在祂的計畫及促成祂對我們的計畫。這表現在我們將靈的成長視為今生的任務及追求靈的提升。 對信仰的瞭解,將提供我們對信仰靈 (spirit of faith) 的認識。信仰靈是一個動力及力量,幫助我們完成上帝對我們今生的計畫。換個方式說,在這信仰靈裡,我們會變得有力量面對事情與挑戰,聖靈是幫助我們靈成長的導師(我們不能與上帝直接溝通,但透過聖靈,上帝可以將祂的訊息傳遞於人類),獲得聖靈的幫助需要透過信仰,正教才是信仰中心,唯有信仰正教才能獲得聖靈的引導、上帝的開啟。聖靈不專屬於某一宗教,真正走在信仰道路上的人,是可以感覺到祂的帶領。聖靈的能力遠超於人類的理解,人類在創造界是無價的,因為只有人類可以接受聖靈的引導,感知聖靈的引導,將可更篤定我們對自己價值,且更珍惜活在地球上的日子。 巴哈歐拉說今天上帝認可的正教包括印度教、猶太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巴哈伊等。透過這些宗教的教導,才能認識真理,並且正確的認識靈。幫助人類淨化心靈,並提升靈性品質是每一正教的工作。所以真正走在信仰道路上,是走在提昇心靈品質的道路上,是需要時時反觀自己的行為舉止並修正之。此外,信仰是找回我們的自性,恢復神創造人類的美善,是回歸 (趨向)上帝之道,這是信仰與迷信的區別。 2. 靈是什麼? 打個比方,它好比地心引力,我們看不見,但當蘋果掉下來時,我們看到它起作用。靈對我們生命引響作用就像地心引力,他是一股力量(force),也是一種能量(power),它左右生命的誕生與延續,也左右我們思想、決定與作為。在自然界,它是宇宙星雲不斷凝聚變動的那股隱藏力量,在植物是生長力量。因為靈是看不見的存在,所以認識靈是在觀察「有」的變化中,去感覺與體認它的存在。 《道德經》云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也就是說,靈是「無」,它的奧妙可在觀察「有」的稀徼去體會。現象界(有)是受著靈(無)的影響與牽動,「無(靈)」可以暸解為創造本體,而「有」可以暸解為萬物根源,是靈的廣大無邊作用。一個是「道」的本體,一個是「道」的作用,這兩者雖有著不同名稱,卻都出於創造主,是創造界及宇宙的奧秘。 宗教信仰裡,靈性的開發就是在認識「靈」及靈起作用的奧妙,讓它成為生命之泉。因為靈是看不見的力量,所以要藉由「有」的現象,來察覺體會它的存在及變化的奧妙。但如果我們的心依附著凡塵事物,過於執著感官的感性知識,就會有障礙去理解體悟靈的理性知識 (真理),所以心的淨化,是為去除那會影響我們獲取理性知識的障蔽。在宗教裡修行、心的沈澱是非常重要的過程,當障蔽我們看到真理的塵世依附(執著)漸漸去除後,真理與靈的奧祕就會漸漸顯現。我們的心就像一面明鏡,當我們有執著時,明鏡就被塵埃蓋住,心靈淨化就是在擦拭塵埃,名鏡乾淨了,心就能反射出真理,也就是在心靈之鏡上看見真理。心淨化了,我們的洞察之眼就明亮了,就會看到我們的「心」及「靈」,就會知道我們本來的面目。 阿博都巴哈告訴我們,靈在進化的層次上可分為四層次,依序為礦物(mineral kingdom)、植物( vegetable kingdom)、動物( animal kingdom)、及人類( human kingdom)。「靈」在礦物界裡,代表的是一種凝聚、黏著力;在植物界裡,代表的是凝聚與生長力;在動物界裡,代表的是凝聚、生長與感官知覺能力(這感官是直覺與對狀況的本能反應);在人類,除具有動物的能力外,讓人類在創造界成為得天獨厚的是靈魂 (或稱理性靈)的大能。Henry Weil 在《比你的靜脈更近(Closer Than Your Life Vein) 》一書中,將靈魂的大能(the powers of the soul)分為七項:(1) 身體的協調性 (The coordinator of bodily functions);(2) 心智能力 (The mental faculties of the soul);(3) 內在洞察之眼 (The faculty of inner vision);(4) 個人獨特性(Individuality);(5) 本質明鏡 (The mirrored reflection of your moral choices);(6) 靈裡的快樂 (Spiritual happiness);(7) 靈魂不朽性 (Immortality) 靈與魂的用語,在很多地方一直很模糊,有時被視為同一樣東西,但它們是有區別的。「靈」代表的是能量的來源(本質),「魂」代表的是屬性(特性);靈與魂之間的關連性,就如太陽(相對於靈)與太陽的輻射(相對於魂),太陽和它的輻射是很難被分開來看的,靈和魂也很難被分開來看的,所以我們常常把靈與魂說成一體,也就是「靈魂」。當我們這個生命有著存在的理由時,「靈魂」在「體(身體)」上就有關聯性並有了作用;當「靈魂」停止了在「體」的關聯性與作用時,「體」的作用就終止,也就是我們稱的死亡。在「體」消失後,「靈魂」將繼續存在。我們這身子的存亡,代表的是這「靈魂」在「體」的關聯性存在與否,所以認識真正生命的意義,也就要認識「靈魂」存在的意義。靈魂大能的認識、開發與靈性的提昇,是我們今生要學習的重要課題,因為靈性的提升,它攸關著我們每個人的來世去向,也就是提升的程度,將決定個人靈魂的下一站旅程起點。此外,認識了「靈魂」才算真正認識了自己,「我」的存在是包括「體(身體)」與「靈魂」;「體」是有時空限制的,而「靈魂」是超越時空的,靈魂的重要性遠超過身體的重要性。千萬別錯把身體當所有,這將錯過我們今生的真正存在目的。 身體存在的實相,是我們必須每隔一段時間進食以供給能量的來源,使它能正常運作;人的靈也有類似的實相,須要常常將我們的心靈轉向上帝,要與我們存在的源頭交流,才能獲得靈性糧食的供應。上帝的顯聖者在宗教裡都告訴我們相同的實相,要走在上帝的道,面向真理之陽與慈悲之水,就能滿足靈性糧食的供應。節制的飲食是為了健康的身體;有戒律的生活是為了維護健康的靈魂。這是實相,也是真理。 人的靈魂(理性功能)來自上帝眾界。人身上的毎一個功能,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均是靈魂的顯示。例如,每一種感官的能力都來自靈魂,每一種靈性品質都由它產生。然而,一個人的內部的所有這些功能的總合並不等於靈魂。靈魂是不可知的,如果一個人仔細思考這一主題直至死去,他也永遠不可能理解自己靈魂的本質,或者猜透珍藏其中的奧秘。 (巴哈歐拉) 儘管我們無法了解自身靈魂的本質,但在有限範圍的認識下,就可一窺上帝創造的奧妙及祂的偉大。 3. 我的概念 將人跟動物區分開的人性靈就是理性靈魂(哲學術語),而這兩個名稱──人性靈及理性靈魂──指的是同一事物。前面我們提過靈魂的大能,這七項大能裡,讓我們先來簡單談談身體的協調性與心智能力兩項。 身體的協調性(心跳的調整與身體化學物質的釋放,以因應身體需求狀況或器官與器官間的協調性…),是身體存在才有的作用。試想想,這能力並非人的意識在掌控,那股協調作用的來源動力,是來自於我們靈性的力量。透過身體各器官及來自靈性的協調力量,這個身體就能活動及有行為的表現。然而,身體死亡後這大能就不再起作用,身體是因緣而有,因緣有的是為了展現無(靈)的作用。而心智能力則與我們的腦作用息息相關,腦部受傷的病患,身體的協調性仍存在,但傳遞心智能力的管道卻受阻礙,這不表示心智能力沒有作用,只是表現起作用的管道受阻。這障礙使心智能力作用,無法藉由身體動作表現出來,有些病患只是部分的能力受阻,這也是為什麼有些腦部受傷者仍能聽見並有情感的表達。藉由這兩個例子,希望讓各位思考我們稱「我」的這個身體,真的只是身子的作用嗎?靈藉由這個身子來起作用,以展現它「無」的存在性,就像重力藉由蘋果來展現它「無」的作用,我們這個身子的存在,就是在展現靈性的作用。這也是創造界「有」與「無」的奧妙。 至此,很清楚的我們可將「自我」分成身體與靈魂兩部分。不過這裡,我們想將「自我」分成三個部分來看:肉體、心與靈魂。「心」被特別區別出來,是因為它可被視為肉體和靈魂之間的一個橋樑(對一個腦部無受損的人,這橋樑是起適當作用的),它連結著肉體和靈魂,是靈魂大能在身體起什麼樣作用的管
【電子書】虛雲和尚傳奇:行腳天涯度蒼生
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 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 綜觀虛公之一生,志大氣剛,悲深行苦,為法忘軀,九死一生。 其建樹、道德、年齒、悟證之偉大高深,為近世所罕見。 他的出生,是一團肉胎;他的出家,單純的只是因為他喜歡聽佛。三年來,他三跪九叩,一路從浙江走到五台山,靠的全是他想報父母養育之恩的堅定信念。六年來,一路從中原走到西藏再到印度,憑藉的只是他虔誠的信仰。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虛雲老和尚的一生,沒有所謂的神蹟,只有一僧一缽一步一腳印,和無比堅定的信心。 虛雲和尚,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泉州。歿於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年),凡一百二十歲,生平歷經清朝、民國建立、二次大戰及中共政權統治。 成長於動盪之中,畢生興佛學、訂新規、修佛寺古剎,把亂世中的佛教重新組織、興盛,並全力促成中國佛教會,誠為當代佛教高僧。 他的出生,是一團肉胎;他的出家,單純的只是因為他喜歡聽佛。三年來,他三跪九叩,一路從浙江走到五台山,靠的全是他想報父母養育之恩的堅定信念。六年來,一路從中原走到西藏再到印度,憑藉的只是他虔誠的信仰。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虛雲老和尚的一生,沒有所謂的神蹟,只有一僧一缽一步一腳印,和無比堅定的信心。
【電子書】跟大師一起修行
探求人生真諦 捕捉智慧之光 能擺脫塵世的困擾,就等於到達真實境界;否則即使身穿袈裟、住在僧院,卻和俗人沒有區別。兩位大師雖然一個在塵世之外,一個在塵世之內,卻都經歷過塵世的歷練,最終擺脫了塵世的糾結,達到了身心自由的境界。 李叔同是關注世事卻又遠離世事的人,他在繁華之外看繁華。所以他多關注於人自我的精神世界。精神富足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足;否則即使富如國王,也會貧如乞丐。 南懷瑾是身在繁華而又笑看繁華的人,他是繁華世間的智者,得享繁華卻又不被繁華所累。如果說李叔同是隱居的禪師,那南懷瑾便是入世的佈道者。他更關注自身與外界的關係,在他看來,幸福的人生不是生存在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中,而是融入外界,在集體中體會融洽。
【電子書】宇宙大調和
凡間的規律.大轉輪 修的東西是這樣,每個人只要是發現到有這個東西,然後有形的東西給他們看,他們這無形的能量就會出來,才會用心去走,去找他的靈根、靈根。 這個宇宙間每樣東西、每樣人物,靈性的運化,運化每樣東西向大宇宙的調和,都一直在調和,調和到大同的境界。每個神明、人呀、動物各方面到最後能接近較融洽,把宇宙空間變成比較美好祥和的大同世界。 各方面的想法,你要去改變他,要去想他,這個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不是說,要給他錢,給他賺錢這反而比較快,更容易,就是要給他靈性恢復到自然,能修到長壽,這比較不容易,也比較難。因為這牽涉到人的過去世的靈性,和他一些過去世修為、罪惡及因因果果都有關係。
【電子書】一偈開悟:六祖惠能大師傳奇
惠能出身貧寒,目不識丁,由於他那天生的秉賦及後天的奮鬥,卻以二十出頭之年華,榮膺禪宗六祖的頭銜。 本書以東土禪宗六祖惠能大師,把印度式的佛教變成中國式的佛教,獨創中國禪學一事為主線,根據《六祖壇經》、《唐史》、《佛典》並結合民間傳說、佛教故事進行構架創作。透過對惠能、惠能的恩師、親友、信徒及官紳學子等三十多個主要人物的刻劃,反映著唐代初期的社會風貌,尤其是佛教蓬勃發展的盛況;宣傳了救世濟人、揚善抑惡、艱苦創業的精神。
【電子書】OH卡與心靈療癒
OH卡心靈圖卡可以應用於: 心理療癒、自我探索、 心靈溝通、潛能開發、 創意聯想、提升直覺、 精神分析、親子互動、 藝術治療、團體培訓 前言:照見潛意識的心靈明鏡—OH卡 楊力虹/文 2009年3月,身心靈整合家園在北京剛開業的那天,塔羅女巫、靈性才女孟想來找我玩,談她們除影響力已經很大的《OUT》雜誌之外,要做一本向內在探索的(後來的《心探索》)雜誌的構想,我極力擁護、贊同,我用直覺告訴她:中國人,往內在探索,是時候了。 那是一個溫暖的春天,一身仙衣、一簾長髮的孟想背著她的牌袋,飄然而至,我們坐在家園的塌塌米上,玩各種卡。 那天,孟想的卡裡有許多色彩斑斕、造型各異、有未見過的吉普賽卡等,但我,只記住了OH卡。因為那天玩OH卡時,對抽的圖片和文字,我都沒有任何感覺,只覺得這種圖文組合的形式有意思。 就此,這顆種子播下了。 後來家園合作的老師中,不少老師都用到了OH卡。再後來,因緣和合,OH卡原創者Moritz Egetmeyer來中國開課時,我參加了並系統地學習了OH卡系列。 這位現住在德國黑森林的心理學家,1982年,他在加拿大攻讀人本心理學碩士時,跟墨西哥裔藝術家Ely Raman共同研創出OH卡。它由88張圖卡和88張字卡組成,共176張卡片可做圖文變化,有7744種可能性。OH卡屬於「自由聯想卡」、「潛意識投射卡」的系統,它運用了聯想法、構造法、完成法、轉念法等投射技術。它是簡單而實用的直覺聯想工具,它可用團體培訓、自我探索、心靈溝通、潛能開發、敘事、完型、行為、釋夢、轉念作業、自由書寫等療法裡,也可以用於創意聯想、親子互動、藝術治療、家族系統排列與團體遊戲裡。 OH卡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自助助人的工具,它是照見潛意識的心靈明鏡,讓所有之前我們沒有看見的部分都清晰地呈現,它的力量強大到我們除了這句「OH」歎外,無處逃遁,唯有面對。 我除了開設「OH卡心靈明鏡工作坊」、「心靈圖卡實戰運用工作坊」外,還大量地把OH卡應用到我的「關係工作坊」、「擁抱內在孩童深度療癒工作坊」、「轉身,走向愛親密伴侶工作坊」裡,當然,在身心靈整合療癒個案中,也非常廣泛地運用。一般用OH卡呈現潛意識深處的真相,同時,配合繪畫、音樂、行星能量頌鉢.、泛音詠唱、舞蹈、催眠、家排、戲劇表演等工具來陪伴、支援案主或學員。 OH卡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印證「萬法唯心」的最佳工具。同一張圖卡被同一位案主在不同時段詮釋時,圖像和意義是不同的。
【電子書】OH卡與心靈療癒
OH卡心靈圖卡可以應用於: 心理療癒、自我探索、 心靈溝通、潛能開發、 創意聯想、提升直覺、 精神分析、親子互動、 藝術治療、團體培訓 前言:照見潛意識的心靈明鏡—OH卡 楊力虹/文 2009年3月,身心靈整合家園在北京剛開業的那天,塔羅女巫、靈性才女孟想來找我玩,談她們除影響力已經很大的《OUT》雜誌之外,要做一本向內在探索的(後來的《心探索》)雜誌的構想,我極力擁護、贊同,我用直覺告訴她:中國人,往內在探索,是時候了。 那是一個溫暖的春天,一身仙衣、一簾長髮的孟想背著她的牌袋,飄然而至,我們坐在家園的塌塌米上,玩各種卡。 那天,孟想的卡裡有許多色彩斑斕、造型各異、有未見過的吉普賽卡等,但我,只記住了OH卡。因為那天玩OH卡時,對抽的圖片和文字,我都沒有任何感覺,只覺得這種圖文組合的形式有意思。 就此,這顆種子播下了。 後來家園合作的老師中,不少老師都用到了OH卡。再後來,因緣和合,OH卡原創者Moritz Egetmeyer來中國開課時,我參加了並系統地學習了OH卡系列。 這位現住在德國黑森林的心理學家,1982年,他在加拿大攻讀人本心理學碩士時,跟墨西哥裔藝術家Ely Raman共同研創出OH卡。它由88張圖卡和88張字卡組成,共176張卡片可做圖文變化,有7744種可能性。OH卡屬於「自由聯想卡」、「潛意識投射卡」的系統,它運用了聯想法、構造法、完成法、轉念法等投射技術。它是簡單而實用的直覺聯想工具,它可用團體培訓、自我探索、心靈溝通、潛能開發、敘事、完型、行為、釋夢、轉念作業、自由書寫等療法裡,也可以用於創意聯想、親子互動、藝術治療、家族系統排列與團體遊戲裡。 OH卡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自助助人的工具,它是照見潛意識的心靈明鏡,讓所有之前我們沒有看見的部分都清晰地呈現,它的力量強大到我們除了這句「OH」歎外,無處逃遁,唯有面對。 我除了開設「OH卡心靈明鏡工作坊」、「心靈圖卡實戰運用工作坊」外,還大量地把OH卡應用到我的「關係工作坊」、「擁抱內在孩童深度療癒工作坊」、「轉身,走向愛親密伴侶工作坊」裡,當然,在身心靈整合療癒個案中,也非常廣泛地運用。一般用OH卡呈現潛意識深處的真相,同時,配合繪畫、音樂、行星能量頌鉢.、泛音詠唱、舞蹈、催眠、家排、戲劇表演等工具來陪伴、支援案主或學員。 OH卡的有趣之處在於:它是一個印證「萬法唯心」的最佳工具。同一張圖卡被同一位案主在不同時段詮釋時,圖像和意義是不同的。
【電子書】浪丐心淚:祈竹仁寶哲自傳
祈竹仁寶哲是一位智者, 但他並不遁離世間以追求智慧境界, 而是把智慧及慈悲帶來這個世界, 以慈悲無私之佛教精神利益眾生。 祈竹仁寶哲為藏傳佛教格律派高僧、四川名剎大藏寺之法台及著名醫師,生於一九三六年四川阿壩州,十歲於大藏寺出家修學三藏佛法,同時亦隨名師習醫多年,後入位列世界三大佛教學府之色拉寺學習至考取「格西」學位(相當於佛學博士學銜),並取得政府認可之傳統西藏醫學醫師資格。 在傳統上,本來只有具德大師之輩的生平才會立傳及流傳,後世讀者可由閱讀這些大德的傳記而對佛法生出敬重之心。 我只是一個凡夫,一生中並無任何足以立傳的成就。在這本或許會引人恥笑的自傳中,所記載的只不過是一位平凡僧人飄泊大半生的平凡故事,絕對不可與歷代大師傳記相提並論,其著寫的目的,亦僅僅是讓非藏族的讀者,聊以瞭解一下西藏文化與藏傳佛教僧人生活的點滴而已。 近年來,由於祖庭大藏寺僧眾及各地弟子的請求,同時為了避免各國弟子及故鄉的人對我生平的失實渲染,我用上了一點時間,由我依回憶口述,林聰、達華譯師及卡瑪仁青比丘筆錄及整理,配合林聰十多年來抄錄而成的片段,最終才結集成為這本自傳。
【電子書】浪丐心淚:祈竹仁寶哲自傳
祈竹仁寶哲是一位智者, 但他並不遁離世間以追求智慧境界, 而是把智慧及慈悲帶來這個世界, 以慈悲無私之佛教精神利益眾生。 祈竹仁寶哲為藏傳佛教格律派高僧、四川名剎大藏寺之法台及著名醫師,生於一九三六年四川阿壩州,十歲於大藏寺出家修學三藏佛法,同時亦隨名師習醫多年,後入位列世界三大佛教學府之色拉寺學習至考取「格西」學位(相當於佛學博士學銜),並取得政府認可之傳統西藏醫學醫師資格。 在傳統上,本來只有具德大師之輩的生平才會立傳及流傳,後世讀者可由閱讀這些大德的傳記而對佛法生出敬重之心。 我只是一個凡夫,一生中並無任何足以立傳的成就。在這本或許會引人恥笑的自傳中,所記載的只不過是一位平凡僧人飄泊大半生的平凡故事,絕對不可與歷代大師傳記相提並論,其著寫的目的,亦僅僅是讓非藏族的讀者,聊以瞭解一下西藏文化與藏傳佛教僧人生活的點滴而已。 近年來,由於祖庭大藏寺僧眾及各地弟子的請求,同時為了避免各國弟子及故鄉的人對我生平的失實渲染,我用上了一點時間,由我依回憶口述,林聰、達華譯師及卡瑪仁青比丘筆錄及整理,配合林聰十多年來抄錄而成的片段,最終才結集成為這本自傳。
【電子書】頌鉢與身心靈整合療癒
封面文案: 呂啟仲老師 強力推薦 在焦慮、抑鬱、躁狂、恐懼……各種情緒失控的今天,頌鉢的出現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紅塵裡安頓身心的最佳工具。 封底文案: 與身體共振之聲 與心靈碰觸之音 帶你走上回歸本心之路 當你看見這些文字和圖片,你會聽見內心的聲音; 生命還有更多的可能性,等著你去探索。 你會發現: 金色陽光下,還有一條更適合你的自助助人之路,正鋪展在你的面前。
【電子書】觀測心中的太空
本書緣起 《說文解字》言,「科」者,「從禾從斗,斗者量也」。「學」者,「覺悟也」。「科」、「學」連起來的意思是透過觀察、測量達到覺悟。在現代泛指西方舶來的解釋自然真理的各種學說。 從懷疑中醒來的覺悟者,我們稱為佛陀。兩千五百年前,印度的王子喬達摩‧悉達多為眾生宣講了覺醒的教言,這些真知的智慧,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消散,反而利用現代科技,跨越鴻溝,震醒了西方--科學發達,佛教新興的國度。截至2012年,已經有超過八千名前沿科學家們投入科學與佛教的研究。 本書是智悲翻譯中心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翻譯的國外各個科研領域,對佛教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論文和演講等內容,很好地闡述了佛教對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有著怎樣的幫助和借鑒作用。 西方科學界對於佛學的實證研究,讓智識分子們重新認識和思考佛教。西方科學對於佛教的實證研究,加強了我們對於佛學的重新認識。佛教是迷信嗎?科學家們怎麼看待佛教?什麼是意識和物質?哪個更為重要?宇宙的運行是指向一個目標嗎?人類的最終定位是什麼?本書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內心世界,並重新思考佛教!
【電子書】靈活處事,禪心待人:老禪師的生活智慧
寬嚴有度,則可自在安樂。 能容天下難容之事者,必是人中之佛。 佛陀說:「對憤怒的人,以憤怒還牙,是一件不應該的事。對憤怒的人,不以憤怒還牙的人,將可得到兩個勝利:知道他人的憤怒,而以正念鎮靜自己的人,不但能勝於自己,也能勝於他人。」 這就是寬恕的力量。
【電子書】行住坐臥都是道
禪是一種解脫的智慧,一種追求快樂和適意生活的心境。佛以非凡的智慧,點破迷惑,以智慧的機鋒給世人以啟示,為世人指明方向。只要用心體會,芸芸眾生、萬 事萬物都是禪理。禪是我們內心的本性,有了禪,我們可以對自身有一個重新的認識,使我們的心靈徹底解縛,禪是治癒現代人浮躁心靈的最好的靈丹妙藥。 與禪結緣,是人生莫大的福分! 透過禪理,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生的意義,進而活出美滿幸福的人生。 放下執著的貪念,一切隨緣、一切隨性。那些曾經擁有的就讓它遠去,那些未來未知的就讓它慢慢靠近,我們只抓住現在擁有的,感受真實的酸甜苦辣。 「要放下」是禪師訓導弟子的誡語,但習慣了「拿起」的人,讓他「放下」談何容易?況且,他能放下手上、肩上的重負,能放得下心裡的牽絆嗎?「心中有事世間小,心中無事一床寬」,欲求心靈解脫的人,須知有捨有得、捨而後得的人生道理。 放下塵緣,在紛繁的生活中,慰藉心靈的疲憊,在喧囂的塵世裏,享受內心的寧靜,從而為自己營造出一段清淨從容、悠然舒緩的幸福時光,在瑣屑的塵世中, 過上灑脫自在的生活。本書的內容包括修心定性找到自我、從善去惡常懷慈悲、心地清淨泰然處之、尊人恕己有容乃大、有捨有得天寬地闊等。
【電子書】聽弘一大師講鹹淡人生
讀弘一大師,我們的內心會獲得一種空靈的美感,那是一種久遠的自然的力量。 他使我們低下頭,開始審視自身,重新關注已被遺忘很久的自我的真實性靈。 所謂看破紅塵,對有些人來說只不過是不入紅塵而已。我們大多數人對紅塵都是很留戀的,即使會有很多傷痛、痠楚、不盡如人意,然而,我們熱愛著俗世的生活。 愛是最大的智慧。因為有愛,我們可以從他們豐富淵博的人生閱歷,和清新平實的話語中,捕捉到智慧之光,探求人生真諦。 李叔同是關注世事,卻又遠離世事的人,他在繁華之外看繁華。所以,他多關注於人自我的精神世界。精神富足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足;否則,即使富如國王,也會貧如乞丐。 讀他,我們的內心會獲得一種空靈的美感,那是一種久遠的自然力量。他使我們低下頭,開始審視自身,重新關注已被遺忘很久的自我的真實性。 一杯淡泊悠遠的心靈之茶,一部處世安身的塵世經書,品李叔同,看透世間繁華,直達精神家園;悟南懷瑾,智享人間百態,收穫塵世幸福。 如果一個人想學習適應社會的手段,那麼,守護精神的家園才是最好的出發點。為了活得好一些、更好一些,為了在塵世獲得幸福,讓我們仔細聆聽兩位大師的叮嚀…… 精 神富足的人才是真正的富足,否則,即使富如國王,也會貧如乞丐。讀李叔同,我們的內心會獲得一種空靈的美感,那是一種久遠的自然的力量。他使我們低下頭, 開始審視自身,重新關注已被遺忘很久的自我的真實性靈。而南懷瑾,身在繁華又笑看繁華,他是繁華世間的智者,得享繁華卻又不被繁華所累。於是,他講述人生 種種人情世故,講處世哲學、講生存策略,這一切,都是為了使我們更好地生活在人與人的世界裏。
【電子書】曾半仙談兔年運程
國內盲派術數大家曾大有先生,生於中國重慶。由於先天失明、家境困難,曾先生的母親為使其將來有一技之長、養家糊口,託人將曾先生送到當地著名的盲派術數師「冉瞎子」門下學習算八字及多種術數。 冉師父門下弟子眾多,唯獨曾先生一人是「盲眼人」,因而冉師父偏愛這個徒弟,幾乎將平生所學及八字的高深學問都傳於曾先生。17歲時,曾先生學業有成、初出茅廬,開始給人算八字、批八字,同時主動鑽研、不斷與同行切磋,在師父的八字理論基礎上,融入個人的理解、心得和實踐經驗。由於八字斷得準確率奇高,曾先生在當地有「曾八字」的美譽。 一般說來,盲派師父礙於眼疾,很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走動。曾先生為了探索八字及易學的精髓,主動離開家鄉,在全國各地尋訪術數高人、為各色人等算批八字,收穫頗豐,美名廣播。如今三十六歲的曾先生已回到老家重慶,繼續為尋常百姓算批八字、指點運勢迷津。 曾先生師承盲派,在眾多的術數流派中,「盲派」堪稱獨樹一幟,一是因為其「只傳盲眼人,不傳明眼人」的師承方式,二是因為盲派「百不失一」的準確率,令人驚歎。 為什麼盲眼人算命如此準確呢?原因主要有兩點:八字算命講究「數」和「象」這兩大方面。拿排八字來說,算某人生辰四柱的天干地支,少不得參考萬年曆。明眼人可以直接翻閱萬年曆查詢結果,而盲眼人只能透過熟記萬年曆,將結果推算出來,這樣看似比較麻煩,卻能在推算的過程中達到「眼中無數,心中有數」的效果;至於八字之「象」,日主與其他七種干支的五行生剋關係,明眼人可以透過畫圖分析,由表像進行推導得出結果,而盲眼人卻是在心中將日主與其他干支的關係成「象」,諸如「比肩」 「劫財」 「正官」 「正印」等關係,猶如一幅流動的博弈圖形,在心中清晰可見。由此可知,盲眼人算命比明眼人更加準確。 曾先生算八字傳承盲派的核心理念:陰陽是根本,生剋是關鍵。無論是預測個人命運還是天時大運,都要「明陰陽,辨五行」,以《易經》「天人合一」的哲學思維進行邏輯推導。白天黑夜,春夏秋冬,不同的時節和氣候,對萬事萬物有著不同的影響,對人有著或吉或凶的預示,曾先生把這種時空轉變稱之為「運」,無論是「時運不濟」還是「時來運轉」,我們都要先知道自己這十年的天時大運以及某一年的流年運程,這樣才好趨吉避凶、躲避衰運、多行旺運。 願曾大有先生首度口述的《2011 年兔年運程》一書,幫助您更好地看清2011年的天時大運,知曉這一年屬於自己的事業運、感情運、財運、子女運及每月運勢究竟如何,從而順天而為,擇時而動,諸事心想事成。
【電子書】人可以貌相
曾國藩是一個朝延命官,曾任禮部侍郎、署工部右侍郎、署吏部左侍郎等職。 曾國藩是一個官運亨通、大紅大紫的大官。十年之中連升十級,並在京師贏得了較好的聲望。 曾國藩是一個重才舉賢的好官。他堅持「行政之要,首在得人」的原則,立志「引用一班人,培養幾個好官」。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先後有四百多位學者志士投身於他的門下。他一生舉荐近千人,其中有「才大心細,勁氣內斂」的李鴻章,有「取勢甚遠,審機甚微」的左宗棠,有「器識才略,實堪大用」的沈葆楨等。到他謝世之時,他所舉荐的門人中,任封疆大吏者二十六人,幾乎占有半壁江山。 曾國藩是一個有志向、有抱負的明白官。他懷抱濟世之志,對「乾嘉盛世」的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認為「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敬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入骨。 「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鑒此,他主張危急之時需要任用德器兼備之才,以倡廉政之風,行禮治、仁政之道,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私的宦吏,毫不手軟,一律予以嚴懲。 曾國藩任官期間,多次上書朝廷,陳述改革措施,指出朝野三大隱患:即人才、財用和兵力三大問題中的弊端,並提出了解決辦法。他說,自古治世不外招賢能,安百姓,正風氣三件事:兵在精,不在多,建議裁軍:民心渙散的根本原因是銀價太昂,錢糧難納,冤獄太多,民心難伸等等。 曾國藩雖為清廷命官,但每為虛職,很少實權。但曾氏根本無視權力的大小,只管盡職盡責而已。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始終貫徹「經民致用」的思想,以「內聖」之學推行「外王」之道,並把它的實行,作為終身致力追求的目標。在長期的治政、督軍活動中,養成了注重實踐,講求實效,因時變通的作風。他的「士貴知古,尤貴通今」,「不說空話,不鶩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可以說是這種作風的精粹概括。 曾國藩的官運可謂稀有,他的官品堪稱世人的楷模。毛澤東在致友人黎錦熙的信中,對他的這位同鄉的官品贊譽有加:「愚於近人,獨服曾文」,認為曾國藩是位「大本大源、倡學促教、陶鑄人心、移風易俗」的學者和政治家。 曾國藩一生為國舉才無數,本書可以說是他選人的準則。透過本書,或許可以作為您的參考,創造另一番的丰采,改變您的人生。
【電子書】歸來一滴曹溪水:南頓北漸篇
《歷代高僧故事》發行再版了,這對著者來說,確是一大鼓勵。 說到鼓勵,很快就會使人聯想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說話,但我卻不著意於此,因為傳與不傳,那是作品本身的事,而不是作者想不想的事,如果作品不夠條件,縱想也是多餘的。雖然「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著作物之能傳,使作者也隨之不朽,這當然是人們所熱望的。 可是,佛徒對於名的看法,是當作假設,是視為身外之物,並不把它當作實有。雖然佛教有所謂「萬法唯有」的「有部」,但更有「一切皆空」的「空宗」,「四大皆空」,名於何有?所以,要想使作品流傳後世,不可必,而且也不必要。 「名」,既不是支持我撰寫本書的原動力,那麼,總得有一股力量曾經促使我孳孳的「鍥而不捨」,在極端艱困的情況下,歷十有餘年的長時間,以完成此幾十名高僧的寫作,這力量,便是所謂「尚友古人」的一句說話。 何以言之?翻開佛教大藏經的史傳部,所有每一人的傳記,所有行事的紀述,學術的論著,竟是我束髮受書幾十年來所從未見過的。他們行誼的高尚,宅心的仁厚,處事的忠誠,修持的堅貞,不求聞達,不圖功利,不避艱險,而又忘其死生,以了其弘願的精神,實非後世人們所可想像其萬一。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只求夢見周公,而我卻日與周公同一類型的先哲們為伍,相與晤言一室之內,故而樂不可支。因此十餘年來,精神生活的佳勝,綜計在以往的歲月中,實無有逾於此時者。古諺云︰「上交千古,下交千古」,下交千古不可必,上交千古竟躬親獲致,又何得而不目為平生的一大快事! 實在的說︰我國的傳統文化,應為漢學與理學的混合體。任捨其一,即捨完整,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所以著者曾經作了一個譬喻說︰我國的傳統文化,為黃河流域文化與印度恒河流域文化的結合,因而產生了「混血兒」,曾有許多明達之士,對佛教教義作過深入之研究而服膺奉行。例如唐代詩人白居易,與香山僧如滿朝夕相處,而自稱香山居士。韓愈弟子李翱太守與榮山惟儼曾留下一首絕句說︰「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樹一函經,我來問道無他語,雲在青天水在瓶」。還有宋儒歐陽修,曾自稱為六一居士,在其所著的《新唐書》裏,對於僧一行之作大衍曆,更曾大事吹噓。程明道過定林寺時,偶見僧眾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代鼓敲鐘,內外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規」。於是程氏慨然的說︰「三代禮樂,盡在斯矣!」此外如蘇東坡之與佛印了元交誼甚篤,其間流風遺韻,常為世人所樂道。像白居易、李翱、歐陽修、程明道、蘇東坡這班學人,始能「與人為善」,而「樂道人之善」,不存「我執」與「法執」,才完成了他們偉大的人格。 又如近世學人梁啟超,曾稱讚東晉時的道安法師說︰「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為大國?吾蓋不敢言。」(見梁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版)。以一僧人之微,而竟關係我整個國家民族之興衰,如非道安確有其道,梁氏絕不至服膺若此。 再就是已逝世的胡適之先生,他從發表所著《荷澤大師傳》(神會和尚,見《胡適文存》四)起,直至他逝世時為止,前後歷三十餘年,為著覓取神會史料,足跡所屆,竟遍東西兩半球,始克完成《神會和尚全集》之編撰,如非神會有其獨到處,豈能使胡氏以如許的長時間,如此辛勤的搜集,而從事於一個和尚的研究呢?古今學者對佛教的稱揚代不乏人,也就足以證明佛教教義的博厚高明了。 佛教教義不僅有其高明處,也有其實用處,它持著圓融、業報、因果、輪迴等理論,以及那「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觀念,掃蕩了人們「唯我獨尊」、「予智自雄」和個人的「福壽康寧考終命」的錯誤見解,而釀成人世上的一切紛擾來。本來,「無壽者相」的解釋,就是要泯去個人的生死觀念。可是佛家還是有其壽者相的。他們信仰輪迴之說,將整個宇宙的生命統一起來,所有的有生之物,都分成為「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的三世,以生命是歷萬劫而來,復應歷萬劫而去,而「現在世」卻是極其短暫的,無窮數的「過去世」,以及無極限的「未來世」,都憑你在這短暫的「現在世」裏,一方面交待前因,一方面創造後果,因因果果,不僅使個人的生命,就是整個的宇宙,也就隨之而生生不已了。如果說人的生命是偶然的,那麼,人生在世,紛紛擾擾、忙忙碌碌,短短的幾十年過後,兩眼一閉,兩腳一伸,便一切都完了,那就實在太沒有意思了。 至於講到佛家的圓融和因果說,實在控制了人心的活動。我們可以拿個極淺近的譬喻來說︰就是把人心比做一輛汽車,如果汽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只能直衝,不能轉彎;只能急駛,不能緩行;只能行動,不能休止;那麼,這輛汽車勢必撞樹、毀屋、墜岩,粉身碎骨而後已。所以,一輛好汽車必定要具備能進能退、能左能右、能行能止、能速能徐的功能,才能算是最優良的交通工具,「心猿意馬」的人類心理現象,亦何獨不然! 所以,《禮記‧曲禮》上幾句話過後便說︰「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佛教教義正是實施這些「不可」的制衡工具。 總而言之,佛家的人和事都是在「戒、定、慧」的三學下,以破除人心貪、瞋、癡的三毒,有理論,有方法,所以才能完成其周密雄健的一大哲學禮系,而昭示千古。
【電子書】燒餅歌與推背圖
天下事,誰能斷言? 《燒餅歌》中,朱元璋與劉伯溫的一席對話,道盡中國自明朝以來各代興亡盛衰的史實,甚至未發生的未來;同樣的,由《推背圖》也推演出唐朝以後的歷史更迭,並將及於現世將可能會發生的情事。 對此兩者預言評論,解析者眾,惟本書並不做任何無端的揣測,僅以客觀的釋疑立場,提供另一種模合預言的方法,其中的可信度或可能性有多少,玄機自在天理循環中!
【電子書】為道忘軀法中王:天竺取經篇
《歷代高僧故事》發行再版了,這對著者來說,確是一大鼓勵。說到鼓勵,很快就會使人聯想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說話,但我卻不著意於此,因為傳與不傳,那是作品本身的事,而不是作者想不想的事,如果作品不夠條件,縱想也是多餘的。雖然「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著作物之能傳,使作者也隨之不朽,這當然是人們所熱望的。可是,佛徒對於名的看法,是當作假設,是視為身外之物,並不把它當作實有。雖然佛教有所謂「萬法唯有」的「有部」,但更有「一切皆空」的「空宗」,「四大皆空」,名於何有?所以,要想使作品流傳後世,不可必,而且也不必要。「名」,既不是支持我撰寫本書的原動力,那麼,總得有一股力量曾經促使我孳孳的「鍥而不捨」,在極端艱困的情況下,歷十有餘年的長時間,以完成此幾十名高僧的寫作,這力量,便是所謂「尚友古人」的一句說話。何以言之?翻開佛教大藏經的史傳部,所有每一人的傳記,所有行事的紀述,學術的論著,竟是我束髮受書幾十年來所從未見過的。他們行誼的高尚,宅心的仁厚,處事的忠誠,修持的堅貞,不求聞達,不圖功利,不避艱險,而又忘其死生,以了其弘願的精神,實非後世人們所可想像其萬一。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只求夢見周公,而我卻日與周公同一類型的先哲們為伍,相與晤言一室之內,故而樂不可支。因此十餘年來,精神生活的佳勝,綜計在以往的歲月中,實無有逾於此時者。古諺云︰「上交千古,下交千古」,下交千古不可必,上交千古竟躬親獲致,又何得而不目為平生的一大快事!實在的說︰我國的傳統文化,應為漢學與理學的混合體。任捨其一,即捨完整,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所以著者曾經作了一個譬喻說︰我國的傳統文化,為黃河流域文化與印度?河流域文化的結合,因而產生了「混血兒」,曾有許多明達之士,對佛教教義作過深入之研究而服膺奉行。例如唐代詩人白居易,與香山僧如滿朝夕相處,而自稱香山居士。韓愈弟子李翱太守與榮山惟儼曾留下一首絕句說︰「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樹一函經,我來問道無他語,雲在青天水在瓶」。還有宋儒歐陽修,曾自稱為六一居士,在其所著的《新唐書》?,對於僧一行之作大衍曆,更曾大事吹噓。程明道過定林寺時,偶見僧眾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代鼓敲鐘,內外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規」。於是程氏慨然的說︰「三代禮樂,盡在斯矣!」此外如蘇東坡之與佛印了元交誼甚篤,其間流風遺韻,常為世人所樂道。像白居易、李翱、歐陽修、程明道、蘇東坡這班學人,始能「與人為善」,而「樂道人之善」,不存「我執」與「法執」,才完成了他們偉大的人格。又如近世學人梁啟超,曾稱讚東晉時的道安法師說︰「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為大國?吾蓋不敢言。」(見梁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版)。以一僧人之微,而竟關係我整個國家民族之興衰,如非道安確有其道,梁氏絕不至服膺若此。再就是已逝世的胡適之先生,他從發表所著《荷澤大師傳》(神會和尚,見《胡適文存》四)起,直至他逝世時為止,前後歷三十餘年,為著覓取神會史料,足跡所屆,竟遍東西兩半球,始克完成《神會和尚全集》之編撰,如非神會有其獨到處,豈能使胡氏以如許的長時間,如此辛勤的搜集,而從事於一個和尚的研究呢?古今學者對佛教的稱揚代不乏人,也就足以證明佛教教義的博厚高明了。佛教教義不僅有其高明處,也有其實用處,它持著圓融、業報、因果、輪迴等理論,以及那「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觀念,掃蕩了人們「唯我獨尊」、「予智自雄」和個人的「福壽康寧考終命」的錯誤見解,而釀成人世上的一切紛擾來。本來,「無壽者相」的解釋,就是要泯去個人的生死觀念。可是佛家還是有其壽者相的。他們信仰輪迴之說,將整個宇宙的生命統一起來,所有的有生之物,都分成為「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的三世,以生命是歷萬劫而來,復應歷萬劫而去,而「現在世」卻是極其短暫的,無窮數的「過去世」,以及無極限的「未來世」,都憑你在這短暫的「現在世」?,一方面交待前因,一方面創造後果,因因果果,不僅使個人的生命,就是整個的宇宙,也就隨之而生生不已了。如果說人的生命是偶然的,那麼,人生在世,紛紛擾擾、忙忙碌碌,短短的幾十年過後,兩眼一閉,兩腳一伸,便一切都完了,那就實在太沒有意思了。至於講到佛家的圓融和因果說,實在控制了人心的活動。我們可以拿個極淺近的譬喻來說︰就是把人心比做一輛汽車,如果汽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只能直衝,不能轉彎;只能急駛,不能緩行;只能行動,不能休止;那麼,這輛汽車勢必撞樹、毀屋、墜岩,粉身碎骨而後已。所以,一輛好汽車必定要具備能進能退、能左能右、能行能止、能速能徐的功能,才能算是最優良的交通工具,「心猿意馬」的人類心理現象,亦何獨不然!所以,《禮記.曲禮》上幾句話過後便說︰「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佛教教義正是實施這些「不可」的制衡工具。總而言之,佛家的人和事都是在「戒、定、慧」的三學下,以破除人心貪、瞋、癡的三毒,有理論,有方法,所以才能完成其周密雄健的一大哲學禮系,而昭示千古。彭楚珩於臺灣
【電子書】禪心本是清淨心:破執開悟的故事
禪也不是理性的文字和概念所能傳遞的。禪家常說「言語道斷」,意思是說,光是用語言文字來討論禪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國禪宗的發展,卻留下一疊疊浩瀚的公案,而這些公案又是不可思議的難懂,特別是公案中師生的對話,絕大部分不能用邏輯來了解。 「參禪悟道」才是它的學習方法。頓悟,就是指經過長久的修行,突然醍醐灌頂的那一刻。學禪的路程就好像登高樓觀風景:在還沒上樓之前,先想知道樓上有什麼東西,什麼景致,是不是值得一看,那是無法享受到登高望遠的樂趣的。若是真正想要看到美麗的景致,了解禪的真意,不用問那麼多的問題,只需要努力的攀登,認真的體悟。
【電子書】無事就是貴人:身心自在的智慧
能體悟每天都是生命中最好的一刻,才可說是真正瞭解人生的人。如果執意生命操縱在自己手裡,就不可能客觀的看清事物。所以,凡事要全力以赴、認真去做,不計較得失毀譽,以光明坦然的態度,接受人生的悲喜,日日就是好日。佛教從漢朝時傳入中土,到達摩西來,開啟了中國的禪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立教。透過生活裡的各種現象,不斷的自我修證和禪師的隨機接引,在彼此的機鋒相對之際,迸出了禪的火花。為了使緊張忙碌的現代人在生活裡能得到心靈上的調適,將禪宗的智慧融入生活,乃輯錄祖師大德的禪詩禪語,分成四卷,按四季景象之不同與內心之感受,以筆記的方式,用生活裡的一些事物來闡述禪理,無非是希望您能從中得到啟示,在生活裡重新思索,賦予生命全新的意義,讓我們能增長智慧見識,寬廣我們的心靈空間。
【電子書】山色無非清淨身:頑石點頭篇
《歷代高僧故事》發行再版了,這對著者來說,確是一大鼓勵。說到鼓勵,很快就會使人聯想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說話,但我卻不著意於此,因為傳與不傳,那是作品本身的事,而不是作者想不想的事,如果作品不夠條件,縱想也是多餘的。雖然「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著作物之能傳,使作者也隨之不朽,這當然是人們所熱望的。可是,佛徒對於名的看法,是當作假設,是視為身外之物,並不把它當作實有。雖然佛教有所謂「萬法唯有」的「有部」,但更有「一切皆空」的「空宗」,「四大皆空」,名於何有?所以,要想使作品流傳後世,不可必,而且也不必要。「名」,既不是支持我撰寫本書的原動力,那麼,總得有一股力量曾經促使我孳孳的「鍥而不捨」,在極端艱困的情況下,歷十有餘年的長時間,以完成此幾十名高僧的寫作,這力量,便是所謂「尚友古人」的一句說話。何以言之?翻開佛教大藏經的史傳部,所有每一人的傳記,所有行事的紀述,學術的論著,竟是我束髮受書幾十年來所從未見過的。他們行誼的高尚,宅心的仁厚,處事的忠誠,修持的堅貞,不求聞達,不圖功利,不避艱險,而又忘其死生,以了其弘願的精神,實非後世人們所可想像其萬一。 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只求夢見周公,而我卻日與周公同一類型的先哲們為伍,相與晤言一室之內,故而樂不可支。因此十餘年來,精神生活的佳勝,綜計在以往的歲月中,實無有逾於此時者。古諺云︰「上交千古,下交千古」,下交千古不可必,上交千古竟躬親獲致,又何得而不目為平生的一大快事!實在的說︰ 我國的傳統文化,應為漢學與理學的混合體。任捨其一,即捨完整,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所以著者曾經作了一個譬喻說︰我國的傳統文化,為黃河流域文化與印度恆河流域文化的結合,因而產生了「混血兒」,曾有許多明達之士,對佛教教義作過深入之研究而服膺奉行。例如唐代詩人白居易,與香山僧如滿朝夕相處,而自稱香山居士。韓愈弟子李翱太守與榮山惟儼曾留下一首絕句說︰「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樹一函經,我來問道無他語,雲在青天水在瓶」。還有宋儒歐陽修,曾自稱為六一居士,在其所著的《新唐書》裡,對於僧一行之作大衍曆,更曾大事吹噓。程明道過定林寺時,偶見僧眾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代鼓敲鐘,內外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規」。於是程氏慨然的說︰「三代禮樂,盡在斯矣!」此外如蘇東坡之與佛印了元交誼甚篤,其間流風遺韻,常為世人所樂道。像白居易、李翱、歐陽修、程明道、蘇東坡這班學人,始能「與人為善」,而「樂道人之善」,不存「我執」與「法執」,才完成了他們偉大的人格。又如近世學人梁啟超,曾稱讚東晉時的道安法師說︰「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為大國?吾蓋不敢言。」(見梁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版)。以一僧人之微,而竟關係我整個國家民族之興衰,如非道安確有其道,梁氏絕不至服膺若此。再就是已逝世的胡適之先生,他從發表所著《荷澤大師傳》(神會和尚,見《胡適文存》四)起,直至他逝世時為止,前後歷三十餘年,為著覓取神會史料,足跡所屆,竟遍東西兩半球,始克完成《神會和尚全集》之編撰,如非神會有其獨到處,豈能使胡氏以如許的長時間,如此辛勤的蒐集,而從事於一個和尚的研究呢?古今學者對佛教的稱揚代不乏人,也就足以證明佛教教義的博厚高明了。佛教教義不僅有其高明處,也有其實用處,它持著圓融、業報、因果、輪迴等理論,以及那「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觀念,掃蕩了人們「唯我獨尊」、「予智自雄」和個人的「福壽康寧考終命」的錯誤見解,而釀成人世上的一切紛擾來。本來,「無壽者相」的解釋,就是要泯去個人的生死觀念。可是佛家還是有其壽者相的。他們信仰輪迴之說,將整個宇宙的生命統一起來,所有的有生之物,都分成為「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的三世,以生命是歷萬劫而來,復應歷萬劫而去,而「現在世」卻是極其短暫的,無窮數的「過去世」,以及無極限的「未來世」,都憑你在這短暫的「現在世」裡,一方面交待前因,一方面創造後果,因因果果,不僅使個人的生命,就是整個的宇宙,也就隨之而生生不已了。如果說人的生命是偶然的,那麼,人生在世,紛紛擾擾、忙忙碌碌,短短的幾十年過後,兩眼一閉,兩腳一伸,便一切都完了,那就實在太沒有意思了。至於講到佛家的圓融和因果說,實在控制了人心的活動。我們可以拿個極淺近的譬喻來說︰就是把人心比做一輛汽車,如果汽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只能直衝,不能轉彎;只能急駛,不能緩行;只能行動,不能休止;那麼,這輛汽車勢必撞樹、毀屋、墜岩,粉身碎骨而後已。所以,一輛好汽車必定要具備能進能退、能左能右、能行能止、能速能徐的功能,才能算是最優良的交通工具,「心猿意馬」的人類心理現象,亦何獨不然!所以,《禮記‧曲禮》上幾句話過後便說︰「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佛教教義正是實施這些「不可」的制衡工具。 總而言之,佛家的人和事都是在「戒、定、慧」的三學下,以破除人心貪、瞋、痴的三毒,有理論,有方法,所以才能完成其周密雄健的一大哲學禮系,而昭示千古。─彭楚珩於臺灣
【電子書】溪聲盡是廣長舌:西行取經篇
《歷代高僧故事》發行再版了,這對著者來說,確是一大鼓勵。說到鼓勵,很快就會使人聯想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說話,但我卻不著意於此,因為傳與不傳,那是作品本身的事,而不是作者想不想的事,如果作品不夠條件,縱想也是多餘的。雖然「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著作物之能傳,使作者也隨之不朽,這當然是人們所熱望的。可是,佛徒對於名的看法,是當作假設,是視為身外之物,並不把它當作實有。雖然佛教有所謂「萬法唯有」的「有部」,但更有「一切皆空」的「空宗」,「四大皆空」,名於何有?所以,要想使作品流傳後世,不可必,而且也不必要。「名」,既不是支持我撰寫本書的原動力,那麼,總得有一股力量曾經促使我孳孳的「鍥而不捨」,在極端艱困的情況下,歷十有餘年的長時間,以完成此幾十名高僧的寫作,這力量,便是所謂「尚友古人」的一句說話。何以言之?翻開佛教大藏經的史傳部,所有每一人的傳記,所有行事的紀述,學術的論著,竟是我束髮受書幾十年來所從未見過的。他們行誼的高尚,宅心的仁厚,處事的忠誠,修持的堅貞,不求聞達,不圖功利,不避艱險,而又忘其死生,以了其弘願的精神,實非後世人們所可想像其萬一。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只求夢見周公,而我卻日與周公同一類型的先哲們為伍,相與晤言一室之內,故而樂不可支。因此十餘年來,精神生活的佳勝,綜計在以往的歲月中,實無有逾於此時者。古諺云︰「上交千古,下交千古」,下交千古不可必,上交千古竟躬親獲致,又何得而不目為平生的一大快事!實在的說︰我國的傳統文化,應為漢學與理學的混合體。任捨其一,即捨完整,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所以著者曾經作了一個譬喻說︰我國的傳統文化,為黃河流域文化與印度?河流域文化的結合,因而產生了「混血兒」,曾有許多明達之士,對佛教教義作過深入之研究而服膺奉行。例如唐代詩人白居易,與香山僧如滿朝夕相處,而自稱香山居士。韓愈弟子李翱太守與榮山惟儼曾留下一首絕句說︰「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樹一函經,我來問道無他語,雲在青天水在瓶」。還有宋儒歐陽修,曾自稱為六一居士,在其所著的《新唐書》?,對於僧一行之作大衍曆,更曾大事吹噓。程明道過定林寺時,偶見僧眾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代鼓敲鐘,內外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規」。於是程氏慨然的說︰「三代禮樂,盡在斯矣!」此外如蘇東坡之與佛印了元交誼甚篤,其間流風遺韻,常為世人所樂道。像白居易、李翱、歐陽修、程明道、蘇東坡這班學人,始能「與人為善」,而「樂道人之善」,不存「我執」與「法執」,才完成了他們偉大的人格。又如近世學人梁啟超,曾稱讚東晉時的道安法師說︰「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為大國?吾蓋不敢言。」(見梁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版)。以一僧人之微,而竟關係我整個國家民族之興衰,如非道安確有其道,梁氏絕不至服膺若此。再就是已逝世的胡適之先生,他從發表所著《荷澤大師傳》(神會和尚,見《胡適文存》四)起,直至他逝世時為止,前後歷三十餘年,為著覓取神會史料,足跡所屆,竟遍東西兩半球,始克完成《神會和尚全集》之編撰,如非神會有其獨到處,豈能使胡氏以如許的長時間,如此辛勤的搜集,而從事於一個和尚的研究呢?古今學者對佛教的稱揚代不乏人,也就足以證明佛教教義的博厚高明了。佛教教義不僅有其高明處,也有其實用處,它持著圓融、業報、因果、輪迴等理論,以及那「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觀念,掃蕩了人們「唯我獨尊」、「予智自雄」和個人的「福壽康寧考終命」的錯誤見解,而釀成人世上的一切紛擾來。本來,「無壽者相」的解釋,就是要泯去個人的生死觀念。可是佛家還是有其壽者相的。他們信仰輪迴之說,將整個宇宙的生命統一起來,所有的有生之物,都分成為「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的三世,以生命是歷萬劫而來,復應歷萬劫而去,而「現在世」卻是極其短暫的,無窮數的「過去世」,以及無極限的「未來世」,都憑你在這短暫的「現在世」?,一方面交待前因,一方面創造後果,因因果果,不僅使個人的生命,就是整個的宇宙,也就隨之而生生不已了。如果說人的生命是偶然的,那麼,人生在世,紛紛擾擾、忙忙碌碌,短短的幾十年過後,兩眼一閉,兩腳一伸,便一切都完了,那就實在太沒有意思了。至於講到佛家的圓融和因果說,實在控制了人心的活動。我們可以拿個極淺近的譬喻來說︰就是把人心比做一輛汽車,如果汽車只能前進,不能後退;只能直衝,不能轉彎;只能急駛,不能緩行;只能行動,不能休止;那麼,這輛汽車勢必撞樹、毀屋、墜岩,粉身碎骨而後已。所以,一輛好汽車必定要具備能進能退、能左能右、能行能止、能速能徐的功能,才能算是最優良的交通工具,「心猿意馬」的人類心理現象,亦何獨不然!所以,《禮記.曲禮》上幾句話過後便說︰「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佛教教義正是實施這些「不可」的制衡工具。總而言之,佛家的人和事都是在「戒、定、慧」的三學下,以破除人心貪、瞋、癡的三毒,有理論,有方法,所以才能完成其周密雄健的一大哲學禮系,而昭示千古。彭楚珩於臺灣
【電子書】煩惱是人生的菩提:妙明真心的故事
禪也不是理性的文字和概念所能傳遞的。禪家常說「言語道斷」,意思是說,光是用語言文字來討論禪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國禪宗的發展,卻留下一疊疊浩瀚的公案,而這些公案又是不可思議的難懂,特別是公案中師生的對話,絕大部分不能用邏輯來了解。「參禪悟道」才是它的學習方法。頓悟,就是指經過長久的修行,突然醍醐灌頂的那一刻。學禪的路程就好像登高樓觀風景:在還沒上樓之前,先想知道樓上有什麼東西,什麼景致,是不是值得一看,那是無法享受到登高望遠的樂趣的。若是真正想要看到美麗的景致,了解禪的真意,不用問那麼多的問題,只需要努力的攀登,認真的體悟。
【電子書】心地清淨方為道:定慧等持的故事
禪也不是理性的文字和概念所能傳遞的。禪家常說「言語道斷」,意思是說,光是用語言文字來討論禪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國禪宗的發展,卻留下一疊疊浩瀚的公案,而這些公案又是不可思議的難懂,特別是公案中師生的對話,絕大部分不能用邏輯來了解。 「參禪悟道」才是它的學習方法。頓悟,就是指經過長久的修行,突然醍醐灌頂的那一刻。學禪的路程就好像登高樓觀風景:在還沒上樓之前,先想知道樓上有什麼東西,什麼景致,是不是值得一看,那是無法享受到登高望遠的樂趣的。若是真正想要看到美麗的景致,了解禪的真意,不用問那麼多的問題,只需要努力的攀登,認真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