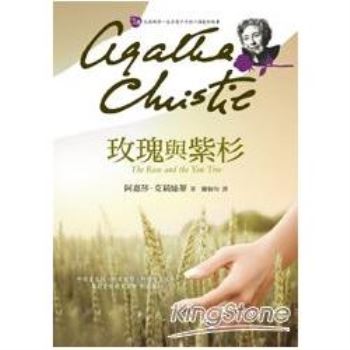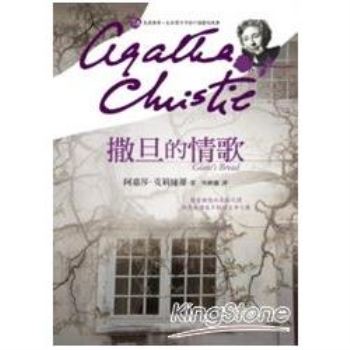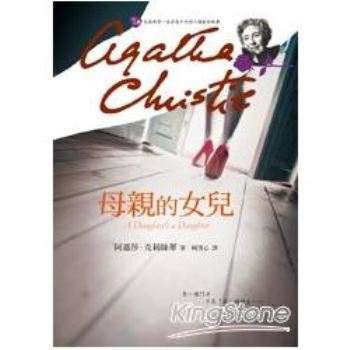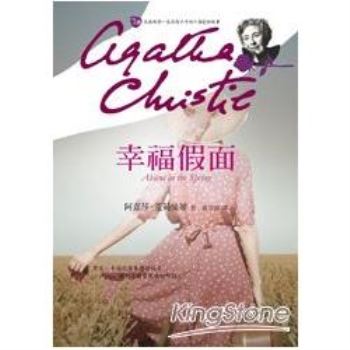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玫瑰與紫杉
……我人生中想要和在意的一切,似乎都結合在她身上。我知道我粗俗、卑鄙、肉慾……但在遇到她之前,我都不以為意。大家都很期待美麗高貴的伊莎貝拉能夠嫁給剛從戰場歸鄉的她的表哥羅伯特!然而充滿野心又無情的戰爭英雄約翰卻突然出現在她的生命中。對伊莎貝拉而言,愛情的代價意謂著失去長久來的夢想和快樂;對約翰來說,這代價則是失去如日中天的事業及對未來的抱負……◎每段愛情、每個人生,都是完整而完美的克莉絲蒂在《玫瑰與紫杉》書中幾次利用一段詩句:「玫瑰飄香和紫杉扶疏的時令,經歷的時間一樣短長……」其實,玫瑰飄香和紫杉扶疏的時令,經歷的時間,當然有很大的落差,但這卻是克莉絲蒂對愛情及人生的見解,因此,她在本書安排了身障者「修」、美麗卻為愛早逝的貴族少女「伊莎貝拉」,以及其貌不揚、自卑、投機的政客「約翰」來闡釋愛情的無可理喻與純粹。◎二次戰後的寫實英國這部小說的場景就發生在克莉絲蒂當時所處的英國,二戰即將結束,整個政局及價值觀面臨極大的改變……天后利用這個時代氛圍來扣連愛情的本質,讓我們在欣賞愛情小說的同時,也窺見了當時英國此般寫實的社會風貌;這個部分,讓本書更具有文學研究的價值。◎一窺推理天后對「純愛」的闡釋本書初版於1947年,克莉絲蒂在書中安排了「修」這位因愛成殘的旁觀者、「伊莎貝拉」這位美麗、因為愛而早逝的貴族少女、「約翰」這位醜陋、自卑卻投機而成功的政客……在真假難辨的五角習題中,他們卻都得到了屬於他們心中的幸福;這也是作者對「愛」的答案了!
撒旦的情歌
他們絕望地看著彼此,對於人生中詭譎難料的變化,為他們之間帶來這樣突然的齟齬感到大惑不解。前一分鐘他們還這麼親近,似乎分享了對方的每一個念頭,下一刻卻分處兩極,因為對方不能理解自己而感到憤怒又受傷……1930年,克莉絲蒂已經是個暢銷且多產的推理小說作家,但當「寫作」成了「工作」,她其實有好幾次覺得厭煩。她在自傳中說:「我永遠渴望著做一件不是我正式工作的事。這種渴望實在使我非常不安。事實上,若非如此,我的生活就太單調了。……現在我想做的事就是寫一些偵探小說以外的東西。因此,我懷著頗為愧疚的心情寫一個叫作Giant’s Bread(直譯為:巨人的麵包)的純小說……那本書得到的評論不錯……我用的是瑪麗.魏斯麥珂特(Mary Westmacott)那個筆名,所以誰也不曉得是我寫的。我居然將這件事保密十五年之久。」◎ 巨人的麵包?本書長約二十萬字,原書名為Giant’s Bread(直譯為「巨人的麵包」)。其中《巨人》是一首偉大曲子的曲名,充滿著當時堪稱前衛的音樂形式;而麵包則是「食糧」的象徵──意即「用來餵養、培植不朽名作的食糧、養分」,或說「一生的悲劇恰用來成就人生的不朽」。但這個隱喻其實只是用來貫穿全書的一條絲線,內容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愛情多角習題與人性的故事。◎ 兩難啊兩難!對於人生、愛情,你能要多少?又得付出多少代價?克莉絲蒂在本書中不斷地讓熱愛音樂(克莉絲蒂本人也對音樂有所涉獵)的男主角弗農陷入兩難(工作的、愛情的、人生的……);即使痛苦地做了抉擇,後續的發展也常令他懊悔不已……一方面是因為弗農猶豫不決的性格,但更重要的則是因為他的貪婪──什麼都想要、什麼都不放,卻什麼都留不住!最終失去一切,只成就了不朽的《巨人》。但話說回來,譜出不朽名作也是弗農的心願,他達成了,藉著犧牲一切,達成了!本書雖是克莉絲蒂「非推理」的第一本小說,有著她自稱的「破綻」,但其實更能看出她對人生及人性最直覺反射的抒發。
母親的女兒
有一種鬥爭只在「愛」裡發生……「你不希望我跟杰洛走的理由究竟是什麼,媽?」「我跟你說過了……」「真正的理由……」她厭惡地緊盯安妮的雙眼說,「是你在害怕,對不對?怕我跟杰洛在一起可能會幸福。」安妮與莎拉原是對非常親膩的母女,卻因為先後反對彼此的交往對象,最純然的親情也變得暗潮洶湧。尊重成了漠視的藉口;犧牲則為嫉妒帶來理由。兩個人都變得極度扭曲而不快樂……她們對彼此的愛還在嗎?在哪裡?是什麼?本書初版於1952年,克莉絲蒂透過自身的生命經驗探討的占有與愛的本質等問題。當故事來到母女倆攤牌且將對方逼入死角之際,曙光也乍然展現……原來,愛與任何形式的傷害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當人們怨恨著彼此時,並不表示愛已消失;我們只要放下這些負面情感,愛就會重現了。
幸福假面
要是你沒事可做,只能想你自己,結果會發現什麼關於自己的事呢?「我不想要知道。」鍾恩高聲說。她的聲音嚇了自己一跳。她究竟不想要知道什麼?場仗,她心想,我正在打一場要輸掉的仗……鍾恩是個徹底務實的人,從小只想過安穩的日子;她挑有前途的律師結婚、阻止丈夫追求田園生活,也要求三個孩子都依她的價值觀去做人生規劃。一次探望小女兒的返程途中,火車因雨季路斷而停開,她受困沙漠中的一個小站,每天只能在附近沙丘散步,走著走著,她開始面對自己,一件件以往刻意忽略的「小事」這時都不請自來……本書初版於1944年,是克莉絲蒂一生最滿意的作品之一。她藉本書滿足了一個對自我的提問:我是誰?我「真正」是個什麼樣的人?我所愛的人對我有何想法?他們對我的想法是否如我所想?……過程峰迴路轉,真實而殘酷,彷彿西方的張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