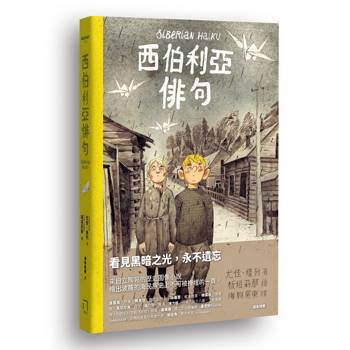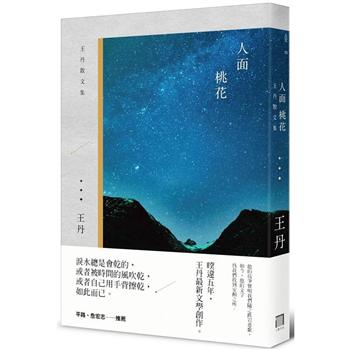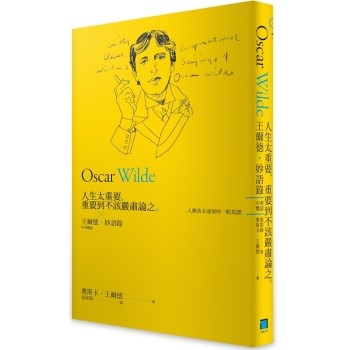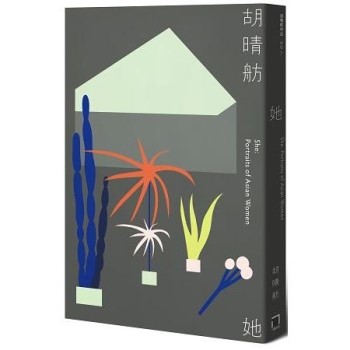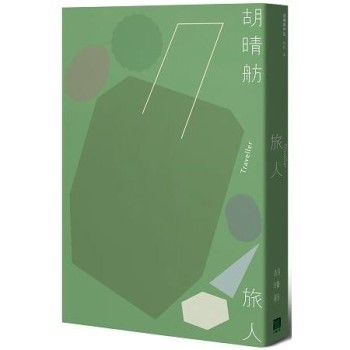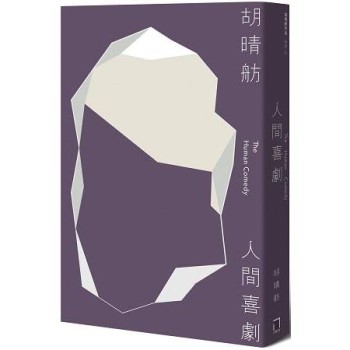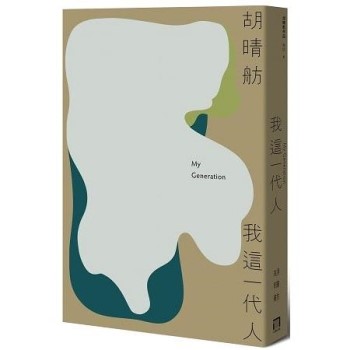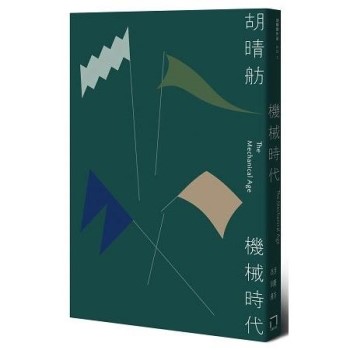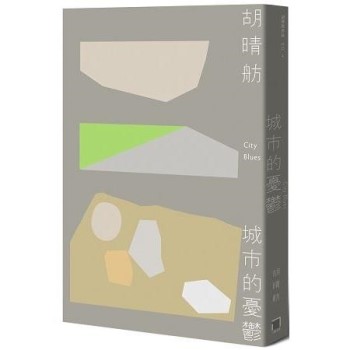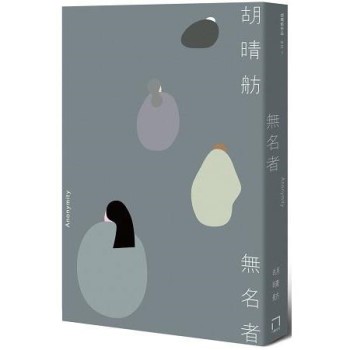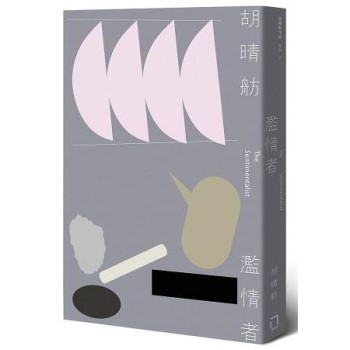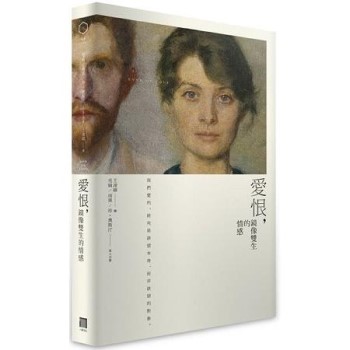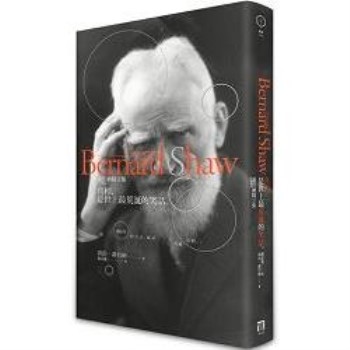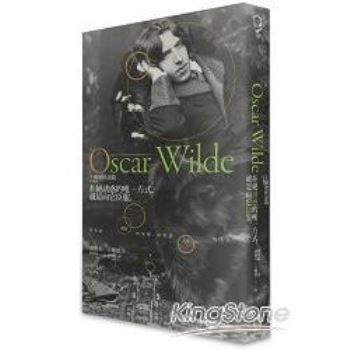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西伯利亞俳句
來自立陶宛的歷史圖像小說,繪出波羅的海民族史上不可被掩埋的一頁。凜冽的西伯利亞集中營內,多個被驅逐的立陶宛家庭,用輕妙的詩句對抗沉重的苦難,以掙扎求存的勇氣與孩童天真想像,譜出二戰期間流放者的哀歌。出版於2017年的立陶宛自傳式歷史圖文書,其深刻的故事與強烈的圖像風格引起讀者的廣泛共鳴。故事從1941年6月的一個早晨說起。大批蘇聯軍隊突然來到立陶宛中部一個安靜的小村莊。八歲的阿吉斯被蘇聯士兵的拍門聲驚醒。他和家人被告知要立刻離開家鄉,但不知道將要去哪裡,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們只知道:有十分鐘時間可以收拾行李。一列密不透風的貨運列車將他們從立陶宛農村的肥沃大地,運載到西伯利亞泰加林區的冰封雪原。在遙遠、荒蕪的西伯利亞,他們開始在凜冽寒冬中過著無盡的苦役與飢餓日子。然而,對於阿吉斯來說,被流放的孤絕生活因孩童想像力、流放者之間相互砥礪的溫暖、西伯利亞善良的當地人民,而透出一絲光明與安慰,即使要與摯愛分離、整天唱著飢餓的歌、有時候勞動一整天都無法獲得丁點麵包而只能喝石頭湯,甚至在面對大風雪的死亡威脅時,阿吉斯與流放者們,仍然要在苦難大地上播下希望的種子。「我想像我的書充滿了光。」尤佳.維列這樣說。《西伯利亞俳句》由立陶宛作家尤佳.維列以當年祖父母一家被蘇聯軍隊強制驅離家鄉,流放西伯利亞的真實經歷,寫下這世界史上少被提及的篇章。她與立陶宛插畫家板垣莉那合作,以短小的章節混合豐富的手繪圖像,以兒童的視角講述這個立陶宛人民以勇氣、善良和超凡意志力共同面對苦難的故事。這個故事要從二戰時期,蘇聯占領波羅的海三國說起。1939年9月,蘇聯迫使波羅的海三國締結互助條約,使蘇聯有權在其領土之上建立軍事基地,隨即占領了波羅的海三國。1940年夏天開始,蘇聯迫使波羅的海三國政府內閣自行辭職,在蘇聯監督之下選出新的「人民議會」,政治反對派被鎮壓,政治組織被清洗,國家被極速蘇維埃化。1941年6月開始,新的蘇維埃政權對各地「人民的敵人」進行大規模強制驅逐行動,當時一共有131,340立陶宛人遭到流放。《西伯利亞俳句》一書所講述的,就是在第一次大規模流放中受害人民的故事。當時大約有17,600人被送往蘇聯的偏遠地帶(包含科米、阿爾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新西伯利亞州、哈薩克),其中約有5,100名是兒童,他們和老年人最先受到各種疾病和死亡的摧殘。被流放者被迫在工地、集體農場和伐木區從事無比粗重的勞力工作,許多人在第一個冬天就因飢餓、酷寒而喪命。這一段被強制驅離與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歷史,一直到1990年,立陶宛終於再次脫離蘇聯而正式宣布獨立時,人們才能真正無顧忌地公開談論。作者尤佳.維列在一次訪問中提及,1990年時她13歲,正好目睹這個歷史時刻。她憶述當時有無數的示威遊行、黃綠紅的國旗在街上飄揚,眼睛裡充滿希望的立陶宛人民通霄達旦的唱歌和唸詩,自由的氣息瀰漫在空氣中。僥倖回到家鄉的被流放者們開始出版回憶錄,這些書被命名為「流亡文學」,尤佳.維列把所有的書都看完了,但她最喜歡的還是祖母的小筆記本,她讀了一遍又一遍。為什麼書名要使用「俳句」?「因為奶奶不太愛說話。她內心背負著西伯利亞的過往,她承受了太多苦難和考驗。但她以簡潔明快的方式寫下她對流放的記憶。她在談論痛苦的同時,也不忘提及美麗的西伯利亞大自然和善良的人們。在閱讀這些用鉛筆書寫、被磨擦至幾乎透明的頁面時,我總覺得周圍有一層溫柔的霧氣,有鹹鹹的水滴從過去落下。」尤佳.維列說,祖母在寫下這些過往在西伯利亞的日子時,往往只能以短語、單字來描述,那一個一個的字與詞,好像蝴蝶一樣在她腦海中飛舞。因此尤佳.維列以「俳句」來命名這樣的記憶。就這樣,書名自然而然地誕生了:《西伯利亞俳句》,一種沉重與輕巧的並置,象徵著立陶宛人民在面對命運的嚴酷考驗時,仍能以短小精妙的詩句作出應對的智慧。「我希望我的書和我奶奶寫的東西有點相似。當你終日只能低頭過活時,仍能感覺到有翅膀在生長。我想像我的書充滿了光。」【本書特色】◎ 題材獨特。以二戰期間蘇聯侵占波羅的海三國這段歷史為題材的中文出版,目前仍不多見,有關立陶宛的歷史與文學出版等也較少。◎ 真實動人。故事出自作者家族的親身經歷,出版至今獲得多項國際獎項,好評不斷,已被翻譯成全球13種語言出版。◎ 繪本作家、推廣人海狗房東翻譯及全力推薦。◎ 特別收錄立陶宛歷史研究所所長許瓦德斯專文導讀。◎ 多位作家、圖文創作者、出版人、導演與立陶宛貿易代表處代表,共同感動推薦。【重要獎項】➢2017立陶宛圖書藝術競賽主獎➢2017立陶宛年度最佳圖書(IBBY)➢2017立陶宛年度最佳童書插圖(IBBY)➢2017白烏鴉奬➢2018 阿洛伊茲.佩特里克(Aloysius Petrikas)文學獎年度童書獎➢2018立陶宛兒童圖書獎➢2020國際兒童圖書評議會榮譽榜➢2020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提名➢2020拉脫維亞兒童圖書評審團入選➢2020拉脫維亞國際 Jānis Baltvilks 獎➢2020義大利波隆那拉加茲獎提名➢2020拉脫維亞版入選拉脫維亞筆會年度最重要書籍名單➢2020拉脫維亞文學獎提名➢2021俄羅斯「閱讀聖彼得堡」國際書籍比賽提名➢2021德國繪本大奬(Deutsche Jugendliteraturpreis)青年讀物類別
【電子書】西伯利亞俳句
來自立陶宛的歷史圖像小說,繪出波羅的海民族史上不可被掩埋的一頁。凜冽的西伯利亞集中營內,多個被驅逐的立陶宛家庭,用輕妙的詩句對抗沉重的苦難,以掙扎求存的勇氣與孩童天真想像,譜出二戰期間流放者的哀歌。出版於2017年的立陶宛自傳式歷史圖文書,其深刻的故事與強烈的圖像風格引起讀者的廣泛共鳴。故事從1941年6月的一個早晨說起。大批蘇聯軍隊突然來到立陶宛中部一個安靜的小村莊。八歲的阿吉斯被蘇聯士兵的拍門聲驚醒。他和家人被告知要立刻離開家鄉,但不知道將要去哪裡,也不知道要去多久,他們只知道:有十分鐘時間可以收拾行李。一列密不透風的貨運列車將他們從立陶宛農村的肥沃大地,運載到西伯利亞泰加林區的冰封雪原。在遙遠、荒蕪的西伯利亞,他們開始在凜冽寒冬中過著無盡的苦役與飢餓日子。然而,對於阿吉斯來說,被流放的孤絕生活因孩童想像力、流放者之間相互砥礪的溫暖、西伯利亞善良的當地人民,而透出一絲光明與安慰,即使要與摯愛分離、整天唱著飢餓的歌、有時候勞動一整天都無法獲得丁點麵包而只能喝石頭湯,甚至在面對大風雪的死亡威脅時,阿吉斯與流放者們,仍然要在苦難大地上播下希望的種子。「我想像我的書充滿了光。」尤佳.維列這樣說。《西伯利亞俳句》由立陶宛作家尤佳.維列以當年祖父母一家被蘇聯軍隊強制驅離家鄉,流放西伯利亞的真實經歷,寫下這世界史上少被提及的篇章。她與立陶宛插畫家板垣莉那合作,以短小的章節混合豐富的手繪圖像,以兒童的視角講述這個立陶宛人民以勇氣、善良和超凡意志力共同面對苦難的故事。這個故事要從二戰時期,蘇聯占領波羅的海三國說起。1939年9月,蘇聯迫使波羅的海三國締結互助條約,使蘇聯有權在其領土之上建立軍事基地,隨即占領了波羅的海三國。1940年夏天開始,蘇聯迫使波羅的海三國政府內閣自行辭職,在蘇聯監督之下選出新的「人民議會」,政治反對派被鎮壓,政治組織被清洗,國家被極速蘇維埃化。1941年6月開始,新的蘇維埃政權對各地「人民的敵人」進行大規模強制驅逐行動,當時一共有131,340立陶宛人遭到流放。《西伯利亞俳句》一書所講述的,就是在第一次大規模流放中受害人民的故事。當時大約有17,600人被送往蘇聯的偏遠地帶(包含科米、阿爾泰、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新西伯利亞州、哈薩克),其中約有5,100名是兒童,他們和老年人最先受到各種疾病和死亡的摧殘。被流放者被迫在工地、集體農場和伐木區從事無比粗重的勞力工作,許多人在第一個冬天就因飢餓、酷寒而喪命。這一段被強制驅離與流放到西伯利亞的歷史,一直到1990年,立陶宛終於再次脫離蘇聯而正式宣布獨立時,人們才能真正無顧忌地公開談論。作者尤佳.維列在一次訪問中提及,1990年時她13歲,正好目睹這個歷史時刻。她憶述當時有無數的示威遊行、黃綠紅的國旗在街上飄揚,眼睛裡充滿希望的立陶宛人民通霄達旦的唱歌和唸詩,自由的氣息瀰漫在空氣中。僥倖回到家鄉的被流放者們開始出版回憶錄,這些書被命名為「流亡文學」,尤佳.維列把所有的書都看完了,但她最喜歡的還是祖母的小筆記本,她讀了一遍又一遍。為什麼書名要使用「俳句」?「因為奶奶不太愛說話。她內心背負著西伯利亞的過往,她承受了太多苦難和考驗。但她以簡潔明快的方式寫下她對流放的記憶。她在談論痛苦的同時,也不忘提及美麗的西伯利亞大自然和善良的人們。在閱讀這些用鉛筆書寫、被磨擦至幾乎透明的頁面時,我總覺得周圍有一層溫柔的霧氣,有鹹鹹的水滴從過去落下。」尤佳.維列說,祖母在寫下這些過往在西伯利亞的日子時,往往只能以短語、單字來描述,那一個一個的字與詞,好像蝴蝶一樣在她腦海中飛舞。因此尤佳.維列以「俳句」來命名這樣的記憶。就這樣,書名自然而然地誕生了:《西伯利亞俳句》,一種沉重與輕巧的並置,象徵著立陶宛人民在面對命運的嚴酷考驗時,仍能以短小精妙的詩句作出應對的智慧。「我希望我的書和我奶奶寫的東西有點相似。當你終日只能低頭過活時,仍能感覺到有翅膀在生長。我想像我的書充滿了光。」【本書特色】◎ 題材獨特。以二戰期間蘇聯侵占波羅的海三國這段歷史為題材的中文出版,目前仍不多見,有關立陶宛的歷史與文學出版等也較少。◎ 真實動人。故事出自作者家族的親身經歷,出版至今獲得多項國際獎項,好評不斷,已被翻譯成全球13種語言出版。◎ 繪本作家、推廣人海狗房東翻譯及全力推薦。◎ 特別收錄立陶宛歷史研究所所長許瓦德斯專文導讀。◎ 多位作家、圖文創作者、出版人、導演與立陶宛貿易代表處代表,共同感動推薦。【重要獎項】➢2017立陶宛圖書藝術競賽主獎➢2017立陶宛年度最佳圖書(IBBY)➢2017立陶宛年度最佳童書插圖(IBBY)➢2017白烏鴉奬➢2018 阿洛伊茲.佩特里克(Aloysius Petrikas)文學獎年度童書獎➢2018立陶宛兒童圖書獎➢2020國際兒童圖書評議會榮譽榜➢2020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提名➢2020拉脫維亞兒童圖書評審團入選➢2020拉脫維亞國際 Jānis Baltvilks 獎➢2020義大利波隆那拉加茲獎提名➢2020拉脫維亞版入選拉脫維亞筆會年度最重要書籍名單➢2020拉脫維亞文學獎提名➢2021俄羅斯「閱讀聖彼得堡」國際書籍比賽提名➢2021德國繪本大奬(Deutsche Jugendliteraturpreis)青年讀物類別
人面桃花:王丹散文集
“多少幸福也許就這樣錯過了, 但是錯過了又如何呢? 有時候我們能做的,也就是在時間的縫隙中, 抓住一點點你抓得住的瞬間。” 現實的荒謬與無奈,如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浪潮,拍打著我們已經消磨殆盡的意志。朝霞再美,也宛如稍縱即逝的春花,徒然留在我們稀薄的記憶裡。人生的苦,說要勇敢面對太矯情,說放下太容易。我們,能怎麼辦呢? 我們還能怎麼辦? 我們還有詩,有滿天星斗,有夢,還有山城的細雨濛濛。 從1989年至今,32年來王丹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從那位勇敢而青澀的北大學生,蛻變為成熟而揮灑自如的公共知識分子,始終如一的是他對自由民主的奉獻與對華人政治的關懷。然而,在政治理想之外,更叫他魂牽夢縈的是對文學的熱愛。突如其來的破曉、雪景、山中小鎮的一場雨、浪花譜成的寧靜旋律、一片掉落的葉子、民宿裡的貌似哲學家的貓、一場把你拋進另一個時空的夢,種種生活中難以言說的美好瞬間與回憶,觸動靈魂深處的剎那,才是叫王丹真正牽掛的守護,也是支撐著他面對現實的終極安慰。 本書收錄45篇王丹從2013年以來陸續寫下的心得筆記,內容涵蓋甚廣,包括遊記、影評、書評、樂評、哲學思辨、生活隨筆等各式體裁,從中反映出他對生活、文學、成長、捨、得、記憶與歲月的態度,對於而更多的是他在某個靈感襲來的剎那,那些如夢似幻的細語呢喃。 年過五十的王丹,經歷過當代中國最劇烈的政治抗爭,體驗了流亡海外二十年的滋味,在波士頓念過書,在台灣講過學,少了慷慨的義憤,多了沉澱,少了犀利的政治批判與感時憂國,多了溫潤的對美的想望、對遺憾的接納,與對現實的包容。 曾經,他帶著我們在廣場上衝撞。如今,在他奔放而柔軟的文字中,我們將找到一個寧靜的角落,得以馳騁想像、撫摸回憶,安頓傷痕。 ▓摘錄▓ ///放下的美好/// 「放下,並不是拋棄,而是不再提起。如果我們的佔有的欲望就是生命的全部,看不到更大的世界,一旦放棄,就是生命的崩塌。我們必須找到其他的空間:歌聲、閱讀、行走,或者是新的方向。我們應當讓放下成為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帶著突圍的心情走過/// 「沒有必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堅強,很多時候我們的臉上都是淚水,只是,淚水總是會乾的,或者被時間的風吹乾,或者自己用手背擦乾,如此而已。隨著年齡增長,慢慢地我也知道了,這個世界上,其實有很多的離去與歸來,很多的關閉與重啟。各種不同的機緣與命運交叉纏綿,像會呼吸的水面一樣輕輕起伏……」 ///窗外的城市/// 「為什麼是在星巴克呢?這是個好問題。那是一種莫名的踏實吧?看過了太多的不同,我們會茫然,這個時候,一些熟悉的東西會給我們某種安全感。就像風箏,總有一條線。或者也許是出於懶惰,因為我們不想換新的口味和環境。我們更喜歡熟悉的空間,音樂,座位,熟悉的感覺。更可能,其實是面對流水一般的生活,我們下意識地要守住一些什麼……」 ///童話永遠不會老去/// 「他們在生活中戴上面具出門去工作和交際,然後在回家以後脫下面具,又回復到另外一種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中,他們試圖在荒漠中開拓一片綠洲,他們想像自己找到最神奇的一匹可以駕馭飛翔的白馬,他們會跌坐在黑暗中的沙發上胡思亂想……總之,他們也長大了,但是他們還想保留童年的某些部分。而文學,就是為他們而存在的。在文字的迷宮中,他們找到知音,得到啟迪和感動,並且能夠回到童年的某種精神狀態……」 ///荒謬與反抗──重讀《薛西弗斯的神話》/// 「一個社會反抗者,要想改變社會,必須首先回到自己的內心,先來反抗自己內心的這些『心魔』,戰勝自己內心的這些焦慮。這種自我反抗,可能比對抗外在的暴政更難,但是也比對抗外在的世界更重要。明瞭自己生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中,並且決定面對這樣的荒謬,承擔這樣的荒謬,在這樣的荒謬中堅持自己的追求。」
【電子書】人面桃花
“多少幸福也許就這樣錯過了, 但是錯過了又如何呢? 有時候我們能做的,也就是在時間的縫隙中, 抓住一點點你抓得住的瞬間。” 現實的荒謬與無奈,如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浪潮,拍打著我們已經消磨殆盡的意志。朝霞再美,也宛如稍縱即逝的春花,徒然留在我們稀薄的記憶裡。人生的苦,說要勇敢面對太矯情,說放下太容易。我們,能怎麼辦呢? 我們還能怎麼辦? 我們還有詩,有滿天星斗,有夢,還有山城的細雨濛濛。 從1989年至今,32年來王丹在世人面前的形象從那位勇敢而青澀的北大學生,蛻變為成熟而揮灑自如的公共知識分子,始終如一的是他對自由民主的奉獻與對華人政治的關懷。然而,在政治理想之外,更叫他魂牽夢縈的是對文學的熱愛。突如其來的破曉、雪景、山中小鎮的一場雨、浪花譜成的寧靜旋律、一片掉落的葉子、民宿裡的貌似哲學家的貓、一場把你拋進另一個時空的夢,種種生活中難以言說的美好瞬間與回憶,觸動靈魂深處的剎那,才是叫王丹真正牽掛的守護,也是支撐著他面對現實的終極安慰。 本書收錄45篇王丹從2013年以來陸續寫下的心得筆記,內容涵蓋甚廣,包括遊記、影評、書評、樂評、哲學思辨、生活隨筆等各式體裁,從中反映出他對生活、文學、成長、捨、得、記憶與歲月的態度,對於而更多的是他在某個靈感襲來的剎那,那些如夢似幻的細語呢喃。 年過五十的王丹,經歷過當代中國最劇烈的政治抗爭,體驗了流亡海外二十年的滋味,在波士頓念過書,在台灣講過學,少了慷慨的義憤,多了沉澱,少了犀利的政治批判與感時憂國,多了溫潤的對美的想望、對遺憾的接納,與對現實的包容。 曾經,他帶著我們在廣場上衝撞。如今,在他奔放而柔軟的文字中,我們將找到一個寧靜的角落,得以馳騁想像、撫摸回憶,安頓傷痕。 ▓摘錄▓ ///放下的美好/// 「放下,並不是拋棄,而是不再提起。如果我們的佔有的欲望就是生命的全部,看不到更大的世界,一旦放棄,就是生命的崩塌。我們必須找到其他的空間:歌聲、閱讀、行走,或者是新的方向。我們應當讓放下成為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帶著突圍的心情走過/// 「沒有必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堅強,很多時候我們的臉上都是淚水,只是,淚水總是會乾的,或者被時間的風吹乾,或者自己用手背擦乾,如此而已。隨著年齡增長,慢慢地我也知道了,這個世界上,其實有很多的離去與歸來,很多的關閉與重啟。各種不同的機緣與命運交叉纏綿,像會呼吸的水面一樣輕輕起伏……」 ///窗外的城市/// 「為什麼是在星巴克呢?這是個好問題。那是一種莫名的踏實吧?看過了太多的不同,我們會茫然,這個時候,一些熟悉的東西會給我們某種安全感。就像風箏,總有一條線。或者也許是出於懶惰,因為我們不想換新的口味和環境。我們更喜歡熟悉的空間,音樂,座位,熟悉的感覺。更可能,其實是面對流水一般的生活,我們下意識地要守住一些什麼……」 ///童話永遠不會老去/// 「他們在生活中戴上面具出門去工作和交際,然後在回家以後脫下面具,又回復到另外一種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中,他們試圖在荒漠中開拓一片綠洲,他們想像自己找到最神奇的一匹可以駕馭飛翔的白馬,他們會跌坐在黑暗中的沙發上胡思亂想……總之,他們也長大了,但是他們還想保留童年的某些部分。而文學,就是為他們而存在的。在文字的迷宮中,他們找到知音,得到啟迪和感動,並且能夠回到童年的某種精神狀態……」 ///荒謬與反抗──重讀《薛西弗斯的神話》/// 「一個社會反抗者,要想改變社會,必須首先回到自己的內心,先來反抗自己內心的這些『心魔』,戰勝自己內心的這些焦慮。這種自我反抗,可能比對抗外在的暴政更難,但是也比對抗外在的世界更重要。明瞭自己生活在一個荒謬的世界中,並且決定面對這樣的荒謬,承擔這樣的荒謬,在這樣的荒謬中堅持自己的追求。」
人生太重要,重要到不該嚴肅論之
「推動一個時代的是個性,不是原則。」——王爾德王爾德,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愛爾蘭作家,作品廣受世人歡迎的跨世代文學傳奇偶像。在其短暫、從華麗到頹敗的戲劇性一生中,他以豐沛生動的文字,創作出無數勾引讀者的劇作和小說,流傳後世百年。王爾德對社會和人性的觀察入微、筆鋒尖銳,形容生動,作品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傲人才氣和獨特性情,也濃縮了他對這個世界的洞悉和體悟。本書擷選自王爾德多部著名劇作、小說、訪談,以及評論,二百一十六則中英雙語精妙語句,談男女情愛、人生哲學、藝術時尚、社交機智……句句聰慧幽默、犀利辛辣、痛快直指人心。* 本書2015年曾以《拒絕誘惑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它臣服:王爾德妙語錄》書名出版。
她(二版)
第一次,我發現了我在世界的身分──一個亞洲女人。 頭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不需再跟亞洲女人這個鬼魅似的身分抗辯。 「亞洲女人」。 ——落後的、邊緣化的、被壓迫的、陰柔的、未開發的、被殖民的、傳統的、屈辱的、苦難的、包袱的、努力現代化的。 每一個詞彙都含有新與舊的對立、不同價值的掙扎,聞上去都充滿悲憤而絕望的氣味。亞洲女人,邊緣中的邊緣,弱勢中的弱勢。「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東方才一直是西方觀看的對象。」 但,真的是這樣的嗎?誰來觀看?誰來定義?又是誰來描繪? 胡晴舫在亞洲較頻繁地旅行時,逐漸看清這個出身邏輯的缺陷。然而不僅僅是對於西方人,對於男人,甚至身為一個東亞的華人,亞洲都更容易被簡化,「我天經地義的身分,讓我更輕易忘記省思亞洲的真正意涵。就像我小時候,以為遠方就是西方,我也以為『我』就是東方。」 於是,胡晴舫開始反省,並描繪她所看到的「她」——亞洲女人,那是和寫東方主義的薩伊德或愛談亞洲女人的曲明霞(Trinh Min Ha)不一樣的視角。胡晴舫承認,「她」也是我的「遠方」。「我於是要求她說故事。她的故事。跟隨她話語的腳步,通過她專注的眼神,我讓自己像個無知的孩童,被領入每一座她進入的客廳、每一個她待過的房間、每一間她喝過茶的茶館,認識她認識的人,傾聽她與別人的交談,參觀她櫥櫃裡的衣服,碰觸她心愛的收藏品。」 在她的筆下,「亞洲女人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擁有清楚的相貌和堅實的生活,而不只是抽象的數字、概念、名詞,她們的生命形態應該如同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種類繁複而多樣,活潑旺盛而充滿鬥志,渾然天成而不需詳加解釋。」 亞洲女人是巨大豐富的存在,她們既在北京、孟買、漢城、馬尼拉和加爾各答;也在香港、東京、吉隆坡、上海、新加坡和台北。胡晴舫坦誠,自己並不很熟悉「她」,也不假裝她們是她失散多年的表妹,然而「只因為我們都是所謂的亞洲女人,我尊重她獨特的存在,不願妄加評斷。我也不掩飾自己在聽完故事之後依然懵懂得厲害。」 然而,「頭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不需再跟亞洲女人這個鬼魅似的身分抗辯。她和我,兩個人,就如兩株從亞洲土壤冒出來的花草,在熱帶太陽下,輕輕隨風搖晃,享受就這麼活著的簡單事實。無須向任何人交代。」 《她》是當代華人作家裡少見的對於亞洲女性的「她方」書寫,胡晴舫以慣有的明敏簡潔的速寫刻畫能力,掌握住每個女性身上稍縱即逝的現代特質,勾勒出五十一個「她」所代表的亞洲性格。
【電子書】旅人(新版)(三版)
這是一本旅行哲學指南 也是一本旅人哲學手冊 無論你能否安全抵達你的目的地,你都已經回不去了。 ◎二十一世紀的旅人面對的旅行,甚至不再是真正的旅行。 只是移動。沒有什麼未發現的大陸,沒有什麼神秘難得的香料,沒有什麼待征服的叢林,沒有什麼文明之外的人種,沒有什麼平常生活的邊緣,需要你的身體進入,直接承受強而有力的精神折磨。不論如何,你總有你的熱水、香皂、保養品和睡覺用的牙套。你移動,所以你旅行。 ◎階級是身份。當一個旅人移動時,階級跟著旅行。透過你的機票艙位、手錶、皮箱和給小費的方式,告訴新社會裡的陌生人你的身份。 ◎為了確保旅人看到他們想看的天堂島,一些峇里島人如同熟練的商業劇場經營者,挑出最易認、最膚淺、最討好的文化符號,大量製造,組合出必定賣座的戲碼,全年無休上演。島嶼上充斥廉價的原始情調。只要旅人的眼睛存在,被觀看的城市就被迫矯情。看與被看之間,是權力關係,是含有默契的協定,是一種交換行為。 ◎旅人帶著他的偏見趕路,有些舊偏見被印證,成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見。經由旅人的闖入,則影響了沒有離家的人們看待世界的態度——或,另一面的偏見。 ◎很久很久之後,我才學會欣賞一些不為旅人眼睛存在的城市。我的智慧逐漸足夠理解旅人的眼睛是一天、兩天或二十天就會結束的狀態,當地人的生活卻是一輩子的事情。他們不應該為了陌生人好奇窺探的私慾而活,他們應該為自己和其子孫而活。他們應該根據他們的需求來打造拼裝他們的城市,而不是為了旅人的眼睛勉強築出不適合生活的空間,只為了擺姿態表演。 ◎我們終於來到一個時代:膚色不再能夠指涉國籍,語言不足以涵蓋區域,服裝無以表達任何身份。食物,成為最後一種辨識文化的方法。你居住的城市多「國際化」,端看你有多少食物選擇;你對異質文化的容忍程度有多寬,端賴你對陌生食物的接受態度。 ◎旅遊工業的發達手段幫助旅人條件式地進入異環境,保留環境的大景觀,但,有效殺菌,清除異己,讓旅人能將全世界當作自家客廳般走來走去。旅館就是這樣的機制,過濾並暫時隔絕旅人與異環境的全面接觸。旅館就像旅人的活動堡壘,每天出去衝鋒陷陣,一身污泥,卻總還能夠安全回來,進到規格化的空間,使用熟悉的生活設備……空調設備、現代浴缸、彈簧床、電話、冰桶與裝有CNN電視頻道的電視機。旅館內外,溫度、濕度的指標屬於兩個世界。 ◎機械的複製能力,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經歷一次讀過聽來的故事中主角。文化的瑰麗色彩,增添旅遊故事的價值性。為了白流蘇的一段愛情,一個城市傾圮了;為了旅人的一段旅行,一個文化拿來當襯底。君王的墮落、公主的愛情、家族的興衰、帝國的爭霸,千萬人的財富、風流、血淚、風采,濃縮在一塊背景布裡,供旅人剪裁,造就一段精彩有味的旅遊故事。遺憾的是,機械複製的文化之旅,終究要像一張梵谷《向日葵》畫作的明信片,一只希臘街頭小販叫賣的仿古單耳陶壺,一把現代印度人做出來的古代西塔琴,它們的唯一用途就是證明你那無藥可救的品味,及大眾商業系統的確無所不在。 胡晴舫《旅人》初次上市是在2001年,是一本探討「旅行」這個行為本身的哲學散文文本,而不是私旅行筆記。作者結合自身經驗,分析並解構了現代生活中的「旅行」這件事,探討旅行的本質。 每一個現代人都渴望旅行,期盼上路,需要回家。當你在路上時窺探他者時,實則是驗證了自己,也同時被他人窺探。當你透過旅行修正自己的偏見時,實則可能形成了新的誤解。當你上路,你帶去的不僅是自己,而同時是你的膚色,你的語文,你的國家,你的種族。是你的闖入,才讓當地人搖身變成舞臺上的演員。而你一邊批判文化在旅遊市場裡逐漸墮落,卻又買了一堆媚俗的工藝品回家。當你離開後,你渴望再次前來。現代旅人覺得自己已經不會再對世界感到驚艷,但,仍不免糾纏於日常生活和異國情調的拉扯抗拒。且,無論你能否安全抵達你的目的地,你都已經回不去了。 「在望見表象世界後的另一個世界之後,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再一個世界躲在更後面。而,這正是旅行刺激迷人的地方。作為一個卑微的旅人,我沒有能力詮釋我旅行過的世界,我只能洞察、紀錄、理解,試圖參與,像其它旅人一樣,真實描述我所見到的世界。在顯然動態的旅行中,釐出靜態的時空,找尋自己能夠信賴寄身的價值;並,為了能夠像一個旅人般擁有獨立思索的自由,而感謝上天。」——胡晴舫
【電子書】她(新版)(二版)
第一次,我發現了我在世界的身分──一個亞洲女人。 頭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不需再跟亞洲女人這個鬼魅似的身分抗辯。 「亞洲女人」。 ——落後的、邊緣化的、被壓迫的、陰柔的、未開發的、被殖民的、傳統的、屈辱的、苦難的、包袱的、努力現代化的。 每一個詞彙都含有新與舊的對立、不同價值的掙扎,聞上去都充滿悲憤而絕望的氣味。亞洲女人,邊緣中的邊緣,弱勢中的弱勢。「我突然意識到,其實東方才一直是西方觀看的對象。」 但,真的是這樣的嗎?誰來觀看?誰來定義?又是誰來描繪? 胡晴舫在亞洲較頻繁地旅行時,逐漸看清這個出身邏輯的缺陷。然而不僅僅是對於西方人,對於男人,甚至身為一個東亞的華人,亞洲都更容易被簡化,「我天經地義的身分,讓我更輕易忘記省思亞洲的真正意涵。就像我小時候,以為遠方就是西方,我也以為『我』就是東方。」 於是,胡晴舫開始反省,並描繪她所看到的「她」——亞洲女人,那是和寫東方主義的薩伊德或愛談亞洲女人的曲明霞(Trinh Min Ha)不一樣的視角。胡晴舫承認,「她」也是我的「遠方」。「我於是要求她說故事。她的故事。跟隨她話語的腳步,通過她專注的眼神,我讓自己像個無知的孩童,被領入每一座她進入的客廳、每一個她待過的房間、每一間她喝過茶的茶館,認識她認識的人,傾聽她與別人的交談,參觀她櫥櫃裡的衣服,碰觸她心愛的收藏品。」 在她的筆下,「亞洲女人是一群活生生的人,擁有清楚的相貌和堅實的生活,而不只是抽象的數字、概念、名詞,她們的生命形態應該如同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種類繁複而多樣,活潑旺盛而充滿鬥志,渾然天成而不需詳加解釋。」 亞洲女人是巨大豐富的存在,她們既在北京、孟買、漢城、馬尼拉和加爾各答;也在香港、東京、吉隆坡、上海、新加坡和台北。胡晴舫坦誠,自己並不很熟悉「她」,也不假裝她們是她失散多年的表妹,然而「只因為我們都是所謂的亞洲女人,我尊重她獨特的存在,不願妄加評斷。我也不掩飾自己在聽完故事之後依然懵懂得厲害。」 然而,「頭一次,在我的生命中,我不需再跟亞洲女人這個鬼魅似的身分抗辯。她和我,兩個人,就如兩株從亞洲土壤冒出來的花草,在熱帶太陽下,輕輕隨風搖晃,享受就這麼活著的簡單事實。無須向任何人交代。」 《她》是當代華人作家裡少見的對於亞洲女性的「她方」書寫,胡晴舫以慣有的明敏簡潔的速寫刻畫能力,掌握住每個女性身上稍縱即逝的現代特質,勾勒出五十一個「她」所代表的亞洲性格。
人間喜劇
21世紀的人間喜劇 「這個社會將成為歷史家,我只應充當它的祕書。」 十篇小說 向慾望、貪婪、掙扎、但偉大的人性致敬 也向現實主義致敬 沉浮不定的愛情、財富與權力,逃脫不了的貪婪、背叛與慾望。 21世紀的《私人生活場景》。 ====================== 這些人,都被他們各自的歷史所牽動,沉浮在不同城市的客廳、派對和職場,更被她們內心的慾望所驅動……上演一幕幕喜劇。然而她們不過是被招募的演員,生活在人間劇場的人民公社裡。本書的主角不是這些人物,而是可敬可嘆的人性。 在〈巴黎不屬於任何人〉中,故事的真相不是本文目的,作者採取推理小說的敘事布局,一層一層精心鋪墊,引誘讀者掉進敘述的陷阱;再一層一層無情剝開,打破你以為接近謎底的幻想。最初,你以為主角是正在鬥智角力的兩個男人:一個有著巴黎政經地位;一個是奮鬥多年、失敗入獄的外省人。然而當檢察官馬龍不經意間拋出一個女人的芳名時,他提審的犯人傑克怔住,並徹底崩潰,你才意識到主角可能是這個女人。 然而並非只有傑克的背後藏著一個欺騙了他的女人。只要你在巴黎,這就不是故事的終結。正如標題,這篇小說的主角是巴黎。這座城市「像一個神氣活現的魅力女人,令所有路過的陌生人都軟弱地拜倒在她的裙衩之下。她卻對陌生人想要為她服務的企圖和野心嗤之以鼻,從來不假以辭色,連帶著長期在她腳下討生活的這些蟑螂也這麼仗勢欺人」。 小說的收場,並不是提審的結果,那推理的層層鋪墊根本就是誘餌,根本不重要。在文末,胡晴舫寫到,檢察官馬龍的二十四歲女友登場,他們一起啖生蠔,彼此加溫情慾。「沒打開前,每個人都拼命要用各種方式撬開那頑強的外殼,一嚐鮮美的滋味。」 而他「最愛燈火輝煌的巴黎,在這裡,時光終於為人停駐,生命是一場醉人的盛宴。他不知道他跟眼前這名年輕女友還能維持多久的濃情蜜意,但今晚的生蠔真是鮮美,終生難忘。」本文的主題:巴黎不屬於任何人。然而此刻,人性卻選擇了飛蛾撲火。 這樣的故事一共十篇。21世紀的胡晴舫戴上了19世紀知識分子的巴爾札克眼鏡,鏡片苛刻地折射出21世紀的人類並沒有多大進步。 她向19世紀的偉大作家致敬,在她的版本的《人間喜劇》裡,「巴黎生活場景」替換為東京、台北、新德里、香港、北京和新加坡的私人生活場景。形形色色的人物,無論是從共產國家出走的孤絕男人伊戈(〈所謂的愛〉);還是和印度權貴之子、她口中的法西斯分子結婚的曼哈頓女權主義者莉娜(〈再見,印度〉);無論是從前現代轉向現代的北京鄉下女子陳紅,一身傷痕地回到質樸鄉村男人身邊取暖,再毅然決然撲回北京(〈高跟鞋〉);還是只在美劇裡才看到「性和男人」,卻被迫要和美國女人一起抓姦的台北大齡女子娟娟(〈捉姦記〉)……這些男女都被胡晴舫的古典鏡頭無情打量。 胡晴舫記錄了她這個時代的人間喜劇、風俗畫和「私人生活場景」。你可以視之為《濫情者》的小說版。《濫情者》中的詞條,附體在這些充滿慾望、人性、痛苦和希望的男男女女身上。 這些小說最與眾不同的是,作者以全知視角的古典特權,既借助於她筆下的人物之口,也充分利用敘述者的特權,肆意評點了她筆下的紅塵男女。小說因此既有故事的張力和鮮活的人物,也充滿知識分子的智識,交織著現代性的反思。「巴黎人最拿手的就是說故事。……他們必須如此,不然他們的生活怎能饒富傳奇色彩,為世人所稱羨。畢竟,巴黎可是世界之都,而他們可是巴黎人啊。」以巴黎人的變態邏輯,「當國王不稀奇,砍了國王的頭才是不朽的榮耀。」故事就鑲嵌在類似的評點裡,像多稜鏡一樣彼此折射。 《人間喜劇》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這句話,不論放在19世紀的巴黎和巴爾札克,還是21世紀的台灣和胡晴舫,都一樣成立。
【電子書】我這一代人(新版)
「我以為,現代性會是我們的巨大翅膀。」 如果每一個人類都有他的神祇,那台灣人的神祇是什麼? 胡晴舫這個世代的台灣人尋找到答案了嗎? 「這是一個台灣「現代性孩子」的視野── 從台北到上海到北京,甚至遠及斯里蘭卡, 胡晴舫一邊觀察一邊省思,用一種她獨有的雋永而帶哲理性的文字, 為她這一代台灣人的心路歷程寫下新的見證。」──李歐梵 ==================== 這一次,她把鏡頭轉向了自己所代表的台灣中生代,這一代人成長於七、八○年代迅速現代化的台灣,「在我人生二十到三十歲的黃金時光,我的台灣努力要成為一個自由的象徵、文化的搖籃;最重要的,一個現代的社會。」 而身為一個台灣人,身上所扛負的政治符號與國族糾葛未免不是一個蛇髮女妖的首級。隨便讓她炯如火炬的雙眼看上一眼,都得當場石化,不得動彈。面對這樣巨大的歷史包袱,胡晴舫以為,「現代性會是我們的巨大翅膀,幫助我們飛高,看清楚整個世界的景色,而不只是從我們所站立的地面角度。」 帶著這樣的醒悟,她被現代性的力量所牽引和推動,遊走在香港、北京、上海和新加坡等華人城市。「引我好奇的卻是一個人如何在所謂兩岸三地的社會中游走。當他撘上飛機、飛機落地後的每一次旅程,他如何維持、或重新塑造他的社會身分;他如何說服陌生人,他就是他所說的那個人。」 「面對上海,台灣人拿捏不準自己的態度,因為我們還不知道自己跟他們的關係,或說,我們還未決定自己該跟對方維持如何的一份關係。因為我們還未琢磨出自己是誰。」台灣人面對上海的猶疑,正因爲文化上的輕易跨越,更烘托出政治歧異的進退兩難。 而台北人不能理解香港中環,猶似一顆金銅鑄成的心臟,冰冷無情卻恰如其分地高效率跳動,強力衝刺著足以支撐全香港甚及半個亞洲的資本血液。香港這等視交易為本命、把現實當事實的處世邏輯,跟台北那種追求優渥文化、講究靈性提升的生活態度,如果不是互相歧視排斥,大概也彼此難以信任。然而,六月三十號夜晚到七月一號早晨,一夕之間,香港和台灣在彼此身上認出了兄弟的影子。因為,沒有了英國政府,香港就跟台灣一樣要掙扎於自己既中國又不中國的處境──香港為了國族定位,台灣則為了政治主權。門裡的香港,門外的台灣,透過半掩的門縫交換意味深長的一瞥。 在北京,她愕然發現北京城的安排本是為了服務一位皇帝。城看起來像是一盤棋,很多高手均以為自己只要懂得下棋,這座城市就會是自己的。坐上北京棋盤的中心,就能擁有北京。擁有北京,也就擁有中國。而這個中國,卻不是現代國家理應只看國籍與稅單,不在乎種族膚色的概念。「華人=中國人」這個身分魂魄不散地跟著你,有股時光的霉味,沾滿古老的灰塵,既是一種光榮又是一種詛咒。讓這個族群理所當然地控制你。 在本書最後,胡晴舫把視野轉移到華人世界之外,天外飛來一筆,寫自己在斯里蘭卡從印度洋海嘯的死神之手脫逃而出的經歷,和由此引發的對台灣現代性的反思。身為台灣人,在一塊緊鄰大陸的移民島嶼上,經歷了複雜的殖民階段,本應形成肥沃的現代性土壤,此刻卻充滿了似是而非的族群論證、政治糾葛及文化分歧。「我們堅持只有自己想出來的答案才是正確答案,其他人都可以去死。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神。」 「我以為,現代性會是我們的巨大翅膀。」那麼,現代性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斯里蘭卡裔加拿大作家麥可翁達傑在他的書裡寫道,「榮格在一件事情上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每個人都受他所信奉的神祇所主宰,錯的是妄想和他的神平起平坐。」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這一代台灣人會面臨怎樣的境況呢? 「耶誕節過後的第二天早晨,上帝決定反撲。人類逃無可逃。那些主義口號、宗教衝突、種族偏見和政治歧異都泡在鹹海水裡。」
【電子書】人間喜劇
21世紀的人間喜劇 「這個社會將成為歷史家,我只應充當它的祕書。」 十篇小說 向慾望、貪婪、掙扎、但偉大的人性致敬 也向現實主義致敬 沉浮不定的愛情、財富與權力,逃脫不了的貪婪、背叛與慾望。 21世紀的《私人生活場景》。 ====================== 這些人,都被他們各自的歷史所牽動,沉浮在不同城市的客廳、派對和職場,更被她們內心的慾望所驅動……上演一幕幕喜劇。然而她們不過是被招募的演員,生活在人間劇場的人民公社裡。本書的主角不是這些人物,而是可敬可嘆的人性。 在〈巴黎不屬於任何人〉中,故事的真相不是本文目的,作者採取推理小說的敘事布局,一層一層精心鋪墊,引誘讀者掉進敘述的陷阱;再一層一層無情剝開,打破你以為接近謎底的幻想。最初,你以為主角是正在鬥智角力的兩個男人:一個有著巴黎政經地位;一個是奮鬥多年、失敗入獄的外省人。然而當檢察官馬龍不經意間拋出一個女人的芳名時,他提審的犯人傑克怔住,並徹底崩潰,你才意識到主角可能是這個女人。 然而並非只有傑克的背後藏著一個欺騙了他的女人。只要你在巴黎,這就不是故事的終結。正如標題,這篇小說的主角是巴黎。這座城市「像一個神氣活現的魅力女人,令所有路過的陌生人都軟弱地拜倒在她的裙衩之下。她卻對陌生人想要為她服務的企圖和野心嗤之以鼻,從來不假以辭色,連帶著長期在她腳下討生活的這些蟑螂也這麼仗勢欺人」。 小說的收場,並不是提審的結果,那推理的層層鋪墊根本就是誘餌,根本不重要。在文末,胡晴舫寫到,檢察官馬龍的二十四歲女友登場,他們一起啖生蠔,彼此加溫情慾。「沒打開前,每個人都拼命要用各種方式撬開那頑強的外殼,一嚐鮮美的滋味。」 而他「最愛燈火輝煌的巴黎,在這裡,時光終於為人停駐,生命是一場醉人的盛宴。他不知道他跟眼前這名年輕女友還能維持多久的濃情蜜意,但今晚的生蠔真是鮮美,終生難忘。」本文的主題:巴黎不屬於任何人。然而此刻,人性卻選擇了飛蛾撲火。 這樣的故事一共十篇。21世紀的胡晴舫戴上了19世紀知識分子的巴爾札克眼鏡,鏡片苛刻地折射出21世紀的人類並沒有多大進步。 她向19世紀的偉大作家致敬,在她的版本的《人間喜劇》裡,「巴黎生活場景」替換為東京、台北、新德里、香港、北京和新加坡的私人生活場景。形形色色的人物,無論是從共產國家出走的孤絕男人伊戈(〈所謂的愛〉);還是和印度權貴之子、她口中的法西斯分子結婚的曼哈頓女權主義者莉娜(〈再見,印度〉);無論是從前現代轉向現代的北京鄉下女子陳紅,一身傷痕地回到質樸鄉村男人身邊取暖,再毅然決然撲回北京(〈高跟鞋〉);還是只在美劇裡才看到「性和男人」,卻被迫要和美國女人一起抓姦的台北大齡女子娟娟(〈捉姦記〉)……這些男女都被胡晴舫的古典鏡頭無情打量。 胡晴舫記錄了她這個時代的人間喜劇、風俗畫和「私人生活場景」。你可以視之為《濫情者》的小說版。《濫情者》中的詞條,附體在這些充滿慾望、人性、痛苦和希望的男男女女身上。 這些小說最與眾不同的是,作者以全知視角的古典特權,既借助於她筆下的人物之口,也充分利用敘述者的特權,肆意評點了她筆下的紅塵男女。小說因此既有故事的張力和鮮活的人物,也充滿知識分子的智識,交織著現代性的反思。「巴黎人最拿手的就是說故事。……他們必須如此,不然他們的生活怎能饒富傳奇色彩,為世人所稱羨。畢竟,巴黎可是世界之都,而他們可是巴黎人啊。」以巴黎人的變態邏輯,「當國王不稀奇,砍了國王的頭才是不朽的榮耀。」故事就鑲嵌在類似的評點裡,像多稜鏡一樣彼此折射。 《人間喜劇》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這句話,不論放在19世紀的巴黎和巴爾札克,還是21世紀的台灣和胡晴舫,都一樣成立。
機械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機械製造的特色便是我們的人格: 單一、呆板、無味、重複、規格化、無個體性。 然而,人性卻前所未有地活躍…… 慾望還在,想像力還在,希望還在,夢想還在,嫉妒還在,憤怒還在,瘋狂還在。 人類一切情感能力均完好如初地保存著。可能變種了,但,絕對沒有消失。 它們藏身在46則胡晴舫精心訂製的「戲劇&隨筆體小說」裡。 ================ 在〈瘋狂〉裡,全城的人在四十八小時內傳染上一種神經失調病,症狀是不由自主地拍手、跺腳、歪臉、尖聲高笑。人們起初對疾病恐懼,然後傳染病變成了一個時髦的象徵,人們慣常做愛、吃飯、上班、應酬,開始炫耀誰的病更嚴重。只有一個人,他,端端正正、毫髮無傷。剛開始,善良的他力圖隱藏自己的優越感,七天之後,他發現所有的人都同情地看著他,可憐他的落伍,猜測他應該有不可告人的隱私。最後,他們無法容忍他的健康,無法掩飾對他的厭惡。他們請員警把他制伏,請醫護人員給他注射一針。「當天晚上,新聞播報一個可喜可賀的大消息,全城那個最瘋狂的傢伙終於被治癒了。」 像這樣表述集體主義的有罪和無辜之類的寓言體小說,充滿了卡夫卡式的想像和卡繆的哲思。既荒誕,又理性;既墮落,也救贖。既有罪,也無辜。這些對立的主題互不抵觸,甚至相輔相成。 機械時代的愛,可能是要借助於和別人上床來確認,要在和他者的高潮中浮現自己愛人的臉孔。(〈我跟別人上了床〉) 機械時代的愛,可能存在於虛幻的網路,而「正是因為你完全不存在,我才能夠如此愛你。」「你的真實存在,只會讓我奄奄一息。」(〈我愛你〉) 機械時代的愛,可能是雄性人類不可自拔地愛上了一個完美的女人,個個自信可以得到她,和她上床,進行一場完美的性愛。「再怎麼樣,她也不過是個機器人。」然而她卻愛上一個全身上下絲毫沒有特色的醜小鴨男人。這件事情深深刺激了女性同類,她們紛紛懷著聖母般的情緒獻身給他,想把這隻迷途羔羊拉回正確的軌道。於是他忘記了自己的醜小鴨經歷,周旋於每一場性的遊戲。不理會她受傷的眼神和歇斯底里的悲痛。「再怎麼樣,她也不過是個機器人。」(〈機器人〉) 胡晴舫的書寫是對時代的介入。她冷冽,冷靜,以旁觀者之眼建構她者/他者的形象,故事常常帶有隱喻的色彩。用略帶誇張的白描、勾勒和對白,讀者猶如欣賞46幕現代短劇輪番上演。 如果你要真正理解這個世界,體會人類從手工時代進入機械時代、又反諸手工時代的這個世界,最好的方式是稍微抽離出來,從而能看得更為清楚明白。 任何一個現代男女讀了這本書,都很少不被擊中,不停下來去思考,但實際上是陷入大腦的停滯── 這就是胡晴舫全球化寫作的特質和視野,既有理論的悲憫──當然理論已經全部溶解為場景、對白、短劇,「卻也掩蓋不住張愛玲風的、稍稍過於世故的抒情。」(廖咸浩語) ◎本書插入羅馬尼亞著名畫家波濟胥(Mircea Bochis)的16幅版畫創作,用古老機械的形式載體,和人類亙古不化的情感形成奇妙的共鳴◎
【電子書】城市的憂鬱(新版)
她承續了西方作家如波特萊爾、本雅明,以及卡爾維諾的城市觀察, 但更具當下氣質和華人作家氣質,再現了我們自己時代的現代性。 這是一本為城市翻案的作品, 城市偉大且不朽,就像人類的肉身,會毀滅,但也會復活與重生。 她並不可憎,而鄉愁是人工製造。 只要地球上還有一個城市人活著,他就會再造一座新的城市。 ========== 在華人世界中,城市很早就存在,但是在華文寫作中,城市卻很少成為被解剖和觀察的對象。古代文人喜歡寫《東京夢華錄》,現在的文人雅士們憎惡大都會,多寫農家樂。談論單一的、個體的城市書寫雖然日漸增多,但都是講在地的城市學,訴求小小的樂趣與生活細節,把「鄉愁」形塑為對都市變遷的「懷舊」。 然而,本書作者胡晴舫則更希望往前推究,探討人類城市的共通本質。 她就像巴爾札克在十九世紀末對巴黎充滿好奇,代筆了那個世紀的文化觀察,因為當時的歐洲從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城市面貌和鄉村生活大不同;胡晴舫對當代全球城市現象的好奇,和巴爾札克、本雅明、波特萊爾相似,或者說她接續了這種文化傳統。《城市的憂鬱》是當代華人作家裡罕見的城市書寫,敏感、睿智,無情、極具洞察力,也充滿同理心,只因她自己就是城市的產品。 某種意義上,胡晴舫想要為城市生活翻案。住在城裡的人們,總是太習慣詛咒城市,演變成一種陳腔濫調和政治正確。而她好奇的是這群人們,既然如此痛恨城市,滿懷鄉愁,卻又為何不離開,也無法離開?她著迷於城市人有許多奇怪的情結:既自大又自卑、自憐又自戀、每天覺得站在世界尖峰上,但又覺得自己渺小如螞蟻。而這些性格的矛盾情態,在她尖刻又包容的筆下,栩栩如生地再現。 作者擁有移動多城的經驗,無論是在東京、紐約和巴黎,還是在香港、上海或北京,她捕捉到現代城市共通的符號、狀態與人物。在本書開篇〈而未來在我面前破滅〉一文,她寫道:世上有座城市,總是企圖活在過去。而有另一座城市,拼命想要擺脫過去。第三座城市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他們只活在當下。這一刻。不多一秒,不少一秒。他們不需看錶,因為每個人體內均有一座上緊發條的時鐘,不等鬧鐘醒,他們早已塞車滿城,擠爆地鐵公車,坐在辦公室電腦前,捲上商店鐵門,等不及充分利用他們眼中即將結束的一天。接著,我住進了第四座城市,過去屬於未來,現在就是未來。未來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雖然她居住在不同城市,但是此城和彼城的人並沒有兩樣。人類架構社會的方式本就差不多,全球化更為明顯地加速,使這些符號更為雷同,不分東西方,只因為人的欲望都相同。 本書的風格,是類似波特萊爾式的城市觀察散文,以生活的各個切片來描述城市,外加上本雅明式的總體檢討和抽象提煉。閱讀本書的過程,似乎先是從空中俯視,看到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原來如此脆弱,最終毀滅。然後,我們逼近地面,仔細端詳城中人的各種生活切片。而在結尾處,它的末日就是復活之日,周而復始。 作者筆下的城市,永遠好像一頭充滿魅惑的巨大怪獸,而腐朽、淪落、寂寞、憂鬱的我們沉溺其中,也迷失其中。但是她也發現了人與城市的力量:城市或許會毀滅。但,城市人,這種生物就跟蟑螂一樣,將在城市消逝之後繼續存活許久許久。 只要地球上還有一個城市人活著,他就會再造一座新的城市。
【電子書】機械時代
在這個時代裡,機械製造的特色便是我們的人格: 單一、呆板、無味、重複、規格化、無個體性。 然而,人性卻前所未有地活躍…… 慾望還在,想像力還在,希望還在,夢想還在,嫉妒還在,憤怒還在,瘋狂還在。 人類一切情感能力均完好如初地保存著。可能變種了,但,絕對沒有消失。 它們藏身在46則胡晴舫精心訂製的「戲劇&隨筆體小說」裡。 ================ 在〈瘋狂〉裡,全城的人在四十八小時內傳染上一種神經失調病,症狀是不由自主地拍手、跺腳、歪臉、尖聲高笑。人們起初對疾病恐懼,然後傳染病變成了一個時髦的象徵,人們慣常做愛、吃飯、上班、應酬,開始炫耀誰的病更嚴重。只有一個人,他,端端正正、毫髮無傷。剛開始,善良的他力圖隱藏自己的優越感,七天之後,他發現所有的人都同情地看著他,可憐他的落伍,猜測他應該有不可告人的隱私。最後,他們無法容忍他的健康,無法掩飾對他的厭惡。他們請員警把他制伏,請醫護人員給他注射一針。「當天晚上,新聞播報一個可喜可賀的大消息,全城那個最瘋狂的傢伙終於被治癒了。」 像這樣表述集體主義的有罪和無辜之類的寓言體小說,充滿了卡夫卡式的想像和卡繆的哲思。既荒誕,又理性;既墮落,也救贖。既有罪,也無辜。這些對立的主題互不抵觸,甚至相輔相成。 機械時代的愛,可能是要借助於和別人上床來確認,要在和他者的高潮中浮現自己愛人的臉孔。(〈我跟別人上了床〉) 機械時代的愛,可能存在於虛幻的網路,而「正是因為你完全不存在,我才能夠如此愛你。」「你的真實存在,只會讓我奄奄一息。」(〈我愛你〉) 機械時代的愛,可能是雄性人類不可自拔地愛上了一個完美的女人,個個自信可以得到她,和她上床,進行一場完美的性愛。「再怎麼樣,她也不過是個機器人。」然而她卻愛上一個全身上下絲毫沒有特色的醜小鴨男人。這件事情深深刺激了女性同類,她們紛紛懷著聖母般的情緒獻身給他,想把這隻迷途羔羊拉回正確的軌道。於是他忘記了自己的醜小鴨經歷,周旋於每一場性的遊戲。不理會她受傷的眼神和歇斯底里的悲痛。「再怎麼樣,她也不過是個機器人。」(〈機器人〉) 胡晴舫的書寫是對時代的介入。她冷冽,冷靜,以旁觀者之眼建構她者/他者的形象,故事常常帶有隱喻的色彩。用略帶誇張的白描、勾勒和對白,讀者猶如欣賞46幕現代短劇輪番上演。 如果你要真正理解這個世界,體會人類從手工時代進入機械時代、又反諸手工時代的這個世界,最好的方式是稍微抽離出來,從而能看得更為清楚明白。 任何一個現代男女讀了這本書,都很少不被擊中,不停下來去思考,但實際上是陷入大腦的停滯── 這就是胡晴舫全球化寫作的特質和視野,既有理論的悲憫──當然理論已經全部溶解為場景、對白、短劇,「卻也掩蓋不住張愛玲風的、稍稍過於世故的抒情。」(廖咸浩語) ◎本書插入羅馬尼亞著名畫家波濟胥(Mircea Bochis)的16幅版畫創作,用古老機械的形式載體,和人類亙古不化的情感形成奇妙的共鳴◎
無名者
「我以一張平庸的臉孔,活在一個庸俗的時代。這是科技最新的時候,也是人性最舊的時候。」 「再沒有一個時代比我的時代更大眾化,庸俗,無名,零碎,人人活得面目模糊,躲在面板後頭過日子,汲汲一生尋找免費升級的途徑。」 [Anonymity無名] Anonymity確實和城市關聯,而那些城市都是生命的背景帷幕。「到了陌地生(Madison,亦作麥迪遜),我才明白我擅長獨處。……我注定不偉大,但我還沒開始瞪視自己的平庸,讓自憐變成習慣。我只是坐在那裡。」 而「二十幾歲到香港,我接受了沒有永恆這件事。無止盡的是過渡。什麼都是過渡,什麼都在過渡。我這個人也是過渡。」坐在九龍往港島開駛的渡輪上,夜幕剛垂,天空仍是深黝的黯藍色,中環、金鐘、灣仔一帶的大樓窗口逐漸浮現點點光輝,隨著夜色加深,不一會兒,整座香港島變成鑽石寶山,漂浮於穹蒼與海洋之間,發出不真實的童話光芒。「但,也是那個魔幻時刻,我會突如其來地悲傷。一股關於生命本質的終極哀愁會像一陣不知從何而來的海風,吹上渡輪,襲倒我。那片繁華燈火再輝煌,即將燒乾夜空那般如火如荼;天亮,終究要熄滅。」 作者在不同的城市之間移動,當她離開一座城市,那段人生就結束了,對原來的城市來說,她已經死了。而講述那些曾經的故事,「我都覺得自己在引述一本早已絕版多時的舊小說,主角不是我,只是一個虛構人物,恰巧與我同名,並且因為寫得不太好,所以早就沒什麼人閱讀。我也覺得自己像電視重播一則五十年前發生的歷史新聞,黑白影像,畫質斑駁,我的部分已經抽離了,剩下一些乾巴巴的事實,只有地點、人名和時間是對的,其餘皆顯得可疑,而觀眾呵欠連連,不明白現在重播這條舊新聞的意義。」 胡晴舫以「我」的故事暗喻了所有的人的故事,以「我」的無名嫁接到過去和現在的所有人的無名性。就像法國小說家莫納克在《暗店街》裡的沙灘人,永遠在時代背景裡。「你說時代與他有關,他創造了時代,他砍掉了國王皇后的頭,築起了高牆,又打碎了偶像,但你叫不出他的名字,也記不住他的長相。你唯一意識到他的存在時,你正在歷史博物館閒蕩,而他屬於牆上一張泛黃陳舊的團體照,而你無緣無故為了這張照片慢下腳步,只因攝影師按下快門時,他忘了微笑,留下怪異的表情,形成了視覺的刺點,於是你慢下腳步──你只是慢下,並沒有停下,仍繼續前進。」 「再沒有一個時代比我的時代更大眾化,庸俗,無名,零碎,人人活得面目模糊,躲在面板後頭過日子,汲汲一生尋找免費升級的途徑。一個按鈕,選項接二連三跳出來,彷彿無窮無盡,但全經由同一套軟體跑數據。以為自己自由而獨立,掌握了命運自決的權力,其實不過是一頭終生被困在購物商場無法逃跑的動物,每次選擇,都在消費,終其一生最大的道德責任,只是當好一名按時繳納帳單的消費者。」 那個無名者無處不在。「公車上,那個人輕輕挨著我坐,隔著冬季大衣,我依然微微覺到他的體溫。辦公室裡,那個人坐在我對面辦公,中間擺了兩大台電腦螢幕,我看不見他的臉,但我能聽見他在擤鼻涕,輕輕哀嚎老闆的火急指令。電梯裡,那個人的體味香水縮小了四方空間,逼我被動參與了他與情人斷斷續續的電話交談。醫院裡,他跟我分坐一排椅子,我們看起來一群垂頭喪氣的囚犯,等待命運的判決。大街上,縱使人行道很寬敞,他猛然撞開我的肩膀,昂首闊步離去。那個人,會在夜晚打開窗子哭泣,當我從他樓下走過,因為聽見他的哭聲而抬頭仰望當晚的冷月。」 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那個人。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當這個世界全是數據、實驗、圖表,充滿了大理論、關鍵字,網路匿名、二十四小時實拍,有了臉書、圖享,我們依然無法掌握自己的人性,雖然我們已經學會暴露它、操弄它、分析它,自稱擁有它。 「我以一張平庸的臉孔,活在一個庸俗的時代。這是科技最新的時候,也是人性最舊的時候。」 在胡晴舫看來,無名世界的救贖,只有文學。這也是她以《人類的星空》開篇、以《關於仰望的距離》結束本書的最大原因,「文學教導我人性,學會同理心,尋找那個片刻,一個人存在的本質將如岩岸退潮之後裸露出黑色嶙峋岩石,光天化日之下,散發海洋的腥味,卻閃耀如星光芒。唯有文學能夠帶領我走過那片凹凸不平的人性岩灘。」
濫情者(15周年紀念版)
獻給都會濫情眾生 {胡晴舫 十五週年}紀念版×{聶永真}獨特詮釋 61個詞條 × 61種情境 多年前,胡晴舫和這個世界談的一場激情戀愛 ──即使這個世界從不回頭多看她一眼 你只有抽取了她寫作的具體時空,才會發現文本超越時空的能力 不到三十歲的胡晴舫,好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佩索阿、班雅明一樣,用辭典式寫作完成了自己的跨世紀觀察——空間是在亞洲,這就是《濫情者》,在15年後的今天看,這個早熟的「台灣現代性小孩」(李歐梵語)和那個世界談的一場戀愛,依舊轟轟烈烈,猶如時代列車滾滾而來。如果你不知道此書文本創作於15-20年前,你會認定,這是作者獻給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濫情讀者的一封封獨特的情書。只有在抽取了寫作的具體時空後,文本超越時空的能力才會綻放。 設計師聶永真也是《濫情者》15年前的讀者,他操刀設計的15週年版,以25/35世代的想像和生命經歷為出發點,選擇了「減色野獸派」來詮釋這本經典之作。 胡晴舫最與眾不同的寫作特質是犀利冷雋,而她的主題是永恆的現代性。你可曾在《旅人》中看到胡晴舫自身,看到她是個沉溺於自己感官和心情日記裡的行人?你可曾在《濫情者》裡看到她自身?當她談論著慾望、香菸、性、濫情、傲慢、曖昧……時,那是她自己還是所有的濫情眾生?在台灣文壇洋溢充沛的感性、自我沉溺和私人書寫之際,胡晴舫的存在幾乎是個意外。她實在太理智、太克制、太無情了。 然而,她如此冷雋犀利,卻懂得克制,明白詼諧的價值;她無疑張愛玲般洞悉世事,卻該停下就停下,點到為止;她看到了現代性和人性融合交織成醜陋,卻也不無悲哀憐憫。她如何做到冷血卻又熱血?如何做到無情卻又多情?她如何做到身在台灣之外,心卻徘徊在世界和台灣之內?這是一個等你去尋找、解答的謎題。
【電子書】無名者
「我以一張平庸的臉孔,活在一個庸俗的時代。這是科技最新的時候,也是人性最舊的時候。」 「再沒有一個時代比我的時代更大眾化,庸俗,無名,零碎,人人活得面目模糊,躲在面板後頭過日子,汲汲一生尋找免費升級的途徑。」 [Anonymity無名] Anonymity確實和城市關聯,而那些城市都是生命的背景帷幕。「到了陌地生(Madison,亦作麥迪遜),我才明白我擅長獨處。……我注定不偉大,但我還沒開始瞪視自己的平庸,讓自憐變成習慣。我只是坐在那裡。」 而「二十幾歲到香港,我接受了沒有永恆這件事。無止盡的是過渡。什麼都是過渡,什麼都在過渡。我這個人也是過渡。」坐在九龍往港島開駛的渡輪上,夜幕剛垂,天空仍是深黝的黯藍色,中環、金鐘、灣仔一帶的大樓窗口逐漸浮現點點光輝,隨著夜色加深,不一會兒,整座香港島變成鑽石寶山,漂浮於穹蒼與海洋之間,發出不真實的童話光芒。「但,也是那個魔幻時刻,我會突如其來地悲傷。一股關於生命本質的終極哀愁會像一陣不知從何而來的海風,吹上渡輪,襲倒我。那片繁華燈火再輝煌,即將燒乾夜空那般如火如荼;天亮,終究要熄滅。」 作者在不同的城市之間移動,當她離開一座城市,那段人生就結束了,對原來的城市來說,她已經死了。而講述那些曾經的故事,「我都覺得自己在引述一本早已絕版多時的舊小說,主角不是我,只是一個虛構人物,恰巧與我同名,並且因為寫得不太好,所以早就沒什麼人閱讀。我也覺得自己像電視重播一則五十年前發生的歷史新聞,黑白影像,畫質斑駁,我的部分已經抽離了,剩下一些乾巴巴的事實,只有地點、人名和時間是對的,其餘皆顯得可疑,而觀眾呵欠連連,不明白現在重播這條舊新聞的意義。」 胡晴舫以「我」的故事暗喻了所有的人的故事,以「我」的無名嫁接到過去和現在的所有人的無名性。就像法國小說家莫納克在《暗店街》裡的沙灘人,永遠在時代背景裡。「你說時代與他有關,他創造了時代,他砍掉了國王皇后的頭,築起了高牆,又打碎了偶像,但你叫不出他的名字,也記不住他的長相。你唯一意識到他的存在時,你正在歷史博物館閒蕩,而他屬於牆上一張泛黃陳舊的團體照,而你無緣無故為了這張照片慢下腳步,只因攝影師按下快門時,他忘了微笑,留下怪異的表情,形成了視覺的刺點,於是你慢下腳步──你只是慢下,並沒有停下,仍繼續前進。」 「再沒有一個時代比我的時代更大眾化,庸俗,無名,零碎,人人活得面目模糊,躲在面板後頭過日子,汲汲一生尋找免費升級的途徑。一個按鈕,選項接二連三跳出來,彷彿無窮無盡,但全經由同一套軟體跑數據。以為自己自由而獨立,掌握了命運自決的權力,其實不過是一頭終生被困在購物商場無法逃跑的動物,每次選擇,都在消費,終其一生最大的道德責任,只是當好一名按時繳納帳單的消費者。」 那個無名者無處不在。「公車上,那個人輕輕挨著我坐,隔著冬季大衣,我依然微微覺到他的體溫。辦公室裡,那個人坐在我對面辦公,中間擺了兩大台電腦螢幕,我看不見他的臉,但我能聽見他在擤鼻涕,輕輕哀嚎老闆的火急指令。電梯裡,那個人的體味香水縮小了四方空間,逼我被動參與了他與情人斷斷續續的電話交談。醫院裡,他跟我分坐一排椅子,我們看起來一群垂頭喪氣的囚犯,等待命運的判決。大街上,縱使人行道很寬敞,他猛然撞開我的肩膀,昂首闊步離去。那個人,會在夜晚打開窗子哭泣,當我從他樓下走過,因為聽見他的哭聲而抬頭仰望當晚的冷月。」 沒人知道他在想什麼。那個人。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當這個世界全是數據、實驗、圖表,充滿了大理論、關鍵字,網路匿名、二十四小時實拍,有了臉書、圖享,我們依然無法掌握自己的人性,雖然我們已經學會暴露它、操弄它、分析它,自稱擁有它。 「我以一張平庸的臉孔,活在一個庸俗的時代。這是科技最新的時候,也是人性最舊的時候。」 在胡晴舫看來,無名世界的救贖,只有文學。這也是她以《人類的星空》開篇、以《關於仰望的距離》結束本書的最大原因,「文學教導我人性,學會同理心,尋找那個片刻,一個人存在的本質將如岩岸退潮之後裸露出黑色嶙峋岩石,光天化日之下,散發海洋的腥味,卻閃耀如星光芒。唯有文學能夠帶領我走過那片凹凸不平的人性岩灘。」
【電子書】濫情者(15周年紀念版)
獻給都會濫情眾生 {胡晴舫 十五週年}紀念版×{聶永真}獨特詮釋 61個詞條 × 61種情境 多年前,胡晴舫和這個世界談的一場激情戀愛 ──即使這個世界從不回頭多看她一眼 你只有抽取了她寫作的具體時空,才會發現文本超越時空的能力 不到三十歲的胡晴舫,好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佩索阿、班雅明一樣,用辭典式寫作完成了自己的跨世紀觀察——空間是在亞洲,這就是《濫情者》,在15年後的今天看,這個早熟的「台灣現代性小孩」(李歐梵語)和那個世界談的一場戀愛,依舊轟轟烈烈,猶如時代列車滾滾而來。如果你不知道此書文本創作於15-20年前,你會認定,這是作者獻給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濫情讀者的一封封獨特的情書。只有在抽取了寫作的具體時空後,文本超越時空的能力才會綻放。 設計師聶永真也是《濫情者》15年前的讀者,他操刀設計的15週年版,以25/35世代的想像和生命經歷為出發點,選擇了「減色野獸派」來詮釋這本經典之作。 胡晴舫最與眾不同的寫作特質是犀利冷雋,而她的主題是永恆的現代性。你可曾在《旅人》中看到胡晴舫自身,看到她是個沉溺於自己感官和心情日記裡的行人?你可曾在《濫情者》裡看到她自身?當她談論著慾望、香菸、性、濫情、傲慢、曖昧……時,那是她自己還是所有的濫情眾生?在台灣文壇洋溢充沛的感性、自我沉溺和私人書寫之際,胡晴舫的存在幾乎是個意外。她實在太理智、太克制、太無情了。 然而,她如此冷雋犀利,卻懂得克制,明白詼諧的價值;她無疑張愛玲般洞悉世事,卻該停下就停下,點到為止;她看到了現代性和人性融合交織成醜陋,卻也不無悲哀憐憫。她如何做到冷血卻又熱血?如何做到無情卻又多情?她如何做到身在台灣之外,心卻徘徊在世界和台灣之內?這是一個等你去尋找、解答的謎題。
愛恨,鏡像雙生的情感
「我們愛的,終究是欲望本身,而非欲望的對象。」 愛,是人性中濃烈且直接的情感,它難以抵抗,教人生死相許,心緒百轉千迴。 恨,是愛的另一張臉。它在一線之隔外,映照著愛的幽微與曖昧,洩露甜蜜背後的酸楚、怨懟、妒忌和不堪,讓愛猶如幻夢泡影,如露亦如電,易逝難留。 「真愛只有一種,但副本卻有千百樣貌。」—拉羅什福柯 《愛恨,鏡像雙生的情感》精選葛林、毛姆、尼采、珍・奧斯汀、吳爾芙、海明威、聖修伯里等多位西方作家、藝術家、思想家作品中之精闢語句,雙語對照,呈現這些偉大心靈對於「愛恨」的感受、體悟、詮釋和解讀。書中犀利文句輔以在冷冽或熱情中帶有張力的插圖,細膩呈現人性感情中那愛與恨的多變形貌。 書中同時搭配北歐Peder Severin Krøyer, Vilhelm Hammershøi , Sven Richard Bergh和法國Émile Friant, Gustave Caillebotte,和英國John William Waterhouse等多位畫家的二十餘幅畫作彩圖。犀利文字輔以冷冽平靜中帶有感情緊繃張力的圖像,細膩呈現愛與恨的多種樣貌。
【電子書】真相,是世上最荒誕的笑話:蕭伯納精言集
「每逢滑稽事,最好仔細探究其背後真相。」—蕭伯納 史上唯一同獲奧斯卡金像獎及諾貝爾文學獎的唯一作家。 只有以語言機鋒聞名、智慧卓絕的大文豪,才能對社會提出幽默諷刺又實事求是的針砭觀點——這就是幽默大師,蕭伯納。愛爾蘭裔的蕭伯納最初以樂評及文學批評為生,發表在報章雜誌上的社會評論亦是字字珠璣,但他最傑出的天分仍是劇本創作。蕭伯納的劇作在批判社會問題的嚴肅中仍帶有喜劇風格,使得這些觀點明確、主題鮮明的劇作廣受大眾喜愛。 蕭伯納是史上唯一一位以個人文學貢獻及電影劇本成就,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25) 及奧斯卡金像獎 (1938) 的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稱讚其「作品具有理想主義和人道主義」。而一九六四年由奧黛莉赫本主演的名片《窈窕淑女》(My Fair Lady),亦是改編自他擔任劇本創作的《賣花女》(Pygmalion) 。 本書擷選自蕭伯納多部劇作及評論,以二百二十二則中英雙語的精闢語句,談社會政治、貧富問題、理性思考、教育方式等……呈現一個理性的靈魂如何用最幽默、但也最深刻的文字,闡述他對知識、社會與世界的觀察。
【電子書】拒絕誘惑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它臣服
「人生太重要,重要到不該嚴肅論之。」——王爾德 他用最輕盈的姿態,面對最沉重的人生。 王爾德,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愛爾蘭作家,作品廣受世人歡迎的跨世代文學傳奇偶像。在其短暫、從華麗到頹敗的戲劇性一生中,他以豐沛生動的文字,創作出無數勾引讀者的劇作和小說,流傳後世百年。 王爾德對社會和人性的觀察入微、筆鋒尖銳,形容生動,作品字裡行間無不流露出傲人才氣和獨特性情,也濃縮了他對這個世界的洞悉和體悟。本書擷選自王爾德多部著名劇作、小說、訪談,以及評論,二百一十六則中英雙語精妙語句,談男女情愛、人生哲學、藝術時尚、社交機智……句句聰慧幽默、犀利辛辣、痛快直指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