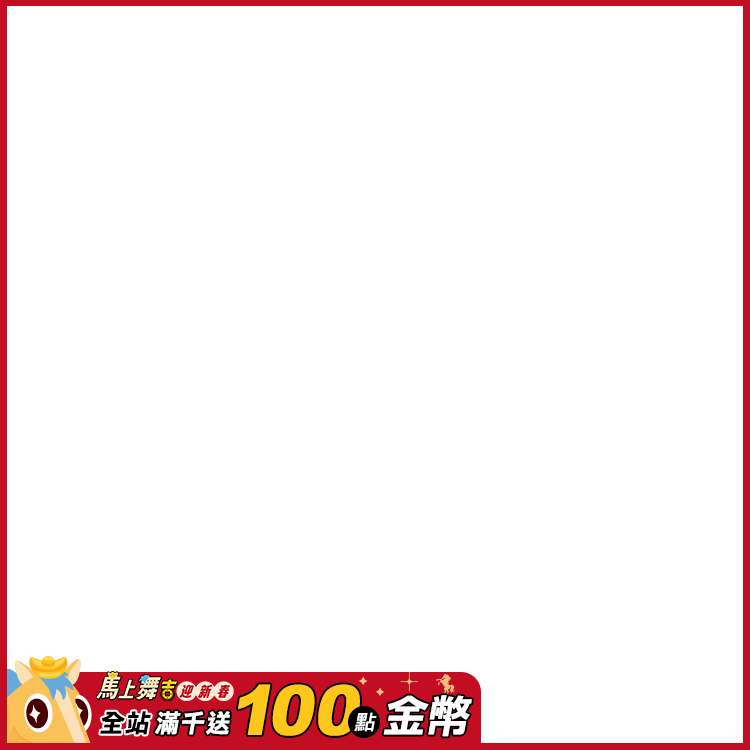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魚雁沈落:狄瑾蓀的詩與翻譯
《莊子.齊物》:「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按莊周齊物之主旨,「沈魚落雁」本指世間美醜是非並無絕對標準,但後人重色,挪用「沈魚落雁」和「閉月羞花」以形容西施、王昭君、貂蟬、楊玉環傾城傾國之美。海德格認為語言召喚存在,如此語言所形構之美才是真實之美/美之真實所在,「沈魚落雁」如何和美有關,我們或許應該從這個觀點出發探索。狄瑾蓀之美正是在於其語言,1775首傳世之作無一不是「絕美」之作。然而此「絕」涵蓄解構之奧義,「絕」是絕無僅有,冠絕群倫,是無法超絕,空前絕後,但也有召喚某種特殊「絕響」之必要,此即源源不絕的不同解釋和翻譯俾以擴充狄瑾蓀之美,希望「異音相從」能交響可能的和諧。「魚雁沈落」於是展示了雙重目的:一是發揮「沈魚落雁」的anagram潛力,使其生生不息,另一則是以「魚雁」往來做為「同情共感」的象徵,藉文學翻譯/詮釋開拓意義的美感,而「沈落」就順勢翻轉成為「鯨落」的暗喻:「一鯨/詩落,萬物/義生」。狄瑾蓀自然生命的結束並非永恆的殞落,反而是felix culpa (fortunate fall),而狄瑾蓀詩的往生更讓文學譯/釋的歷史意義/意義歷史充滿了無限變化的契機。
姯影:七○年代台灣女性小說家的文學再發現
肖瓦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觀察到,女性作家經常被屏棄在經典之外。即使她們關注的議題與男性相同,其創作仍有意無意地被遺忘、忽視。因此,唯有重新挖掘被淹沒和不被重視的女作家作品,文學史的關照才能更多元全面。幾乎所有文學史的著作論及台灣二十世紀女性創作的兩個黃金期,都坐落在五、六○年代和八、九○年代,僅輕描淡寫地帶過七○年代的女性作家。然而,儘管女性確實不喜歡寫鄉土,但是七○年代為數不多的女性鄉土小說也不應在文學史中缺席。尤其男性作家呈現單聲調的創作公式與女性形象,挖掘女性的聲音才能更立體地呈現鄉土文學的全貌。雖然台灣女性文學研究在現今學界已然大鳴大放,但七○年代女性作家的相關研究卻相對闕如。因此,本書就以七○年代的四位小說家曾心儀、謝霜天、季季、荻宜為研究對象,將同類型文學的主流男性作家為參照的隱線,分別自勞工文學、女性性工作者文學、大河小說、農村文學以及武俠小說的主題文學,從而產生性別的對話、差異與補充。此書的五篇專文不僅讓台灣文學的樣貌呈現出不只是單一性別的論述,同時讓七○年代的女性小說家浮出歷史地表。
【電子書】姯影:七0年代台灣女性小說家的文學再發現
肖瓦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中觀察到,女性作家經常被屏棄在經典之外。即使她們關注的議題與男性相同,其創作仍有意無意地被遺忘、忽視。因此,唯有重新挖掘被淹沒和不被重視的女作家作品,文學史的關照才能更多元全面。幾乎所有文學史的著作論及台灣二十世紀女性創作的兩個黃金期,都坐落在五、六○年代和八、九○年代,僅輕描淡寫地帶過七○年代的女性作家。然而,儘管女性確實不喜歡寫鄉土,但是七○年代為數不多的女性鄉土小說也不應在文學史中缺席。尤其男性作家呈現單聲調的創作公式與女性形象,挖掘女性的聲音才能更立體地呈現鄉土文學的全貌。雖然台灣女性文學研究在現今學界已然大鳴大放,但七○年代女性作家的相關研究卻相對闕如。因此,本書就以七○年代的四位小說家曾心儀、謝霜天、季季、荻宜為研究對象,將同類型文學的主流男性作家為參照的隱線,分別自勞工文學、女性性工作者文學、大河小說、農村文學以及武俠小說的主題文學,從而產生性別的對話、差異與補充。此書的五篇專文不僅讓台灣文學的樣貌呈現出不只是單一性別的論述,同時讓七○年代的女性小說家浮出歷史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