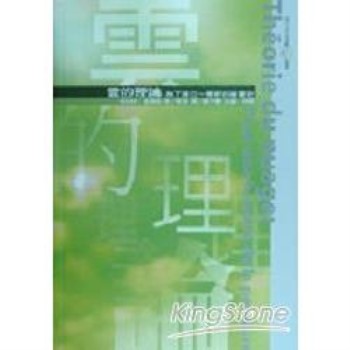當代文化思維@rt叢書
書系 ,共計2筆
-
排序
- 圖片
- 條列
雲的理論:為了建立一種新的繪畫史
揚智文化 出版
2002/01/01 出版
從中世紀一直到十九世紀末,雲一直瀰漫著西方繪畫中的天空。它並非單單是一個描繪性的主題,而是一個繪畫符號學的因素,它的功能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最初,它被用來使神聖事物出現在現實中(基督升天、神秘主義幻象等等,其作用正如戲劇中的機械道具;在文藝復興時期,它的功能變得模稜兩可,因為當時透視模式開始起調節作用。在這一背景下,雲的作用是遮掩住無法表現的無窮,同時它又指示無窮。這樣就保證了一種跟科學條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繪畫機制的悖論式均衡。在本書中探討的,是透過對符號能指/雲/的不同功能的清點,將傳統上歸於藝術的領域與職能,重新分配給處於表現結構中的科學與意識形態:其真正目的是要使藝術史重新找回它的體系性與物質性。
消失的美學
揚智文化 出版
2001/10/01 出版
從經常性失神癲到戀科技癖,從連續攝影術到催眠異語症(xenoglossie),藝術終究不過速度之事,而事件卻翻飛於速度之中,成就了唯一真實的景觀。 一切都再真實不過,虛擬空間以絕對速度慢漶了當下空間。當速度學(dromologie)瞬間粉碎了光速牆,我們懷疑還會有什麼東西是假的?速度成為真實的唯一環境,而二十世紀最終不過是十九世紀諸重大災難的無限擴張與加速。在此,時間的政治經濟學獨領風騷,資本、科技、知識及溝通交叉織構其變貌。科技物件已等同於藝術物件,消失的美學獨樹一幟,絕對的速度機成為絕的原則……
頁數1/1
移至第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