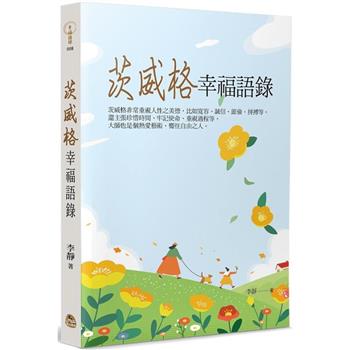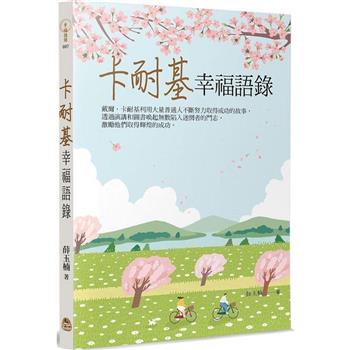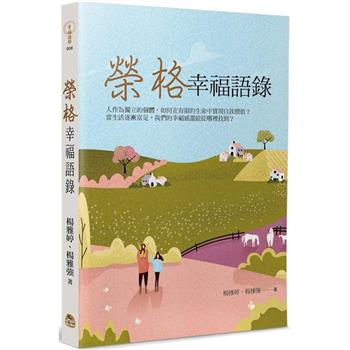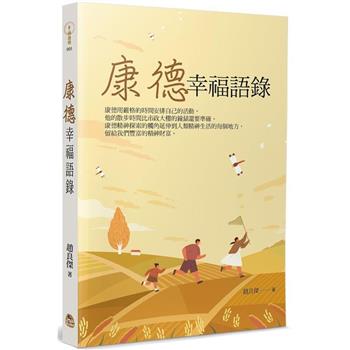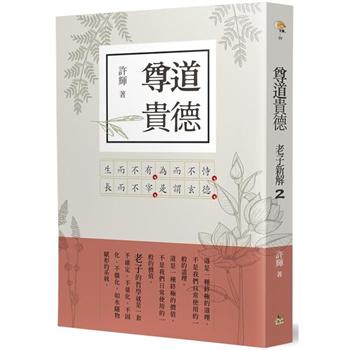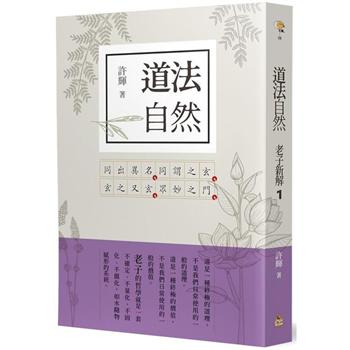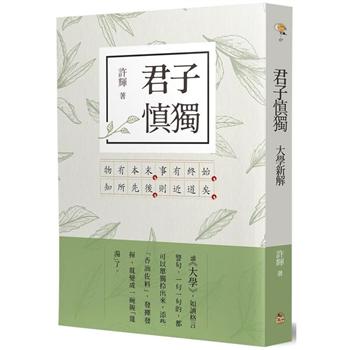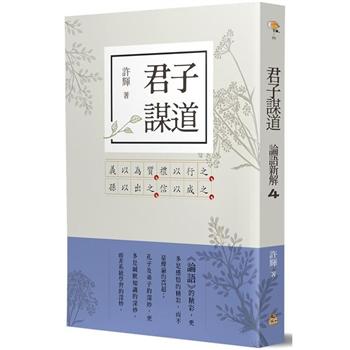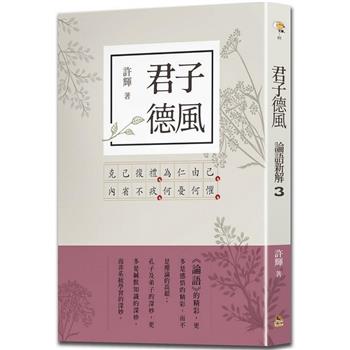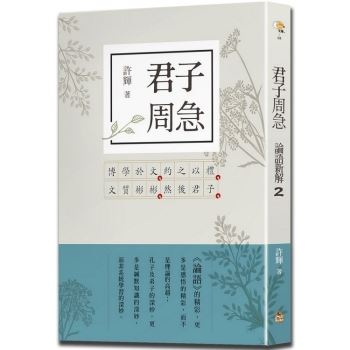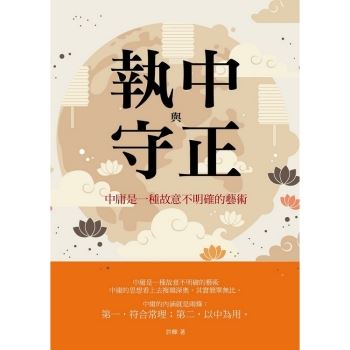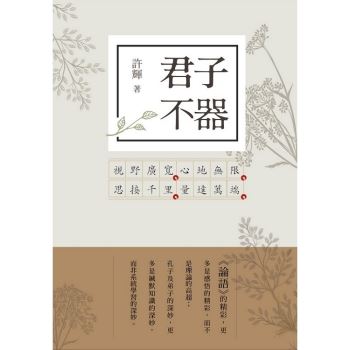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電子書】茨威格幸福語錄
斯蒂芬.茨威格是一個充滿智慧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探討生活的藝術,尋覓快樂生活的真諦。 他熱愛讀書,把書籍當做朋友,與書為伴。 愛情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茨威格在作品中描寫了初戀的細膩、熱戀的熾熱,讓人回味良久。 茨威格的一生中結交了世界各地眾多的朋友,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來自不同的國度、迥異的階層,性格各異,但他們都是一些睿智之人,茨威格都能從他們身上發現優點。 在書中,茨威格非常重視人性之美德,比如寬容、誠信、節儉、拼搏等,還主張珍惜時間、牢記使命、重視過程等。 大師也是個熱愛藝術、嚮往自由之人。
【電子書】卡耐基幸福語錄
世界上發行量最多的書籍非《聖經》莫屬了,但是僅次於《聖經》的又是哪一部著作呢?對此,有不同的答案,有人說是戴爾•卡耐基的《成功學全書》。這一公案暫且擱置,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戴爾•卡耐基其人其作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個世界。 卡耐基的著作卷帙浩繁,我們從中選取了《人性的弱點》、《人性的優點》、《美好的人生》、《快樂的人生》、《成熟的人生》、《寫給女性的忠告》、《語言的突破》、《偉大的人物》、《林肯傳》等九部著作,以期從中擷取一些對我們人生有益的故事,奉獻給讀者。
【電子書】榮格幸福語錄
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自我價值? 當生活逐漸富足,我們的幸福感還能從哪裡找到? 帶著這兩個問題,我們一起閱讀榮格。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是瑞士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 他曾師從佛洛依德,後成為分析心理學(亦稱原型心理學或榮格心理學)的創立者。 本書之所以編選榮格有關幸福的語錄,源自他對現代人靈魂與精神矛盾的關注。
康德幸福語錄
追求永恒的人生價值,是康德終其一生的目的,或者說,是康德幸福論的核心。康德在追求一種超越一般幸福觀念的幸福論。 康德認為,只有站在普遍人類正義的立場,人生才具有意義。每個人終將逝去,而人類卻永恒。只有與普遍人類的福祉相聯繫,個體生命的意義才具有永恒不滅的光輝。因此,研究人成了康德哲學的唯一主題。 康德的一生是屬於學者的一生,他的日常生活單調而重複。為了追求真理,康德對自己的生活極為苛嚴。他終身未離開他的出生地——小鎮格尼斯堡半步,用嚴格的時間安排自己的活動,他的散步時間比市政大樓的鐘錶還要準確。在這狹小的地理空間裡,康德精神探索的觸角卻延伸到人類精神生活的每個地方,留給我們豐富的精神財富。
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電子書】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
同出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電子書】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
同出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君子慎獨:大學新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讀《大學》,如讀格言警句,一句一句的,都可以單獨拎出來,添些「香油佐料」,發揮發揮,就變成一碗碗「雞湯」了。《君子慎獨》是著名作家許輝對儒家經典《大學》的解讀。許輝將《大學》置於厚重的淮河文化背景下,本書既有對《大學》彰顯光明的主題的精彩闡釋,也有對這一主題進行的詳細品讀。著名作家許輝的《君子慎獨》,是以淮河文化解讀儒家經典《大學》的著作,透通過對《大學》的個性化闡釋和具有地域色彩的解讀,反應了許輝多年來對淮河文化進行的文化思考。本書在對《大學》十一章內容進行逐條解讀的基礎上,精彩地闡釋了《大學》的主題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電子書】君子慎獨:大學新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讀《大學》,如讀格言警句,一句一句的,都可以單獨拎出來,添些「香油佐料」,發揮發揮,就變成一碗碗「雞湯」了。《君子慎獨》是著名作家許輝對儒家經典《大學》的解讀。許輝將《大學》置於厚重的淮河文化背景下,本書既有對《大學》彰顯光明的主題的精彩闡釋,也有對這一主題進行的詳細品讀。著名作家許輝的《君子慎獨》,是以淮河文化解讀儒家經典《大學》的著作,透通過對《大學》的個性化闡釋和具有地域色彩的解讀,反應了許輝多年來對淮河文化進行的文化思考。本書在對《大學》十一章內容進行逐條解讀的基礎上,精彩地闡釋了《大學》的主題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君子謀道:論語新解(4)
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說:「君子為道義用心而不為衣食盡力。種地的人有時還會挨餓,學習能夠得到俸祿。君子擔心的是不得道,而不擔心窮困。」人們總是習慣於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更高的標準,說出更多的理由,開出更高的價碼,以使自己的生活變的更美好、環境變的更悅目、物質變的更豐裕、精神變的更充實、規則變的更利己。社會體制和道德體制不得不無止境地,順應人們這種不斷提升的高標準和嚴格要求,這正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特點。
【電子書】君子謀道:論語新解4
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說:「君子為道義用心而不為衣食盡力。種地的人有時還會挨餓,學習能夠得到俸祿。君子擔心的是不得道,而不擔心窮困。」人們總是習慣於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更高的標準,說出更多的理由,開出更高的價碼,以使自己的生活變的更美好、環境變的更悅目、物質變的更豐裕、精神變的更充實、規則變的更利己。社會體制和道德體制不得不無止境地,順應人們這種不斷提升的高標準和嚴格要求,這正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特點。
君子德風:論語新解(3)
克己復禮 為仁由己 內省不疚 何憂何懼《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季康子向孔子問政事:「假如殺掉壞人來成就好人,怎麼樣?」孔子回答道:「您治理社會,還用的著殺?您政風清明,社會風氣就清明。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季康子真是粗陋不堪的,說起話來毫無遮掩。他只知用武,不知有文;只想得到殺人,想不到教化。孔子卻也多見不怪,穩的住,和他談榜樣的力量、德行的風尚。有耐心,有比喻,有文采。
【電子書】君子德風:論語新解3
克己復禮 為仁由己 內省不疚 何憂何懼《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季康子向孔子問政事:「假如殺掉壞人來成就好人,怎麼樣?」孔子回答道:「您治理社會,還用的著殺?您政風清明,社會風氣就清明。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季康子真是粗陋不堪的,說起話來毫無遮掩。他只知用武,不知有文;只想得到殺人,想不到教化。孔子卻也多見不怪,穩的住,和他談榜樣的力量、德行的風尚。有耐心,有比喻,有文采。
君子周急:論語新解(2)
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是外向型人才,而不是內向型人才。以前印象裡他是內向型人才,保守而老態,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或者說,孔子是中庸式人才,他既外向,又內向;需要外向時外向,需要內向時內向。需要唱歌時,他跟人哼唱;需要思考時,他足不出戶;需要輕鬆時,他燕居;需要傳道時,他遊學;需要回絕時,他不賣馬車;需要誨人時,束脩薄禮即可。他既看好顏回的窮困好學,也看好子貢的富足有為;既看好閔子騫的孝順,也看好祝的口才。孔子機靈著呢!
【電子書】君子周急
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是外向型人才,而不是內向型人才。以前印象裡他是內向型人才,保守而老態,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或者說,孔子是中庸式人才,他既外向,又內向;需要外向時外向,需要內向時內向。需要唱歌時,他跟人哼唱;需要思考時,他足不出戶;需要輕鬆時,他燕居;需要傳道時,他遊學;需要回絕時,他不賣馬車;需要誨人時,束脩薄禮即可。他既看好顏回的窮困好學,也看好子貢的富足有為;既看好閔子騫的孝順,也看好祝的口才。孔子機靈著呢!
執中與守正: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的思想看上去複雜深奧,其實簡單無比。 中庸的內涵就是兩條:第一,符合常理;第二,以中為用。 中庸的思想、行為、方式,都是看起來簡單的,似乎只要不冒進、不出頭、不極端、不過分即可,但由於所有的事物都是動態、變化的,所以有時候不冒進恰是消極、不出頭正是貽誤戰機、不極端則是不及、不過分卻是保守。 中庸既是一種內因,也是一種外因,既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迫使。當我們自覺中庸時,我們就少受外力驅使,因為我們已經做到了「最好」。當我們做不到中庸時,外力就會迫使我們中庸,迫使我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到好處」。
君子不器
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 《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 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 多才多藝,就是現在常說的複合型人才。孔子說,君子不能像器物一樣,只有一種用途,第一是說才智和能力,不能過於單一,僅作一用;過於單一,僅作一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器物的浪費。第二是說君子的器量,君子不能像器物般囿於一地,限於一處,可稱可量、可見可算,而應該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第三是說對君子,不能只見一面、不能只觀一方、不能只視一角,君子並非僅此一用;君子本就是複合型的,既有常人情感,也有君子氣質;既有大眾需求,亦有人所不及。
【電子書】執中與守正: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的思想看上去複雜深奧,其實簡單無比。 中庸的內涵就是兩條:第一,符合常理;第二,以中為用。 中庸的思想、行為、方式,都是看起來簡單的,似乎只要不冒進、不出頭、不極端、不過分即可,但由於所有的事物都是動態、變化的,所以有時候不冒進恰是消極、不出頭正是貽誤戰機、不極端則是不及、不過分卻是保守。 中庸既是一種內因,也是一種外因,既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迫使。當我們自覺中庸時,我們就少受外力驅使,因為我們已經做到了「最好」。當我們做不到中庸時,外力就會迫使我們中庸,迫使我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到好處」。
【電子書】君子不器
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 《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 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 多才多藝,就是現在常說的複合型人才。孔子說,君子不能像器物一樣,只有一種用途,第一是說才智和能力,不能過於單一,僅作一用;過於單一,僅作一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器物的浪費。第二是說君子的器量,君子不能像器物般囿於一地,限於一處,可稱可量、可見可算,而應該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第三是說對君子,不能只見一面、不能只觀一方、不能只視一角,君子並非僅此一用;君子本就是複合型的,既有常人情感,也有君子氣質;既有大眾需求,亦有人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