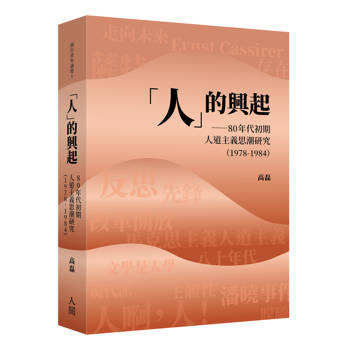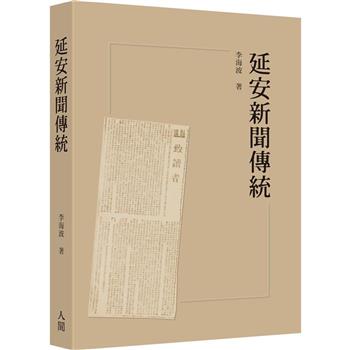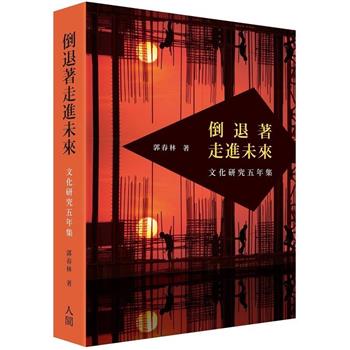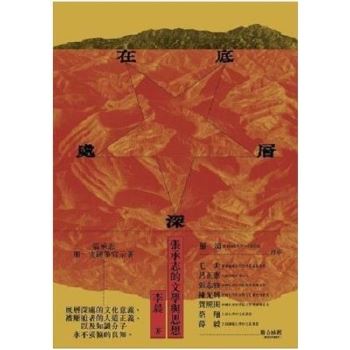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人的興起:80年代初期人道主義思潮研究(1978-1984)
在20世紀中國眾多社會思潮中,人道主義是一股雖時斷時續,但始終綿延不絕的思潮。1980年代初的中國,處於思想與社會劇烈轉向的時代。歷經長期的政治運動之後,改革開放的時代曙光,重新召喚出對「人」的思考。正是在此契機中,「人道主義思潮」再次浮現。由此開啟對「人」的廣泛討論,成為了幾個重要「思想事件」之一,對當時和後來的中國思想走向,都產生了較大影響。本書即以「1980年代初期人道主義思潮」為核心論題,追索它的發生動因、理論資源和思想意涵。研究立足思想與知識的互動關係,兼顧文本細讀與理論分析,重點探討「人道主義」作為一種觀念體系,如何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轉型中被重新激活、詮釋與爭辯,揭示出當代中國思想史中重建人之尊嚴、價值與主體性努力的曲折過程。 研究指出,1980年代初期「人」的問題不只是對啟蒙現代性的再版,而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人」之處境的內在反思。人道主義思潮借助文學話語的「傷痕書寫」,美學與哲學話語的「人學辯論」,並在意識形態領導者周揚、胡喬木的公開論爭中,共同織就了一場跨越文學、美學、哲學的思想大潮。思潮參與者們對「人」的感性書寫與理性思考,目的在於將「人」從階級話語中解救出來,重申「人」生而有之的尊嚴、價值和權利。雖然思潮最終在1984年趨於式微,但其在理論上完成了對「人」的再發現、再探討和有限的再確認,成為後來主體性論述、人學研究和「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思想起點。
延安新聞傳統
中國特色新聞學自延安開始,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因為它與革命黨的使命、執政黨的命運休戚與共。本書描述了延安新聞傳統的來龍去脈,打開了諸多討論的空間。作者把起點放在延安整風和政黨政治革新的敘述框架下,也即「革命史範式」中。雖然「革命史範式」在當下受到諸多質疑和挑戰,但這並不是因為「革命史範式」已經失效,毋寧是對這一範式的把握並沒有真正做到「內在視野」的貫通,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理解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打開「革命史範式」的活力,這也是本書試圖展開的工作。――呂新雨 延安新聞傳統,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現代新聞規範。如果與當代新聞專業主義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無論在形而上的價值訴求,還是在形而下的操作準則方面,都形成鮮明差異,我概括為「業餘路線」。這裡的「業餘」,並不意味著技術水準的低劣,而是強調一種打破專業化社會分工及其局限的自覺狀態,一方面新聞知識分子與社會民眾、進步政治建立有機聯繫,一方面人民群眾投身新聞傳播事業之中,使之真正成為共有、開放的公共領域。用汪暉的話說,「業餘」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一種倫理性的政治」。對於當代的新聞狀況,這無疑提供了一種批判性的思想資源。――李海波
倒退著走進未來:文化研究五年集
這些體式雜亂的文字之所以能放在一起,完全是因「文化研究」之名。它是個嘗試,嘗試著跨出文學領域,看看更大的世界;嘗試著用一套還並不很熟悉的知識和理論重新結構對世界的認識;嘗試著走出書齋和學校,走進更大的人群,了解他們,理解他們;嘗試著轉換一下身分,重新體會向實踐者學習的狀態;嘗試著更直接地面對現實和社會問題;嘗試著重新思考知識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集子中相當一部分文字與新工人這一當代世界最龐大的群體有關,即使涉及歷史和現實中其他議題,也多少與他們相關。我固執地以為他們關乎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郭春林
在底層深處:張承志的文學與思想
張承志是「紅衛兵」這一稱謂的命名者和那場備受爭議的政治運動的參與者,卻拒絕以單純的懺悔對此一帶而過,而是背負著歷史的重量,以身體力行的實踐堅守理想並匡正錯誤;他是新時期初崛起的第一代青年作家,作為上山下鄉運動的親歷者卻從未以哀傷怨懟的筆調記敘無可挽回的青春,而是堅守「為人民」的創作原則,書寫邊疆底層生活帶來的啟示;他是文革結束恢復高考後率先踏足菁英學府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新一代學者,卻從未將知識困於書齋,而是讓雙腳邁入廣袤貧瘠的西北大地深處,更及至東西方接壤的阿拉伯地域;他是早早疏離主流文學圈、毅然放棄公職的自由文人,卻從未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為標尺來丈量中國,而是對新帝國主義霸權在全球的蔓延有超前的警覺和疾呼;他是八十年代理想主義的旗幟,卻從未在理想潰散後的商業主義浪潮中隨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標舉「抗戰文學」;他是虛無主義全面降臨時刻的信仰者,闌入伊斯蘭教卻從未畫地為牢,將宗教版圖視為終極,而是更深地描寫中國,將批判的矛頭和情感的歸宿一併指向中國。 本書特色 張承志用一支硬筆 宣示著底層深處的文化意義、 被壓迫者的人道正義, 以及知識分子永不妥協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