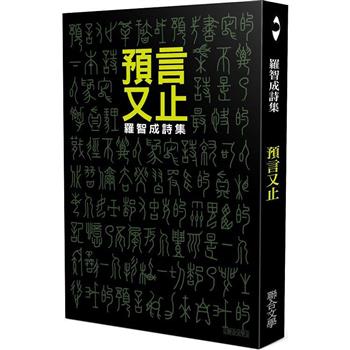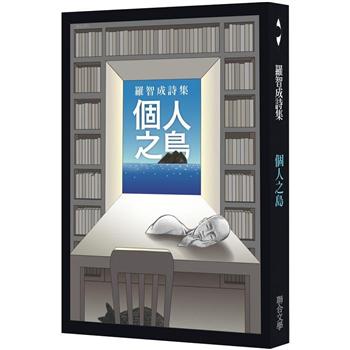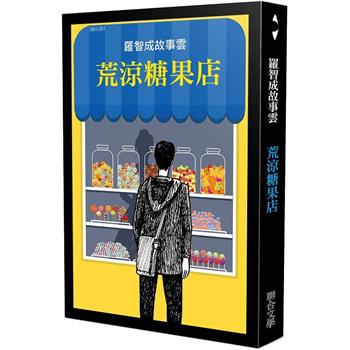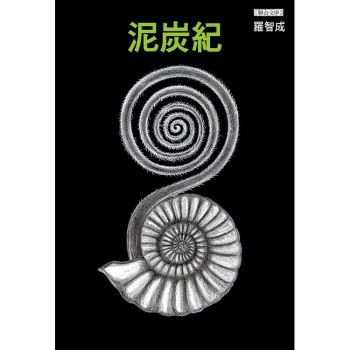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光之書(45週年經典版)
眾方向侷促之所日夜分道的岬角海水奇寒,風浪兇猛這群海不曾負載一條船甚至不曾負載過任河水族邊緣只是嶙岩的剝落和歌唱。巨大是無法馴養的。你要在一萬個行人的袖子裡找到門環叩門如果祂睡著了你要安心等待 ──引自《光之書》,〈芝麻開門〉在詩人的作品中,《光之書》是未經籌謀策畫、在無意識的慣性所作出的作品,可稱為創作時期的某一過渡期、分水嶺,是「結束」,也是「開始」。詩人說,《光之書》的年輕與久遠,讓今日的他感到臉紅,而此書,卻也是他最具個人風格的一本詩集。《光之書》是詩人的第二本詩集,非常年輕,意義卻如此重大:最基本的個性、文字風格以及無法歸類的多樣變貌,在此已有相當完備的展示;往後的各個面向的演變與創新也都可以在此找到明確的線索。而那時的專注與真誠,現在看來已經有了最好的回報。當詩人為自身平凡渺小的生命極力感受、思考、書寫、塗改,甚至頗有煩言時,也正是命運最眷顧詩人的時刻之一。
預言又止
每個女巫都有 一個古老的靈魂 她的記憶已不屬於個體 而是一個族群 一個物種 「一切都已發生過 我預言的能力 來自我的記憶」 《預言又止》基本上是針對某些特定主題長期觀察與省思而來的組詩,每首詩各自獨立,同時又和其它作品有著節奏、主題、情緒、結構或邏輯上的聯繫,所以也帶著某種複合詩體或劇場的氛圍。 這次的主題重返詩人最為關切的文明與人性,不過由於對現實世界以及相關議題有了更直接而深刻的認識,所以減少了長久以來的浪漫憧憬與豪情壯志,顯得沉重、悲觀而殘酷。 開啟這本詩集書寫的另外一個有趣的概念,就是「下一本詩集」;正如以往的每一次,它是詩人突然發現了某件事情的弔詭的修辭,或一次成功地命名。它是一個複雜的象徵,一步一步反應詩人對詩作趨勢的觀察,對詩本質的了解與掌握,以及某種在創作中不停被新發現擠迫的焦慮。「下一本詩集」後設於此刻的書寫,後設於詩人所觀察的一切主題,讓詩人長期陷入一種無所憑依的觀察位置或窘境。
迷宮書店(修訂新版)
請輕聲推門進來 握著僅有的孤獨 誰都知道 孤獨是閱讀的鎖鑰…… 越界、跨界,全新詩劇創作的嘗試,『故事雲』書寫計畫首部曲, 結合故事,詩的元素或某種詩想,和別的表現、表演形式結合在一起 詩皇羅智成邀請你一起進入這本想像中的「迷宮書店」! 在文學領域,文字呈現就是作品的最終形式,在『故事雲』系列裡,這些文字將由視聽、影劇形式進行再創作,而且在書寫期間就已經把這些元素預先植入了。所以,與『故事雲』同步發生的,是對於詩創作的想像一次更大膽的拓展。 文字是現實世界的一環,現實世界靠文字而流傳,他們交集在大腦而安置了世界,腐蝕書中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界線,當你專心閱讀、全神投入,漸漸忘卻分辨真假的,書外世界這個座標的時候,你就已經陷身於文字迷宮。 想像在一間迷宮的書店裡,人們冒險進入閱讀裡面的書,出不來……羅智成把對於書店的種種光怪陸離想像,通過劇場方式召喚出來。藉由劇本說故事的熱情,融入詩句,彼此疊合,互成表裡。 與古人對話,與文學聊天;從《鶯鶯傳》到《紅樓夢》,從《浮士德》到《追憶似水年華》,李清照、小王子、魯迅……等古今中外的文豪與書中角色齊聚,如同波赫士筆下穿梭在黑暗與光明間的先知,羅智成把天堂想像成圖書館,再將世界織就成一座座如迷宮般的花園。他以如夢如幻的文字魅力,建構出無與倫比的詩意迷宮。柔美的語言,訴盡教皇的浪漫多情與魔幻美學。 當初構思《迷宮書店》的時候,我是想用一種比較間接、有趣的方式,來介紹我從小到大幾次印象深刻的閱讀體驗與心得。但我不是在排書單,也不是記流水帳,所以做了許多取捨而漸漸失去原貌。談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學名著,最大的挑戰在於:你的改寫必須符合讀者對它們的印象,但又必須提出超越這些印象的獨到見解,甚至形成對話、辯證或Insight,因為那才是你獨有的貢獻。──羅智成 給我一個好的鬧鐘吧 給我一個安靜的空間 我將好好地讀一本書 我最珍貴的夢想 就在裡頭。
【電子書】迷宮書店(修訂新版)
請輕聲推門進來 握著僅有的孤獨 誰都知道 孤獨是閱讀的鎖鑰…… 越界、跨界,全新詩劇創作的嘗試,『故事雲』書寫計畫首部曲, 結合故事,詩的元素或某種詩想,和別的表現、表演形式結合在一起 詩皇羅智成邀請你一起進入這本想像中的「迷宮書店」! 在文學領域,文字呈現就是作品的最終形式,在『故事雲』系列裡,這些文字將由視聽、影劇形式進行再創作,而且在書寫期間就已經把這些元素預先植入了。所以,與『故事雲』同步發生的,是對於詩創作的想像一次更大膽的拓展。 文字是現實世界的一環,現實世界靠文字而流傳,他們交集在大腦而安置了世界,腐蝕書中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界線,當你專心閱讀、全神投入,漸漸忘卻分辨真假的,書外世界這個座標的時候,你就已經陷身於文字迷宮。 想像在一間迷宮的書店裡,人們冒險進入閱讀裡面的書,出不來……羅智成把對於書店的種種光怪陸離想像,通過劇場方式召喚出來。藉由劇本說故事的熱情,融入詩句,彼此疊合,互成表裡。 與古人對話,與文學聊天;從《鶯鶯傳》到《紅樓夢》,從《浮士德》到《追憶似水年華》,李清照、小王子、魯迅……等古今中外的文豪與書中角色齊聚,如同波赫士筆下穿梭在黑暗與光明間的先知,羅智成把天堂想像成圖書館,再將世界織就成一座座如迷宮般的花園。他以如夢如幻的文字魅力,建構出無與倫比的詩意迷宮。柔美的語言,訴盡教皇的浪漫多情與魔幻美學。 當初構思《迷宮書店》的時候,我是想用一種比較間接、有趣的方式,來介紹我從小到大幾次印象深刻的閱讀體驗與心得。但我不是在排書單,也不是記流水帳,所以做了許多取捨而漸漸失去原貌。談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學名著,最大的挑戰在於:你的改寫必須符合讀者對它們的印象,但又必須提出超越這些印象的獨到見解,甚至形成對話、辯證或Insight,因為那才是你獨有的貢獻。──羅智成 給我一個好的鬧鐘吧 給我一個安靜的空間 我將好好地讀一本書 我最珍貴的夢想 就在裡頭。
【電子書】迷宮書店
請輕聲推門進來 握著僅有的孤獨 誰都知道 孤獨是閱讀的鎖鑰…… 越界、跨界,全新詩劇創作的嘗試,『故事雲』書寫計畫首部曲, 結合故事,詩的元素或某種詩想,和別的表現、表演形式結合在一起 詩皇羅智成邀請你一起進入這本想像中的「迷宮書店」! 在文學領域,文字呈現就是作品的最終形式,在『故事雲』系列裡,這些文字將由視聽、影劇形式進行再創作,而且在書寫期間就已經把這些元素預先植入了。所以,與『故事雲』同步發生的,是對於詩創作的想像一次更大膽的拓展。 文字是現實世界的一環,現實世界靠文字而流傳,他們交集在大腦而安置了世界,腐蝕書中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界線,當你專心閱讀、全神投入,漸漸忘卻分辨真假的,書外世界這個座標的時候,你就已經陷身於文字迷宮。 想像在一間迷宮的書店裡,人們冒險進入閱讀裡面的書,出不來……羅智成把對於書店的種種光怪陸離想像,通過劇場方式召喚出來。藉由劇本說故事的熱情,融入詩句,彼此疊合,互成表裡。 與古人對話,與文學聊天;從《鶯鶯傳》到《紅樓夢》,從《浮士德》到《追憶似水年華》,李清照、小王子、魯迅……等古今中外的文豪與書中角色齊聚,如同波赫士筆下穿梭在黑暗與光明間的先知,羅智成把天堂想像成圖書館,再將世界織就成一座座如迷宮般的花園。他以如夢如幻的文字魅力,建構出無與倫比的詩意迷宮。柔美的語言,訴盡教皇的浪漫多情與魔幻美學。 當初構思《迷宮書店》的時候,我是想用一種比較間接、有趣的方式,來介紹我從小到大幾次印象深刻的閱讀體驗與心得。但我不是在排書單,也不是記流水帳,所以做了許多取捨而漸漸失去原貌。談這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文學名著,最大的挑戰在於:你的改寫必須符合讀者對它們的印象,但又必須提出超越這些印象的獨到見解,甚至形成對話、辯證或Insight,因為那才是你獨有的貢獻。──羅智成 給我一個好的鬧鐘吧 給我一個安靜的空間 我將好好地讀一本書 我最珍貴的夢想 就在裡頭。
個人之島
為了尋找一句美麗的話 幾乎不可能存在 卻滿心期待 觹刻我們豐盛的記憶 觸撫彼此疲憊的靈魂 也許妳就是那句話 而我已無法說出…… 但我仍必須去說 去尋找 為了妳 為了在語言的蜂巢中 蜜的醞釀而酩酊 但我忍不住在此告白,每當我忽略掉寫詩這件事,只是專心在想,專心在感受時,似乎更能直接與我所追求的事物對話,像詩的靈媒一樣。那時,我更接近詩,甚至與它同生共存,在片刻歡愉與憂傷裡…… ──羅智成 《個人之島》書名和《地球之島》同時產生。但是兩本詩集的屬性不同。 《個人之島》是一本選集,沒有特定的形式,沒有特定的主題,是詩人把過去發表過或沒有發表過的一些作品,做一次與時俱進的整理。 《個人之島》粗略分做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接近《寶寶之書》或《黑色鑲金》的微型書寫,所以大部分連題目都沒有冠上,直接叫「未命名的詩行」。 與書名「個人之島」相同的第二部分,以現實生活裡的時空記憶為主,特別是在台灣各個角落或不同時刻的體驗與心情。詩人在這方面的書寫非常多(本書只選了一部分),而且極少發表。另外,也忍不住把過去收在別的集子裡的幾首相關作品擺進來。 第三部分,「51%甜言蜜語」,是詩人對於詩的聽覺元素特別關心與好奇,總想把語言或文字還原成為被聽見那一刻的感覺,所以除了「新絕句」在《地球之島》裡的嚐試外,這裡的許多作品,甚至是帶著填寫歌詞或哼歌的節奏在進行。這樣的表現因為要訴諸聽覺,所以遣詞用句或語法都必須更為淺白、直接,跟過去嚴格要求精確、或貼近意識的工筆寫實有很大的差別。 詩人自述:因為沒有計畫、沒有架構性思維,反而更靠近平常的自己,少了對作品慣性的保護與防衛,因而也帶著某種冒險趣味。
【電子書】個人之島
為了尋找一句美麗的話 幾乎不可能存在 卻滿心期待 觹刻我們豐盛的記憶 觸撫彼此疲憊的靈魂 也許妳就是那句話 而我已無法說出…… 但我仍必須去說 去尋找 為了妳 為了在語言的蜂巢中 蜜的醞釀而酩酊 但我忍不住在此告白,每當我忽略掉寫詩這件事,只是專心在想,專心在感受時,似乎更能直接與我所追求的事物對話,像詩的靈媒一樣。那時,我更接近詩,甚至與它同生共存,在片刻歡愉與憂傷裡…… ──羅智成 《個人之島》書名和《地球之島》同時產生。但是兩本詩集的屬性不同。 《個人之島》是一本選集,沒有特定的形式,沒有特定的主題,是詩人把過去發表過或沒有發表過的一些作品,做一次與時俱進的整理。 《個人之島》粗略分做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接近《寶寶之書》或《黑色鑲金》的微型書寫,所以大部分連題目都沒有冠上,直接叫「未命名的詩行」。 與書名「個人之島」相同的第二部分,以現實生活裡的時空記憶為主,特別是在台灣各個角落或不同時刻的體驗與心情。詩人在這方面的書寫非常多(本書只選了一部分),而且極少發表。另外,也忍不住把過去收在別的集子裡的幾首相關作品擺進來。 第三部分,「51%甜言蜜語」,是詩人對於詩的聽覺元素特別關心與好奇,總想把語言或文字還原成為被聽見那一刻的感覺,所以除了「新絕句」在《地球之島》裡的嚐試外,這裡的許多作品,甚至是帶著填寫歌詞或哼歌的節奏在進行。這樣的表現因為要訴諸聽覺,所以遣詞用句或語法都必須更為淺白、直接,跟過去嚴格要求精確、或貼近意識的工筆寫實有很大的差別。 詩人自述:因為沒有計畫、沒有架構性思維,反而更靠近平常的自己,少了對作品慣性的保護與防衛,因而也帶著某種冒險趣味。
【電子書】個人之島
為了尋找一句美麗的話 幾乎不可能存在 卻滿心期待 觹刻我們豐盛的記憶 觸撫彼此疲憊的靈魂 也許妳就是那句話 而我已無法說出…… 但我仍必須去說 去尋找 為了妳 為了在語言的蜂巢中 蜜的醞釀而酩酊 但我忍不住在此告白,每當我忽略掉寫詩這件事,只是專心在想,專心在感受時,似乎更能直接與我所追求的事物對話,像詩的靈媒一樣。那時,我更接近詩,甚至與它同生共存,在片刻歡愉與憂傷裡…… ──羅智成 《個人之島》書名和《地球之島》同時產生。但是兩本詩集的屬性不同。 《個人之島》是一本選集,沒有特定的形式,沒有特定的主題,是詩人把過去發表過或沒有發表過的一些作品,做一次與時俱進的整理。 《個人之島》粗略分做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接近《寶寶之書》或《黑色鑲金》的微型書寫,所以大部分連題目都沒有冠上,直接叫「未命名的詩行」。 與書名「個人之島」相同的第二部分,以現實生活裡的時空記憶為主,特別是在台灣各個角落或不同時刻的體驗與心情。詩人在這方面的書寫非常多(本書只選了一部分),而且極少發表。另外,也忍不住把過去收在別的集子裡的幾首相關作品擺進來。 第三部分,「51%甜言蜜語」,是詩人對於詩的聽覺元素特別關心與好奇,總想把語言或文字還原成為被聽見那一刻的感覺,所以除了「新絕句」在《地球之島》裡的嚐試外,這裡的許多作品,甚至是帶著填寫歌詞或哼歌的節奏在進行。這樣的表現因為要訴諸聽覺,所以遣詞用句或語法都必須更為淺白、直接,跟過去嚴格要求精確、或貼近意識的工筆寫實有很大的差別。 詩人自述:因為沒有計畫、沒有架構性思維,反而更靠近平常的自己,少了對作品慣性的保護與防衛,因而也帶著某種冒險趣味。
荒涼糖果店
在生命與死亡過度的地方, 假如有一家神秘的糖果店, 人們將在此註銷原先的記憶, 或者,甚至換上全新的記憶, 死亡或重生之旅是否不再令人畏懼? 詩人在文字裡寄託、留下令人牽掛的審美對象,就是《荒涼糖果店》最早先的構想,也是「故事雲」另一個新的實驗。 空間是「終極媒體」,因為你(讀者)已經在現場了,不再需要任何媒介,就可以親身接觸、感受這個空間所傳達的訊息。 在這裡,詩人布置的空間是一座古城、一間糖果店、一處濱海的庭園。 這樣的特定空間裡會讓你聯想到什麼?想做甚麼?或預期發生甚麼? 倒推回去,就是你所接收到的訊息。
【電子書】荒涼糖果店
在生命與死亡過度的地方, 假如有一家神秘的糖果店, 人們將在此註銷原先的記憶, 或者,甚至換上全新的記憶, 死亡或重生之旅是否不再令人畏懼? 詩人在文字裡寄託、留下令人牽掛的審美對象,就是《荒涼糖果店》最早先的構想,也是「故事雲」另一個新的實驗。 空間是「終極媒體」,因為你(讀者)已經在現場了,不再需要任何媒介,就可以親身接觸、感受這個空間所傳達的訊息。 在這裡,詩人布置的空間是一座古城、一間糖果店、一處濱海的庭園。 這樣的特定空間裡會讓你聯想到什麼?想做甚麼?或預期發生甚麼? 倒推回去,就是你所接收到的訊息。
【電子書】荒涼糖果店
在生命與死亡過度的地方, 假如有一家神秘的糖果店, 人們將在此註銷原先的記憶, 或者,甚至換上全新的記憶, 死亡或重生之旅是否不再令人畏懼? 詩人在文字裡寄託、留下令人牽掛的審美對象,就是《荒涼糖果店》最早先的構想,也是「故事雲」另一個新的實驗。 空間是「終極媒體」,因為你(讀者)已經在現場了,不再需要任何媒介,就可以親身接觸、感受這個空間所傳達的訊息。 在這裡,詩人布置的空間是一座古城、一間糖果店、一處濱海的庭園。 這樣的特定空間裡會讓你聯想到什麼?想做甚麼?或預期發生甚麼? 倒推回去,就是你所接收到的訊息。
泥炭紀
無法歸類的作者‧無法歸類的文體 《泥炭紀》的代表思想略早於《光之書》,其中許多字句則可以溯源到作者最初的練習作品。其基本材料來自1974至1979年間的殘稿與札記,包括1973年「異教徒手札」(收錄於1975年《畫冊》)的餘緒及未收進「語錄」的各式構想;可謂微宇宙教皇青年時期狂放思想的證據。 整體而言,《泥炭紀》迷漫著極為純粹、質樸的「異教徒」氛圍。「異教徒」是作者從高中時期就十分偏好的詞語,它原本是西方主流宗教對其他教派、無神論者或異議者的指稱,先天帶著排斥、歧視的負面意含,更帶有孤立、神秘、特立獨行的形象,因此給予很多想像的空間與能量。 「我不以為《泥炭紀》需要任何說明;騷動與年輕應足以懂騷動與年輕。而我愛極這讓我受窘的,那時候的自己。」 「《泥炭紀》是一段孤獨、漫長而自我慰藉的創作歷程與結果,那樣的勇氣與天真,已無法再現。有時,我甚至視之為成長過程中,一段「誤入歧途」的過程,必須在往後強作解人,不時加以合理化。但是當時多相關的記憶早已模糊淹沒,《泥炭紀》的內容,竟成為某個時期我唯一的記憶。」--羅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