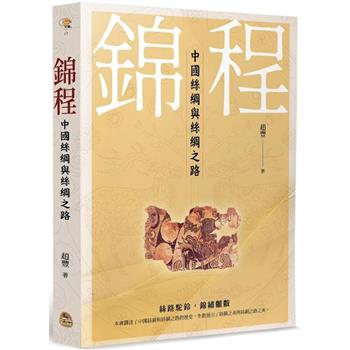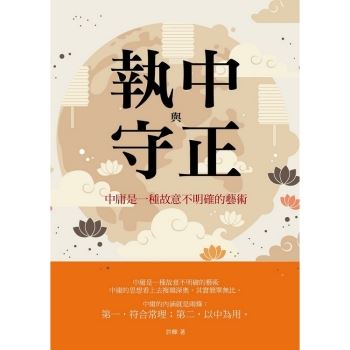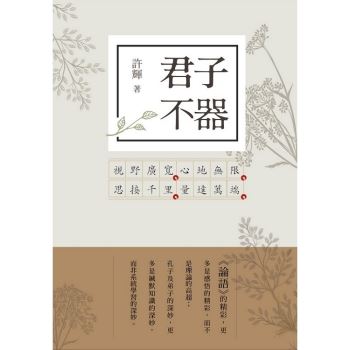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執中與守正: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的思想看上去複雜深奧,其實簡單無比。 中庸的內涵就是兩條:第一,符合常理;第二,以中為用。 中庸的思想、行為、方式,都是看起來簡單的,似乎只要不冒進、不出頭、不極端、不過分即可,但由於所有的事物都是動態、變化的,所以有時候不冒進恰是消極、不出頭正是貽誤戰機、不極端則是不及、不過分卻是保守。 中庸既是一種內因,也是一種外因,既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迫使。當我們自覺中庸時,我們就少受外力驅使,因為我們已經做到了「最好」。當我們做不到中庸時,外力就會迫使我們中庸,迫使我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到好處」。
君子不器
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 《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 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 多才多藝,就是現在常說的複合型人才。孔子說,君子不能像器物一樣,只有一種用途,第一是說才智和能力,不能過於單一,僅作一用;過於單一,僅作一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器物的浪費。第二是說君子的器量,君子不能像器物般囿於一地,限於一處,可稱可量、可見可算,而應該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第三是說對君子,不能只見一面、不能只觀一方、不能只視一角,君子並非僅此一用;君子本就是複合型的,既有常人情感,也有君子氣質;既有大眾需求,亦有人所不及。
【電子書】執中與守正: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是一種故意不明確的藝術 中庸的思想看上去複雜深奧,其實簡單無比。 中庸的內涵就是兩條:第一,符合常理;第二,以中為用。 中庸的思想、行為、方式,都是看起來簡單的,似乎只要不冒進、不出頭、不極端、不過分即可,但由於所有的事物都是動態、變化的,所以有時候不冒進恰是消極、不出頭正是貽誤戰機、不極端則是不及、不過分卻是保守。 中庸既是一種內因,也是一種外因,既是一種自覺,也是一種迫使。當我們自覺中庸時,我們就少受外力驅使,因為我們已經做到了「最好」。當我們做不到中庸時,外力就會迫使我們中庸,迫使我們「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到好處」。
【電子書】君子不器
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 《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 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 多才多藝,就是現在常說的複合型人才。孔子說,君子不能像器物一樣,只有一種用途,第一是說才智和能力,不能過於單一,僅作一用;過於單一,僅作一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器物的浪費。第二是說君子的器量,君子不能像器物般囿於一地,限於一處,可稱可量、可見可算,而應該視野廣寬、心地無限,思接千里、量達萬端。第三是說對君子,不能只見一面、不能只觀一方、不能只視一角,君子並非僅此一用;君子本就是複合型的,既有常人情感,也有君子氣質;既有大眾需求,亦有人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