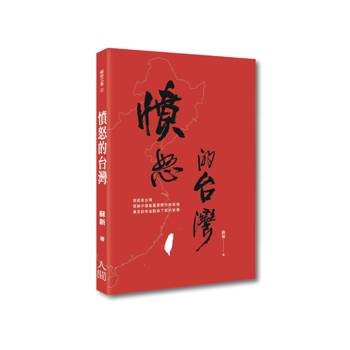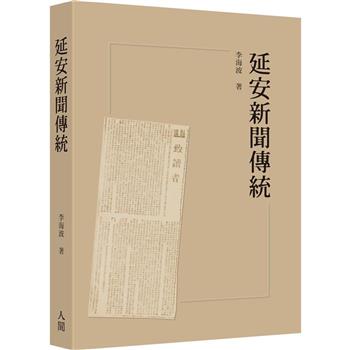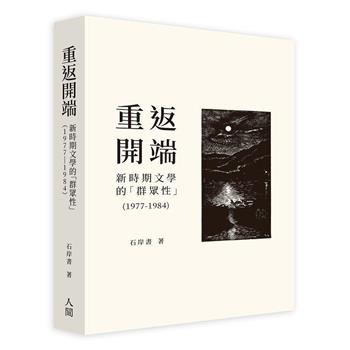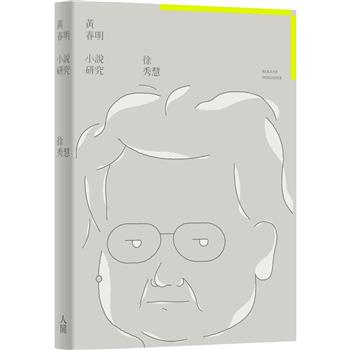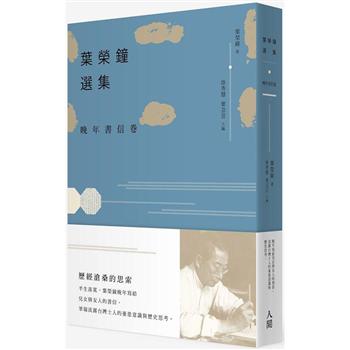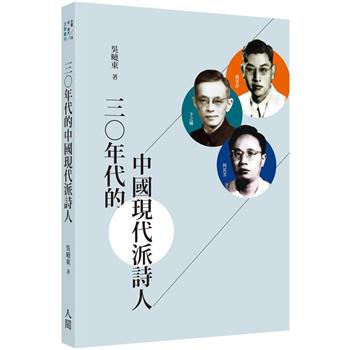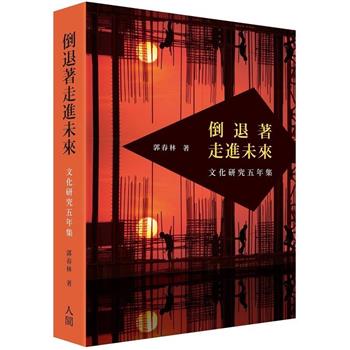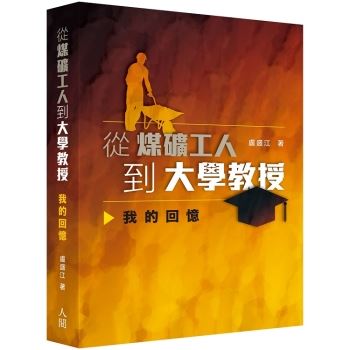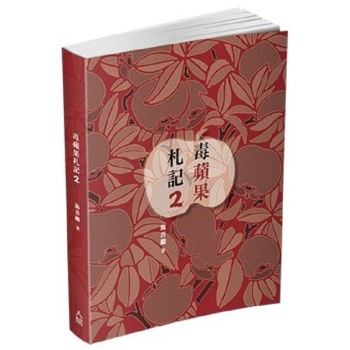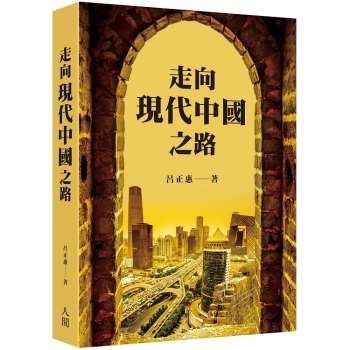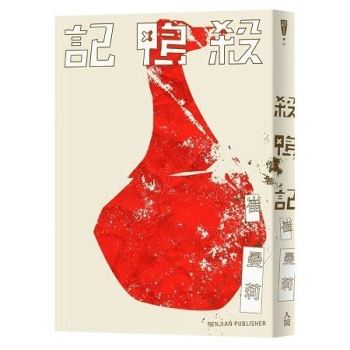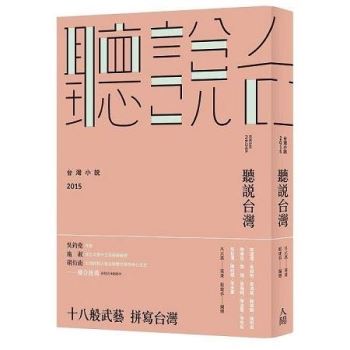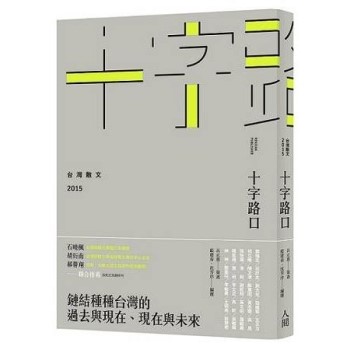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憤怒的台灣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二年,從香港到台北,《憤怒的台灣》所走過的曲折歷程,恰恰反映了台灣.中國近代史中的悲劇性,只是這樣的歷史悲劇似乎又到了另一個轉折的關鍵年代!然而,悲劇的歷史顯然沒有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從而讓人們有智慧地處理歷史遺留的台灣問題。三十三年之後,在帝國主義與野心政客的刻意操弄下,兩岸關係又瀕臨兵凶戰危的悲劇邊緣,戰火一觸即發,人民的身家性命朝不保夕。歷史彷彿又回到一九四九年的關鍵節點,當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也到了不得不面對解決的時刻。 今年恰逢台灣建省一百四十年,馬關割台一百三十年,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八十週年。值此具有重大意義的光榮年代,人間出版社取得蘇新滯留大陸後出生的兒子蘇宏先生的授權,重新出版已經絕版多年的《憤怒的台灣》,同時收錄了曾健民醫師生前從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光明報》第二卷第十二期挖掘出來的蘇新遺作〈談台灣解放問題〉,以及林書揚與陳映真先生閱讀後的感懷回應,作為節日的紀念與人間再出發的獻禮。
現代中國文藝與伊斯蘭表述
現代中國伊斯蘭的命運如何?其發生了怎樣的歷史變遷?她如何表述與被表述?本書由文藝視角出發,兼及文藝深刻勾連的思想和歷史視野,通過查閱大量現代中國各族知識分子的相關實踐文本,以此鉤稽、深描和重思現代中國伊斯蘭及穆斯林人群的革變、再造和流動,及其在多種文藝形式中的表述史,呈現他們被遮隱的另一重面影與心靈,為跨體系社會的中國及其現實與未來提供可資借鑒的思想參照。
延安新聞傳統
中國特色新聞學自延安開始,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因為它與革命黨的使命、執政黨的命運休戚與共。本書描述了延安新聞傳統的來龍去脈,打開了諸多討論的空間。作者把起點放在延安整風和政黨政治革新的敘述框架下,也即「革命史範式」中。雖然「革命史範式」在當下受到諸多質疑和挑戰,但這並不是因為「革命史範式」已經失效,毋寧是對這一範式的把握並沒有真正做到「內在視野」的貫通,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理解沒有、也不可能真正打開「革命史範式」的活力,這也是本書試圖展開的工作。――呂新雨 延安新聞傳統,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現代新聞規範。如果與當代新聞專業主義進行比較分析,可以發現無論在形而上的價值訴求,還是在形而下的操作準則方面,都形成鮮明差異,我概括為「業餘路線」。這裡的「業餘」,並不意味著技術水準的低劣,而是強調一種打破專業化社會分工及其局限的自覺狀態,一方面新聞知識分子與社會民眾、進步政治建立有機聯繫,一方面人民群眾投身新聞傳播事業之中,使之真正成為共有、開放的公共領域。用汪暉的話說,「業餘」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一種倫理性的政治」。對於當代的新聞狀況,這無疑提供了一種批判性的思想資源。――李海波
重返開端:新時期文學的「群眾性」(1977-1984)
如今,改革中國已處在歷史的又一個轉折路口。此時,重新理解我們今天的歷史處境的必要方式之一,或許就是重返改革的開端之處。1980年代就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開端。然而,1980年代同時也是終結。從整體上來說,它是被稱為「革命世紀」的「短20世紀」之尾聲,其次,它也是毛澤東時代的終結。――然而,1980年代又終究是改革的開端,它開啟了中國社會主義新的探索,沒有這一新的探索,就不可能成就今天的「中國道路」。這就是1980年代的複雜性。它是終結,也是開端,暮氣沉沉而又朝氣蓬勃。就此而言,重返1980年代,既是重返終結,也是重返開端。但更是重返開端。從19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入手,或許是理解這一開端的恰切的方式。不僅因為中國現代文學自五四以來就是「感時憂國」的,也不僅由於從左翼文學到社會主義文藝,從來都是「時代的風雨表」,從來都是「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原因更在於,「新時期文學」本身就是1980年代創造開端的基本方式。
葉榮鐘選集.晚年書信卷
葉榮鐘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六持續不斷的寫作,除了為日據時代和光復初期的台灣留下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回憶和記錄,其晚年書信也非常有價值。這些書信對於民族、國家的未來與人類道德遠景的承擔,顯示其所思考的並不僅僅是台灣的出路問題,也是崛起後的中國如何維護世界和平,關乎人類命運的倫理問題。這是終生致力於反殖民、反壓迫志業的葉榮鐘先生其人其文,以一個殖民地台灣的抗日文人,留給兩岸中國人珍貴的思想遺產。
三○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詩人
在我心目中,二十世紀三○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為代表的「現代派」詩人群在中國現代詩歌史是具有相對成熟的詩藝追求的派別,成熟的原因之一體現在詩歌意象世界與作家心理內容的高度吻合,以及幻想性的藝術形式與渴望烏托邦樂園的普遍觀念之間的深切契合,最終生成為一些具有原型意味的藝術模式和藝術母題。 這也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視角,可以通過藝術母題的方式考察一個派別或者群體的共同體特徵,考察他們之間具有共通性的藝術形態、文學思維乃至價值體系。――吳曉東
倒退著走進未來:文化研究五年集
這些體式雜亂的文字之所以能放在一起,完全是因「文化研究」之名。它是個嘗試,嘗試著跨出文學領域,看看更大的世界;嘗試著用一套還並不很熟悉的知識和理論重新結構對世界的認識;嘗試著走出書齋和學校,走進更大的人群,了解他們,理解他們;嘗試著轉換一下身分,重新體會向實踐者學習的狀態;嘗試著更直接地面對現實和社會問題;嘗試著重新思考知識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集子中相當一部分文字與新工人這一當代世界最龐大的群體有關,即使涉及歷史和現實中其他議題,也多少與他們相關。我固執地以為他們關乎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郭春林
從煤礦工人到大學教授:我的回憶
盛江除了和同世代的知青一樣上山下鄉務農之外,他還當過礦工,下過礦坑,盡心盡力的當了好幾年的煤礦工人,因此被選為工農兵學員,推薦到江西師範學院讀書。這樣,他才有機會讀上來,最後成為著名的學者。 中國人具有極佳的“品格”,在困難的時候非常能夠吃苦,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只要客觀條件有了改變,他們就能夠把握時機,迅速往前發展。盛江生長於貧困的農家,又經過十年文革的波折,最後成為全國知名的教授,寫出兩本引人矚目的學術大作,所憑藉的就是這種中國人所具有的優秀的品格。
毒蘋果札記2
“詩人在日常生活的消費中,儘可能通過自主勞動減少對商品世界的依賴,其實就是對勞動異化的批判與反抗。雖然這樣的反抗註定是要失敗,但卻保持著一個戰鬥者不合時宜的、但卻優雅的姿態。” “因此,表現在《毒蘋果札記》中詩人對現實生活的扞格不入,對現行體制的喋喋不休,實際上是詩人對改造現實、改造社會、改造自身存在狀態的急切要求。”- 陳福裕 “愛中國與愛台灣矛盾嗎?一點兒也不!作為一個「正港」的鹿港人,詩人敏銳的觸鬚更本然地攀緣延伸在無盡的台灣時空中。在人與物的豐富中,寄寓著他豐富的興發懷思。” “因此,異議份子與中國忠僕之外,詩人還是一個平凡公民(或市民)。我認為這其實更是毒蘋果之所以為毒的一個重要源頭,而且是一極重要但又常被忽略的鬥爭場域。《毒蘋果札記》是一本抵抗布爾喬亞的生活之書、品味之書。”- 趙剛 “善繼就是有善,善繼如果變,本就是「善變」,沒什麼問題的吧?相比時代與時代中人心詭辯╱變,其實不曾變的該是詩人,他的真摯、誠懇、直白與敘敘叨叨。我們必須體認,詩人施善繼,他的創作,連同他寫作的內容與形式轉化,就是世界範圍的中國史的台灣的產物,就是我們的。因故任何時候,如果詩人顯現強烈個人特徵,那也是因為太過關心台灣、兩岸、世界,關心我們。台灣、兩岸、世界、你、我,不是我們都該關心的?那就試試來讀《毒蘋果》。況2019年的此際,世局好了嗎?太平洋那頭的狂人還在全球封鎖與挑釁,台灣海峽那頭也在變與穩的辯證中,無不牽動島內心情,我們該慶幸還有一個人如此寫著、寫著。”- 張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