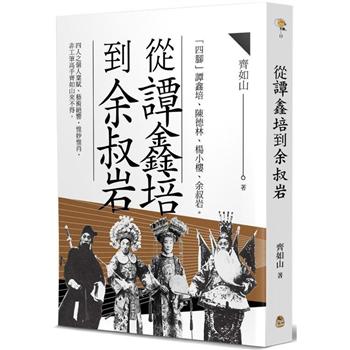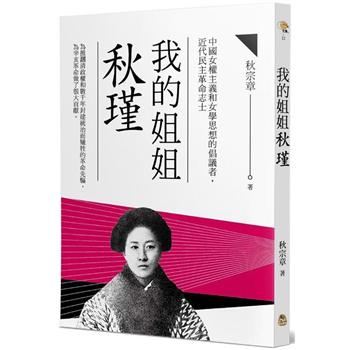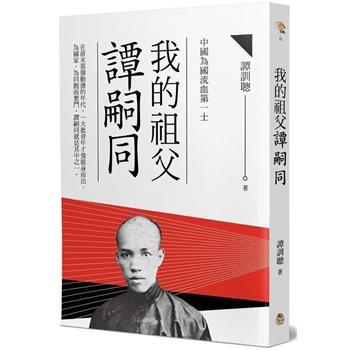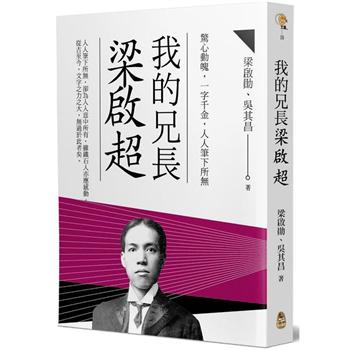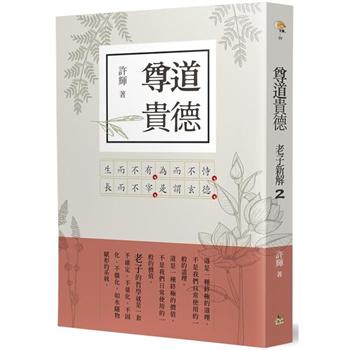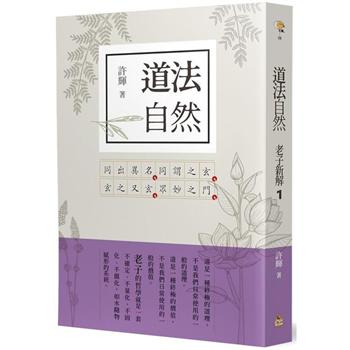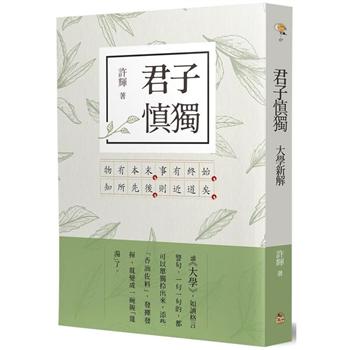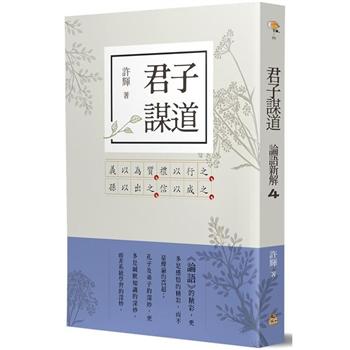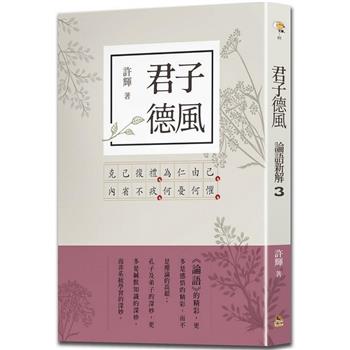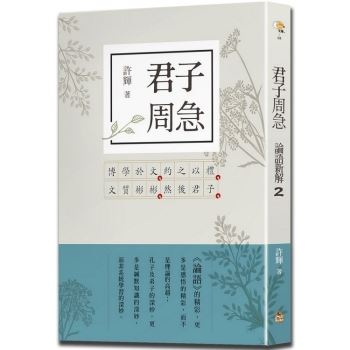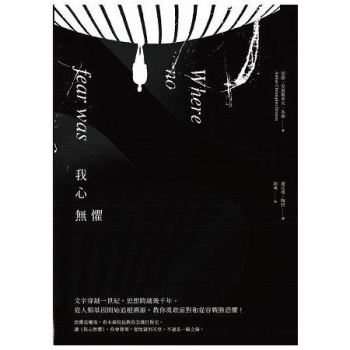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從譚鑫培到余叔岩
「四腳」譚鑫培、陳德林、楊小樓、余叔岩。四人之個人稟賦、藝術絕響,惟妙惟肖,非工筆高手齊如山來不得。梁啟超親筆為譚鑫培題詩:四海一人譚鑫培,聲震廿紀轟如雷。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劇學月刊》中寫道:「三十三天天上天,玉皇頭戴平天冠。平天冠上豎桅杆,鑫培站在桅杆巔。」陳德林是清代光緒以來青衣演員的代表人物,其主要特色在於繼承老派青衣演唱的傳統,偏於陽剛一路,而在唱法上較前人略有變化,是近代青衣重要流派,世稱「陳派」。楊小樓,楊月樓之子,在當時和梅蘭芳、余叔岩並稱為「三賢」,成為京劇界的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師」的盛譽。余叔岩在全面繼承譚(鑫培)派藝術的基礎上,以豐富的演唱技巧,對譚(鑫培)派藝術進行了較大的發展與創造,成為「新譚派」的代表人物,世稱「余派」。本書為齊如山回憶譚鑫培、陳德林、楊小樓、余叔岩等四大京劇名家的文集,所記事情均為親身經歷,可以從中得見京劇名角一生行事。
【電子書】從譚鑫培到余叔岩
「四腳」譚鑫培、陳德林、楊小樓、余叔岩。四人之個人稟賦、藝術絕響,惟妙惟肖,非工筆高手齊如山來不得。梁啟超親筆為譚鑫培題詩:四海一人譚鑫培,聲震廿紀轟如雷。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劇學月刊》中寫道:「三十三天天上天,玉皇頭戴平天冠。平天冠上豎桅杆,鑫培站在桅杆巔。」陳德林是清代光緒以來青衣演員的代表人物,其主要特色在於繼承老派青衣演唱的傳統,偏於陽剛一路,而在唱法上較前人略有變化,是近代青衣重要流派,世稱「陳派」。楊小樓,楊月樓之子,在當時和梅蘭芳、余叔岩並稱為「三賢」,成為京劇界的代表人物,享有「武生宗師」的盛譽。余叔岩在全面繼承譚(鑫培)派藝術的基礎上,以豐富的演唱技巧,對譚(鑫培)派藝術進行了較大的發展與創造,成為「新譚派」的代表人物,世稱「余派」。本書為齊如山回憶譚鑫培、陳德林、楊小樓、余叔岩等四大京劇名家的文集,所記事情均為親身經歷,可以從中得見京劇名角一生行事。
我的姐姐秋瑾
她是中國女權主義者,她是女學思想的倡議者,她更是民主革命志士! 秋瑾,字璿卿,別號競雄,又稱鑑湖女俠,浙江會稽人,隸籍山陰。幼隨其父宦於閩,旋復隨父入湘;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鈞。廷鈞入資為部郎,需次京師,瑾與之俱,生有子女。旋與廷鈞定約,分家產,瑾得萬金,即以之經商,所託非人,盡耗其資。又與廷鈞不睦,同鄉戚屬陶大均(會稽人)、陳靜齋(山陰人)等為之和解,不得,乃盡以其所有首飾,託大均妾荻意為變賣,集資東渡日本留學;值寧河王照以戊戌案自首,繫刑部獄,瑾聞之,出所集得留學費送入獄,以濟其急,並囑使者勿以其名告之,逮照出獄,始悉其事。瑾之天性義俠常如此。 秋瑾是中國女權主義和女學思想的倡議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為推翻清政權和數千年封建統治而犧牲的革命先驅,為辛亥革命做了很大貢獻,該書全面詳細的介紹了秋瑾,且配有珍貴圖片,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圖書輯錄了秋瑾弟弟秋宗章回憶秋瑾的文字,對作為姐姐、女兒、革命戰士的秋瑾作了詳盡而全面的介紹,字裏行間可見作者對秋瑾英勇就義的哀痛,和對姐姐的敬仰、愛戴和懷念。
【電子書】我的姐姐秋瑾
她是中國女權主義者,她是女學思想的倡議者,她更是民主革命志士! 秋瑾,字璿卿,別號競雄,又稱鑑湖女俠,浙江會稽人,隸籍山陰。幼隨其父宦於閩,旋復隨父入湘;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鈞。廷鈞入資為部郎,需次京師,瑾與之俱,生有子女。旋與廷鈞定約,分家產,瑾得萬金,即以之經商,所託非人,盡耗其資。又與廷鈞不睦,同鄉戚屬陶大均(會稽人)、陳靜齋(山陰人)等為之和解,不得,乃盡以其所有首飾,託大均妾荻意為變賣,集資東渡日本留學;值寧河王照以戊戌案自首,繫刑部獄,瑾聞之,出所集得留學費送入獄,以濟其急,並囑使者勿以其名告之,逮照出獄,始悉其事。瑾之天性義俠常如此。 秋瑾是中國女權主義和女學思想的倡議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為推翻清政權和數千年封建統治而犧牲的革命先驅,為辛亥革命做了很大貢獻,該書全面詳細的介紹了秋瑾,且配有珍貴圖片,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圖書輯錄了秋瑾弟弟秋宗章回憶秋瑾的文字,對作為姐姐、女兒、革命戰士的秋瑾作了詳盡而全面的介紹,字裏行間可見作者對秋瑾英勇就義的哀痛,和對姐姐的敬仰、愛戴和懷念。
【電子書】我的祖父譚嗣同
中國為國流血第一士!在清末那個動盪的年代,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而出,為國家、為同胞而奮鬥,譚嗣同就是其中之一。康有為稱譚嗣同是「挾高士之才,負萬夫之勇,學奧博而文雄奇,思深遠而仁質厚,以天下為己任,以救中國為事,氣猛志銳。」《我的祖父譚嗣同》是作者譚訓聰追憶其祖父──清末維新鬥士譚嗣同的文集,既有他人寫譚嗣同的記傳,又有譚嗣同生平撰寫的文章、與親朋至交的書信。按照時間的順序,寫清了譚嗣同思想的變化以及生平經歷。本書帶您回到清末那個動盪的年代,讓您回望那個年代不斷奮鬥的人們,感受譚嗣同的人物風貌。
【電子書】我的兄長梁啟超
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本書收錄了梁啟超的弟弟梁啟勛和學生吳其昌,對於梁啟超的回憶性文字,並收錄了梁啟超與梁啟勛的來往信件,從中可以窺見梁啟超的治學、治家之路,可以直觀感受到梁啟超身為家庭「主心骨」的擔當,以及他在社會上的交遊之道。
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電子書】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尊道貴德:老子新解(2)》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
同出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電子書】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
同出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是一種終極的道理,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道理。道是一種終極的價值,不是我們日常使用的一般的價值。老子的哲學就是一套不確定、不量化、不固化、不僵化,如水隨物賦形的系統。作者以品讀《老子》的感受開篇,以凝練、幽默的文字表達品讀《老子》的心得,繼而從對《老子》進行逐條解讀,《道法自然:老子新解(1)》是許輝先生以個人化視角感悟《老子》、十年磨一書的嘔心之作,是對《老子》別具一格的傾情悟讀,展現了作者深邃的眼光、厚重的思考、廣闊的視野、精妙的文筆和寬博的知識。
君子慎獨:大學新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讀《大學》,如讀格言警句,一句一句的,都可以單獨拎出來,添些「香油佐料」,發揮發揮,就變成一碗碗「雞湯」了。《君子慎獨》是著名作家許輝對儒家經典《大學》的解讀。許輝將《大學》置於厚重的淮河文化背景下,本書既有對《大學》彰顯光明的主題的精彩闡釋,也有對這一主題進行的詳細品讀。著名作家許輝的《君子慎獨》,是以淮河文化解讀儒家經典《大學》的著作,透通過對《大學》的個性化闡釋和具有地域色彩的解讀,反應了許輝多年來對淮河文化進行的文化思考。本書在對《大學》十一章內容進行逐條解讀的基礎上,精彩地闡釋了《大學》的主題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電子書】君子慎獨:大學新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讀《大學》,如讀格言警句,一句一句的,都可以單獨拎出來,添些「香油佐料」,發揮發揮,就變成一碗碗「雞湯」了。《君子慎獨》是著名作家許輝對儒家經典《大學》的解讀。許輝將《大學》置於厚重的淮河文化背景下,本書既有對《大學》彰顯光明的主題的精彩闡釋,也有對這一主題進行的詳細品讀。著名作家許輝的《君子慎獨》,是以淮河文化解讀儒家經典《大學》的著作,透通過對《大學》的個性化闡釋和具有地域色彩的解讀,反應了許輝多年來對淮河文化進行的文化思考。本書在對《大學》十一章內容進行逐條解讀的基礎上,精彩地闡釋了《大學》的主題及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
君子謀道:論語新解(4)
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說:「君子為道義用心而不為衣食盡力。種地的人有時還會挨餓,學習能夠得到俸祿。君子擔心的是不得道,而不擔心窮困。」人們總是習慣於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更高的標準,說出更多的理由,開出更高的價碼,以使自己的生活變的更美好、環境變的更悅目、物質變的更豐裕、精神變的更充實、規則變的更利己。社會體制和道德體制不得不無止境地,順應人們這種不斷提升的高標準和嚴格要求,這正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特點。
【電子書】君子謀道:論語新解4
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 信以成之《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說:「君子為道義用心而不為衣食盡力。種地的人有時還會挨餓,學習能夠得到俸祿。君子擔心的是不得道,而不擔心窮困。」人們總是習慣於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更高的標準,說出更多的理由,開出更高的價碼,以使自己的生活變的更美好、環境變的更悅目、物質變的更豐裕、精神變的更充實、規則變的更利己。社會體制和道德體制不得不無止境地,順應人們這種不斷提升的高標準和嚴格要求,這正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特點。
君子德風:論語新解(3)
克己復禮 為仁由己 內省不疚 何憂何懼《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季康子向孔子問政事:「假如殺掉壞人來成就好人,怎麼樣?」孔子回答道:「您治理社會,還用的著殺?您政風清明,社會風氣就清明。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季康子真是粗陋不堪的,說起話來毫無遮掩。他只知用武,不知有文;只想得到殺人,想不到教化。孔子卻也多見不怪,穩的住,和他談榜樣的力量、德行的風尚。有耐心,有比喻,有文采。
【電子書】君子德風:論語新解3
克己復禮 為仁由己 內省不疚 何憂何懼《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季康子向孔子問政事:「假如殺掉壞人來成就好人,怎麼樣?」孔子回答道:「您治理社會,還用的著殺?您政風清明,社會風氣就清明。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季康子真是粗陋不堪的,說起話來毫無遮掩。他只知用武,不知有文;只想得到殺人,想不到教化。孔子卻也多見不怪,穩的住,和他談榜樣的力量、德行的風尚。有耐心,有比喻,有文采。
君子周急:論語新解(2)
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是外向型人才,而不是內向型人才。以前印象裡他是內向型人才,保守而老態,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或者說,孔子是中庸式人才,他既外向,又內向;需要外向時外向,需要內向時內向。需要唱歌時,他跟人哼唱;需要思考時,他足不出戶;需要輕鬆時,他燕居;需要傳道時,他遊學;需要回絕時,他不賣馬車;需要誨人時,束脩薄禮即可。他既看好顏回的窮困好學,也看好子貢的富足有為;既看好閔子騫的孝順,也看好祝的口才。孔子機靈著呢!
【電子書】君子周急
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 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論語》的精彩,更多是感悟的精彩,而不是理論的高超;孔子及弟子的深妙,更多是緘默知識的深妙,而非系統學習的深妙。孔子是外向型人才,而不是內向型人才。以前印象裡他是內向型人才,保守而老態,其實完全不是這樣。或者說,孔子是中庸式人才,他既外向,又內向;需要外向時外向,需要內向時內向。需要唱歌時,他跟人哼唱;需要思考時,他足不出戶;需要輕鬆時,他燕居;需要傳道時,他遊學;需要回絕時,他不賣馬車;需要誨人時,束脩薄禮即可。他既看好顏回的窮困好學,也看好子貢的富足有為;既看好閔子騫的孝順,也看好祝的口才。孔子機靈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