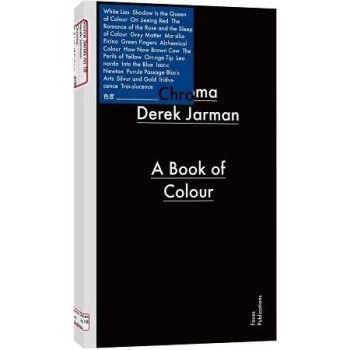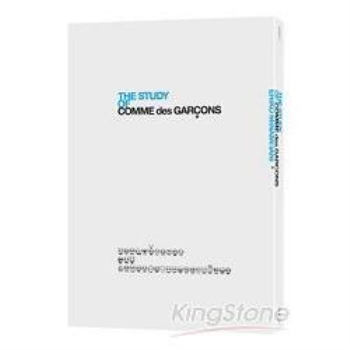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色度
英國前衛藝術家、電影導演的色彩論 ,唯一繁體中文版著作 一個失明者離世前以詩一般的語言,訴說對藝術的熱愛與生命的回憶 轟動世界的電影《藍》,即出自本書第13章〈進入藍色Into the Blue〉 本書由一篇引言與十九篇小品文所構成,作者談論繪畫、電影、人物,以及個人對於色彩的種種思考與回憶。作者旁徵博引,援引哲學家語錄、詩作、神話故事,並論及歷史、社會文化現象,說明各種顏色的意涵。此外,也提及從童年回憶到晚年罹病等種種個人經歷。 就文體而言,本書是以散文寫作,然而文中有詩,而整體的用字與意境頗具詩意與想像力,令人讚嘆,像一道單色光芒通過稜鏡之後,散發出繽紛色彩。本書寫作方式並非闡明一項論點,而是將和每種顏色的相關知識與回憶,累積成一個篇章: 白色謊言White Lies 白色似乎是單純、缺乏色彩,然而果真如此?本篇談到白色被視為是缺乏色彩,直到牛頓發現白色包含多種顏色(光的白色其實是由三原色以不同比例構成。)而在文化上,白色也有多種意義:例如純真、貞潔,但白色也有強大的掩飾能力,例如新娘白色婚紗底下其實有蠢蠢欲動的慾望。 白色也不是一種絕對的顏色,例如花朵的白帶點黃,雪的白則帶點藍。文章後半部提起作者在成長過程中,白色所代表的意義,例如住在「白人」社區。綜言之,白色並非如表面般那麼單純,其意涵無法一言以蔽之。 陰影是色彩之后Shadow Is the Queen of Colour 本篇論及亞里斯多德的《論色彩》,與畫家小普林尼(Pliny)的美學觀。亞里斯多德認為一切顏色皆源自於風火水土四元素,其與黑色及光線混和之後,就是我們眼睛所看見的色彩。普林尼則認為,繪畫越是擬真、越和大自然的物體相同,則越是佳作。無論是亞里斯多德或普利尼,都重視大自然本真的顏色,然而眾人卻漸漸偏好用從大自然掠奪的昂貴礦物,來創作藝術品與調配精美的顏料。 作者筆鋒一轉,表示當前的繪畫並非重視畫家的才能,而是重視材料探索。然而無論是以何種素材作畫,最好的作品往往是過往輝煌時代的影子。色彩,終究會在歷史的薄暮中逐漸褪去。 看見紅色On Seeing Red 紅色是一種特殊的顏色,和黑或白都不同,因為提到紅色時,每個人心中的紅色一定都不同。本篇先談到作者在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紅色,例如檢查視力使用的器材、童年記憶中蔓延無際的紅色花海,接著談起紅色的文化意義(例如愛、戰爭),以及歷史上紅色出現的知名場景(如十字軍東征)。此外,作者也提到鎘紅、威尼斯紅、茜草深紅等各種紅色的製作知識。作者在文末指出,這篇文章是給讀者的信,他把這信裝在紅信封裡,代表「急件」,接著放在紅色的信箱裡,下午四點,郵差會開紅色的車來收信。 玫瑰的傳奇與沉睡的色彩The Romance of the Rose and the Sleep of Colour 提到中世紀,多數人會想到為數眾多的農奴,腦海浮現的也是單調的褐色。然而賈曼指出,其實這時期的宗教建築與書籍上,會運用如寶石般繽紛亮眼的色彩,不僅顏色鮮艷,顏料也很貴重。今天雖然顏料取得容易,然而現在採用標準化的「色表」與略帶有石灰色彩的塗料限制之下,恐怕很難會再出現如中世紀那樣光彩奪目的建築與藝術。 馬西里歐.費奇諾Marsilio Ficino 李奧納多Leonardo 牛頓Isaac Newton 這三篇是以人物為主題的小品文。費奇諾將柏拉圖的論述譯成拉丁文,對文藝復興影響甚大。他是提出「柏拉圖式愛情」的人,讚美同性之愛。他的思想(例如對顏色的看法)不受基督教認可,著作也被打入冷宮,但仍影響深遠。 李奧納多是指達文西。賈曼在文中表示,他並不熱中達文西的畫作,反倒喜歡達文西的筆記,因為達文西觀察入微,對於光影的觀察有獨到之處,而從筆記中更能看出他的天才。然而,賈曼在讚賞達文西之際,還寫了一段軼聞:蒙娜麗莎的微笑原本要畫翡冷翠的銀行家之妻,但是要幫肖像畫上臉龐的那天,她罹患重感冒,於是派了俊美年輕的男孩告知達文西。達文西乾脆在肖像上畫男孩的臉,之後還給他一個吻。 牛頓這一篇非常短,文中提到他發現白色的光,其實是由各種顏色所組成。這一篇雖然沒有提到太多牛頓的軼事,但他曾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牛頓是「很知名的單身漢」,似乎暗指這名天才也是同性戀。 本書中只有這三篇是以人物為主題,作者在說明這些人的天分之餘,不忘指出他們同性戀的身分,由此觀之,這幾篇其實涉及同性戀的身份認同。 進入藍色Into the Blue 本書的多數文章是以一種顏色為主題,以許多觀點來看這種顏色的意涵,並抒發自己的美學觀或情感。和其他章節不同的是,這篇除了談論藍色的意涵之外,還有一大段是賈曼電影《藍》的腳本。這部電影的手法特殊,畫面只有一整片藍,並配上旁白與音效,以模擬賈曼因愛滋病失明,什麼都看不見,而旁白就是在訴說他的境遇。文中提及他失明、接受治療的狀況,還提到他許多朋友已死於愛滋,字裡行間透露出無盡的憂傷,是全書中最悲傷的一篇。 賈曼在寫本書時已病重,然而我們看不到怨天尤人或激進憤怒的言語,只有一個在步入人生最後階段的失明者,以詩一般的語言,訴說對藝術的熱愛與生命的回憶。
COMME des GARCONS研究
川久保玲為何如此令人動容?首本剖析COMME des GARÇONS祕密的教科書從未知的形狀、不對稱結構的衣版,探索她前衛的創造原點——「不明的根源」川久保玲親自審閱、井上嗣也裝幀設計、官方認可決定本!「我喜歡惡搞布料。」「我想要設計前所未有的衣服。」「我不是進行破壞,只是附加嶄新解釋或可能性而已」「與其遭到漠視,不如遭到貶斥。」——川久保玲羅蘭巴特在《流行體系》一書中指出:「能夠閳述樣式的字彙只有兩個:一是『流行』,一是『過時』。」承認西方時尚中不存在的事物是流行,等於承認自己以往架構而成的事物是「曾經的流行」,也就是過時,意味將自己的時尚逼上死路。從1982年至今,COMME des GARÇONS飽受褒貶兩極的評價,既有熱烈的支持,認為「時尚界唯有川久保玲是萬丈光芒的」,也有嘲諷訕笑,認為她「沒有見過世面」。這類極端的評價,或許是前衛的宿命。川久保玲(Rei Kawakubo),1942年出生於東京,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是受嬉皮文化洗禮的世代。遊走在時尚和藝術邊界的川久保玲,自小未曾碰觸也從沒受過正式的服裝設計訓練。1969年,在原宿公寓的一室中,她和兩位工作者開始公寓品牌「COMME des GARÇONS」,1973年成立公司,至今除擔任主要設計師之外,同時兼任總經理,以企業家之姿面對品牌經營。她的店面沒有櫥窗,也沒有窗戶,對不認識COMME des GARÇONS的人而言,完全無法預測店內擺放哪些商品,這是前所未見的商業模式。通常應該開放給大眾的時尚系列作品發表會,她也將出席貴賓嚴選到只剩五分之一,可以看出她刻意回歸封閉空間的決心。不曾為了擴大企業規模而增開店面,也不利用知名度、多元化,開發一般消費者容易接受的商品,更不進行多品項的授權事業,她的經營方針在於防止形象的無限擴散。1981年COMME des GARÇONS進軍巴黎,82年的時裝週是她在國際舞台綻放光芒的起點,《紐約時報》以「日本襲來的新浪潮」讚譽她和同期展出的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黑色」、「破壞」、「不對稱」是COMME des GARÇONS的特有風格,COMME des GARÇONS是西方服飾體系與日本文化的混血產品,在外形上強調平面及空間構成,在結構中融入現代的建築美學概念,纏繞人體的多層次結構,以及抽象的平面圖案設計。她的構思源頭不是來自於穿著衣服或是裝飾著衣服的身體,而是設計衣服本身。穿上衣服後看起來知性或是性感她也從不在意,重要的是穿著COMME des GARÇONS所呈現出的「接受嶄新事物」、「具有自由價值觀」的獨立精神。在創造的現場,她始終保持著身體的零度,穿著主體不存在的冷酷觀點,彷彿規範穿著者,同時亦為遏止設計的僭越。這可說是川久保玲的美學,也讓她成為全球服裝設計師中最前衛的女性。1983年川久保玲獲得每日新聞時尚設計獎(Mainichi Fashion Award ),1987年獲得美國時尚技術學院(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榮譽學位。被稱為「破壞主義者」的川久保玲,是針對西方時尚第一線根深柢固的製作偏見,拋出最激烈質疑的設計師。可是她究竟破壞了什麼呢?是樣式體系、時尚的美學規範,還是女性性的神話呢?本書並非探討川久保玲究竟破壞了什麼,而是探討川久保玲打算創造什麼,來循序檢證COMME des GARÇONS。我們將面對的第一線現場,存在著「創造」行為和「破壞」行為,這種表裡一體的關係。在面對現場時,我們是否還能夠持續稱川久保玲為「破壞主義者」呢?……這些問題都將在書中一一解答。本書同時公開川久保玲長達22年間的創作活動實績和特徵,展開從嶄新的設計論證到身為企業家的獨特經營策略、行銷理論,是最接近川久保玲身為尖端時尚產業經營者面貌的「COMME des GARÇONS論」決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