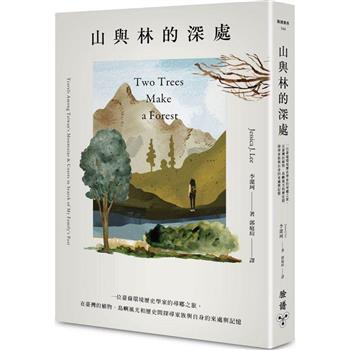國中組 ‧ 佳作
苗栗縣縣立建國國中 八年八班 詹羽芊
苗栗縣縣立建國國中 八年八班 詹羽芊
心中的花園
「台灣深深吸引我們,有時卻把我們推開,我心裡萌生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渴望,到底這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作者在過世的外公遺留下的信件中,一步一腳印的走進了那個從前只存在於想像中的台灣,發現了她未曾了解過的世界,她見證了天地的壯美和崇高,感覺自己在風景裡找到一種表達方式。
「山與林的深處」看起來像是一本豐富的地理雜誌,夾雜著台灣的發展史,但包裹在其中的是一段孤寂又迷失的家族故事。因為成長過程和語言隔閡,作者筆下的台灣帶著一種淡淡的憂愁,又彷彿像是一種薄薄的霧氣,縈繞在心中。
在描寫作者外公包水餃的那段文字中,我腦海中遠在南半球的外公身影就這樣和文字交疊在一起,他們是那樣的相似,排行老三、軍旅出身、喜歡麵食、在中年移居國外、一樣在異鄉努力生活著。我忍不住想起移居南半球的親人們,他們在紐西蘭落地生根已有超過二十年的時光。二十年啊,讓人遺忘很多曾經,久到幾乎都快忘記夏天的芒果是如此的香甜,忘記那些年九降風的呼嘯,也許也常常忘記,還有這樣的一個我在這悶濕的小島上。相處的時光太少,我和那些所謂的親人,都有著說不出的尷尬和陌生,就像隔著一層薄薄的霧,因為文字和語言的距離,我們中間隔著的不僅僅是太平洋,那是從我想你到I miss you之間的距離,要把那樣的感受化為任何一種文字描述都很困難,感覺就像個填不滿的黑洞,刻在我的血液裡。
思緒跟著回到懵懵懂懂的那一年,在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我終於踏上遠在南半球的紐西蘭。一踏進外公的家就被他豐富的花園吸引住目光,各式各樣的果樹,草地修剪的平平整整,一旁還有著各式各樣的蔬菜,看見妹妹在身旁採著她喜愛的小白花,想編織一個花環,我想起在山與林的深處一書中出現過一種叫做清飯藤的植物,如米粒般的小白花,在台灣和東南亞地區是當地的原生種,但是到了國外就被貼上,外來入侵種的標籤,這個概念轉換至人類身上時就像是移民,那是一張寫著孤獨的標籤,生來就貼在作者的身上,我突然有點理解她心中那一份無法擺脫的孤寂,身為移民第二代,一開始並不是她自己的選擇,但卻為此背負了一輩子的漂流。身為一個擁有紐西蘭護照,但卻幾乎對這片土地一無所知的我,本質上擁有相同的靈魂。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應該要英文流利、態度大方、見多識廣,其實除了比別人多看過幾次羊群,我的人生平凡無奇,甚至連一株移入植物都稱不上,頂多只能算是一顆隨風飄揚而來的蒲公英吧。
看著外公俐落的剪下一把蔥,紐西蘭人只認識洋蔥,不吃青蔥,這些都是思念家鄉的移民們,偷偷夾著藏著才能飄洋過海偷渡而來的家鄉味,我發現原來青蔥在乾燥的紐西蘭,依樣生存的挺立,就像外公一樣。他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帶領著我做蔥油餅,和麵、切蔥、?皮,外公一切都是信手捻來,抓麵粉,加水都不使用一般工具,看起來有一份自得的灑脫。當時我怎麼都無法將餅?成一個大圓,心裡一陣挫敗,外公拉開嗓門大聲笑著說:「方的又怎樣?吃下去都是一樣的,慢慢來,多練幾次。」外公握著我的手來回滾動,他手心的溫度傳遞到我的心中,我抬頭望著他,覺得自己好像離他近了一點點。看著他略帶笨拙生澀的為妹妹在樹上掛起一個鞦韆,外公就是他那個時代的典型男性,關懷不會說出口,但總是默默地注意著你所有的需求。我好像也慢慢地了解作者說過的,當自己來到某處,在某個地方曾經有過一段過往,牽絆,就此產生。
牽絆這種東西很微妙,起初只是一條細線,慢慢纏繞,讓作者和這座島產生羈絆,在遊走台灣的日子裡,她找回失去連絡的親人,發現心靈的安慰,看見了一種永恆。「有些失去,不可能濃縮成簡單的故事。」書中的這句話一直在我的心中迴盪著,聽著媽媽和阿姨像說笑般討論著過往的故事,說到激動處流下眼淚,那些失去無法再重來,也許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珍惜自己現在所擁有的,把握每一次的相聚,用盡全力去愛、去感受、去珍惜。所謂的愛,其實很簡單、很純粹、也許我們都想得太難,那些愛就包裹在這些單調的日常中,在那張鞦韆,在餐桌上的那張蔥油餅中。
不知道外公家窗前那棵大樹下的鞦韆,是否還隨風搖蕩著?我還是常常想起那紅磚搭建成的平房,想起佈置的很有台灣味道的房間,想起那一天,我這株小小的蒲公英,從外公的花園中,飄入作者心中的那片山林,在心的深處,我彷彿發現愛、找到牽絆,刻劃出想念的溫度,看見了存在的意義。
「山與林的深處」看起來像是一本豐富的地理雜誌,夾雜著台灣的發展史,但包裹在其中的是一段孤寂又迷失的家族故事。因為成長過程和語言隔閡,作者筆下的台灣帶著一種淡淡的憂愁,又彷彿像是一種薄薄的霧氣,縈繞在心中。
在描寫作者外公包水餃的那段文字中,我腦海中遠在南半球的外公身影就這樣和文字交疊在一起,他們是那樣的相似,排行老三、軍旅出身、喜歡麵食、在中年移居國外、一樣在異鄉努力生活著。我忍不住想起移居南半球的親人們,他們在紐西蘭落地生根已有超過二十年的時光。二十年啊,讓人遺忘很多曾經,久到幾乎都快忘記夏天的芒果是如此的香甜,忘記那些年九降風的呼嘯,也許也常常忘記,還有這樣的一個我在這悶濕的小島上。相處的時光太少,我和那些所謂的親人,都有著說不出的尷尬和陌生,就像隔著一層薄薄的霧,因為文字和語言的距離,我們中間隔著的不僅僅是太平洋,那是從我想你到I miss you之間的距離,要把那樣的感受化為任何一種文字描述都很困難,感覺就像個填不滿的黑洞,刻在我的血液裡。
思緒跟著回到懵懵懂懂的那一年,在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我終於踏上遠在南半球的紐西蘭。一踏進外公的家就被他豐富的花園吸引住目光,各式各樣的果樹,草地修剪的平平整整,一旁還有著各式各樣的蔬菜,看見妹妹在身旁採著她喜愛的小白花,想編織一個花環,我想起在山與林的深處一書中出現過一種叫做清飯藤的植物,如米粒般的小白花,在台灣和東南亞地區是當地的原生種,但是到了國外就被貼上,外來入侵種的標籤,這個概念轉換至人類身上時就像是移民,那是一張寫著孤獨的標籤,生來就貼在作者的身上,我突然有點理解她心中那一份無法擺脫的孤寂,身為移民第二代,一開始並不是她自己的選擇,但卻為此背負了一輩子的漂流。身為一個擁有紐西蘭護照,但卻幾乎對這片土地一無所知的我,本質上擁有相同的靈魂。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應該要英文流利、態度大方、見多識廣,其實除了比別人多看過幾次羊群,我的人生平凡無奇,甚至連一株移入植物都稱不上,頂多只能算是一顆隨風飄揚而來的蒲公英吧。
看著外公俐落的剪下一把蔥,紐西蘭人只認識洋蔥,不吃青蔥,這些都是思念家鄉的移民們,偷偷夾著藏著才能飄洋過海偷渡而來的家鄉味,我發現原來青蔥在乾燥的紐西蘭,依樣生存的挺立,就像外公一樣。他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帶領著我做蔥油餅,和麵、切蔥、?皮,外公一切都是信手捻來,抓麵粉,加水都不使用一般工具,看起來有一份自得的灑脫。當時我怎麼都無法將餅?成一個大圓,心裡一陣挫敗,外公拉開嗓門大聲笑著說:「方的又怎樣?吃下去都是一樣的,慢慢來,多練幾次。」外公握著我的手來回滾動,他手心的溫度傳遞到我的心中,我抬頭望著他,覺得自己好像離他近了一點點。看著他略帶笨拙生澀的為妹妹在樹上掛起一個鞦韆,外公就是他那個時代的典型男性,關懷不會說出口,但總是默默地注意著你所有的需求。我好像也慢慢地了解作者說過的,當自己來到某處,在某個地方曾經有過一段過往,牽絆,就此產生。
牽絆這種東西很微妙,起初只是一條細線,慢慢纏繞,讓作者和這座島產生羈絆,在遊走台灣的日子裡,她找回失去連絡的親人,發現心靈的安慰,看見了一種永恆。「有些失去,不可能濃縮成簡單的故事。」書中的這句話一直在我的心中迴盪著,聽著媽媽和阿姨像說笑般討論著過往的故事,說到激動處流下眼淚,那些失去無法再重來,也許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珍惜自己現在所擁有的,把握每一次的相聚,用盡全力去愛、去感受、去珍惜。所謂的愛,其實很簡單、很純粹、也許我們都想得太難,那些愛就包裹在這些單調的日常中,在那張鞦韆,在餐桌上的那張蔥油餅中。
不知道外公家窗前那棵大樹下的鞦韆,是否還隨風搖蕩著?我還是常常想起那紅磚搭建成的平房,想起佈置的很有台灣味道的房間,想起那一天,我這株小小的蒲公英,從外公的花園中,飄入作者心中的那片山林,在心的深處,我彷彿發現愛、找到牽絆,刻劃出想念的溫度,看見了存在的意義。





 國小組
國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