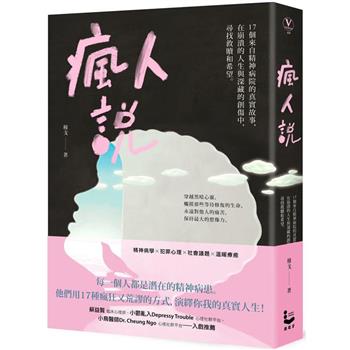
瘋人說:17個來自精神病院的真實故事,在崩潰的人生與深藏的創傷中,尋找救贖和希望
79折特價379元

高中組 ‧ 佳作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 高二誠 謝詠萱
雲林縣私立正心高中 高二誠 謝詠萱
我們與瘋子的距離
一開始吸引我閱讀這本書的,是一個有關雙重人格的故事。故事中優秀弟弟方宇奇是由成績差的主人格方宇可分裂出來,為了讓媽媽快樂的人格。但是他母親仍不滿足,她恐懼自己那個不聰明的兒子不時出現,毀滅她的幻想,因此想消滅他的存在,欺騙醫生方宇可是副人格。故事的最後,方宇可心甘情願地被消滅了。
當一個孩子出生時,他不一定是母親的一切,可母親卻是他的全部。他沒有辦法讓母親開心,讓母親認可,那他就沒有存在的價值……那些熱烈地隨著心臟跳動的愛,深沉得無法言說的愛,最終都隨著一次治療消亡。
方宇可只在乎母親,所以逼弟弟學習,但卻沒人在乎弟弟的感受。他被迫代替哥哥成為那個學習機器,被迫代替他活下去承受苦難。媽媽最在乎的考試被奉為至上,甚至比自己的存在還重要。為了一份好的成績,他可以消失。也許他早就死了心,母親每一次對弟弟的笑,都是剜他心口的刀。於是他沉默地承受被切片的心臟,他心尖滴落的血液滋養弟弟,種果得果。
沒關係,他本就是為母親而生,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為母親而死。一個陰沉、自閉、孤獨、本就不被關注的生命,他最終能回饋外界期待的,能對外界產生價值的事情,竟然是他的消亡。
方宇可說:「你要代替我給媽媽幸福。」
他母親說:「請你放過我兒子。」他最親愛、最想給予幸福的母親,求他放過她「聰明的兒子」。
我感受到一陣悲哀,卻無從向故事中的哪個人控訴,只因我感覺這個故事實在是千千萬萬個學生的寫照。方宇可曾說:「你永遠不會知道我為你放棄了什麼。」這句話,何嘗不是我最想對我的成績傾訴的呢?我總覺得,如今的我與方宇可之間,已無甚差別。我曾彈得一手好琴,用音符共鳴情感與靈魂;我曾經開朗愛笑,熱衷與朋友分享生活的喜怒哀樂。
可後來,一切都變了。那個名為「方宇奇」的我,在某個不知名的時刻悄然浮現,並逐漸掌控了我的人生。我停下了練琴的雙手,握起筆桿,放下了與親友歡笑的時光,壓抑了所有的熱情與喜好——只為了更高的成績。成績,成了唯一的目標,唯一的答案,唯一的我。
當興趣與夢想被壓進厚重的書本裡,當我逐漸麻木於站在高峰的淒涼,當那些曾讓我熠熠生輝的事物一一退場,忒修斯之船的悖論此時竟是那麼有意義。當我的零件全被換成了「讀書」,我還是原本的那個我嗎?若有一天,成績終於如我所願,那曾為它放棄的一切,又是否能被換回?
書中的另一個故事,是有關一個一直在「找褲子」的患者。裘非在國中時經歷霸凌,在廁所被脫下褲子,一直躲到隔天才敢走出廁所,這個經歷從此對他造成了創傷。
可惜,他的一輩子,只會是他們眼中的一粒沙。多年以後,裘非成為了精神病患者,而當年的施暴者,不但沒有遭到報應,還成為了富有的企業家。當裘非那樣卑微地站在他面前,他卻說:「誰還沒有年少不懂事的時候。」他們作惡,然後忘記;忘掉施惡,稱作成熟。
當我因你的一時興起,撕裂出了永久的疤,你卻輕易地忘記。我只不過是你人生中的小沙粒,任你踢擺。十幾年過去,你笑著問我:「你怎麼變成精神病患者了?」那樣的輕狂,原來只有我仍陷在過去的泥濘中,只有你繼續享受光明璀璨的未來。報應真的會到來嗎?暴力只是一瞬間的事,承受暴力卻是漫長而無盡的煎熬。裘非不斷地問:「我的褲子在哪裡?」看似是在尋找一件衣物,實則是在尋找那早已被踐踏殆盡的尊嚴與勇氣。
我始終認為生活太安逸的人,往往寫不出真正動人的文章。裘非身處黑暗之中,但他的痛苦成就了寫作的敏感和靈氣。裘非說:「我寧願我自己是個愚蠢又快樂的商人。」這句話令我印象深刻。常有人說我的文章負面、悲慘,殊不知這些都是用現實中點滴血淚換取的。我何嘗不渴望我沒經歷過那些苦痛呢?我寧願我活得天真爛漫,對著悽慘的作文題目,卻發現自己不曾有過挫折。歲月不可回首,人生中的每一步都是單行道,於是我記住了書中的那句話——「請別忘了在泥裡的時刻,而僅作為一支花活著。」
書的最後,作者以小說式的筆法向讀者描述常人對精神患者的偏見。不論再怎麼努力治療患者,只要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迎接他們的依然是異樣的眼光與冷漠的歧視,使他們在好轉之後,又重新墜入黑暗。那些生活中常聽見的話:「精神病患者就該好好關起來,不准他們出來。」、「他爸爸是精神病,他一定也是。」人們未能參與他的悲慘過去,卻能輕易決斷他的現在與未來,人生有比這更荒謬嗎?
書中十七個亦真亦假的故事,向我們訴說著,他們既是精神病患,也是正常人。故事中他們經歷的——家暴、拋棄老人、猥褻、必須強顏歡笑的「微笑抑鬱症」……竟是那麼的稀鬆平常。不論是其中的患者或是周邊的人物,都讓讀者更容易看清書腰所說的那句:「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精神病患」。
《瘋人說》讓我明白,那些被標籤為「瘋子」的人,其實只是更早承受了這個世界的重量。他們並不遙遠,他們可能就在我們之中。隔絕、評斷,傷己又傷人,我們該學會理解與陪伴。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看見——那不只是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我們自己的倒影。
當一個孩子出生時,他不一定是母親的一切,可母親卻是他的全部。他沒有辦法讓母親開心,讓母親認可,那他就沒有存在的價值……那些熱烈地隨著心臟跳動的愛,深沉得無法言說的愛,最終都隨著一次治療消亡。
方宇可只在乎母親,所以逼弟弟學習,但卻沒人在乎弟弟的感受。他被迫代替哥哥成為那個學習機器,被迫代替他活下去承受苦難。媽媽最在乎的考試被奉為至上,甚至比自己的存在還重要。為了一份好的成績,他可以消失。也許他早就死了心,母親每一次對弟弟的笑,都是剜他心口的刀。於是他沉默地承受被切片的心臟,他心尖滴落的血液滋養弟弟,種果得果。
沒關係,他本就是為母親而生,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為母親而死。一個陰沉、自閉、孤獨、本就不被關注的生命,他最終能回饋外界期待的,能對外界產生價值的事情,竟然是他的消亡。
方宇可說:「你要代替我給媽媽幸福。」
他母親說:「請你放過我兒子。」他最親愛、最想給予幸福的母親,求他放過她「聰明的兒子」。
我感受到一陣悲哀,卻無從向故事中的哪個人控訴,只因我感覺這個故事實在是千千萬萬個學生的寫照。方宇可曾說:「你永遠不會知道我為你放棄了什麼。」這句話,何嘗不是我最想對我的成績傾訴的呢?我總覺得,如今的我與方宇可之間,已無甚差別。我曾彈得一手好琴,用音符共鳴情感與靈魂;我曾經開朗愛笑,熱衷與朋友分享生活的喜怒哀樂。
可後來,一切都變了。那個名為「方宇奇」的我,在某個不知名的時刻悄然浮現,並逐漸掌控了我的人生。我停下了練琴的雙手,握起筆桿,放下了與親友歡笑的時光,壓抑了所有的熱情與喜好——只為了更高的成績。成績,成了唯一的目標,唯一的答案,唯一的我。
當興趣與夢想被壓進厚重的書本裡,當我逐漸麻木於站在高峰的淒涼,當那些曾讓我熠熠生輝的事物一一退場,忒修斯之船的悖論此時竟是那麼有意義。當我的零件全被換成了「讀書」,我還是原本的那個我嗎?若有一天,成績終於如我所願,那曾為它放棄的一切,又是否能被換回?
書中的另一個故事,是有關一個一直在「找褲子」的患者。裘非在國中時經歷霸凌,在廁所被脫下褲子,一直躲到隔天才敢走出廁所,這個經歷從此對他造成了創傷。
可惜,他的一輩子,只會是他們眼中的一粒沙。多年以後,裘非成為了精神病患者,而當年的施暴者,不但沒有遭到報應,還成為了富有的企業家。當裘非那樣卑微地站在他面前,他卻說:「誰還沒有年少不懂事的時候。」他們作惡,然後忘記;忘掉施惡,稱作成熟。
當我因你的一時興起,撕裂出了永久的疤,你卻輕易地忘記。我只不過是你人生中的小沙粒,任你踢擺。十幾年過去,你笑著問我:「你怎麼變成精神病患者了?」那樣的輕狂,原來只有我仍陷在過去的泥濘中,只有你繼續享受光明璀璨的未來。報應真的會到來嗎?暴力只是一瞬間的事,承受暴力卻是漫長而無盡的煎熬。裘非不斷地問:「我的褲子在哪裡?」看似是在尋找一件衣物,實則是在尋找那早已被踐踏殆盡的尊嚴與勇氣。
我始終認為生活太安逸的人,往往寫不出真正動人的文章。裘非身處黑暗之中,但他的痛苦成就了寫作的敏感和靈氣。裘非說:「我寧願我自己是個愚蠢又快樂的商人。」這句話令我印象深刻。常有人說我的文章負面、悲慘,殊不知這些都是用現實中點滴血淚換取的。我何嘗不渴望我沒經歷過那些苦痛呢?我寧願我活得天真爛漫,對著悽慘的作文題目,卻發現自己不曾有過挫折。歲月不可回首,人生中的每一步都是單行道,於是我記住了書中的那句話——「請別忘了在泥裡的時刻,而僅作為一支花活著。」
書的最後,作者以小說式的筆法向讀者描述常人對精神患者的偏見。不論再怎麼努力治療患者,只要讓他們重新回到社會,迎接他們的依然是異樣的眼光與冷漠的歧視,使他們在好轉之後,又重新墜入黑暗。那些生活中常聽見的話:「精神病患者就該好好關起來,不准他們出來。」、「他爸爸是精神病,他一定也是。」人們未能參與他的悲慘過去,卻能輕易決斷他的現在與未來,人生有比這更荒謬嗎?
書中十七個亦真亦假的故事,向我們訴說著,他們既是精神病患,也是正常人。故事中他們經歷的——家暴、拋棄老人、猥褻、必須強顏歡笑的「微笑抑鬱症」……竟是那麼的稀鬆平常。不論是其中的患者或是周邊的人物,都讓讀者更容易看清書腰所說的那句:「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精神病患」。
《瘋人說》讓我明白,那些被標籤為「瘋子」的人,其實只是更早承受了這個世界的重量。他們並不遙遠,他們可能就在我們之中。隔絕、評斷,傷己又傷人,我們該學會理解與陪伴。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看見——那不只是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我們自己的倒影。





 國小組
國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