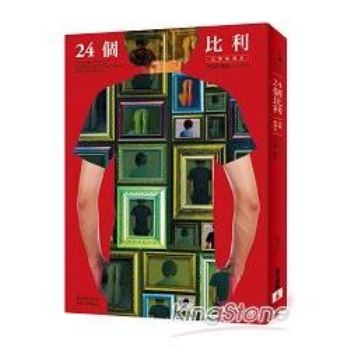
24個比利(完整新譯本)
9折特價342元

高中組 ‧ 佳作
屏東女子高級中學三年六班 林芸懋
屏東女子高級中學三年六班 林芸懋
捨去偏見,於是平等
比利˙密利根,罹患多重人格,是同儕嘲笑霸凌的箭靶,師長眼中的問題學生。無人知曉他內在碎裂如拼圖片片,只知道他陰晴不定,每分每秒都像不同的人。直到他因搶劫及強暴被捕,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師才發現他不是個狡詐的罪犯,而是個急需幫助的病人。終於有人願意明白他為何如此怪異且希冀幫助他,而非一味責怪嘲笑。
因此他說:「我現在明白了,警察到查寧威來找我,我並沒有真的被捕,我是獲救了,我很遺憾必須先傷害到別人,可是我覺得在過了二十二年之後,上帝終於對我微笑了。」
他被送至艾森斯接受治療,以受審判。在那裏他抓住一小片希望,第一次相信痊癒的可能。然而命運似乎仍對他冷笑——他得到盟友,也招來更多人對他大作文章。可怕的強暴犯和精神病患是報紙強烙在他身上的印記,讀者惶惑不安,因全然相信與放大的恐懼。醫生准許他外出的決定,被「驚人的批判聲浪」所拍打沖刷。
比利被迫暫時放棄請假外出等權利。他一直都遵守醫院規定,沒有觸犯法律,可是「現在他的權利卻被奪走了」。
種種挫敗及敵意使他在融合與裂解之中擺盪。然而人們不明白是他們加深了傷痛。即使醫生指出「因為媒體及密利根對媒體的反應,導致比利˙密利根的治療出現反效果。」議員卻嗤之以鼻,「責怪媒體報導真相簡直是推卸責任。」
報紙大肆報導比利,以一種預設立場。形塑著某些人的想法。
於是他在一次外出中遭槍擊,靈魂又因此碎片滿地。
法官判決將其送至惡名昭彰的利馬醫院,那裏是絕望的具象,因為患者不被視而為人。儘管二年半後,比利獲准回艾森斯,期間造成的損傷卻難以修復。
而這並非精神病患第一次受不公對待。自古老的年代,初民便視其為惡靈附身,將其驅逐是方法之一;中世紀的他們是惡魔與女巫,被焚燒、鞭打、吊死;文藝復興時代以餓死、鞭笞、放血加以「治療」;十八世紀的病人被監禁於牢獄及救濟院,受各種器具束縛自由。是人道精神醫療推動後,他們才再次成為人、成為需要治療的病人。
但常人對待他們的態度也跟著大幅改變了嗎?或許,只是自露骨的嫌惡轉為內心的偏見吧。「罹患精神病是可恥的,使家族蒙羞。」、「他們是無法治療的瘋子,應該和社會隔離。」不可否認,仍有人的觀念這樣扭曲,態度如此敵意。如此,我們該如何幫助他們本已傷痕累累的心?僅僅是一把更銳利的刀剜出他們的希望和自尊,逼迫他們演繹出我們預期看見的瘋狂罷了。
如果我們願給同等尊重,而非偏執視之洪水猛獸,願以平等看待,而非因畏怕而扭曲的目光,他們也許,就能少承受一些苦痛。
然而,盲目地排擠異類、偏執地厭惡特類,從不是罕異的現象。精神病患僅為一角冰山。
比利其中一個人格,菲利普,就曾以「死玻璃」輕蔑同性戀者,甚至打劫他們,因為清楚他們不敢聲張。其中一名被害人如此答覆比利的哥哥:「因為我目前正要應徵一份很重要的新工作,而且我是同性戀,要是我報警了,不但自己的身分曝光,連我幾個朋友也會遭殃。」
原來我們的目光無形中剝奪著特定族群的權利,逼迫他們收起不同顏色的羽翼,要他們安靜不喧譁,偽裝成所謂正常。有太多太多的無理觀念已深根於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是令人痛苦的刻板印象。精神病患和同性戀者如是,原住民、外籍勞工、伊斯蘭教徒等等,又何嘗不是。
是怎樣的心態准許我們歧視較小的群眾,允許我們拋棄尊重,不肯給予他們相同的待遇,反而歧視、打壓、嘲諷,甚或傷害他們?
是莫名的、自以為「正常」的優越感作祟,使我們排斥非我族類,還是害怕著遭遇排斥、追尋認可與歸屬,想藏進「正常」的羽絨下呢?
似乎,我們忘了,從來不是由聲音大小決定對錯是非,不是這樣的。正常與否當然也不能如此斷定。
剛出獄的比利和一個女孩驅車共遊,當他提起並非每個人都會如此對待剛出獄的人時,她說:「我不會為那種事評斷一個人,我也不願意別人來評斷我。」
也許每個人都該如她所言,不為了那種事──那些迥異於自身的種族、宗教、性別、性向、疾病──任意為別人標上註記。放下預設立場後,才真正看見那個人,而非標籤化的版。
或許,爭吵會因此沉睡,打鬥會因而離去,歧視與偏見也悄然踏上旅行。那時的世界,該是個平等快樂,容許各色羽翼的人們在蒼穹昂揚飛舞,自由唱出心曲的美麗世界吧。
因此他說:「我現在明白了,警察到查寧威來找我,我並沒有真的被捕,我是獲救了,我很遺憾必須先傷害到別人,可是我覺得在過了二十二年之後,上帝終於對我微笑了。」
他被送至艾森斯接受治療,以受審判。在那裏他抓住一小片希望,第一次相信痊癒的可能。然而命運似乎仍對他冷笑——他得到盟友,也招來更多人對他大作文章。可怕的強暴犯和精神病患是報紙強烙在他身上的印記,讀者惶惑不安,因全然相信與放大的恐懼。醫生准許他外出的決定,被「驚人的批判聲浪」所拍打沖刷。
比利被迫暫時放棄請假外出等權利。他一直都遵守醫院規定,沒有觸犯法律,可是「現在他的權利卻被奪走了」。
種種挫敗及敵意使他在融合與裂解之中擺盪。然而人們不明白是他們加深了傷痛。即使醫生指出「因為媒體及密利根對媒體的反應,導致比利˙密利根的治療出現反效果。」議員卻嗤之以鼻,「責怪媒體報導真相簡直是推卸責任。」
報紙大肆報導比利,以一種預設立場。形塑著某些人的想法。
於是他在一次外出中遭槍擊,靈魂又因此碎片滿地。
法官判決將其送至惡名昭彰的利馬醫院,那裏是絕望的具象,因為患者不被視而為人。儘管二年半後,比利獲准回艾森斯,期間造成的損傷卻難以修復。
而這並非精神病患第一次受不公對待。自古老的年代,初民便視其為惡靈附身,將其驅逐是方法之一;中世紀的他們是惡魔與女巫,被焚燒、鞭打、吊死;文藝復興時代以餓死、鞭笞、放血加以「治療」;十八世紀的病人被監禁於牢獄及救濟院,受各種器具束縛自由。是人道精神醫療推動後,他們才再次成為人、成為需要治療的病人。
但常人對待他們的態度也跟著大幅改變了嗎?或許,只是自露骨的嫌惡轉為內心的偏見吧。「罹患精神病是可恥的,使家族蒙羞。」、「他們是無法治療的瘋子,應該和社會隔離。」不可否認,仍有人的觀念這樣扭曲,態度如此敵意。如此,我們該如何幫助他們本已傷痕累累的心?僅僅是一把更銳利的刀剜出他們的希望和自尊,逼迫他們演繹出我們預期看見的瘋狂罷了。
如果我們願給同等尊重,而非偏執視之洪水猛獸,願以平等看待,而非因畏怕而扭曲的目光,他們也許,就能少承受一些苦痛。
然而,盲目地排擠異類、偏執地厭惡特類,從不是罕異的現象。精神病患僅為一角冰山。
比利其中一個人格,菲利普,就曾以「死玻璃」輕蔑同性戀者,甚至打劫他們,因為清楚他們不敢聲張。其中一名被害人如此答覆比利的哥哥:「因為我目前正要應徵一份很重要的新工作,而且我是同性戀,要是我報警了,不但自己的身分曝光,連我幾個朋友也會遭殃。」
原來我們的目光無形中剝奪著特定族群的權利,逼迫他們收起不同顏色的羽翼,要他們安靜不喧譁,偽裝成所謂正常。有太多太多的無理觀念已深根於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是令人痛苦的刻板印象。精神病患和同性戀者如是,原住民、外籍勞工、伊斯蘭教徒等等,又何嘗不是。
是怎樣的心態准許我們歧視較小的群眾,允許我們拋棄尊重,不肯給予他們相同的待遇,反而歧視、打壓、嘲諷,甚或傷害他們?
是莫名的、自以為「正常」的優越感作祟,使我們排斥非我族類,還是害怕著遭遇排斥、追尋認可與歸屬,想藏進「正常」的羽絨下呢?
似乎,我們忘了,從來不是由聲音大小決定對錯是非,不是這樣的。正常與否當然也不能如此斷定。
剛出獄的比利和一個女孩驅車共遊,當他提起並非每個人都會如此對待剛出獄的人時,她說:「我不會為那種事評斷一個人,我也不願意別人來評斷我。」
也許每個人都該如她所言,不為了那種事──那些迥異於自身的種族、宗教、性別、性向、疾病──任意為別人標上註記。放下預設立場後,才真正看見那個人,而非標籤化的版。
或許,爭吵會因此沉睡,打鬥會因而離去,歧視與偏見也悄然踏上旅行。那時的世界,該是個平等快樂,容許各色羽翼的人們在蒼穹昂揚飛舞,自由唱出心曲的美麗世界吧。





 國小組
國小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