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從明代中期的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與明末的制藝風潮三股風潮的遞嬗變動中,將視角轉向一群常被忽略,卻可能左右時代思潮的隱形推手──小讀書人及其社集活動。
當十六世紀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從巔峰走向中衰,思想界迎來了何種轉變?全書跳脫傳統以大儒為中心的視角,深入探討這群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的小人物。他們並不只是大儒學說的被動傳播者,而是鄉里風氣的真正塑造者。面對科舉功名的壓力與未來生計的不確定性,他們的集體焦慮與務實抉擇,最終將時代風潮從心性義理的講說,導向與科舉功名相關的制藝寫作。
本書以江右陽明學派所在的江西為場域,剖析三股風潮的交織與消長,並指出小讀書人在大儒之外,走出自己的道路,匯聚成一股足以牽動明末思潮走向的力量。這部從基層出發的「小人物思想史」,為理解明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不一樣的視野,也讓我們看見一個時代的變遷,往往始於無數小人物在生存與理想間的微小抉擇。
當十六世紀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從巔峰走向中衰,思想界迎來了何種轉變?全書跳脫傳統以大儒為中心的視角,深入探討這群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的小人物。他們並不只是大儒學說的被動傳播者,而是鄉里風氣的真正塑造者。面對科舉功名的壓力與未來生計的不確定性,他們的集體焦慮與務實抉擇,最終將時代風潮從心性義理的講說,導向與科舉功名相關的制藝寫作。
本書以江右陽明學派所在的江西為場域,剖析三股風潮的交織與消長,並指出小讀書人在大儒之外,走出自己的道路,匯聚成一股足以牽動明末思潮走向的力量。這部從基層出發的「小人物思想史」,為理解明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不一樣的視野,也讓我們看見一個時代的變遷,往往始於無數小人物在生存與理想間的微小抉擇。
目錄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自序
導 論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二、小讀書人的動向與社集活動
三、應舉與窮經的分歧
四、章節安排及主旨課題
五、對陽明學研究的反思
第一章 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二、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
三、將變未變之際
結語
第二章 江西復古派詩社的發展與風潮的轉向
前言
一、江西文學復古運動:士紳與宗室
二、寧王府宗室的躍昇
三、新風潮下的宗室與小讀書人
四、轉向:制藝為主旋律的明末社集
結語
附錄
第三章 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之起
前言
一、從鼎盛到中衰
二、大儒的形象爭議
三、講會的萎縮及中衰
四、江西陽明心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四章 明末江西派的成型與選本的流行
前言
一、各地制藝文社的興起
二、豫章社的舉行
三、明末選本的流傳
結語
第五章 江西派及其主張
前言
一、應舉與窮經合一:標榜古學的制藝寫作
二、制藝為新文體及其定位
三、制藝與陽明學的關係
四、所謂古學:古籍復興下的博覽博學
五、諸子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六章 江西派的挑戰:風氣之變與江南復社
前言
一、諸子學流風對江西派古學的弊害
二、江南復社諸子與標舉經學的主張
三、艾南英與復社諸子的分歧及競爭
四、競爭或合作?
五、江南復社的政治爭議及江西派的兩種立場
結語
第七章 清初江西遺民與學風思潮的變化
前言
一、清初江西社集的沉寂與萎縮
二、背離又淵源於明末制藝風潮的兩人
三、喪亂之餘的重新出發
四、清初的重新定位與異軍突起:李來泰與李紱
結語
結 論
附 錄 對制藝解經的反思
徵引書目
自序
導 論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二、小讀書人的動向與社集活動
三、應舉與窮經的分歧
四、章節安排及主旨課題
五、對陽明學研究的反思
第一章 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二、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
三、將變未變之際
結語
第二章 江西復古派詩社的發展與風潮的轉向
前言
一、江西文學復古運動:士紳與宗室
二、寧王府宗室的躍昇
三、新風潮下的宗室與小讀書人
四、轉向:制藝為主旋律的明末社集
結語
附錄
第三章 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之起
前言
一、從鼎盛到中衰
二、大儒的形象爭議
三、講會的萎縮及中衰
四、江西陽明心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四章 明末江西派的成型與選本的流行
前言
一、各地制藝文社的興起
二、豫章社的舉行
三、明末選本的流傳
結語
第五章 江西派及其主張
前言
一、應舉與窮經合一:標榜古學的制藝寫作
二、制藝為新文體及其定位
三、制藝與陽明學的關係
四、所謂古學:古籍復興下的博覽博學
五、諸子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六章 江西派的挑戰:風氣之變與江南復社
前言
一、諸子學流風對江西派古學的弊害
二、江南復社諸子與標舉經學的主張
三、艾南英與復社諸子的分歧及競爭
四、競爭或合作?
五、江南復社的政治爭議及江西派的兩種立場
結語
第七章 清初江西遺民與學風思潮的變化
前言
一、清初江西社集的沉寂與萎縮
二、背離又淵源於明末制藝風潮的兩人
三、喪亂之餘的重新出發
四、清初的重新定位與異軍突起:李來泰與李紱
結語
結 論
附 錄 對制藝解經的反思
徵引書目
序/導讀
序(節錄)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一、關於《小人物的思想史》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張藝曦教授見面,是在二○二四年六月一日由香港中華書局主辦的「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陽明心學:首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藝曦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輕、帥氣、文質彬彬,感覺是香港或台灣某高校的在讀博士生或青年教師,一交流才知道,藝曦確實是年輕,但並不是在讀博士生,而是成果已經相當豐碩的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與家族史的研究者,不但多次獲得「國科會」的項目支持,而且獲得過余英時人文研究獎。
那次會議之後,我們保持著微信聯系,不久,收到藝曦教授寄來的大作《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讓我受益匪淺。友情繼續,藝曦教授在他的第三部學術專著《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即將出版之際,囑我為序,於情於理不容推托,特別是即將出版的大作又是討論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的「小人物」,引起我的興趣和共鳴,遂欣然承命。
《小人物的思想史》繼續了作者《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裡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二○○五)、《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二○二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風格,可以說是在前兩部著作基礎上的持續推進和拓展,其中又有諸多的創新與突破,構成其研究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小讀書人」的三部曲,整個研究過程將近三十年。
《小人物的思想史》分為「導論」和七章正文,依次討論:儒家經典闡釋過程中發生的明中晚期三股風潮(陽明心學、文學復古、制藝風潮)的變動、江西復古派詩社的形成發展及其對學術風潮轉向的影響、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的興起、明末江西制藝派的形成及選本流行、江西制藝派的特征與主張、江南復社的興起及其對江西派的挑戰、清初江西社集的全面式微與回光返照。其中,對於風潮變化過程中江右王門及文學復古、江西制藝的代表性人物,如余曰德與朱多煃、陳弘緒與傅占衡、陳際泰與艾南英、魏禧與謝文洊,以及李紱等,均辟專節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少具有開創性的見解。在討論「江右王門」的時候,藝曦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區分,即將「陽明學」區分為「作為學說的陽明學」和「作為運動的陽明學」,從而發現了一個更有趣的現象:將陽明學作為「學說」的是「大儒」,如鄒守益、羅洪先等,將陽明學作為「運動」的是「小讀書人」,即鄒、羅等人的沒有功名或功名較低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們,他們將老師的學說向更為廣闊的縣鄉「小讀書人」群體傳播。既然本書是以「小讀書人」的角度切入,那麼所討論的「陽明學」,當然主要傾向於「運動陽明學」。
在討論「制藝解經」的時候,藝曦教授指出: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對陽明心學的批評,很大程度是在批評通過講會、注經、制藝等方式「改造」了的陽明學,而並非以「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為核心內容的王陽明及江右王門第一、二代弟子所倡導的陽明學:「顧炎武等人所批評的,恐怕不是明中期以來師友講學的陽明學,而是進入制藝寫作中的陽明學。」
藝曦教授又以曾在吉安學習陽明心學的建昌府南城縣人涂伯昌為例,指出其對陽明心學的學習和闡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寫作制藝文。而當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傳來後,涂伯昌痛心疾首之余,並沒有反省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儒」及「小讀書人」一門心思鑽研「制藝文」、追求過精致的利己主義生活而全然不顧民眾的苦難,卻將「誤國」的責任推向被他們引入歧途的變異了陽明學,而完全無視陽明心學本質上乃是「致用之學」「行動之學」。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第三本學術論著,也是我對自己過去在陽明學研究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回溯到我的第一本書《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這是從我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以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為研究對象,完成於2005年,距今恰好二十年。
江西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是極特殊的地方,它從兩宋以來,便是思想及文化中心,既有江西詩派(黃庭堅),有唐宋八大家之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有明初臺閣體(楊士奇),人們會討論這些文學流派,但卻鮮少關注江西這個地方。十六世紀陽明學極盛期,它是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連泰州學派的多位代表人物(顏鈞、何心隱、羅汝芳),也是出自此地,但直到2000年左右,仍很少研究者注意江西。江西在明初的科舉功名有極驚人的表現,明末則以制藝引領風氣,有艾南英等江右四大家,但亦不受肯定。也因此,當我決定以江西為研究區域時,我就好像看著一個得獎無數,卻接不到任何戲約的演員。大小獎項都有它的提名及得獎,但下了舞臺以後,就沒人找上它了。
正因為江西是一個在思想、文化的豐富、特色及成就皆不下於江南的地方,所以當年我的博論題目便選擇江右陽明學派,討論其學說宗旨、群體活動,以及學術思想的實踐,尤其把重點放在陽明學大儒所倡導的社會事業及其後續的政治效應。但我在完成博論以後,其實仍有許多的不安及疑惑。這些疑惑與不安來源於研究與現實的落差。在研究上,我們會限定對象,封鎖地域範圍,以及集中閱讀相關資料,但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如此。人的思想及情感是複雜而多樣的,一個人不會僅習陽明學而不理會其他學問,也不會只考慮心性義理而不顧其他,而在生活中更不會只尋求同群的人的認同,無論再任性的人,也不會只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也因此,當我遍閱江右陽明學派的大儒及小讀書人的著作及相關資料,而始終未見這些大儒與陽明學以外的人物有較密切或頻繁往來時,我不免感到好奇。而大儒率領小讀書人展開社會事業時,卻鮮少談及人生前途與出路、功名與未來時,更令我不安。
陽明學不會在只有陽明學的環境下發展,所以人們會在理學與文學、講會與詩社間徘徊,而科考功名更是極切身的課題。大儒對現實的考量及各式的徘徊焦慮不會太過突顯,畢竟大儒是成功者,成功者不必選擇。(或許羅洪先是例外,他到五十歲以後才真正放下心來。)但小讀書人卻有更多須猶慮的事。這就像高教教師,由於已有職位,所須考慮的是在職位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學生卻須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們不能夠過份執著矢志學術的心志,也必須同時準備公務人員考試,加強英語能力,隨時注意其他領域的就業機會。高教教師有專業,專業是這些教師的現在與未來,既有與所有。但學生一無所有,於是反而更須面對不確定且多元的現在與未來。
拜近三十年來四庫系列叢書及一些大部頭叢書的出版之賜,過去不易接觸到的古籍,許多都已垂手可得,加上地方志資料──這是過去思想史研究較少用,我見到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的人際往來與活動、思想與立場,但這些小讀書人往往只有三兩行的文字敘述,或一兩篇序文、傳記或墓誌銘,資料太有限,以致於我雖知有這群人,卻難以下筆。於是我只能夠著眼於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包括兩者在講會及社會事業上的合作,但即使如此,小讀書人仍僅側見旁出於大儒之間,而沒有給我太多筆墨勾勒描寫的機會。
於是我著手寫作兩本書,一本是2022年出版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除了繼續討論陽明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流傳及作用以外,我也選擇幾個小讀書人的個案及區域,利用文集、地方志,加上大量的族譜資料,以更具體寫出小讀書人所遭遇的問題及困境。若說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中,大儒仍是主角,在此書中則是專門寫小讀書人的境遇及處境,讓更多鎂光燈落在小讀書人身上。另一本即此刻的這本書,我著手處理萬曆朝中期陽明學趨於中衰以後的變化,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以及小讀書人的處境將會有何轉變?
無論大儒或小讀書人,他們都處在某個運動或風潮中,他們既有獨立自主的思想及能力,但同時也會隨風潮而移動或擺盪。十六世紀是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的鼎盛期,但萬曆朝中期,也就是進入十七世紀以後,兩運動皆已走向中衰,而制藝風潮繼之而起,在風潮的遞嬗轉變之際,人們將會面臨許多抉擇的難題,與選擇的困境。當年我寫作陽明學的鄉里實踐,談其社會事業,寫到萬曆中期便幾乎無法再寫,因為我發現萬曆朝的陽明學變了,不是學術內容變質,而是講會與社會事業皆起了質變,而大儒與小讀書人皆遭遇極大的危機與挑戰。嘉靖朝的陽明學有強大的動能,大儒引領而小讀書人跟隨,周遭都是極樂觀的氣氛與氛圍。但萬曆朝不同,此時的陽明學遭遇太多內在及外來的挑戰,而這些挑戰都不是從陽明學及其社群便可以找到原因與答案的。我試過幾種思路及切入角度,卻都發現已無法只從陽明學來談陽明學,以致於我一度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中,我既不能無視我所讀所見的一切,更不能曲解史料,但又深知這是一個既大又難解的難題,於是只好暫且作結,而以鄒元標作為我的博論的結尾。
這本書所處理的,正是十七世紀前半葉約四、五十年的時間中,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與制藝風潮,這三股風潮的興衰與作用,相關社集及小讀書人的動向,以及諸多方面的發展及影響。也是在完成這本書後,我才了解何以當年的我寫不出來,因為在經歷一百年陽明學的洗禮後,小讀書人已經具備更大的動能,思潮的走向已不僅由大儒引領,還有更多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來決定的。若忽略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便難以理解明末的思想文化史。至於影響小讀書人群體動向的因素,不只有理學與文學而已,還有制藝寫作,三股風潮及力量的交集交錯,才是解讀明末思想文化史的關鍵所在。
這本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2013年,這一年我以「明末江西社集活動、復古風潮與文化實踐──兼及與復社的比較」為題,申請國科會計劃。當時我過度自信,也過度樂觀,以為至多四到六年,便可以完成這個計劃。有次我問老師,一本書應該預估幾年完成?老師說:至少七年,才能夠深入一個課題。我當下想,七年,好久,等於又寫一本博論。當時的我卻不知道,七年其實已經是很樂觀的年數了。
當時老師提醒我,即使寫書,仍必須持續發表單篇論文,畢竟書的完成是某年的事,學界無法容許我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發表。於是我有一系列跟陽明畫像、淨明道、小讀書人等有關的論文發表。這或算是實踐老師曾說的,必須同時有幾個題目在手上寫的叮囑。只是我做不到像老師一樣,能夠以單篇文章被人所知,我所寫的論文,也許沒有多少影響力吧。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得到許多人的幫忙。我最初決定以社集為題時,其實是很猶豫的,加上最初的幾年幾乎沒有明顯進展,讓我不免萌生是否選錯題的焦慮。老師幾次告訴我,他以前在《國粹學報》上讀到有人說江西的社集極多(我後來才知道這是黃節的話),所以老師認為這是好題目,非常值得研究。也是老師幾次的篤定及確認,才讓我得以堅持下來。
導論(節錄)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本書主要從小讀書人及社集的角度,談明中晚期江西三股風潮或運動之間的遞嬗變動,三股風潮分別是明中期興起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明末的制藝風潮。
文學復古運動以復古派為核心,有前七子及後七子先後主盟文壇。陽明心學運動中,王守仁(1472—1529)的門人弟子散布及往來各地倡學,以浙中、江右、泰州三學派最盛。兩運動對當時的臺閣體、程朱學皆有所不滿,於是皆以復古為取向。以前、後七子為首,訴求回歸古代的詩與古文辭,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陽明學則訴求不藉由典籍,而直接觸及本心良知,而將此視為兩千年的絕學,但其實也是另一種回歸想像古代的方式。
兩運動都有從大儒、大文人而向下擴展流傳的傾向。陽明心學家積極往下走,不僅小讀書人參與其間,甚至是農工商賈也有參加講會的例子。過去學界對左派王學的研究,正是聚焦在陽明心學往基層百姓的流傳。文學領域從前七子以來,其創作視角下移及日常化的傾向,也體現了明中期以後文化下移的趨勢,如李夢陽(1472-1529)「真詩乃在民間」的主張便頗為人們所熟知。至於復古派講究模擬,雖然頗受訾議,被嘲諷為「依倣唐人聲律以為詩,摘拾秦漢字句以為文」,但其實這類「依倣」「摘拾」的方式,從另個角度看,正是降低了作詩的門檻,於是作詩的不僅僅只有文人雅士,小讀書人(或甚至庶民)間也多有詩人。
儘管從時序上來看,文學復古運動先行,而陽明運動後起,但各地仍有差異。若是從社集來判斷,江西作為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陽明學的風氣從嘉靖朝便已極盛,從南昌、撫州到吉安三府,都有陽明心學的代表人物,其中吉安府的安福、吉水兩縣更是大儒輩出,加上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讓陽明心學進一步有草根化的傾向。相對於此,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較不顯著,江西在宋代雖有江西詩派,但入明以後此詩派不盛,待文學復古運動起,復古派對兩宋以來的江西詩派的訾議攻擊,往往讓人忽略了同時期江西的文學活動,而僅湯顯祖(1550-1616)較受注意而已。待王世貞(1526-1590)主盟時期,以余曰德(1514-1583)及宗室朱多煃(1534-1593)為首,與後七子相應和,直到隆慶、萬曆朝左右才有復古派詩社──芙蓉社,在南昌成立。也因此,儘管兩運動同時併起,但江西的陽明心學運動則從嘉靖朝便居主流,而主導整個學術流風及走向,文學復古運動則相對較弱,居於支線的位置。以江西寧王府宗室為例,嘉靖年間拱字輩的宗室所接觸的是陽明心學,但不活躍。直到晚明,多字輩的宗室與南昌當地士紳共組芙蓉社,宗室在詩作上的長才及優勢才得以展現。(詳第2章)也因此,本書將以陽明心學為主線,輔以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展開討論。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一、關於《小人物的思想史》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張藝曦教授見面,是在二○二四年六月一日由香港中華書局主辦的「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陽明心學:首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藝曦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輕、帥氣、文質彬彬,感覺是香港或台灣某高校的在讀博士生或青年教師,一交流才知道,藝曦確實是年輕,但並不是在讀博士生,而是成果已經相當豐碩的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與家族史的研究者,不但多次獲得「國科會」的項目支持,而且獲得過余英時人文研究獎。
那次會議之後,我們保持著微信聯系,不久,收到藝曦教授寄來的大作《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讓我受益匪淺。友情繼續,藝曦教授在他的第三部學術專著《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即將出版之際,囑我為序,於情於理不容推托,特別是即將出版的大作又是討論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的「小人物」,引起我的興趣和共鳴,遂欣然承命。
《小人物的思想史》繼續了作者《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裡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二○○五)、《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二○二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風格,可以說是在前兩部著作基礎上的持續推進和拓展,其中又有諸多的創新與突破,構成其研究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小讀書人」的三部曲,整個研究過程將近三十年。
《小人物的思想史》分為「導論」和七章正文,依次討論:儒家經典闡釋過程中發生的明中晚期三股風潮(陽明心學、文學復古、制藝風潮)的變動、江西復古派詩社的形成發展及其對學術風潮轉向的影響、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的興起、明末江西制藝派的形成及選本流行、江西制藝派的特征與主張、江南復社的興起及其對江西派的挑戰、清初江西社集的全面式微與回光返照。其中,對於風潮變化過程中江右王門及文學復古、江西制藝的代表性人物,如余曰德與朱多煃、陳弘緒與傅占衡、陳際泰與艾南英、魏禧與謝文洊,以及李紱等,均辟專節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少具有開創性的見解。在討論「江右王門」的時候,藝曦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區分,即將「陽明學」區分為「作為學說的陽明學」和「作為運動的陽明學」,從而發現了一個更有趣的現象:將陽明學作為「學說」的是「大儒」,如鄒守益、羅洪先等,將陽明學作為「運動」的是「小讀書人」,即鄒、羅等人的沒有功名或功名較低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們,他們將老師的學說向更為廣闊的縣鄉「小讀書人」群體傳播。既然本書是以「小讀書人」的角度切入,那麼所討論的「陽明學」,當然主要傾向於「運動陽明學」。
在討論「制藝解經」的時候,藝曦教授指出: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對陽明心學的批評,很大程度是在批評通過講會、注經、制藝等方式「改造」了的陽明學,而並非以「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為核心內容的王陽明及江右王門第一、二代弟子所倡導的陽明學:「顧炎武等人所批評的,恐怕不是明中期以來師友講學的陽明學,而是進入制藝寫作中的陽明學。」
藝曦教授又以曾在吉安學習陽明心學的建昌府南城縣人涂伯昌為例,指出其對陽明心學的學習和闡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寫作制藝文。而當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傳來後,涂伯昌痛心疾首之余,並沒有反省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儒」及「小讀書人」一門心思鑽研「制藝文」、追求過精致的利己主義生活而全然不顧民眾的苦難,卻將「誤國」的責任推向被他們引入歧途的變異了陽明學,而完全無視陽明心學本質上乃是「致用之學」「行動之學」。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第三本學術論著,也是我對自己過去在陽明學研究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回溯到我的第一本書《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這是從我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以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為研究對象,完成於2005年,距今恰好二十年。
江西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是極特殊的地方,它從兩宋以來,便是思想及文化中心,既有江西詩派(黃庭堅),有唐宋八大家之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有明初臺閣體(楊士奇),人們會討論這些文學流派,但卻鮮少關注江西這個地方。十六世紀陽明學極盛期,它是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連泰州學派的多位代表人物(顏鈞、何心隱、羅汝芳),也是出自此地,但直到2000年左右,仍很少研究者注意江西。江西在明初的科舉功名有極驚人的表現,明末則以制藝引領風氣,有艾南英等江右四大家,但亦不受肯定。也因此,當我決定以江西為研究區域時,我就好像看著一個得獎無數,卻接不到任何戲約的演員。大小獎項都有它的提名及得獎,但下了舞臺以後,就沒人找上它了。
正因為江西是一個在思想、文化的豐富、特色及成就皆不下於江南的地方,所以當年我的博論題目便選擇江右陽明學派,討論其學說宗旨、群體活動,以及學術思想的實踐,尤其把重點放在陽明學大儒所倡導的社會事業及其後續的政治效應。但我在完成博論以後,其實仍有許多的不安及疑惑。這些疑惑與不安來源於研究與現實的落差。在研究上,我們會限定對象,封鎖地域範圍,以及集中閱讀相關資料,但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如此。人的思想及情感是複雜而多樣的,一個人不會僅習陽明學而不理會其他學問,也不會只考慮心性義理而不顧其他,而在生活中更不會只尋求同群的人的認同,無論再任性的人,也不會只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也因此,當我遍閱江右陽明學派的大儒及小讀書人的著作及相關資料,而始終未見這些大儒與陽明學以外的人物有較密切或頻繁往來時,我不免感到好奇。而大儒率領小讀書人展開社會事業時,卻鮮少談及人生前途與出路、功名與未來時,更令我不安。
陽明學不會在只有陽明學的環境下發展,所以人們會在理學與文學、講會與詩社間徘徊,而科考功名更是極切身的課題。大儒對現實的考量及各式的徘徊焦慮不會太過突顯,畢竟大儒是成功者,成功者不必選擇。(或許羅洪先是例外,他到五十歲以後才真正放下心來。)但小讀書人卻有更多須猶慮的事。這就像高教教師,由於已有職位,所須考慮的是在職位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學生卻須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們不能夠過份執著矢志學術的心志,也必須同時準備公務人員考試,加強英語能力,隨時注意其他領域的就業機會。高教教師有專業,專業是這些教師的現在與未來,既有與所有。但學生一無所有,於是反而更須面對不確定且多元的現在與未來。
拜近三十年來四庫系列叢書及一些大部頭叢書的出版之賜,過去不易接觸到的古籍,許多都已垂手可得,加上地方志資料──這是過去思想史研究較少用,我見到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的人際往來與活動、思想與立場,但這些小讀書人往往只有三兩行的文字敘述,或一兩篇序文、傳記或墓誌銘,資料太有限,以致於我雖知有這群人,卻難以下筆。於是我只能夠著眼於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包括兩者在講會及社會事業上的合作,但即使如此,小讀書人仍僅側見旁出於大儒之間,而沒有給我太多筆墨勾勒描寫的機會。
於是我著手寫作兩本書,一本是2022年出版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除了繼續討論陽明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流傳及作用以外,我也選擇幾個小讀書人的個案及區域,利用文集、地方志,加上大量的族譜資料,以更具體寫出小讀書人所遭遇的問題及困境。若說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中,大儒仍是主角,在此書中則是專門寫小讀書人的境遇及處境,讓更多鎂光燈落在小讀書人身上。另一本即此刻的這本書,我著手處理萬曆朝中期陽明學趨於中衰以後的變化,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以及小讀書人的處境將會有何轉變?
無論大儒或小讀書人,他們都處在某個運動或風潮中,他們既有獨立自主的思想及能力,但同時也會隨風潮而移動或擺盪。十六世紀是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的鼎盛期,但萬曆朝中期,也就是進入十七世紀以後,兩運動皆已走向中衰,而制藝風潮繼之而起,在風潮的遞嬗轉變之際,人們將會面臨許多抉擇的難題,與選擇的困境。當年我寫作陽明學的鄉里實踐,談其社會事業,寫到萬曆中期便幾乎無法再寫,因為我發現萬曆朝的陽明學變了,不是學術內容變質,而是講會與社會事業皆起了質變,而大儒與小讀書人皆遭遇極大的危機與挑戰。嘉靖朝的陽明學有強大的動能,大儒引領而小讀書人跟隨,周遭都是極樂觀的氣氛與氛圍。但萬曆朝不同,此時的陽明學遭遇太多內在及外來的挑戰,而這些挑戰都不是從陽明學及其社群便可以找到原因與答案的。我試過幾種思路及切入角度,卻都發現已無法只從陽明學來談陽明學,以致於我一度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中,我既不能無視我所讀所見的一切,更不能曲解史料,但又深知這是一個既大又難解的難題,於是只好暫且作結,而以鄒元標作為我的博論的結尾。
這本書所處理的,正是十七世紀前半葉約四、五十年的時間中,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與制藝風潮,這三股風潮的興衰與作用,相關社集及小讀書人的動向,以及諸多方面的發展及影響。也是在完成這本書後,我才了解何以當年的我寫不出來,因為在經歷一百年陽明學的洗禮後,小讀書人已經具備更大的動能,思潮的走向已不僅由大儒引領,還有更多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來決定的。若忽略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便難以理解明末的思想文化史。至於影響小讀書人群體動向的因素,不只有理學與文學而已,還有制藝寫作,三股風潮及力量的交集交錯,才是解讀明末思想文化史的關鍵所在。
這本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2013年,這一年我以「明末江西社集活動、復古風潮與文化實踐──兼及與復社的比較」為題,申請國科會計劃。當時我過度自信,也過度樂觀,以為至多四到六年,便可以完成這個計劃。有次我問老師,一本書應該預估幾年完成?老師說:至少七年,才能夠深入一個課題。我當下想,七年,好久,等於又寫一本博論。當時的我卻不知道,七年其實已經是很樂觀的年數了。
當時老師提醒我,即使寫書,仍必須持續發表單篇論文,畢竟書的完成是某年的事,學界無法容許我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發表。於是我有一系列跟陽明畫像、淨明道、小讀書人等有關的論文發表。這或算是實踐老師曾說的,必須同時有幾個題目在手上寫的叮囑。只是我做不到像老師一樣,能夠以單篇文章被人所知,我所寫的論文,也許沒有多少影響力吧。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得到許多人的幫忙。我最初決定以社集為題時,其實是很猶豫的,加上最初的幾年幾乎沒有明顯進展,讓我不免萌生是否選錯題的焦慮。老師幾次告訴我,他以前在《國粹學報》上讀到有人說江西的社集極多(我後來才知道這是黃節的話),所以老師認為這是好題目,非常值得研究。也是老師幾次的篤定及確認,才讓我得以堅持下來。
導論(節錄)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本書主要從小讀書人及社集的角度,談明中晚期江西三股風潮或運動之間的遞嬗變動,三股風潮分別是明中期興起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明末的制藝風潮。
文學復古運動以復古派為核心,有前七子及後七子先後主盟文壇。陽明心學運動中,王守仁(1472—1529)的門人弟子散布及往來各地倡學,以浙中、江右、泰州三學派最盛。兩運動對當時的臺閣體、程朱學皆有所不滿,於是皆以復古為取向。以前、後七子為首,訴求回歸古代的詩與古文辭,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陽明學則訴求不藉由典籍,而直接觸及本心良知,而將此視為兩千年的絕學,但其實也是另一種回歸想像古代的方式。
兩運動都有從大儒、大文人而向下擴展流傳的傾向。陽明心學家積極往下走,不僅小讀書人參與其間,甚至是農工商賈也有參加講會的例子。過去學界對左派王學的研究,正是聚焦在陽明心學往基層百姓的流傳。文學領域從前七子以來,其創作視角下移及日常化的傾向,也體現了明中期以後文化下移的趨勢,如李夢陽(1472-1529)「真詩乃在民間」的主張便頗為人們所熟知。至於復古派講究模擬,雖然頗受訾議,被嘲諷為「依倣唐人聲律以為詩,摘拾秦漢字句以為文」,但其實這類「依倣」「摘拾」的方式,從另個角度看,正是降低了作詩的門檻,於是作詩的不僅僅只有文人雅士,小讀書人(或甚至庶民)間也多有詩人。
儘管從時序上來看,文學復古運動先行,而陽明運動後起,但各地仍有差異。若是從社集來判斷,江西作為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陽明學的風氣從嘉靖朝便已極盛,從南昌、撫州到吉安三府,都有陽明心學的代表人物,其中吉安府的安福、吉水兩縣更是大儒輩出,加上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讓陽明心學進一步有草根化的傾向。相對於此,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較不顯著,江西在宋代雖有江西詩派,但入明以後此詩派不盛,待文學復古運動起,復古派對兩宋以來的江西詩派的訾議攻擊,往往讓人忽略了同時期江西的文學活動,而僅湯顯祖(1550-1616)較受注意而已。待王世貞(1526-1590)主盟時期,以余曰德(1514-1583)及宗室朱多煃(1534-1593)為首,與後七子相應和,直到隆慶、萬曆朝左右才有復古派詩社──芙蓉社,在南昌成立。也因此,儘管兩運動同時併起,但江西的陽明心學運動則從嘉靖朝便居主流,而主導整個學術流風及走向,文學復古運動則相對較弱,居於支線的位置。以江西寧王府宗室為例,嘉靖年間拱字輩的宗室所接觸的是陽明心學,但不活躍。直到晚明,多字輩的宗室與南昌當地士紳共組芙蓉社,宗室在詩作上的長才及優勢才得以展現。(詳第2章)也因此,本書將以陽明心學為主線,輔以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展開討論。
試閱
第一章 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三類書籍為主。由於很少連結到尊經或復興經書等口號,所以能夠疏離於「文以載道」的要求,而歸向於文學本位。但在蒐獵古籍的風氣下而大量刊行的諸子書,影響所及,則已逸出文學本位之外。
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說,所對抗的是僵化以後的程朱理學,而有意在程朱理學所壟斷的儒學詮釋以外開闢新途。良知雖不假知識聞見,但「六經註我」的立場讓人在詮釋典籍上較為自由,人們可以不必進入典籍的考證、章句的講究,而可以用一套原則來貫通諸多典籍。這其實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典籍時,是相對簡捷便當的一種作法及立場,而這些古籍等於提供了陽明心學詮釋儒經的思想資源。
另一方面,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最初是若即若離的,王守仁雖以儒經的內容來印證所悟,最初所側重的在致良知說而不在儒經的詮釋,但陽明心學不可能跟儒經詮釋完全無關,如心學大儒對《大學》改本各類詮釋及見解,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讓陽明心學很容易被制藝寫作所用,至少在萬曆朝便已見到科舉用書中引用陽明心學來詮釋儒經。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中,古籍的復興與陽明心學作為儒經詮釋,是兩項凸出的特點。
制藝也有變,從單純的應試之文,到漸漸受到正面肯定。萬曆朝制藝宗匠湯賓尹先是高度肯定制藝詮釋儒經的價值,已開了明末制藝風潮的風氣之先。明末江西派對湯賓尹的某些見解雖有批評,但對於以制藝詮釋儒經則又更往前推了一步,而形成以制藝作為新文體,以古學為內容的主張,而古學的主軸即諸子百家之學。
第五章將談到,由於不少人把諸子書定位為羽翼六經,相當於把諸子書納入到六經的詮釋中,待明末制藝風潮起,由於制藝被定位為經義之學,是詮釋儒經的新文體,於是這些重刊的諸子書,便被入制藝寫作中,如江西派便擅長援引諸子書入制藝寫作中,以諸子書來詮釋儒經。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1. 從文學復古到古籍的校訂刊刻
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詩作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古文辭則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原則上,對詩的重視甚於對古文辭。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須在內容感情上神似,標榜「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要求人們在寫作詩及古文辭,模擬盛唐詩及秦漢文。但復古派並不是簡單為復古而復古而已,而是有寓創新於復古之意。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他們認為從事文學的不二法門,無他,只要精研這些有限的古代典型之作,字模句擬,依樣葫蘆,如能求其近似或一致,便可進入文學的堂奧,上比古人,自成名家」,「這樣的方法就更直截了當,可謂簡易率直之至」。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以摹倣為入手法,人們為了參考先秦兩漢的典籍及漢魏盛唐的詩作,而有更多閱讀古籍的需要,於是帶動蒐獵古籍的風潮。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三類書籍為主。由於很少連結到尊經或復興經書等口號,所以能夠疏離於「文以載道」的要求,而歸向於文學本位。但在蒐獵古籍的風氣下而大量刊行的諸子書,影響所及,則已逸出文學本位之外。
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說,所對抗的是僵化以後的程朱理學,而有意在程朱理學所壟斷的儒學詮釋以外開闢新途。良知雖不假知識聞見,但「六經註我」的立場讓人在詮釋典籍上較為自由,人們可以不必進入典籍的考證、章句的講究,而可以用一套原則來貫通諸多典籍。這其實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典籍時,是相對簡捷便當的一種作法及立場,而這些古籍等於提供了陽明心學詮釋儒經的思想資源。
另一方面,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最初是若即若離的,王守仁雖以儒經的內容來印證所悟,最初所側重的在致良知說而不在儒經的詮釋,但陽明心學不可能跟儒經詮釋完全無關,如心學大儒對《大學》改本各類詮釋及見解,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讓陽明心學很容易被制藝寫作所用,至少在萬曆朝便已見到科舉用書中引用陽明心學來詮釋儒經。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中,古籍的復興與陽明心學作為儒經詮釋,是兩項凸出的特點。
制藝也有變,從單純的應試之文,到漸漸受到正面肯定。萬曆朝制藝宗匠湯賓尹先是高度肯定制藝詮釋儒經的價值,已開了明末制藝風潮的風氣之先。明末江西派對湯賓尹的某些見解雖有批評,但對於以制藝詮釋儒經則又更往前推了一步,而形成以制藝作為新文體,以古學為內容的主張,而古學的主軸即諸子百家之學。
第五章將談到,由於不少人把諸子書定位為羽翼六經,相當於把諸子書納入到六經的詮釋中,待明末制藝風潮起,由於制藝被定位為經義之學,是詮釋儒經的新文體,於是這些重刊的諸子書,便被入制藝寫作中,如江西派便擅長援引諸子書入制藝寫作中,以諸子書來詮釋儒經。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1. 從文學復古到古籍的校訂刊刻
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詩作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古文辭則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原則上,對詩的重視甚於對古文辭。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須在內容感情上神似,標榜「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要求人們在寫作詩及古文辭,模擬盛唐詩及秦漢文。但復古派並不是簡單為復古而復古而已,而是有寓創新於復古之意。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他們認為從事文學的不二法門,無他,只要精研這些有限的古代典型之作,字模句擬,依樣葫蘆,如能求其近似或一致,便可進入文學的堂奧,上比古人,自成名家」,「這樣的方法就更直截了當,可謂簡易率直之至」。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以摹倣為入手法,人們為了參考先秦兩漢的典籍及漢魏盛唐的詩作,而有更多閱讀古籍的需要,於是帶動蒐獵古籍的風潮。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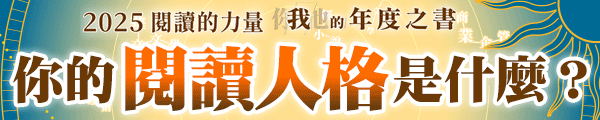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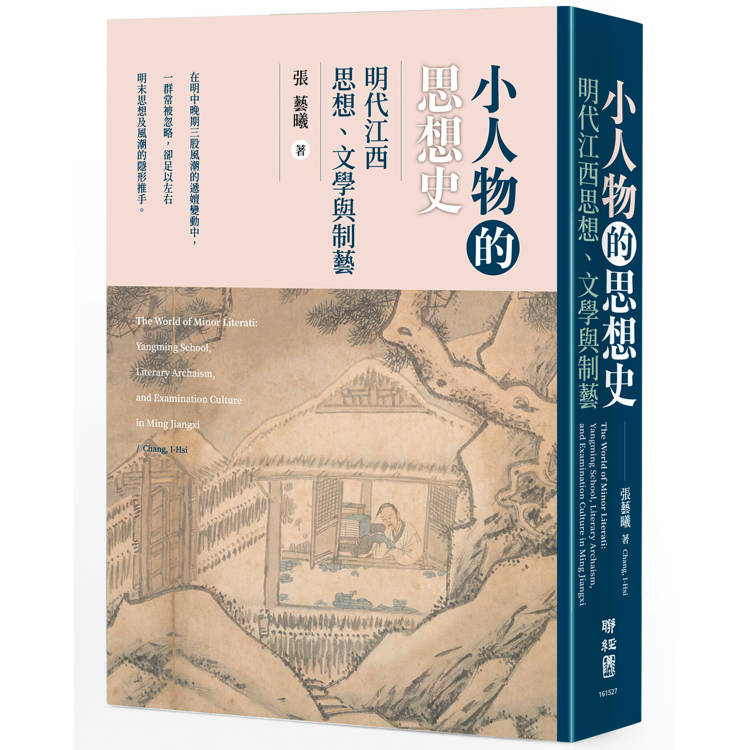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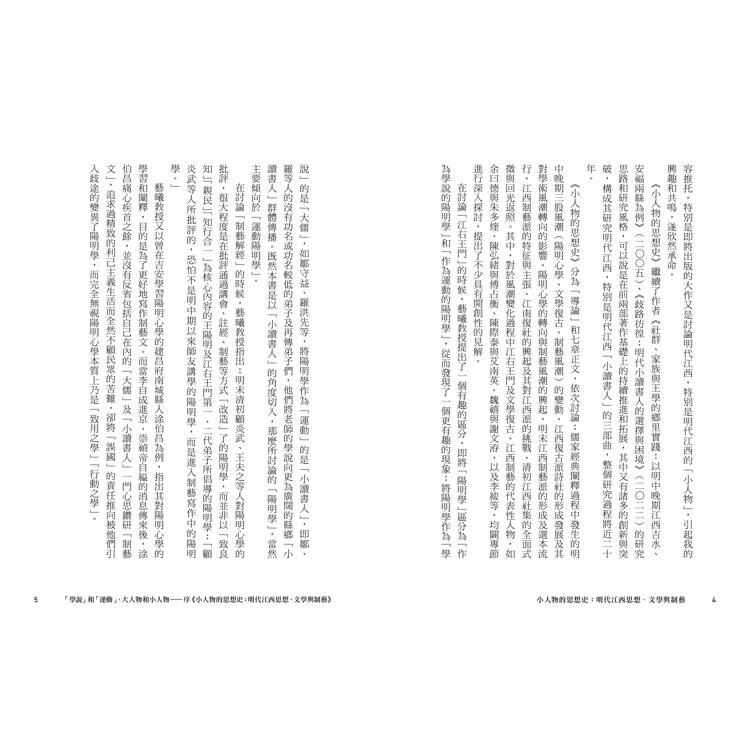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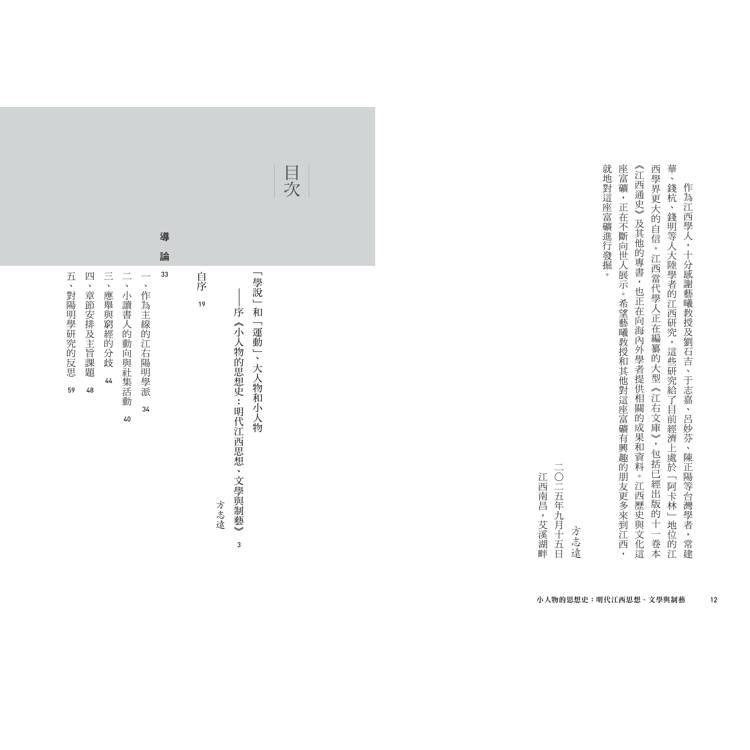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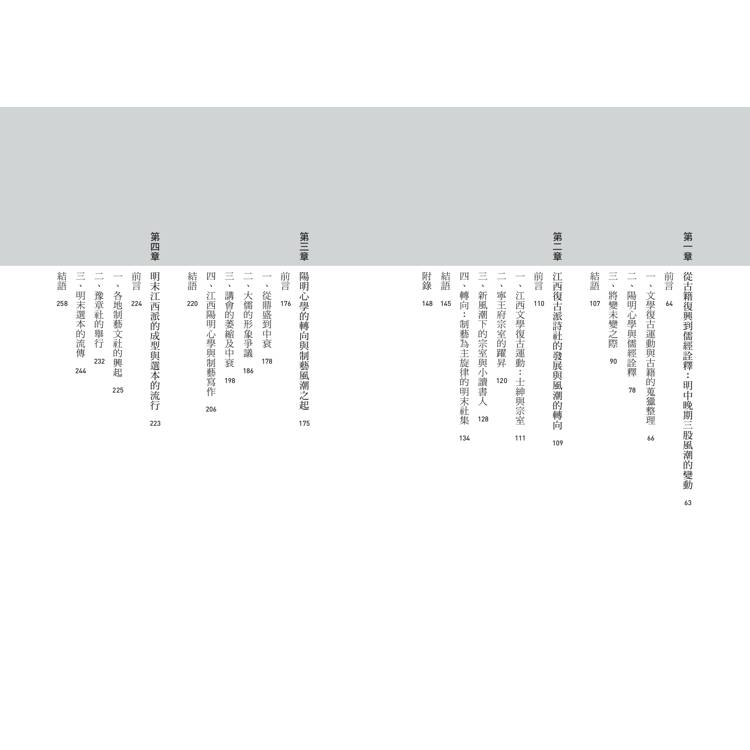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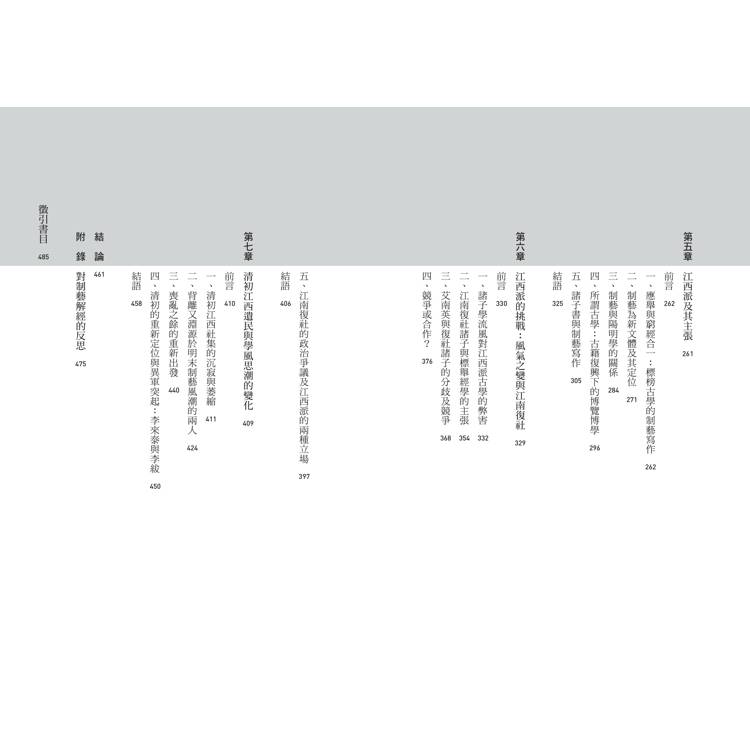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