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永遠在路上:《天下》的故事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一個信念、30年的堅持、∞的夢想
追尋心中的鼓聲走出去,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這本書,獻給所有努力實踐夢想的人們!
辦雜誌,「只是一個媒介,一個推動社會朝向美好未來的平台。」
30年來新聞幕後的故事,分享這群媒體人不畏的單純力量。
創辦於一九八一年六月的《天下雜誌》,目前已發展成「天下雜誌媒體事業群」,所屬事業包括了:《天下雜誌》、《康健雜誌》、《Cheers雜誌》、《親子天下雜誌》、天下雜誌出版(含財經、日本館、人文館、教育、童書、健康生活等書系)、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等等。
透過發行人兼總編集長殷允芃的自述訪談,以及蒐羅天下同事、故舊友人、採訪對象,以及新聞學者等等的觀察見證,本書記錄了《天下雜誌》創辦的緣起,更透過對三十年一路走來的回顧,具體的描繪出天下堅持專業精神、關注社會與公共利益的理念,如何落實在自身事業的經營發展上,進而一步步建立起今天所擁有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天下自創辦之初,就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以記者親臨現場採訪報導的方式,選擇具有正面示範果的題材,以「積極、前瞻、放眼天下」自我期許,從財經新聞議題開始,擴大至對生活的、社會的關懷。而當台灣社會經濟面成熟,個人需求被喚起,一九九八年創辦第二本雜誌《康健》,二○○○年創辦《Cheers》,二○○八年再創辦《親子天下》,以及相關叢書的出版,陸續開展,每一個產品的開創都起自於回應社會的需求。
今天,「天下雜誌媒體事業群」員工從創辦初期的二十三人到現在二百七十人,每天服務超過五十萬名讀者;每年創造十億元營業額。但是,創辦人殷允芃還是篤定的認為,辦雜誌,「只是一個媒介,一個推動社會朝向美好未來的平台。」對於天下的成功關鍵,她在書中開宗明義指出,就是要「愛你所做,做你所愛」;至於如何做到,她認為就是憑藉著「單純的傻勁」以及堅持--三十年不懈的堅持。《希望,永遠在路上——《天下》的故事》,看起來簡單,做起來似乎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追尋心中的鼓聲走出去,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這本書,獻給所有努力實踐夢想的人們!
辦雜誌,「只是一個媒介,一個推動社會朝向美好未來的平台。」
30年來新聞幕後的故事,分享這群媒體人不畏的單純力量。
創辦於一九八一年六月的《天下雜誌》,目前已發展成「天下雜誌媒體事業群」,所屬事業包括了:《天下雜誌》、《康健雜誌》、《Cheers雜誌》、《親子天下雜誌》、天下雜誌出版(含財經、日本館、人文館、教育、童書、健康生活等書系)、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等等。
透過發行人兼總編集長殷允芃的自述訪談,以及蒐羅天下同事、故舊友人、採訪對象,以及新聞學者等等的觀察見證,本書記錄了《天下雜誌》創辦的緣起,更透過對三十年一路走來的回顧,具體的描繪出天下堅持專業精神、關注社會與公共利益的理念,如何落實在自身事業的經營發展上,進而一步步建立起今天所擁有的公信力與影響力。
天下自創辦之初,就走上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以記者親臨現場採訪報導的方式,選擇具有正面示範果的題材,以「積極、前瞻、放眼天下」自我期許,從財經新聞議題開始,擴大至對生活的、社會的關懷。而當台灣社會經濟面成熟,個人需求被喚起,一九九八年創辦第二本雜誌《康健》,二○○○年創辦《Cheers》,二○○八年再創辦《親子天下》,以及相關叢書的出版,陸續開展,每一個產品的開創都起自於回應社會的需求。
今天,「天下雜誌媒體事業群」員工從創辦初期的二十三人到現在二百七十人,每天服務超過五十萬名讀者;每年創造十億元營業額。但是,創辦人殷允芃還是篤定的認為,辦雜誌,「只是一個媒介,一個推動社會朝向美好未來的平台。」對於天下的成功關鍵,她在書中開宗明義指出,就是要「愛你所做,做你所愛」;至於如何做到,她認為就是憑藉著「單純的傻勁」以及堅持--三十年不懈的堅持。《希望,永遠在路上——《天下》的故事》,看起來簡單,做起來似乎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名人推薦
媒體的探照燈,具有鼓舞的力量
天下雜誌
「天下擁有的穿透力,穿透事物本質的視野」--龍應台
「提供我們政治人物一個反省的機會」-馬英九
「是積極的,是出版界最珍貴的資產」-張忠謀
「看到社會需要什麼,就朝這方面來推動」--蕭萬長
「讓人在紛擾中不會喪失對台灣的信心。」--蔡英文
「始終堅持積極樂觀,帶著大家往前走,台灣怎麼可以沒有這本雜誌。」-林懷民
「感性的良知、知性的智識和理性的經營」-吳清友
天下雜誌
「天下擁有的穿透力,穿透事物本質的視野」--龍應台
「提供我們政治人物一個反省的機會」-馬英九
「是積極的,是出版界最珍貴的資產」-張忠謀
「看到社會需要什麼,就朝這方面來推動」--蕭萬長
「讓人在紛擾中不會喪失對台灣的信心。」--蔡英文
「始終堅持積極樂觀,帶著大家往前走,台灣怎麼可以沒有這本雜誌。」-林懷民
「感性的良知、知性的智識和理性的經營」-吳清友
編輯推薦
《天下》殷允芃:大學重考,從此不怕摔跤
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常做人人都說不可行結果卻都成功的事,比如發動天下人遍訪全台灣319個鄉鎮,挖掘美麗的台灣,掀起許多人走完台灣各鄉鎮,蓋完戳記,並且十年來不停止,目前仍在持續報導。
正向思考、不怕挫折、浪漫地追逐理想但又有彈性適時調整、永遠懷抱希望,這樣的個性與收穫,相信是很多人想擁有,或為人父母希望培養兒女們具備的。
這樣的個性是天生,還是可培養的?
她說這個性跟很小就經歷挫折有關。第一個挫折是13歲喪父,瞬間全家失去依靠,母親為扛家計,帶?三個小孩子遷到員林工作,留下老大殷允芃留在台北唸初中,寄宿在阿姨家。除了醫生阿姨與圖書館員的媽媽,給了她很多職業婦女的身教,而且「學會獨立,很多事情要自己解決,還要能與表姊弟們相處,不能任性,要寬容。」
也因媽媽常借書回家,她養成大量?讀小說與電影的習慣,從中了解人性。
「這一生影響我最大的挫折,則是北一女畢業卻沒考上大學,這是很丟臉的。」她說,媽媽沒說她什麼,半年多後她自己想通了,分析失敗原因是沒有認識自己的個性、興趣與長短,明明自己不喜歡做數理練習題,卻只因功課不錯就跟?別人選考甲組,其實自己喜歡有想像力的課業,讀小說、歷史、地理。重考前夕她轉報乙組,上了成大外文系。
很少人在這麼年輕時就想清楚自己的興趣,她卻在那時分析自己,做了一個選擇,「對我而言,這是人生重要轉折點,從挫敗中更加認識自己,從此以後就比較不怕摔跤了。因為曾經摔過一次跤,還可以站起來,不再怕摔、不再怕做不成什麼事。」
難怪她老是跟有養兒育女的天下同事說:「要教小孩跌倒了趕快爬起來。」或常開示:「樂觀跟積極不一樣,樂觀是相信明天會更好,積極是即使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更好,還是要很努力去做。」(文/康健雜誌總編輯李瑟)
目錄
一. 愛你所做,做你所愛
訪談殷允芃:為什麼創辦天下?
二. 探索 台灣競爭力
新聞幕後:尋找台灣優勢
台灣過去靠什麼走過來?
三. 拓展 國際視野
訪談殷允芃:決定啟動,櫻花計畫
新聞幕後:現場直擊歷史一刻
大陸動盪的根源
四. 打開 歷史縱深
訪談殷允芃:一同走過「從前」,一起「發現」台灣
五. 追求 事實真相
新聞幕後:調查報導 推動改革
黑金民主蔓延時
六. 深耕 在地關懷
訪談殷允芃:為什麼我們不能「哈台」
美麗台灣為什麼這麼重要?
未來,我們要往哪裡走?
七. 堅持 媒體獨立
訪談殷允芃:聯盟企業做公益
八. 分流匯流,多元發聲
新聞幕後:關注教改 思考未來
海闊天空的一代
九. 後記:希望,永遠在路上
附錄:天下大事記
訪談殷允芃:為什麼創辦天下?
二. 探索 台灣競爭力
新聞幕後:尋找台灣優勢
台灣過去靠什麼走過來?
三. 拓展 國際視野
訪談殷允芃:決定啟動,櫻花計畫
新聞幕後:現場直擊歷史一刻
大陸動盪的根源
四. 打開 歷史縱深
訪談殷允芃:一同走過「從前」,一起「發現」台灣
五. 追求 事實真相
新聞幕後:調查報導 推動改革
黑金民主蔓延時
六. 深耕 在地關懷
訪談殷允芃:為什麼我們不能「哈台」
美麗台灣為什麼這麼重要?
未來,我們要往哪裡走?
七. 堅持 媒體獨立
訪談殷允芃:聯盟企業做公益
八. 分流匯流,多元發聲
新聞幕後:關注教改 思考未來
海闊天空的一代
九. 後記:希望,永遠在路上
附錄:天下大事記
序/導讀
前言
時空的變遷快速,往往超出意料
在天下三十年的時刻
謹以此書
紀念 那些一同走過的日子
記錄 某些里程碑吉光片羽的歷程
分享 一些新聞幕後的故事
感念 那些在天下崎嶇成長
向上的途中,陪走或長或短
一段路程的讀者與伙伴
邀約 在未來向前的路上
仍共同堅持理想與溫暖的必要
後記
希望,永遠在路上
訪談 殷允芃
對我而言,與其當經營者,我更喜歡做記者。
做記者給我一個免費的護照,讓我探索世界,you are paid to learn,是別人付錢讓你有不斷學習的機會,實際上是很有趣的工作。而且一個好的訪問,幾乎是人生的一場對談,我們去訪問人,然後分享他的人生智慧,對於自己往後的人生受用無窮。
我年輕時採訪過張愛玲,她說,「人生是樂不抵苦的,但生下來就要好好的活下去」,這句話常常在我有困擾的時候,給我很大的鼓舞。張愛玲一再強調,「深入淺出是重要的」,她說最好的文章是讓大家有興趣地看下去時,自然而然地停下來思索,這對我創辦《天下》之初有很大的啟發。
《天下》的英文名字CommonWealth,是均富的思想,是一種修正的資本主義。目前台灣社會氣氛強調個人利益,金錢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天下》堅持的一些價值,不是目前台灣一般媒體、社會表面上看到的價值,比如專業的精神、理想、關懷、勇氣與公共利益。可是我覺得,在每個人內心深處,《天下》堅持的價值,還是大家期待的價值,因為,這都是亙古不變的價值。
人們認為記者就是替代閱聽大眾來探索事實真相的,這話講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很困難。因為很多事實加起來不見得是真相,但記者是為了公眾來做這件事情,所以記者就像探照燈一樣,帶著閱聽人去看一些他沒有機會看到的角落。
舞台上是黑暗的,記者就是那盞燈,探照燈打到哪裡,大家就往哪邊看。你可以把角落有人打架的情況照出來,但探照燈也可以把有人默默努力工作的情況照出來。
所以,媒體如果是探照燈,我們就必須慎選要照到哪裡。
戒嚴期間,很多人辦媒體都選擇站在政府的對立面,監督政府。但是當解嚴後,國家政府的控制力越來越小時,隨之而來的反而是市場化、新聞商品化的問題。當媒體也成了市場的一環,在市場裡運作,面臨的挑戰就更大。
媒體必須完全跟隨市場運作嗎?這必須先釐清,媒體只是商品嗎?新聞只是商品嗎?
社會責任的必要
其實,媒體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媒體應該要有社會責任,否則憑什麼說媒體有代表人民知的權利,誰給你這個權力呢?媒體對公眾有很大的責任,對社會必須有貢獻,有好的影響力,而不只是賺錢不賺錢的思考。媒體應該是文化事業,而不只是商品、商業。
台灣的新聞商品化越來越激烈,我覺得很遺憾。二○一○年獲頒卓越新聞終身成就獎時,我忍不住當著新聞局長的面前致詞說:台灣有一個怪現象,就是政府帶頭做置入性行銷,這是從扁政府時代就開始,但很不幸的,在馬政府時代也延續了:
「政府在媒體做置入性行銷,說直接點,就是拿人民的納稅錢,來欺騙人民。這樣的民主不值得我們驕傲。」
還好,這件事已有改善。在中時記者黃哲斌辭職起義,《天下》給予報導,他也在網路上寫部落格揭露,得到數百位傳播學者聯名支持後,政府終於通過法律禁止政府單位再做置入性行銷。對此,我還是懷抱著期待。因為媒體的影響力非常大,媒體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以及下一代的視野,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媒體拼湊了閱聽大眾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雖然我們現在身處黑暗的媒體環境,我還是希望可以早一點走出黑暗,讓我們堅持久一點、互相鼓勵,找回當初加入新聞行業的熱情、理想與好奇心。
很多社會與政治問題,我們沒有一定的答案,但是我們努力給一點解決的方向,讓社會朝向美好公平的方向,盡量讓讀者開卷有益。即使社會中有許多黑暗面、負面新聞,我們還是願意報導黑暗中有一群人努力做事,社會裡還有希望存在。
要說這是理想性嗎?其實全世界在六○、七○年代學習成長的人,都有這種理想吧,因為當時我們身處的時代是艱苦的環境。那時社會比較窮,沒那麼多自由,但我們經歷過只要努力,就可以把社會推動到一個更好的方向。
世界不會總是如你想像的美好,不管怎麼樣的逆境,你都可以站起來,在逆境中找到一些樂趣。我不是樂觀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而是強調積極的態度,即使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更好,還是要很努力去做。美好社會的願景,不是一個人的相信,或一家雜誌社的相信,而是這塊土地上有很大一群人的共同相信,這也是支撐《天下》走下去的動力。
我一向欣賞勇敢作夢的人。肯作夢,不管夢多大或多小,然後一直去追求夢想,聽到心中的不同鼓聲,就跟著鼓聲走出去。
經營《天下》也是如此,當初並不是做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但就是有一個聲音叫你應該去試一試。過了一關,就會大膽一點,再過一關,就會更大膽一點,其實就是這樣一路走來。
我一直認為,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未來,我們會繼續積極面對。
時空的變遷快速,往往超出意料
在天下三十年的時刻
謹以此書
紀念 那些一同走過的日子
記錄 某些里程碑吉光片羽的歷程
分享 一些新聞幕後的故事
感念 那些在天下崎嶇成長
向上的途中,陪走或長或短
一段路程的讀者與伙伴
邀約 在未來向前的路上
仍共同堅持理想與溫暖的必要
後記
希望,永遠在路上
訪談 殷允芃
對我而言,與其當經營者,我更喜歡做記者。
做記者給我一個免費的護照,讓我探索世界,you are paid to learn,是別人付錢讓你有不斷學習的機會,實際上是很有趣的工作。而且一個好的訪問,幾乎是人生的一場對談,我們去訪問人,然後分享他的人生智慧,對於自己往後的人生受用無窮。
我年輕時採訪過張愛玲,她說,「人生是樂不抵苦的,但生下來就要好好的活下去」,這句話常常在我有困擾的時候,給我很大的鼓舞。張愛玲一再強調,「深入淺出是重要的」,她說最好的文章是讓大家有興趣地看下去時,自然而然地停下來思索,這對我創辦《天下》之初有很大的啟發。
《天下》的英文名字CommonWealth,是均富的思想,是一種修正的資本主義。目前台灣社會氣氛強調個人利益,金錢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天下》堅持的一些價值,不是目前台灣一般媒體、社會表面上看到的價值,比如專業的精神、理想、關懷、勇氣與公共利益。可是我覺得,在每個人內心深處,《天下》堅持的價值,還是大家期待的價值,因為,這都是亙古不變的價值。
人們認為記者就是替代閱聽大眾來探索事實真相的,這話講起來很簡單,但做起來很困難。因為很多事實加起來不見得是真相,但記者是為了公眾來做這件事情,所以記者就像探照燈一樣,帶著閱聽人去看一些他沒有機會看到的角落。
舞台上是黑暗的,記者就是那盞燈,探照燈打到哪裡,大家就往哪邊看。你可以把角落有人打架的情況照出來,但探照燈也可以把有人默默努力工作的情況照出來。
所以,媒體如果是探照燈,我們就必須慎選要照到哪裡。
戒嚴期間,很多人辦媒體都選擇站在政府的對立面,監督政府。但是當解嚴後,國家政府的控制力越來越小時,隨之而來的反而是市場化、新聞商品化的問題。當媒體也成了市場的一環,在市場裡運作,面臨的挑戰就更大。
媒體必須完全跟隨市場運作嗎?這必須先釐清,媒體只是商品嗎?新聞只是商品嗎?
社會責任的必要
其實,媒體是有不一樣的地方。媒體應該要有社會責任,否則憑什麼說媒體有代表人民知的權利,誰給你這個權力呢?媒體對公眾有很大的責任,對社會必須有貢獻,有好的影響力,而不只是賺錢不賺錢的思考。媒體應該是文化事業,而不只是商品、商業。
台灣的新聞商品化越來越激烈,我覺得很遺憾。二○一○年獲頒卓越新聞終身成就獎時,我忍不住當著新聞局長的面前致詞說:台灣有一個怪現象,就是政府帶頭做置入性行銷,這是從扁政府時代就開始,但很不幸的,在馬政府時代也延續了:
「政府在媒體做置入性行銷,說直接點,就是拿人民的納稅錢,來欺騙人民。這樣的民主不值得我們驕傲。」
還好,這件事已有改善。在中時記者黃哲斌辭職起義,《天下》給予報導,他也在網路上寫部落格揭露,得到數百位傳播學者聯名支持後,政府終於通過法律禁止政府單位再做置入性行銷。對此,我還是懷抱著期待。因為媒體的影響力非常大,媒體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以及下一代的視野,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媒體拼湊了閱聽大眾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雖然我們現在身處黑暗的媒體環境,我還是希望可以早一點走出黑暗,讓我們堅持久一點、互相鼓勵,找回當初加入新聞行業的熱情、理想與好奇心。
很多社會與政治問題,我們沒有一定的答案,但是我們努力給一點解決的方向,讓社會朝向美好公平的方向,盡量讓讀者開卷有益。即使社會中有許多黑暗面、負面新聞,我們還是願意報導黑暗中有一群人努力做事,社會裡還有希望存在。
要說這是理想性嗎?其實全世界在六○、七○年代學習成長的人,都有這種理想吧,因為當時我們身處的時代是艱苦的環境。那時社會比較窮,沒那麼多自由,但我們經歷過只要努力,就可以把社會推動到一個更好的方向。
世界不會總是如你想像的美好,不管怎麼樣的逆境,你都可以站起來,在逆境中找到一些樂趣。我不是樂觀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而是強調積極的態度,即使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更好,還是要很努力去做。美好社會的願景,不是一個人的相信,或一家雜誌社的相信,而是這塊土地上有很大一群人的共同相信,這也是支撐《天下》走下去的動力。
我一向欣賞勇敢作夢的人。肯作夢,不管夢多大或多小,然後一直去追求夢想,聽到心中的不同鼓聲,就跟著鼓聲走出去。
經營《天下》也是如此,當初並不是做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但就是有一個聲音叫你應該去試一試。過了一關,就會大膽一點,再過一關,就會更大膽一點,其實就是這樣一路走來。
我一直認為,只要在路上,就有希望。
未來,我們會繼續積極面對。
試閱
【訪談 殷允芃】
為什麼創辦天下? 林秀姿 採訪
,而我關心的地方與人在台灣,不是在美國,所以才決定回台灣。
一九七○年我回到台灣,先後在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工作撰稿,盡量將台灣的訊息傳到國際上。
但是,真正促使我創辦《天下雜誌》的關鍵則是中美斷交。
為台灣在國際發聲
中美斷交前,我是台灣少數先知道的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半夜,我接到紐約時報的電話,說白宮再過幾個小時,會召開記者會,應該是卡特總統要宣布承認中共,然後跟台灣斷交。第二天,我從台北發的斷交新聞,短暫的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
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國代表克里斯多夫(Warren Christopher),率團來台灣談判,我跟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一同坐在美方的車中,同車的還有美方的經濟代表。在前往圓山飯店途中,車外很多人手持木棒,也有人拿國旗,大家都在抗議,向美方車隊丟蕃茄、雞蛋,敲打車窗,車子幾乎開不動。
我看著窗外群情激憤的同胞,心中不斷地問自己︰「做個記者,到底我的立場在哪裡?」
中美斷交期間,我為美國媒體工作,但是我沒辦法不動感情,只冷靜的用美方觀點處理新聞。我的位置與經歷強迫我把自己的立場想清楚。我也開始反思台灣的立場與位置,「當國家衰弱,人民憤怒抗議也沒用。台灣要讓世界看得起,就必須自己站起來。」
當時對國際事務最深刻的體會,是自己要強、要有能力否則沒有人會幫助你。台灣可以做一個民主的典範,可是如果你沒有經濟實力,沒有人要理你。
我曾經擔任過五年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的記者,跟財經新聞有所接觸,國外有許多財經媒體,可以把財經寫的讓一般人民看得津津有味,為何台灣沒有一般人都看得懂的經濟刊物?
經濟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命脈,與人息息相關。但當時一般人卻不十分了解,也不重視,經濟成了枯燥、艱澀難懂或俗不可耐的代名詞。
定位與驅動力
當初創辦《天下雜誌》,定位為財經的、生活的、社會的,而不是窄義的財經雜誌,因為要了解經濟背後還有許多其他的驅動力。
經濟其實就是人的生活。
我們的目標是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客觀、翔實地探討、報導和分析人人都應該了解的經濟問題,我們要求經濟學家要講「人」話,我們希望能忠實的反應工商界的意見,期盼能為政府與民間企業、海外與國內搭一座溝通橋樑。
我一開始當記者,就常疑問:「為什麼壞的消息才是新聞?」災難、社會事件、兇殺案,越扭曲、越殘忍、越不幸的新聞都被媒體當成頭條新聞。有人跟我說:「這是人性」,人性都喜歡知道一些負面痛苦的消息,人都有偷窺的本性等。但是我不懂,為什麼新聞都是集結全世界各地的壞消息,讓那些災難、痛苦放在自己的客廳裡、餐桌上呢?面對擺滿哀傷的餐桌,也沒告訴我們能不能共同解決、幫忙那些受苦的人。
我希望創辦的媒體,是盡量把人心中的惡縮小一點,把善擴大一點,積極一點。
世界每天發生很多事,台灣每天也發生很多事,媒體的探照燈如果看到問題,出發點應該出於善意,把問題照出來,讓大家一起來解決。
媒體探照燈也可以投射到美好的人事上,他們可能不是高官,只是一些小人物,就像前些時陳樹菊的故事,她的收入只有一點點,但是她仍堅持每天存下一點點錢,也要去幫助別人。這塊土地上有各式各樣的人,媒體探照燈可以把燈光投射在這些人身上,照亮他們默默耕耘的身影。
就企業來看,我們也可以把企業如何成功、有效率、具競爭力、負社會責任的一面呈現出來,不只可以讓其他企業學習,也能達到鼓舞的目的,這就是積極的意思。
走高品質的策略
我和高希均教授,以及王力行女士,加上十幾位其他的朋友,決定一起合辦一本財經雜誌。原本高希均教授建議,雜誌可以盡量邀請專家寫稿,可是我希望,要辦一本以記者採訪為主的雜誌,才會不一樣。
我心目中的《天下雜誌》,是擁有《經濟學人》(Economist)的內涵、《時代》(Time)雜誌的寫法,以及《財富》(Fortune)雜誌的Layout版面跟照片編排形式。
不過,決定創辦雜誌後,很多朋友都不看好,因為在那個時代辦雜誌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認為我選了一條難走的路。詩人朋友余光中還寫了一篇小文章半開玩笑說:「Why would such a smart girl want to do such a stupid thing?」說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連朋友贊助我們資金,也多當作義助,當成丟了就是丟了的心情。眾多朋友裡,當時只有浪漫的蔣勳贊成我辦雜誌。王永慶先生在《天下雜誌》創辦的時候也很幫忙,第一期創刊號台塑就買了一千本,那是很大的肯定。
一開始《天下雜誌》鎖定的讀者群是年齡約三十五歲左右,中產階級,他是具有理想性,有國際視野或是期望自己具有國際視野的人,他可能是企業家、政府領導人,但也可能是一個普通人、一個高中生。但他是有企圖做決策的,即使是對自己的生命做決策,也是在做決策。
我們試想,這樣的讀者不就是寫下「天下為公」、年輕時候的孫中山嗎?
動之以理想
《天下雜誌》創辦初期的記者幾乎都是我在政大教書的學生,因為那時大部分人都對雜誌沒信心。徐梅屏當時已是中央日報的資深記者、溫曼英則曾任「仕女」雜誌總編輯,周玉蔻、楊艾俐、蕭昭君、以及稍後加入的吳迎春、李瑟、莊素玉、金玉梅、孫曼蘋等人,也都曾在政大修過我的課。
從美國回國以來,我一直在政大新聞系兼課,教新聞攝影與新聞英文寫作研究。寫作課教的是四年級生,每學期的第一堂課,我都會問學生說︰「你們有多少人在畢業後要從事新聞工作?」結果,舉手的通常都非常少。原因是,這些學生認為新聞界很黑暗,尤其到媒體實習過後,感覺更不喜歡。
「如果新聞界真的這麼爛、這麼黑暗,你們這麼優秀的學生都不願意加入,那這個爛跟黑暗可以改變嗎?」我每次都會這麼問他們,讓他們想一想。就像當年在美國留學工作,面臨要不要回台灣時,我問自己的問題。
唯一能打動她們的,就是跟她們說︰「我們要辦一本理想中比較好的雜誌,要不要一起來?」
只能用「理想」打動他們。我想,這批人願意來,一方面是他們都擁有理想性格,另一方面,可能是對老師比較信任吧。其實我就是想把書上教的那一套,拿來真實的新聞界實踐。
創刊號規劃封面故事(cover story)時,想讓大家看看台灣經濟是怎麼發展的,而且以人物的方式來說故事。
創刊號封面故事,「細數財經首長的背景,台灣起飛的關鍵人物」,是由周玉蔻來寫,因為希望創刊號要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讓人驚喜,把枯燥的經濟議題,就像生動的故事一樣寫出來。如副總統陳誠、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行政院長孫運璿、政務委員李國鼎等的決策過程,串起台灣如何用米糖鹽換取外匯,滿足人民最基本需求,累積少許資本,發展工業,建立加工出口區,吸收過剩勞力的經濟發展過程,直到八○年代初,我國才有開始發展高科技的本錢。
符合潮流的需求
一九八一年六月份的創刊號再版了好幾次,所以我們第一年就已經賺錢。
有人問我這是不是運氣?我想運氣是有一點。但我猜某種程度跟個性有關,就是比較單純。
那個單純是不計較賺錢得失,只懂想做就去做,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牽絆,所以變成別人覺得困難的事情,我們反而很容易做成,可以說是單純傻勁,也算是一種相信,一種belief。
我承認《天下雜誌》是菁英的。
既然是菁英,就應該維持理想。
《天下雜誌》強調社會關懷與國際化的視野,不會去教人如何快速成功,或是買甚麼股票、如何賺到一千萬;我們喜歡從積極面去看事情,試著提出解決的方向,從而對政府的政策產生影響。
作家龍應台曾經說:「有能力的人,請你把你的光照得更遠一點。」我也覺得是這樣,如果你有能力,就多做事,多幫助別人,對推動美好的社會盡一份力量。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希望,永遠在路上》第一章內容)
為什麼創辦天下? 林秀姿 採訪
一九七○年我回到台灣,先後在合眾國際社、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工作撰稿,盡量將台灣的訊息傳到國際上。
但是,真正促使我創辦《天下雜誌》的關鍵則是中美斷交。
為台灣在國際發聲
中美斷交前,我是台灣少數先知道的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半夜,我接到紐約時報的電話,說白宮再過幾個小時,會召開記者會,應該是卡特總統要宣布承認中共,然後跟台灣斷交。第二天,我從台北發的斷交新聞,短暫的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
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國代表克里斯多夫(Warren Christopher),率團來台灣談判,我跟紐約時報資深記者一同坐在美方的車中,同車的還有美方的經濟代表。在前往圓山飯店途中,車外很多人手持木棒,也有人拿國旗,大家都在抗議,向美方車隊丟蕃茄、雞蛋,敲打車窗,車子幾乎開不動。
我看著窗外群情激憤的同胞,心中不斷地問自己︰「做個記者,到底我的立場在哪裡?」
中美斷交期間,我為美國媒體工作,但是我沒辦法不動感情,只冷靜的用美方觀點處理新聞。我的位置與經歷強迫我把自己的立場想清楚。我也開始反思台灣的立場與位置,「當國家衰弱,人民憤怒抗議也沒用。台灣要讓世界看得起,就必須自己站起來。」
當時對國際事務最深刻的體會,是自己要強、要有能力否則沒有人會幫助你。台灣可以做一個民主的典範,可是如果你沒有經濟實力,沒有人要理你。
我曾經擔任過五年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的記者,跟財經新聞有所接觸,國外有許多財經媒體,可以把財經寫的讓一般人民看得津津有味,為何台灣沒有一般人都看得懂的經濟刊物?
經濟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命脈,與人息息相關。但當時一般人卻不十分了解,也不重視,經濟成了枯燥、艱澀難懂或俗不可耐的代名詞。
定位與驅動力
當初創辦《天下雜誌》,定位為財經的、生活的、社會的,而不是窄義的財經雜誌,因為要了解經濟背後還有許多其他的驅動力。
經濟其實就是人的生活。
我們的目標是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客觀、翔實地探討、報導和分析人人都應該了解的經濟問題,我們要求經濟學家要講「人」話,我們希望能忠實的反應工商界的意見,期盼能為政府與民間企業、海外與國內搭一座溝通橋樑。
我一開始當記者,就常疑問:「為什麼壞的消息才是新聞?」災難、社會事件、兇殺案,越扭曲、越殘忍、越不幸的新聞都被媒體當成頭條新聞。有人跟我說:「這是人性」,人性都喜歡知道一些負面痛苦的消息,人都有偷窺的本性等。但是我不懂,為什麼新聞都是集結全世界各地的壞消息,讓那些災難、痛苦放在自己的客廳裡、餐桌上呢?面對擺滿哀傷的餐桌,也沒告訴我們能不能共同解決、幫忙那些受苦的人。
我希望創辦的媒體,是盡量把人心中的惡縮小一點,把善擴大一點,積極一點。
世界每天發生很多事,台灣每天也發生很多事,媒體的探照燈如果看到問題,出發點應該出於善意,把問題照出來,讓大家一起來解決。
媒體探照燈也可以投射到美好的人事上,他們可能不是高官,只是一些小人物,就像前些時陳樹菊的故事,她的收入只有一點點,但是她仍堅持每天存下一點點錢,也要去幫助別人。這塊土地上有各式各樣的人,媒體探照燈可以把燈光投射在這些人身上,照亮他們默默耕耘的身影。
就企業來看,我們也可以把企業如何成功、有效率、具競爭力、負社會責任的一面呈現出來,不只可以讓其他企業學習,也能達到鼓舞的目的,這就是積極的意思。
走高品質的策略
我和高希均教授,以及王力行女士,加上十幾位其他的朋友,決定一起合辦一本財經雜誌。原本高希均教授建議,雜誌可以盡量邀請專家寫稿,可是我希望,要辦一本以記者採訪為主的雜誌,才會不一樣。
我心目中的《天下雜誌》,是擁有《經濟學人》(Economist)的內涵、《時代》(Time)雜誌的寫法,以及《財富》(Fortune)雜誌的Layout版面跟照片編排形式。
不過,決定創辦雜誌後,很多朋友都不看好,因為在那個時代辦雜誌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認為我選了一條難走的路。詩人朋友余光中還寫了一篇小文章半開玩笑說:「Why would such a smart girl want to do such a stupid thing?」說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連朋友贊助我們資金,也多當作義助,當成丟了就是丟了的心情。眾多朋友裡,當時只有浪漫的蔣勳贊成我辦雜誌。王永慶先生在《天下雜誌》創辦的時候也很幫忙,第一期創刊號台塑就買了一千本,那是很大的肯定。
一開始《天下雜誌》鎖定的讀者群是年齡約三十五歲左右,中產階級,他是具有理想性,有國際視野或是期望自己具有國際視野的人,他可能是企業家、政府領導人,但也可能是一個普通人、一個高中生。但他是有企圖做決策的,即使是對自己的生命做決策,也是在做決策。
我們試想,這樣的讀者不就是寫下「天下為公」、年輕時候的孫中山嗎?
動之以理想
《天下雜誌》創辦初期的記者幾乎都是我在政大教書的學生,因為那時大部分人都對雜誌沒信心。徐梅屏當時已是中央日報的資深記者、溫曼英則曾任「仕女」雜誌總編輯,周玉蔻、楊艾俐、蕭昭君、以及稍後加入的吳迎春、李瑟、莊素玉、金玉梅、孫曼蘋等人,也都曾在政大修過我的課。
從美國回國以來,我一直在政大新聞系兼課,教新聞攝影與新聞英文寫作研究。寫作課教的是四年級生,每學期的第一堂課,我都會問學生說︰「你們有多少人在畢業後要從事新聞工作?」結果,舉手的通常都非常少。原因是,這些學生認為新聞界很黑暗,尤其到媒體實習過後,感覺更不喜歡。
「如果新聞界真的這麼爛、這麼黑暗,你們這麼優秀的學生都不願意加入,那這個爛跟黑暗可以改變嗎?」我每次都會這麼問他們,讓他們想一想。就像當年在美國留學工作,面臨要不要回台灣時,我問自己的問題。
唯一能打動她們的,就是跟她們說︰「我們要辦一本理想中比較好的雜誌,要不要一起來?」
只能用「理想」打動他們。我想,這批人願意來,一方面是他們都擁有理想性格,另一方面,可能是對老師比較信任吧。其實我就是想把書上教的那一套,拿來真實的新聞界實踐。
創刊號規劃封面故事(cover story)時,想讓大家看看台灣經濟是怎麼發展的,而且以人物的方式來說故事。
創刊號封面故事,「細數財經首長的背景,台灣起飛的關鍵人物」,是由周玉蔻來寫,因為希望創刊號要超出一般人的想像、讓人驚喜,把枯燥的經濟議題,就像生動的故事一樣寫出來。如副總統陳誠、美援會副主委尹仲容、行政院長孫運璿、政務委員李國鼎等的決策過程,串起台灣如何用米糖鹽換取外匯,滿足人民最基本需求,累積少許資本,發展工業,建立加工出口區,吸收過剩勞力的經濟發展過程,直到八○年代初,我國才有開始發展高科技的本錢。
符合潮流的需求
一九八一年六月份的創刊號再版了好幾次,所以我們第一年就已經賺錢。
有人問我這是不是運氣?我想運氣是有一點。但我猜某種程度跟個性有關,就是比較單純。
那個單純是不計較賺錢得失,只懂想做就去做,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牽絆,所以變成別人覺得困難的事情,我們反而很容易做成,可以說是單純傻勁,也算是一種相信,一種belief。
我承認《天下雜誌》是菁英的。
既然是菁英,就應該維持理想。
《天下雜誌》強調社會關懷與國際化的視野,不會去教人如何快速成功,或是買甚麼股票、如何賺到一千萬;我們喜歡從積極面去看事情,試著提出解決的方向,從而對政府的政策產生影響。
作家龍應台曾經說:「有能力的人,請你把你的光照得更遠一點。」我也覺得是這樣,如果你有能力,就多做事,多幫助別人,對推動美好的社會盡一份力量。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希望,永遠在路上》第一章內容)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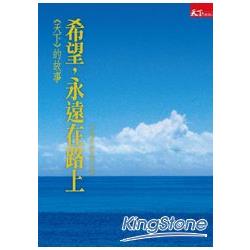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