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新二代:多元文化與地緣政治下的跨國婚姻子女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對於臺灣「新二代」及其身分認同的田野調查報告
★《跨國灰姑娘》、《拚教養》作者,臺大社會系特聘教授藍佩嘉最新著作
在臺灣,跨國婚姻子女的人數推估超過五十萬。這些孩子曾被稱為「新臺灣之子」,自新南向政策推動後,官方改稱他們「新二代」,正面標示其移民背景。然而,「新二代」如何看待這個標籤?不同族群、階級、移動經歷的二代,又如何定義自己、回答「我是誰」的提問?本書要探問的是,在地緣政治情勢與多元文化政策的張力下,這些「新二代」年輕人如何在複雜的族群身分政治中協商自我的認同。
本書深入訪談六十一位母親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的成年二代子女,以及其中十五位的新移民母親。希望透過他們的生命故事,理解國家政策的轉變與地緣政治的脈絡,如何影響新移民子女的生命經驗與族群認同。母親來自不同國家的二代,尤其是「臺灣東南亞二代」與「臺灣中國二代」的經驗有怎樣的差異?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認同策略,來抵禦或迴避族裔╱地緣政治因素衍生的外來者汙名?而在現今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中,這些新二代的多元文化背景,是否能順利轉化為身分紅利(比如特殊選才或入學機會)?還是造成非預期的負面後果?海外歸國子女,以及海航(逆向遷移回父母原生國度)的二代,在跨國流動的過程中,又經歷怎樣的認同變化?
本書也根據田野分析提出相關的行動建議,包括改變既定認知框架,視新移民子女為積極的行動者而非弱勢;更廣泛地界定「新二代」,看見其中的差異與不平等;以及更細緻的區辨--例如將新二代與母親國度的連結定義在文化與地方層次,而非過度上綱,避免將他們排除在共同體之外。
這些「新二代」的生命經驗與認同演變,也讓我們重新思索臺灣人的定義。隨著臺灣人口逐步納入更多元的移民來源、臺灣人的界線也不斷地被改寫與延伸。一如祖輩於不同歷史時期、在族群與文化交會處「成為」臺灣人的我們,其父母沿著移民之路進入臺灣的「新二代」,也將繼續擴展臺灣人的認同與文化邊界。
★《跨國灰姑娘》、《拚教養》作者,臺大社會系特聘教授藍佩嘉最新著作
在臺灣,跨國婚姻子女的人數推估超過五十萬。這些孩子曾被稱為「新臺灣之子」,自新南向政策推動後,官方改稱他們「新二代」,正面標示其移民背景。然而,「新二代」如何看待這個標籤?不同族群、階級、移動經歷的二代,又如何定義自己、回答「我是誰」的提問?本書要探問的是,在地緣政治情勢與多元文化政策的張力下,這些「新二代」年輕人如何在複雜的族群身分政治中協商自我的認同。
本書深入訪談六十一位母親來自東南亞或中國大陸的成年二代子女,以及其中十五位的新移民母親。希望透過他們的生命故事,理解國家政策的轉變與地緣政治的脈絡,如何影響新移民子女的生命經驗與族群認同。母親來自不同國家的二代,尤其是「臺灣東南亞二代」與「臺灣中國二代」的經驗有怎樣的差異?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認同策略,來抵禦或迴避族裔╱地緣政治因素衍生的外來者汙名?而在現今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中,這些新二代的多元文化背景,是否能順利轉化為身分紅利(比如特殊選才或入學機會)?還是造成非預期的負面後果?海外歸國子女,以及海航(逆向遷移回父母原生國度)的二代,在跨國流動的過程中,又經歷怎樣的認同變化?
本書也根據田野分析提出相關的行動建議,包括改變既定認知框架,視新移民子女為積極的行動者而非弱勢;更廣泛地界定「新二代」,看見其中的差異與不平等;以及更細緻的區辨--例如將新二代與母親國度的連結定義在文化與地方層次,而非過度上綱,避免將他們排除在共同體之外。
這些「新二代」的生命經驗與認同演變,也讓我們重新思索臺灣人的定義。隨著臺灣人口逐步納入更多元的移民來源、臺灣人的界線也不斷地被改寫與延伸。一如祖輩於不同歷史時期、在族群與文化交會處「成為」臺灣人的我們,其父母沿著移民之路進入臺灣的「新二代」,也將繼續擴展臺灣人的認同與文化邊界。
目錄
謝辭
卷首說明
導論 誰是「新二代」?
第一章 國家移民治理的劃界
鞏固界線:人口素質與國家安全
個人跨界:母職作為同化過渡儀式
搭橋穿界:「多元文化」火炬還是煙花?
界線擴展:新南向政策
第二章 跨國婚姻與族裔文化傳遞
跨國婚姻的矛盾與挑戰
打造自己的鳳梨田
我在等你長大
搭著越南舊字典起飛
單親媽媽的越南小聚落
一起走向全球化
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是「混血兒」?
制度善意或強迫「出櫃」?
外勞的部落汙名
中國背景的地緣政治汙名
第四章 閃閃發光的臺灣東南亞二代?
認同多數:無感與防禦
擁抱差異:雙文化認同與多元文化紅利
抗拒:對新南向政策的批評
矛盾:自我種族化、冒牌者效應
第五章 海歸與海航的認同旅程
高社經地位海歸二代
家庭團聚的海歸子女
東南亞尋根的海航二代
第六章 地緣政治陰影下的臺灣中國二代
認同多數:淡化中國背景與強調臺灣忠誠
蒙混過關與矯正差異
重新調整認同尺度
建立在地認同與跨族群連結
結論 誰是「臺灣人」?
附錄 二代受訪者統計表
注釋
參考書目
卷首說明
導論 誰是「新二代」?
第一章 國家移民治理的劃界
鞏固界線:人口素質與國家安全
個人跨界:母職作為同化過渡儀式
搭橋穿界:「多元文化」火炬還是煙花?
界線擴展:新南向政策
第二章 跨國婚姻與族裔文化傳遞
跨國婚姻的矛盾與挑戰
打造自己的鳳梨田
我在等你長大
搭著越南舊字典起飛
單親媽媽的越南小聚落
一起走向全球化
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是「混血兒」?
制度善意或強迫「出櫃」?
外勞的部落汙名
中國背景的地緣政治汙名
第四章 閃閃發光的臺灣東南亞二代?
認同多數:無感與防禦
擁抱差異:雙文化認同與多元文化紅利
抗拒:對新南向政策的批評
矛盾:自我種族化、冒牌者效應
第五章 海歸與海航的認同旅程
高社經地位海歸二代
家庭團聚的海歸子女
東南亞尋根的海航二代
第六章 地緣政治陰影下的臺灣中國二代
認同多數:淡化中國背景與強調臺灣忠誠
蒙混過關與矯正差異
重新調整認同尺度
建立在地認同與跨族群連結
結論 誰是「臺灣人」?
附錄 二代受訪者統計表
注釋
參考書目
試閱
第三章 校園生活的劃界與汙名
「誰的媽媽是外國人?」老師對著全班同學大聲問,並要舉手的同學到教務處集合,下課後參加課後輔導。「天啊又來了~」,媽媽來自越南的小曉皺起了眉頭,每個學年老師都要問一次這個讓她非常「彆扭」、「尷尬」的問題。她在心裡碎唸:「媽媽已經拿到身分證了、臺語現在講得那麼溜,難道媽媽永遠都是『外國人』嗎?」即便小曉的長相看不出明顯的族群差異,她還是默默地舉了手,頭微低著,擔心下課後同學可能的訕笑。她也用眼角餘光瞄見其他舉手的同學,有點驚訝、也鬆了一口氣:「啊,原來他們的媽媽跟我的一樣啊」。坐在角落的小光心情同樣忐忑,他的媽媽來自中國,他不想舉手,又怕被老師發現。他總是叫媽媽不要來學校,就怕她講中文的口音被同學發現。老師之前也做過其他公開調查,像是「誰家是低收入戶?誰可以吃免費的營養午餐?」小光心裡忿忿不平:「我家裡也沒有比較窮,我成績也沒有比較差,為什麼我要跟同學不一樣?」
我根據訪談資料重建了上述場景,本書中的許多受訪者回憶起十多年前的「被出櫃」的情境,仍然感到傷痛。臺灣中小學校園強調集體主義與制式化的管理,新移民子女的「不同」與「特殊」經常被視為奇怪,未必是優勢。先前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對於仲介婚姻、移工的社會汙名,可能有損移民二代的自尊心,從而影響其學業表現或人際關係。學校環境的不友善,對中學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影響更巨;由於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的重要發展時期,當他們面對母親原生國文化與臺灣主流文化的衝撞時,要比其他同儕承載更多心理調適與文化統合的壓力,這也經常在二代的內心烙下隱性傷痕。
本章將透過新二代在中小學時期的成長回憶來探討:在新南向政策推動之前,新二代的身分差異如何被指認以及汙名化。國外的移民後代多從外表、名字或語言而被辨識,但臺灣長大的新二代多數不容易被辨識出來,這顯示出跨國婚姻中父方與母方文化的權力不平等。新二代多數沒有明顯可見的外表差異,因為臺灣丈夫在尋找外籍伴侶時就偏好中國漢人、或外表較接近臺灣人的越南女性,好生出看起來像臺灣人的孩子。其次,二代的口音跟一般臺灣孩子差不多,因為孩子在家裡不被鼓勵學習母親的語言,孩子也都採用臺灣父親的姓。換言之,母親的文化差異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被刻意抹去。當族群差異不易辨識,他們的「隱性身分」如何被指認出來?在怎樣的社會情境與文化框架下,這樣的差異被轉換為汙名、甚至排除?
本章借用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有關汙名化的理論分析,他強調「汙名化」作為一個過程,而非特質。意思是說,某一身分或屬性,因為與主流多數或社會規範下的「正常」或「主流」有所不同,而被標示為「不可欲的差異」、並賦予負面貶抑,因而成為被汙名的對象。換句話說,不是該特質本身有問題,而是脈絡或框架造成了汙名化的效果。高夫曼也區分出「明貶者」(the discredited)與「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前者的差異明顯可見,後者的差異比較隱性,當事人因而有管理、掩飾的空間。臺灣的新二代絕大多數是「可貶者」,他們的身分通常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情境容易被指認出來。
移民母親的出現是最常見的現身場景。當母親出現在學校或其他同儕互動場合、被聽見口音或母語時,新移民子女的身分最容易被辨識出來。同屬漢人的中國新移民,外表上的差異並不明顯,多半是開口說話時,因為口音或家鄉方言才被標示出中國背景。有些新二代因此避免在公共場所與母親用母語或方言溝通,擔心引發周遭人群的注目或歧視。此外,母親族群身分的延伸,如午餐便當的異國料理,也讓孩子在學校容易被指認身分。
其次,學校的制度介入是區分新移民子女的重要媒介。許多受訪者在中小學時期經歷前述的「被出櫃」經驗,尤其是在二???年代初期就學者,老師要求新移民子女用舉手方式公開現身,下課後被要求參加課後輔導也是常見的標籤化經驗。學校調查旨在服務國家的統計與治理,在政府尚未開始進行系統性地統計新移民子女人數之前,許多學校採取粗糙的「人工調查」,要求新移民子女公開舉手,或是透過全校廣播唸出新移民子女的名字並要求他們到哪裡集合。這些非惡意的「強迫現身」,反映老師的便宜行事與缺乏敏感度。
高夫曼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強調,汙名化需要經過一個學習的歷程,受汙名者,特定互動情境「召喚」其身分認同,讓他們看見社會劃界的邏輯、發現自己的差異受到社會的貶抑。許多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透過直接或間接的人群互動經驗,體察到身分相關的汙名。本章後面的分析會呈現,就算是能夠成功隱藏身分者,無意中聽見非二代同儕對於東南亞的歧視話語,或是對已現身的二代同學的嘲笑,讓他們瞥見所謂「後臺的種族歧視」(backstage racism)。
然而,高夫曼的精細觀察也被批評過於集中於微觀的人際互動,輕忽了再生產權力不平等的歷史因素、地理環境與制度結構。因此,近期的學者呼籲研究「汙名的文化與政治經濟學」,包括汙名背後的交織的文化框架、權力矩陣,以及受汙名化的個人與群體如何發展「去汙名化」的策略。我很同意上述的批評,本章雖集中分析受訪者的校園生活與同儕互動,但這些敘事與經驗投射出更廣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例如臺灣的種族與族群的不平等,多元文化政策與國際化論述、以及兩岸地緣政治的緊張與衝突。
我們的研究發現,新二代面臨的汙名經常未必基於個人特質或家庭屬性,而是其身分連結的「外來者汙名」,這樣的汙名連結,讓土生土長的新二代面臨從自己人(insider)變成外來者(outsider)的風險,可能滑落到臺灣人共同體的界線之外。我們的訪談資料顯示,臺灣東南亞二代經常被同儕連結到東南亞外勞,這群臺灣境內的底層移工,體現的是族群與階級交織的汙名。中國對於臺灣的威脅,則是持續籠罩的迷霧陰影,衍生對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汙名化;雖然這樣的地緣政治汙名多在政治化的情境中浮現,卻也擴散到日常生活的不同領域。
誰是「混血兒」?
我(國小)會說我自己是混血兒,我每次講這個,反應都不是你預想要的回應,大家對混血兒都有一種幻想,可能你英文要很好,或長得很西方,或長得不像臺灣人,可是我又不是,我不是長得很外國的臉,然後大家都會說:那你混哪裡的?.....
(未完)
「誰的媽媽是外國人?」老師對著全班同學大聲問,並要舉手的同學到教務處集合,下課後參加課後輔導。「天啊又來了~」,媽媽來自越南的小曉皺起了眉頭,每個學年老師都要問一次這個讓她非常「彆扭」、「尷尬」的問題。她在心裡碎唸:「媽媽已經拿到身分證了、臺語現在講得那麼溜,難道媽媽永遠都是『外國人』嗎?」即便小曉的長相看不出明顯的族群差異,她還是默默地舉了手,頭微低著,擔心下課後同學可能的訕笑。她也用眼角餘光瞄見其他舉手的同學,有點驚訝、也鬆了一口氣:「啊,原來他們的媽媽跟我的一樣啊」。坐在角落的小光心情同樣忐忑,他的媽媽來自中國,他不想舉手,又怕被老師發現。他總是叫媽媽不要來學校,就怕她講中文的口音被同學發現。老師之前也做過其他公開調查,像是「誰家是低收入戶?誰可以吃免費的營養午餐?」小光心裡忿忿不平:「我家裡也沒有比較窮,我成績也沒有比較差,為什麼我要跟同學不一樣?」
我根據訪談資料重建了上述場景,本書中的許多受訪者回憶起十多年前的「被出櫃」的情境,仍然感到傷痛。臺灣中小學校園強調集體主義與制式化的管理,新移民子女的「不同」與「特殊」經常被視為奇怪,未必是優勢。先前研究發現,臺灣社會對於仲介婚姻、移工的社會汙名,可能有損移民二代的自尊心,從而影響其學業表現或人際關係。學校環境的不友善,對中學階段的新住民子女影響更巨;由於青少年處於自我認同的重要發展時期,當他們面對母親原生國文化與臺灣主流文化的衝撞時,要比其他同儕承載更多心理調適與文化統合的壓力,這也經常在二代的內心烙下隱性傷痕。
本章將透過新二代在中小學時期的成長回憶來探討:在新南向政策推動之前,新二代的身分差異如何被指認以及汙名化。國外的移民後代多從外表、名字或語言而被辨識,但臺灣長大的新二代多數不容易被辨識出來,這顯示出跨國婚姻中父方與母方文化的權力不平等。新二代多數沒有明顯可見的外表差異,因為臺灣丈夫在尋找外籍伴侶時就偏好中國漢人、或外表較接近臺灣人的越南女性,好生出看起來像臺灣人的孩子。其次,二代的口音跟一般臺灣孩子差不多,因為孩子在家裡不被鼓勵學習母親的語言,孩子也都採用臺灣父親的姓。換言之,母親的文化差異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被刻意抹去。當族群差異不易辨識,他們的「隱性身分」如何被指認出來?在怎樣的社會情境與文化框架下,這樣的差異被轉換為汙名、甚至排除?
本章借用社會學家高夫曼(Erving Goffman)有關汙名化的理論分析,他強調「汙名化」作為一個過程,而非特質。意思是說,某一身分或屬性,因為與主流多數或社會規範下的「正常」或「主流」有所不同,而被標示為「不可欲的差異」、並賦予負面貶抑,因而成為被汙名的對象。換句話說,不是該特質本身有問題,而是脈絡或框架造成了汙名化的效果。高夫曼也區分出「明貶者」(the discredited)與「可貶者」(the discreditable),前者的差異明顯可見,後者的差異比較隱性,當事人因而有管理、掩飾的空間。臺灣的新二代絕大多數是「可貶者」,他們的身分通常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情境容易被指認出來。
移民母親的出現是最常見的現身場景。當母親出現在學校或其他同儕互動場合、被聽見口音或母語時,新移民子女的身分最容易被辨識出來。同屬漢人的中國新移民,外表上的差異並不明顯,多半是開口說話時,因為口音或家鄉方言才被標示出中國背景。有些新二代因此避免在公共場所與母親用母語或方言溝通,擔心引發周遭人群的注目或歧視。此外,母親族群身分的延伸,如午餐便當的異國料理,也讓孩子在學校容易被指認身分。
其次,學校的制度介入是區分新移民子女的重要媒介。許多受訪者在中小學時期經歷前述的「被出櫃」經驗,尤其是在二???年代初期就學者,老師要求新移民子女用舉手方式公開現身,下課後被要求參加課後輔導也是常見的標籤化經驗。學校調查旨在服務國家的統計與治理,在政府尚未開始進行系統性地統計新移民子女人數之前,許多學校採取粗糙的「人工調查」,要求新移民子女公開舉手,或是透過全校廣播唸出新移民子女的名字並要求他們到哪裡集合。這些非惡意的「強迫現身」,反映老師的便宜行事與缺乏敏感度。
高夫曼從符號互動論的角度強調,汙名化需要經過一個學習的歷程,受汙名者,特定互動情境「召喚」其身分認同,讓他們看見社會劃界的邏輯、發現自己的差異受到社會的貶抑。許多新二代在成長過程中,透過直接或間接的人群互動經驗,體察到身分相關的汙名。本章後面的分析會呈現,就算是能夠成功隱藏身分者,無意中聽見非二代同儕對於東南亞的歧視話語,或是對已現身的二代同學的嘲笑,讓他們瞥見所謂「後臺的種族歧視」(backstage racism)。
然而,高夫曼的精細觀察也被批評過於集中於微觀的人際互動,輕忽了再生產權力不平等的歷史因素、地理環境與制度結構。因此,近期的學者呼籲研究「汙名的文化與政治經濟學」,包括汙名背後的交織的文化框架、權力矩陣,以及受汙名化的個人與群體如何發展「去汙名化」的策略。我很同意上述的批評,本章雖集中分析受訪者的校園生活與同儕互動,但這些敘事與經驗投射出更廣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例如臺灣的種族與族群的不平等,多元文化政策與國際化論述、以及兩岸地緣政治的緊張與衝突。
我們的研究發現,新二代面臨的汙名經常未必基於個人特質或家庭屬性,而是其身分連結的「外來者汙名」,這樣的汙名連結,讓土生土長的新二代面臨從自己人(insider)變成外來者(outsider)的風險,可能滑落到臺灣人共同體的界線之外。我們的訪談資料顯示,臺灣東南亞二代經常被同儕連結到東南亞外勞,這群臺灣境內的底層移工,體現的是族群與階級交織的汙名。中國對於臺灣的威脅,則是持續籠罩的迷霧陰影,衍生對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汙名化;雖然這樣的地緣政治汙名多在政治化的情境中浮現,卻也擴散到日常生活的不同領域。
誰是「混血兒」?
我(國小)會說我自己是混血兒,我每次講這個,反應都不是你預想要的回應,大家對混血兒都有一種幻想,可能你英文要很好,或長得很西方,或長得不像臺灣人,可是我又不是,我不是長得很外國的臉,然後大家都會說:那你混哪裡的?.....
(未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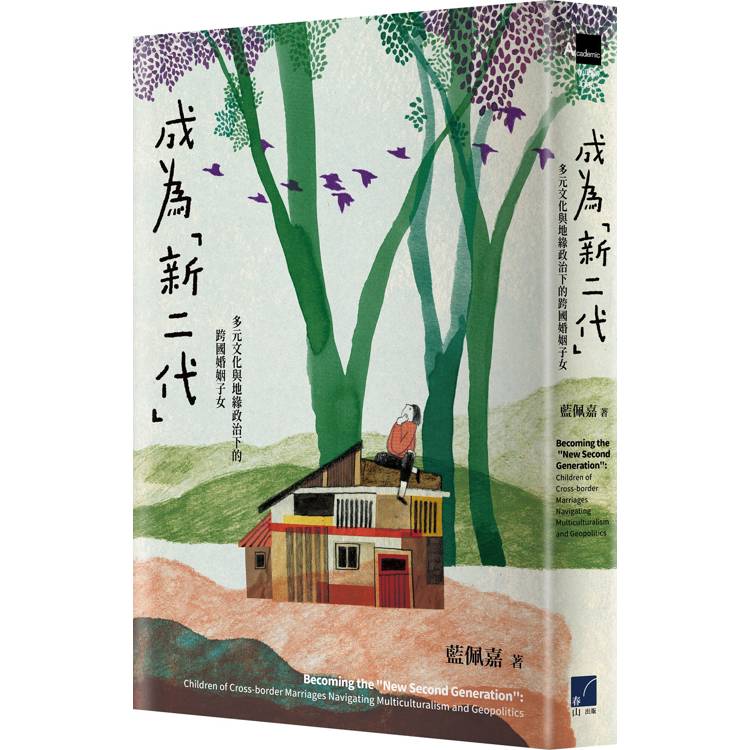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