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篇小說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原民部落的成長背景成為作者小說創作的養分
故事皆圍繞於部落底層人物的生活、城鎮間生活的矛盾與衝突、親情與愛情的羈絆,以及謀生的落差,失業、失婚、失蹤、失職,伴隨著酗酒問題,資本主義入侵下,不復有人人景仰的獵人勇士,而成為只為求得溫飽的卑微人物,對女性心理與處境更有細膩描寫,堪稱原住民族的生活浮世繪。
本書特色
本書以〈哈勇來看我〉(2013年第4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村裡消息〉(2015年第六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告別〉(2017年第8屆臺灣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第二名)、〈Puniq Utux〉(2020年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果園裡的撒韻〉(2021年第12屆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佳作)、〈小祕密〉(2022年屏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伊萬的踟躕〉(2022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正獎)、〈夏日午後〉(2022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首獎)、〈等待曙光〉(2023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最後的遺言〉(2024年第15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類佳作)等11短篇小說合集,堪稱獲獎含金量最高的作品集。
故事皆圍繞於部落底層人物的生活、城鎮間生活的矛盾與衝突、親情與愛情的羈絆,以及謀生的落差,失業、失婚、失蹤、失職,伴隨著酗酒問題,資本主義入侵下,不復有人人景仰的獵人勇士,而成為只為求得溫飽的卑微人物,對女性心理與處境更有細膩描寫,堪稱原住民族的生活浮世繪。
本書特色
本書以〈哈勇來看我〉(2013年第4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村裡消息〉(2015年第六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告別〉(2017年第8屆臺灣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第二名)、〈Puniq Utux〉(2020年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果園裡的撒韻〉(2021年第12屆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佳作)、〈小祕密〉(2022年屏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伊萬的踟躕〉(2022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正獎)、〈夏日午後〉(2022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首獎)、〈等待曙光〉(2023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最後的遺言〉(2024年第15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類佳作)等11短篇小說合集,堪稱獲獎含金量最高的作品集。
目錄
【自序】我是離開的人,也將是返回的人
【導讀】從裂縫裡照見的光芒 瓦歷斯.諾幹
哈勇來看我
(2013年第4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
村裡消息
(2015年年第六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
告別
(2017年第8屆臺灣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第二名)
Puniq Utux
(2020年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
果園裡的撒韻
(2021年第12屆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小祕密
(2022年屏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
伊萬的踟躕
(2022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正獎)
夏日午後
(2022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首獎)
等待曙光
(2023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
最後的遺言
(2024年第15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類佳作)
嫁給漢人的撒韻
【導讀】從裂縫裡照見的光芒 瓦歷斯.諾幹
哈勇來看我
(2013年第4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
村裡消息
(2015年年第六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第一名)
告別
(2017年第8屆臺灣原住民文學獎小說組第二名)
Puniq Utux
(2020年臺灣文學獎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
果園裡的撒韻
(2021年第12屆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小祕密
(2022年屏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
伊萬的踟躕
(2022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正獎)
夏日午後
(2022年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首獎)
等待曙光
(2023年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
最後的遺言
(2024年第15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類佳作)
嫁給漢人的撒韻
序/導讀
作者序
我是離開的人,也將是返回的人
二○一三年左右,一張酒桌上,一個尊敬的長輩聽聞我常在臉書上寫文章,就當面勸我:「為何寫這麼多了不拿去參賽?」也許在這般有力的驅使下,我在當年就參加了原住民族文學獎,並幸運地以〈哈勇來看我〉此篇獲得了小說首獎。之後,就一直寫,至今。
十年以來,我的創作方式大抵如此:有個主題,或者想法,我就將它們具化為一篇小說。換言之,小說於我僅是一種表達方式,一個載體。但說實在的,我並沒有值得驕人的道理或民族大義要講述,而且我厭惡如此,至少目前是這樣。我只想聲音不大地「說」點什麼,這就是我所謂的「小說」。
必須聲明的是,我所有的創作都是習作,對於如何寫,我仍在摸索,至今眼前還是一片黑暗。我最終的創作目標是:為追求美學而努力;為不平的人生做吶喊;對庸俗不堪的深惡痛絕。我試圖描繪多種村裡人物形象,竟猛然發現概括性的語言力有未逮,是的,他們不能被概括,或許正因如此,才需要小說吧。
回到我的身分,我屬泰雅族群,本該為族群發聲,本該創作有族群特色的文字,但我似乎沒有。這部分正是我缺乏的,也是必須努力的。做為Walice,我沒有好好讀書,做了幾年代課教師後便以打零工來維持生計,所以我常感到生命的空虛和恍惚。做為卓璽,雖然在網上寫這麼多了,但自己是不敢回看的,碌碌半生,矯情地說,就是無言無行。阿根廷文豪波赫士有句詩寫:「我是黃昏時刻,那些迷惘的人」,可以說我長期就處於這種精神晃蕩的心境。
現在這本小說集呈現在讀者面前了,所謂十年磨一劍,我羞赧於說自己作品的優劣,這必須留給讀者,不容我來置喙。小說集有篇〈等待曙光〉,其中有段文字我是這麼寫的:「我走出三弟家,四周靜謐,什麼都看不見,農地、老屋、群山似乎都消失了,但它們仍真切地在那裡,只需等待一線曙光。我哪裡也不想去了,就想和親人一起,和他們在土地上勞作、苦惱、歡笑⋯⋯,終此一生。」我是個離開(部落)的人,有一天,也將是返回(部落)的人。我相信與我有著相同身分的同胞,應該也會有此感慨。就像鍾理和在〈原鄉〉裡寫:「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最後,要誠摯感謝尊敬的作家瓦歷斯.諾幹,若非他的屢次鼓舞、當頭棒喝以及牽成提攜,就不會有這本小說。此外,也致謝曾在一路上激勵我創作的兄弟友朋,爾等期待的爆破聲,總算可以驚天一響。
是為序。
導讀
從裂縫裡照見的光芒
一九七○年五月三日,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文化藝術中心,一位「身材消瘦、蓄著濃密的小鬍子、點著根菸」的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一九二七∼二○一四)在三年前寫下《百年孤寂》之後,為他取得了在藝術中心的演講,他坐著說話,因為「如果我站著,恐怕會嚇得兩腿發軟,癱倒在地。」那天的講話要再過十二年他才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馬奎斯當日恐怕也無法預知會有那麼一天吧,何況,眼前的南美文學巨人路易斯.波赫士(Jerge Luis Borges,一八九九∼一九八六)還未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呢!儘管羞怯地坐在椅子上說話,我想像馬奎斯內心的膽怯終究是讓文學的熱情一掃而光,他大著膽子說:「對我而言,文學創作就和登台演講一樣,都是被逼的。」為了要堵《觀察家報》文學副刊主編的嘴(不是他不登,是年輕人不寫),青年馬奎斯逼迫自己寫了短篇小說。其後的幾年,出版了五本小說集,並明白了一個道理,「寫作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以至於《百年孤寂》足足想了十九年才得以下筆。
在南美洲世界一端的台灣,在經過殖民歷史三百年的台灣原住民族的書寫,特別是小說的書寫,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才由排灣族人谷灣.打鹿勒,以漢名陳英雄出版《域外夢痕》短篇小說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他是台灣原住民作家中,最早以漢語寫作並集結出版小說的作者。陳英雄寫作的那個年代裡,台灣原住民的議題還沒有走到以原住民作為主體性的位置,但陳英雄從一開始就毫不閃避的將自己族群的經驗和觀點融進他的創作中,日後也許陳英雄也痛苦的體悟到小說的寫作一如馬奎斯所言,「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其後雖於二○○三年再版《域外夢痕》,書名更之為《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晨星出版),便無其他重要創作。台灣原住民族的小說寫作,還要再等到十六年後才會被台灣文壇看見。
布農人拓拔斯.塔瑪匹瑪(一九六○∼)的小說《最後的獵人》(小說集,一九八七,晨星)、《情人與妓女》(小說集,一九九二,晨星),主要是短篇小說,是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中最早受到漢人社會廣泛注意的對象,獲有「吳濁流文學獎」(一九八六年)、「賴和文學獎」(一九九○年)這兩個台灣文學界重要的獎項,文學評論家注意到拓拔斯作品中溫厚的人道精神,我認為拓拔斯是被這個台灣政經社會施加在台灣原住民族身體與精神的病症所逼迫而寫作,正如他作為一位文學作家,另一個身分是醫生,小說寫作是文字藝術的問診、把脈、處方。其後,再過上十幾年,才由泰雅人瓦歷斯.諾幹接下棒子。
二○一三年出版《城市殘酷》、二○一四年出版《戰爭殘酷》,小說評論者才再次將眼光注意到原住民作家的小說藝術。二○一四年出版的《瓦歷斯微小說》,更是將短篇小說的篇幅壓縮成三百五十字以內的「微小說」,作者自述著將小說壓縮在三百五十字以內,是「用來考驗文字的力量可以發揮到多大的效用,用以考掘類型文學的空間可以堅強到承受多少壓力,毋寧這是某種殘酷以極的自我鍛造與逼問—小說還能夠怎麼說話?」這是小說家對小說藝術的自我逼迫。
二○ 一三年, 泰雅人卓璽( 陳宏志) 以短篇小說〈Puniq Utux〉一文獲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首獎,寫的是在風雨夜中,一家人尋找夜歸的父親,小兒子尤命卻遇見Puniq Utux(鬼火)的故事,透過綿密而和緩的敘述,展現出一種簡單乾淨的風格,像是有個人在旁邊悠緩地說著故事。此時,我們還無法單憑一篇小說確認卓璽的小說家身分,但〈Puniq Utux〉所展示的情感內斂、節制,文字簡潔乾淨,人物鮮活,人物的性格推動情節的特色,延續著他後來得獎或未得獎的小說。等到二○二四年卓璽交出《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我終於可以確認卓璽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特別是精於藝術的短篇小說家。
我記得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美學的面向》寫下:「美,當它對抗社會的醜惡時,它便會成為一種顛覆的力量。」〈村裡消息〉中的漢人女老師趙曉芬正是翻轉了大眾視部落醜惡習見的顛覆的力量,卓璽卻以平鋪直敘、平淡無奇的筆法,不動聲色的「顛覆」一般大眾對部落生活的俗見,精準且有力的展示了小說的力量。
〈告別〉,是一篇看來極其平淡的自述,是對父親、對老劉,也是對自己的告別,恰恰是隱藏在自述裡的「告白」,才能夠看到隱匿在日常生活中的洶湧的情感,於是,告別的意旨才能是對自己無聊人生的揮別。
〈Puniq Utux〉,從一件孩子找爸爸回家的村中小事,一路不著痕跡的鋪排出生活、生命和文化交織匯流成的「puniq utux」(鬼火),最魔幻的鬼火傳說以細膩的寫實主義鋪敘為日常生活。小說可以怎樣說故事,〈Puniq Utux〉會告訴你。
一切起源於女孩想為她男友洗滌衣物而邀男友的弟弟夜行到溫泉池洗衣褲開始。這是〈小祕密〉的開端,而夜行出獵的男友一夥人返程想洗溫泉,意外逼得這男女共處溫泉室內,與戶外焦急想洗浴的獵人們,形成一內一外的拉鋸。正是作者設計的這個「意外」,讓整個故事成為「存在卻無法張揚」的小祕密。「意外」,正是說故事的方法之一。
讀過卓璽的一些短篇之後,油然而生的感覺是弱者、失敗者、小人物的幸福與苦情,看來就像是一枚錢幣的兩面,這些人物的精神自覺,從來就不是出於否定理性邏輯,是那恍惚失魂、破碎的生活細節,在生命底層活動的普遍性與本質性的蠕動。〈伊萬的踟躕〉主人翁伊萬的生命情調正是失魂與破碎的總和。
〈夏日午後〉,由理財專員與客戶(中年單身原住民)激烈的語言攻防,精準地捕捉到弱勢者不安於命運的擺布,並在語言敘事的裂縫中偶而閃現溫暖的光芒,也可能會照進人們心底那些孤苦或沮喪或失落或迷茫的昏暗角落。
以上的小說,都是得獎的作品,《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另收錄一篇未得獎(或說是尚未得獎)的短篇小說,但我不認為稍遜得獎之作,你得細細閱讀,重構零碎又真切的細節片段,才能讀懂隱藏在冷靜敘事的豐沛情感,因為好的短篇小說是一門精煉的手工藝術。
一九七八年六月某一天,波赫士在離世的八年前面對南美洲文學,甚至是世界文學的趨向不無感慨地寫下一段話:「我們的文學在趨向混亂, 在趨向自由體的散文。⋯⋯我們的文學在趨向取消人物,取消情節,一切都變得含混不清。」緊接著,似乎有一道幽微的光芒讓波赫士重拾些許信心,「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裡,還有某些東西仍然保持著經典著作的美德。」波赫士指的是小說,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正是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裡拯救了秩序。
我認為,所有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作為一門手工藝術,它所呈現最好的美德都是象徵性的,即便小說的基礎有一大部分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卻在作家表述自己的思想、為表述其思想而採用的形式,無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至於魔幻現實之技術,均無損於小說展示的象徵—黑暗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
卓璽的《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正是挖掘台灣原住民族族人尋常生活中那黑暗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現實,經常是匪夷所思,讓芸芸眾生的我們失去了想像力,好的小說,特別是手藝精湛的短篇小說,就是讓失去想像力的人們可以並願意相信真實的生活。讀過《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之後,我可以不再有疑問地宣稱,他的短篇小說,拯救了日常生活的秩序。
瓦歷斯.諾幹
我是離開的人,也將是返回的人
二○一三年左右,一張酒桌上,一個尊敬的長輩聽聞我常在臉書上寫文章,就當面勸我:「為何寫這麼多了不拿去參賽?」也許在這般有力的驅使下,我在當年就參加了原住民族文學獎,並幸運地以〈哈勇來看我〉此篇獲得了小說首獎。之後,就一直寫,至今。
十年以來,我的創作方式大抵如此:有個主題,或者想法,我就將它們具化為一篇小說。換言之,小說於我僅是一種表達方式,一個載體。但說實在的,我並沒有值得驕人的道理或民族大義要講述,而且我厭惡如此,至少目前是這樣。我只想聲音不大地「說」點什麼,這就是我所謂的「小說」。
必須聲明的是,我所有的創作都是習作,對於如何寫,我仍在摸索,至今眼前還是一片黑暗。我最終的創作目標是:為追求美學而努力;為不平的人生做吶喊;對庸俗不堪的深惡痛絕。我試圖描繪多種村裡人物形象,竟猛然發現概括性的語言力有未逮,是的,他們不能被概括,或許正因如此,才需要小說吧。
回到我的身分,我屬泰雅族群,本該為族群發聲,本該創作有族群特色的文字,但我似乎沒有。這部分正是我缺乏的,也是必須努力的。做為Walice,我沒有好好讀書,做了幾年代課教師後便以打零工來維持生計,所以我常感到生命的空虛和恍惚。做為卓璽,雖然在網上寫這麼多了,但自己是不敢回看的,碌碌半生,矯情地說,就是無言無行。阿根廷文豪波赫士有句詩寫:「我是黃昏時刻,那些迷惘的人」,可以說我長期就處於這種精神晃蕩的心境。
現在這本小說集呈現在讀者面前了,所謂十年磨一劍,我羞赧於說自己作品的優劣,這必須留給讀者,不容我來置喙。小說集有篇〈等待曙光〉,其中有段文字我是這麼寫的:「我走出三弟家,四周靜謐,什麼都看不見,農地、老屋、群山似乎都消失了,但它們仍真切地在那裡,只需等待一線曙光。我哪裡也不想去了,就想和親人一起,和他們在土地上勞作、苦惱、歡笑⋯⋯,終此一生。」我是個離開(部落)的人,有一天,也將是返回(部落)的人。我相信與我有著相同身分的同胞,應該也會有此感慨。就像鍾理和在〈原鄉〉裡寫:「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
最後,要誠摯感謝尊敬的作家瓦歷斯.諾幹,若非他的屢次鼓舞、當頭棒喝以及牽成提攜,就不會有這本小說。此外,也致謝曾在一路上激勵我創作的兄弟友朋,爾等期待的爆破聲,總算可以驚天一響。
是為序。
導讀
從裂縫裡照見的光芒
一九七○年五月三日,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文化藝術中心,一位「身材消瘦、蓄著濃密的小鬍子、點著根菸」的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一九二七∼二○一四)在三年前寫下《百年孤寂》之後,為他取得了在藝術中心的演講,他坐著說話,因為「如果我站著,恐怕會嚇得兩腿發軟,癱倒在地。」那天的講話要再過十二年他才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馬奎斯當日恐怕也無法預知會有那麼一天吧,何況,眼前的南美文學巨人路易斯.波赫士(Jerge Luis Borges,一八九九∼一九八六)還未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呢!儘管羞怯地坐在椅子上說話,我想像馬奎斯內心的膽怯終究是讓文學的熱情一掃而光,他大著膽子說:「對我而言,文學創作就和登台演講一樣,都是被逼的。」為了要堵《觀察家報》文學副刊主編的嘴(不是他不登,是年輕人不寫),青年馬奎斯逼迫自己寫了短篇小說。其後的幾年,出版了五本小說集,並明白了一個道理,「寫作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以至於《百年孤寂》足足想了十九年才得以下筆。
在南美洲世界一端的台灣,在經過殖民歷史三百年的台灣原住民族的書寫,特別是小說的書寫,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才由排灣族人谷灣.打鹿勒,以漢名陳英雄出版《域外夢痕》短篇小說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他是台灣原住民作家中,最早以漢語寫作並集結出版小說的作者。陳英雄寫作的那個年代裡,台灣原住民的議題還沒有走到以原住民作為主體性的位置,但陳英雄從一開始就毫不閃避的將自己族群的經驗和觀點融進他的創作中,日後也許陳英雄也痛苦的體悟到小說的寫作一如馬奎斯所言,「恐怕是這世上唯一越做越難做的行當」,其後雖於二○○三年再版《域外夢痕》,書名更之為《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晨星出版),便無其他重要創作。台灣原住民族的小說寫作,還要再等到十六年後才會被台灣文壇看見。
布農人拓拔斯.塔瑪匹瑪(一九六○∼)的小說《最後的獵人》(小說集,一九八七,晨星)、《情人與妓女》(小說集,一九九二,晨星),主要是短篇小說,是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中最早受到漢人社會廣泛注意的對象,獲有「吳濁流文學獎」(一九八六年)、「賴和文學獎」(一九九○年)這兩個台灣文學界重要的獎項,文學評論家注意到拓拔斯作品中溫厚的人道精神,我認為拓拔斯是被這個台灣政經社會施加在台灣原住民族身體與精神的病症所逼迫而寫作,正如他作為一位文學作家,另一個身分是醫生,小說寫作是文字藝術的問診、把脈、處方。其後,再過上十幾年,才由泰雅人瓦歷斯.諾幹接下棒子。
二○一三年出版《城市殘酷》、二○一四年出版《戰爭殘酷》,小說評論者才再次將眼光注意到原住民作家的小說藝術。二○一四年出版的《瓦歷斯微小說》,更是將短篇小說的篇幅壓縮成三百五十字以內的「微小說」,作者自述著將小說壓縮在三百五十字以內,是「用來考驗文字的力量可以發揮到多大的效用,用以考掘類型文學的空間可以堅強到承受多少壓力,毋寧這是某種殘酷以極的自我鍛造與逼問—小說還能夠怎麼說話?」這是小說家對小說藝術的自我逼迫。
二○ 一三年, 泰雅人卓璽( 陳宏志) 以短篇小說〈Puniq Utux〉一文獲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首獎,寫的是在風雨夜中,一家人尋找夜歸的父親,小兒子尤命卻遇見Puniq Utux(鬼火)的故事,透過綿密而和緩的敘述,展現出一種簡單乾淨的風格,像是有個人在旁邊悠緩地說著故事。此時,我們還無法單憑一篇小說確認卓璽的小說家身分,但〈Puniq Utux〉所展示的情感內斂、節制,文字簡潔乾淨,人物鮮活,人物的性格推動情節的特色,延續著他後來得獎或未得獎的小說。等到二○二四年卓璽交出《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我終於可以確認卓璽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特別是精於藝術的短篇小說家。
我記得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美學的面向》寫下:「美,當它對抗社會的醜惡時,它便會成為一種顛覆的力量。」〈村裡消息〉中的漢人女老師趙曉芬正是翻轉了大眾視部落醜惡習見的顛覆的力量,卓璽卻以平鋪直敘、平淡無奇的筆法,不動聲色的「顛覆」一般大眾對部落生活的俗見,精準且有力的展示了小說的力量。
〈告別〉,是一篇看來極其平淡的自述,是對父親、對老劉,也是對自己的告別,恰恰是隱藏在自述裡的「告白」,才能夠看到隱匿在日常生活中的洶湧的情感,於是,告別的意旨才能是對自己無聊人生的揮別。
〈Puniq Utux〉,從一件孩子找爸爸回家的村中小事,一路不著痕跡的鋪排出生活、生命和文化交織匯流成的「puniq utux」(鬼火),最魔幻的鬼火傳說以細膩的寫實主義鋪敘為日常生活。小說可以怎樣說故事,〈Puniq Utux〉會告訴你。
一切起源於女孩想為她男友洗滌衣物而邀男友的弟弟夜行到溫泉池洗衣褲開始。這是〈小祕密〉的開端,而夜行出獵的男友一夥人返程想洗溫泉,意外逼得這男女共處溫泉室內,與戶外焦急想洗浴的獵人們,形成一內一外的拉鋸。正是作者設計的這個「意外」,讓整個故事成為「存在卻無法張揚」的小祕密。「意外」,正是說故事的方法之一。
讀過卓璽的一些短篇之後,油然而生的感覺是弱者、失敗者、小人物的幸福與苦情,看來就像是一枚錢幣的兩面,這些人物的精神自覺,從來就不是出於否定理性邏輯,是那恍惚失魂、破碎的生活細節,在生命底層活動的普遍性與本質性的蠕動。〈伊萬的踟躕〉主人翁伊萬的生命情調正是失魂與破碎的總和。
〈夏日午後〉,由理財專員與客戶(中年單身原住民)激烈的語言攻防,精準地捕捉到弱勢者不安於命運的擺布,並在語言敘事的裂縫中偶而閃現溫暖的光芒,也可能會照進人們心底那些孤苦或沮喪或失落或迷茫的昏暗角落。
以上的小說,都是得獎的作品,《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另收錄一篇未得獎(或說是尚未得獎)的短篇小說,但我不認為稍遜得獎之作,你得細細閱讀,重構零碎又真切的細節片段,才能讀懂隱藏在冷靜敘事的豐沛情感,因為好的短篇小說是一門精煉的手工藝術。
一九七八年六月某一天,波赫士在離世的八年前面對南美洲文學,甚至是世界文學的趨向不無感慨地寫下一段話:「我們的文學在趨向混亂, 在趨向自由體的散文。⋯⋯我們的文學在趨向取消人物,取消情節,一切都變得含混不清。」緊接著,似乎有一道幽微的光芒讓波赫士重拾些許信心,「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裡,還有某些東西仍然保持著經典著作的美德。」波赫士指的是小說,小說這種文學體裁正是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裡拯救了秩序。
我認為,所有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作為一門手工藝術,它所呈現最好的美德都是象徵性的,即便小說的基礎有一大部分來自於日常生活的經驗,卻在作家表述自己的思想、為表述其思想而採用的形式,無論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以至於魔幻現實之技術,均無損於小說展示的象徵—黑暗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
卓璽的《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正是挖掘台灣原住民族族人尋常生活中那黑暗的過去與時間的深淵。現實,經常是匪夷所思,讓芸芸眾生的我們失去了想像力,好的小說,特別是手藝精湛的短篇小說,就是讓失去想像力的人們可以並願意相信真實的生活。讀過《伊萬的踟躕—卓璽的11 篇小說》之後,我可以不再有疑問地宣稱,他的短篇小說,拯救了日常生活的秩序。
瓦歷斯.諾幹
試閱
哈勇來看我
一
進入九月,秋天的氣息更濃厚了,這是沒辦法的事。秋天來到部落,農地草葉枯黃,一片頹敗,就是說,各種農忙要開始了。農地整理一番後(砍草、翻土等),再種上新農作,這一切作息,跟季節同步,循環不已,也是沒辦法的事。
他們一樣在凌晨爬起來,在雞鳴的時候,展開一天繁重的農活。天色未亮,顯得特別寧靜,露水依然凝重。夫妻剛起床,不願意說話,總感覺說話的力氣已在睡眠中失去,看起來十分憂愁。自古至今,部落的生活作息,大概如此,要深究原因,很難說個明白。
哈勇蹲在門口磨刀,霍霍地引起一陣嘈雜,當然,磨刀聲僅擴散於他家空地,空地上趴著那條黑狗鐵木,因而伸了個懶腰,尾巴像蛇一樣捲起,走向哈勇身邊。這個時候開始傳來幾聲狗叫,此起彼落,然而,鐵木並沒有隨之應和,牠只靜靜坐在主人旁,牠期待主人準備吃的給牠。確實,撒韻左手抓隻雞過來了,右手端著盛有隔夜飯菜混著肉湯的碗公,後者就是鐵木的早飯。
「哈勇!把這隻雞殺了。」撒韻的聲音劃破寧靜,在別人還在貪睡的時刻,顯得格外清亮。她把雞甩在哈勇身邊的泥地,動作相當有力。這是隻母雞,考慮到牠的肥碩,砰地一響可想而知,雞落地後叫了幾聲,翅膀拍打著,騰起了些許塵埃。雞腳被細繩捆綁,動彈不得,一旁鐵木除了低頭吃飯,也用狗眼監視著,此雞就算掙扎,並無脫逃的機會,牠渾然不覺自己性命垂危。
哈勇沒說話,繼續磨刀,嘴裡含著水,邊磨邊噴,灰色磨刀石已呈弧狀,被磨的凹槽十分光滑,可見消磨有一些年日了。
「殺雞做什麼?」哈勇說話簡短,夾帶著怒氣。痰在其喉嚨上下滑動,非常頑固,卻始終無法吐出,或者說,痰不到火候,即便哈勇要一吐為快,也極為困難。這是他長年抽菸之故,一天兩包,撒韻每天都嘮叨,但顯然毫無警惕作用。所以一到早上,哈勇總會咳那麼幾聲,老是有咳不完的痰。終於,刀磨好了,哈勇用長繭的姆指在刀鋒輕擦著,並在下巴那麼刮一下,刀面上有些細微鬍渣,這說明刀磨得夠利了。這是把山刀,是哈勇的爺爺給他的,刀身散發濃厚的歷史氣味。想當年,他爺爺快死之前,躺在床上跟他說:「哈勇!我沒有什麼留給你,什麼都可以丟掉,只有這把刀一定要擺身邊⋯⋯。」說完這句,他爺爺就死了。
你大概知道了,哈勇的爺爺是我的曾祖父,哈勇是我爸,撒韻是我媽。我叫鐵木,跟那黑狗一樣的名字。那年我離開部落,要去都市所謂「社會上」闖一下,父親非常不捨,大概思念之故,或者希望我留在他身邊,暫且用狗替代了我。
父親殺完雞,也燒完了毛,手上鮮血沒有洗去,他只在地上抹一下。他面無表情,坐在板凳上抽菸,白煙嬝嬝像鬼魂在他頭頂上方,交錯,扭曲,繚繞。此時,天也亮了。「快來吃飯,我們還要去田裡除草!」母親在廚房喊,父親沒有即時回應。這就是他們每日生活的常態,沒有例外。父親一向沉默寡言,跟他說話,必須等他搞清楚談話的內容,他才適時開口,也就是說,找他聊天,要有耐性,否則真會以為他陰沉冷酷,不好相處。沒辦法,父親總是這個性。後來我逐漸明白實情並非如此,他只有國小畢業,學歷使他感到某種程度的自卑,所以在人面前總不擅言詞,謹慎發言。這也沒什麼不尋常的,哲學一點說法,「自卑是一種無能的體現」,好像說得也很像那麼回事。但,父親並非無能之人,在我看來,這只是鄉下人所具備的質樸個性,個性怎麼說呢?誰也說不清,沒有對錯。他把菸吸短了,看見隔壁的瓦旦正要下田去了,問候了一下,把菸捻熄,就進屋裡去了。
餐桌上,父親夾起一塊他弟弟獵到的飛鼠,嚼出聲音說:「肉很嫩,我很久沒吃到山肉了。」一旁走動的母親,已經吃完飯,拿著抹布在瓦斯爐上擦拭,擦過之處,泛著銀光。母親愛乾淨,稍微一點汙垢塵埃,她看著全身不舒服,一定要動一動。我印象中,母親確實做起家事一點都不馬虎,近乎苛求。我姊我弟的衣物都是母親分類擺齊的,她時常念我們,要求我們自己整理,不過她仍然看不慣,抱怨我們「不會做家事」,最後還是由她承攬一切。這是她作為母親的宿命,古今中外,大概都如此。如果有機會你到我家來坐坐,你會發現地板上的每塊磁磚熠熠生輝,像一面鏡子。
「你兒子鐵木打電話來,聽口氣好像有事,電話裡沒講清楚,你去看他吧!」母親小聲地說,好像在說什麼祕密,怕別人聽見。這個時候父親也吃飽了,把碗筷放下,也不丟到洗碗槽裡。這也像平常的他,幾乎不做家事。身為所謂「戶長」,父親很清楚自己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這可以理解為他是一個很傳統的人,即女人做的事就由女人,男人不該僭越身分去搶著做,反過來說,道理也一樣。所以,碗筷放在那裡等著母親去收拾、洗刷,在我家是一件極自然的事,無須辯駁。「又吵架啦?」父親疑惑地問。母親沒正面回答,只唯唯諾諾。其實她很清楚鐵木的情況,即本人我,與老婆最近感情不和睦,大吵小吵不斷,有離婚之虞。這都在母親心裡擱著,看在眼裡,她不會讓父親知道得太多。父親是個嚴肅又顧家的人,一旦讓他知道這些事,會徒增其對我的責備。這是母親向來對我呵護有加的措施,我很感激她。
時值秋天,老家後面那棵柿子樹結滿了柿子,有些熟了,大部分還青黃不接,但總的來說,迎著陽光,果實紅彤彤的,由遠處看,蠻像一幅畫,你若想成電影裡什麼童年爬樹的幸福畫面,也是可以的。父親在一個午睡中醒來,赤腳爬上了樹,吩咐在樹下的母親接著。起先母親徒手接,她覺得麻煩,後來想到用身上的衣服兜起一個袋狀,父親朝下丟。的確,這樣有效率,不致使母親誤接而讓果實摔落地面。依此辦法,不到半小時,他們摘了一個麻袋那麼多。那些摘不到隱藏在枝葉其間,或是父親故意遺漏的,就留給鳥獸蟲蟻吧。大自然有其生命規律,動物亦然,牠們也要存活,也要延續下一代。
柿子實在太多,父親與母親當然吃不完。他們如果每餐都各吃一個,當飯後水果,大概可以吃到年底。柿子是這樣的,必須擺放一段時間,自然會熟,熟而變成軟捏捏的,老人家愛吃。據說也可用鹽水泡過,又脆又甜,像蘋果那樣芬芳。多虧有了柿子樹,它默默地貢獻一切它該貢獻的,夏天遮起餘蔭供人乘涼,枝幹可供村裡孩童攀爬,到了秋天則更加努力長出這些果實,其功德實在不小於人類。
父親留著一些,一顆顆妥善放置,在他自製的竹籃裡,待其成熟。其他則分送親友,藉以增加鄰里間的感情,也是不錯。
一
進入九月,秋天的氣息更濃厚了,這是沒辦法的事。秋天來到部落,農地草葉枯黃,一片頹敗,就是說,各種農忙要開始了。農地整理一番後(砍草、翻土等),再種上新農作,這一切作息,跟季節同步,循環不已,也是沒辦法的事。
他們一樣在凌晨爬起來,在雞鳴的時候,展開一天繁重的農活。天色未亮,顯得特別寧靜,露水依然凝重。夫妻剛起床,不願意說話,總感覺說話的力氣已在睡眠中失去,看起來十分憂愁。自古至今,部落的生活作息,大概如此,要深究原因,很難說個明白。
哈勇蹲在門口磨刀,霍霍地引起一陣嘈雜,當然,磨刀聲僅擴散於他家空地,空地上趴著那條黑狗鐵木,因而伸了個懶腰,尾巴像蛇一樣捲起,走向哈勇身邊。這個時候開始傳來幾聲狗叫,此起彼落,然而,鐵木並沒有隨之應和,牠只靜靜坐在主人旁,牠期待主人準備吃的給牠。確實,撒韻左手抓隻雞過來了,右手端著盛有隔夜飯菜混著肉湯的碗公,後者就是鐵木的早飯。
「哈勇!把這隻雞殺了。」撒韻的聲音劃破寧靜,在別人還在貪睡的時刻,顯得格外清亮。她把雞甩在哈勇身邊的泥地,動作相當有力。這是隻母雞,考慮到牠的肥碩,砰地一響可想而知,雞落地後叫了幾聲,翅膀拍打著,騰起了些許塵埃。雞腳被細繩捆綁,動彈不得,一旁鐵木除了低頭吃飯,也用狗眼監視著,此雞就算掙扎,並無脫逃的機會,牠渾然不覺自己性命垂危。
哈勇沒說話,繼續磨刀,嘴裡含著水,邊磨邊噴,灰色磨刀石已呈弧狀,被磨的凹槽十分光滑,可見消磨有一些年日了。
「殺雞做什麼?」哈勇說話簡短,夾帶著怒氣。痰在其喉嚨上下滑動,非常頑固,卻始終無法吐出,或者說,痰不到火候,即便哈勇要一吐為快,也極為困難。這是他長年抽菸之故,一天兩包,撒韻每天都嘮叨,但顯然毫無警惕作用。所以一到早上,哈勇總會咳那麼幾聲,老是有咳不完的痰。終於,刀磨好了,哈勇用長繭的姆指在刀鋒輕擦著,並在下巴那麼刮一下,刀面上有些細微鬍渣,這說明刀磨得夠利了。這是把山刀,是哈勇的爺爺給他的,刀身散發濃厚的歷史氣味。想當年,他爺爺快死之前,躺在床上跟他說:「哈勇!我沒有什麼留給你,什麼都可以丟掉,只有這把刀一定要擺身邊⋯⋯。」說完這句,他爺爺就死了。
你大概知道了,哈勇的爺爺是我的曾祖父,哈勇是我爸,撒韻是我媽。我叫鐵木,跟那黑狗一樣的名字。那年我離開部落,要去都市所謂「社會上」闖一下,父親非常不捨,大概思念之故,或者希望我留在他身邊,暫且用狗替代了我。
父親殺完雞,也燒完了毛,手上鮮血沒有洗去,他只在地上抹一下。他面無表情,坐在板凳上抽菸,白煙嬝嬝像鬼魂在他頭頂上方,交錯,扭曲,繚繞。此時,天也亮了。「快來吃飯,我們還要去田裡除草!」母親在廚房喊,父親沒有即時回應。這就是他們每日生活的常態,沒有例外。父親一向沉默寡言,跟他說話,必須等他搞清楚談話的內容,他才適時開口,也就是說,找他聊天,要有耐性,否則真會以為他陰沉冷酷,不好相處。沒辦法,父親總是這個性。後來我逐漸明白實情並非如此,他只有國小畢業,學歷使他感到某種程度的自卑,所以在人面前總不擅言詞,謹慎發言。這也沒什麼不尋常的,哲學一點說法,「自卑是一種無能的體現」,好像說得也很像那麼回事。但,父親並非無能之人,在我看來,這只是鄉下人所具備的質樸個性,個性怎麼說呢?誰也說不清,沒有對錯。他把菸吸短了,看見隔壁的瓦旦正要下田去了,問候了一下,把菸捻熄,就進屋裡去了。
餐桌上,父親夾起一塊他弟弟獵到的飛鼠,嚼出聲音說:「肉很嫩,我很久沒吃到山肉了。」一旁走動的母親,已經吃完飯,拿著抹布在瓦斯爐上擦拭,擦過之處,泛著銀光。母親愛乾淨,稍微一點汙垢塵埃,她看著全身不舒服,一定要動一動。我印象中,母親確實做起家事一點都不馬虎,近乎苛求。我姊我弟的衣物都是母親分類擺齊的,她時常念我們,要求我們自己整理,不過她仍然看不慣,抱怨我們「不會做家事」,最後還是由她承攬一切。這是她作為母親的宿命,古今中外,大概都如此。如果有機會你到我家來坐坐,你會發現地板上的每塊磁磚熠熠生輝,像一面鏡子。
「你兒子鐵木打電話來,聽口氣好像有事,電話裡沒講清楚,你去看他吧!」母親小聲地說,好像在說什麼祕密,怕別人聽見。這個時候父親也吃飽了,把碗筷放下,也不丟到洗碗槽裡。這也像平常的他,幾乎不做家事。身為所謂「戶長」,父親很清楚自己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什麼。這可以理解為他是一個很傳統的人,即女人做的事就由女人,男人不該僭越身分去搶著做,反過來說,道理也一樣。所以,碗筷放在那裡等著母親去收拾、洗刷,在我家是一件極自然的事,無須辯駁。「又吵架啦?」父親疑惑地問。母親沒正面回答,只唯唯諾諾。其實她很清楚鐵木的情況,即本人我,與老婆最近感情不和睦,大吵小吵不斷,有離婚之虞。這都在母親心裡擱著,看在眼裡,她不會讓父親知道得太多。父親是個嚴肅又顧家的人,一旦讓他知道這些事,會徒增其對我的責備。這是母親向來對我呵護有加的措施,我很感激她。
時值秋天,老家後面那棵柿子樹結滿了柿子,有些熟了,大部分還青黃不接,但總的來說,迎著陽光,果實紅彤彤的,由遠處看,蠻像一幅畫,你若想成電影裡什麼童年爬樹的幸福畫面,也是可以的。父親在一個午睡中醒來,赤腳爬上了樹,吩咐在樹下的母親接著。起先母親徒手接,她覺得麻煩,後來想到用身上的衣服兜起一個袋狀,父親朝下丟。的確,這樣有效率,不致使母親誤接而讓果實摔落地面。依此辦法,不到半小時,他們摘了一個麻袋那麼多。那些摘不到隱藏在枝葉其間,或是父親故意遺漏的,就留給鳥獸蟲蟻吧。大自然有其生命規律,動物亦然,牠們也要存活,也要延續下一代。
柿子實在太多,父親與母親當然吃不完。他們如果每餐都各吃一個,當飯後水果,大概可以吃到年底。柿子是這樣的,必須擺放一段時間,自然會熟,熟而變成軟捏捏的,老人家愛吃。據說也可用鹽水泡過,又脆又甜,像蘋果那樣芬芳。多虧有了柿子樹,它默默地貢獻一切它該貢獻的,夏天遮起餘蔭供人乘涼,枝幹可供村裡孩童攀爬,到了秋天則更加努力長出這些果實,其功德實在不小於人類。
父親留著一些,一顆顆妥善放置,在他自製的竹籃裡,待其成熟。其他則分送親友,藉以增加鄰里間的感情,也是不錯。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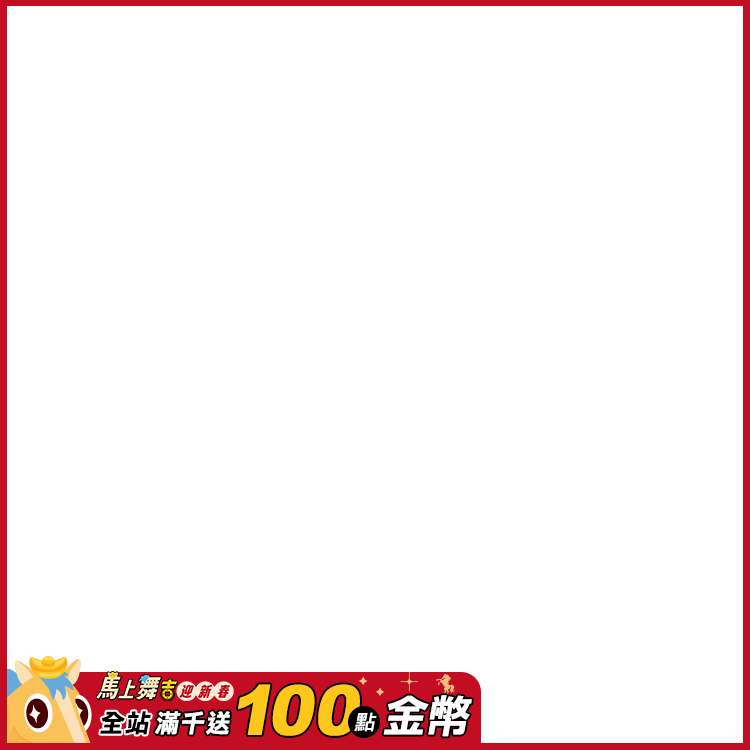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