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些失去救了我
那雙寫作的手始終在發燙,即使摸黑前進,也要繼續寫。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林榮三文學獎得主姜泰宇(敷米漿)首次將自己置於聚光燈下,公開書寫個人生命經驗與疾病,以及寫作這件事之於他的重要性。讀者將跟隨作者的文字,走入一度受困於疾病的時空、洗車的時空、不曾真正離去的寫作時空。
★內容簡介
誰都是不斷失去,然後不斷撿起。
那些逃離的、佚失的、
急欲捨棄的,
最終都去了哪裡?
───────────────────
姜泰宇首度書寫個人生命經驗,
講述疾病、一次次的落隊與歸返。
▎我知道自己沒有第一名的能力與運氣。
▎所以捧著一顆弱者之心,或蹲或站,
▎與黑暗為伍。
「也許我電腦螢幕壞了,我會拿起紙筆。紙筆被偷走了,我會走到海邊,在沙地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若海也乾涸,吹散了沙,我在腦子裡繼續寫。我不會懷疑這件事。而我明白,你們也不會懷疑這件事,在我說完了這些日子我的經歷之後。」──姜泰宇
因為眼疾,他站不久、走不遠,讀書不過三行,更別說書寫。他一度將逃離文壇的自己丟棄,在洗車場與汗水汙泥共度日日夜夜。如今,十五年的洗車人生也將成為記憶……
繼《洗車人家》之後,姜泰宇在第二部散文書寫中,首次將自己擺在聚光燈下,直視老天擲來的一顆顆曲球:寫作巔峰期,罕見的「眼球震顫」發作,震碎一個年輕寫作者的自尊與視力。洗車場人們來來去去,如同人生路上不知何故就走散了的人與事。再次回歸寫作,鼻咽驗出了腫瘤。
曾經雙手插口袋、抬頭看天走路,如今只有隨前方險途過彎,把身子壓低再壓低。而那雙寫作的手始終在發燙,即使摸黑前進,也要繼續寫。
///
像拔著指頭裡的木屑,費勁卻舒坦。
是這些珍貴的失去救了我。
所以我還在這裡。
我自願的。
///
★動容推薦
藤井樹(作家)
_專文作序
吳妮民(醫師、作家)
陳栢青(作家)
曹馭博(作家)
翁禎翊(作家)
廖志峰(作家、允晨文化發行人)
_動容推薦(依姓氏筆劃序排列)
●藤井樹(作家):
當你以為場景是他的洗車廠,其實場景是他這個人那顆討人厭又討人喜歡的心,只是他慷慨地把它蓋成了片場,跟大家說歡迎光臨。
●吳妮民(醫師、作家):
站起又蹲下的生活是血肉,而文字是溫柔覆生的肌膚──姜泰宇的散文是負傷的,他真摯、懇切的文字,寫下生命中曾經的耀眼與滄桑。
《是這些失去救了我》舉重若輕地回望了少年的懺情,初生之犢的意氣,也有被大病和命運重拳搏倒後的頹敗。然而,罹患「眼球震顫」的那雙眼睛並沒有放棄奮力睜開,即使黑暗、即使暈眩。十年沉潛讓姜泰宇明白自己對寫作的熱愛,十五年的洗車生涯讓他更貼近人世冷暖。
然後我們才看見:真正的勇者不是從未被擊倒,卻是被擊倒後,仍然蹣跚地,站起來。
●翁禎翊(作家):
我每天有十分鐘的高鐵通勤時間,照理來說,一本散文集,一次一兩篇,很容易就能閱讀完畢。但《是這些失去救了我》不容我這麼做。最優秀的小說家掏出真心說自己的故事,幾個場景、幾句話,便能讓人有掉淚的衝動。這樣百感交集、蕩氣回腸地開啟一天,不好見人。
泰宇哥把自己中年病後重拾寫作比擬為負重前行。你會在這本書裡面看到他負得到底有多重,還有走得到底有多遠。那都是平常笑笑鬧鬧的他,低調誠懇、並且努力至極的證明。
目錄
【聯合推薦】他的文字,是溫柔覆生的肌膚
【推薦序】史上最爛推薦序 ◎藤井樹
【自序】弱者之心
輯一 返程票
桃林鐵路往返票
抵達後的歧路
不念書,啾啾會被蟑螂吃掉
阿凱沒牙齒
六十公分見方
輯二 落隊
走近與視覺的葬禮
病至不老橋
末路
正義市場老將軍
老大哥
再也不能趕時間了
敬你一杯高蛋白乳清
輯三 過彎
大爺的水壺
那些超級跑車們
阿伯,你老婆打電話找你
那個罵我三字經的客人喔
請你幫我簽名
謝謝你沒有嫌棄我的手髒
老鼠的報恩
洗車場的分手擂台
此後洗車無奧客
神奇的算命仙
輯四 請繼續直行
再見阿龍
那個追風少年兄
回收阿伯的逆襲
搶救貓咪大作戰
山姆的沛納海
失而復得的五百元
一個人的洗車場
與蹲姿等長且滂沱
【後記】作家夢──隧道盡頭的微小光束
序/導讀
史上最爛推薦序
◎藤井樹(作家)
因為我不想寫。
我不想寫這篇推薦序,不是因為這本書不好看,而是因為我知道這本書會好看,叫我寫推薦序等於是在彩色鮮花上面澆兩匙鳥屎,遠看像是幾朵白花點綴,近看就會看見那黑白混濁一坨一坨的,散發出來的是一種叫做老創作人的臭味。
是的,我是鳥屎,我有老創作人臭味。
說個故事給你們聽。
我壓根忘了怎麼跟姜泰宇變好朋友的,只記得是先知其名後才知其人,但就算知其人,我也忘了去哪裡知其人。總之我以朋友身分去找他,順便洗車,他以朋友身分跟我喇賽,順便幫我洗車。我們就在他洗車廠後面那個吵死人的空壓機旁邊,交換了很多創作路上一路走來的心得(還有咒罵業界陋習)。
坦白說,姜泰宇書寫得好好的突然去開洗車廠,我很驚訝。我去請他洗車的時候,是有種試探心態的,不知道洗車技術到底怎樣。我心想他一定是寫書當正業,洗車當交朋友,就像人家富二代去當上班族,錢不是重點,交到朋友才是關鍵。
我還真的開口問了,「怎樣?版稅不夠花,洗車比較好賺?」
這時的他跟我就坐在空壓機旁邊,一人手裡一根菸,他微微一笑看向旁邊,那眼神告訴我「這題拎北回答了幾百遍」。
「再怎樣也沒你好賺,你藤井樹欸!」他直接打頭式地問A答B。
然後話題就掉到版稅數字的井裡,回聲與空壓機的聲音在比大小,搭配著煙霧彌漫,菸味籠罩的小倉庫畫面,從彩色變成黑白,就印在腦子裡,直到現在。
「我的眼睛有問題。」他說。
「看醫生了嗎?」
「廢話,當然有,不然我哪會知道它有問題。」
「所以你是因為眼睛的關係不寫了?」
「能寫,我就會寫。」
講完了。
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幾句話,講完了。
雲淡風輕,輕描淡寫。像別人的故事,像隔壁的家事,像從前的小事,像根本不曾發生的事。
很靠北。
但姜泰宇就是個機掰人啊,他喜歡「寫」這件事就像他多愛他老婆一樣,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不然我說真的,他現在這本我正在寫推薦序的書,在我來看,至少是二十年後才會交出來的東西。那東西有個大家熟悉的名字,叫回憶錄。
回憶錄都錄些什麼呢?錄的就像是他這本書在說的,誰走來了,誰走過了,像一部只有一個場景的電影,用所有能用的鏡位,打最複雜的光,講最表面的台詞,演最深層的戲。
當你以為場景是他的洗車廠,其實場景是他這個人那顆討人厭又討人喜歡的心,只是他慷慨地把它蓋成了片場,跟大家說歡迎光臨。
坦白說,身為好朋友寫上面那句話實在讓我想吐,但我又沒辦法盡是用違心之論來逃避我看到的真實。他就是那種一直留在那裡的人,你轉頭他就在,你繞了地球一整圈回來,他還在。
幹,我真的不想寫,因為寫著寫著就是會寫成這樣。
明明他就住我家旁邊,走路三分鐘就到了,為什麼要用這麼遙遠的推薦序,來推薦一個離我很近的人呢?
因為他直接Line我一堆廢話,其實重點就一句:「寫推薦序嘿!乖。」
乖你老師。
最後,米漿啊,我要跟你說。
沙特的「他人凝視」,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它有個深層意涵叫做自由。
一體兩面化的理解後,它也會變自縛。
這個你懂,我懂,獨眼龍也懂。
但我有個看法跟你交換。
「他人」,是在生命終點回頭看你的,你自己。
到時,所有他人的凝視,都沒有「他人」的凝視更有力道,因為「他人」的眼神會問你。
「你是否,不枉此生?」
【自序.節錄】弱者之心
◎姜泰宇
二○○三年出版第一本書,我就是個寫小說的人。一直到二○二○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我都略微害怕那種必須主動站上光線明亮的台前,毫無遮掩的樣貌與手足無措。於是我在書寫洗車生涯時,雖然是當事人,卻總帶著一種旁觀者的姿態,將關於那些人事物的故事,編排得更加故事化。當然這些事本身就很戲劇性,但我始終站在一個俯視的角度,看著那些年的自己。
也許有人說這樣的散文太小說化,但我不在乎。可以書寫關於自己、也提及他者的這些過往,這樣的角度確實在倫理以及真實性上得以兼顧。書寫時候我俯視,然而被書寫之時的我,其實總是蹲姿。
第一個問我有沒有興趣寫散文的,是蕙慧姐。在最初出道的出版社縮編而作品輾轉遷徙到另外一家老牌出版社時,我對她的印象就是,當年去參加韓國書展,記者會上她說,藤井樹的新書出版兩週賣出十五萬本。那是什麼誇張的美好年代。後來她成了我的總編,我陷入健康與寫作的雙重困境,卻突然收到她的邀約。那個晚上在日本料理店深談,我才知道蕙慧姐是我大學的學姐。
她問我,有沒有興趣寫散文,我說我不會。她說你當然會,我花了好長的時間把你部落格文章看完,你應該寫散文。我說我試試看,然後我就停筆了蹲下了,很久之後才站起來。
而當年那個兩週賣十五萬本的傢伙,跑去拍電影,搬到我家附近,三不五時就會拿好東西餵食我。在深夜接到那個當年暢銷天王的電話,都沒有好事,每一次都要我開車去載他,每一次都是他的車子出問題。
於是人生步伐邁得太亂了,那些人這些事有的疏於聯繫,有的兜兜轉轉纏繞一起,我總對大導演吳子雲(過去筆名藤井樹)的暢銷作家說,我小時候都看你的書長大。然後他會罵我三字經。這是真的。我看他的書長大是真的,他罵我三字經也是。
最終我沒有在那時開始散文之路,後來卻也用自己任性的方式寫起了散文,然後寫到如今。總是對洗車的時光感到魔幻,如同我覺得青少年時期的自己像被附身般荒腔走板,洗車這些年總也感覺過分突兀,一如那個十六、七歲,雙手插口袋,走路搖搖擺擺,看似將人生過得精彩,其實相較於很多人是受迫性的人生崎嶇,我多半是自己亂搞,怨不得人。除了生病。而偏偏生病也是其中一個引子,或輕或重,不可言說,只能揣測。
在出版了第一本散文之後,成績還不錯,出版社給我爆滿的情緒價值以及實質幫助,聰明的作者就該一鼓作氣乘勝追擊,而我用流浪狗的眼神看著亞君社長(其實是看著電腦螢幕),不好意思地告訴她,我下一本要寫鬼故事。透過文字我能感受到她愣了一下,好吧,透過文字無法感受這個,但我知道她肯定愣了一下。絕對又愣了第二下,接著告訴我,非常棒,她很期待。我說,如果覺得題材不適合,退稿也沒關係,我會自己想辦法。她說,只會寫不好退回去重新寫好,但稿子她要了。
我曾反思自己為何如此荒謬,思來想去大抵是理解自己的。或者走過寫作的路那麼多年,好長,中間還空白了將近十年,我最恐懼的是從此以後只墮落在這可以被看見的洗車身分。以一個小說作家而言,硬生生將自己活成了那個模樣,即使可以獲取更多注視,卻也帶著遺憾。
創作是一種跟自己的對決,文字上的、精神上的,當然也有理念上的。整整十年不在文學這個地方打滾,於是我可以用更長的視線看向遠方。遠方有霧,也有在懸崖上的美麗小黃花,你敢不敢走過去?
我或蹲或站,拿著拋光機或者抹布。我有一顆弱者之心,相對於強者,我更加明白承認自己不夠強大是勇敢的,明白自己永遠距離第一名有恆常難以打破的距離也是勇敢的。我就那麼勇敢,真是無可奈何。
沒有好好複製回到作家身分的散文,是一種任性,卻也是一種無能。我明白自己辦不到,即使在出版艱困的時刻做這樣不負責的決定很幼稚,但我有耐心可以等待。相較於躲在故事背後的小說家,散文終究需要自己站上舞台表演,而回望人生,卻也逃不了洗車的十五年。可敢想像,那已是我如今超過三分之一的年華。
這次我稍微準備好舞台燈光,直直打在正中央,期許自己可以站在向光處。我總慣於用旁觀者的視線凝望自己,凝望身周所有,以及那些也凝望著自己的他者。這總會讓身體偏離了光線,讓文字充滿了陰影充滿了吞吞吐吐。有人說那是種節制,但我知曉那更多是因為一種膽怯與破口。過往那些年歲的一切我都捨棄了,妄圖重拾片刻都顯得慌張且蒼白。而我需一意孤行。
旁觀者並不是漠視者,而是一種緊貼著監牢鐵欄杆的姿態回望。於是,我果然分不清我在監牢裡或者監牢外,而這恰好也拯救了我;人生如此,寫作當然更是如此。因為分不清此時此刻是被困住,或對被綑綁的過去的探望,於是寫下這些文字。
誰都是不斷失去然後不斷撿起,留下連串腳印卻難以確認腳印的主人。走著走著就再也不見了。我是真的很想知道究竟什麼不見了。畢竟,那些失去的才堆疊成如今的我。直到有一天,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失去。
試閱
〈病至不老橋〉(摘錄)
我的世界陷入混沌的那些日子,我迷上了不老橋。說迷上有些怪,那些日子無法閱讀,遑論寫作,鎮日躲在床上,移動便暈,視差越發嚴重,伴隨著劇烈嘔吐感。但我總想起不老橋,詩人口中的「再也不能再也不能/我們再也不能一起變老」。
最好笑的是,我總能記得那天的午後,我寫完了小說稿件,正鬆一口氣準備從和室椅起身。那些年我維持著最初寫作的習慣,在燠熱的租屋處,和室桌椅,黏在地板上,偶爾盤腿,偶爾勉強伸直,還不清楚何謂腰痠背痛。
我起身,一個懶腰,然後倒下。
那次倒下,我真的起來了嗎?那麼多年了其實尚且無法老實地回答。若那一年那個下午,人生出現不一樣的風景,我會不會走往另外一條路?不明白,我就躺在地上,直到終於恢復意識。以為是低血糖或者暈眩症犯了,正準備下樓,但我看不見。在喊家人前來救我之前,我便不斷地想著,再也不能一起變老了。
寬鬆地敘述起來,不要太嚴格看待,我確實倒下之後沒有爬起來。他們說,跌倒了,爬起來再哭。而我在地上哭完了,也沒爬起來,一直到今天。後來我不知為何一直掛記著不老橋,終於央求了朋友帶我去,他開車,路途遙遠。在這個島的很南的地方,幾個小時的車程我不記得了,路上風景我想看也看不見,處於既不能等待終點,也無法享受過程的狀態。
然後不老橋只是一座小小的橋,我蹲在橋頭拍下照片。不知道那時候為何這麼堅持,在身體已然垮掉的時候任性。
或許我心中也有一座橋,小小的橋,比東港的不老橋更小,而那一年被大水沖垮了。我抱著橋墩左右張望,看不清自己身在何處,要去何方。於是我沒走,我抱著,怨恨但沒有大張旗鼓地怨恨,憤怒卻不敢明目張膽地憤怒。我只是在大水來的時候,在它毫不留情沒有預兆沖來之時,水至不去,水至不去。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
尾生憨呆守信,或者說,只是一廂情願。而我?我等的是什麼,是誰,又在哪裡等著?一概不知。
那不老橋的照片早已遺失在幾次的電腦更換中。那年的我也遺失在某個大雨傾盆的夜裡。當我的世界開始發顫,眼球疼痛之時,我沒有與父母喊痛、喊難受,我只希望母親帶我去醫院。尚未當兵,每個醫生都覺得你要開什麼妄想逃兵的證明,於是每回我講完自己的狀況之後,我都會補上一句,沒有要開什麼兵役證明,我只想治好。
有的醫生說不知道怎麼處理,但拿出尚未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會出現的數位相機,拍下我發病時充滿韻律感的眼球,顫動如同興奮的貓尾巴。顫動的是我的眼球,也是他的手。有的退我掛號,讓我去其他醫院,並且疑惑為何我驗光時度數會不停改變。一下子五百度,一下子一千五百度,一下子八百度。我說我也很想知道。
最後在教學醫院確認病名,醫生向我解釋為何其他醫院很難處理。我做了腦神經檢查、斷層掃描,眼科、神經內科、神經外科,腫瘤科、免疫風濕科,掛了各種號。他說,「眼球震顫」比較麻煩,既是一種疾病,也是一種症狀。中風的人可能會有,外力撞擊造成腦震盪也會有,視神經病變也會,內耳不平衡也會。
既是疾病,亦是症狀,於是束手無策。
改善方法是有的,在眼球上打肉毒桿菌,但醫生說,不一定會好,還可能視覺有些後遺症。我沒打,跟母親說在眼球上插針太恐怖,我不敢。接下來就是無止境的偏方,有蜂針、有針灸、有冥想法,還有收驚。最後我躺在床上,對著天花板伸出我的手,但看不見想抓住什麼。
我總喜歡說一些笑話,關於眼疾的。最喜歡拿當兵的時候來講,例如我的同袍會架著我去連集合場集合,像晴天娃娃,然後再把我放在位置上,像下象棋。實際上在好轉到足以入伍之前,從來不是那麼樂觀幽默的。我不是,絕對不是。
我重複對自己說,我連續十七週書店排行榜第二名,第一名是《哈利波特》,我輸得心甘情願。那是我國小畢業後,人生距離拿第一最靠近的一次。我對自己說,我寫作出道即巔峰,然後走下坡,所以我明白走上坡雖然累,但下坡傷膝蓋,我寧願上坡。
這種自我催眠式的反覆內耗,無非是為了讓自己振作,豈料達到反效果了。我幾乎一蹶不振,然後不停問老天爺,為什麼是我?為什麼不是別人?我明明很努力沒偷懶。以為在問天,其實在問自己。如果我回答不出來,那麼答案必定很傷人。不,很傷自己。
一直到我重新站起來,扶著牆慢慢走,我大約花了八個月。重新與眼疾共處,時常注意會不會突然眼睛顫抖起來,不管何處我都要停下來。我的遙控器暫停鍵壞了,或者說,遙控器被拿走了,暫停不是我能控制的。這樣也好,從大學時期趕緊趕忙,追著寫作的夢想,也該放慢腳步。而放慢等於漸漸走失的這件事,我當時並不知道。我以極緩慢的速度恢復寫作,在那之後努力寫了幾本小說,他們不清楚但我知道,作品很多瑕疵,但唯一能讓我往前走的也只剩下這件事了。
一直到我真正脫離了寫作,成為洗車場老闆,意外地讓眼睛得到充分休息,是失去也是一種獲得。如同它是個症狀也是個疾病一般。身體關節的磨耗與肌肉的反覆折磨,偶爾加班至深夜只能拿意志力去拚搏,我很熟悉。無數個夜裡,我一個人面對電腦螢幕。就這樣,是一種放逐亦是假裝的豁達。
相較患病之初那種恨天恨地,從作家變成勞動者的我,不恨天地,只恨有時洗車機故障。不恨天地,只恨員工又突然消失。恨的沒少,但也沒多。
刻意不走入書店,也不再買書。閉口不提那眼睛怎麼了,卻學會了如何用淘汰的牙刷將指縫洗乾淨。每次都說,正在寫新的作品,然後寫了十八個字之後就關掉檔案,因為恨的沒多,但也不少。那幾年我的閱讀都是中國網路小說,尤其修仙小說,那千篇一律的屌絲逆襲橋段看得我人生充滿了無盡希望。勤勞時候一年可以看幾千萬字的網路小說,有些看完便忘,有些還沒看就知道自己不會記得。
當有人說我出道很久我總會疑惑,中間空白了那麼多年,不必扣掉嗎?我總說,我就是在二○二○年重新回到寫作行列的時候出道。並非一個全新的我,而是被餽贈了第二次的機會,是個全新的我,所以我很珍惜,我總戰戰兢兢。
讓我回來的是台北文學獎,入圍了,一年後將作品寫完,再做最後一次競爭。
我知道我始終沒有第一名的能力與運氣,所以結果我並不意外,這不僅是對手太強,也是自己太弱。然後覺得臉紅,後悔自己當時敲鑼打鼓自己得獎,從那時開始,才明白我或者從來沒有好好爬起來,一直趴在地上耍賴,連快樂都變得不敢大張旗鼓。
我猜是眼疾讓我習慣了摸黑過巷,與黑暗為伍久了,便不怕鬼了。鬼永遠是自己,只能是自己。我開始學會躲在角落暗自開心,小小的、用氣音,用慣常沒有表情的,才能不害怕。我其實沒特別失敗,即使成績無法與當年剛開始寫作相比。能重新走上脫隊的行列,當年與我同行的人已經面向大海背朝光,一片光明在眼前。而我……
也曾想仗劍走天涯,後來工作忙,沒去。
我喜歡這插科打諢的話,很喜歡。
雖然晚了,但我回來的路很平順。一切都那麼好,都那麼開心。我是那麼珍惜,如同當年剛出道,做夢都會笑。當你可以做著自己喜歡的事,而因此賺取的生活的金錢,那是多麼幸福。
便是在此時,健康檢查通知我,CEA(癌胚抗原)指數過高。建議再次分項逐一精密檢查,包含鼻咽、肺部,以及大腸。
我掐指一算,肺部感覺很麻煩,大腸鏡聽說很痛苦,於是我選擇一個不至於出問題的鼻咽檢查。鼻咽鏡如同疫情這些年大家熟悉的捅鼻子快篩,只是捅深一點,直達口腔。
醫生說,你有一顆腫瘤,我們切片看一下,大約小拇指一半大小。政府的健保快易通APP上,註記著「鼻咽良性腫瘤」,不是惡性,我點點頭。但腫瘤有點大,每年都要檢查,我說好,同時轉過身去看看自己,看看那個曾被疾病擊倒卻不曾起身的自己。他還趴著呢。雙手撐在下巴,饒有興致地看著我,眼睛眨啊眨地,好像會說髒話一樣。
(全文未完,詳見本書)
〈老大哥〉
老大哥經常在店外徘徊,額頭很高,身高也高,方方的臉頰總是感覺咬牙切齒,咀嚼肌很發達。那時候師仔總是會笑,說老大哥可能檳榔吃了四十年,所以咬合力道很強。
最開始,老大哥在店門口走來走去,我們總以為他是在等人。後來覺得有點不對,開店做生意最怕就是無法掌控的風險,總會派一個人靠近店門口,看看那個老大哥大概要做些什麼,是拿放置在門口的回收物呢?還是要詢問我們的服務呢?但每一次想湊上前去,老大哥就會笑笑地揮手,然後離開。
洗車場門口的地板總是濕,偶爾會積水。老大哥站在那裡,感覺不違和,彷彿那太陽照射之後會反射陽光的地板,就是他的舞台,來回的腳步如同貓步。直到我後來問起,老大哥才跟我說,他實在不好意思為難我們,知道自己年紀較大,但就想碰碰運氣,也想先看看這店裡做事的方法,自己能否適應。
老大哥那時做汽車美容快二十年了,一身傳統汽車美容的功夫或許就是他賴以為生的本錢。「我有兩個小孩,老婆身體不好沒辦法工作,原本做的店又收起來了,想找一個可以發揮所長的地方。」老大哥這樣說。
我問了老大哥,原本的店怎麼會收起來,想要以此警惕自己,居安思危。「這幾年洗車場不一樣了,」老大哥幽幽地嘆了口氣,「本來很穩定,附近卻開了很多新的店,噱頭也多。跟老闆說要改進設備,老闆也不想。最後客人都跑掉,老闆要扣薪水,我也認了,最後還是支撐不下去。」
超過十年了,老大哥說。大約是自己最青春、最有精力的歲月,都耗在那個只有兩個車位的小洗車場,日復一日,好像自己扎了根一樣。我明白這種感覺,好像我們身軀是自由的,在這個世界漫無目的地走啊走,實際上卻被綁在小小的一方園地,走的、想的、做的,也都是黏著在這潮濕陰暗的地方。
看著老大哥,我已經想像得出自己多年後的樣貌,好想踏步離開,但地板極黏,踏出一步都千難萬難。老大哥是怎麼鼓起勇氣走進來的呢?我並沒有開口詢問。
對於新的鍍膜產品,老大哥也是一知半解,以為就是傳統的大美容。那一天下著雨,老大哥可能覺得下雨過來比較不會打擾我們,我親自在老大哥面前,示範我們的施工方式。換上新的拋光綿,老大哥好奇地低下頭仔細看。
「想摸摸看嗎?」我說。
「可以嗎?」老大哥伸出手,仔細搓揉著新款海綿,如同我們,習慣性地去感受海綿的粗細、角度。
我說,傳統的拋光方式,跟我們如今做法不大相同,海綿不可以斜置,必須與漆面平行,才能避免金油層推擠。
老大哥眉頭一皺,不多說話,靜靜看著我施工、解說。
「這……有點麻煩啊。」老大哥說。傳統習慣斜放海綿,所以很多車子鈑件的轉折處可以直接帶過去,現在必須平放,就得在一個小部分慢慢拋光。
我果斷地把拋光機遞給老大哥,讓他親手嘗試一下。不到五分鐘,他的眉頭更加糾結了。
「老闆,這跟我會的方式,差別有點大。唉……」他說。
我點頭,沒有多說什麼。差別很大可以重新學習,但又有幾個人,可以打破自己擅長的溫暖世界,重新面對嶄新的技術?那彷彿否定了過往自己的生存價值,如同那麼多年在那洗車場的時光,瞬間變得毫無意義。
我是很想讓他來我這裡試試看的。但我或者低估了那種世界毀滅一般的新知,對於這種老師傅帶來的衝擊。老大哥跟我聊了很多,這幾年面對過的客人、自己現在的經濟壓力、乍看到新技術的衝擊。
「變化太快了,太快了。」老大哥離開前,跟我道謝,眉頭糾結。
我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他,面對變化,我自己也經常手足無措,唯有接受,唯有改變自己。但,這談何容易。
中年失業是一種負重前行。
重量除了來自於生活那莫大的壓力,還有過往自己背負的一切驕傲。也因為這驕傲,讓前行步履蹣跚。我真的懂,所以不想再失去一次。但也因為不想再失去,於是綁手綁腳,於是裹足不前。終於困在這一畝三分地,打滾在泥濘中,再也脫離不了。
再次看見他,那堅毅咀嚼肌,是在一個工地的門口。老大哥頭戴工地白色安全帽,拿著指揮棒引導水泥車。我沒有停下車跟老大哥打招呼,因為我們都不容易,遠遠看著老大哥,一個紅燈的時間,也足夠我與他在時空之外敘舊了。
老大哥拋下了過往引以為傲的技術。
我想著,接下來我應該何去何從?這一塊地面太潮濕也太黏膩,不知道能不能離開。而離開了,耗費了人生十多年在這個行業的我,還有哪裡可以去呢?
到頭來,我以為自己是有用的人,其實是很容易被取代的,無用的人。
我想我完全理解老大哥。
那一年離開寫作的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我還有地方想去,即使負重前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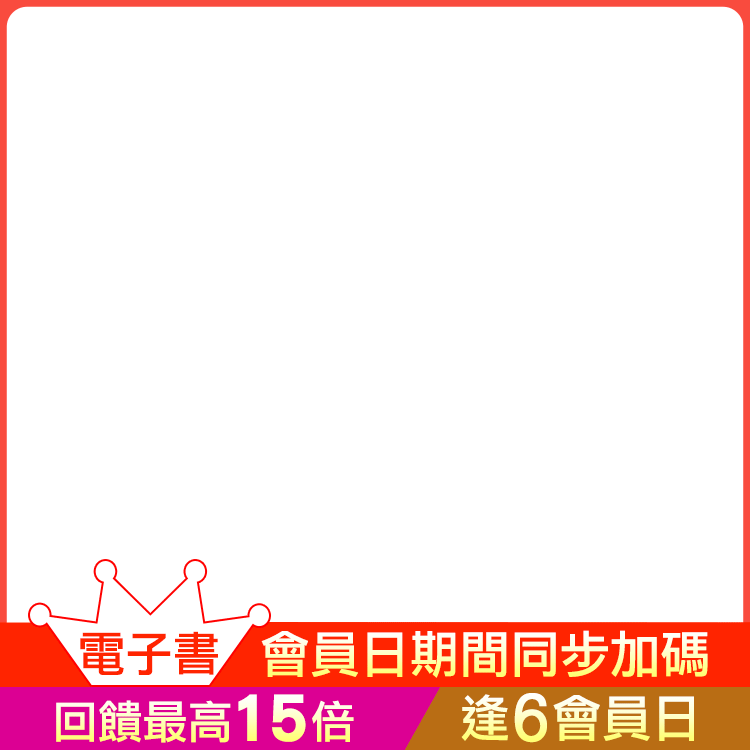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