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然後呢?
More Than This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卡內基獎決選作品!
所謂地獄,就是永遠孤獨地困在最慘痛的回憶中嗎?
除了生與死、天堂與地獄,生命是否還有其他選擇?
充滿詩意與哲思,令人揪心落淚的故事,
今年最別出心裁的科幻小說!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作者,約翰‧葛林:關於內容,我不再多說什麼,讀就對了。
冰冷狂暴的海浪攫住賽斯,耍弄著他。然後,毫無預警地,大海最後一次緊抓著他,將他的腦袋撞上礁岩。他痛得眼前一片漆黑,現在就連試著游泳、抵禦海水的力氣也沒了,只能任憑海浪再次將他傾覆。
他的頭蓋骨裂開,碎片插進腦中,數節脊椎被壓碎,切斷了腦動脈與脊椎神經,這麼嚴重的傷勢,救不了也回不去。一點機會都沒有。
他就這麼死了。
然後……
賽斯睜開雙眼,再次醒來,發現自己赤身裸體、渾身瘀傷,但似乎還活著。這是怎麼回事?眼前的一切如此熟悉,但為何他對此全無記憶?
這個屋舍傾圯、頹敗荒涼的地方,是地獄、來生,或是世界終結後的樣貌?
賽斯努力探索,想弄清頭緒,但隨著記憶逐漸浮現,疑團卻越來越多。直到這天,在這理應只有他一個人的專屬地獄中,出現了另一個身影,也為背後的真相帶來一線曙光……
名人推薦
全球媒體一致讚譽
派崔克•奈斯漂亮地以反差概念:生與死、隱私與曝露、罪惡與純真,交出這部作品。這位「噪反三部曲」作者以其獨特風格,在這個故事如夢魘般的情境中進行一場人類心靈的存在主義式探索。──寇克斯書評雜誌
被人用「令人驚豔」形容的書中,這是少數能讓我讀得連連高聲驚呼:「天哪!」的幾本……關於內容,我不再多說什麼,讀就對了。──《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作者,約翰‧葛林
一個節奏洗鍊、情節令人難忘的出色故事。──波士頓環球報
對話生動,情節懸疑,劇情曲折離奇又寓意深遠。──週日泰晤士報
驚魂動魄,提出質疑且富含哲思,令人印象深刻……從故事開始到最後,無不扣人心弦。──每日電訊報
起初令人極度不安,繼而讓人振奮不已的故事。──觀察家報
令人無法放鬆,始終緊抓住讀者不放。──每日郵報
派崔克•奈斯超越了自己。──衛報
這個複雜而讓人心驚膽顫的故事,正足以證明派崔克•奈斯得以屢屢獲獎的文學才華。──金融時報
情節緊湊、突破想像邊界、極具挑戰性。──書商雜誌
派崔克•奈斯在眾多角色與複雜情節間交錯的敘事手法能引人入勝,得歸功於他對青少年成長時的痛楚與渴望抱持的高度同理心。──愛爾蘭時報
我的本年度第一愛書。──Simon Mayo,BBC電台「賽門•梅約讀書會」顧問
一個極大膽而不尋常的故事,優美文筆中帶著濃厚的憂傷。引人感嘆、後勁極強、並令人心痛。──英國圖書信託基金會
試閱
男孩溺水了。
在這最後關頭,奪走他性命的不是海水,而是寒意。無論他多努力掙扎要浮上水面,寒意卻抽乾體內的所有精力,迫使肌肉痛苦收縮、失去作用。他年輕力壯,將滿十七歲,但寒冬的浪濤一波波向他襲來,每波浪潮似乎都比前浪更猛。海浪拍得他暈頭轉向,將他翻轉傾覆,害他越來越往下沉。儘管他抓住幾秒鐘驚駭地破浪而出、喘了幾口氣,可是身子抖得厲害,吸不到一半空氣又往下沉。空氣不夠用,越消耗就越少,他內心渴求更多卻徒勞無功的同時,也感到肺部一個勁地巴望著空氣。
現在他慌了手腳。他很清楚,自己漂得離岸邊有點遠,遠到回不去了,酷寒的潮水以一波波海浪把他越拉越遠,推向使這條海岸線危機四伏的礁岩。他也知道不會有人及時發現他失蹤,不會有人在海水將他吞噬前有所警覺。他也不可能運氣好到獲救。不會有海邊拾荒的流浪漢或遊客從岸邊潛入水中救他,這個時節不會有的,天寒地凍下不會有的。
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
他死定了。
而且會孤伶伶地死去。
教人措手不及、毛骨悚然的覺知更是令他發慌。他再次嘗試浮出水面,不敢去想這或許是最後一次,其實也什麼都不敢多想了。他強迫雙腿踢水,強迫自己用雙臂上撐,起碼回復頭上腳下,想辦法從咫尺之遙的水面吸到一口氣──
無奈波瀾太猛。讓他揪心地靠近水面,卻在能破浪而出前拽得他上下顛倒,把他拖向礁岩那頭。
海浪耍弄著他,他再次嘗試。
再次失敗。
然後,毫無預警地,大海好像一直玩不膩的這個遊戲,讓他勉強呼吸、誤以為自己能撐過去的殘酷遊戲,彷彿要宣告結束了。
一陣洶湧波濤將他撞向無比堅硬的礁岩。即使在水中,即使在奔騰的浪潮中,他也能聽見啪一聲,右肩胛骨高聲斷成兩截。劇痛的生理反應大到讓他放聲慘叫,口中瞬間湧入帶鹽味的冰冷海水。他嗆得猛咳,但弄巧成拙,只是將更多海水吸進肺中。他疼得肩膀直縮,錐心刺骨的痛使得眼前一片漆黑,全身也隨之癱瘓。現在他就連試著游泳的力氣、抵禦海水的力氣也沒有,只能任憑海浪再次將他傾覆。
拜託,他就這麼一個念頭。就這麼兩個字,在他腦中迴蕩。
拜託。巨浪最後一次緊攫住他。像準備扔擲般往後一拉,直接將他的腦袋撞上礁岩。他就這麼迎頭撞上,身後彷彿有隻怒海狂濤全力一壓的巨手。他甚至連舉起手,試圖緩和那一擊的力氣都沒有。
撞擊點在左耳正下方。頭蓋骨裂開,碎片插進腦中,衝擊力也壓碎第三與第四節脊椎,切斷腦動脈與脊椎神經,這麼嚴重的傷勢,救不了也回不去。一點機會都沒有。
他就這麼死了。
***
對男孩來說,剛死的階段是一團亂糟糟、沉甸甸的朦朧。他依稀感到疼痛,但主要是覺得累到無以復加,像是被一層又一層厚到極點的毯子罩住。他盲目地試圖掙脫,但揮動手腳只(再次)令他恐慌,對於彷彿束縛著他的隱形繩索恐慌。
他腦袋不清。思緒發像高燒般疾馳狂悸,他甚至對思想毫無覺察。這比較像是種狂亂的、垂死的直覺,害怕將要面臨的事,害怕已經發生的事。
害怕他的死亡。
彷彿還能奮力一搏,還有機會跑贏對方。
他甚至依稀感到一股衝勁,身體繼續抵抗海浪,即使那場仗已經打輸。他感覺一波駭浪頓時湧現,將他往前、往前、往前推,可是他一定得想辦法掙脫束縛。因為,在黑暗中盲目掙扎的同時,肩膀已不再疼痛,他對什麼都沒感覺,唯獨那必須移動的駭人迫切感──
接著,他感覺臉涼涼的。幾乎像是微風徐拂。不過有太多理由可以證明這不可能發生。冰涼的感覺使他清醒過來──使他的心靈?他的魂魄?還是什麼來著?──在瘋狂的旋轉中暫停。
這一剎那,他靜止不動。
眼前的陰鬱有了變化。亮了起來。有道無法言喻,但覺得可以進入的光亮,他感覺自己倚向那頭,他那如此虛弱、幾近失能的身體,向增強的光亮靠近。
他跌落。落在一個堅硬的地方。冰涼感升起,他允許自己陷入,任它將自己裹緊。
他靜止不動。放棄掙扎。任憑自己陷入昏沉。
那昏沉宛如煉獄,是灰色的。他還算有意識,沒有睡著但也不太清醒,彷彿與一切脫節,無法移動、思考、接受輸入,只能被動地存在。
無法計算的時間過去了,是一天、一年、或甚至永恆,究竟多久他無從得知。最後,那道光在遠方慢慢地,微乎其微地有了變化。某個灰色的東西冒出頭,接著幻化成淺灰,他漸漸回過神。他的第一個念頭,但應該說是依稀意識到而非清楚思考,是感覺自己貼著水泥磚。他朦朧察覺身子底下有多涼、多硬,他好像得緊扒著不放,免得飛向外太空。他不確定自己繞著這念頭轉了多久,讓它變得清晰,讓它與身體相連,與其他念頭相連──
停屍間這三個字在他內心深處倏地閃過──不然你還會躺在什麼冰涼堅實的塊狀物上──隨著恐懼加深,他猛地睜眼,這才發現眼睛一直閉著。他試著嘶吼,要他們千萬不能把他埋了,千萬不能解剖他,說這是天大的誤會。無奈喉嚨像是多年沒用過似地,不願組構詞句。飽受驚嚇的他咳著坐起身,兩眼混濁、霧濛濛地,宛如透過層層厚重的髒玻璃去看外面的世界。
他不斷眨眼,想看個清楚。周圍的影像漸漸成形。他發現,自己並非躺在停屍間的板子上──
而是在──
而是在──
他到底在哪裡?
迷惘中,他瞇著眼痛苦地望著高升的日光。他環顧四周,努力消化,去看、去理解。
他好像躺在一條鋪在房子前院的混凝土步道上,步道從人行道一路延伸至身後的大門。
但這不是他家。
而且,不對勁的事還不只這一樁。
他用力到幾近喘氣地呼吸了一會兒。他思緒茫然,視線逐漸變得略為清晰。他感覺自己打著寒顫,用雙臂環抱自己,感覺有東西濕濕地附在他的──
這不是他的衣服。
他低頭一看,只是生理反應趕不及下指令的念頭。他又瞇起眼,設法看個仔細。這些好像根本不是衣服,只是幾條勉強可稱為襯衫或褲子的白色布料,與其說是衣物,其實更像緊黏在身上的繃帶。而其中一側,繃帶濕了──
他止住念頭。
不是被海水弄濕的,不是浸在他剛──
(溺斃)的,又鹹又冷的海水。
而且身子只濕了一半。另一半,貼著地的另一半雖然冰涼,卻挺乾燥。
他左顧右盼,困惑得不得了。因為唯一可能沾濕他的只有朝露。太陽低垂,看樣子肯定是早上。他甚至可在身子底下一直躺著的地方認出一塊乾掉的輪廓。
彷彿他在那裡躺了一整夜。
但是不可能呀。他對冬季酷寒的海水記憶猶新,頭頂深灰色的冰冷天空絕不可能讓他撐過一晚──
但天空變了樣。他抬頭一望。這根本不是冬季的天空。他覺得冷只是因為清晨的寒意,這說不定是風和日麗的一天,說不定是夏天。跟海灘的凜冽冷風天差地遠。跟他──
跟他死去當下天差地遠。他又花了點時間呼吸,可以的話,只做呼吸這個動作。圍繞他的只有沉默,只有他自己發出的聲音。
他慢慢轉身,目光再次落在那棟房子上。等雙眼越來越適應光線,幾乎像是等它重新適應「看」的動作時,房子的模樣也越來越清晰明朗。
接著,穿過迷濛的五里霧,他感覺被層層裹住的心微微一顫。
輕輕一拂、一個暗示、輕如一片鴻毛的是──
是──
是熟悉感嗎?
***
他試著起身,熟悉感消失了。起身好難,出奇地難,他也果真起不來。他感覺身體虛到一點力氣也沒有,肌肉連最簡單的指令都執行不了。光是把腰挺直坐好就讓他上氣不接下氣,他還得暫時停止動作,再歇口氣。
他又試著起身,儘管一度晃得厲害,但終究成功了。他腦袋無力,有如千斤重,身子仍舊直打哆嗦。包覆他的白色繃帶豈止不保暖,更令他猛然驚覺的是,其實自己衣不蔽體。他的兩腿、軀幹和雙臂被緊裹著,整個背部也大半如此。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從肚臍一直到大腿中段,無論正面背面,這一整片都赤裸裸地面對世界,最私密的部位也教人難以置信地露在外面迎接黎明。他瘋了似地想把襤褸布料往下拉以遮蓋私處,可是那幾塊破布卻緊黏著皮膚。
他只好用手遮擋,東張西望,看看有沒有被別人瞧見。
但這裡沒人。一個人都沒有。
這是一場夢嗎?他不禁暗忖,那幾個字宛若從千里之遙的彼端,慢慢向他游來。死前的最後一場夢?
每座庭院都跟這裡一樣雜草蔓生。幾戶有草坪的人家,如今草已長到及肩高,好似片片原野。
路上停著車,可是車子覆滿厚重的塵土而且幾乎每輛車都因洩了氣的四個輪胎而下陷。
眼前毫無動靜。沒有車子駛過馬路,而且從野草的外觀看來,已是經年累月沒有來車。他左邊的馬路不斷延伸,最後與一條更寬的大街會合,看樣子那是條熙來攘往的大馬路。不過路上也沒有行駛的車輛,他還看見路上開了個四、五十呎寬的巨洞。洞裡似乎長了一整片野草。
他仔細聽。但哪裡都聽不見引擎聲。這條街沒有,下條街也一樣。他等了好久。等了又等。他望向右邊的馬路彼端,視線穿過兩棟公寓樓房間的夾縫,看見突起的火車鐵軌,彷彿等著要聽可能駛過鐵軌的火車。可是沒有火車。
也沒有人。
倘若現在真如看起來的是白天,照理說人們會走出家門,開車上班。不然也該出門蹓狗、寄信、上學。
街上應該車水馬龍。大門應該開了又關。
可是,連個人影也沒有。沒有車、沒有火車、也沒有人。
如今,他的心和眼都稍微更加清晰,所以連這條街的地形看起來也怪怪的。房子全都擠在一塊兒,緊貼成一條線,沒有車也沒有寬敞的前院。每隔四、五間房子只能見到窄得不能再窄的巷弄。一點都不像他家那條街。其實看起來根本不像美國會有的街道。看上去幾乎──
看上去幾乎像在英國。
那兩個字好似金屬相擊,不停在他腦中迴響。感覺挺重要的,彷彿迫不及待想把什麼拴住鎖緊,無奈他的思緒太混亂、太震驚、太困惑,那兩個字只是徒增焦慮。
那兩個字很不對勁。不對勁到了極點。
他身子微晃,得倚著其中一叢看似較結實的灌木才能保持平衡。他有種強烈的欲望想要進門,想找東西遮掩自己的赤身裸體,但這房子,這房子──
他對它蹙起眉頭。
這房子怎麼了?
出乎意料的是,他還沒感覺下定決心,就邁開蹣跚步伐走向它,差點跌跤也無所謂。他還是無法清楚辨析自己的思緒。他說不上來究竟為何要走向那間房子,為什麼出於某種本能之外的東西想要進屋、想要躲避這詭異荒涼的世界;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一切,無論是什麼,都像一場夢,只有夢裡的邏輯才說得過去。
他說不上來為什麼,但這房子就是吸引著他。
所以他往前走。
他走到大門前梯,跨過第一階上的裂縫,最後在門前駐足。他在門前靜待片刻,不曉得接下來要做什麼,不確定要怎麼開門,或假如門鎖上了要怎麼辦。雖然如此,他還是伸出手──
微乎其微地輕輕一推,門開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條長廊。這時陽光燦爛耀眼,照亮身後晴朗的藍天──天氣暖到肯定是某種樣貌的夏天,暖到他感覺烈日在曝露的皮膚上灼燒,他過於暗淡白晳的皮膚經不起這麼毒的陽光照射──不過,即使在陽光普照下,長廊過了一半之後也幾乎消逝在黑暗中。他只能辨出盡頭有道樓梯通往樓上。樓梯前的左方是通向主廳的門。
屋裡沒有燈光,也沒有聲響。
他再次環顧四周。還是一樣,哪裡都聽不見機器和引擎單調的運作聲,但這也是他第一次察覺,這裡沒有蟲鳴、沒有鳥叫,就連微風拂過葉面的聲音也聽不見。只有自己的呼吸聲。
一時之間,他只是杵在那裡。他感覺自己病入膏肓,如此虛弱、如此疲憊,幾乎可以直接躺在門階上睡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永遠不要醒來──
但他選擇踏進屋內。雙手扶牆好穩住身子,緩步向前,好像每一秒都可能被人攔下,都會聽見有人質問他為何擅闖這棟怪屋。不過,他踉踉蹌蹌步入暗影的同時,縱使雙眼無法按常理迅速適應光線變化,卻能感覺腳下的地面積了厚厚一層灰,可想而知,這裡似乎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待過了。
越往內走就越暗,說也奇怪,那道透進敞開大門的陽光,竟然什麼也沒照亮,只讓陰影在他朦朧的眼前顯得更暗更險惡。他摸索前行,能看見得越來越少,抵達樓梯底層時,他身子一轉,這時還是悄然無聲,不只沒有居家的聲音,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他自己。
形單影隻的自己。
他在客廳門口駐足,感到新一波恐懼襲來。螫伏在黑暗中的可能是任何東西,靜靜等他自投羅網的也可能是何東西,但他強迫自己往裡看,讓雙眼適應光線。
適應之後,一切盡收眼底。
幾束充滿灰塵的陽光射進他面前拉上的百葉窗,他藉光看見一間簡樸的客廳,與右邊開放式的餐廳合而為一,通往一道門,穿過門即是位於屋子後方的廚房。
屋裡有家具,跟一般房間沒兩樣。不同的是,家具都蒙著好厚一層灰,活像上頭多鋪了一塊布。仍舊精疲力竭的男孩,努力把這些形體跟腦中的字彙兜在一塊兒。
他的雙眼越適應光線,房間就越能展現原貌,不僅開始成形,細節也一一顯露──
壁爐台上那匹尖叫的馬浮現眼前。
一隻狂亂的眼,鐵釘般的舌頭,困在一個燃燒的世界,從畫框裡看著他。
直視他。
一見著牠,男孩立刻放聲驚叫,因為這下全都水落石出,他知道了,他知道,在疑慮的陰影背後,真相如浪潮襲捲而來。
他知道自己在哪兒了。
***
他以這雙疲憊的腿僅剩的力量盡快跑開。男孩搖搖晃晃退回走廊,掀起的朵朵塵雲直奔陽光的樣子,就像──
(就像溺水的人探頭吸氣──)
他能依稀聽見自己的哀嚎,但仍說不出話,字句仍未成形。
可是他知道。
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
他蹣跚步向大門前的階梯,幾乎無法站直身子,後來也真的站不住了。他跪倒在地,使不出力氣起身,彷彿剛才的頓悟是壓在背上的一塊大石。
他倉惶地望著房子,覺得身後一定有什麼東西、什麼人尾隨著,追逐著他──可是啥都沒有。
還是半點聲音都聽不見。機器運作聲、人聲、蟲鳴聲獸吼聲,全都沒有。這個世界萬籟俱寂,靜到他能聽見自己胸膛下的心跳聲。
他暗忖:我的心。這幾個字俐落地劃破他思緒中的一團迷霧。
他的心。
他那枯槁的心。他那溺水的心。
他不寒而慄,因為他看見的可怕真相,那可怕真相背後的意義,開始將他吞没。
這裡是他的老家。
好多好多年前住的老家。英國的老家。母親說什麼都不願再多看一眼的家。他們飄洋過海、換了一個大陸才擺脫的家。
但是不可能呀。他好多年沒見過這個家、或這個國家了。小學畢業後就沒見過了。
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
自從他弟弟出院後就沒見過了。
自從最教人不堪回首的事發生後就沒見過了。
他暗忖道:不要。
不,拜託不要。
他知道自己人在哪兒了。他知道為什麼會在──
在死後,來到這裡,在這裡醒來。
這裡是地獄。
專為他所打造的地獄。
一座他得注定孤單的地獄。
直到永遠。
他斷氣之後,在個人專屬的地獄中醒來。
他吐了。
他往前一撲、雙手撐地,將胃裡的殘留物吐進步道旁的灌木叢。費力嘔吐使他淚眼汪汪,儘管如此,他仍能看見自己吐了一片詭異而清澈的凝膠,嚐起來略帶甜味。他吐個沒完,直到最後精疲力盡,反正他早已淚眼婆娑,似乎離哭泣也相去不遠。他開始掉淚,最後直接往混凝土地面頹然倒下。
他一度像是重溫溺水的感覺,渴望著呼吸,抵抗著比自己強大、一心只想把他往下拽的力量;他根本打不過,怎樣也阻止不了它,只能任它將自己吞噬,使他在世間消失。他躺在步道上,把自己交給對方,就像海浪不斷要他棄械投降那樣──
(差別在於,他的確曾與海浪一較高下,一直拚到最後一刻,真的。)
然後,打從他初次睜眼後就不斷威嚇的疲倦感,終於將他擊潰,他也因此陷入昏迷。
越漂越遠,越漂越遠,越漂越遠──
***
賽斯睜開眼。
他仍躺在混凝土步道上,蜷著身子,抵著硬梆梆的地面讓他因為僵硬而幾近抽搐。他暫時一動也不動。
賽斯,他心想。我叫賽斯。
在這最後關頭,奪走他性命的不是海水,而是寒意。無論他多努力掙扎要浮上水面,寒意卻抽乾體內的所有精力,迫使肌肉痛苦收縮、失去作用。他年輕力壯,將滿十七歲,但寒冬的浪濤一波波向他襲來,每波浪潮似乎都比前浪更猛。海浪拍得他暈頭轉向,將他翻轉傾覆,害他越來越往下沉。儘管他抓住幾秒鐘驚駭地破浪而出、喘了幾口氣,可是身子抖得厲害,吸不到一半空氣又往下沉。空氣不夠用,越消耗就越少,他內心渴求更多卻徒勞無功的同時,也感到肺部一個勁地巴望著空氣。
現在他慌了手腳。他很清楚,自己漂得離岸邊有點遠,遠到回不去了,酷寒的潮水以一波波海浪把他越拉越遠,推向使這條海岸線危機四伏的礁岩。他也知道不會有人及時發現他失蹤,不會有人在海水將他吞噬前有所警覺。他也不可能運氣好到獲救。不會有海邊拾荒的流浪漢或遊客從岸邊潛入水中救他,這個時節不會有的,天寒地凍下不會有的。
現在說什麼都太遲了。
他死定了。
而且會孤伶伶地死去。
教人措手不及、毛骨悚然的覺知更是令他發慌。他再次嘗試浮出水面,不敢去想這或許是最後一次,其實也什麼都不敢多想了。他強迫雙腿踢水,強迫自己用雙臂上撐,起碼回復頭上腳下,想辦法從咫尺之遙的水面吸到一口氣──
無奈波瀾太猛。讓他揪心地靠近水面,卻在能破浪而出前拽得他上下顛倒,把他拖向礁岩那頭。
海浪耍弄著他,他再次嘗試。
再次失敗。
然後,毫無預警地,大海好像一直玩不膩的這個遊戲,讓他勉強呼吸、誤以為自己能撐過去的殘酷遊戲,彷彿要宣告結束了。
一陣洶湧波濤將他撞向無比堅硬的礁岩。即使在水中,即使在奔騰的浪潮中,他也能聽見啪一聲,右肩胛骨高聲斷成兩截。劇痛的生理反應大到讓他放聲慘叫,口中瞬間湧入帶鹽味的冰冷海水。他嗆得猛咳,但弄巧成拙,只是將更多海水吸進肺中。他疼得肩膀直縮,錐心刺骨的痛使得眼前一片漆黑,全身也隨之癱瘓。現在他就連試著游泳的力氣、抵禦海水的力氣也沒有,只能任憑海浪再次將他傾覆。
拜託,他就這麼一個念頭。就這麼兩個字,在他腦中迴蕩。
拜託。巨浪最後一次緊攫住他。像準備扔擲般往後一拉,直接將他的腦袋撞上礁岩。他就這麼迎頭撞上,身後彷彿有隻怒海狂濤全力一壓的巨手。他甚至連舉起手,試圖緩和那一擊的力氣都沒有。
撞擊點在左耳正下方。頭蓋骨裂開,碎片插進腦中,衝擊力也壓碎第三與第四節脊椎,切斷腦動脈與脊椎神經,這麼嚴重的傷勢,救不了也回不去。一點機會都沒有。
他就這麼死了。
***
對男孩來說,剛死的階段是一團亂糟糟、沉甸甸的朦朧。他依稀感到疼痛,但主要是覺得累到無以復加,像是被一層又一層厚到極點的毯子罩住。他盲目地試圖掙脫,但揮動手腳只(再次)令他恐慌,對於彷彿束縛著他的隱形繩索恐慌。
他腦袋不清。思緒發像高燒般疾馳狂悸,他甚至對思想毫無覺察。這比較像是種狂亂的、垂死的直覺,害怕將要面臨的事,害怕已經發生的事。
害怕他的死亡。
彷彿還能奮力一搏,還有機會跑贏對方。
他甚至依稀感到一股衝勁,身體繼續抵抗海浪,即使那場仗已經打輸。他感覺一波駭浪頓時湧現,將他往前、往前、往前推,可是他一定得想辦法掙脫束縛。因為,在黑暗中盲目掙扎的同時,肩膀已不再疼痛,他對什麼都沒感覺,唯獨那必須移動的駭人迫切感──
接著,他感覺臉涼涼的。幾乎像是微風徐拂。不過有太多理由可以證明這不可能發生。冰涼的感覺使他清醒過來──使他的心靈?他的魂魄?還是什麼來著?──在瘋狂的旋轉中暫停。
這一剎那,他靜止不動。
眼前的陰鬱有了變化。亮了起來。有道無法言喻,但覺得可以進入的光亮,他感覺自己倚向那頭,他那如此虛弱、幾近失能的身體,向增強的光亮靠近。
他跌落。落在一個堅硬的地方。冰涼感升起,他允許自己陷入,任它將自己裹緊。
他靜止不動。放棄掙扎。任憑自己陷入昏沉。
那昏沉宛如煉獄,是灰色的。他還算有意識,沒有睡著但也不太清醒,彷彿與一切脫節,無法移動、思考、接受輸入,只能被動地存在。
無法計算的時間過去了,是一天、一年、或甚至永恆,究竟多久他無從得知。最後,那道光在遠方慢慢地,微乎其微地有了變化。某個灰色的東西冒出頭,接著幻化成淺灰,他漸漸回過神。他的第一個念頭,但應該說是依稀意識到而非清楚思考,是感覺自己貼著水泥磚。他朦朧察覺身子底下有多涼、多硬,他好像得緊扒著不放,免得飛向外太空。他不確定自己繞著這念頭轉了多久,讓它變得清晰,讓它與身體相連,與其他念頭相連──
停屍間這三個字在他內心深處倏地閃過──不然你還會躺在什麼冰涼堅實的塊狀物上──隨著恐懼加深,他猛地睜眼,這才發現眼睛一直閉著。他試著嘶吼,要他們千萬不能把他埋了,千萬不能解剖他,說這是天大的誤會。無奈喉嚨像是多年沒用過似地,不願組構詞句。飽受驚嚇的他咳著坐起身,兩眼混濁、霧濛濛地,宛如透過層層厚重的髒玻璃去看外面的世界。
他不斷眨眼,想看個清楚。周圍的影像漸漸成形。他發現,自己並非躺在停屍間的板子上──
而是在──
而是在──
他到底在哪裡?
迷惘中,他瞇著眼痛苦地望著高升的日光。他環顧四周,努力消化,去看、去理解。
他好像躺在一條鋪在房子前院的混凝土步道上,步道從人行道一路延伸至身後的大門。
但這不是他家。
而且,不對勁的事還不只這一樁。
他用力到幾近喘氣地呼吸了一會兒。他思緒茫然,視線逐漸變得略為清晰。他感覺自己打著寒顫,用雙臂環抱自己,感覺有東西濕濕地附在他的──
這不是他的衣服。
他低頭一看,只是生理反應趕不及下指令的念頭。他又瞇起眼,設法看個仔細。這些好像根本不是衣服,只是幾條勉強可稱為襯衫或褲子的白色布料,與其說是衣物,其實更像緊黏在身上的繃帶。而其中一側,繃帶濕了──
他止住念頭。
不是被海水弄濕的,不是浸在他剛──
(溺斃)的,又鹹又冷的海水。
而且身子只濕了一半。另一半,貼著地的另一半雖然冰涼,卻挺乾燥。
他左顧右盼,困惑得不得了。因為唯一可能沾濕他的只有朝露。太陽低垂,看樣子肯定是早上。他甚至可在身子底下一直躺著的地方認出一塊乾掉的輪廓。
彷彿他在那裡躺了一整夜。
但是不可能呀。他對冬季酷寒的海水記憶猶新,頭頂深灰色的冰冷天空絕不可能讓他撐過一晚──
但天空變了樣。他抬頭一望。這根本不是冬季的天空。他覺得冷只是因為清晨的寒意,這說不定是風和日麗的一天,說不定是夏天。跟海灘的凜冽冷風天差地遠。跟他──
跟他死去當下天差地遠。他又花了點時間呼吸,可以的話,只做呼吸這個動作。圍繞他的只有沉默,只有他自己發出的聲音。
他慢慢轉身,目光再次落在那棟房子上。等雙眼越來越適應光線,幾乎像是等它重新適應「看」的動作時,房子的模樣也越來越清晰明朗。
接著,穿過迷濛的五里霧,他感覺被層層裹住的心微微一顫。
輕輕一拂、一個暗示、輕如一片鴻毛的是──
是──
是熟悉感嗎?
***
他試著起身,熟悉感消失了。起身好難,出奇地難,他也果真起不來。他感覺身體虛到一點力氣也沒有,肌肉連最簡單的指令都執行不了。光是把腰挺直坐好就讓他上氣不接下氣,他還得暫時停止動作,再歇口氣。
他又試著起身,儘管一度晃得厲害,但終究成功了。他腦袋無力,有如千斤重,身子仍舊直打哆嗦。包覆他的白色繃帶豈止不保暖,更令他猛然驚覺的是,其實自己衣不蔽體。他的兩腿、軀幹和雙臂被緊裹著,整個背部也大半如此。不過令人費解的是,從肚臍一直到大腿中段,無論正面背面,這一整片都赤裸裸地面對世界,最私密的部位也教人難以置信地露在外面迎接黎明。他瘋了似地想把襤褸布料往下拉以遮蓋私處,可是那幾塊破布卻緊黏著皮膚。
他只好用手遮擋,東張西望,看看有沒有被別人瞧見。
但這裡沒人。一個人都沒有。
這是一場夢嗎?他不禁暗忖,那幾個字宛若從千里之遙的彼端,慢慢向他游來。死前的最後一場夢?
每座庭院都跟這裡一樣雜草蔓生。幾戶有草坪的人家,如今草已長到及肩高,好似片片原野。
路上停著車,可是車子覆滿厚重的塵土而且幾乎每輛車都因洩了氣的四個輪胎而下陷。
眼前毫無動靜。沒有車子駛過馬路,而且從野草的外觀看來,已是經年累月沒有來車。他左邊的馬路不斷延伸,最後與一條更寬的大街會合,看樣子那是條熙來攘往的大馬路。不過路上也沒有行駛的車輛,他還看見路上開了個四、五十呎寬的巨洞。洞裡似乎長了一整片野草。
他仔細聽。但哪裡都聽不見引擎聲。這條街沒有,下條街也一樣。他等了好久。等了又等。他望向右邊的馬路彼端,視線穿過兩棟公寓樓房間的夾縫,看見突起的火車鐵軌,彷彿等著要聽可能駛過鐵軌的火車。可是沒有火車。
也沒有人。
倘若現在真如看起來的是白天,照理說人們會走出家門,開車上班。不然也該出門蹓狗、寄信、上學。
街上應該車水馬龍。大門應該開了又關。
可是,連個人影也沒有。沒有車、沒有火車、也沒有人。
如今,他的心和眼都稍微更加清晰,所以連這條街的地形看起來也怪怪的。房子全都擠在一塊兒,緊貼成一條線,沒有車也沒有寬敞的前院。每隔四、五間房子只能見到窄得不能再窄的巷弄。一點都不像他家那條街。其實看起來根本不像美國會有的街道。看上去幾乎──
看上去幾乎像在英國。
那兩個字好似金屬相擊,不停在他腦中迴響。感覺挺重要的,彷彿迫不及待想把什麼拴住鎖緊,無奈他的思緒太混亂、太震驚、太困惑,那兩個字只是徒增焦慮。
那兩個字很不對勁。不對勁到了極點。
他身子微晃,得倚著其中一叢看似較結實的灌木才能保持平衡。他有種強烈的欲望想要進門,想找東西遮掩自己的赤身裸體,但這房子,這房子──
他對它蹙起眉頭。
這房子怎麼了?
出乎意料的是,他還沒感覺下定決心,就邁開蹣跚步伐走向它,差點跌跤也無所謂。他還是無法清楚辨析自己的思緒。他說不上來究竟為何要走向那間房子,為什麼出於某種本能之外的東西想要進屋、想要躲避這詭異荒涼的世界;但他同時也意識到這一切,無論是什麼,都像一場夢,只有夢裡的邏輯才說得過去。
他說不上來為什麼,但這房子就是吸引著他。
所以他往前走。
他走到大門前梯,跨過第一階上的裂縫,最後在門前駐足。他在門前靜待片刻,不曉得接下來要做什麼,不確定要怎麼開門,或假如門鎖上了要怎麼辦。雖然如此,他還是伸出手──
微乎其微地輕輕一推,門開了。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條長廊。這時陽光燦爛耀眼,照亮身後晴朗的藍天──天氣暖到肯定是某種樣貌的夏天,暖到他感覺烈日在曝露的皮膚上灼燒,他過於暗淡白晳的皮膚經不起這麼毒的陽光照射──不過,即使在陽光普照下,長廊過了一半之後也幾乎消逝在黑暗中。他只能辨出盡頭有道樓梯通往樓上。樓梯前的左方是通向主廳的門。
屋裡沒有燈光,也沒有聲響。
他再次環顧四周。還是一樣,哪裡都聽不見機器和引擎單調的運作聲,但這也是他第一次察覺,這裡沒有蟲鳴、沒有鳥叫,就連微風拂過葉面的聲音也聽不見。只有自己的呼吸聲。
一時之間,他只是杵在那裡。他感覺自己病入膏肓,如此虛弱、如此疲憊,幾乎可以直接躺在門階上睡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爛,永遠不要醒來──
但他選擇踏進屋內。雙手扶牆好穩住身子,緩步向前,好像每一秒都可能被人攔下,都會聽見有人質問他為何擅闖這棟怪屋。不過,他踉踉蹌蹌步入暗影的同時,縱使雙眼無法按常理迅速適應光線變化,卻能感覺腳下的地面積了厚厚一層灰,可想而知,這裡似乎已經很久、很久、沒有人待過了。
越往內走就越暗,說也奇怪,那道透進敞開大門的陽光,竟然什麼也沒照亮,只讓陰影在他朦朧的眼前顯得更暗更險惡。他摸索前行,能看見得越來越少,抵達樓梯底層時,他身子一轉,這時還是悄然無聲,不只沒有居家的聲音,什麼聲音都沒有,只有他自己。
形單影隻的自己。
他在客廳門口駐足,感到新一波恐懼襲來。螫伏在黑暗中的可能是任何東西,靜靜等他自投羅網的也可能是何東西,但他強迫自己往裡看,讓雙眼適應光線。
適應之後,一切盡收眼底。
幾束充滿灰塵的陽光射進他面前拉上的百葉窗,他藉光看見一間簡樸的客廳,與右邊開放式的餐廳合而為一,通往一道門,穿過門即是位於屋子後方的廚房。
屋裡有家具,跟一般房間沒兩樣。不同的是,家具都蒙著好厚一層灰,活像上頭多鋪了一塊布。仍舊精疲力竭的男孩,努力把這些形體跟腦中的字彙兜在一塊兒。
他的雙眼越適應光線,房間就越能展現原貌,不僅開始成形,細節也一一顯露──
壁爐台上那匹尖叫的馬浮現眼前。
一隻狂亂的眼,鐵釘般的舌頭,困在一個燃燒的世界,從畫框裡看著他。
直視他。
一見著牠,男孩立刻放聲驚叫,因為這下全都水落石出,他知道了,他知道,在疑慮的陰影背後,真相如浪潮襲捲而來。
他知道自己在哪兒了。
***
他以這雙疲憊的腿僅剩的力量盡快跑開。男孩搖搖晃晃退回走廊,掀起的朵朵塵雲直奔陽光的樣子,就像──
(就像溺水的人探頭吸氣──)
他能依稀聽見自己的哀嚎,但仍說不出話,字句仍未成形。
可是他知道。
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
他蹣跚步向大門前的階梯,幾乎無法站直身子,後來也真的站不住了。他跪倒在地,使不出力氣起身,彷彿剛才的頓悟是壓在背上的一塊大石。
他倉惶地望著房子,覺得身後一定有什麼東西、什麼人尾隨著,追逐著他──可是啥都沒有。
還是半點聲音都聽不見。機器運作聲、人聲、蟲鳴聲獸吼聲,全都沒有。這個世界萬籟俱寂,靜到他能聽見自己胸膛下的心跳聲。
他暗忖:我的心。這幾個字俐落地劃破他思緒中的一團迷霧。
他的心。
他那枯槁的心。他那溺水的心。
他不寒而慄,因為他看見的可怕真相,那可怕真相背後的意義,開始將他吞没。
這裡是他的老家。
好多好多年前住的老家。英國的老家。母親說什麼都不願再多看一眼的家。他們飄洋過海、換了一個大陸才擺脫的家。
但是不可能呀。他好多年沒見過這個家、或這個國家了。小學畢業後就沒見過了。
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
自從他弟弟出院後就沒見過了。
自從最教人不堪回首的事發生後就沒見過了。
他暗忖道:不要。
不,拜託不要。
他知道自己人在哪兒了。他知道為什麼會在──
在死後,來到這裡,在這裡醒來。
這裡是地獄。
專為他所打造的地獄。
一座他得注定孤單的地獄。
直到永遠。
他斷氣之後,在個人專屬的地獄中醒來。
他吐了。
他往前一撲、雙手撐地,將胃裡的殘留物吐進步道旁的灌木叢。費力嘔吐使他淚眼汪汪,儘管如此,他仍能看見自己吐了一片詭異而清澈的凝膠,嚐起來略帶甜味。他吐個沒完,直到最後精疲力盡,反正他早已淚眼婆娑,似乎離哭泣也相去不遠。他開始掉淚,最後直接往混凝土地面頹然倒下。
他一度像是重溫溺水的感覺,渴望著呼吸,抵抗著比自己強大、一心只想把他往下拽的力量;他根本打不過,怎樣也阻止不了它,只能任它將自己吞噬,使他在世間消失。他躺在步道上,把自己交給對方,就像海浪不斷要他棄械投降那樣──
(差別在於,他的確曾與海浪一較高下,一直拚到最後一刻,真的。)
然後,打從他初次睜眼後就不斷威嚇的疲倦感,終於將他擊潰,他也因此陷入昏迷。
越漂越遠,越漂越遠,越漂越遠──
***
賽斯睜開眼。
他仍躺在混凝土步道上,蜷著身子,抵著硬梆梆的地面讓他因為僵硬而幾近抽搐。他暫時一動也不動。
賽斯,他心想。我叫賽斯。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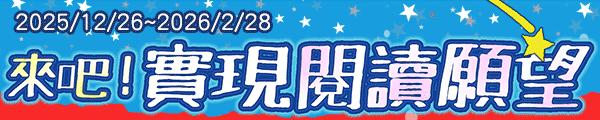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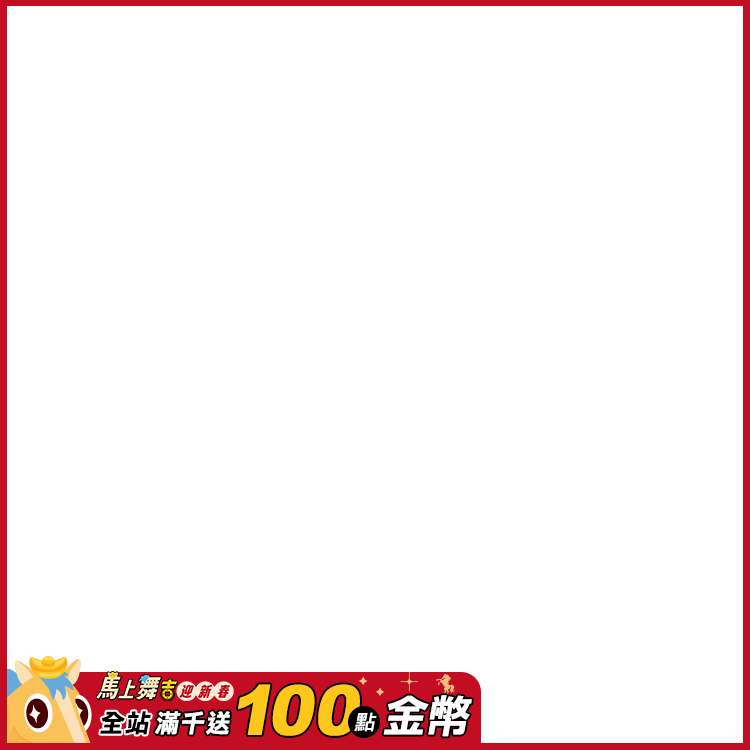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