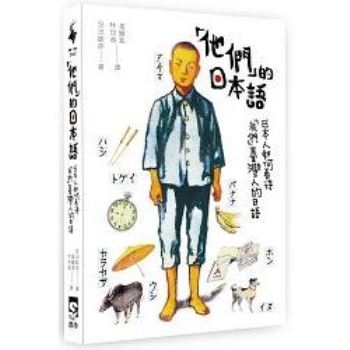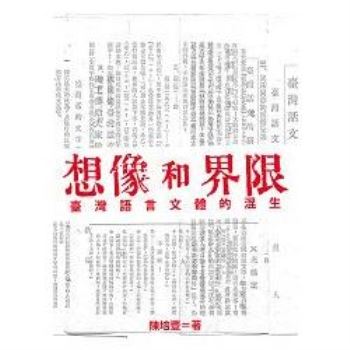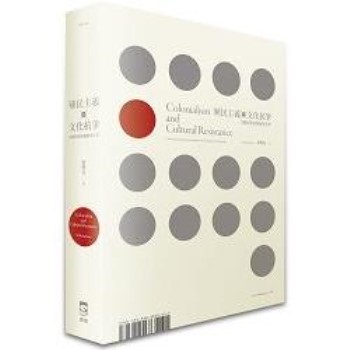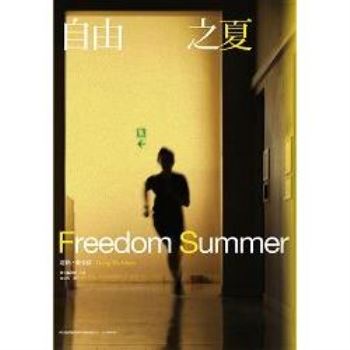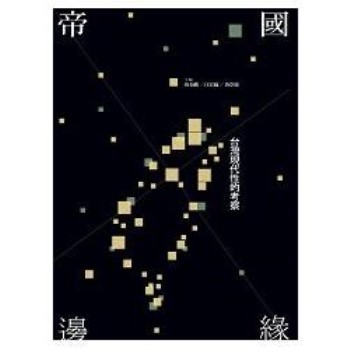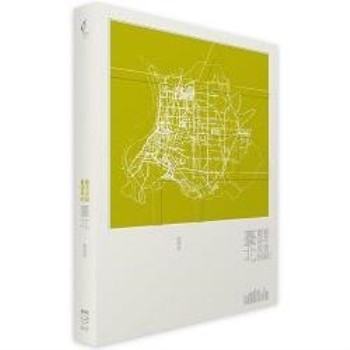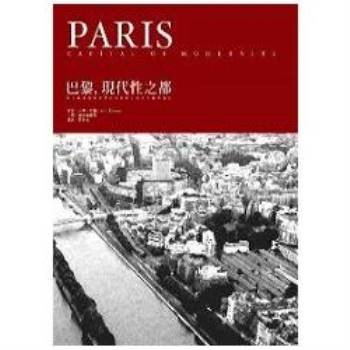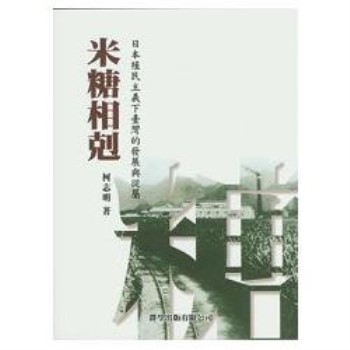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
從漢字文化圈的一員,到獨立的民族國家,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國族建構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文化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如何定位文學, 或毋寧說:核心就是文學 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東亞,正好是「清末」,也是「明治」。彼時日本開始現代化,但其核心並非器物,而是文學。日本文人進行了一連串討論與轉型運動,界定了新一代日本人文化與認同基底,發揮了深遠流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梁啟超。齋藤希史以「漢文脈」與「écriture(書寫)」兩大概念切入,涵括了當時紛亂未定的「文學」狀態,並以之為對象進行詳實考察,展示了日本現代化與文化國族建構的過程。 齋藤的研究詳實貼近文本,並且更深刻理解到:考察écriture的世界,絕不可只關注單一的線性發展,而該將視線投向在各式各樣潮流互相合流、衝突的文學場景。在日本國族性確立中,梁啟超意外扮演重要角色。齋藤貼近文本的研究之手,悉心點選各文本──報章雜誌連載小說、章回小說、翻譯小說。「小說」文類會成為主軸,正在於此載體可以吸納涵蓋所有關於國族與文化的討論。思想家探尋如何透過連載小說吸引大眾進而達到普世教育之效,而翻譯小說,更挑戰了日語範疇的邊界與定義。 作者繼而以細膩俯瞰東亞的視線,涵納到技術場域,探討銅版印刷如何助長了新日文的傳播。如果沒有銅版印刷,新型態之日文也不可能快速傳達至民間以及學校體系中。本書展現了一個國家之民族性乃是集體事業,實端賴各方各業群體群力。 最後,再從西洋人費諾羅沙看待日文的視線,來理解西洋人投射的對東亞的想像。費諾羅沙在漢文以及日文中尋找到的象徵主義意義,恰好回返與西方結合,然而東方並非僅只是召喚西方的橋樑,而乃是大一統文明進展的一部分。齋藤透過費諾羅沙,又更將漢文脈的變革,接合上了世界精神的一體性之中。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臺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
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
從「大家的日本語」到「他們的日本語」, 「我們」學習「他們」的日語,真的這麼理所當然? ──從語言的混生變種現象,探討日本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1898年,一位日本人, 對全臺灣發布政令,要臺灣人學習日語,以培養「本國精神」。 1930年,一位日本人, 操著一口濃厚九州腔日語,大聲訓斥臺灣學童的發音不夠標準。 1941年,一位日本人, 用臺語、日語交雜的混種語言,跟臺灣菜販你來我往的殺價。 1963年,一位日本人, 在臺灣爬山時,發現原住民小孩居然會哼唱日本童謠《桃太郎》。 1994年,一位日本人, 發現臺北某處公園內,一群老人流利地說著他們的臺灣腔日語。 2016年,一位臺灣人, 正努力背誦日文課本例句,希望發音能跟日文老師一模一樣。 語言使用的混雜與不完整,一直是殖民統治的常態。 然而,在臺灣的日語現象又更為複雜, 原因在於日本做為殖民者的特殊性。 做為一個有強烈「語言民族主義」意識的早熟亞洲帝國, 日本在臺灣推行了近乎宗教狂熱式的國語同化教育, 相信唯有推行國語,才能在精神上將臺灣人同化成日本人。 然而,事情沒那麼簡單。 除了日語源自漢文、本身即已非純粹外, 即便在日本內地,也存在著腔調迥異的方言, 而臺灣本就為多語言社會,更加深語言單一化的難度。 二十世紀的臺灣,身處連續殖民的政治情境。 戰後的國語同化政策,從日語換成了北京語; 但日本人發現,臺灣人在戰後仍繼續使用日語。 這不只引發其濃厚鄉愁,也引發關於國語教育的多方論戰。 針對這些現象的論辯及實例介紹,即為本書的主軸。 對親日的臺灣而言,應如何面對、理解日治時期的歷史? 除了懷想溫馨感人的歷史小故事,本書對日本的批判立場, 可提供我們理解臺灣史的另一個知識管道。 畢竟除了「親日」,要「知日」,也才更能「知臺」。
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
本書由以下各層次的析論組成:(1)整理在東亞區域中被現代政治與傳統文化左右的漢字在臺灣引發的「混成語現象」;(2)分析這種混成的漢字漢文帶給臺灣人的想像;(3)探討這種文體想像的崩壞與重構,以及對這種想像的見解問題;(4)究明眾多文體的分界與生成過程;(5)探究在日本帝國擴張下,新的漢文解釋共同體重組的實際狀況。以上五個主題依序為本書前5章,第6章則為本書的考察與總結;以此篇幅試圖探討日治時期臺語文成立的歷史過程,為現代臺灣人的精神文化史進行點描。 本書最關心的課題,是以世界殖民史與東亞區域文化史的視角,考察出現在臺灣的漢字漢文諸相各具什麼意涵;這將在第5章及結論探討。 本書特色 本書將向來被視為既定分析概念的「漢文」當成主要分析對象,考察臺灣語言文體在東亞漢字文化圈與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混成語現象」,以自創的概念「殖民地漢文」當成貫穿整體論述的概念,分析、考證臺灣的各種文體及其背後隱含的政治、文化、社會、階級、思想與歷史意義,試圖探討日治時期臺語文成立的歷史過程,為現代臺灣人的精神文化史進行點描。 「殖民地漢文」存在於臺灣,與其說是歷史的偶然,不如說是文化發展的必然。 如今,臺灣社會上的漢文書寫具有高度恣意性和創作性,是種由民間主導、「約定俗成」的文體表記規範,而這種「臺灣國語」的創出及默契規範,將逐漸成為臺灣人內涵的一部分。因此,尊重多元、保持融合,反映臺灣文化的自主性和特色,策略性地利用混雜以達成「同中求異」的理想,應該是臺語文發展最自然且可行的一條路。
殖民主義與文化抗爭:日據時期臺灣解殖文學
不論是解嚴前的中國民族主義反抗史觀,或解嚴後研究立場「客觀化」的新史觀,都是與強權站在一起、侵奪臺灣主體地位,將臺灣「邊緣化」的殖民化論述;而左翼知識分子由反支配的本土主義立場出發,對新、舊知識分子進行精神殖民化的批判,不僅在殖民時期就起著內部解殖的功用,也是清理後殖民知識分子精神殖民化時可以憑藉倚重的歷史資源。本書通過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突出當中「反支配」與「本土」的價值立場,指出對解嚴後才真正邁入後殖民時期的臺灣社會而言,解精神殖民化才是重建臺灣主體性的關鍵。 日據時代臺灣作家的認同問題,近來成為臺灣文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儘管對個別作家的討論為數不少,但相關研究多止於對被建構者的認同進行個案式的分析與討論;由於對形成這種主體狀態的根本原因鮮少追本溯源,無法對日本殖民主義如何建構臺灣人的主體性進行比較完整的研究,所以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覆。 為彌補這方面的缺憾,本書第2章對日本殖民主義及其如何建構臺灣人主體的研究探討,先是由日本殖民主義的形成歷史入手,接著探討日本如何接收西方殖民主義的進步意識形態,並用以建構「被殖民者」認同的日本主體。日本殖民主義通過文化二元分類系統,深入臺灣人的日常生活網絡,導致臺灣人除非接受日本文明的同化,否則便無所逃遁,只能被分類為非文明的存在。 奠基於本書第2章的分析,第3章則以殖民主義論述內容為對照系,分析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認同位置與殖民主義的親疏關係。實際討論則以1937年為界,將日據時代的文學活動分為兩大階段,這兩個歷史階段最大的不同在於進入戰時體制的第二階段,言論受到更嚴苛的控制,臺灣作家不僅不能公開批評日本殖民統治,還要被迫配合國策發表言論。 而第一階段的漢文作家中,賴和無疑最具代表性。他沒有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背景,但素樸的反強權支配立場,卻讓他將殖民地問題直接放在弱肉強食的不義上,發展出本書所稱的「原生本土立場」,讓他的文學創作既能不受「近代意識形態」的宰制,又能充分發散政治上去權、文化上解殖的文化政治效應。因此第4章以賴和的思考及文學創作為焦點,探討他如何將殖民問題重新聚焦在權力支配,由此與殖民主義、啟蒙主義的進步意識形態對話,進行「全方位的去殖」。 而在活躍於 1940年代的臺灣作家當中,張文環是真正能繼承左翼本土主義路線的人,所以本書第5、6兩章以他為主,兼及黃得時、呂赫若、龍瑛宗等人在文化論述及文學上的表現,探討戰爭體制下這批臺灣人作家如何堅守臺灣人立場、如何逼近皇民化論述中的文化差異界線,以「想像與象徵的再定位」挑戰殖民主義二元制所欲鞏固的等級關係,亦即鬆動殖民權力的支配關係。 這批臺灣先人選擇了「更艱難的途徑」——站在「反支配」立場,與較為不幸、被威脅、面臨完全滅絕危險的被統治者站在一起,由異化的文化位置回歸「本土」立場,為「屈從的經驗以及被遺忘的聲音和人們的記憶」發聲,這是我們身為被殖民者無可迴避要走上的解殖民化漫漫長路。本書討論的左翼知識分子、賴和及張文環,已為臺灣人的精神解殖邁出第一步,後續當然還有很多解殖民化的精神工程需要我們持續面對戰前、戰後的殖民主義接力進行。 臺灣的左翼運動及其思想遺產被埋葬在歷史最陰暗的角落,這份寶貴的左翼「後殖民理論」遺產,一直未能作為重要的思想參照系而對當前臺灣社會的解殖民化產生作用。長久以來,掩蓋在這份思想遺產上的各種歷史與文化偏見已非常深厚,本書對左翼反支配本土主義的闡發,只是用「後殖民」這個有限的視角,開挖這份思想遺產一個很小部分的意義。這份思想遺產對當下的臺灣究竟還有什麼啟發意義,則有待後續研究繼續發掘與闡發。
自由之夏
本書榮獲1988年Gustavus Myers中心頒發美國非暴力議題最佳書籍獎。 「每一天發生的每樣事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資訊不斷轟炸著我,經驗不斷轟炸著我……而我衰微的精神狀態幾乎要失控了。」 「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性一刻;在一區域中,整體生活模式裡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要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些方面來看是全然無私無我的,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它讓我欣喜若狂……第一次這些片段碎塊嵌合在一塊……感覺像我自己……我認為透過它,我們不但成就了些事,也是實現我個人的救贖。」 「它是我人生中最長的夢魘:三個月──一九六四年的六月、七月、八月。」 本書即是詳述這個撼動美國六○年代,歷時不到三個月的「自由之夏」運動(Freedom Summer)。這段期間,超過一千人聚集至美國密西西比州,共同居住在「自由之家」,或寄住在當地不懼種族隔離主義者威脅的黑人家庭中。計劃期間,難以緩解的恐懼、令人苦惱的貧困,以及間或發生的暴力事件,都困擾計劃的進行,最後造成四位自願者被毆打致死、八十位自願者受傷、一百位自願者被逮捕,並有六十七間教堂、房屋及商店被砸毀或焚燒。這個夏天是每位參與者心中難以磨滅的經驗,他們的生命被改變,進而撼動整個世代。 「自由之夏」是美國社運的重要轉捩點,透過它所引發的文化與政治效應,孕生了日後其他重要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等。自由之夏不僅為六○年代眾多行動主義的嘗試提供了組織基礎,同時也關鍵性地推動這個時代茁生的反文化思潮發展。
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
本書嘗試使用「帝國邊緣」來捕捉台灣現代性的特質,乃是因為現代性在台灣的濫觴與開展,自始即與台灣所處的帝國統治邊緣位置有關。各種曾經或正在滲透、決定台灣現代性走向與過程的力量體系,是討論台灣現代性不能忽視的條件,而其對照出來的邊緣處境與在地化發展,正是本書要探究的焦點。 現代性作為一種時代表徵,背後交織著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叢結運作。由於現代性牽涉的時程和範圍甚廣,議題包羅萬象,要剖析這些眾多、複雜的面貌,需要集體的努力。因此,本書邀集13位跨領域學者,就其研究專長分工寫作,多採社會學的視角,進行歷史性的分析和反省。這本中文世界遲來卻仍具及時意義的專書,將發揮刺激思考的作用,引領讀者對台灣現代性做出深刻反思與細細品察。
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修訂一版)
完整一個現代臺北市的出現,並非人口增加、市地擴張的「自然」結果,而是現代權力在空間上運作的「社會」產物。清代的傳統治理 「看不見」擁有獨特意義的「地方」;日治時代的現代治理則從根拆解地方的原有意義,從而「看得見」每塊空無意義的「空間」。清末到日治的社會變遷深沉而複雜,透過臺北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似乎可以窺見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的登臺之路。 在這條現代空間之路,地方情感已被剝除,任何空間皆可停泊,但也將不再久留。這是易於流動的「空間」,易於看穿、易於監視、易於穿越,卻不是可以積累生命意義的「地方」。 此乃是條不可逆也不可擋的旅程,但活在現代空間裡的我們,終究仍須省思如何會走到這樣的時代。現代化未必是什麼好字眼;推動現代化也未必是值得禮讚的事。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現代都市空間的出現,只是在說明臺北有過這樣一個美麗的汙名。 本書特色 臺灣政府自2009年以來,在徵地與都市更新問題上搞得輿論譁然、眾怒難平。相較於清朝末年當官的含糊敷衍、委曲求全,當前的政府看似展現了點兒現代國家的權威,但辦法拙劣、手段粗暴,比起縝密算計、操作細膩的日本殖民政府可謂望塵莫及。當然,本書可不只是國家(政府)權力如何施用於人民的操作說明,更可作為人民理解國家施為本質以便應對進退的教戰手冊。
巴黎,現代性之都
巴黎一直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城市,迄今魅力不減反增,但它卻是在「第二帝國」時期,才翻身成為我們今日所知的現代性樣板。在一八四八到一八七一年兩次失敗的革命之間,巴黎經歷了一場驚人的轉變,俗稱「巴黎大改造」。奧斯曼男爵,傳奇的巴黎首長,一手打造巴黎的外觀,以今日巴黎四處可見的林蔭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紀地圖,巴黎才變成今日如夢如幻的巴黎。這段期間也興起 了以高級金融為主體的新資本主義形式,以及現代的大眾消費文化。城市外貌及社會景觀的遽變,帶來嶄新的現代主義文化,同時也脅迫巴黎沿著階級的界線斷裂,結果是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興起,以及隨後的血腥鎮壓。 巴黎為何成為巴黎?哈維的全景式觀照與戲劇式的敘述,使得閱讀本書一直充滿著張力。本書與卡爾.休斯克《世紀末的維也納》,允為研究現代都市興起的兩大歷史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