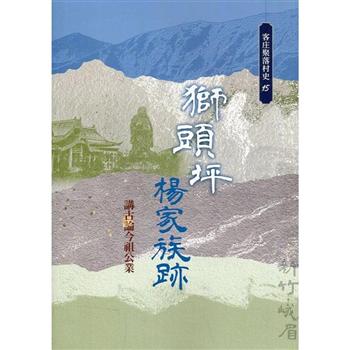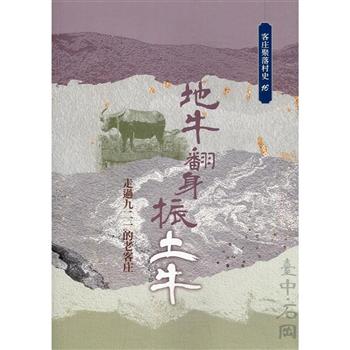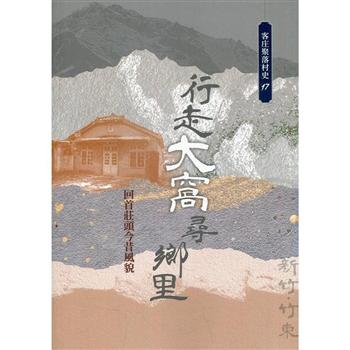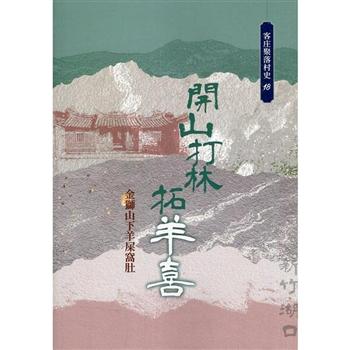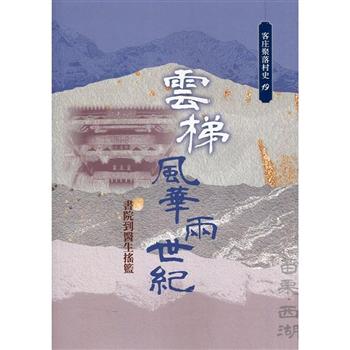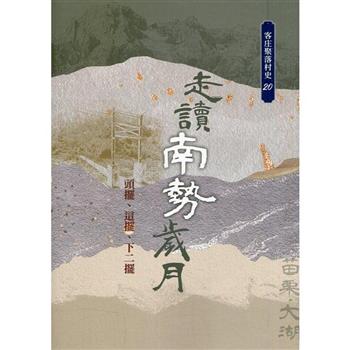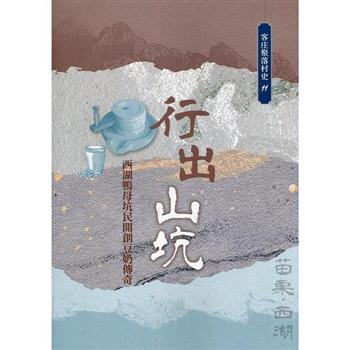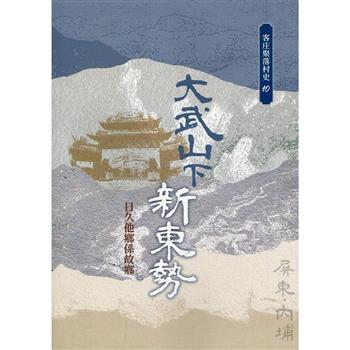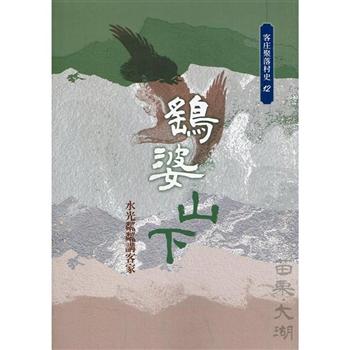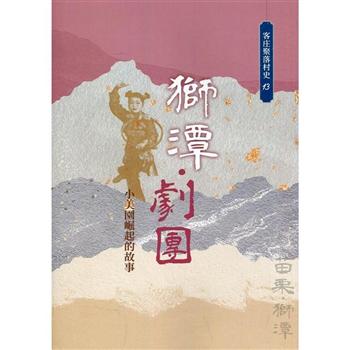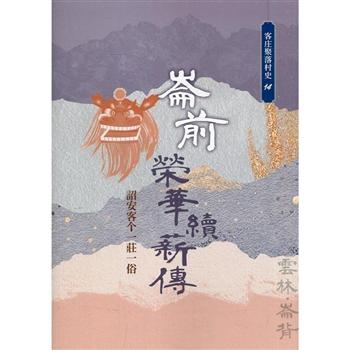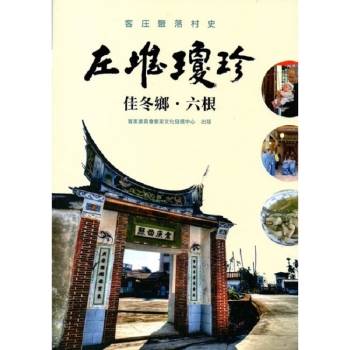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南外蝶村講古今:再現客庄桃花源
北埔鄉南外社區的地形以山地為主,大坪溪、大南坑溪、小南坑溪流經境內,山高谷深,水流湍急,適合農耕的地方不多。 有些人說,那裡自古以來一直是父不疼、母不愛的新竹縣北埔鄉邊陲棄兒;但也有人說,那是一個小橋流水,蝴蝶飛舞,與世界無爭的樂園,是遠離塵囂,區民和樂,與蝶共餐的世界。到底南外是一個怎麼樣的村莊? 南外社區,在清治時期原為賽夏族與其他平埔族原住民的混居地,其後客家人入墾當地,日治時期繁華一時,而在民國50年代快速沒落,爾後又在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原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輔導之下,蛻變成今日一個兼具歷史人文與環保休閒的人間樂土,透過本書,讓我們一起來探索南外社區的古往今來。
北岸河畔探南豐:話講頭擺南岸庄
六堆客家人的墾殖路線,可以分為北、中、南三線,其中南線為今新埤、佳冬二鄉,也就是六堆的左堆。南豐村是左堆新埤較早發展的聚落,地理位置在北岸河的南邊,故昔日被稱為「南岸」,因與客家話「難願」諧音相似,故在民國60 年(1971)改名為南豐村,以求村民能年年豐收。南豐村客家族群在不同年代遷入,此地聚落除了南岸本庄還有豬高崙、永興寮、阿發寮,各聚落開墾時間雖有不同,但各具特色,居民都對這片土地有著感恩及熱忱的心。透過在地耆老、熱心民眾的帶路,作者多次田野調查,讓我們可以一窺先民墾拓的過程,以及聚落發展、產業變遷的歷史,同時了解當地的宗教信仰活動與祭品製作技藝是如何傳承至今,為南豐這個文獻紀錄稀少的客庄聚落留下珍貴故事。
薈萃新北勢:繁華‧沒落‧再生
內埔鄉新北勢是由豐田與振豐兩村所組成,相對於老北勢而言,是較晚開發的聚落。昔日由於位處交通要道,加上礱穀間林立,以及士紳家族背後撐起聚落秩序的隱形力量,使新北勢在過往的客家聚落中佔有一席之地,最顯著的代表就是巴洛克式建築的豐田老街,這條特殊風格的街道在南部客家地區非常少見。但隨著時代演變,家族規模式微,老街也褪去亮眼的外表,從繁華富麗轉為散發出古意樸實的老建築。可新北勢沒有隨著老街的沒落而凋零,藏身巷弄的古老釀造產業吹起創新風潮,透過行銷與包裝,這項看似快要沒落的傳統產業循著文青風格重新進入市場,新北勢這塊老招牌就此從華麗老街手上傳遞給釀造產業,期能再次光耀下個世紀。
獅頭坪楊家族跡:講古論今祖公業(客庄聚落村史15)
新竹縣峨眉鄉湖光村6 鄰,一個樸實的小村落,因為獨特的地形而被賦予「獅頭坪」這個蘊含靈性的名字。故事的主角是獅頭坪的開墾祖先-楊姓家族,隨之圍繞著這片土地不停的流轉,將土地上的人物故事與民俗傳說敘寫至今。除了探究楊家先祖與楊家將的關聯性,更多著墨於楊家入墾獅頭坪的勤奮鋤耕與傑出的後人事蹟,並透過客語詞彙、俗諺和童謠等,將獅頭坪的產業、習俗與信仰以趣味動人的文字傳遞呈現。楊姓先祖千百年來顛沛流離,輾轉從中原遷臺落腳獅頭坪,自此,獅頭坪與楊家的發展便密不可分,就讓我們一起追尋楊家人的腳印,一步一步探索獅頭坪的古往今來。
地牛翻身振土牛:走過九二一的老客庄(客庄聚落村史16)
臺中市石岡區的土牛庄,位於大甲溪西畔,一年四季溪水潺潺,人與自然生態環境和諧,因而孕育出豐富的人文故事。這裡是聞名中外的客家老伙房,自清領時期以降,為防止漢人與原住民族因拓墾衍生不斷的衝突,設立「土牛」這樣的界線來維持和平,就此展開土牛庄的發展足跡。幾百年來,土牛原漢界碑之歌不斷傳唱著,從早期漢原之間的戰爭與和平、劉家與朱家在這片土地的開墾、庄民和水圳的互動到客家的文化信仰,當然還有九二一令人震撼悲慟的那一夜,客庄的生命歌謠令人動容,在在都值得我們仔細聆聽、深入探索。即使歷經不少風霜與考驗,土牛庄還是走過來了,一如依舊矗立在地圖上的那條界線,堅守著自己的崗位,傳承屬於客庄的文化與歷史。
行走大窩尋鄉里:回首莊頭今昔風貌(客庄聚落村史17)
新竹縣竹東鎮的大鄉里,古名大窩,得名於其地形凹陷的樣子,為三面環山,向西南深入的坑谷地區。如今雖已沒有那古老的地名,在街道巷弄之間信步穿梭,仍能從一磚一瓦中,看見老大窩的今昔風貌。有聚落的地方就會有信仰,不論是承襲自客家文化的伯公信仰,還是香火鼎盛的萬善祠,都承載著大窩居民的希望與寄託,也是鄰里聯繫感情的重要地點。不只如此,大林製藥廠、大林玻璃廠,以及在天時地利人和下,創造過無限風光的新竹玻璃公司,也都在此發光發熱。如今的老大窩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的成立,開始有了新風貌,過往的產業雖已退出歷史舞臺,走過工廠的舊址,從老員工的口中訴說的一個個故事裡,依舊能瞧見當年的熱鬧與繁華。
開山打林拓羊喜:金獅山下羊屎窩肚(客庄聚落村史18)
新竹縣湖口鄉,有一處名為羊喜窩的客庄,「羊喜」為「羊屎」諧音,因有原住民族牧羊或野生山羊活動,在山谷中留下羊屎而名之。「窩」是指三面較高、凹口向低處發展的地形,通常是有河流發源的地方,而在客家話裡,「窩」有讓人感到溫暖的寓意。這片土地就是客家遷徙移民的窩,溫暖的包容著在這裡生活、耕耘的人們,他們來到這裡的時間、過程不一樣,後來也因環境條件與經營方式的差異,產生不同的結果,但在大環境潮流下,他們共同寫下了一篇庶民的開發史。一個地區的延續與繁榮有時並不需要轟轟烈烈的大事,也可以像羊喜窩一樣,用一個個小小的故事堆疊,累積出無限大的能量,在臺灣客家文化發展上留下輝煌的一頁。
雲梯風華兩世紀:書院到醫生搖籃(客庄聚落村史19)
苗栗縣西湖鄉四湖庄,現已劃為四湖村,全村面積雖小,卻蘊含著龐大的文化能量。自清領時期道光年間即興建了雲梯書院,而後延伸設立鸞堂、地方宮廟,其孕育的人才多不勝數,從清末科舉人數之眾到日治培育醫生密度之高,放眼全臺儼然只有四湖可以號稱為秀才之鄉。文化當然不僅只有教育一環,各大宗姓在四湖的發展、風水傳說、宗教信仰的演變和傳承,各式各樣的人文地景、文化習俗與產業變遷,錯綜交織為一篇篇精彩的章節,構築出超群絕倫的四湖風華。
走讀南勢歲月:頭擺、這擺、下二擺(客庄聚落村史20)
苗栗縣大湖鄉大南村,早期是原住民族泰雅族人的聚落,後來漢人進入開墾,又經日人的理蕃管理,大量客人遷徙至此落地生根,以大南為鄉。如同許多土地開墾史總是與原住民族有著深深的糾葛,大南也不例外,在清領時期,大南村仍屬原住民族生活區域,漢人不敢在山區落腳,與原住民族交集甚少,直至日治時期的政策實施,才讓雙方有機會交流,族群的隔閡也在這一來一往的互動下,從初始的敵意轉變為親密往來。隨著時光的流逝,過往的人們在大南這片土地扎根、繁衍、茁壯,屬於此地的故事逐漸沉澱累積,一處處景物,一張張老舊的照片,留下前人生活的足跡以及歲月流轉的印記,細細耳聞,能聽見前人的低聲呢喃,娓娓道來那些年華的甘苦與酸甜。
行出山坑:西湖鴨母坑民開創豆奶傳奇(客庄聚落村史11)
苗栗縣西湖鄉鴨母坑(金獅、龍洞村),舊名阿末坑,原是平埔族人之地,清初漢人從粵、閩渡海來臺開墾,因多數是山崗、壁壢,謀生困難,早期以龍眼、木炭、竹篾為主要產業,被視為鴨母坑三寶。鴨母坑因環境惡劣,早年連挑水飲用都很艱辛,很晚才有現代化水電,民國五、六十年代隨著臺灣工業化起飛,鴨母坑三寶產業沒落,居民紛紛「行出」山坑,有人到臺北、桃園、新竹一帶工業區打工、求學;亦有不少人隨著邱豐彩的腳步到臺北學做豆漿(奶),帶動西湖「豆奶移民潮」。豆奶原是山東老兵帶進臺灣的飲食,因經營很辛苦,後來將豆奶飲食文化發揚光大的,竟是刻苦耐勞的客家人,領航者即是從鴨母坑「行出」的邱豐彩。
大武山下新東勢:日久他鄉係故鄉(客庄聚落村史10)
屏東縣內埔鄉的東勢村,從清領時期開始,外來移民不斷進入東勢村,隨著人口逐漸增長,慢慢在這裡形成了緊密的聚落。不只是東勢庄,也有大路關人所遷移定居的大和庄、北客南遷的臺北庄,這些聚落都擁有各自豐厚的歷史,交匯融合的結果,亦發展出在地化的信仰,村裡可以看到許多伯公廟,也有杜君英衣冠塚、福泉堂等。伴隨著時間的流逝,村內地名雖有所變遷,但就如同屹立不搖的大武山,在山腳下的東勢村,無論名字如何變化、人口怎樣遞減,數不盡的年頭裡累積的居住陳跡,終究還是讓此處,成為外移居民的新故鄉。
鷂婆山下:水光粼粼講客家(客庄聚落村史12)
苗栗縣大湖鄉的富興村,是進入苗栗內山最主要的入口,雖然現在放眼多是鮮紅嬌豔的草莓園,但自古這裡卻是臺灣泰雅族傳統勢力範圍。清咸豐11年吳定新率56家丁入墾大湖時,這塊位於鷂婆山下的心形臺地,便是美如傳說的天許之境,可惜因為水源不足,就算底下有二條大河在此交會,她依然只能是個取水困難的不毛之地。不過,正也因為如此,水尾坪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走出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色,發展出更多有趣的故事與悠長的歷史。富興村包含許多庄頭,有水尾坪、八寮灣、芎蕉坑、化人公及砲石等,村中不只包含了鷂婆山和觀音山等人文地景,更有天后宮與法雲寺的鐘聲鎮村保佑村民,這裡同時還是大湖事件等著名歷史事件的發源地,這些由我們祖先所經歷的點點滴滴而今成了一個個有趣的傳說,不僅豐實了富興村的歷史,也添增了地方的趣味。
獅潭.劇團:小美園崛起的故事(客庄聚落村史13)
靠近苗栗縣內山的獅潭鄉,自民國60年代以來,因為加工業的快速發展,人口移出率增加,直至今日,獅潭鄉還是全縣人口最少的行政區域,但卻有著超過90%的客家人口比例,展示著客庄文化獨特的風貌。獅潭從清代時的原住民居住地,歷經了馬偕牧師在獅潭底的傳教、漢人的開墾、日本人對當地資源與產業的挖掘等歲月痕跡。而在獅潭所歷經的故事中,王家的小美園劇團,無疑是最燦爛的一齣戲。早在清領時期就來到獅潭一帶開墾定居的王家,在當地深耕,直到日治大正11年,小美園客家戲曲劇團在王德循手中誕生。而後在短短幾十年間,劇團將熱情與感動刻劃在臺灣這片土地上,演藝著一齣齣拍案叫絕的劇目,為客家戲曲在歷史上留下濃墨的痕跡。
崙前榮華續薪傳:詔安客个一莊一俗(客庄聚落村史14)
雲林崙背鄉,舊稱崙前村。以崙前順天宮為信仰中心,是詔安客家先民在臺灣最早聚居的客庄之一。崙前村以及「面前厝」、「崗仔背」及「溪底」所聚集而成的「崙前聚落」,隨著時代的更迭,賦予一個個鮮明的文化記憶。從歷經日治時期耆老們口中的農村景象、隨時間流逝交互更替的產業發展、朱府王爺在順天宮裡流傳的傳說,到以招牌戲碼《五爪金鷹一生傳》紅極一時的隆興閣掌中劇團。除此之外,被稱做「詔安三寶」的「武術、開口獅、布袋戲」,無論是歷史的沿革,還是一路走到現今的傳承足跡,詔安客家文化館裡,以靜態的展覽和每年三節、詔安客家文化節舉辦的活動形式,細細的描繪出「崙前聚落」客家村庄的一頁頁精彩。
左堆瓊珍-佳冬鄉‧六根(客庄聚落村史04)
六根庄,今佳冬鄉佳冬村、六根村,六堆唯二之近海客庄,清治以來左堆重鎮,左堆領導中心。六根一地原為平埔族故地,鄰近山地原住民勢力範圍,因漢人入墾的早,早年族群間關係緊張,聚落舊城為中心放射狀,以石牆包圍聚落開四柵門。清代移墾眾多客籍民眾,遺留眾多傳統建築風情。日治時期行政中心設於聚落外圍,保留眾多日治風采,文化精彩度極高。 因近海飲食融入海鮮特色,部分建材使用咾咕石砌牆,為少數具有五營信仰的六堆聚落。近代以古蹟保存及社區文化資產保存運動聞名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