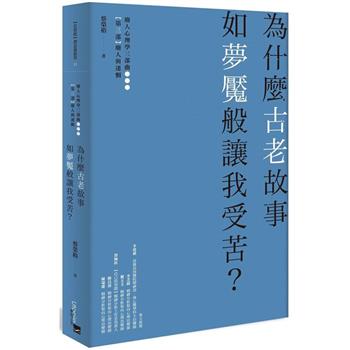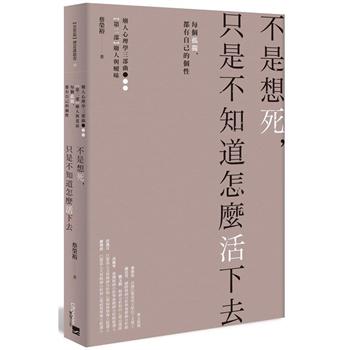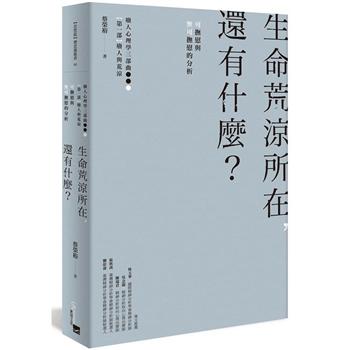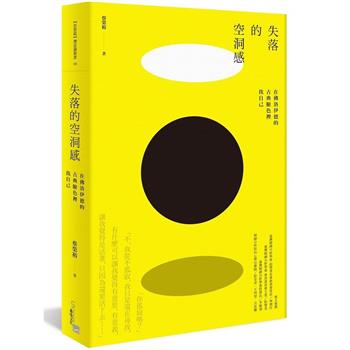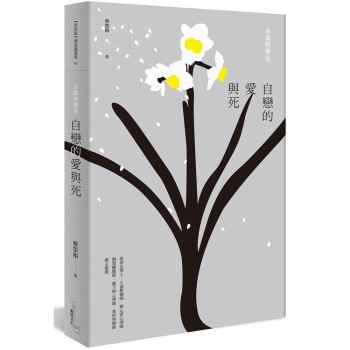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內心荒涼地帶起風了:關於「創傷與精神官能症」:精神分析對團體心理治療的想像
佛洛伊德早就關切群體心理學和「自我」(ego)的關係,加上義大利精神分析師斐羅(A. Ferro)等在「舞台理論」(field theory)添加比昂的論點,強調的是,同一個舞台上,個案內心世界出場的眾多角色,和治療師內在裡的眾多角色相互影響,構成了治療情境的豐富性。 在心身醫學科和一般精神科裡,除了現有的門診和住院之外,為了建構處理精神官能症的模式,我們開始有了精神分析對「團體治療」的想像;雖然生物學因素已經是目前精神醫學的強項,但距離能真正解決精神官能症問題,仍有一段長路。我們將以「創傷與精神官能症」為主軸,偏重強調其中的心理因子,「起風了」是方案的名稱,內容除了「團體心理治療」模式,也將會有教學、訓練和研究的功能;我們想要建構長期門診式的深度心理團體治療,不只以人際關係處理為焦點,更是往內在心智探索,如同現有的個別心理治療。 內心荒涼地帶起風了 精神分析對團體心理治療的想像 起風了六因子 配對/依賴/打帶跑/無力感/無助感/無望感 起風了七夢思 feeling/thinking/dreaming/linking/digesting/ playing/living 起風了三態度 無可了解unknown/無可確定uncertainty/無可撫慰unconsoled 起風了六忍耐 力忍/忘忍/反忍/觀忍/喜忍/慈忍 依精神分析家溫尼科特(Winnicott)的說法,內在客體關係的心理世界裡,沒有「嬰兒」這件事,有的是「嬰兒與母親」。比昂(Bion)提出「自戀」和「社會戀」是同時存在,如同一輛馬車前面和後面的兩匹馬。因此我們想像著,是否沒有「個體」這件事,有的是「個體與群體」;或者沒有「孤獨」這件事,有的是「孤獨與合作」? 佛洛伊德也早就關切群體心理學和「自我」(ego)的關係,加上義大利精神分析師斐羅(A. Ferro)等在「舞台理論」(field theory)添加比昂的論點,強調的是,同一個舞台上,個案內心世界出場的眾多角色,和治療師內在裡的眾多角色相互影響,構成了治療情境的豐富性——就這樣,我們的想像起風了......。 起風了268想想 「起風了」團體心理治療的通則,首先是以「268想想」作為基礎的概念,我們提出了〈起風了六因子〉作為團體動力過程觀察的指標。六因子中有三項是比昂提出的「基本假設團體」(basic assumption goup)動力因子:依賴、配對和打帶跑。我們再加上因失落創傷,帶來的三項常見的個體深沈感受:無力感、無助感和無望感。 我們以一些通則作為各個團體的參考點,首先要讓成員了解,參與「起風了」團體心理治療的主要目的,是從團體經驗裡學習認識自己。這裡的「自己」不只是意識上期待的自己,更是著重在不想認識的那個自己。這是一條長路,不是一般想像的,透過一些方便的說法,就要確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要做的,不是精神醫學的診斷,而是傾向了解自己的深度心理學。 所謂「從經驗學習」,我們先暫時把這些經驗的視野設定在〈起風了七夢思〉:feeling, thinking, dreaming, linking, digesting, playing和living;佛洛伊德提出的「分析的金、暗示的銅」,依著精神分析的推展,至今依然著重「移情」在臨床過程的重要性,因此我們提出,把「分析的金」更具體化為「移情的金」。「移情的金」在內心戲裡,是透過這七項現在進行式的心理作用,推衍出「移情」的樣貌,也就是,我們利用這七項來分解「移情」形成的心理機制。 簡略的說法是,我們想從成員說出的故事,以及在團體當刻和他人合作的困局,透過對移情和反移情的觀察,並以〈起風了六因子〉和〈起風了七夢思〉作為基礎,不只停留在表面故事和合作困局中,而是往深度心理學慢慢走——我們強調慢慢走,不急著強加什麼因子來加速過程。〈起風了六因子〉和〈起風了七夢思〉是讓我們從表象穿透雲霧,慢慢走向深度想法的工具;它們是讓心理過程慢下來,好好地被看、被想,一步一步走。雖然我們認為以〈起風了六因子〉和〈起風了七夢思〉,並不足以完整說清楚人的心智功能,但它們提供了方便觀察和思索的大方向。 這個過程需要再搭配〈起風了三態度〉:無可了解(unknown)、無可確定(uncertainty)和無可撫慰(unconsoled),這是治療師對於未來想像的三種基本態度。我們主張,人心理潛在的未來是,無可了解、無可確定和無可撫慰,就治療的過程來說,是「此時此地」的態度,雖然已有「中立的態度」或「分析的態度」的說法,但我們試著以這三種態度再出發,來體會中立和分析的態度裡,更深細的某種「境界」。 既然語詞要表達的是某種「境界」,就表示它們不容易抵達,需要一般常說的,忍受或忍耐許多不如預期的挫折。什麼是忍耐呢?我們提出了〈起風了六忍耐〉:力忍、忘忍、反忍、觀忍、喜忍和慈忍。 內心戲 關於治療的關係,一般認為,個別心理治療是兩人的關係,而團體心理治療是眾人的關係,不過,依照F. Carrao的論點,就算是屬於兩個人的分析,也是治療師和個案的內在團體動力(internal group dynamic)的總和。這是有趣的說法,他進一步說,並沒有只是兩個人之間的分析,每個分析都涉及團體。依我們的意見,如果每個人都有自我、原我和超我,這三個「我」是構成了,想像中的三人為團體的說法。 A. Ferro等人運用「舞台理論」(field theory),搭配比昂的論點,強調舞台上出場的每個角色,會和治療師內在裡的眾多角色相互影響,這構成了治療情境的豐富性。例如,成員說著他和誰發生了什麼事,就是他讓那個人出場,扮演某個角色,這些不同故事裡的不同角色,都有他們想要說的話。因此,我們要觀察、想像和猜測這些不同角色想說什麼,而不只是依著成員的眼光來看事情;我們可以在想像裡,和舞台上忙碌的角色們進行對話,也可與某些角色互動。 在團體裡情況也是如此,我們要觀察和想像,而不是只依成員的說法,就定位他們口中的某些角色;這些過程,可以讓角色們透過治療師的穿針引線來對話。然而,在團體進行的技術上,是否要說明這些作法讓成員知道?這是可以再考量的,因為不是所有的成員都可以理解。但是,當治療師這麼想像時,才有機會聽出不一樣的訊息。 我們假設,人生舞台的第一場戰爭,發生在嬰孩和父母之間,雖然一般強調母親的涵容功能,以及要完全地配合嬰孩的作息,不過這只是某種期待;在這場戰役裡,就是團體的戰爭,涉及剛出生的嬰孩和父母三人間的團體動力,他們相互影響,例如,如果父母不和,或者為了夜間誰來餵奶而有爭議時,父母間的角力,自然會成為這場人生戰役的一部分,很難不影響嬰孩。尤其父母為了盡快回到生活和工作的日常,勢必會在這場人性戰爭中擔任重要角色,不論時間和內容上,該如何讓嬰孩早日適應或進入大人的節奏呢?畢竟,大人日常生活的穩定是很重要的,而且也有益於照顧嬰孩,但是快慢之間,會發生什麼心理戰爭呢?只要想一想流行的說法:「不要輸在起跑點」,就知道這場人性戰爭,是起源於多早的人生!這當中的團體動力,例如父母之間協調的困局,並不是以父母是否愛小孩為理由,就可以完全避免。 這是必然發生的「人生」和「人性」的戰爭,任何一方贏,就是另一方挫敗和壓力的來源,對嬰孩來說,其中的影響涉及了失落和痛苦的過程。透過觀察成員們在團體裡和他人互動的困局,可以讓我們有機會推想,他們早年經歷這場人性戰爭時,可能存在的團體動力的經驗,這些構成了我們的視野。 內心戲的舞台,眾多角色都上演著自己,如同我們主張夢中的所有角色,不論生物或非生物,都有著夢者自己的影子,不管在故事裡是否具有明顯的角色,他們都想要說出自己心中的話;有時候微弱者,也想要大聲地說說話,這些都需要治療師去想像。 功效、侷限和副作用 關於個別心理治療和團體心理治療,我們主張,需要同時注意功效、侷限和副作用這三項要素;藥物使用,早就有這些規範和習慣,必須同時注意會有什麼功效和侷限,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會產生什麼副作用。以語言和肢體作為開展心理治療的模式,自然也得在建議或詮釋時,同時關注功效、侷限和副作用,才不會因忽略了侷限和副作用,而過度建議和詮釋,甚至有言語侵犯或言語暴力的傾向。 佛洛伊德當年從注意阻抗的現象,拓展了精神分析的視野。我們在治療過程裡,也必須隨時對自己所做所說的留意,某些個案或許有能力上的侷限,我們是無法過度要求和期待的。而若忽略了副作用,可能會讓所說所做的,走向和預期相反的結果;起初也許功效顯著,但如果隨後而來的副作用也跟著強大,會如同外科手術,雖然手術本身成功,但後續副作用出現,吞噬了先前的功效,帶來的結果是失敗。 因此,任何建議或詮釋都需要先思索功效、侷限和可能的副作用
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
蔡榮裕醫師【廢人心理學三部曲】: ◆第一部 廢人與荒涼 / 生命荒涼所在,還有什麼? (2020年3月1日出版) ◆第二部 廢人與曖昧 / 不是想死,只是不知道怎麼活下去(2020年9月1日出版) ◆第三部 廢人與迷惘 / 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2021年3月1日出版) 【廢人心理學第三部】廢人與迷惘 / 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 「你說,都是記憶出現在你前面,你只是追著記憶跑。 你突然靈光一閃說,你的記憶都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它們都是被派出來應付你的好奇,難怪你老是覺得不對勁。 有時,你不由自主地這麼想:難道自己有什麼問題嗎? 不然何以會出現那些記憶,來阻擋自己的迷惘呢?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記憶, 你就會完全迷失了,像是個徹底失落的人。 難道一直緊抓著這些記憶, 就只是為了不讓自己被這種失落感淹沒嗎?」 從實況來看,有些地方,你細緻刻劃了自己沒有察覺的苦, 那些苦後來都四散,在無家可歸的經驗裡遊走。 你建造了美麗的城牆來安置那些遊魂暗鬼, 只因它們被拋棄了,也失去了起源於何處的記憶, 變成沒有名字的苦痛。 不再和原始起因相連結的苦和痛並不會暗暗消失, 反而四處尋找依附的對象, 於是生活到處都是苦、心裡充滿各種痛, 你淡漠那些苦痛,只覺得無以名之的迷惘...... 今夜,又是哪個晚上呢? ◎蔡醫師這本書的重點之一在於闡明理論與實作永遠有一道鴻溝,百年來臨床實務技術的修正,解決了某些問題,但也看到了其他問題...... 越來越多個案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邊緣型人格、是躁鬱症,自己會解離、有多重人格、有伊底帕斯情結,很容易產生移情等等,這或許意味個案對於自己的症狀有一定的認知,當然,也或許有更多的錯誤認知。透過網路媒介,有情緒困擾的個案自助管道越來越多樣化,這個趨勢對於心理治療工作者來說不見得是好事,假設診斷與症狀是一種防衛,一種阻抗,蔡醫師形容個案「只是說著一句死掉的語言」,然後安枕無憂、好整以暇地躲在一處庇護所或是蔡醫師形容的「古堡」中,也就是說,個案進入診療室前已經重度(再度)武裝(防衛)自己了。現今心理治療工作者面臨的現實挑戰是個案屬性從過去的neurotic與non-neurotic世代進入borderline與non-borderline世代,亦即個案的問題涉及更早期更深層的失落與創傷,人格碎裂的程度更嚴重,更缺乏彈性,治療難度更高。(李俊毅醫師) ◎在蔡醫師的大作【廢人心理學三部曲】第三部「廢人與迷惘」中,延續著廢人與憂鬱的核心主軸,這次所談的是千古不散的迷惘。好似說書人翻開了書,隨著聲音一落下,手杖一揮點,眼前就突然現出了婆娑幻化的潛意識,載浮載沉的看起來不太真實,但裡面會不會有著別有洞天的境地,或鬱鬱蔥蔥的桃花林呢?就這麼勾引人從幻境般的入口走探進來,讓人邊看邊猜想著「薩所羅蘭」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藏在古老村落裡到底有著什麼?為何會是心理治療師與病人交會的戰場?既可繁複遞變如萬花筒世界,又是每個人所建造出來的內在景象或用以保護自身的城牆?甚至「薩所羅蘭」它就自己活了起來,走到你的面前?!在【小小說】段落裡,從治療師第一人稱細膩的心思,看似具像化了潛意識幻想與心理治療中的潛意識交流(或交手),與艱緩的行走步調(或稱作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的技藝吧!)但其實卻更突顯出「迷惘」的本質是多麼地空洞,令人困惑與捉摸不定啊!(李芝綺心理師) ◎蔡醫師以拼接方式將不同形式卻觸及迷惘的生命故事和探究串接著,一篇小說、一份邀請、一場聚會討論、一個回應、一齣舞台劇,有如運用蒙太奇的處理方式,讓不同距離和角度的拍攝鏡頭重組,構成獨特的影片邏輯。這些被提取、看似無秩序的章節,以阿莎布魯的獨角戲在更高一層的觀點上進行串聯和編輯工作,讓現實的洶湧波瀾景象與無法言說之境,被聚合在一個層次中,產生強烈的對比與想像空間。每個迷惘的結尾,悲傷的阿莎布魯現身都讓我感到好奇,這個常被用來描述亂七八糟,行為不合理的用語,在賦予具生命的角色之後,既在暗喻這樣的生命本身便充滿了迷惑和茫然,也讓古老的故事有了新意,緊扣著「廢人與迷惘」《為什麼古老故事如夢魘般讓我受苦?》的核心佈展。(劉玉文心理師)
不是想死,只是不知道怎麼活下去:每個孤獨,都有自己的個性
對不少個案來說,活下來後,還要生活,生活反而比生存更難熬;他們拼命為了生存而活下來,卻不知道怎麼在日常生活裡慢慢地活著——這是人生的曖昧嗎?因為「曖昧」,治療師聽不懂個案的話,一如個案不懂治療師的話。但彼此都是為了要生存下去,左思右想,努力說出如何活下去的理論和言語。「生存」是只要活下去,但「生活」除了要活著,還要活得有自己的尊嚴、品味和風格...... 蔡榮裕醫師【廢人心理學三部曲】: ◆第一部 廢人與荒涼 / 生命荒涼所在,還有什麼? (2020年3月1日出版) ◆第二部 廢人與曖昧 / 不是想死,只是不知道怎麼活下去(2020年9月1日出版) ◆第三部 廢人與迷惘 / 對假我沒興趣,談真我只是空話(2021年3月1日出版) 【第二部】 廢人與曖昧 / 不是想死,只是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有無止盡的曖昧,有無止盡的閱讀 /劉又銘 在有盡的生命之中,不得不體驗生命的侷限,與死亡的破壞,累積於這兩方之間的體驗乃是無盡厚重,如何在有盡之間裝載得下無盡厚重的感覺?與之相處,有無止盡?在閱讀了蔡醫師於本書末的〈無可了解、無可確定、無可撫慰〉一文後,我興起了這樣的「疑情」,並想從這個點出發作為回應「廢人與曖昧」的起點。 廢人心理學三部曲第二部「廢人與曖昧」,蔡醫師再次發聲,一步一步鋪下通往心之深處的前進道路,在迂迴之中慢慢堅定前行。我們見到孤獨的廢人,從第一步的荒涼之中,再踏向這一步:曖昧。 踏入廢人心理學第二部曲的第一步,所見到的便是自有生以來即開始的難題:「每個孤獨,都有自己的個性——不是想死,只是不想活」(p.43)。我於是跟隨著這句話想起了,人生種種要死要活、半死不活的困難處境。存在於死活之間一息尚存的感受與思索,則為此提供了掙扎之地:那地方不是人間樂土,倒像是逃難之處,那地方經由「活下來」與「死掉了」的揉合,造就了死活之間留有曖昧的餘地。那地方有些什麼?做些什麼?是死?是活?可能不是我們以為的,那樣容易取捨的是非題選答,而是近似於對人生人死之間留有願望的申論題文章。蔡醫師的文章中,在這些地方不斷聆聽、探討、延伸與翻譯,閱讀這許許多多生死之間半死不活的心聲。 當閱讀下去,路越走越遠的時候,眼中所見乃是越來越多條蹊徑。藉著聽見並談論這些生死之間愛恨交織的心聲,我們是否能夠將生死之中的難題解析?可否藉著談得更多,彷彿誕生了走出一片荒原中的感受呢?一路的足跡,來自荒原的衝擊,那些死而復生的記憶,終究被發現蘊藏著更多想要活下去的失敗與成功。我們能窺見廢人們是如何與這些相處而走過荒原的嗎? 在本文中,「孤獨」是第一個登場的了,而且還很有個性,「每個孤獨,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個性,也有不同的命運,不是想死,只是不想活。就這樣,有著不同的銅像,走來走去,都叫做孤獨。」是啊,生的時候,死的時候,都有著孤獨的陪伴,孤獨做為兩邊的共同陪伴者,是很適合利用它獨一無二的存在,走來走去呢!生也孤,死也獨,人世間充滿孤家寡人(雖然實際上可能是在滿滿家庭中才成為孤家寡人的)、孤魂野鬼(不是想死,只是不想活,無法活)。孤獨與廢人怎麼樣走過來的呢?在這種難以陪伴的情況下,要陪著生死之間的難題。蔡醫師說,「甚至『孤獨』早就是自己長大的存在,不是人感到孤獨,而是『孤獨』不斷的依著自己的方式成長,它再回頭來說話,讓人感受到它的存在,雖然在先前它是被拋棄的。」(p.47)孤獨陪隨著廢人長大,或許像是不得不的紀念,無法哀悼故而凝結成為銅像,矗立在人生之中,做為保留那無法言說的感受存在之地的一個移動地標。 在有盡的生命之中,不得不體驗生命的侷限,與死亡的破壞,累積於這兩方之間的體驗乃是無盡厚重,如何在有盡之間裝載得下無盡厚重的感覺?與之相處,有無止盡?孤獨銅像夠不夠力能夠承載這些重量?孤獨需要幫手嗎?第二個登場的,是「曖昧」的舞台。 曖昧的舞台,有趣而令人玩味,因為有這個地方,各種可能變得得以「存活」。直觀地想起,青春年少時那曖昧不明的戀情,能愛?可愛?這愛能否被愛?被接受?所有混沌不明的憂愁與焦慮,不確定的信念,不可靠的期望,當愛情如果不被接受就彷彿只有死去一途的衝動,如此害怕,該如何跟這樣的自己相處?於是有了曖昧,於是產生了曖昧,於是在曖昧之中,不生不死,有愛有恨,那些陰晴難圓,於是借住在曖昧之地中,愛恨流動著。這是關於如何求其生不知可得否的曖昧。而關於聞其死不知如何否的曖昧,關於結束、關於家破人亡、關於再也回不來的淒涼景色,如何說出「啊,這就是死了」?很多時候太難,只好寄托給了曖昧。而在曖昧之中,那些說不清楚的話,也許有著「說不清楚」的任務,又要如何繼續說下去呢? 常常是,逃脫好像比理解什麼更重要,被曖昧搞得很煩,以為去曖昧化就好,將事情好好說出來就好。但套一句蔡醫師說的:如何才不會以為事情只有這樣子而已。蔡醫師說:「何謂『愛恨是難分難解』?真的是這樣嗎?愛和恨怎麼會分不清楚,它們不是條條分明的嗎?這是期待,很多人的期待,也許符合人性的期待,但是期待和實情可能是兩回事。(中略)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些語詞,讓我們遠離二元對立的說詞。」(p.57-p.62)我並不樂觀也不悲觀地,既正向也有負向地說,我們像是作繭自縛的靈魂,在生死之間被痛苦擺弄著,而發明了讓痛苦暫住的曖昧方式,接著反過來期待脫離這令自己窒息不已的感覺,然後又發現逃離了曖昧的沉重,要繼續前進時,回返的是痛苦的經驗。雖然,或許已經能夠以不同的方式逃脫,或是不同的方式讀取這些痛苦,這是否會是新的經驗呢?會是新的出路嗎?而又通往「無可了解」的哪裡呢? 在談論曖昧之時,蔡醫師有很有趣的書寫方式,用同樣的開頭語句,說了一段,再說一段,說了三段,也許用流行的說法是,因為很重要所以說三次!也許因為要為不同而各自存在的「孤獨」發聲:「憤怒的抑鬱、邊緣分裂和自戀的同時存在(中略)本文嘗試從這三種臨床現象,合起來談論技術的觀點(中略)它們之間有所差異,各有不同的話想說,只是本文是採取三者一起合談的方式來書寫。」(p.50-51)而我私自想的是,也許還因為這樣很有用。從廢人所說的曖昧的話語,在曖昧裡出發,一遍一遍的提問,爾後藉著一遍一遍的回答,走出了不同的生命。至少一遍又一遍之後,開始知道事情不會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在有盡的生命之中,不得不體驗生命的侷限,與死亡的破壞,累積於這兩方之間的體驗乃是無盡厚重,如何在有盡之間裝載得下無盡厚重的感覺?與之相處,有無止盡?我說啊,儘管已在這人世間看過許多次孤獨、曖昧、與廢人,是否仍也可藉著不同次的閱讀而每次得到了不同的生命? 那麼,閱讀有無止盡? 我想,可以的是,在時間的有盡尚未到來之前,再閱讀一次。 ( 劉又銘:臺中美德醫院精神醫療部主任、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門診兼任醫師)
生命荒涼所在,還有什麼?可撫慰與無可撫慰的分析
診療室的個案,除了重複訴說表象症狀外,更多的是無以名狀的孤獨感,彷彿一切的努力都只是在荒漠大地的獨自旋舞,「成功了要給誰看?」「人出生下來是一無所有,但是自己不會自覺,之後跟重要客體接觸,很快地,隨時都會經驗著失落......」如果「失落」是人終其一生要面對的課題,其衍生的「孤獨」「荒涼」感受,如何從精神分析的歷史脈絡再深入探索?臨床上的分析,可以撫慰到荒涼的地帶嗎?以在地的文化和語言,可否再進一步貼近西方專業術語的詮釋,讓術語融入在地生活,具有更細膩的精神內涵?蔡榮裕醫師【廢人心理學三部曲】:◆第一部 廢人與荒涼 / 生命荒涼所在,還有什麼? (2020年3月1日出版)◆第二部 廢人與曖昧 / 不是想死,只是不想活(2020年9月1日出版)◆第三部 廢人與真假 / 對假我沒興趣,談真我只是空話(2021年3月1日出版)【第一部】 廢人與荒涼 / 生命荒涼所在,還有什麼? 不是躺在床上當廢人,就是出門做事滿足他人。什麼都有,卻一無所有;什麼都不缺,卻一無所得;什麼都勝利了,卻一無所成;什麼都成功了,卻一無所獲。診療室的個案,除了重複訴說表象症狀外,更多的是無以名狀的孤獨感,彷彿一切努力都只是在荒漠大地的獨自旋舞,「成功了要給誰看?」「心理治療的工作,常相遇的是不少無名者無止盡的荒涼;他們看似循著生活的迴圈,卻是空轉著過日子,那種從內在折射出來的況味,是揮之不去、尋尋覓覓的身影,到底他們在尋找什麼呢?有的人尋找著『曾經擁有』,也有的人啟程是為了尋找那『從未擁有』,還有些人就像是配帶著一枚故事失傳的香火袋,此生總被提醒可以尋找......?原來,人不只是因遺失而尋找,也會因遺憾而尋找,也會因遺忘而尋找......我們能夠想像那種處處是暗示,但卻處處找不到指示的迷失感嗎?在荒涼大漠中,不是死寂般的荒廢,更不是荒蕪的不毛之地,或許,每個無名者都像是那倖存香火袋的化身一般,是重要的存在,但困難之處卻是史料尚不可考。」 (推薦序/陳瑞君)人出生下來是一無所有,但是自己不會自覺,之後跟重要客體接觸,很快地,隨時都會經驗著失落,這種失落是佛洛伊德在《哀悼與憂鬱》的說法,也是長大後,形成重要客體消失後,引發憂鬱的深層心理基礎——這是一片早已存在的荒涼地帶。(p.56)除了明顯外來的暴力和忽略所帶來的創傷,在嬰兒的日常生活裡,可能有什麼失落帶來創傷嗎?是誰給的創傷,或是任何人都是難免的,生而為人,必然就會存在創傷?如果這是真相之一,在分析治療的過程裡,是誰給自己真相呢?〈荒涼的所在,還有什麼?〉15篇短文從古典理論的後設心理學出發,摻入臨床經驗及社會心理現象,以生的本能、死亡本能、焦慮和歇斯底里為主要場域,作者試圖從精神分析的歷史脈絡裡再深入探索「憂鬱」、「失落」「孤獨」、「荒涼」等,在目前診療室裡常見又棘手的課題。臨床上的實作何以困難重重?也許可以如佛洛伊德或克萊因說的,那是「死亡本能」或「破壞本能」的作用。是「本能」派出什麼代理者,來跟我們交手,讓我們難以藉由言語和它們溝通嗎?而且是否有些失落的苦痛是無可撫慰?Antonino Ferro(2017)提出的精神分析的三個重要典範是,佛洛伊德、克萊因和比昂,其中比昂是以精神的「苦痛」做為焦點。〈可撫慰與無可撫慰的分析〉試著對臨床上的難題,提出一些想法,但並不認為這是精神分析取向的窮途,而是正視言語難以抵達的領域,重新思索詮釋的言語是否有它的侷限,而需要言語之外的撫慰,但卻又可能陷於無可撫慰的處境......〈精神分析的自由(free),是解脫(free)的境界嗎?〉作者探討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的養成過程裡,幾個值得再深思的課題。精神分析過程的真正自由是什麼?達到後就可以放下不評斷自己和他人的慾望嗎?或者需要是的解脫的概念和過程,才能做到不評斷人呢?雖然這可以廣泛被說是反移情,但需要更細緻的想像和探索這個課題,才有機會了解,在實踐精神分析取向這個外來技藝時,我們是如何動員已有的資源,來協助落實在地化,而這些被引用的文化、思想、宗教概念和實作的資源,可能讓我們有意識地觀察和思索,我們對於精神分析的貢獻是什麼的方式。依佛洛伊德的說法:「分析師如同鏡子般,反映個案內在世界」,精神分析取向者大都了解這比喻的困難度......鏡映個案的內在世界,是一種理想,卻是相當困難成為臨床事實。「鏡子說」是期待分析師可以做到如實如是的反映個案的內在世界,讓個案知道自己的狀況。如果以精神分析的焦點,從移情和反移情的觀察來說,要反映給個案知道的內在世界,除了一般人想像的之外,還要讓他知道生命發展過程,在說出來的故事或未說出的故事裡,自己內在的可能狀態。〈鏡子說和月亮說〉闡述佛洛伊德「鏡子說」的實然困境,克萊因「負面移情」的詮釋也是如同「鏡子說」般,接收陽光的投射,再直接反射出來。而葛林的「同理共感」,比昂的涵容、連結(linking)及思考理論的說法,就技術流程來說,是緩和了直接反射陽光般的技藝,採取消化(digesting)和思考過的方式,如同陽光被月亮本身的種種特性,轉折後成為月光才回應出來。精神分析的理論,是地面的心理地圖,或是天上的星空圖?〈地面的心理地圖VS.天上的星空圖〉談論催眠術、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和精神分析之間的差異,它們是如何被描繪的?地面的心理地圖以「一串粽子」為例,這是臨床常見的態度,也可能是簡化問題的方式,讓我們好像看見了問題,卻反而是走向死巷的過程。這反映著一般人對於抽象心理的不安,而希望在潛意識心理,能有具體且明確的連結,可以被清楚的辨識。這忽略了早年創傷個案,心理如破碎般的失憶和失聯,若期待過往的事件可以像粽子一樣,一整串拉起來,這和實情是有距離的。至於「一團迷霧」,是說明治療雙方在診療室裡的工作,有如在迷霧裡慢慢前行,這是我們跟潛意識工作的實情,也是如天上的星星,等待我們有更多想像和拼湊,去創造新的星象圖。〈記憶和夢境,是失落的起死回生嗎?〉是作者以石黑一雄的小說《無可撫慰》為題材的上課側記,藉由晚近的精神分析者的論點,加上作者的診療室臨床觀察,想從石黑一雄的個人部份經驗的說法,和他已出版的小說,來建構某種可能性——人的「失落」是如何存在,並藉由各種不同的形象,如不同的小說題材來展現自己?「失落」做為主角來展現自己的方式,如佛洛伊德的原本論點是「夢做了我」,而這些是「小說做了石黑一雄」,一如《夢的解析》是佛洛伊德的最佳自傳。如果心智的苦痛,果真如精神分析家比昂標示的,它是無可了解和無可確定,也如小說家石黑一雄開展的無可撫慰,那麼,內心戲的舞台上,這三個「無」會如何展現呢?37 篇〈掌中小說〉寓意心智結構的各個角色,輪番上場發聲。
失落的空洞感:在佛洛伊德的古典臉色裡找自己
在診療室裡,在意個案的治療師經常會遭遇到一種需要去體會個案的內在,原來到底是有一種「有」的特質還是「沒有」呢?做完工作後,是否在下一次的相遇一切又歸諸原點呢?失落與空洞的關係究竟是什麼?難道每一次與治療師道再見的失落,就讓人回到空洞裡了嗎?榮裕預設了失落造成空洞,直觀上確是如此,假如我們轉一個角度看,失落,是失落了自己原本的想像與自以為的「具有」卻未真的擁有,空洞似成必然。 《夢的解析》雖然是處理夢的潛在動機和意義,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佛洛伊德的自傳,因為比一般的人生記錄還更像自傳。這本書是十九世紀重要的文明之書,內容繁複,改變了人對於自己是什麼的認知。筆者試著以直接或間接和李宇宙醫師的接觸,以及2016年紀念演講會相關的一些細節為材料,說明濃縮(condensation)和取代(displacement)機制,做為了解佛洛伊德對於「夢工作」(dream work)的論點及其複雜性的方式,顯示夢境背後可能的無止盡故事。 在精神分析至今有限的焦點下,如果我們說嬰孩從母體出來、斷奶、原初場景、陽具欽羡和伊底帕斯情結種種挫折失落後,留下陰影和空洞,人要如何在這種處境裡,想辦法讓自己持續活著,仍能維持著對於未來的「錯覺」?這需要什麼必要的防衛機制呢?以及後來的人生裡,何以有著超高的理想,卻變成「殘酷的失敗者」,如同佛洛伊德所說的處於「潛意識的悲慘」?如何能在分析治療過程裡,走到「意識上的不快樂」呢?文明趕走黑暗後,黑暗去了哪裡呢?這才是主要追蹤的焦點,如果以目前的知識來說,黑暗推演出焦慮、憂鬱、邊緣和自戀...... 重讀古典精神分析理論,有趣的是何以當代「憂鬱症」是被接受的理由?何以有人說現在是「憂鬱」和「邊緣」的年代,而不再那麼強調是「焦慮」的年代?真的是如此嗎?我們從這些背景基礎,以佛洛伊德的《哀悼與憂鬱》和《在自我防衛機能裡的分裂機制》為核心,加上他的其它文章,觀看臨床上,「憂鬱」和「邊緣」的現行狀態,讓古典結合當代的新意。 在診療室裡,如果要掀開所謂「人性本質」,常是一場正面對幹的總攻擊,的確是一場冒險,偶爾還會是攸關生死的冒險,當然需要更多的謹慎。但是在文字象徵的工作裡,這種冒險的確值得做,反正就算是說錯了,或者說歪了,永遠有再校正的機會;精神分析和文學藝術的對話,談談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無謂的盛宴》,在微不足道的細微裡,看見了人性。
自戀的愛與死:水仙與櫻花
當我們提到『自戀』這語詞時,我們是在說什麼呢?我們確定大家之間說的是相同的事嗎?是一種很原始的,就是相信自己能夠活下去的意思嗎?或者連自己是什麼的概念也沒有,就只是一種神奇的能量或者思想,讓自己能活著並活下去,因此周遭給予的乳汁和溫暖,與自戀是相同的、等同的事物;這是如一般說的『人性的本質』嗎?希臘神話中,納西瑟斯(Narcissus)是一位俊秀的美少年,他出生時,先知預言,這個孩子若不看到自己,便可以長壽。有一天納西瑟斯到森林打獵,走到湖邊,水面中映射著他的影像,他癡癡地看著自己的美貌,從此迷戀上水面中的自己。他趴在水邊呼喚自己的倒影,日復一日,連暗戀著他的美麗的回音女神(Echo)也無法吸引他的目光。納西瑟斯陷溺在求愛不得的痛苦中,直到憔悴不堪,掉進水裡死去。在他死去的水邊,開出了瑰麗的花朵,英文名為Narcissus(水仙花),日日夜夜映照著水面。1914年佛洛伊德在「論自戀:一篇引言」中,引用納西瑟斯的故事,描述自己會愛上自己影子的可能性。1968年美國的精神醫學診斷條例(DSM)出現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自戀型人格疾患)的用詞。直到近代心理學,將「自戀」的通俗說法掛在嘴邊,其中的意義和認知有多少的不同?蔡榮裕醫師從精神分析的歷史觀點以及臨床實作的經驗,或敘或議,帶大家重新看待「自戀」的豐富內涵。本書第一部分,33則「小小說」,描繪的是治療場景。蔡醫師「意識流」的書寫,彷彿帶著我們,用「平均懸浮的注意力(evenly suspended attention)」,讓想像力自由流動在第一人稱(我),兩個第三人稱(他/她,治療師/個案)之間,重現個案和治療者在治療室中交會的瞬間。但文字的洗鍊,寓意的深遠,又的確像是在看小說。在閱讀中,讓人不時掩卷低迴,思考身為人無奈的處境。「她」或「他」的話語,呈現何種外在現實?又代表哪些精神現實?「我」的自由聯想,在治療室內外的穿越;在過去、現在、未來流轉;有時貼近有時遠離個案的感受和矛盾;有時喃喃自語充滿不解和疑問,在黑暗中掩卷低迴,在沈默中絞盡腦汁......,這些「小小說」彷彿上演一幕幕治療中的心理劇,讓我們一窺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室的日常,也同時享受閱讀文學的樂趣。(葉怡寧)第二部分包括三篇「雜文」:一. 〈語言的困境:自戀和本能相遇,如何說哈囉和再見?〉是蔡醫師在準備2018年9月16日由臺灣精神分析學會主辦的台中工作坊「愛自己的N種方式:自戀面面觀」演講的成果,由於在準備過程的書寫時,對於這個主題有不少想法同時湧現,因此成就了「自戀」的五個版本。二. 〈關於翻譯: 以「精神分析」來了解 psycho-analysis是可能的嗎? 〉探討不同文化的語言內涵的差異,我們可能將異國文字的精神完整的翻譯出來嗎?我們對於已經約定成俗的譯辭有多少失真的想像?回到診療室,治療者聆聽個案的過程,是否也像是不同國度的人,有相當個人化的意義附著在表面的意義裡?三. 〈回到佛洛伊德:歇斯底里的命運簡史〉蔡醫師回想自己與精神分析相遇的經歷,十七回文章一步步從理論發展談到與實作經驗的歧異,建議「提出疑問再回到佛洛伊德的文本裡,尋找古典說法,再往前走。」另穿插在文章之間的小詩,以一身器官、風景自然擬人喻意,爭相替心靈深處奔走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