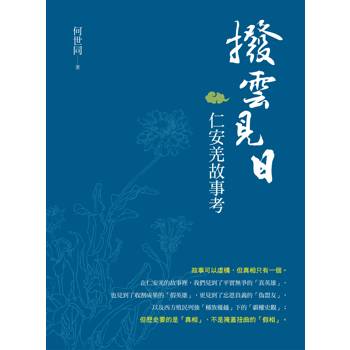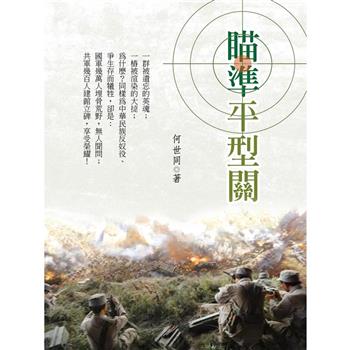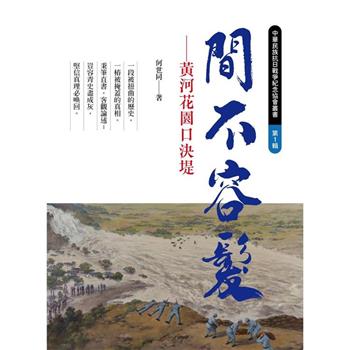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撥雲見日:仁安羌故事考
1942年「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作戰,雖然折戢沉沙,歸於失敗,但也有兩次卓越的戰場表現;一次是戴安瀾第200師堅守同古(東吁、東瓜,Taungoo) 13天的「防禦戰鬥」,另一次是劉放吾新編第38師第113團在仁安羌奮勇解救英軍的「攻擊戰鬥」。尤其後者,儘管參戰兵力只是1個小型步兵團,然而卻能一舉擊潰日軍1個加強聯隊,解救英緬軍7千餘人,加上順勢脫逃的英印軍及邊防軍、警察,共計約7萬人(見後文),成為守住印度的「有生戰力」,不但是中國自「甲午戰爭」以降,首次在「境外戰場」的勝仗,也影響了爾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展,歷史意義重大。遺憾的是,由於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政府就因內戰失敗而退到台灣,忽略了緬戰戰史的整理,又因受到一些中、外人物對真相的刻意掩蓋與扭曲,及1955年「孫立人案」的影響,致使這段歷史變得各說各話,而晦暗不明。為完整呈現本戰的全過程與結果,本書論述之範圍,開始於日軍「南方作戰」,結束於國軍解救仁安羌英軍脫困,並置重點於4月18、19兩日,在賓河兩岸戰鬥資料之耙梳,及相關史料檢視與考證。期能釐清事實,還原這段歷史的本來面貌,並論述「仁安羌大捷」在二戰中應有的歷史定位。
扭轉乾坤:石牌要塞保衛戰
1943年5月上旬,占領宜昌以西長江北岸之日軍,以3個師團、1個獨立混成旅團與若干支隊之兵力,渡過長江,向南岸之國軍第6戰區,發動所謂的「江南殲滅作戰」,國軍稱之為「鄂西會戰」。本戰日軍攻勢順利,以短短20天的時間,就由洞庭湖北畔之湖泊河流地帶,越過其西之丘陵地帶,一路打到鄂西之山岳地帶前緣。就在日軍即將攻入三峽,進窺重慶,狀況萬分驚險之際,蔣介石委員長急令國軍第11師死守三峽門戶的石牌要塞。師長胡璉將軍於受命後,率全師8千官兵,人人抱「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與日軍浴血苦戰7晝夜,不但擊退日軍,守住石牌,擋住日軍入川迷夢,使重慶轉危為安,而且還支撐戰區之反擊,恢復會戰前態勢,創造了「鄂西大捷」。苟無「石牌保衛戰」之勝,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之結果,恐怕是另外一回事。如同6月6日會戰結束時蔣委員長在日記中所說,守住石碑實為抗戰六年中最重要之關鍵;郝柏村先生也說:年輕世代要了解抗戰,不可不知石牌。
瞄準平型關
中國的「八年全面抗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主戰場;我們犧牲了三百二十多萬軍隊,死難了二千多萬人民,上億同胞無家可歸,擋住了日軍西進與納粹德國會師,牽制了百多萬日軍使其無法投入太平洋戰場,幫助同盟國家贏得了二戰的最後勝利。 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崛起,已成世界超強,也逐漸了解到「對日抗戰」的勝利,是全中華民族、包括兩岸中國人最珍貴的精神資產,遂開始在「蘆溝橋事變」、「日本無條件投降」及「南京大屠殺」等「標的」事件上,舉辦了高規格的紀念、慶祝與譴責儀式;雖值肯定,但是不夠。 筆者認為,為期抗戰與二戰中的盟國作戰接軌,奪回該屬中國的二戰「話語權」,最優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抗戰」不是為了哪一個黨派而戰?而是為了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而戰的認知。在這種認知下,才會深切認真地去還原抗戰的歷史真相;試問一場連真相都搞不定戰爭,如何能與二戰接軌?吾人以為,在那個中共積極謀求發展壯大的延安時期,將「喬溝伏擊戰」奏功,渲染成「平型關大捷」,可以理解;但八十多年過去了,在網路資訊如此發達的時代,仍擺脫不了「平型關大捷」的演義思維,則不能理解。 今天,雖然兩岸分治,惟俱屬中華民族。但願大陸新世紀的領導人,能完全放棄「內戰史觀」,以更寬闊的心胸,本實事求是精神,探討抗戰,還給中國抗戰的原本面貌,至少要讓國軍在「平型關之戰」陣亡的官兵英靈,也進入「平型關大捷紀念館」,或另建一館,規模小一點也沒有關係,以接受全中華民族同胞的悼念。果能這樣做,不僅無傷於中共的政權,更會贏得所有炎黃子孫的尊敬與掌聲。
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
1938年6月9日,國軍第1戰區在黃河南岸花園口,於「間不容髮」之際,決堤引水,造成廣大氾濫區,擋住了日軍沿隴海路西進的攻勢,成了中國「持久抗戰」改變日軍「作戰線」戰略構想成功的「臨門一腳」,但也給地區老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生命財產損失。然而這樁建立在犧牲平民百姓生命財產基礎上的禦敵行動,雖然成功,惟也寫下中華民族在「反奴役」、「爭生存」的對抗日寇侵略戰爭中,最悲痛、最無奈、最遺憾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