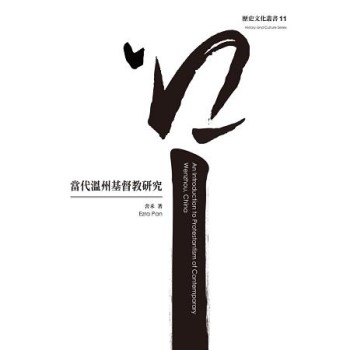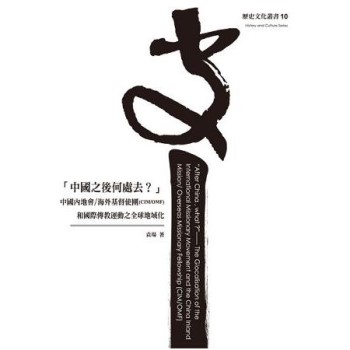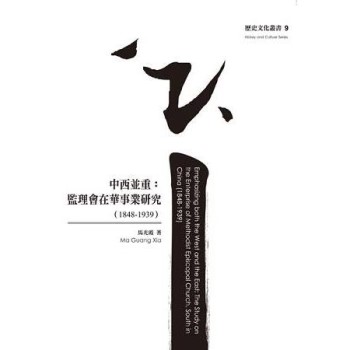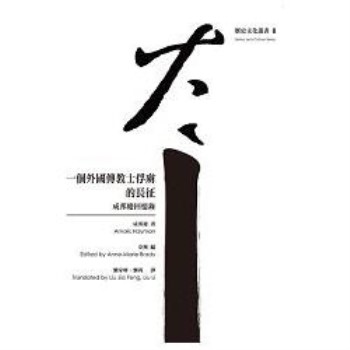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當代溫州基督教研究
本書的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筆者從不同層面、不同渠道展開資料的收集,並以學術規範的要求進行創作。 1、第一手資料:親歷當代溫州教會 《歷史》需要閱讀大量的文獻材料,進行嚴謹地考證。《當代溫州基督教》則增加了親身經歷,感同身受。筆者出生在溫州的鄉村,十歲蒙恩重生,十二歲開始講道,十六歲來到溫州城,二十七歲前往美國讀神學,在美國有十年的學習和事奉經歷。地理和空間的跨越(從農村到城市),使筆者對溫州教會有更為全面的認識。自身身份的變更(從鄉下人到城裡人),使筆者對溫州教會的內在狀況有更為切身的體驗。此外,筆者先後事奉的崗位包括兒童主日學、民工福音、大學生、青年團契、福音組、栽培組、加州硅谷留學生事工、華人教會牧會等。更加有趣的是,筆者童年的母會曾經加入過「三自會」,又在幾年之後脫離「三自會」,因此,筆者也經歷過在「三自會」,出「三自會」,後在家庭教會成長及事奉。筆者是當代溫州教會的目擊者之一,也是當代溫州教會拼圖上一個細微的部分。這一切都為本書的創作提供全面、客觀的幫助。 2、寬廣的視角:以普世眼光看溫州教會 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於溫州教會,筆者作了十七年的「當局者」,之後也作了十年的「旁觀者」。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擴大了筆者的人生視窗,讓筆者懂得了如何以普世的眼光看待溫州教會。因此,本書並非是一本「流水帳」,其內容包含豐富的敘述,切中時弊的分析,以及將溫州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所作的銜接。 3、詳實的資料:從溫州社會看教會 由於本書描述的是當代溫州基督教(眼前的歷史),所以,除了自身主觀體驗外,在創作過程中也閱讀和參考溫州地方性的報刊,如《溫州日報》、《溫州商報》、《溫州晚報》、《溫州都市報》、《今日永嘉》、《瑞安日報》;政府機關報刊,如《溫州統戰》、《瑞安政協》等;溫州企業報刊如《現代集團報》、《溫州市人民醫院報》等;以及溫州之外的報紙,如《浙江日報》、《西寧晚報》等。 4、創作的規範:從學術層面看溫州教會 筆者在美國修讀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其過程能不斷提升筆者的學術能力。本書的創作符合學術的規範和要求,從學術的層面闡述溫州教會的處境與現象。為了增強學術品質,筆者也搜尋和閱讀大量學術界、社會各界對溫州的論述性期刊文章,內容和範圍涉及溫州經濟、教育、社會、民生、宗教、史地等,這將更加充實全書的內容,使全書血肉豐滿,且具時代的親切感。
中國之後何處去?
在宗教與國際關係研究領域中,現當代國際傳教運動的議題日益引起學者的關注。然而,尚未有學者對「中國因素」在新老傳教運動交替轉型過程中的作用加以深度梳理與剖析。本書選用了「中國內地會/海外基督使團」(CIM/OMF)這一國際傳教機構作為研究对象,試圖超越純組織學進路、描述性個案研究的舊套,結合國際關係學、社會學、差傳學和史學的研究成果與分析方法,通過對該「老中國通」傳教組織之轉型與發展的解析研究,展示宗教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在方法論層面的新潛能。通過這一中階命題的個案分析,結合歷史與現狀、理論與實踐、差傳學思潮與國際關係現象,展現西方傳統居重的基督教如何在影響了中國的同時,也被中國影響和改造,而基於「中國經驗」的傳教活動如何對國際傳教運動產生催化和制約這兩種自相矛盾的張力。作者選用全球化理論家羅蘭•羅伯茨頓(Roland Robertson)所提出的「全球地域化」(Glocalisation)之概念來演繹中國基督教在整個國際體系中所占之地位與影響,而CIM/OMF的案例研究正可用以展示全球範圍內「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基督教之普傳)和普遍主義的特殊化(各國各族教會的本土化)」兩大交叉並行的過程,並彌補目前相關研究停滯與缺乏實證研究的空洞理論建構。
中西並重
美國監理會在近代來華差會中並不是一個大差會,但是該會卻在近代中國留下深刻的影響。思想開放的林樂知教士創辦了晚清最具影響的中文報刊《萬國公報》,成為許多近代中國思想家的啟蒙讀本;他們又創辦了第一流大學(東吳大學)、中學(中西女塾),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一流的人才(謝洪賚、宋耀如、宋慶齡、吳經熊、費孝通、趙紫宸等)。為什麼監理會能在中國建立起包括佈道、文教、醫療衛生、婦女成長等在內的龐大教會事業?它的經費來自何處?它的人力支撐是什麼?顯然本土社會在其中發揮了相當關鍵的作用,但本土社會究竟是怎樣與教會關聯互動的?通過什麼機制實現互動?所有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討論,本書即對這些關鍵議題做了深入的觀察和分析。 從監理會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看,地方社會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客體,在等待基督教與之相遇,而是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基督教在此既是外來的,又是本土的,所有外來性元素都參與了本土社會的建構,而中西兩種元素塑造的基督教社區具有不同於傳統地方社會的鮮明的複合文化特徵。監理會憑藉佈道、醫療衛生、教育、文字出版、社會服務等活動,與當地信徒和民眾在宗教認同或不排斥的基礎上在不同的地域建立了涵蓋不同內容的若干基督教社區,嵌入到當地社會之中,不自覺地與當地社會一起參與到近代化發展的歷史潮流中;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有別於當地社會,西學元素較多的基督教社區,其所開展的教育、醫療等現代化活動,為當地社會的教育及醫療等事業提供了學習的範式。 作者也發現,監理會將傳教總站設在傳統江南最核心的城市蘇州,同時又在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上海謀求發展空間,其傳教觸角分佈環太湖流域,監理會的傳教圈與中國最具活力且傳統積澱極為深厚的江南經濟文化圈的重合,可能正是該會能在近代中國發揮重大影響的關鍵所在,馬光霞博士對此的立論和分析實是一項重要的發現,值得學術界予以關注。
一個外國傳教士俘虜的長征
中共的歷史著作已經把二十世紀三○年代共軍在中國內地的「長征」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神話。當時的潰敗現在被描述成勝利。長征途中的暴力、絕望和迷惘都在官方歷史消失。成邦慶的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紅軍營地嚴酷的生活畫面,還原了被扭曲的歷史。 本書是紐西蘭傳教士成邦慶 (Arnolis Hayman) 跟隨紅軍長征的回憶錄。1934年10月2日成邦慶在貴州被蕭克的紅六軍團扣押,跟隨紅軍長征413天後被釋放。本書忠實地「記錄了紅軍長征的一個側面」,內容有他們被俘、談判與釋放的經過,也有關於紅軍戰鬥、艱難行軍及政治宣傳等的記錄,更多是長征途中的日常生活細節,讓讀者如同置身歷史現場,對復原紅二方面軍的長征歷史及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都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目前所見關於紅軍長征的歷史敍述中,最具史料價值的文獻應該是《紅軍長征記》,這是一本由眾多親歷者回憶錄編纂而成的作品。這些回憶錄都是在長征結束不久完成,沒有後來的思想路線鬥爭等條條框框的限制,因而被當代史家高華看作「最真實的長征記憶」。由外國人撰寫的長征回憶錄現有:共產國際顧問李德(Otto Braun)寫的一部,他在1932至1937年間與中共一起生活和工作,還有內地會傳教士薄復禮的兩本書,以及成邦慶的回憶錄。 其中成邦慶的手稿一直湮沒無聞,直到2003年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安琳教授(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亞發現原稿,整理後於2010年在美國出版。成邦慶手稿的特殊價值在於他獲釋後就立即撰寫,內容翔實豐富。手稿是非常個人化的敍述,記錄了成邦慶作為紅軍人質的生活,也描寫了紅軍擺脫政府軍艱苦而快速的行軍歷程,以及日常生活中不時發生的暴力。成邦慶是個富有經驗的作者,他已在中華內地會雜誌《億萬華民》上發表了許多關於傳教工作的文章。 成邦慶對他被俘經歷的記錄展示了較為全面的長征圖景,揭示了當時共軍儘管面臨許多困難卻仍能團結一致的原因。中國共產黨黨史裡的長征集中於毛澤東以及他與其他領導人的關係,成邦慶回憶錄卻記載了中共其他高級將領和中級將領如賀龍、王震、吳德峰、戚元德等人的故事。中華蘇維埃區的生活是怎樣的?長征的生活是怎樣的?中共軍隊如何讓士兵保持忠誠?中共如何向大眾灌輸他們的基本理念?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都可以在成邦慶回憶錄中找到答案。成邦慶回憶錄是他對紅軍近距離的忠實觀察和毫無保留的記錄。這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資料,72年之後才得以公佈於眾。 本書第一章至第十八章,主要是論及被俘及紅軍控制底下長征的故事。成邦慶和他家人的被俘是被精心策劃的,而薄復禮和妻子只是他們在拜訪成邦慶後的回家途中不幸撞上中共部隊。成邦慶回想起在他被俘的數周前,有兩個湖南人來拜訪他,他們似乎在搜集情報。當紅軍最終到達舊州時,他們逕直到了成邦慶的住所。他和他的妻子被扣押,他們的屋子也被洗劫。紅軍對他們的態度讓成邦慶和他的孩子們感到懼怕,這些人稱他們為「帝國主義間諜」,威脅要殺了他們。這群被俘獲的人總共被罰贖金70萬鷹洋,每人10萬鷹洋。雖然妻子們和孩子們因成邦慶和薄復禮的「間諜」行為同樣被罰,但紅軍第二天就釋放了他們,並指導他們如何為所有人獲取贖金。成邦慶、薄復禮和他們的同工林榮貞小姐被迫加入了長征隊伍。 成邦慶和他的家人及同工被自稱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的軍隊俘虜,書裡記錄了對他們著裝的印象。書裡亦披露了紅軍戰鬥力方面的資訊,但經常是無意的。例如紅六軍團通過無線電與紅一方面軍保持密切聯繫,因為他們最初的無線電報員在之前的一次戰役中犧牲,他們不得不讓被俘的一位政府軍話務員繼續為他們工作。 此外紅軍戰士每隔兩周會得到「零花錢」,去購買小吃和其他生活用品。因為他們的特殊狀況,成邦慶和薄復禮最終也享受到這項特權。紅軍用以購買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的「零花錢」來源於劫掠,劫掠是紅軍戰士例行的職責之一。成邦慶的回憶錄提供了許多長征中日常生活的細節,揭露了士兵經常面臨飢餓,因為軍隊資源的供給僅是靠徵用。有時士兵會從傳教士那裡偷取食物,成邦慶和薄復禮的家人給他們送去的食物經常被紅軍將領沒收。紅軍以為所有外國人都很富有,因此他們的劫掠行為是公正的。較中國人而言,西方傳教士過著相對奢侈的生活,雇用了大量僕人等等,他們被認為是大地主,也由此被當作大地主來對待。成邦慶自己根本沒有錢,但他很難說服審訊者相信他經濟困難。 唱歌是政治教育的一個重要手段,大多數人是文盲。讓成邦慶尤其惱怒的是紅軍中流行的一首歌是「殺,殺,殺,讓整個世界灑滿鮮血」,其旋律竟然與一首很有名的基督教聖歌「耶穌喜愛一切小孩」完全一樣。 最後一章十九章論及成邦慶的釋放,經歷413天的囚禁和被迫行軍後,成邦慶突然被告知他可以獲釋了。成邦慶1935年11月18日獲釋,那一天,蕭克和賀龍的部隊最終離開他們被蠶食分割了的蘇維埃根據地,動身與張國燾將軍的部隊會合。成邦慶獲得自由,是因為他身體太虛弱,無法在長征中行軍,但薄復禮沒有獲釋,因為他對再次行軍的紅二軍團和紅六軍團仍有價值。 成邦慶在長征途中極端困難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勇氣和謙卑,為他贏得身後的名譽,也為中共黨史中一段關鍵時期提供新的視角。
修辭.符號.宗教格言
本書以晚明耶穌會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c. 1566–1640)譯寫的格言集《譬學》(1633),與英國國教牧師亨利.皮坎(Henry Peacham, Sr., 1547–1634)纂輯的文藝復興修辭格手冊《說苑》(The Garden of Eloquence, 1593)為平行研究標的文本,而以列日學派(Groupe µ)的《普通修辭學》(Rhétorique générale, 1971)及佩雷爾曼(Chaïm Perelman, 1912–1984)的《新修辭學》(Traité de l’argumentation: La nouvelle rhétorique, 1958)兩本歐陸新修辭學專著為分析的準據。 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嘗論譬法十種,其論述的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即譬喻中「已明的所取之端」與「未明的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進一步實踐說教與證道的宗教功能。而列日學派提出普通修辭理論的本意,是欲藉現代結構語言學的分析模式,提供更為科學而具系統性的辭格分類方法。因此本書之論旨有二:其一,以皮坎《說苑》中的文藝復興修辭格分類系統,比對高氏《譬學》中各式設譬手法;其二,以列日學派提出的修辭操作模式──抑損、增添、增損、更序──分別重新檢視《譬學》與《說苑》中的語形(metaplasms)、語義(metasememes)、語法(metataxes)、邏輯(metalogisms)四種修辭格,並以佩雷爾曼所謂「論辯」(argumentation),解讀無法歸類於列日學派修辭理論中的其餘辭格。於此架構之下,本書分為五章進行析論: 第一章 本章首先爬梳兩部標的文本與文藝復興修辭學傳統間的關連,並藉由對西方修辭學史的討論,建立本書並時性研究的歷史實證性。其次,高一志在《譬學.自引》中的論述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而一則譬喻中的「所取之端」與「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則成為本書申論的起點。本章最後將引導修辭問題至更為深入的結構語言及符號層面,即「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 第二章 本章以語義辭格的分析為出發點,討論上述「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語義辭格討論的是字詞(或小於字詞的單位)與內容意義間的關聯,四種主要轉義俱屬此類。若按《譬學.自引》中所謂「由顯推隱,以所已曉,測所未曉」的設譬原則著眼,則本書欲解答的「為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問題,應由兩個語彙單位(lexeme)間如何形成表達形式的轉換著手;易言之,這也是語言符號中符表(signifiant)與符旨(signifié)的形式與內容問題。 第三章 《譬學.自引》所析「明、隱、直、曲、單、重」六種譬法,都屬於語義辭格的探討範圍,而以重譬為界,之後的「有解、無解、對而相反、無對而疊合為一」四種譬法,除了仍依高氏所謂「兩端相類相稱」的基本法則施譬之外,已經由單純的「轉義」(trope)進入「句式」(schemate)的解析而成為另一個譬法討論範疇,本書也由此進入語法辭格的分析。本章由《普通修辭學》中零度及偏離的理論為始,分別析論《譬學》與《說苑》中語法辭格的四種修辭操作。 第四章 前文已析的語形、語義、語法三種辭格,乃基於語規(code)而成,建立在「文法↔修辭」的關係之上,而本章討論的邏輯辭格則基於符物(object)與符解(interpretant)間的聯結,建立在「修辭↔邏輯」的關係之上。《說苑》中仍有相當數量的辭格無法納入列日學派的辭格總表,而這類辭格在譬法與句式的背後,往往還涉及價值判斷──比方格言背後欲傳達的宗教意蘊。本章藉由佩氏《新修辭學》中的論辯及非形式邏輯理論,補充《普通修辭學》無法解讀的其餘辭格。 第五章 引發佩雷爾曼《新修辭學》理論的關鍵問題是「價值判斷能否通過推理加以證明」,佩氏的這則提問亦為本書關懷所繫,即宗教上的價值判斷能否藉修辭的操作而致正面的效果?譬法與句式的運用不僅只是表面的修辭現象,其背後牽涉的是在四個修辭場之外以勸服為目標的論辯。本書最後提出對列日學派普通修辭理論的檢討,也在修辭、論辯與證道三者間覓得關聯,而重新看待本書發軔的可見與不可見兩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