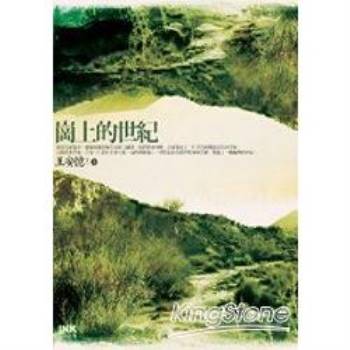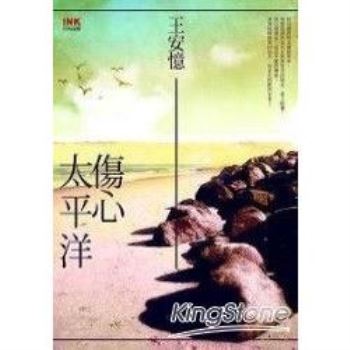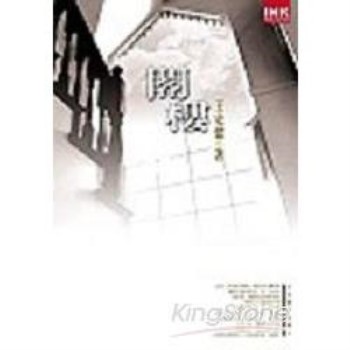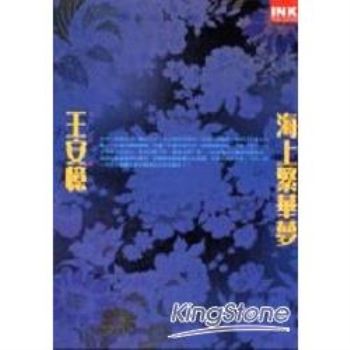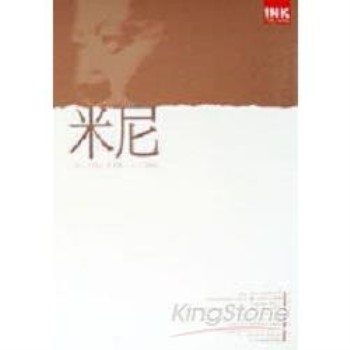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崗上的世紀
他們亢奮起來,緩緩地優美地在涼席上翻滾。他們閉著眼睛,涼席變成了一片茸茸的開著紅花的草地。太陽照著草地,只有一片雲彩下著小雨。這快樂抵過了一切對生的渴望與對死的畏懼,開創了一個極樂的世紀。命運 懸而未決。是選擇 被動等待 而 錯過?還是 主動創造 卻招致 毀滅?王安憶的中篇小說:荒曠寂寞,卻激情流溢有別於中後期以上海為場景的寫作,八O年代崛起中國文壇的青年小說家王安憶將鏡頭從城市調度到鄉野,在天開地闊的田埂間、以文字搭架兩座似幻還真的農莊「大楊莊」、「大劉莊」,有如人性的密室實驗,讓外來下放知青與本地農村幹部在其中互相試探、扮演、步步為營、短兵相接,卻終將卸下看似無交集的階級面具,暗傷累累,奔赴相同的命運洪荒……
傷心太平洋
詩是什麼?是命運;命運是什麼?是詩。王安憶關於詩的兩部精采中篇!穿越時光遙隔與茫茫人海,以小說寫就溯尋家族漂流命運的詩,以及窮究詩與詩人命運悲劇源頭的小說──◎傷心太平洋背景是太平洋的一隅的新加坡,從苦難中站起來的「獅子城」;敘事者訪溯一個家族漂浪於島嶼間的身世與故事,處境與情感的流轉:從祖父到父親,從南洋到大陸,從二○年代的小漁島到今日的花園國家,筆端到處,宛如親歷。堪稱王安憶作品中難得一見充滿南洋風情與海外視野的家史傳奇悲喜劇。◎神聖祭壇詩人發願要寫下一首一萬行詩句的長詩,詩人的女追隨者想要接近他的人生──他知道這首詩是自己生命意義的開始與終結,她卻看到他人生的堅強與軟弱。兩人彷彿共同經歷一場浩劫,充滿激情,又極度疲倦。他們因此註定要漸行漸遠;詩人完成了他的詩,毀了愛情,毀了別人,也毀了自己。
流逝
這本集子所收的兩個中篇<流逝>與<「文革」軼事>,情節極其簡潔,簡潔到其實以短篇的篇幅就可以呈現。但是王安憶卻以中長篇的篇幅來敘述故事內容,多的便是對物質瑣事外在世界以及人物角色內心世界的細節描寫,千言萬語,綿綿不盡。小說中那細膩的、似乎永不止息的綿長敘述正是王安憶小說的特色與其引人入勝之處。 在<流逝>中,女主角端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擔負照顧全家大小的重任,每日在窘迫的景況中張羅衣食,辛苦工作,處理各種棘手事務。雖然端麗也曾暗自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力強一點」,好讓她依賴,但是她終究由一個小鳥依人的富嬌女磨鍊成獨立幹練的家庭主婦。經過十年的苦難後,端麗夫家的抄家物資與房舍得到歸還,生活回復到文革前的情景。從工作的壓力中解放出來,端麗雖然感到安慰,卻也深自悲哀。她的日子在逛街、舞會的揮霍中變得無聊煩悶。她時常回想:「當時自己是多麼能幹,多麼有力量。那個能幹的女人這會兒到哪兒去了呢?而且,究竟那個能幹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裡充滿了一種迷失的感覺。」時代造就端麗,但卻無法接納她的女性自覺。在歷史的洪流中,端麗期盼文革苦難十年的成長經驗「不會白白地流逝」,究竟只是一個中年女性謙卑的願望。 <「文革」軼事>以「文革」為篇名,說的卻是城市的故事。政治的文革只是做為一個引子,引出張家兒女彼此之間的恩怨情仇,以及他/她們與上海這城市合而又離的糾纏關係。在小說一開始,資產階級出身的女主角張思葉因文革而「受盡損失」,工人階級出身的男主角趙志國也處在「沒有位置」的虛空狀態。當趙志國跟隨張思葉從「後門」走進張家,他驚訝地發現張家房子是上海城市的縮影,他「走進張家這房子可說是他首次親身體驗這城市的繁榮景象」。住進張家後,趙志國憑著英俊瀟灑的外表、能說善道的口才與他對上海都會生活菁華的領會,「得到」張家全家人的喜愛與倚重,成為張家的主角。而小說的結尾則呼應開端的「損失/得到」辯證,來呈現上海人與城市的合離關係。當初趙志國在張家占有一席之地,是藉著張家在亂世紀律鬆懈的方便。張家父親在隔離審查回來後,重整紀律,規畫分房。趙志國與張思葉覺得受了委屈,決定去杭州,離開上海,他/她們了解到:「這個家不能待了,上海也不能待了……這本就是一個受損失的時代,假如得到什麼,結果就是加倍地失去」。
閣樓
<閣樓>描寫一位執著於節源研究的科技人才,為了宣導上海市民採用他苦心研究出來的省煤鍋爐而四處奔走。從機關部門到街坊巷弄,他越是大力推廣就越是遭到拒絕、處處碰壁。更糟的是,他為了取信眾人而隨意亂發的鍋爐製造圖,竟被不肖者盜用,製造出劣質品在市面上販售。然而完全不求圖利只為推動理想的主角,最後還是擇善固執地選擇沿鄉挨鎮地繼續宣導他節約能源的理念。 <悲慟之地>描述幾位從山東鄉下第一次進到上海大城來的年輕人,因為片面的判斷而誤以為上海民生急需大量的薑,因此懷著發財夢、擔著大批的薑進城準備大發利市。結果,不但薑賣不出去,同行幾人猶如誤入叢林般地在上海鬧區裡逡巡穿梭,其中一位更墜樓而死。 <阿蹺傳略>描述主角阿蹺因為身體先天上的殘疾,所以一直活在外界「平等」的「差別待遇」裡,他深知如何讓別人對他處處遷就忍讓,然而這樣的匱缺/優勢卻導致他變成一個十足的無賴。最後阿蹺卻意外地在一場專注認真的走路過程中,贏得他生平第一次最真誠的尊敬與尊嚴。 <人人之間>描述一個頑劣小學童與一位溫吞的小學教員,兩人彼此乍暖還寒的情誼交流;<阿芳的燈>像是一篇恬適的散文,透過敘述者「我」娓娓托出一股平穩紮實的生命力。這兩篇作品看似素樸,卻貼近生命最實在而敏感的層次,寫人與人交往的微妙關係、寫綿密不盡的奮鬥生活……,在在表現出作家對現實環境的細膩觀察與複雜人性的好奇探究。
海上繁華夢
第一個中篇〈海上繁華夢〉寫了五則故事,以幾近傳奇的筆法,描摹出黃埔江碼頭蘆蓆篷小船間被女子誘引入夢的水手;靜安寺前法國勇士環龍駕機在十里錦繡的海市蜃樓沖飛上天的魔幻奇景;著玻璃絲襪的精明城市女郎;陸家石橋下活埋的「千人踩,萬人踏」淒豔女鬼;以及藉名旦巧妙扳轉劣勢的冷門醫生。 第二個中篇〈好姆媽、謝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講一個原本善良幸福的弄堂人家,因為夫妻倆不孕,千辛萬苦終於收養了女娃妮妮,卻不料妮妮漸長後,一再為偷竊問題引起糾紛,造成夫妻倆彼此仇恨,連一向照顧愛護她的保姆小妹阿姨都束手無策,只好把她發配邊疆甘肅,試圖重新找回過去的平靜。然而,這一家人早已在對付妮妮的過程中,變成了三張傷害而殘虐的臉。 第三個短篇〈鳩雀一戰〉,是小妹阿姨為將來的居住打算用盡心機,卻終於期待落空,黯然向命運低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