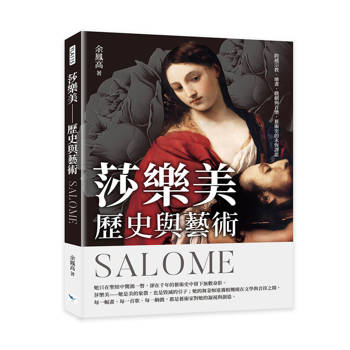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莎樂美─歷史與藝術:跨越宗教、繪畫、戲劇與音樂,藝術史的永恆謬思
希羅底的女兒進來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歡喜。王就對女子說,妳隨意向我求什麼,我必給妳。又對她起誓說,隨妳向我求什麼,就是我國的一半,我也必給妳。──「我願王立時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裡給我。」莎樂美說。貝諾佐.戈佐利〈莎樂美的舞蹈〉: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性敘事與人物對比早期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貝諾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 1420-1407)以油畫〈三王行列〉和為佛羅倫斯梅迪契.里卡爾小教堂所作的一組壁畫而聞名。他於1461年創作了一幅〈莎樂美的舞蹈〉(The Dance of Salome)的油畫。此畫以莎樂美為中心人物,她在向希律獻舞,而這位王者是幾乎有些驚恐看著她的舞蹈,王后則坐在一旁;其他的人表情各異,顯示了不同的心態。作者特地將施洗者約翰的被殺安排在左邊的一個角落,使主題形成強烈的反差。整幅作品場面宏大,色彩濃烈,風格與中世紀的繪畫完全不同。莎樂美題材的文學傳承不僅是中世紀和文藝復興前後,就是19世紀、甚至20世紀的作家、藝術家,對莎樂美的傳說,也同樣會像早些年的藝術家一樣的熟知和感興趣。同樣也就不難理解,莎樂美的故事就很自然地會受到眾多作家的青睞,激發他們投入自己的情感來重現這一故事。布萊恩.派克(Brian Parker)在〈斯特林堡的「朱麗小姐」和莎樂美的傳說〉(Brian Parker: Strindberg’s Miss Julie and the Legend of Salome)中曾作過統計,說是至1912年,僅僅在法國,就難以置信地竟然有2,789位詩人、作家曾運用過莎樂美的故事作為他們創作的題材。當然,這些作品,大多都沒有流傳下來,如今所知的以此題材創作的最著名作家,主要有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等幾位。馬拉梅筆下的莎樂美:超越故事表層的美學追求雖然眾所周知,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已有大量的繪畫再現過有關莎樂美的故事,但是一直追求作品個人特色的馬拉梅表示,他不想從這些藝術家的創作中獲得任何啟示。研究者相信,馬拉梅描寫希羅底、莎樂美和施洗者約翰的關係只不過是表層的主題(ostensible subject),馬拉梅的〈埃羅提亞德〉的真正主題是美。馬拉梅在1865年2月給歐也妮.勒費弗爾(Eugene Lefebvre)的信中就說過:「既然我的女主角被名為莎樂美,我就要使〈埃羅提亞德〉像開裂的石榴那樣烏黑又鮮紅,我的目的是創作一個純潔的美夢和獨立的故事。」 他創作〈埃羅提亞德〉,是要像寫〈花〉一樣,對玫瑰似的鮮血的讚美,也就是對死亡的讚美。居斯塔夫.莫羅〈幽靈〉:莎樂美的誘惑與象徵在所有近現代有關莎樂美故事的繪畫作品中,最著名、影響最大的,是首推法國畫家居斯塔夫.莫羅創作的〈幽靈〉和〈莎樂美的舞蹈〉。 〈幽靈〉在布滿色調的畫布上,運用了富有特色的光,以提高其明亮的、類似寶石的色彩效果,充滿夢幻的情色成分和熱情。畫面不僅色彩華麗,具有濃重的異國情調,特別是莎樂美的紗巾和舞姿所顯示出的挑逗成分,使人覺得畫家是有意以充滿夢幻的情色成分,強烈地表達了莎樂美在舞蹈中的熱情。一位論者這樣描繪這幅畫:「他對她的種族、國家和時代不作確切的描述,……只讓它在一個世界歷代藝術家組成的博物館裡棲居下來。」 沒錯,〈幽靈〉曾在西元1876年的巴黎沙龍和西元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展出,十分為人所欣賞,引起極大的震盪,並極大地影響了很多作家、藝術家的創作。本書特色:本書深入追溯莎樂美的歷史淵源與聖經背景,從考古與傳說中尋找她真實的面貌,並橫跨繪畫、雕塑、文學、戲劇、音樂、舞蹈與電影等藝術領域,探討她如何成為西方文化中象徵「愛與毀滅」的經典形象。透過大師之作,呈現莎樂美如何在不同時代中被重塑與再現,是一本結合歷史考證與藝術賞析的跨領域研究之作。
帕格尼尼的手:死亡之吻、木乃伊詛咒、吸血鬼傳說……對文藝軼聞趣事的獨到見解,余鳳高藝術隨筆集
水中精靈昂丁與人類的愛恨糾葛,如何從煉金術士的筆下,變成流傳百年的文學與藝術經典?戴著鐵面具、身份成謎的囚犯,是王室的祕密、政治的醜聞,還是歷史上最無解的傳說?安徒生筆下的《夜鶯》,藏著這位童話大師對「瑞典的夜鶯」珍妮林德怎樣一段動人又無望的愛情故事?受到小說影視渲染的法國傳奇「鐵面人」這名罪犯在獄中所受的待遇非常好,只是有兩名槍手隨時站在他的身旁,奉命如果他卸下面具,就殺死他。而他無論什麼時候,總是戴著一副鐵製的面具,即使吃飯、睡覺,也沒有卸下來過,甚至他死後還戴著這面具。只是他的身分,就連皇宮裡的人也覺得是一個謎。文學的奇幻,實際上是為了重溫一場不復存在的愛學史和作家傳記的大量例證表明,完美的愛情只會帶來幸福的婚姻,而不得回報的愛情才能激發作家創作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對珍妮的苦澀之愛萌發在安徒生的心底。既然不能再在所愛之人面前表達,那麼只能藉由自己的作家之筆來表達。親愛的夜鶯,我是多麼地想描寫妳……事實和傳說交織,「希望鑽石」的無盡爭論事情起於一則古老的傳說:世界上有一顆碩大的藍色鑽石,十分名貴。但當它被從印度的一位神像身上摘下,也就是偷走,落入某個人的手裡時,就會有可怕的詛咒降臨到鑽石主人和觸摸過它的人身上。不管這個傳說是否可信,與藍色的「希望鑽石」有牽連的事故,確實發生過很多次。本書特色:本書為著有多種文藝專書的名家余鳳高所著,透過藝術隨筆的形式,精心編織出一幅跨越歷史與文化的華麗圖景。作者以細膩的筆觸,探索文藝界充滿魅力的題材,並挖掘華格納、畢卡索等名士的內心世界,展現人性、命運與藝術的深刻交融。本書將歷史、藝術與人文精髓融為一體,是一部既知性又感性的閱讀饗宴。
徐悲鴻論藝境──審美是一生的修行:以美支配藝術,以藝術傳遞美,凝聚中西藝術精髓,塑造一生的審美境
徐悲鴻,集藝術家與教育家於一身的偉大先驅,以其卓越的繪畫技藝和深邃的美學思想,成為中國現代藝術的開拓者。他不僅以西方寫實技法革新中國畫風,還用思想闡述藝術的本質與美學的精髓。徐悲鴻論美與藝吾所謂藝者,乃盡人力使造物無遁形;吾所謂美者,乃以最敏之感覺支配、增減,創造一自然境界,憑藝傳出之。藝可不借美而立(如寫風俗、寫像之逼真者),美必不可離藝而存。藝僅足供人參考,而美方足令人耽玩也。徐悲鴻論中國畫至詩人王維,創水墨山水,破除常格。於是張璪一筆寫兩棵古樹,大膽揮寫。劉明府之山水幛,據大詩人杜甫所贊「元氣淋漓幛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者,必於歷來繪畫之方術大異。故唐畫既大成於已有之方術,又創新格,且多第一流人物從事於此,所以有中興之業也!徐悲鴻論藝術之品性人有善惡之分,藝有美醜之殊,一如味有香臭,理有是非,相對而立,並生並長,譬諸虱蒼蠅,夫乎不在,文物昌明之世,兩性界劃清晰,善者升張,寄惡者斂跡,暨乎末世,則漢奸亦處國中,盜賊時相接席,黑白溷淆,賢愚不分,及言藝事,則魚目混珠,騙術公行,張醜怪於通衢,設邪說以惑眾,在歐洲,若巴黎畫商,在中國,若海派小人,志在欺騙,行同盜賊,法所不禁,詬罵罔聞,市井賤民,生不知恥,溯其所以能存在與寄生社會之理由,約有數端:(1)其製作極易;(2)常人以為凡藝術即美,或視若無睹,漠不關心:(3)利用人之虛榮弱點心理;(4)有組織。徐悲鴻論中西藝術之異同與比較歐洲國家教育發達,人人有普通常識。故藝術家任何不文,必不致如吾國工匠多目不識丁者。溯中國之所以重視文人畫,無非求其雅。藝術中唯一惡魔為俗,西洋藝術亦同一觀點。特西洋藝術所標舉之德如華貴、高超、靜穆,次則雄強、壯麗,匪如中國審美觀念之簡單明瞭,僅標舉一雅字而已。★本書特色:本書第一部分精選徐悲鴻的藝術與美學思想,探討創作與感悟;第二部分為其自述生平,記錄藝術成長之路。透過大師文字,品味美學思想,提升審美能力,將審美融入一生的修行。
舞臺與真實,演員的自我探索之路:從放鬆肌肉到最高目標,步步引領內在的藝術創作
◎表演從不只是記住臺詞! ◎用內心的經歷喚醒角色的靈魂 ◎跨越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無形之線一次次跌倒,再一次次從失誤中汲取經驗 走進表演藝術的深層心理,找到震撼人心的創作之道 【表演的內外統一】 真正的表演藝術不僅僅是塑造角色的內心世界,更要透過精湛的外在表現將這個內心世界傳達給觀眾。表演過程需要演員對自身的聲音、肢體、表情等外在手段擁有精準的控制力,這是讓觀眾感受到角色內心的關鍵。演員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台詞,都應該源於角色內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刻意模仿或強行表現。因此,表演藝術家需要更深入的情感體驗和精確的身體反應能力。 【動作的真實性與內在情感】 在舞臺上,所有動作和情感的表達都應該是真實的,而非強行做出來的假象。演員需要回憶起類似的情感經歷,讓內心自然地產生情緒,隨後才會自然地展現出來。這樣,動作才能帶著情感的力量,真實而感人。書中指出,表演應該是「回到自己」的過程,演員必須摒棄機械的模仿,並從自身的生活經驗中提取情感和形象,這樣塑造出來的角色才會具有生命力。 【適應與心理技巧的培養】 本書還提到,演員需要將角色的情感、觀點和價值觀內化成為自己的東西,並且在表演時建立起一種屬於內在的「適應」能力。這種適應不是單純的機械記憶,而是讓演員與臺詞和角色產生深層的內在連結,使觀眾在觀看時能感受到演員對角色的真實投入,還能進一步激發演員的創造力,讓表演更加充滿層次與力量。 【靈感與表演的最高境界】 當演員完全投入到角色的情感和目標之中時,他會進入一種「靈感狀態」,這種狀態下的表演並非源於理性分析,而是來自於潛意識的創作力。真正優秀的表演是意識與潛意識的完美結合,演員在完全沉浸於角色的目標時,能夠自然而然地展現出動人心弦的演技。因此,本書鼓勵演員透過不斷的情感體驗和角色探究,達到創作的最高境界,成為真正具有靈魂的表演藝術家。 本書特色:本書深入探討表演藝術的核心技巧與心理過程,以學員的視角記錄成長歷程,包括主角在排練與表演中經歷的挫折、突破和內心掙扎,細緻地闡述了如何透過想像力、肢體語言、場景適應來進入角色的內在世界。全書充滿詳盡而生動的描寫,讓人身臨其境地感受到舞臺表演的魅力和挑戰,一窺演員背後的心靈鍛鍊與藝術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