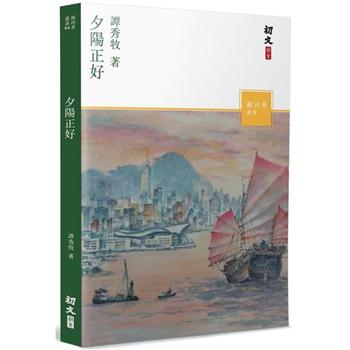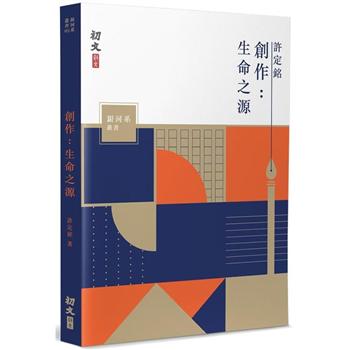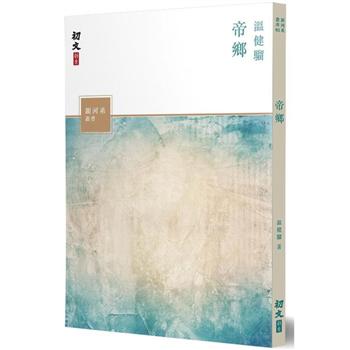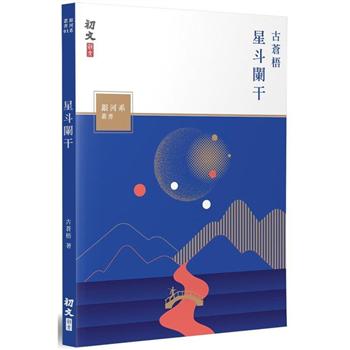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颱風季:盧因小說集
《颱風季》收錄盧因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短篇小說共二十三篇,此中〈暖春〉和〈颱風季〉均寫於一九六六年,前者發表於《文藝伴侶》,後者見刊於《海光文藝》,是集中寫得較遲的兩篇,其餘二十一篇均寫於一九五七至六二的六年間。盧因很早就非常注意現代主義寫作技巧,常運用獨白及時空跳接等表達方式。盧因首篇發表於《文藝新潮》的〈餘溫〉近四千字,全篇以獨白的形式,展示一位二十歲青年墮落後底懺悔。如果你深入探究,即會發現盧因筆下的「我」和「他」其實是同一個人,那是個人思想流中,正反兩方的戰鬥與掙扎。一九五○年代的香港小說,採用這種近乎「人格分裂」的演繹方式,是相當罕見的!
【電子書】颱風季:盧因小說集
《颱風季》收錄盧因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短篇小說共二十三篇,此中〈暖春〉和〈颱風季〉均寫於一九六六年,前者發表於《文藝伴侶》,後者見刊於《海光文藝》,是集中寫得較遲的兩篇,其餘二十一篇均寫於一九五七至六二的六年間。盧因很早就非常注意現代主義寫作技巧,常運用獨白及時空跳接等表達方式。盧因首篇發表於《文藝新潮》的〈餘溫〉近四千字,全篇以獨白的形式,展示一位二十歲青年墮落後底懺悔。如果你深入探究,即會發現盧因筆下的「我」和「他」其實是同一個人,那是個人思想流中,正反兩方的戰鬥與掙扎。一九五○年代的香港小說,採用這種近乎「人格分裂」的演繹方式,是相當罕見的!
【電子書】創作:生命之源
書話名家「醉書翁」許定銘之力作!「著手整理《創作:生命之源》時,原意是希望編本純抒情及記事的散文集。無奈一開手,就翻開了書話的資料夾,近十幾年來寫書語已成了習慣,編書亦如是。算啦,算啦,反正書話也是散文的一種,就讓它佔一席,好好延續我的生命!書分三輯:「記憶:無限延伸的思維」、「異域:自我流放的汨羅」和「閱讀:生命的延續」正好代表了我近年的生活寫照。自二〇〇七年退下教壇以後,我的生活就剩下這三個主題,年中除了香港、洛杉磯的雙城奔波,我亦不能脫離一般老人的習慣,回憶舊時的生活,拿往昔與現存對比,好好的反省,面對已然不長的將來。」──許定銘
【電子書】長廊的短調
梓人是香港一名少人提及的傑出小說作家,尤其精於短篇。他是和崑南、盧因、蔡炎培等,都是從一九五〇年代成長的文藝青年。他的作品散見刊於《中學生》、《文藝季》、《文壇》、《文藝沙龍》、《好望角》等文藝刊物。而發表在《好望角》第二期的《長廊的短調》後來更多次入選各香港小說選集,儼然其著名的作品。是次整理出版的作品,除了有早期的作品,更有投稿海外刊物《蕉風》的小說,以及後來寫於《文壇》、《香港文學》的篇章,讓讀者一次過見證作者各個創作階段的風格轉變。
【電子書】帝鄉
一九七四年溫健騮出版詩集《帝鄉》,作品大多寫成於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之間,作品絕大多數不分行,内容頗多與現實社會政治互相呼應,與溫氏前期作品,大異其趣。可惜詩集沒有公開發行,時下讀者難以尋覓索閲。本次復刻,除修正個別錯別字外,内容不作更動,保留當年原貌,重新出版,領略溫氏如何貫通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抒寫當時當地的家國感懷。「一九六八年以後,在外國,作為中國人,感受是強烈的。我重溫了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投身到與中國人有切身關係的現實裏。我覺得,寫詩光是弄弄矛盾語法,做些古語翻新,追求文字的感性,是不夠的。那樣,只能走到死巷裏,我要走出來。現在,我高興自己走出來了。」——溫健騮《學苑・文社講演》,一九七四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