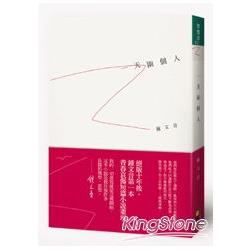出版故事 /書的故事
2012.08.27
鍾文音談《一天兩個人》的創作故事
文/蔡鳳儀(大田出版主編)
Q:《一天兩個人》的重新出版可以說是妳再對自己做了一次提醒:「我從不曾失去寫作的初衷,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是」,在創作路上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這篇有如宣誓般的序言對妳的意義。
A:我說這本書是我的出生證明。在這條創作的路上,很多人雖然擁有作品的出生證明,卻也有很多人就此夭折,因為台灣這個母體並不夠健全來養活純文學的孩子,尤其如我這般的專業寫作者。我對於台灣作家生命期的縮短有很深的憂慮,那就是創作者生活的窄化。我在長期的創作時間也面臨這樣的困境,你可能有段時間會很低潮,雖然表現上繼續如常,但內心是封閉的,我一直認為那是寫小說的致命傷。寫詩與散文只要有一個點的感覺,就足以擴張一個小品,但小說以人作主體,如果你的心是封閉的,就無法寫出小說。最近剛從日本採訪烏龍麵與企業家的生活歸來,其實透過這個方式也是想給自己歷練。現在的讀者被很多東西吸引,不同我那個年代,所以我很珍惜寫作這麼多年,仍被讀者珍視,現在重新出版這本作品,也是回應我的讀者:我仍然是我。
A:寫作風格的演變是很自然的,我發現以前的寫法跟現在差異很大。以前是以一個旁觀的寫作者審視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讀《一天兩個人》我的手中好像有一台照相機在觀看著裡面的角色,後來我的創作是把自己融入,我願意去揭開自己的血肉,與悲同悲;在《一天兩個人》的寫法是作者與小說主角有所距離,唯恐揭露自己太多似的。實際上人願意揭露自己是源自於認識自己,年輕時的我並不是那麼想要認識自己,比較是躲在屏幕或觀景窗背後,透過觀照別人來折射自己內心的風景與諸多叩問。可以說是過去我觀察別人,後來轉變成我觀察自己,因此寫作的濃度越來越高,傷口越來越深,黑暗愈來愈暗(黎明前的漫長黑夜)。當你年輕時還沒有能力去認識自己,只能透過他者來回應自己,所以這本小說是我比較少見的寫法。
A:觀察別人也是因為自己與他人遭逢,於是產生了很多錯身的故事。現在的寫法就是「我身」,「我身在此」,而過去是「與他者錯身」。而這個風格不太有人看過,因為這本書在一九九八年出版時壽命不長,僅兩千本。大田總編輯當時也有來找我,但我剛好前一天已簽給當時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當時我並不了解出版的生態與狀況,好笑的是把簽給別人要出版的稿子還影印一份給總編輯看,很單純地完全站在一個分享文章的角度……後來隔了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大田總編輯再度主動來找我,才談成在大田出版的第一本書:《寫給你的日記》。沒想到多年後,這本短篇小說集又回到了大田。我想想當時自己完全不懂什麼社會化,小說〈一天兩個人〉裡的陳瑜剛社會化得慢,很像年輕時的自己,不容易找到自己的舞台。年輕時雖然有舞藝,但有可能會跳上一個不牢固的舞台,我常說寫作大於成為作家的欲望與本質。我喜歡寫作,這才是初衷。但寫作之後會不會成為作家則是沒有去想的。這本書是我年輕時的一個寫作座標。
A:我的小說有一個特色,有時會重複出現一些場域。就好像你會看到莒哈絲不斷重複她母親的片段,那是因為作者想要用不同的方式或者語言再說一次,我的短篇小說集《過去》《一天兩個人》也有一些些重複可見的片段,年輕時候的場域,出現在我的部分小說裡,我一直忘不了那些場域,可見那時的孤獨有多龐大,《一天兩個人》出現的開羅紫玫瑰,《在河左岸》的寶宮戲院,《少女老樣子》《豔歌行》都曾用不同的人提到相似的地方,有些重複再現的場景,是因為纏繞不去的魅影猶在,這些片段的再現,一直到《豔歌行》才可說是做了一個終結。當時的畫面是這樣的:一個年輕女子已經開始寫作了,但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要走到何方?常在台北街頭孤獨地搜索,獨自感知這城市。我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像個夢遊者。從《一天兩個人》到《豔歌行》可以說是一個人孤獨亂走在城市的起與終。而《一天兩個人》作為一個我創作的原型,也是因為如此,就好像奧德賽永遠是踏上鄉愁旅程的原型,鄉愁雖不是我的主題,但《一天兩個人》就彷彿奧德賽般,踏上漫長的原鄉之旅。我的心就是我的原鄉,不斷地觀照著心。(摘自大田出版《一天兩個人》)
A:我說這本書是我的出生證明。在這條創作的路上,很多人雖然擁有作品的出生證明,卻也有很多人就此夭折,因為台灣這個母體並不夠健全來養活純文學的孩子,尤其如我這般的專業寫作者。我對於台灣作家生命期的縮短有很深的憂慮,那就是創作者生活的窄化。我在長期的創作時間也面臨這樣的困境,你可能有段時間會很低潮,雖然表現上繼續如常,但內心是封閉的,我一直認為那是寫小說的致命傷。寫詩與散文只要有一個點的感覺,就足以擴張一個小品,但小說以人作主體,如果你的心是封閉的,就無法寫出小說。最近剛從日本採訪烏龍麵與企業家的生活歸來,其實透過這個方式也是想給自己歷練。現在的讀者被很多東西吸引,不同我那個年代,所以我很珍惜寫作這麼多年,仍被讀者珍視,現在重新出版這本作品,也是回應我的讀者:我仍然是我。
透過他者來折射自己
Q:本書收錄了十篇原版舊作,加添了三篇新作,總共十三篇,從最早一篇一九九○年〈妳說的我都記得〉到二○一二增補的〈放狗出去〉,這二十二年之間妳寫作風格的追求是甚麼?A:寫作風格的演變是很自然的,我發現以前的寫法跟現在差異很大。以前是以一個旁觀的寫作者審視自己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讀《一天兩個人》我的手中好像有一台照相機在觀看著裡面的角色,後來我的創作是把自己融入,我願意去揭開自己的血肉,與悲同悲;在《一天兩個人》的寫法是作者與小說主角有所距離,唯恐揭露自己太多似的。實際上人願意揭露自己是源自於認識自己,年輕時的我並不是那麼想要認識自己,比較是躲在屏幕或觀景窗背後,透過觀照別人來折射自己內心的風景與諸多叩問。可以說是過去我觀察別人,後來轉變成我觀察自己,因此寫作的濃度越來越高,傷口越來越深,黑暗愈來愈暗(黎明前的漫長黑夜)。當你年輕時還沒有能力去認識自己,只能透過他者來回應自己,所以這本小說是我比較少見的寫法。
我喜歡寫作,這才是初衷
Q:妳的短篇像午後雷陣雨,長篇小說像冬天的雪,細細密密下著,纏綿不休,回應妳剛剛所謂觀照自己,是用長時間的感受來理解自己。A:觀察別人也是因為自己與他人遭逢,於是產生了很多錯身的故事。現在的寫法就是「我身」,「我身在此」,而過去是「與他者錯身」。而這個風格不太有人看過,因為這本書在一九九八年出版時壽命不長,僅兩千本。大田總編輯當時也有來找我,但我剛好前一天已簽給當時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當時我並不了解出版的生態與狀況,好笑的是把簽給別人要出版的稿子還影印一份給總編輯看,很單純地完全站在一個分享文章的角度……後來隔了一段時間沒有聯絡,大田總編輯再度主動來找我,才談成在大田出版的第一本書:《寫給你的日記》。沒想到多年後,這本短篇小說集又回到了大田。我想想當時自己完全不懂什麼社會化,小說〈一天兩個人〉裡的陳瑜剛社會化得慢,很像年輕時的自己,不容易找到自己的舞台。年輕時雖然有舞藝,但有可能會跳上一個不牢固的舞台,我常說寫作大於成為作家的欲望與本質。我喜歡寫作,這才是初衷。但寫作之後會不會成為作家則是沒有去想的。這本書是我年輕時的一個寫作座標。
孤獨的起與終
Q:妳說《一天兩個人》是後來很多小說的原型,微型。為什麼?A:我的小說有一個特色,有時會重複出現一些場域。就好像你會看到莒哈絲不斷重複她母親的片段,那是因為作者想要用不同的方式或者語言再說一次,我的短篇小說集《過去》《一天兩個人》也有一些些重複可見的片段,年輕時候的場域,出現在我的部分小說裡,我一直忘不了那些場域,可見那時的孤獨有多龐大,《一天兩個人》出現的開羅紫玫瑰,《在河左岸》的寶宮戲院,《少女老樣子》《豔歌行》都曾用不同的人提到相似的地方,有些重複再現的場景,是因為纏繞不去的魅影猶在,這些片段的再現,一直到《豔歌行》才可說是做了一個終結。當時的畫面是這樣的:一個年輕女子已經開始寫作了,但她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要走到何方?常在台北街頭孤獨地搜索,獨自感知這城市。我大概有兩三年的時間,像個夢遊者。從《一天兩個人》到《豔歌行》可以說是一個人孤獨亂走在城市的起與終。而《一天兩個人》作為一個我創作的原型,也是因為如此,就好像奧德賽永遠是踏上鄉愁旅程的原型,鄉愁雖不是我的主題,但《一天兩個人》就彷彿奧德賽般,踏上漫長的原鄉之旅。我的心就是我的原鄉,不斷地觀照著心。(摘自大田出版《一天兩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