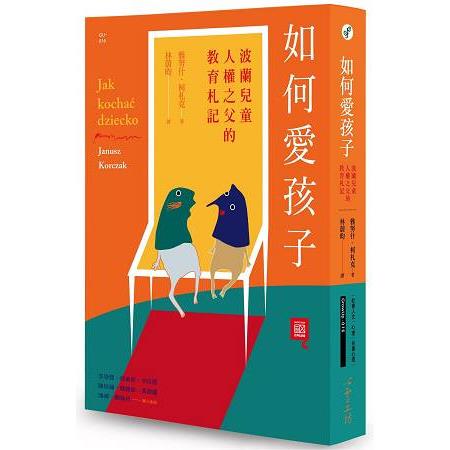出版故事 /書的故事
2016.10.18
與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相遇
文/林蔚昀(本書譯者、《我媽媽的寄生蟲》作者)
會接觸到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雅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的人和他的作品,可以說是機緣巧合,但也有一種冥冥中註定的感覺。
兒子快滿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帶他來到克拉科夫(Krakow)的「綿羊電影院」(Kino pod Baranami),去參加一場兒童電影的放映。那天看的是一部動畫,改編自柯札克所著的少年小說《麥堤國王》(Krol Maciu? Pierwszy/King Matt the First)。 主人翁麥堤的父親過世了,於是小小年紀的他就得接下王位。在學習當國王的過程中,他遇到了許多困難及挑戰,比如野心勃勃的將軍一直想篡位;麥堤和全國小孩成立了兒童議會,然而孩子們缺乏經驗,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在他們摸索的期間,國家失去了原有的秩序,戰爭一觸即發…幸好,憑藉著智慧、勇氣、從錯誤中學習的反省能力、以及來自他人的幫助,麥堤化解了危機,並且建立了社會的新秩序…
我和兒子都很喜歡這部電影,雖然兒子看到老國王去世會難過、害怕,但是他很喜歡麥堤率領兒童去島嶼尋找動物(為了建立一個開放的、人和動物平等相處的動物園)的橋段。而我最喜歡這個故事的地方,是它沒有塑造出一個兒童救世主的神話。麥堤不是來解放兒童或拯救他們,更不是要創造一個屬於兒童的獨裁政權。他相信兒童的自主權,並且相信兒童和大人可以彼此溝通、互相幫助,共同創造一個適合兩者居住的世界。
柯札克很早就開始關注兒童的處境及權益。在童年時看到華沙猶太貧民窟兒童的困苦生活,令他印象深刻。戰時的經驗(柯札克曾以軍醫身分被徵召到前線,參與過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遠到過哈爾濱),也讓他看到戰爭帶給孩子的痛苦。他曾參觀歐洲各地的孤兒院,也透過閱讀教育和心理學理論讓自己更了解兒童。他以寫作和廣播喚起人們對兒童權益的重視(他的筆名包括「老醫生」、「醫生先生」、「柯札克」,他身後留下二十餘本著作),同時身體力行,以行醫、義診維護兒童的健康。
1904到1908年間,他幾乎每年都會帶領提供給貧窮猶太孩子的夏令營。1912年,他成為猶太孤兒院「孤兒之家」(Dom Sierot)的院長,和合作夥伴史蒂芬‧維琴絲卡(Stefania Wilczy?ska)一同經營孤兒院長達三十年,直到他們和孤兒們一起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猶太人身分被納粹殺害為止。
雖然柯札克和孤兒院的結局充滿悲劇性,但在悲劇到來之前,他和兒童曾經一起做出許多不凡的努力,讓兒童人權、兒童自治在理念和實踐上都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他的理念及著作深深影響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制定(這個公約有超過兩百個國家簽屬,台灣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即依據公約的精神與內容所制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1978年訂為柯札克年,聯合國(UN)亦將1979年訂為「國際兒童年」向柯札克致敬。
柯札克如此重要,可惜的是台灣關於他的資料很少,只有林真美老師翻譯的,關於柯札克生平事蹟的童書《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親子天下,2012),除此之外沒有他自己的著作出版。我於是向心靈工坊推薦柯札克的代表作《如何愛孩子》,幸運的是,我的建議被採納了,並且獲得大力支持。
「沒有孩子 ── 只有人;但是他們的認知和我們不同,經驗和我們不同,衝動和我們不同,情感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記得,我們不了解他們。」在孩子面前,大人必須知道自己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並且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這呼應著英國小兒科醫生/兒童心理學家溫尼考特說的「不需要完美,夠好就好」),如此他們才能尊重孩子、同理孩子、不以威權的方式管教他們眼中低人一等的孩子,而是把孩子當成平等、同樣不完美(也就是「夠好」)的人來愛。
我相信柯札克的《如何愛孩子》可以成為一座橋樑。這座橋樑的目的不光是為了引進,也是為了輸出。它可以讓我們與不同的人交流對話,並且結合過去與現在的經驗,到達更豐富的明天 ── 就像柯札克所說的一樣。
兒子快滿四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帶他來到克拉科夫(Krakow)的「綿羊電影院」(Kino pod Baranami),去參加一場兒童電影的放映。那天看的是一部動畫,改編自柯札克所著的少年小說《麥堤國王》(Krol Maciu? Pierwszy/King Matt the First)。 主人翁麥堤的父親過世了,於是小小年紀的他就得接下王位。在學習當國王的過程中,他遇到了許多困難及挑戰,比如野心勃勃的將軍一直想篡位;麥堤和全國小孩成立了兒童議會,然而孩子們缺乏經驗,不知道如何治理國家。在他們摸索的期間,國家失去了原有的秩序,戰爭一觸即發…幸好,憑藉著智慧、勇氣、從錯誤中學習的反省能力、以及來自他人的幫助,麥堤化解了危機,並且建立了社會的新秩序…
我和兒子都很喜歡這部電影,雖然兒子看到老國王去世會難過、害怕,但是他很喜歡麥堤率領兒童去島嶼尋找動物(為了建立一個開放的、人和動物平等相處的動物園)的橋段。而我最喜歡這個故事的地方,是它沒有塑造出一個兒童救世主的神話。麥堤不是來解放兒童或拯救他們,更不是要創造一個屬於兒童的獨裁政權。他相信兒童的自主權,並且相信兒童和大人可以彼此溝通、互相幫助,共同創造一個適合兩者居住的世界。
柯札克很早就開始關注兒童的處境及權益。在童年時看到華沙猶太貧民窟兒童的困苦生活,令他印象深刻。戰時的經驗(柯札克曾以軍醫身分被徵召到前線,參與過日俄戰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最遠到過哈爾濱),也讓他看到戰爭帶給孩子的痛苦。他曾參觀歐洲各地的孤兒院,也透過閱讀教育和心理學理論讓自己更了解兒童。他以寫作和廣播喚起人們對兒童權益的重視(他的筆名包括「老醫生」、「醫生先生」、「柯札克」,他身後留下二十餘本著作),同時身體力行,以行醫、義診維護兒童的健康。
1904到1908年間,他幾乎每年都會帶領提供給貧窮猶太孩子的夏令營。1912年,他成為猶太孤兒院「孤兒之家」(Dom Sierot)的院長,和合作夥伴史蒂芬‧維琴絲卡(Stefania Wilczy?ska)一同經營孤兒院長達三十年,直到他們和孤兒們一起在二次大戰期間因為猶太人身分被納粹殺害為止。
雖然柯札克和孤兒院的結局充滿悲劇性,但在悲劇到來之前,他和兒童曾經一起做出許多不凡的努力,讓兒童人權、兒童自治在理念和實踐上都往前推進了一大步。他的理念及著作深深影響了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制定(這個公約有超過兩百個國家簽屬,台灣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即依據公約的精神與內容所制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把1978年訂為柯札克年,聯合國(UN)亦將1979年訂為「國際兒童年」向柯札克致敬。
柯札克如此重要,可惜的是台灣關於他的資料很少,只有林真美老師翻譯的,關於柯札克生平事蹟的童書《好心的國王:兒童權利之父—柯札克的故事》(親子天下,2012),除此之外沒有他自己的著作出版。我於是向心靈工坊推薦柯札克的代表作《如何愛孩子》,幸運的是,我的建議被採納了,並且獲得大力支持。
「沒有孩子 ── 只有人;但是他們的認知和我們不同,經驗和我們不同,衝動和我們不同,情感和我們不同。我們要記得,我們不了解他們。」在孩子面前,大人必須知道自己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並且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這呼應著英國小兒科醫生/兒童心理學家溫尼考特說的「不需要完美,夠好就好」),如此他們才能尊重孩子、同理孩子、不以威權的方式管教他們眼中低人一等的孩子,而是把孩子當成平等、同樣不完美(也就是「夠好」)的人來愛。
我相信柯札克的《如何愛孩子》可以成為一座橋樑。這座橋樑的目的不光是為了引進,也是為了輸出。它可以讓我們與不同的人交流對話,並且結合過去與現在的經驗,到達更豐富的明天 ── 就像柯札克所說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