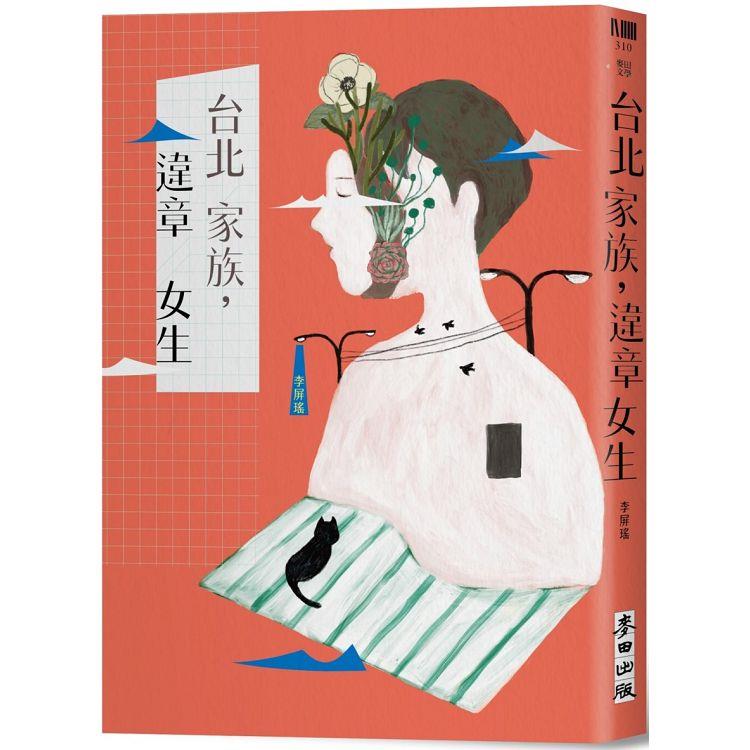出版故事 /書的故事
2019.09.23
沒有一種「典型」需要絕對服從
文/張桓瑋(麥田出版特約編輯)
「女生該是什麼樣子?女生該怎麼穿、怎麼吃、怎麼生活?為什麼總有個『典型』女生中央伍,必須時刻對齊?」
這是李屏瑤在《台北家族,違章女生》中所拋出的提問,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反思,或許不只是女生,關於人,是不是都得有個必須遵從的典型,必須套入的模具?於是總拿別人的眼光丈量自己,必須分毫不差、規避特別,彷彿與眾不同皆是不合群的展演,攤在世俗審判下,所有變異都是原罪。
李屏瑤透過這本散文集,突破性別規尺,在整齊劃一的框架上蔓生繁花異草,蓋起一棟又一棟違章建築。或者如她所言:「曾經令人感到痛苦的,現階段可以回頭去面對,如同在噩夢中停止奔跑,轉身細看魔鬼的面孔身形,違章建築也可以長成霍爾的移動城堡。」於是這本書從雞腿飯、躲避球、校園裡的綽號玩笑、家族間的重男輕女,透過戲謔幽默,抽取世俗搭建的疊疊樂,所有「典型」崩塌在字裡行間,每每被絆倒,彷彿都在提醒我們:別再虧待自己,可以長到那麼大,你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確實,難的是在他人眼光下求生,所以選擇權必須回到自己身上。比方「出櫃」,作者與母親的攻防戰橫跨十年,她寫下:「出櫃不是看一場電影,無法用兩小時就得到完美的結局;出櫃更像是一千集的鄉土劇,必須吃過很多很多頓飯,過上很多很多平凡的日子,才會有一點點的情節推進。」原來對自己與生活誠實,是那麼費力,每一次的微小堅持都在無數次演練、攻防中消耗心神。這些文章像是作者與外在、與自我拉鋸的過程,要有搭建違章的勇氣,也需受人質疑的心理建設,然而這總是一段漫漫長路,難以斷然停工。
編輯過程中,一直覺得這是本關於「鬆綁」的書,寫的雖是作者的成長與生活,但我們或多或少都能投影出自身的故事:那些關乎家人之間的糾結羈絆(可能是愛,也可能是互相傷害),以及在世俗傾軋下生存之不易??我們該如何回應,該如何迎擊外在襲來的控制慾?
「在人多的時候不能從眾,躲不掉的時候更不能逃跑,直球對決是非常痛的,但可能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李屏瑤在〈無聲的躲避球〉這篇文章回顧童年幾近「霸凌」的遊戲,也像在提醒對生活無能為力的我們,或許受到威脅進逼時,轉身是一種本能反應,但還有另一種選擇——即使受痛點被狠狠踩過,也能在這世代的威脅下直球對決,試著找出回應困難的方式。
這是李屏瑤在《台北家族,違章女生》中所拋出的提問,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反思,或許不只是女生,關於人,是不是都得有個必須遵從的典型,必須套入的模具?於是總拿別人的眼光丈量自己,必須分毫不差、規避特別,彷彿與眾不同皆是不合群的展演,攤在世俗審判下,所有變異都是原罪。
李屏瑤透過這本散文集,突破性別規尺,在整齊劃一的框架上蔓生繁花異草,蓋起一棟又一棟違章建築。或者如她所言:「曾經令人感到痛苦的,現階段可以回頭去面對,如同在噩夢中停止奔跑,轉身細看魔鬼的面孔身形,違章建築也可以長成霍爾的移動城堡。」於是這本書從雞腿飯、躲避球、校園裡的綽號玩笑、家族間的重男輕女,透過戲謔幽默,抽取世俗搭建的疊疊樂,所有「典型」崩塌在字裡行間,每每被絆倒,彷彿都在提醒我們:別再虧待自己,可以長到那麼大,你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確實,難的是在他人眼光下求生,所以選擇權必須回到自己身上。比方「出櫃」,作者與母親的攻防戰橫跨十年,她寫下:「出櫃不是看一場電影,無法用兩小時就得到完美的結局;出櫃更像是一千集的鄉土劇,必須吃過很多很多頓飯,過上很多很多平凡的日子,才會有一點點的情節推進。」原來對自己與生活誠實,是那麼費力,每一次的微小堅持都在無數次演練、攻防中消耗心神。這些文章像是作者與外在、與自我拉鋸的過程,要有搭建違章的勇氣,也需受人質疑的心理建設,然而這總是一段漫漫長路,難以斷然停工。
編輯過程中,一直覺得這是本關於「鬆綁」的書,寫的雖是作者的成長與生活,但我們或多或少都能投影出自身的故事:那些關乎家人之間的糾結羈絆(可能是愛,也可能是互相傷害),以及在世俗傾軋下生存之不易??我們該如何回應,該如何迎擊外在襲來的控制慾?
「在人多的時候不能從眾,躲不掉的時候更不能逃跑,直球對決是非常痛的,但可能是唯一的生存之道。」李屏瑤在〈無聲的躲避球〉這篇文章回顧童年幾近「霸凌」的遊戲,也像在提醒對生活無能為力的我們,或許受到威脅進逼時,轉身是一種本能反應,但還有另一種選擇——即使受痛點被狠狠踩過,也能在這世代的威脅下直球對決,試著找出回應困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