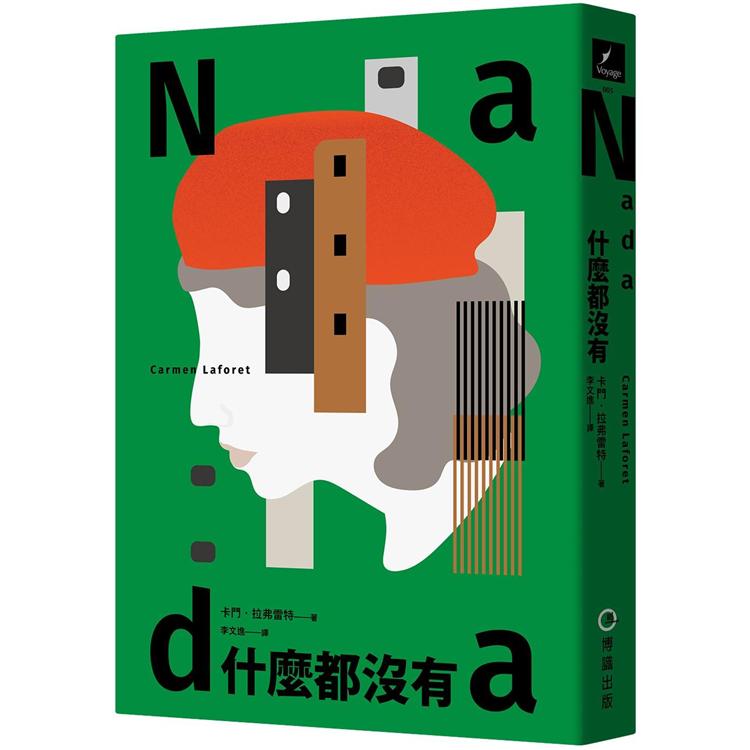出版故事 /書的故事
2020.01.06
西班牙文學注目焦點,轟動巴塞隆納的傳奇才女
文/博識出版編輯 何秉修
當我們回想上個世紀四○年代的西洋文學時,或許會有幾個經典大師的名字在腦海浮現,或許會聯想到那是存在主義興起的年代,或許心中的文學版圖特別打亮了法國和美國。但如果我們將目光移向西班牙,就會發現另一種讓人驚異的景象──有個二十三歲的女生寫了她的第一部小說,沒想到竟成為文學界地位崇高的納達爾獎的第一屆得主,還造成極大轟動,讓她躍為新一代文學偶像。這位作家就是卡門‧拉弗雷特,那本小說就是被譽為西班牙內戰後文學經典的《Nada什麼都沒有》。這麼年輕的女性在小說藝術上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恐怕是史上前所未有。唯一可以比擬的可能是中國的張愛玲,她只比拉弗雷特早一年出生,也是在二十三、四歲就寫出傳世經典,如《金鎖記》等。張愛玲和拉弗雷特都在作品中描繪了自己的城市(上海、巴塞隆納),裡面都有戰爭的影子,個人在少年時期都有和繼母不愉快的經歷──這兩位才女雖然中、西背景不同,卻在許多方面驚人地相似。
《Nada》首度出版時以清新的書寫風格,讓眾人經歷戰爭的苦悶心靈獲得紓解。即使到了現在,讀起來仍然十足「現代」。如果你不曉得《Nada》的年代,撇除書中對時空的指涉,讀了之後很可能會覺得這是我們同時代的作品。當我們說某作品是「經典」,可能會想像那是結構性很強的鉅作。但《Nada》並非如此。它的敘述充滿流動性,像是作者興之所至,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彷彿靈感接連不斷地湧現。主角的聲音就像是直接發自靈魂,吸引讀者隨著她到故事現場感受著一切。各個篇章並非以線性貫串,而像是散記,卻冥冥中有關聯,讓讀者自己在心中堆疊組合,形成脈絡。
故事簡介會說,這本書描寫一個大學新生到巴塞隆納投奔親戚,在校園與家中的遭遇。但故事內容絕非年輕人的喃喃自語或心情抒發。事實上,這本書有很強烈的描繪現實的企圖,只是這種企圖並非像寫實主義諸公那樣採取客觀超然的態度,而是讓時光中出現的種種事物透過主角安德蕾雅的心靈映現。她是個很有覺察力的主體,不斷敏感地覺知她遇到的各個人物和情景。她讓自我拋向他者,再返回自我,顯現出一個很突出的主體心靈,卻又有一種衝向世界、勇敢寫實的氣魄。
因此我們隨著安德蕾雅的腳步,看到了巴塞隆納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場景。她在不同的階級間穿梭:既有富裕的資本家,也有貧窮落魄的中產階級;有仿貴族式的文藝沙龍,也有抗拒主流價值的波希米亞人;乞丐、吉普賽女郎、傭人等各種市井人物都受到某種程度的關注與透視。這些階級典型常常會在安德蕾雅的意識中彼此碰撞,產生耐人尋味的不和諧音。書裡的一段話就清楚顯示了這樣的特色:
千百種氣味、悲傷、故事從石頭路面竄了出來,伸進阿里保街沿路的陽台和大門。一大群精神奕奕從對角線大道優雅的街區要往下走的人,遇上另一大群從大學廣場活躍的生活圈要往上走的人。交錯的生活、特質、品味,這就是阿里保街。 (《Nada什麼都沒有》頁206)
這部小說的敘事方式靈活多變,直教人驚嘆。有時候不著痕跡地在白描中嵌入某個意象,看起來雖是在如實描述當前情景,卻隱約和書中別處構成寓意(如在浴室淋浴和大雨的意象)。有時敘事者處於「非正常」的意識中,譬如半夢半醒或極度飢餓,讓她感知到的一切產生了不穩定性。有時敘述當中突然跳出一段倒敘,或從回憶中突然跳回現實,在時間的自由跳接之間,文字彷彿跟著敘事者的意識流動。我們甚至還會看到一些神話式的描述,讓巴塞隆納的某個角落敷上了魔幻的色彩。這些筆法或許會讓我們聯想到某些名家,契訶夫、普魯斯特、馬奎斯,甚至描寫死亡有點莎士比亞的影子……但拉弗雷特卻又誰都不像,她不留戀於某種寫法,而是忠實於自己描寫的對象,保持心靈感受的開放性,讓安德蕾雅扮演「小小、卑微的觀察者」(《Nada什麼都沒有》頁205)。
在當年,這是一部打破規範的小說,而直到今天,它仍能引起讀者的激賞,繼續呼應人們對自由的嚮往。從一九四五年出版以來,它在西班牙每年賣出至少八千本。二○一九是《Nada》誕生的七十五週年,有學術機構以紀念拉弗雷特為名舉辦學術研討會。文學愛好者持續對《Nada》做各種解讀,從虛無主義、心理學、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成長小說……等各種角度,甚至有人從可能連作者都始料未及的同性戀文學理論切入。就如書名所揭示的,「什麼都沒有」的東西原本就有抗拒定義的特性。但它又不是「什麼都沒有」,因為在讀者心中產生的共鳴是絕對真實不虛的。在這樣的有無之間,在無法定義與個人解讀之間,存在著作品與時俱進的動力。這本書就充滿這種超越時代的能量,不管你是業餘讀者,還是文學小說的行家,它都會讓你耳目一新。
《Nada》首度出版時以清新的書寫風格,讓眾人經歷戰爭的苦悶心靈獲得紓解。即使到了現在,讀起來仍然十足「現代」。如果你不曉得《Nada》的年代,撇除書中對時空的指涉,讀了之後很可能會覺得這是我們同時代的作品。當我們說某作品是「經典」,可能會想像那是結構性很強的鉅作。但《Nada》並非如此。它的敘述充滿流動性,像是作者興之所至,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彷彿靈感接連不斷地湧現。主角的聲音就像是直接發自靈魂,吸引讀者隨著她到故事現場感受著一切。各個篇章並非以線性貫串,而像是散記,卻冥冥中有關聯,讓讀者自己在心中堆疊組合,形成脈絡。
故事簡介會說,這本書描寫一個大學新生到巴塞隆納投奔親戚,在校園與家中的遭遇。但故事內容絕非年輕人的喃喃自語或心情抒發。事實上,這本書有很強烈的描繪現實的企圖,只是這種企圖並非像寫實主義諸公那樣採取客觀超然的態度,而是讓時光中出現的種種事物透過主角安德蕾雅的心靈映現。她是個很有覺察力的主體,不斷敏感地覺知她遇到的各個人物和情景。她讓自我拋向他者,再返回自我,顯現出一個很突出的主體心靈,卻又有一種衝向世界、勇敢寫實的氣魄。
因此我們隨著安德蕾雅的腳步,看到了巴塞隆納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場景。她在不同的階級間穿梭:既有富裕的資本家,也有貧窮落魄的中產階級;有仿貴族式的文藝沙龍,也有抗拒主流價值的波希米亞人;乞丐、吉普賽女郎、傭人等各種市井人物都受到某種程度的關注與透視。這些階級典型常常會在安德蕾雅的意識中彼此碰撞,產生耐人尋味的不和諧音。書裡的一段話就清楚顯示了這樣的特色:
千百種氣味、悲傷、故事從石頭路面竄了出來,伸進阿里保街沿路的陽台和大門。一大群精神奕奕從對角線大道優雅的街區要往下走的人,遇上另一大群從大學廣場活躍的生活圈要往上走的人。交錯的生活、特質、品味,這就是阿里保街。 (《Nada什麼都沒有》頁206)
這部小說的敘事方式靈活多變,直教人驚嘆。有時候不著痕跡地在白描中嵌入某個意象,看起來雖是在如實描述當前情景,卻隱約和書中別處構成寓意(如在浴室淋浴和大雨的意象)。有時敘事者處於「非正常」的意識中,譬如半夢半醒或極度飢餓,讓她感知到的一切產生了不穩定性。有時敘述當中突然跳出一段倒敘,或從回憶中突然跳回現實,在時間的自由跳接之間,文字彷彿跟著敘事者的意識流動。我們甚至還會看到一些神話式的描述,讓巴塞隆納的某個角落敷上了魔幻的色彩。這些筆法或許會讓我們聯想到某些名家,契訶夫、普魯斯特、馬奎斯,甚至描寫死亡有點莎士比亞的影子……但拉弗雷特卻又誰都不像,她不留戀於某種寫法,而是忠實於自己描寫的對象,保持心靈感受的開放性,讓安德蕾雅扮演「小小、卑微的觀察者」(《Nada什麼都沒有》頁205)。
在當年,這是一部打破規範的小說,而直到今天,它仍能引起讀者的激賞,繼續呼應人們對自由的嚮往。從一九四五年出版以來,它在西班牙每年賣出至少八千本。二○一九是《Nada》誕生的七十五週年,有學術機構以紀念拉弗雷特為名舉辦學術研討會。文學愛好者持續對《Nada》做各種解讀,從虛無主義、心理學、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成長小說……等各種角度,甚至有人從可能連作者都始料未及的同性戀文學理論切入。就如書名所揭示的,「什麼都沒有」的東西原本就有抗拒定義的特性。但它又不是「什麼都沒有」,因為在讀者心中產生的共鳴是絕對真實不虛的。在這樣的有無之間,在無法定義與個人解讀之間,存在著作品與時俱進的動力。這本書就充滿這種超越時代的能量,不管你是業餘讀者,還是文學小說的行家,它都會讓你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