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故事 /人物動向
2010.01.18
閱讀哈金作品 勝過在中國行萬里路
文/顏擇雅(文字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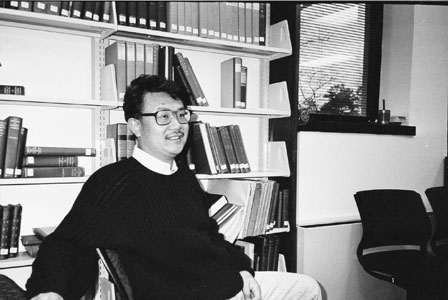
法拉盛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在美國算是歷古悠久,一度蕭條房價便宜,六、七○年代先移入一批留在美國安家立業的台灣留學生。台美斷交後,湧入的台灣移民更多,他們所經營的旅行社、超市、書局把普通話變成鎮上比英語更通行的語言。六四之後,美國大發綠卡給中國留學生,他們再申請親友來美,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就有了後來居上之勢。《2018740637972》(時報文化)寫的就是這些新移民。
《落地》的故事型態略可粗分為兩種,一種戲劇張力十足,情節自有一股急推眼球前滾的虎虎勁兒,也許是大癥結、大謎團或者大荒謬,轉折處也令人拍案叫絕。〈互連網之災〉、〈美人〉、〈兩面夾攻〉皆屬此類。另一種則平淡自然,收尾亦不特別出人意表。讀者之所以興味盎然讀下去,被勾起的與其說是好奇心,較多的其實是同情心。隨著故事進展,讀者不知不覺愈來愈在乎書中人物。平淡的小說其實最難寫,好的小說家只需要會說故事,偉大的小說家卻必須做到興觀群怨。像〈櫻花樹後的房子〉,寫的是血汗工廠熨衣工與妓女之間的愛情,情節就平淡無奇,但我們讀完,優美而且心痛的感受卻會在心頭縈迴久久。
〈作曲家和他的鸚鵡〉也是淡而有味的愛情故事,奇特的是這次愛的對象並不是人,而是一隻鸚鵡。熟悉西洋經典的讀者一定會想起福婁拜中篇〈簡單的心〉。福婁拜的女主角是透過對鸚鵡的愛,進入出凡入聖的最高境界,並在臨終之際看見已死的鸚鵡領她上天堂。哈金作品中的鸚鵡也扮演類似的引領角色,在死後讓主角的藝術造詣更上層樓。哈金敢把大師已處理到盡善盡美的素材用自己的機杼再處理一遍,擺明就是不怕貨比貨的意思,真是藝高膽更大。 哈金在技巧上也許與中國文學沒多少淵源,素材上卻有。中文讀者看到〈英語教授〉結尾一定會想起「范進中舉」。堂堂哈佛博士,可以跟美國大學生談史坦貝克,瘋癲起來唱的竟是《紅燈記》,其中的突兀也是英語顯現不出的。這讓我想起哈金最知名的短篇之一〈光天化日〉。英語讀者只能讀到連環反諷,中文讀者卻能一眼看出是重新詮釋潘金蓮。還有本書中的〈落地〉,中文讀者也會比英語讀者感受到更多荒謬,因為中文讀者會想到少林寺,英語讀者則沒有類似想像。
既是寫移民社會,文化衝突當然少不了,像〈孩童如敵〉、〈兩面夾攻〉都是,這兩篇應該會讓老一輩在勸下一代移民美國之前三思。哈金筆下的美國從來不是適合老年人的國度,〈養老計畫〉中養老院的洗澡方式真是恐怖極了。
〈臨時愛情〉就像許多寫婚外戀的名作,也是反應時代精神的道德故事,這裡所反應的時代精神正是中共中央喜歡掛嘴邊的那四個字:把握機遇。把握機遇可以很激勵,也可以把人變成只重利益或便利。故事中的婚外戀是為了便利,女主角的丈夫來團聚,男主角的妻子求去,則是為利益。〈互連網之災〉反應的則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消費主義。中國變成全球最大汽車市場,這篇故事為我們探討一片榮景背後的心理變態。
哈金的九本小說,可以說是涵蓋中共建政以來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城市、農村、軍隊、學校、工廠、學校、醫院。要了解中國當代文壇生態,只需要讀《自由生活》。要去中國設廠開店,收在《新郎》中的〈牛仔炸雞進城來〉則是最好的企管教材。讀哈金九卷書,絕對勝過在中國行萬里路。他能把中國寫得那麼真,多虧是英語寫作才變成可能。想想看,如果他像許多中文創作者一樣,也想把握大好機遇,打著兩岸三地的如意算盤,〈櫻花樹後的房子〉可能就必須刪去北京官員那一段,〈落地〉也沒辦法把宗教界貪腐寫得那麼徹底。
哈金成名後,常被拿來和康拉德或納博科夫相比。其實,除了非母語寫作之外,哈金與那兩位並無相似之處。康船長的小說從沒寫過波蘭,他是用英語寫大英帝國。納遺少則打五歲就用英語寫蝴蝶研究,英語是他的第一書寫語,他在美國成名也是寫美國事。哈金卻不同,即使場景已移到美國,探討的依然是中國。他是用略嫌稚拙的英語,寫英語讀者不算有興趣的素材。他選擇用英語寫作,一不為錢,二不為他英語好,純是為了創作自由。不然,以今日中國的稿費之優,如果不是為了寫中國,如果不是為了百分之百的創作自由,他大可轉成中文寫作才對。
這樣的選擇,注定讓他在中美兩國文學界都感到孤獨,就像〈選擇〉男主角的處境。《落地》中許多篇都顯見哈金是寫孤獨的高手。這種孤獨是出於自由意志的選擇,比中國文學中的隱者少了點恬適,卻多了勇氣。這種精神是美國文學的重要傳統。所以說,狄瑾遜與佛洛斯特的詩,還有《頑童流浪記》與《老人與海》,才是哈金精神上的最重要傳承。
*文中哈金照片,由時報文化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