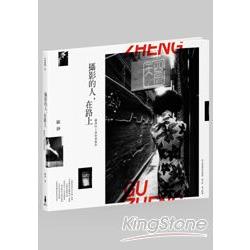出版故事 /書的故事
2013.06.06
都市漫遊者的自由靈魂
文/郭力昕(政大傳播學院副教授)
我得先告白。三年前顧錚教授在台北送我大陸版本的《觀念的街頭》,書裡簽了「一笑了之」時,我竟當真了。這位中國大陸攝影論述最豐、影響力可能最廣的評論家的謙遜之語,我早該很熟悉的;但翻閱顧錚這本街頭攝影創作時,我真的也就以一種隨興的眼光,瀏覽著書中諸般充滿視覺趣味、欲望表徵、都市謠言的符號及其隱喻。這位都市符號學家的影像,固然趣味橫生、意象豐富;然而,當木馬文化出版社邀我為此書繁體字版《攝影的人,在路上》寫點文字,從而將原先的與為此版新增的圖文內容,仔細再讀過一遍時,我才臉紅地發現,自己嚴重怠慢了顧錚的街頭攝影。
顧錚的創作,不能只看單張作品,必須整體地閱讀;不能只閱讀照片,要配合他的文字一起閱讀。最重要的是,不能只在他的街頭攝影圖文裡尋找符號意義,而需要將他的攝影,放在中國的政治社會語境裡,才能比較深刻一些地理解這位都市漫遊者的街頭攝影,究竟意味著什麼。顧錚在新版作者序裡提到,一九八○年代中期,在中國幾個沿海城市出現的街頭攝影,既是對官方意識型態欲以沙龍攝影,轉移人們關注現實,自動產生了對抗的意義,同時也是企圖扭轉攝影者嗜奔偏遠鄉野蒐獵「新鮮」影像、卻不看腳下都市的一種批判性實踐。
這樣的對抗與實踐,於顧錚的城市和街頭,是從身體出發的:攝影家的身體穿梭於都市街道中,並且以攝影捕捉都市中的身體。顧錚在書中對於攝影與身體的思考,極具啟發。他提醒我們,攝影乃是一個從束縛/支配身體,到身體擺脫束縛的技術性過程。都市化過程裡,通過攝影,人的身體逐漸自由,進而心靈得以解放。在朱浩的訪談裡,顧錚提到他街頭攝影的一個關注焦點,是「都市的性化與性的都市化」。都市是性感的,也充滿性感的人物或影像符號,但「都市的性化」卻不能只從這層意思來理解。中國近代歷史上對政治與身體的長期禁錮之下,通過性化中國的都市,並且讓身體與性因為都市化、影像化,而從僵硬或沉睡中打開、甦醒,繼而讓身體活潑、大方、充滿動能,是何等迫切卻依然欠缺的「第一件差事」。因為人對身體與性的積極探索,從而對政治與行動進取,這恐怕是不僅中國且所有深受儒家禮教禁錮的華人社會,集體的重要功課。
從這個政治與文化語境,回頭閱讀顧錚的街頭攝影,特別意味深長,引人反思。顧錚的許多都市影像,是飽含欲望之明喻或暗喻的。可他的「欲望城市」,不僅僅是為了「解放城市」這個大命題,同時或者首先也在解放著自己。他的攝影,一直是從個人實踐與反身思考出發的。在「攝影於我」這段書寫裡,顧錚對於自身和欲望,以及城市與攝影之間的共謀、對峙、轉化、救贖…自剖得深刻率真,令人肅然起敬。我認識的顧錚,對政治的誠實與不妥協,有著少見的純粹;在他自我審視的文字裡,我又看到同樣純粹的一種誠實與無畏。
我一直相信,藝術、政治與人,是纏繞接合、精神上互通的一體三面;其中一者若真正誠實,其他兩者不可能太虛偽。在顧錚身上,我看到這三者的高度吻合,與相互印證。通過拍照、不斷地拍照,顧錚的攝影,見證著他對自由的熱愛,和精神解放的堅定實踐。是這樣一種追尋自由的靈魂,讓拿著相機的都市漫遊者,遠遠超越了中產閒逛者對街頭景觀無所事事的蒐集,讓街頭影像最後產生了政治意義
。 在《攝影的人,在路上》裡,除了為此新版所寫的作者序,顧錚也特別加上一篇〈街頭攝影發展小史〉,扼要地勾勒了攝影史上有代表性的街頭/城市攝影家,是很有價值的參考文獻。他在書末,也提供了最新的幾幅黑白攝影作品,我認為幾乎張張皆是精品。顧錚在最後〈想念台北〉一節,則展示了一些他在台北停留時的街頭影像。對照著居住地上海的作品,別有另一番情趣。
從顧錚第一次到台北開始,他就愛上這個城市了。一方面,台北確實有其可愛之處。另一方面,任何人初訪一個不至於完全無趣的城市,總比較容易先感受到它明顯的優點與特色,而暫時不追究它的問題面;人們也總是比較對自己居住的城市與社會,有著較嚴厲的批評──設若他們有反省能力的話。顧錚的台北街頭影像,大抵溫暖而人性,可清楚感受他對台北的喜愛。他比較貼近這個城市的人與活動,並且反映著台北的某種斯文與慢節奏。相對地,顧錚比較冷凝地看著上海,常常有距離地捕捉著那個城市的符號。
比起台北的緩慢、陳舊與溫馨,那個密佈著廣告看板、視覺符號、新奇事物的上海,在顧錚的攝影裡,似乎顯得遠比台北喧囂、躁動。但是,仔細閱讀顧錚的上海街頭攝影,雖不乏冷厲如羅伯特.弗蘭克者,卻仍有更多溫暖如艾爾維特(Elliot Erwitt)風格的作品。上海在視覺空間或市民活動上的某種喧嚷繁忙,固然提供了諸多劇場的、欲望的影像材料,但顧錚並不打算像貝蕾尼絲.阿波特那樣,在一九三○年代拍攝紐約曼哈頓時,對高樓硬體文明的那種崇拜與表揚。相反地,上海做為城市,在物質建設上的膨脹與浮誇,使做為影像話語建構者的顧錚,努力在他的作品中,將上海「縮小」:他很少描述上海那些全球最多的高樓大廈,高樓在他作品中的符號意義也並不太正面,甚至常是嘲諷的。他的目光,更多的放在上海各個角落的特寫,在細節、紋理,和氣氛中說故事,讓過大的都市,在影像裡回歸到一個合於人性意義的尺寸上。
在顧錚街頭攝影的這個特質裡,他雖然藉著「欲望城市」抒發著自己的自由靈魂,又回過頭來同時讓一種具有溫度的觀看,將不斷「非人化」的城市,試圖拉回到人的感覺和意義上。這或許是顧錚街頭攝影希望提供的多元觀念吧。
顧錚的創作,不能只看單張作品,必須整體地閱讀;不能只閱讀照片,要配合他的文字一起閱讀。最重要的是,不能只在他的街頭攝影圖文裡尋找符號意義,而需要將他的攝影,放在中國的政治社會語境裡,才能比較深刻一些地理解這位都市漫遊者的街頭攝影,究竟意味著什麼。顧錚在新版作者序裡提到,一九八○年代中期,在中國幾個沿海城市出現的街頭攝影,既是對官方意識型態欲以沙龍攝影,轉移人們關注現實,自動產生了對抗的意義,同時也是企圖扭轉攝影者嗜奔偏遠鄉野蒐獵「新鮮」影像、卻不看腳下都市的一種批判性實踐。
這樣的對抗與實踐,於顧錚的城市和街頭,是從身體出發的:攝影家的身體穿梭於都市街道中,並且以攝影捕捉都市中的身體。顧錚在書中對於攝影與身體的思考,極具啟發。他提醒我們,攝影乃是一個從束縛/支配身體,到身體擺脫束縛的技術性過程。都市化過程裡,通過攝影,人的身體逐漸自由,進而心靈得以解放。在朱浩的訪談裡,顧錚提到他街頭攝影的一個關注焦點,是「都市的性化與性的都市化」。都市是性感的,也充滿性感的人物或影像符號,但「都市的性化」卻不能只從這層意思來理解。中國近代歷史上對政治與身體的長期禁錮之下,通過性化中國的都市,並且讓身體與性因為都市化、影像化,而從僵硬或沉睡中打開、甦醒,繼而讓身體活潑、大方、充滿動能,是何等迫切卻依然欠缺的「第一件差事」。因為人對身體與性的積極探索,從而對政治與行動進取,這恐怕是不僅中國且所有深受儒家禮教禁錮的華人社會,集體的重要功課。
從這個政治與文化語境,回頭閱讀顧錚的街頭攝影,特別意味深長,引人反思。顧錚的許多都市影像,是飽含欲望之明喻或暗喻的。可他的「欲望城市」,不僅僅是為了「解放城市」這個大命題,同時或者首先也在解放著自己。他的攝影,一直是從個人實踐與反身思考出發的。在「攝影於我」這段書寫裡,顧錚對於自身和欲望,以及城市與攝影之間的共謀、對峙、轉化、救贖…自剖得深刻率真,令人肅然起敬。我認識的顧錚,對政治的誠實與不妥協,有著少見的純粹;在他自我審視的文字裡,我又看到同樣純粹的一種誠實與無畏。
我一直相信,藝術、政治與人,是纏繞接合、精神上互通的一體三面;其中一者若真正誠實,其他兩者不可能太虛偽。在顧錚身上,我看到這三者的高度吻合,與相互印證。通過拍照、不斷地拍照,顧錚的攝影,見證著他對自由的熱愛,和精神解放的堅定實踐。是這樣一種追尋自由的靈魂,讓拿著相機的都市漫遊者,遠遠超越了中產閒逛者對街頭景觀無所事事的蒐集,讓街頭影像最後產生了政治意義
。 在《攝影的人,在路上》裡,除了為此新版所寫的作者序,顧錚也特別加上一篇〈街頭攝影發展小史〉,扼要地勾勒了攝影史上有代表性的街頭/城市攝影家,是很有價值的參考文獻。他在書末,也提供了最新的幾幅黑白攝影作品,我認為幾乎張張皆是精品。顧錚在最後〈想念台北〉一節,則展示了一些他在台北停留時的街頭影像。對照著居住地上海的作品,別有另一番情趣。
從顧錚第一次到台北開始,他就愛上這個城市了。一方面,台北確實有其可愛之處。另一方面,任何人初訪一個不至於完全無趣的城市,總比較容易先感受到它明顯的優點與特色,而暫時不追究它的問題面;人們也總是比較對自己居住的城市與社會,有著較嚴厲的批評──設若他們有反省能力的話。顧錚的台北街頭影像,大抵溫暖而人性,可清楚感受他對台北的喜愛。他比較貼近這個城市的人與活動,並且反映著台北的某種斯文與慢節奏。相對地,顧錚比較冷凝地看著上海,常常有距離地捕捉著那個城市的符號。
比起台北的緩慢、陳舊與溫馨,那個密佈著廣告看板、視覺符號、新奇事物的上海,在顧錚的攝影裡,似乎顯得遠比台北喧囂、躁動。但是,仔細閱讀顧錚的上海街頭攝影,雖不乏冷厲如羅伯特.弗蘭克者,卻仍有更多溫暖如艾爾維特(Elliot Erwitt)風格的作品。上海在視覺空間或市民活動上的某種喧嚷繁忙,固然提供了諸多劇場的、欲望的影像材料,但顧錚並不打算像貝蕾尼絲.阿波特那樣,在一九三○年代拍攝紐約曼哈頓時,對高樓硬體文明的那種崇拜與表揚。相反地,上海做為城市,在物質建設上的膨脹與浮誇,使做為影像話語建構者的顧錚,努力在他的作品中,將上海「縮小」:他很少描述上海那些全球最多的高樓大廈,高樓在他作品中的符號意義也並不太正面,甚至常是嘲諷的。他的目光,更多的放在上海各個角落的特寫,在細節、紋理,和氣氛中說故事,讓過大的都市,在影像裡回歸到一個合於人性意義的尺寸上。
在顧錚街頭攝影的這個特質裡,他雖然藉著「欲望城市」抒發著自己的自由靈魂,又回過頭來同時讓一種具有溫度的觀看,將不斷「非人化」的城市,試圖拉回到人的感覺和意義上。這或許是顧錚街頭攝影希望提供的多元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