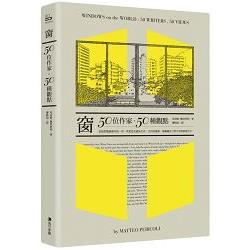出版故事 /書的故事
2015.12.14
《窗》──50位作家,50幅窗景,50種視野
文/馬帝歐.佩里柯利(建築師、《窗》企劃者&繪者)
打從我在紐約上西區公寓的窗前駐足,心有所感的那天起,轉眼十年了。當時內人和我正要搬出那一房一廳的公寓,我心頭湧上一股渴望,想把那幅窗景捲起來一併帶走。那景致我觀看了七年,日復一日,窗外那些樓宇錯落排列,深印我腦海。不知不覺中,那幅窗景成了我對那城市最熟悉的印象。它成了我的一部分,可是我將 從此與它揮別。
要密切留意已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的事物並不容易。「它們明天還是會在那裡。」往往要等到即將失去,或者已經失去,才赫然明白它們的重要。我納悶的是,我怎麼會沒有多加留意窗外的景色。這疏忽讓我不禁尋思,我們如何體驗與感知窗外的一切。說到底不外是,我們如何體驗與感知生活。
對我來說,窗口和窗景就像某種「重啟按鈕」。好比眼睛累了會眨一眨一樣,每當我想讓腦袋放空、思緒停頓,我會默默地任目光穿透玻璃,在窗外遊移,不加分析,不有意識地解讀。我的雙眼單純只是瞥向某個景致,並沒有真的盯著什麼看,而下意識裡對於那景致的熟稔——尋常的屋頂、著名的飾板、附近的中庭,遠方的山丘,反倒可以讓我分心恍神。我不經意地望穿一片玻璃,這玻璃把我和世界連接起來,也把我和世界分隔開來。
因此,二○○四年那天,我總算仔細打量那幅窗景。我甚至試圖拍照,但很快便發覺拍照行不通。照片無法傳達我眼中的風景,單純僅呈現窗外景物。於是我取來鉛筆和粉蠟筆,把窗景畫在一大張包裝用的牛皮紙上,窗框等一切都畫進來,並且頭一次注意到,我觀看了那麼久的風景裡蘊藏著那麼多的事物,而之前我竟渾然不察,它們都躲哪去了?
打從那時起,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素描一幅幅窗景。在二○○四年至二○○八年之間,為了一本以紐約市為題的書進行研究時,我發現作家通常和我有類似的處境: 在書桌前一坐就是數小時,所以他們若不是把書桌擺在靠窗的位置,盡可能飽覽風景,就是刻意避開窗景。當我邀請作家們以文字描述他們的窗景,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我在素描裡捕捉到的元素,都由他們的文字補足了(或者甚至是補強了)。
這就是二○一○年起在《紐約時報》發表以及後續刊在《巴黎每日評論》裡的「世界窗景」系列的發想與初衷:描繪全世界作家的窗景,並附上他們的一段文字—— 線條和文字透過有形的觀看角度結合在一起。本書裡的五十幅素描(有些從未發表過),每一幅都提供了一座觀景臺,也可以說是一個「視野」,讓你在五十趟的環 遊世界行旅中歇息和沉思。
經過這些年,我終於學會在窗前停留更久一點,也往往會思索著,假使我擁有那些窗景,我會有什麼感受。它們會如何影響我?如果我天天看著那些樓宇或樹木或船隻經過,我會有所不同嗎?我慢慢體會到,一扇窗終究不僅僅是與外在世界接觸或分隔的界面,它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向內的凝視,投射回到我們自身的生活。
要密切留意已融入日常生活之中的事物並不容易。「它們明天還是會在那裡。」往往要等到即將失去,或者已經失去,才赫然明白它們的重要。我納悶的是,我怎麼會沒有多加留意窗外的景色。這疏忽讓我不禁尋思,我們如何體驗與感知窗外的一切。說到底不外是,我們如何體驗與感知生活。
對我來說,窗口和窗景就像某種「重啟按鈕」。好比眼睛累了會眨一眨一樣,每當我想讓腦袋放空、思緒停頓,我會默默地任目光穿透玻璃,在窗外遊移,不加分析,不有意識地解讀。我的雙眼單純只是瞥向某個景致,並沒有真的盯著什麼看,而下意識裡對於那景致的熟稔——尋常的屋頂、著名的飾板、附近的中庭,遠方的山丘,反倒可以讓我分心恍神。我不經意地望穿一片玻璃,這玻璃把我和世界連接起來,也把我和世界分隔開來。
因此,二○○四年那天,我總算仔細打量那幅窗景。我甚至試圖拍照,但很快便發覺拍照行不通。照片無法傳達我眼中的風景,單純僅呈現窗外景物。於是我取來鉛筆和粉蠟筆,把窗景畫在一大張包裝用的牛皮紙上,窗框等一切都畫進來,並且頭一次注意到,我觀看了那麼久的風景裡蘊藏著那麼多的事物,而之前我竟渾然不察,它們都躲哪去了?
打從那時起,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素描一幅幅窗景。在二○○四年至二○○八年之間,為了一本以紐約市為題的書進行研究時,我發現作家通常和我有類似的處境: 在書桌前一坐就是數小時,所以他們若不是把書桌擺在靠窗的位置,盡可能飽覽風景,就是刻意避開窗景。當我邀請作家們以文字描述他們的窗景,奇妙的事情發生了:我在素描裡捕捉到的元素,都由他們的文字補足了(或者甚至是補強了)。
這就是二○一○年起在《紐約時報》發表以及後續刊在《巴黎每日評論》裡的「世界窗景」系列的發想與初衷:描繪全世界作家的窗景,並附上他們的一段文字—— 線條和文字透過有形的觀看角度結合在一起。本書裡的五十幅素描(有些從未發表過),每一幅都提供了一座觀景臺,也可以說是一個「視野」,讓你在五十趟的環 遊世界行旅中歇息和沉思。
經過這些年,我終於學會在窗前停留更久一點,也往往會思索著,假使我擁有那些窗景,我會有什麼感受。它們會如何影響我?如果我天天看著那些樓宇或樹木或船隻經過,我會有所不同嗎?我慢慢體會到,一扇窗終究不僅僅是與外在世界接觸或分隔的界面,它也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向內的凝視,投射回到我們自身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