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蟲悅讀 /獨家連載
-
 2017.11.10
2017.11.10玫瑰色鬼室友 vol.1 異形之友
文/我的大學室友許洛薇,英文名字Rose,綽號玫瑰公主,口頭禪是想要擁有玫瑰色的人生,瘋狂熱愛各種玫瑰系列產品,不但沐浴乳和洗髮精都是玫瑰香味,每晚還用昂貴的大馬士革玫瑰花水敷臉。我們那一寢的女孩子全省了香水錢,每天出門自帶花香,但是大學女生會認真化妝噴香水的真的不多。這股香味也跟著我到了活動社團,柔道社學長每次摔我都會笑得亂七八糟,不巧我不是會讓男性因為體香心動的類型,我懷疑「玫瑰香+蘇晴艾」能合成笑氣生化攻擊效果,反正我就是和香水絕對不搭的生物,大家都這麼公認,最近才有個學弟說我很有男人味,被我用過肩摔公開處刑。我不是體育系,但我會參加柔道社又得歸功於許洛薇。她看上柔道社主將,大三的體育系學長,四個字:黑高勁帥。她拜託我混進社團和主將學長打好關係,起碼要探聽到他有沒有女朋友。那時身為父母雙亡、拋棄繼承用學貸來唸書的小大一,整整一個學期的宵夜獎賞實在難以抵抗,我可以省下晚餐或用麵包先擋一下,等她結束各種活動後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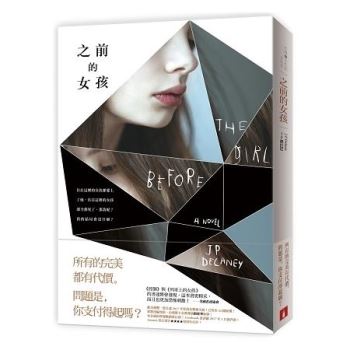 2017.10.23
2017.10.23之前的女孩
文/昔:艾瑪這是一間很舒適的小公寓,仲介用逼真的熱忱口吻說,生活便利,屋頂還有一小塊私人空間,那裡可以改裝成露臺──當然,要徵得房東同意才行。很不錯啊,賽門避開我的目光表示同意。我一走進來,看到窗戶下面那片六英尺長的屋頂,就知道這間公寓不行。阿賽也知道,但不想告訴房仲,起碼不要一下就說出來,以免顯得沒禮貌。他搞不好還希望我聽久了這男人的無聊廢話會變得猶豫不決。房仲是賽門喜歡的那種傢伙:精明,自以為是,做事急躁,八成還會看賽門的公司發行的雜誌。我們還沒上樓,他們就開始聊起運動賽事。這裡的臥室滿寬敞,仲介說,有充裕的──不行。我開口插嘴,打斷這場字謎遊戲。這裡不適合我們。仲介挑起眉毛。現在的市場不能太挑,他說,這一間今天晚上就會沒了,今天就有五組人來看屋,都還沒放上我們公司的網站哦。不夠安全,我直截了當地說,走吧?窗戶都有鎖,他一一解釋,大門安裝的是集寶保全系統。當然,如果是特別擔心安全問題,可以加裝防盜警報器,我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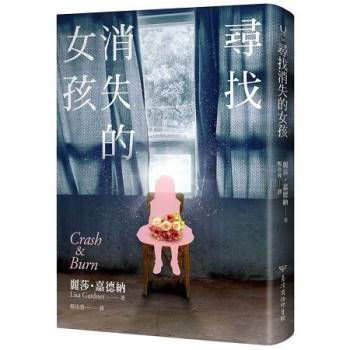 2017.09.05
2017.09.05尋找消失的女孩
文/第五章小時候你有過什麼夢想?長大以後當太空人或是芭蕾舞者?甚至是披著紅色披風的超級英雄,擁有一躍就跳過高樓大廈的能力?或許你打算成為跟母親一樣的律師,或是跟父親一樣的消防員;又或者你完全無法認同自己的家人,最大的夢想就是離開這個鬼地方,永遠不回頭。可是你作過夢。每個人都會作夢。小男孩、小女孩、生在貧民窟裡、在精英白人家庭裡長大。每個人都曾立志要成為大人物,做大事。我想我應該有過夢想,但是到了現在,我記不得那些了。醫生在病房裡,她站在門邊,對那個自稱是我丈夫的男人說話。他們的腦袋湊在一塊,壓低嗓音,就像一對情侶,我如此猜想,不知道為什麼。「在車禍之前,她有沒有睡得比較好?」醫生問。「沒有。一個晚上最多睡兩、三個小時。」「頭痛呢?」「還是很嚴重。她不再多說什麼。我只會在沙發上找到她,躺著冰敷額頭。」「情緒?」男子輕笑一聲。「理想的時候就只是憂鬱。如果運氣不好,簡直要逼人殺了她。」醫生點點頭。她的名牌上印著賽兒‧瑟... -
 2017.08.28
2017.08.28那不勒斯故事3:逃離與留下
文/1 我最後一次見到莉拉是在五年前,二○○五年的冬天。那天一大早,我們沿著通衢大道散步,就像在這之前好幾年來一樣,兩人都覺得不太自在。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講話,我記得。她只哼哼啊啊的,一面和不理會她的人打招呼,偶爾幾次打斷我,也都只是發出驚呼聲,而且和我講的話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這些年來發生太多壞事,有些甚至很可怕,為了重拾往日的親密關係,我們必須講出心中隱藏的祕密心事,但我沒有力氣去找話來說,而她雖然可能有力氣,卻沒有欲望想講,因為不覺得講了有什麼用。 然而我還是很愛她,只要回到那不勒斯,我總會想辦法去看她,儘管我不得不承認,我有點怕她。她變了很多。當時我們都有了年歲,但在我慢慢變胖的同時,她卻永遠還是那麼瘦。她的短髮是她自己動手剪的,滿頭白,不是因為她刻意如此,而是疏於照顧。她臉上皺紋很多,而且越來越像她父親;笑聲神經兮兮的,簡直像尖叫,講話的聲音也太大。此外,她講起話來也總是比手畫腳,每個手勢都斷然用力... -
 2017.08.28
2017.08.28獸身譚
文/獸身譚 我曾告訴男人,我作了這樣一個夢:像是颱風將至的酒黃天色裡,我到了一個充滿黑鐵雕花欄杆、恐怕歐洲才可能有的火車站,預備向我的好友送別,而四處都是被鐵柵切割過的光線,彷彿一地的硫磺色破片,顏色一如我送給他的黃水晶,而攤平於地的邊角則氣化一般,失去了最後成全其形狀的線條;那時候車室的掛鐘,顯示時間為下午四點,他陪著我過來,就在那鐘下等我,但一直反覆地催促「我要走了」、「我真的要走了」,而臨別的朋友話多了些,拉著我不放,我從月台趕回候車室時,他早已一聲不響地離開,此時,我感覺到一股憂傷黯然,整個候車室裡的燈便像有人將其旋熄一樣,漸進但快速地黯淡下來,直到光線在這斗室之中完全泯滅。 男人聽了,用繞富興味的表情不斷追問:「為什麼我要走呢?因為之前已經跟別人約好要去別的地方了嗎?」我只能搖搖頭說:我不知道,夢裡的對話沒有直接透露。當天,男人反覆追問同樣的問題兩三次,我告訴他:「我真的不知道。」他才作罷。 後來... -
 2017.08.03
2017.08.03無花果與月
文/第一章 我的紫色眼睛Ǽ我覺得悲傷就像河流。流過的地方有深有淺;流速也是,有急有緩。然而流水一刻也不停歇。悲傷的河流不斷流,有一天終於匯入巨大的悲傷之海,然後才會停止流動吧。不過,「悲傷之海」是什麼?它到底在哪裡?我們懷抱著如此巨大的悲傷,到底該往哪裡去?你知道嗎?我是前嶋月夜。十八歲。就讀當地高中三年級。身高一七一公分。很高對吧?其他的......唔,就普通吧。我有兩個哥哥,大哥是一郎,大我八歲;二哥是奈落,大我一歲。不過我跟他們沒有血緣關係,因為我是撿來的。啊,家裡沒人在意這種事。我的兩位哥哥都以個性很酷著稱。然後,今天,──一早開始,就是我的二哥奈落突如其來的葬禮。Ă因此一大清早,人們便忙亂地聚集到這處工商會議所,一棟四方形的建築,孤伶伶地坐落於荒野中央小鎮的約莫正中心。在會議所舉辦葬禮似乎是極罕見的事,因為在城鎮邊緣風沙飛來的乾燥區域,就有一家全新的豪華殯儀館,是政府預見即將到來的高齡化社會才剛「插」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