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暈的樹林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簡媜筆下搖曳恣縱,其作品莫不使讀者如享盛宴,餘味無窮。本書內容包括尋常生活、懷鄉、旅行、閱讀等多種題目,其中約三分之一取自絕版多時的《浮在空中的魚群》,餘皆未嘗結集,但都經重新檢視增修,精緻投射,展現盎然之新意。
試閱
竹本小姐
說自己聰明,需要勇氣;承認笨,則需要智慧。我很笨,愈來愈笨。
發現自己確實很笨的那天,我的心情很好。太要強把自己訓練成人群中的聰明者,且要時時顯露其聰明,是一種危險的人生觀,占盡榮寵不留給他人與自己餘地,得到的往往只是一頂虛幻的聰明草帽,而災厄與傷害可能丟給別人分攤。只要在形上層次做個理性、健康、聰明的人就夠了,生活層面不妨笨一些,留點餘地讓別人去聰明,相處起來才有樂趣。
笨拙大概有三種來源:能力欠缺、心理恐懼與心不在焉。就生活技術而言,我不難拿個八十分,烹調、持家、修理電燈、牽電話線、治療水管漏水……這種小事難不倒我。但是碰到精密複雜的電器用品操作,我的笨拙暴露無遺。由於非常害怕觸電的心理陰影,轉而投射對電器恐懼,凡是附有中英文說明書,遙控器、昂貴的、精巧的,我的操作能力就愈低劣;連從自動捲片傻瓜相機中取出底片這麼簡單的小動作,都能被我抽出五呎六吋長的底片麵條兒,那麼,想從錄影機中取出片匣卻卡死在裡面的事兒也就值得諒解了。具有紀念性的底片報銷,錄影機送修,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我也懶得自責。通常,笨人不願意立刻承認自己笨;有一回,自作聰明把音響解剖開來再重新組合,以測試自己的能力,結果多出一條線,怎麼也找不到插孔。我深知自己「天賦異稟」,上朋友家,絕對敬慎小心,除了調音量大小、按電源開關之外不碰貴重電器。當然,他最好先告訴我開關在哪裡,否則,我會去拔插頭!
那些能夠輕鬆使用各種遙控器、摸熟電器功能的人,很容易成為我心目中的「偶像」,如果他還會開車,我就更「崇拜」了。熟識的朋友一直譏笑我對好萊塢電影明星「阿諾史瓦辛格」投注過多激動而盲目的崇拜,斥之為肌肉全餐以此「批判」我的品味。其實,除了暴跳如雷的肌肉外(相當程度,他彌補了我對自己瘦弱體型的卑微情結),《魔鬼終結者》與《魔鬼總動員》中激烈的科技文明追擊場面才是吸引我的地方。商業娛樂片本就具有煽動力,讓平凡人在電影院變成英雄暫時遺忘現實缺陷。像我這種對科技產物低能的人,自然會藉助科幻片,尤其是阿諾的冷酷與神勇取得一百二十分鐘的銀幕補償。我不會要求阿諾帶給我大腦,他只要不斷地在科技文明裡展現肌肉就行了。步出電影院,會持續亢奮一小時,走起路來虎虎生風,甚至煽情地把「阿諾史瓦辛格」的譯名改成「阿諾使我性格」。所以,為了我的緣故,不准他演文藝愛情片,否則馬上吊銷「英雄執照」。
開車,恐怕是永遠克服不了的笨拙。有段時期,我懷疑自己的運動神經有問題,跑去學網球、柔道、游泳,成績也不錯,證明不是能力欠缺而是心理恐懼。我當然知道恐懼的因由也試圖克服,下決心先學摩托車,繞場三兩圈後大了膽上路,鄉間柏油路一根腸子通到底,閉眼睛也沒問題,我卻開始冒冷汗,手腳發軟,突然尖叫一聲,跳車,摩托車獨自「碰碰碰」往前駛,終於歪倒草叢像狗一般呻吟。我無法描述當我從地上爬起來用腳走路時感到多麼有安全感,竟生出「解脫」的喜悅。當然,更不好意思張揚那只是一台五十CC輕巧型的摩托車。
兩輪的招架不住,四輪的甭提。熱心的朋友體恤我住得遠,替我去駕訓班報名,我在她的鼓動下幻想有一天能很神氣地開車。通知書寄來了,五月二十開始上課。日期愈逼近,所有焦慮的反應都出現了;開始做噩夢、剝指甲、對汽油反胃……。五月二十那天,我再也受不了,把通知書撕掉,立刻快樂如一隻小鳥──逃避成功!朋友不可思議地批評一頓,「好啦,總有一天我會去學的,人格保證!」我說。有那麼一天嗎?如果有人用武力押我去駕訓場,逼著學,學不會就抽鞭子,可能學得成。唉!要是阿諾在就好了。
心不在焉而導致「短路」,這種笨拙最具拙趣。像我祖母那樣機伶敏銳的女人,有一回煮稀飯時,居然被我從飯鍋裡舀出一隻手錶,可以媲美愛迪生煮蛋的趣事了。做為她的徒孫的我,也常常一心三手,充分發揚家族脫線傳統。小時候,媽媽叫我買胡椒,我買辣椒;要我去竹叢下把鴨子趕回來,我聽成去剝竹籜──這兩句閩南語音近,我也絲毫不懷疑指示,因為她是一個常常有新奇做法的母親。於是,當我捧著一畚箕的竹殼子交給她時,我看到她氣得大笑的表情,彷彿不相信我是她親生的女兒。
這種心不在焉的毛病隨著沉浸稿田太深、一時無法回到現實而時常發作。明明往廚房走,忘了去廚房做什麼?撥通電話,忽然不記得撥給誰?只好這麼問:「我是簡媜,請問你是誰?」有一天臨出門,急著找眼鏡,翻遍客廳、書房,找得天雷勾動地火,喊妹妹:「妳有沒有看到我的眼鏡?」她忽然用很怪異、說不出話的表情趴在樓梯上「痙攣」。當時,覺得她這種隔岸觀火的笑鬧態度很令我不舒服,她斷斷續續地把話說完:「眼鏡……在……妳臉上!」我才想起剛才找眼鏡時曾習慣性地扶眼鏡的,只好自我解嘲:「難怪覺得視力變清楚了!」聰明人做起笨事比笨的人更笨! 大部分的心不在焉發生在盥洗室。洗澡忘了帶衣服,隔門喊救兵,偏偏家人拿蹻,談條件敲竹槓,或乾脆跩跩地:「竹本小姐,我們不知道妳喜歡穿什麼衣服,妳自己出來拿?」這種尷尬時刻最能檢驗對自己身體的開放程度。拜家族脫線淵源之賜,我也不難抓到復仇機會,浴室裡有人喊了:「拜託啦,幫我拿衣服!」「口木先生,你學小狗叫,我就去拿!」「汪!汪汪!」「不對,那是母的,我要聽公狗叫!」「嗯……汪汪!汪汪汪!」「不對,我要聽公狗被踩到尾巴的!」「該該!該該該!」
還好,在外頭盥洗室鬧的笑話沒人知道──我必須經過「思考」才能分辨哪一扇門是「女廁」。
有一回,跟朋友上啤酒屋,兩扇盥洗室門上各掛一個俏皮布偶,必須掀開它們腰部的布才能分辨男女,由於不好意思,我沒掀,逕自進入其中一間。當我出來,等在門外的一位男士立刻表情錯愕,嘟囔著往另一間走,正巧,也出來一位女士,他完全被打敗了以至於搔著腦袋去掀門上的布偶再看清楚,臉上充滿懷疑,像驚嚇過度忽然懷疑自己是不是男人一般。
另一家布置雅致的茶藝館,同樣兩扇門,只標示「♂」、「♀」符號。我傻眼了,完全不記得哪個屬於我?由於走錯門害那位男士失去信心的記憶令我不敢再輕舉妄動,又不想坦承忘了符號意義,只好用小技巧掩飾大笨拙,問服務小姐:「麻煩您幫我開女廁的燈!」顯然,我必須記住這兩個鬼符號,總不能笨到連廁所都找不到。我站在門口「思考」,符號的原始來源既不可得,只好賦予新的解釋以強化記憶。「♀」像什麼?棒棒糖?一對小野花?都不好,後來想通了,背十字架的是女人,像箭一般射出去的是男人。下回,我會記得走向苦難的十字架,去從事神聖的解放。
M與W的英文縮寫也困擾我,在某種情況下,我對形體一樣、位置不同的符號辨識能力很差──包括禁止左轉、右轉的交通號誌。總之,某次聚餐,我與另一位男士同時打算去化妝室,我們沿途交談,由於小酌幾杯酒,微醺加上歡愉的談話,柔和的燈光曖昧地照在M與W兩個鍍金字上,瞬間讓我喪失判斷能力──或者,在那種暈然的氛圍中,潛意識裡自以為雌雄同體或渴望成為男人或不願承認自己是女人的原始念頭出來作怪,於是,我選擇M,而他以反射動作走向W不經思索。忽然,他慌張地推門而入彷佛遭受極大的打擊:「我們錯了!」「什麼錯了?」我以為他想延續剛才的話題修正什麼意見。「妳應該去那裡,我應該在這裡!」我很窘,居然問了一句笨話:「難道不能同時在這裡嗎?」他說:「原則上不行!」「哦!這樣啊!」所以生平第一次,我被趕出男廁。叫我這張臉往哪兒擱呢?心裡暗罵自己:「妳笨死了,笨到要別人告訴妳是男的女的!妳是W,W裡面的W,再搞錯就是豬!」
現在,我賦予這兩個字母新的解釋,W是女人上半身的素描,M是男人下半身的寫實線條。
笨到這種程度有藥可救嗎? 兩床毛毯
在浮誇的末世荒城裡,我像一隻傷感的鷹,停棲在暗夜的一棵枯木上,眺望遠處、梳理記憶,搜尋那些在航飛過程中令我眼角微溼的故事。總要找出一兩件事、一兩個人,帶著它們跨過世紀門檻,提燈一樣,才能在新世紀裡安頓。
他是社區警衛,五年前就已瘦得像一截沾雪老樹幹。他慣常沉默,不是因為上了年紀或脾氣古怪,而是一種自在清明的沉默;彷彿看多了人、嚐遍了事,知道人間是怎麼回事,也就不需多言。
「看到沒?以後要用功讀書,才不會像他一樣當工友,知不知道!」「知道。」小公園裡,一個媽媽看他推著單輪推車到處整理廢園,趁機對小孩進行機會教育。
他沒聽到,但我想他知道。塵風不能蒙蔽玫瑰花園的丰采,烏雲倒影也不會改變河流的清澈吧!他沒有分別心,義務幫社區人家整理園子,尤其是那些未住人的荒院,他救活花木,默默布置社區入口的花圃,多餘的盆景就運到喜歡園藝的住戶門口,也不留話,他想有心人會懂得另一個有心人留在空中的氣息吧! 你無法報答他,當你發現門口的信箱太小老是塞不進雜誌,忽然被他的巧手改裝成大信箱時;當你發現搖搖晃晃的院燈也被旋緊時;當你又發現不知哪來的花木裝扮著你的花台時;你才知道你這麼個每天出門去斤斤計算的一坯土是無法報答巨嚴的關懷的。
可是,不利於他的言語開始溢散。有人指責他只幫某幾戶理院子,不幫他打掃門口;有人說他年紀大了,社區需要孔武有力的人以維護安全……。真正原因是,他知道太多事情了,包括角逐委員會總幹事的兩組人馬如何明爭暗鬥,包括選舉時原本要用來賄選的金錢如何落入某人口袋,以及每個月有點奇怪的小工程帳目。所以,犧牲一個老警衛,是那撮人僅有的共識。反正,他只是個警衛。
就這樣走了,不知去處。直到有一天,公司樓下的警衛伯伯說有人找我,就在警衛室昏暗的角落,我再次看到他。他說:從報上知道妳在這兒上班,今天有事得辦,從桃園上臺北來,順道把東西帶來。年前回大陸探親,經過香港買了兩條毛毯,用不上,送妳們姊妹,冬天保暖。
「妳們姊妹,都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他誠懇地說。
我欣然接受。不只是收毛毯,是收一個長輩對小輩的祝福與期許。藉著這份期許,我知道不管在末世荒城也好,險惡行旅也罷,我這一生要找的珍貴之寶,其中一項叫做「人的尊貴與厚重」。 藏與不藏──後記
藏
發現那只紙箱,才驚覺自己的某些行為愈來愈像母親與祖母。
高齡九十四的阿嬤雖然失明仍然保存「藏東西」癖好,眼前的姑且不提,就說四五十年前她兩眼炯炯有神、身手矯捷還是個年輕祖母的那時候;轄區內有五個孫子,皮的皮、懶的懶,愛哭的愛哭、貪吃的貪吃。很快地,她制定「鞭子與胡蘿蔔」規章予以管教。鞭子,無須贅言,胡蘿蔔,換算成當年物資就是蕃薯餅、蜜餞、果子及金柑仔糖等零食。
祖母雖不識字卻是個精算高手,她對孩童的咀嚼、消化能力甚有研究,其名言是:鐵塊放入小孩嘴裡都會溶,還說我們「餓到青狂狂,連桌腳嘛強強欲拖去嚼」。因此,為了延緩零食被吃光的時間,她最愛買一小包硬梆梆的金柑仔糖犒賞「員工」,經濟實惠,最適合用來驅趕小鬼。我們領得那粒深褐或五彩的小糖球,必定立刻放入口中以免滾落於地找不著,癡癡地吮吸一會兒後,忍不住從嘴裡掏出來觀看它被溶解的程度,如掏眼珠般小心翼翼,通常是,放回嘴裡沒多久,它就溶光了。
溶光了,當然再去討一顆!不約而同,五個小鬼又纏上來,阿嬤兇巴巴地說:「沒有就是沒有!」於是耍賴的耍賴、跺腳的跺腳,年紀小的乾脆躺在地上哭喊、翻滾,狀甚痛苦;阿嬤掏出口袋以證明所言不假──這真是重要的一刻,同時啟發我們兩件事理:一、大人會說謊,二、糖果被藏起來了。
小鬼們一哄而散,跑入屋內,在客廳、穀倉、眠床、密腳、衣櫥分頭翻找,齊力「抄家」,終於抄出日曆紙包著的糖球,一人一顆,剩餘的放回原處──當然,沒多久,被移往他處,再不久,又換一處,直到只剩那張薄薄的日曆紙。
藏匿與搜尋的戲碼不斷上演,阿嬤的手法愈來愈複雜,我們破解的功夫也愈來愈純熟,甚至出現馬戲團才看得到的疊羅漢或體育老師不敢教的民俗雜技。問題來了,阿嬤刻意追求高難度的分批藏匿術,以致連她自己都忘了還有一些藏在哪裡?每隔一段時日,總會在穀倉一角找到長滿青霉的椪柑兩個,在棉被縫隙看到黏成一團的五顆糖果或在碗櫥頂端一頂斗笠下發現四片軟趴趴的餅乾,螞蟻走成的虛線比我們的嘆息還長。 零食本屬奢侈品,又被如此糟蹋,難免惹出「民怨」,自此之後我們要求她「權力下放」,務必平分完畢,讓我們吞入腹內一了百了,或各自藏匿自行負責──由此衍生之手足鬩牆情節,如誘拐、共謀、爭吵、偷取、打架、哭訴則不在此詳述,參照現今政治生態即可。
移居臺北,阿嬤老了,五個孫子長大後皆承續家族基因,從嗜糖小童轉骨變成討厭甜食的人,慶生時迫不得已買生日蛋糕只為了有個地方可以插蠟燭,昔日哭喊糖果、在地上打滾如喪考妣的情景已永遠消逝。這確實剝奪了一個祖母的樂趣,若孫子孫女喜好甜食,她可以到處購買鳳梨酥、綠豆椪、牛舌餅犒賞員工,如今,她無計可施,只能問:你鄉下阿姑做的醬油要不要拿一瓶回去?
我母親的藏匿哲學是不藏謂之大藏。昔年,她手上無零食管轄權,小孩不會找她,但女孩們總會對母親的抽屜、衣櫥感興趣,東翻西找,偷偷挖一點面霜抹臉,穿上大衣照照鏡子,甚為滿足。在我們看來,她不只不藏而且不收,東西、物件隨意置放,如此鬆散,誰也不會懷疑她有什麼收藏。有一次,我問她當年出嫁戴什麼金飾,她回房一會兒,竟現出一條令人眼睛一亮的項鍊,我心想:「嚇!妳的房間被我們翻過上百次了,怎從來沒見過這玩意兒?真會藏哩!」我因此懷疑她一定具有蜘蛛人功夫,能飛簷走壁、倒吊晃盪,才能藏得天衣無縫。
藏匿的樂趣就在「攻於心計」的過程──不被他人找到又不致連自己都找不到,前者難,後者更難。因此,藏功猶如設定密碼,皆屬一種自我挑戰,而且,自己一定要戰勝自己,否則,領不到錢事小,所藏之物曝光事大。
祖母與母親最重要的一次藏匿戰役不是防著我們,是針對從未謀面的人,小偷。
十幾年前,我還住在娘家。有一陣子社區頻傳竊案,小偷連白晝亦出沒,左鄰右舍皆遭殃,財物損失慘重,轄區警方雖加強巡邏,但怎麼巡也巡不到案發現場。照這種進度,遲早會輪到我家。家人商量對策,既然不願花數萬元更換鐵門鐵窗,只能消極因應;各人藏好錢財珠寶,家中儘量保持破舊、雜亂(平日即已如此),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用品,要偷就請便,只要小偷不嫌重。 某日清早,我剛起床,見母親蹲在陽台整理花木,從背影看,大約是替植栽換盆添土。我走近,她嘻然傻笑,彷彿做什麼不可告人之事被逮到,此時我才看見地上有一牛奶罐,她招認,所有的金飾已用塑膠袋層層包覆,置於罐內,現正要藏入花盆裡。我大笑,讚她一流。只見她速速覆土,把原來那棵半死不活的榕樹種回去,土上又佈置了石頭、蛋殼、煙蒂,將盆景放回窗台原處。我很放心,甚至覺得可以夜不閉戶。
相較於母親的「掩埋法」,祖母因視力退化必須儘量單純,省去複雜手法以免造成自己不便。我們盤問數次,她不露口風。後來,一再保證不會告訴小偷、我們也不會去偷,她才吐實;原來,她把數萬元現金用報紙、塑膠袋包好,偽裝成一條豬肉狀,藏入冰箱冷凍庫,與貢丸、魚、排骨、雞肉共處一室。這招「急凍法」堪稱出神入化,至此我非常放心,除了小偷找不著,我相信想得出這種妙招的祖母這輩子不會得老人癡呆症。
不久,某個鼾聲大作的夜裡,小偷果然來了。料想他無處下手又不想業績掛零,只好偷書包。天亮,準備上學的小弟找不到書包,隨後在陽台發現書本、作業散落一地,裝車票與零用錢的皮夾被丟在花盆上,損失兩百元,那是他當日的營養午餐與晚餐費。可怪的是,我們一點也不在意被闖空門,甚至懊惱自己睡死了沒看到賊兒臉上複雜的表情。唯一激動的是兩百元苦主,他很氣,罵小偷為什麼不乾脆把課本、作業一起偷走?我們提醒他,「才兩百元,不要要求太多。」
冰箱裡那條「五花肉」愈來愈瘦了,舉凡叫瓦斯、收報費、清潔費或身上欠缺現金時,就把那條五花肉拿出,無須退冰,即取可用,剩餘的復歸原處。唯一提出質疑的是一位瓦斯先生,「鈔票怎是冰的?」「不然怎樣?你要燙的嗎?」
就像幼時,金柑仔糖只剩那張日曆紙,阿嬤藏的五花肉最後也只剩那張報紙。 不藏
一年半前,為了搬家不得不整理地下室儲藏間,從最黑暗的角落拖出一只紙箱,上頭只寫「稿子,暫存」,卻完全不記得是什麼稿子。用美工刀劃開膠帶時,猶如法醫解剖無名身軀,不帶感情又摻雜好奇。一疊原稿、剪報現身了,散出紙張的潮溼味,這味道屬於活的世間,像一頭淋著暴雨的耕牛窩在草堆上,身體乾不了,遂閉目養神,現在,陽光出來,可以睜眼了。
於是,發覺自己的行為像母親與阿嬤;亂藏像媽,藏到忘了像阿嬤。
我對寫過的文稿常有自暴自棄傾向,除非隸屬計劃中作品或足以歸併出主題的才會收妥,其餘皆隨之生滅;因此,有的只見原稿,有的只剩剪報,有的只記下篇名及發表處,原稿剪報俱無。海明威形容寫過的書像一頭死去的獅子,深得我心。寫作最快活之時在於構思、書寫過程,如一趟孤獨的攀岩之旅,外人不解把自己吊在半空中有何樂趣,攀岩者卻樂此不疲,繼續挑戰更高的海拔。然而,一旦作品完成,其後續瑣事令人不耐,猶如攀岩者回家之後,總是腰痠背痛。
這箱稿子乃過去十多年間未結集之作,長長短短一百二、三十篇,十分龐雜,隨手抽幾篇流覽──我得決定丟棄或保留,發覺混亂之中不乏趣筆,遂原箱封妥,搬至新家。新居不像舊宅有儲藏室可存放一切礙眼之物,這箱子放在我天天看得到之處,成了眼中釘。
加拿大作家楊‧馬泰爾(Yann Martel,著有《少年Pi的奇幻漂流》)處理失敗之作的法子是放逐──不是放逐自己,是稿子;他從印度某個小鎮寄出那包原稿,收信地址是虛擬的,在西伯利亞,信封上還寫了回信地址,也是虛擬的,在玻利維亞。當他看到郵局職員蓋上郵戳時,心情跌入谷底,痛不欲生。 相較之下,海明威的遭遇更慘。一九二二年,海明威二十三歲,為報社駐歐記者,他的妻子飛來相會,卻在巴黎的里昂車站等火車時,把海明威的整箱原稿遺失了,這是他四年間的全部原稿,包括長篇一、短篇十八、詩十篇,就這麼永遠丟掉了。然而,海明威一點也不沮喪──請恕我如此想像:見面時,大他八歲的妻子伊麗莎白哭出聲:「我把你的稿子搞丟了,我該去撞牆!」海明威安慰她:「親愛的,沒關係,那些都是失敗之作!」伊麗莎白瞪大眼睛:「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丟呢?」海明威乾笑兩聲,答:「我下不了手。」
好。海明威一點也不沮喪,他重寫。次年,出版第一本書《三個短篇和十首詩》,接著,《我們的時代》,再來,……。我推測,隨著「救回」的作品愈來愈多,他與太太的感情卻愈來愈糟,因為,到了二十八歲(挽救「四年間原稿」滿四年之後),海明威離婚了。可見,他很在意這件事。
將近一年半,我既迷惘又煩躁,不想讓稿子坐飛機去西伯利亞或是利比亞,也缺乏薩伐旅獵人海明威重寫的能耐,只剩修改、整編一途;其箇中滋味猶如減肥塑身,看那團肥肉如如不動,很想衝至廚房拔刀,因此,一度罷筆。之後,想起舊作《浮在空中的魚群》《七個季節》早已自書市絕跡,不妨趁機歸併,一起調控。此舉乃搬石頭砸腳後又用力敲頭,是自我凌虐。果然,「開挖」不久,即倣效工地圈著圍籬寫上完工日期欺騙路人,裡頭放一部挖土機,沒動靜了。
後來,我尋思這事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萬一我遭逢意外,文稿落入壞脾氣編輯手裡有礙我安息;若是一病不起,豈非得躺在病床上一面痛苦呻吟一面吊點滴改稿跟時間賽跑─果真是「忙得要死」,屆時必定憎恨現在的我荒廢光陰、疏懶度日。這一想,有所警覺,加上思及偏遠地區、失能家庭的眾多孩童欠缺學費與午餐錢,那箱殘膏賸馥若能換版稅給他們些微溫飽也是美事。於是,鼓起精神比對稿件記錄簿,央朋友從圖書館搜尋未留存的數十篇文章(泰半已找不到),再與百餘篇原稿、剪報匯整,共挑出六十七篇較有可觀者;又拆解《浮在空中的魚群》(原有四十篇,其中十四則小品擬併入《下午茶》,四篇刪除,剩二十二篇留用),前後共存八十九篇,逐一增筆、修潤,務使殘膏恢復甘醇、賸馥散發香氛。
每當我宛如遊牧民族背著我的牛羊(稿子)在星巴克、麥當勞或街角咖啡館、捷運車廂放牧時,眼倦神勞之際,總浮現孩子吃午餐情景(這大概是小學時我特別期待吃營養午餐的情感餘緒罷),遂踴躍前進,依稿性、旨趣劃分五輯:或爬梳尋常事理、提煉生活滋味,或懷想鄉園舊情,或閒話旅行、閱讀之所見所思,或變奏為小說化寓言,或歸返自身記述成長、創作、夢境之體會與感悟;復按以東北西中南沿步道而行的意象貫串全書,以雜樹、野鳥、藤、亂石、芒叢寄託這一段修繕舊稿的心情。
梅雨時節,竣工,名為《微暈的樹林》。
註:《七個季節》舊稿與其他小品、短文另匯成《密密語》一書。
二○○六年六月,臺北
說自己聰明,需要勇氣;承認笨,則需要智慧。我很笨,愈來愈笨。
發現自己確實很笨的那天,我的心情很好。太要強把自己訓練成人群中的聰明者,且要時時顯露其聰明,是一種危險的人生觀,占盡榮寵不留給他人與自己餘地,得到的往往只是一頂虛幻的聰明草帽,而災厄與傷害可能丟給別人分攤。只要在形上層次做個理性、健康、聰明的人就夠了,生活層面不妨笨一些,留點餘地讓別人去聰明,相處起來才有樂趣。
笨拙大概有三種來源:能力欠缺、心理恐懼與心不在焉。就生活技術而言,我不難拿個八十分,烹調、持家、修理電燈、牽電話線、治療水管漏水……這種小事難不倒我。但是碰到精密複雜的電器用品操作,我的笨拙暴露無遺。由於非常害怕觸電的心理陰影,轉而投射對電器恐懼,凡是附有中英文說明書,遙控器、昂貴的、精巧的,我的操作能力就愈低劣;連從自動捲片傻瓜相機中取出底片這麼簡單的小動作,都能被我抽出五呎六吋長的底片麵條兒,那麼,想從錄影機中取出片匣卻卡死在裡面的事兒也就值得諒解了。具有紀念性的底片報銷,錄影機送修,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我也懶得自責。通常,笨人不願意立刻承認自己笨;有一回,自作聰明把音響解剖開來再重新組合,以測試自己的能力,結果多出一條線,怎麼也找不到插孔。我深知自己「天賦異稟」,上朋友家,絕對敬慎小心,除了調音量大小、按電源開關之外不碰貴重電器。當然,他最好先告訴我開關在哪裡,否則,我會去拔插頭!
那些能夠輕鬆使用各種遙控器、摸熟電器功能的人,很容易成為我心目中的「偶像」,如果他還會開車,我就更「崇拜」了。熟識的朋友一直譏笑我對好萊塢電影明星「阿諾史瓦辛格」投注過多激動而盲目的崇拜,斥之為肌肉全餐以此「批判」我的品味。其實,除了暴跳如雷的肌肉外(相當程度,他彌補了我對自己瘦弱體型的卑微情結),《魔鬼終結者》與《魔鬼總動員》中激烈的科技文明追擊場面才是吸引我的地方。商業娛樂片本就具有煽動力,讓平凡人在電影院變成英雄暫時遺忘現實缺陷。像我這種對科技產物低能的人,自然會藉助科幻片,尤其是阿諾的冷酷與神勇取得一百二十分鐘的銀幕補償。我不會要求阿諾帶給我大腦,他只要不斷地在科技文明裡展現肌肉就行了。步出電影院,會持續亢奮一小時,走起路來虎虎生風,甚至煽情地把「阿諾史瓦辛格」的譯名改成「阿諾使我性格」。所以,為了我的緣故,不准他演文藝愛情片,否則馬上吊銷「英雄執照」。
開車,恐怕是永遠克服不了的笨拙。有段時期,我懷疑自己的運動神經有問題,跑去學網球、柔道、游泳,成績也不錯,證明不是能力欠缺而是心理恐懼。我當然知道恐懼的因由也試圖克服,下決心先學摩托車,繞場三兩圈後大了膽上路,鄉間柏油路一根腸子通到底,閉眼睛也沒問題,我卻開始冒冷汗,手腳發軟,突然尖叫一聲,跳車,摩托車獨自「碰碰碰」往前駛,終於歪倒草叢像狗一般呻吟。我無法描述當我從地上爬起來用腳走路時感到多麼有安全感,竟生出「解脫」的喜悅。當然,更不好意思張揚那只是一台五十CC輕巧型的摩托車。
兩輪的招架不住,四輪的甭提。熱心的朋友體恤我住得遠,替我去駕訓班報名,我在她的鼓動下幻想有一天能很神氣地開車。通知書寄來了,五月二十開始上課。日期愈逼近,所有焦慮的反應都出現了;開始做噩夢、剝指甲、對汽油反胃……。五月二十那天,我再也受不了,把通知書撕掉,立刻快樂如一隻小鳥──逃避成功!朋友不可思議地批評一頓,「好啦,總有一天我會去學的,人格保證!」我說。有那麼一天嗎?如果有人用武力押我去駕訓場,逼著學,學不會就抽鞭子,可能學得成。唉!要是阿諾在就好了。
心不在焉而導致「短路」,這種笨拙最具拙趣。像我祖母那樣機伶敏銳的女人,有一回煮稀飯時,居然被我從飯鍋裡舀出一隻手錶,可以媲美愛迪生煮蛋的趣事了。做為她的徒孫的我,也常常一心三手,充分發揚家族脫線傳統。小時候,媽媽叫我買胡椒,我買辣椒;要我去竹叢下把鴨子趕回來,我聽成去剝竹籜──這兩句閩南語音近,我也絲毫不懷疑指示,因為她是一個常常有新奇做法的母親。於是,當我捧著一畚箕的竹殼子交給她時,我看到她氣得大笑的表情,彷彿不相信我是她親生的女兒。
這種心不在焉的毛病隨著沉浸稿田太深、一時無法回到現實而時常發作。明明往廚房走,忘了去廚房做什麼?撥通電話,忽然不記得撥給誰?只好這麼問:「我是簡媜,請問你是誰?」有一天臨出門,急著找眼鏡,翻遍客廳、書房,找得天雷勾動地火,喊妹妹:「妳有沒有看到我的眼鏡?」她忽然用很怪異、說不出話的表情趴在樓梯上「痙攣」。當時,覺得她這種隔岸觀火的笑鬧態度很令我不舒服,她斷斷續續地把話說完:「眼鏡……在……妳臉上!」我才想起剛才找眼鏡時曾習慣性地扶眼鏡的,只好自我解嘲:「難怪覺得視力變清楚了!」聰明人做起笨事比笨的人更笨! 大部分的心不在焉發生在盥洗室。洗澡忘了帶衣服,隔門喊救兵,偏偏家人拿蹻,談條件敲竹槓,或乾脆跩跩地:「竹本小姐,我們不知道妳喜歡穿什麼衣服,妳自己出來拿?」這種尷尬時刻最能檢驗對自己身體的開放程度。拜家族脫線淵源之賜,我也不難抓到復仇機會,浴室裡有人喊了:「拜託啦,幫我拿衣服!」「口木先生,你學小狗叫,我就去拿!」「汪!汪汪!」「不對,那是母的,我要聽公狗叫!」「嗯……汪汪!汪汪汪!」「不對,我要聽公狗被踩到尾巴的!」「該該!該該該!」
還好,在外頭盥洗室鬧的笑話沒人知道──我必須經過「思考」才能分辨哪一扇門是「女廁」。
有一回,跟朋友上啤酒屋,兩扇盥洗室門上各掛一個俏皮布偶,必須掀開它們腰部的布才能分辨男女,由於不好意思,我沒掀,逕自進入其中一間。當我出來,等在門外的一位男士立刻表情錯愕,嘟囔著往另一間走,正巧,也出來一位女士,他完全被打敗了以至於搔著腦袋去掀門上的布偶再看清楚,臉上充滿懷疑,像驚嚇過度忽然懷疑自己是不是男人一般。
另一家布置雅致的茶藝館,同樣兩扇門,只標示「♂」、「♀」符號。我傻眼了,完全不記得哪個屬於我?由於走錯門害那位男士失去信心的記憶令我不敢再輕舉妄動,又不想坦承忘了符號意義,只好用小技巧掩飾大笨拙,問服務小姐:「麻煩您幫我開女廁的燈!」顯然,我必須記住這兩個鬼符號,總不能笨到連廁所都找不到。我站在門口「思考」,符號的原始來源既不可得,只好賦予新的解釋以強化記憶。「♀」像什麼?棒棒糖?一對小野花?都不好,後來想通了,背十字架的是女人,像箭一般射出去的是男人。下回,我會記得走向苦難的十字架,去從事神聖的解放。
M與W的英文縮寫也困擾我,在某種情況下,我對形體一樣、位置不同的符號辨識能力很差──包括禁止左轉、右轉的交通號誌。總之,某次聚餐,我與另一位男士同時打算去化妝室,我們沿途交談,由於小酌幾杯酒,微醺加上歡愉的談話,柔和的燈光曖昧地照在M與W兩個鍍金字上,瞬間讓我喪失判斷能力──或者,在那種暈然的氛圍中,潛意識裡自以為雌雄同體或渴望成為男人或不願承認自己是女人的原始念頭出來作怪,於是,我選擇M,而他以反射動作走向W不經思索。忽然,他慌張地推門而入彷佛遭受極大的打擊:「我們錯了!」「什麼錯了?」我以為他想延續剛才的話題修正什麼意見。「妳應該去那裡,我應該在這裡!」我很窘,居然問了一句笨話:「難道不能同時在這裡嗎?」他說:「原則上不行!」「哦!這樣啊!」所以生平第一次,我被趕出男廁。叫我這張臉往哪兒擱呢?心裡暗罵自己:「妳笨死了,笨到要別人告訴妳是男的女的!妳是W,W裡面的W,再搞錯就是豬!」
現在,我賦予這兩個字母新的解釋,W是女人上半身的素描,M是男人下半身的寫實線條。
笨到這種程度有藥可救嗎? 兩床毛毯
在浮誇的末世荒城裡,我像一隻傷感的鷹,停棲在暗夜的一棵枯木上,眺望遠處、梳理記憶,搜尋那些在航飛過程中令我眼角微溼的故事。總要找出一兩件事、一兩個人,帶著它們跨過世紀門檻,提燈一樣,才能在新世紀裡安頓。
他是社區警衛,五年前就已瘦得像一截沾雪老樹幹。他慣常沉默,不是因為上了年紀或脾氣古怪,而是一種自在清明的沉默;彷彿看多了人、嚐遍了事,知道人間是怎麼回事,也就不需多言。
「看到沒?以後要用功讀書,才不會像他一樣當工友,知不知道!」「知道。」小公園裡,一個媽媽看他推著單輪推車到處整理廢園,趁機對小孩進行機會教育。
他沒聽到,但我想他知道。塵風不能蒙蔽玫瑰花園的丰采,烏雲倒影也不會改變河流的清澈吧!他沒有分別心,義務幫社區人家整理園子,尤其是那些未住人的荒院,他救活花木,默默布置社區入口的花圃,多餘的盆景就運到喜歡園藝的住戶門口,也不留話,他想有心人會懂得另一個有心人留在空中的氣息吧! 你無法報答他,當你發現門口的信箱太小老是塞不進雜誌,忽然被他的巧手改裝成大信箱時;當你發現搖搖晃晃的院燈也被旋緊時;當你又發現不知哪來的花木裝扮著你的花台時;你才知道你這麼個每天出門去斤斤計算的一坯土是無法報答巨嚴的關懷的。
可是,不利於他的言語開始溢散。有人指責他只幫某幾戶理院子,不幫他打掃門口;有人說他年紀大了,社區需要孔武有力的人以維護安全……。真正原因是,他知道太多事情了,包括角逐委員會總幹事的兩組人馬如何明爭暗鬥,包括選舉時原本要用來賄選的金錢如何落入某人口袋,以及每個月有點奇怪的小工程帳目。所以,犧牲一個老警衛,是那撮人僅有的共識。反正,他只是個警衛。
就這樣走了,不知去處。直到有一天,公司樓下的警衛伯伯說有人找我,就在警衛室昏暗的角落,我再次看到他。他說:從報上知道妳在這兒上班,今天有事得辦,從桃園上臺北來,順道把東西帶來。年前回大陸探親,經過香港買了兩條毛毯,用不上,送妳們姊妹,冬天保暖。
「妳們姊妹,都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他誠懇地說。
我欣然接受。不只是收毛毯,是收一個長輩對小輩的祝福與期許。藉著這份期許,我知道不管在末世荒城也好,險惡行旅也罷,我這一生要找的珍貴之寶,其中一項叫做「人的尊貴與厚重」。 藏與不藏──後記
藏
發現那只紙箱,才驚覺自己的某些行為愈來愈像母親與祖母。
高齡九十四的阿嬤雖然失明仍然保存「藏東西」癖好,眼前的姑且不提,就說四五十年前她兩眼炯炯有神、身手矯捷還是個年輕祖母的那時候;轄區內有五個孫子,皮的皮、懶的懶,愛哭的愛哭、貪吃的貪吃。很快地,她制定「鞭子與胡蘿蔔」規章予以管教。鞭子,無須贅言,胡蘿蔔,換算成當年物資就是蕃薯餅、蜜餞、果子及金柑仔糖等零食。
祖母雖不識字卻是個精算高手,她對孩童的咀嚼、消化能力甚有研究,其名言是:鐵塊放入小孩嘴裡都會溶,還說我們「餓到青狂狂,連桌腳嘛強強欲拖去嚼」。因此,為了延緩零食被吃光的時間,她最愛買一小包硬梆梆的金柑仔糖犒賞「員工」,經濟實惠,最適合用來驅趕小鬼。我們領得那粒深褐或五彩的小糖球,必定立刻放入口中以免滾落於地找不著,癡癡地吮吸一會兒後,忍不住從嘴裡掏出來觀看它被溶解的程度,如掏眼珠般小心翼翼,通常是,放回嘴裡沒多久,它就溶光了。
溶光了,當然再去討一顆!不約而同,五個小鬼又纏上來,阿嬤兇巴巴地說:「沒有就是沒有!」於是耍賴的耍賴、跺腳的跺腳,年紀小的乾脆躺在地上哭喊、翻滾,狀甚痛苦;阿嬤掏出口袋以證明所言不假──這真是重要的一刻,同時啟發我們兩件事理:一、大人會說謊,二、糖果被藏起來了。
小鬼們一哄而散,跑入屋內,在客廳、穀倉、眠床、密腳、衣櫥分頭翻找,齊力「抄家」,終於抄出日曆紙包著的糖球,一人一顆,剩餘的放回原處──當然,沒多久,被移往他處,再不久,又換一處,直到只剩那張薄薄的日曆紙。
藏匿與搜尋的戲碼不斷上演,阿嬤的手法愈來愈複雜,我們破解的功夫也愈來愈純熟,甚至出現馬戲團才看得到的疊羅漢或體育老師不敢教的民俗雜技。問題來了,阿嬤刻意追求高難度的分批藏匿術,以致連她自己都忘了還有一些藏在哪裡?每隔一段時日,總會在穀倉一角找到長滿青霉的椪柑兩個,在棉被縫隙看到黏成一團的五顆糖果或在碗櫥頂端一頂斗笠下發現四片軟趴趴的餅乾,螞蟻走成的虛線比我們的嘆息還長。 零食本屬奢侈品,又被如此糟蹋,難免惹出「民怨」,自此之後我們要求她「權力下放」,務必平分完畢,讓我們吞入腹內一了百了,或各自藏匿自行負責──由此衍生之手足鬩牆情節,如誘拐、共謀、爭吵、偷取、打架、哭訴則不在此詳述,參照現今政治生態即可。
移居臺北,阿嬤老了,五個孫子長大後皆承續家族基因,從嗜糖小童轉骨變成討厭甜食的人,慶生時迫不得已買生日蛋糕只為了有個地方可以插蠟燭,昔日哭喊糖果、在地上打滾如喪考妣的情景已永遠消逝。這確實剝奪了一個祖母的樂趣,若孫子孫女喜好甜食,她可以到處購買鳳梨酥、綠豆椪、牛舌餅犒賞員工,如今,她無計可施,只能問:你鄉下阿姑做的醬油要不要拿一瓶回去?
我母親的藏匿哲學是不藏謂之大藏。昔年,她手上無零食管轄權,小孩不會找她,但女孩們總會對母親的抽屜、衣櫥感興趣,東翻西找,偷偷挖一點面霜抹臉,穿上大衣照照鏡子,甚為滿足。在我們看來,她不只不藏而且不收,東西、物件隨意置放,如此鬆散,誰也不會懷疑她有什麼收藏。有一次,我問她當年出嫁戴什麼金飾,她回房一會兒,竟現出一條令人眼睛一亮的項鍊,我心想:「嚇!妳的房間被我們翻過上百次了,怎從來沒見過這玩意兒?真會藏哩!」我因此懷疑她一定具有蜘蛛人功夫,能飛簷走壁、倒吊晃盪,才能藏得天衣無縫。
藏匿的樂趣就在「攻於心計」的過程──不被他人找到又不致連自己都找不到,前者難,後者更難。因此,藏功猶如設定密碼,皆屬一種自我挑戰,而且,自己一定要戰勝自己,否則,領不到錢事小,所藏之物曝光事大。
祖母與母親最重要的一次藏匿戰役不是防著我們,是針對從未謀面的人,小偷。
十幾年前,我還住在娘家。有一陣子社區頻傳竊案,小偷連白晝亦出沒,左鄰右舍皆遭殃,財物損失慘重,轄區警方雖加強巡邏,但怎麼巡也巡不到案發現場。照這種進度,遲早會輪到我家。家人商量對策,既然不願花數萬元更換鐵門鐵窗,只能消極因應;各人藏好錢財珠寶,家中儘量保持破舊、雜亂(平日即已如此),電視、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用品,要偷就請便,只要小偷不嫌重。 某日清早,我剛起床,見母親蹲在陽台整理花木,從背影看,大約是替植栽換盆添土。我走近,她嘻然傻笑,彷彿做什麼不可告人之事被逮到,此時我才看見地上有一牛奶罐,她招認,所有的金飾已用塑膠袋層層包覆,置於罐內,現正要藏入花盆裡。我大笑,讚她一流。只見她速速覆土,把原來那棵半死不活的榕樹種回去,土上又佈置了石頭、蛋殼、煙蒂,將盆景放回窗台原處。我很放心,甚至覺得可以夜不閉戶。
相較於母親的「掩埋法」,祖母因視力退化必須儘量單純,省去複雜手法以免造成自己不便。我們盤問數次,她不露口風。後來,一再保證不會告訴小偷、我們也不會去偷,她才吐實;原來,她把數萬元現金用報紙、塑膠袋包好,偽裝成一條豬肉狀,藏入冰箱冷凍庫,與貢丸、魚、排骨、雞肉共處一室。這招「急凍法」堪稱出神入化,至此我非常放心,除了小偷找不著,我相信想得出這種妙招的祖母這輩子不會得老人癡呆症。
不久,某個鼾聲大作的夜裡,小偷果然來了。料想他無處下手又不想業績掛零,只好偷書包。天亮,準備上學的小弟找不到書包,隨後在陽台發現書本、作業散落一地,裝車票與零用錢的皮夾被丟在花盆上,損失兩百元,那是他當日的營養午餐與晚餐費。可怪的是,我們一點也不在意被闖空門,甚至懊惱自己睡死了沒看到賊兒臉上複雜的表情。唯一激動的是兩百元苦主,他很氣,罵小偷為什麼不乾脆把課本、作業一起偷走?我們提醒他,「才兩百元,不要要求太多。」
冰箱裡那條「五花肉」愈來愈瘦了,舉凡叫瓦斯、收報費、清潔費或身上欠缺現金時,就把那條五花肉拿出,無須退冰,即取可用,剩餘的復歸原處。唯一提出質疑的是一位瓦斯先生,「鈔票怎是冰的?」「不然怎樣?你要燙的嗎?」
就像幼時,金柑仔糖只剩那張日曆紙,阿嬤藏的五花肉最後也只剩那張報紙。 不藏
一年半前,為了搬家不得不整理地下室儲藏間,從最黑暗的角落拖出一只紙箱,上頭只寫「稿子,暫存」,卻完全不記得是什麼稿子。用美工刀劃開膠帶時,猶如法醫解剖無名身軀,不帶感情又摻雜好奇。一疊原稿、剪報現身了,散出紙張的潮溼味,這味道屬於活的世間,像一頭淋著暴雨的耕牛窩在草堆上,身體乾不了,遂閉目養神,現在,陽光出來,可以睜眼了。
於是,發覺自己的行為像母親與阿嬤;亂藏像媽,藏到忘了像阿嬤。
我對寫過的文稿常有自暴自棄傾向,除非隸屬計劃中作品或足以歸併出主題的才會收妥,其餘皆隨之生滅;因此,有的只見原稿,有的只剩剪報,有的只記下篇名及發表處,原稿剪報俱無。海明威形容寫過的書像一頭死去的獅子,深得我心。寫作最快活之時在於構思、書寫過程,如一趟孤獨的攀岩之旅,外人不解把自己吊在半空中有何樂趣,攀岩者卻樂此不疲,繼續挑戰更高的海拔。然而,一旦作品完成,其後續瑣事令人不耐,猶如攀岩者回家之後,總是腰痠背痛。
這箱稿子乃過去十多年間未結集之作,長長短短一百二、三十篇,十分龐雜,隨手抽幾篇流覽──我得決定丟棄或保留,發覺混亂之中不乏趣筆,遂原箱封妥,搬至新家。新居不像舊宅有儲藏室可存放一切礙眼之物,這箱子放在我天天看得到之處,成了眼中釘。
加拿大作家楊‧馬泰爾(Yann Martel,著有《少年Pi的奇幻漂流》)處理失敗之作的法子是放逐──不是放逐自己,是稿子;他從印度某個小鎮寄出那包原稿,收信地址是虛擬的,在西伯利亞,信封上還寫了回信地址,也是虛擬的,在玻利維亞。當他看到郵局職員蓋上郵戳時,心情跌入谷底,痛不欲生。 相較之下,海明威的遭遇更慘。一九二二年,海明威二十三歲,為報社駐歐記者,他的妻子飛來相會,卻在巴黎的里昂車站等火車時,把海明威的整箱原稿遺失了,這是他四年間的全部原稿,包括長篇一、短篇十八、詩十篇,就這麼永遠丟掉了。然而,海明威一點也不沮喪──請恕我如此想像:見面時,大他八歲的妻子伊麗莎白哭出聲:「我把你的稿子搞丟了,我該去撞牆!」海明威安慰她:「親愛的,沒關係,那些都是失敗之作!」伊麗莎白瞪大眼睛:「既然如此,你為什麼不丟呢?」海明威乾笑兩聲,答:「我下不了手。」
好。海明威一點也不沮喪,他重寫。次年,出版第一本書《三個短篇和十首詩》,接著,《我們的時代》,再來,……。我推測,隨著「救回」的作品愈來愈多,他與太太的感情卻愈來愈糟,因為,到了二十八歲(挽救「四年間原稿」滿四年之後),海明威離婚了。可見,他很在意這件事。
將近一年半,我既迷惘又煩躁,不想讓稿子坐飛機去西伯利亞或是利比亞,也缺乏薩伐旅獵人海明威重寫的能耐,只剩修改、整編一途;其箇中滋味猶如減肥塑身,看那團肥肉如如不動,很想衝至廚房拔刀,因此,一度罷筆。之後,想起舊作《浮在空中的魚群》《七個季節》早已自書市絕跡,不妨趁機歸併,一起調控。此舉乃搬石頭砸腳後又用力敲頭,是自我凌虐。果然,「開挖」不久,即倣效工地圈著圍籬寫上完工日期欺騙路人,裡頭放一部挖土機,沒動靜了。
後來,我尋思這事再拖下去也不是辦法。萬一我遭逢意外,文稿落入壞脾氣編輯手裡有礙我安息;若是一病不起,豈非得躺在病床上一面痛苦呻吟一面吊點滴改稿跟時間賽跑─果真是「忙得要死」,屆時必定憎恨現在的我荒廢光陰、疏懶度日。這一想,有所警覺,加上思及偏遠地區、失能家庭的眾多孩童欠缺學費與午餐錢,那箱殘膏賸馥若能換版稅給他們些微溫飽也是美事。於是,鼓起精神比對稿件記錄簿,央朋友從圖書館搜尋未留存的數十篇文章(泰半已找不到),再與百餘篇原稿、剪報匯整,共挑出六十七篇較有可觀者;又拆解《浮在空中的魚群》(原有四十篇,其中十四則小品擬併入《下午茶》,四篇刪除,剩二十二篇留用),前後共存八十九篇,逐一增筆、修潤,務使殘膏恢復甘醇、賸馥散發香氛。
每當我宛如遊牧民族背著我的牛羊(稿子)在星巴克、麥當勞或街角咖啡館、捷運車廂放牧時,眼倦神勞之際,總浮現孩子吃午餐情景(這大概是小學時我特別期待吃營養午餐的情感餘緒罷),遂踴躍前進,依稿性、旨趣劃分五輯:或爬梳尋常事理、提煉生活滋味,或懷想鄉園舊情,或閒話旅行、閱讀之所見所思,或變奏為小說化寓言,或歸返自身記述成長、創作、夢境之體會與感悟;復按以東北西中南沿步道而行的意象貫串全書,以雜樹、野鳥、藤、亂石、芒叢寄託這一段修繕舊稿的心情。
梅雨時節,竣工,名為《微暈的樹林》。
註:《七個季節》舊稿與其他小品、短文另匯成《密密語》一書。
二○○六年六月,臺北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紅嬰仔:一個女人和她的育嬰史【20週年紀念版】
79折
特價284元
加入購物車
陪我散步吧
9折
特價359元
停售
女兒紅(二版)
9折
特價252元
貨到通知
我為你灑下月光:獻給被愛神附身的人
9折
特價432元
加入購物車
吃朋友
9折
特價315元
貨到通知
夢遊書(25K)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私房書(25K)
9折
特價198元
加入購物車
下午茶(25K)
9折
特價225元
加入購物車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一個小男孩的美國遊學誌
9折
特價288元
停售
密密語
9折
特價234元
貨到通知
微暈的樹林
9折
特價252元
加入購物車
月娘照眠床(25K)
9折
特價207元
加入購物車
頑童小番茄(新版)
9折
特價216元
加入購物車
好一座浮島
9折
特價225元
加入購物車
舊情復燃
9折
特價180元
貨到通知
只緣身在此山中
9折
特價252元
加入購物車
水問
79折
特價237元
加入購物車
跟阿嬤去賣掃帚
9折
特價288元
貨到通知
女兒紅
9折
特價207元
停售
胭脂盆地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八十一年散文選
9折
特價243元
停售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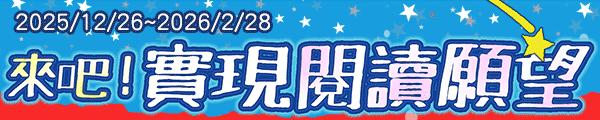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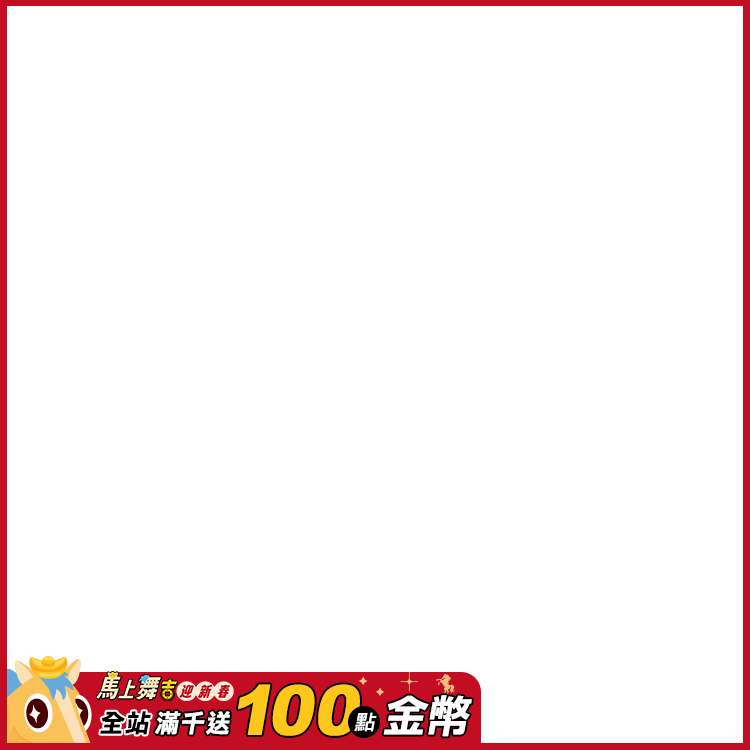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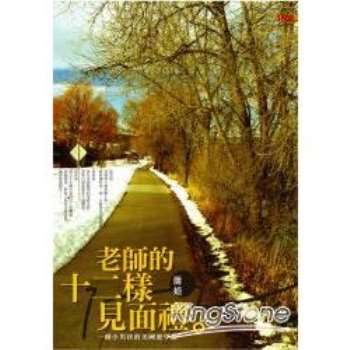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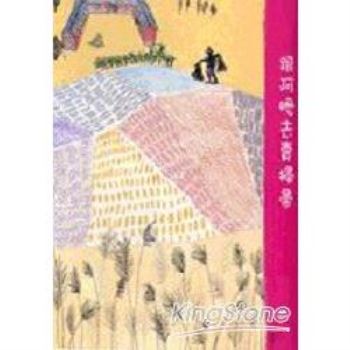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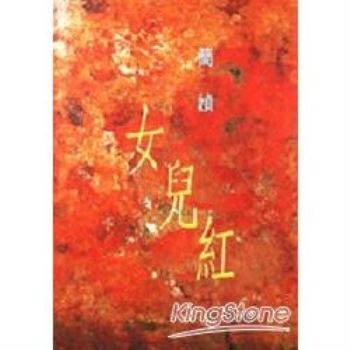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