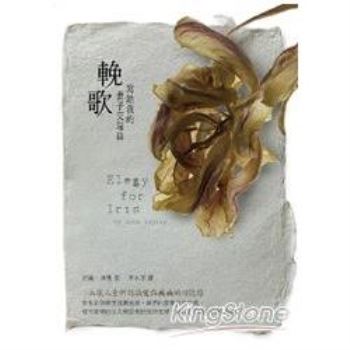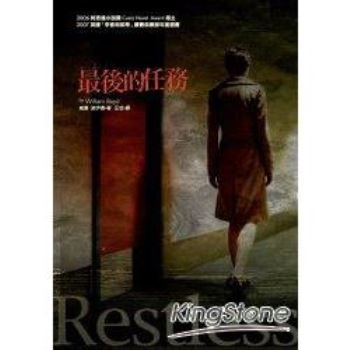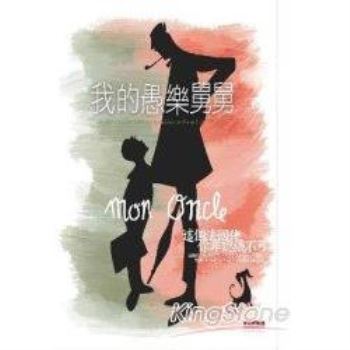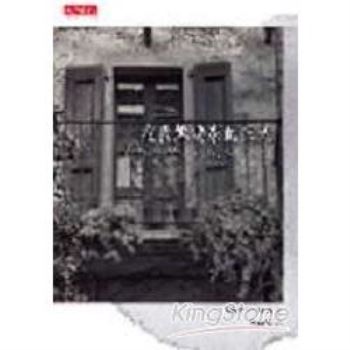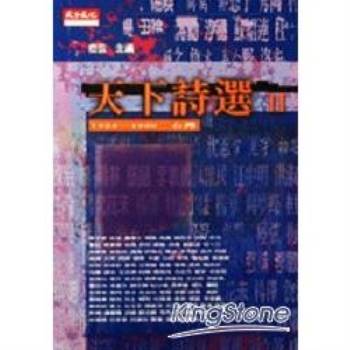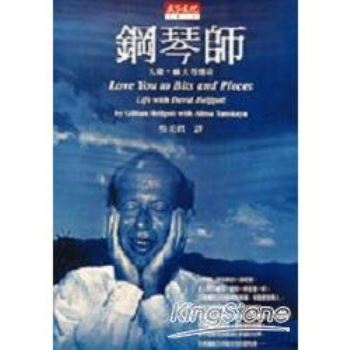-
排序
- 圖片
- 條列
輓歌(新版)
一本讓人重新認識「愛」與「疾病」的回憶錄當生命的速度逐漸放緩,痛苦的節奏日益升高,唯有愛情的注入與甜美記憶的支撐,得以維持晚年的明朗曠達……「這個女人看起來,並不像擁有過去或未可知的現在。」知名文學評論家暨牛津大學教授約翰.貝禮,在書中如此回憶他初見妻子艾瑞絲.梅鐸時的印象。 艾瑞絲是英國知名哲學家,同時著有二十餘本小說,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語作家之一。一九五四年,這名具有獨特魅力的哲學家,在牛津聖安東尼舞會上擄獲了貝禮的心,兩年後,二人攜手步入禮堂。婚後,他們珍惜彼此相守的幸福,同時也享受著婚姻中必然的孤獨,保有各自原有的心靈生活。但在一九九四年,曾被喻為「黃金頭腦」的艾瑞絲,被診斷出罹患了阿茲海默症,從此,時間對她失去了意義。過去與現在瓦解成一團結合黑暗與焦慮的混沌;當初她帶給貝禮的第一印象,似乎成為某種不祥的預言……。而曾經一起分享文學心得、因名畫而感動的他們,此後只能一起觀看電視上播出的「天線寶寶」……。 這是一本特別的回憶錄——它回顧了青春的短暫美好,記錄了步入衰老的殘酷現實;它呈現出生命的堅韌與脆弱,同時卻也描繪出一段二十世紀最動人的愛情故事。透過對往日喜樂與悲傷的抒情追憶,這部卓越的作品,擴展了我們對於「愛的可能」及「愛的範疇」的想像空間。——《紐約時報》
最後的任務
1976年的夏天,露絲‧葛馬丁發現她平凡而深居簡出的母親莎莉是二次大戰時的優秀女間諜,而且她的真實名字叫做伊娃.德列托斯卡雅!1939年,二十八歲的伊娃定居巴黎,是個美麗的俄國移民。二次大戰爆發後,她被英國秘密情報局的路卡斯.羅瑪吸收,在他的指導下,學習技能,成為一個完美的間諜。她隱藏起內心的情緒,不信任任何人,包括她最愛的幾個人。戰爭結束後,伊娃小心的重新建立她的生活,成為一個典型的英國妻子和母親。然而一旦當過間諜以後,就永遠是間諜。現在她必須完成最後一項任務,這一次,伊娃沒法獨力完成:她需要她女兒的幫忙。作者波伊德以交叉書寫方式,一方面以露絲為小說的敘事者,一方面以倒敘方式回到二次大戰的間諜世界,讓讀者在緊湊的時空交錯中,看到人性的光明與黑暗,戰爭的殘忍,愛情的虛幻及母女親情的可貴。
天下詩選II
新詩這座殿堂是怎樣建造起來的 中華自古有詩國之稱號,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個國家,詩與生活的關係像我們中國人這麼密切的。中國人過年把詩貼在大門口,稱為春聯;每家牆上掛的字畫,都是詩語;男女青年談情說愛,把詩句題在紅葉上,繡在絹帕上;到廟裡抽籤,籤條上有詩;在家裡喝茶,茶壺茶杯上亦有詩;夏天天熱拿起一把扇子,扇面上有詩;說個笑話、打個謎語,用詩;嬰兒夜哭寫一張「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的紅條兒收驚,用的也是詩。總之,中國人一生下來,就跟詩發生了密切關係,也因此有人稱中華民族是詩的民族。由於詩或韻文的形式深入生活,詩的語言也融 然而,這值得我們驕傲、珍惜的優美傳統,正逐漸式微。今日的詩國子民,已經不再讀詩了;儘管當代台灣的新詩壇百花盛放,春景燦爛,但一般人仍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冷漠以對,工商業掛帥的霧翳,已經使很多人變成詩盲。 當僅占人群中少數又少數的詩人,孤絕地立於文學創造的頂峰,他們的心情是寂寥的、落寞的。他們多麼盼望有更多的愛詩人,走進新詩這宏麗殿堂,在這「靈照之戶,應物之軒」(柳宗元語)中熙然而歌,婆然而舞,盡情徜徉,歡喜讚歎;放眼飛閣亭榭的檻外,展望一個詩國再興的明日。 詩歌改良的前奏,從黃遵憲說起 中國古典詩不但在人類的美學經驗中,創造了無以倫比的不朽業績,更為詩與大眾生活的結合,提供了少見的範例。但自晚清以後,漸漸露出衰象來。 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詩壇,擬古、因襲之風瀰漫,詩人們寫詩,不從自我的文學生命出發,去追求藝術的獨立創造,而一味抱殘守缺,在陳腐的舊形式中揀拾古人的唾餘,「模宋規唐」、「抄書寫詩」的結果,使詩歌完全脫離社會大眾,而淪為少數人孤芳自賞、酬應唱和的工具。 那是一個各方面都在試圖改變、突破的年代,對於詩運的衰落,自然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感到隱憂,並不約而同地發出改良的呼聲。「詩界革命」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興起的。一八六八年,此一運動的倡導者黃遵憲首先發難,向終日埋首故紙堆中無病呻吟的「俗儒」們展開批判,並以「我手寫吾口」、創造「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以及在舊詩體中開發新內容、廣納新名詞為號召,展開一項有理論主張、也有創作實踐的詩歌改良運動。 外交官出身的黃遵憲富有現代觀念,文化視野遠大,他希望自己能成為詩歌界的「華盛頓、傑佛遜、富蘭克林」。他所掀起的文學新風潮,也的確稱得上波瀾壯闊,影響深遠(與他同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丘逢甲等都曾受到他的啟發),但稱之為「詩界革命」,卻嫌有欠周延、不夠徹底,詩的革命,應該是從思想內容到語言形式全面的脫胎換骨,不是舊瓶裝新酒,把火車、輪船等等新名詞納入詩中,就算完成了改革。儘管黃氏一再強調他寫詩「疏於詩律,選韻尤寬」,有決心突破一切羈絆去開創新局,但自始至終,他一直未能徹底擺脫舊有的格律 黃遵憲的文學改良,在整個中國現代詩歌的發展上,雖然只有階段性的意義,但他的出現,無形中為後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新詩的發韌,作了最好的先期準備,對隨之而來的真正的詩歌革命,明顯的產生了催生的作用。 新詩的誕生 新詩又稱白話詩、自由詩或現代詩,它的歷史,始於五四白話文學運動。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八項主張: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爛詞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對這八項主張,胡適雖然沒有明白指出針對那一種文類,但對清末民初文壇情況稍有了解的人,一眼便看出來,那多半是衝著舊詩而發的。 按清代小說文學發達,其書寫的工具不是淺近的文言,就是市井流行的口語,要說把小說列為革命對象,意義是不大的,而最應該大加改革的,其實應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舊詩。不過胡適的八項主張,只限於詩的形式層面的糾正,尚未深入到詩歌內容和本質的提升,論者每每把這種偏失歸咎於胡的眼光短淺,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其實明智如胡適者,怎會只重視詩形而忽略詩質?他只不過認為當時最急切的事,還是語言工具的改變,一旦白話能夠順利搶灘登陸,接下來的工作就可以循序漸進了。 一九一八年,也就是五四的前一年,《新青年》雜誌率先改刊白話文章,小說、議論文字之外,也兼及新詩。胡適除了發表他的白話詩作外,並進一步提出詩體大解放的主張,認為中國詩歌要想起死回生,必須打破五言七言的格式,打破平仄,廢除押韻,另外就是重視域外詩歌作品(如美國意象派的詩)的譯介,以便從中學習別人的長處。胡適這些大膽而富創意的文學觀念,立刻引起了文壇競寫新詩的熱潮,康白情、劉半農、劉大白、朱自清、冰心等,都是那個時期湧現的詩作者。這些人的新詩,無論題材、內容或表現技法,都令人耳目一新。雖然少數作品 新詩運動對中國詩歌總的發展來說,可以稱得上是大破大立。胡適之後,詩的後續建設工作,更有另一批俊偉之士經營拓殖,成效卓著;而幾個重要文學社團的成立,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如「文學研究會」(一九二一)的提倡為人生而藝術,主辦《小說月報》及《詩》月刊,推展小詩的創作;「創造社」(一九二一)的主張尊崇自我、張揚個性的浪漫主義,開拓自由詩的審美領域;「新月派」(一九二三)的重視人生的愛、美與自由,提倡新格律;「普羅詩派」(一九二八)的指出改造社會新途徑,反映勞工疾苦,謳歌革命;「現代派」(一九三二)的 台灣的新詩 日本占據台灣長達半個世紀,其間雖用盡一切高壓、懷柔手段迫使台胞歸順,以遂其「皇民化」的目的,但被污稱為「清國奴」的台灣同胞絕不向異族屈服,五十年間,武力的抵抗活動從未間斷,其英勇事蹟可歌可泣,光耀史冊。武力的抗爭之外,文學,也是抗爭的方式之一。 漢文教育被迫廢止、書刊改用日文後,台灣的本土文學活動幾乎被趕盡殺絕,呈現全面停頓狀態,最後只剩下一批寫漢詩(舊體格律詩)的詩人,以廟宇、祠堂、會館、書院或私塾作掩護,默默地延續文化的薪火。雖然他們的文學思想比較保守,詩藝上的創意也不大,但他們為喚起大眾民族意識所作的貢獻,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值得肯定。 根據陳少廷的研究,台灣的新文學
鋼琴師
琴鍵上的癲狂靈魂 藝評家和精神科大夫都小心翼翼,鑑別診斷誰是天才,誰又是瘋子,這兩個族類經常難以一線畫分。難怪米歇爾‧傅柯在《癲狂與文明》開宗明義就引帕斯卡的話,「人必然發瘋,若不瘋便等於是癲狂的另一種形式」。 我第一次閱讀《傅雷家書》,比台灣正式的版權本還早十年,十分欣喜而錯愕。當年我的聆樂書慣剛啟蒙不久,對書中頻頻出現的新鮮雋語鼓動不已,奇妙地妄想自己也是收信人。那時我初到外地求學,差不多結束聯考壓力和青春期叛逆,開始與父親建立「劃時代的和諧」。當我讀到傅雷以悔罪的心境,向傅聰求贖懺情時,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這樣的一個中國父親。我總以為中國父親,大概都像賈政那副霸相,天經地義的債權人。眼前這位自承大惡難赦的父親,竟是通達中西文史哲,一個幾近完美而值得崇拜的偶像。 我在《傅雷家書》嘗到音樂的美與親子的苦,帶來相當深遠的影響。所幸我的聆樂啟蒙,幾乎是單打獨鬥的「創世紀」,我就是逼勵自己進取的隱形父親。謝天謝地,我總算沒把自己塑造成瑪麗‧雪萊筆下的《科學怪人》,科學家創造了一個他駕馭不住的合成人,科學怪人因為容貌醜陋難容於世,竟然變成復仇的惡靈。邇來科學界又奮力於動物複製的高科技,「科學怪人寓言」多少帶來人文氣息的省思,像傅雷那麼通達的教育家,都可能「誤入歧途」,我真不知普天下的凡夫凡父要如何步步為營了。 想像一個人每天要喝十五到二十杯咖啡,每杯都要加五塊糖,而且他會任咖啡和糖潑在地板各處。他還要沖無數次澡,讓十條濕毛巾隨意散置屋內。他還無時無刻不點菸,一天平均要抽一百二十五枝菸,他的話匣子比菸還多,衣服、書籍、樂譜比叨叨絮絮的話匣子還紊亂。這位名叫大衛‧赫夫考,在精神病院流浪十年的過氣鋼琴家,可不可以算是「一個科學怪人」?在咖啡因、糖、尼古丁、裸體、口吃不絕之前,鋼琴也曾像專制的主人,全盤占領他童年的時時刻刻。 由於奧斯卡得獎電影的傳媒強勢散播,大衛‧赫夫考的傳奇事蹟,在國內外都不是陌生的話題。「每一個約翰,都會有一個匹配他的瑪麗」,大衛和吉莉安的結縭,真像是他們各自「神祕表演」的一部分。如果吉莉安不嫻熟占星術,她大概不會那麼快就相信命理,下了一個平常人所不敢的決心。我們總以為崇尚玄學的人,性格往往會有反智的傾向,吉莉安給我們極正面的例子,她並不率爾善變,不是完全依附水晶球行事的人。 占星學家收容了癲狂鋼琴家,這是二十世紀的喜劇還是悲劇?一個半世紀前,帕格尼尼病故時,尼斯教會拒絕他葬入教會墓地,因為他那超絕技巧的小提琴琴藝,謠傳為妖魔附身,理該下地獄受審。這顯然是笛卡爾崇尚理性以來,一則矯枉過正的例子。精神病患在基督教國家,曾被集中趕上「愚人船」,任由河流和海洋的莫測自然力量,決定他們的生死下落。痲瘋病匿跡後,兩萬多間病院改收癲狂病人,精神病患又進入「大禁閉」時代。直到精神分析醫學奠立基礎後,癲狂患者才被當作疾病醫治。 我們總算不再輕鄙帕格尼尼,認為他活該死無葬身之地,給與其音樂人格尊貴地位。舒曼、沃爾夫、慕索斯基、史麥塔納都是被癲狂吞噬生命的作曲家,白遼士、李斯特、蕭邦、柴可夫斯基、馬勒也一直徘徊在躁鬱邊緣。這些浪漫而幾乎脫序的音樂家,再也不必被拘捕於愚人船或禁閉院,反而能被供奉在藝術殿堂。藝評家和精神科大夫都小心翼翼,鑑別診斷誰是天才,誰又是瘋子,這兩個族類經常難以一線畫分。難怪米歇爾‧傅柯在《癲狂與文明》開宗明義就引帕斯卡的話:「人必然直瘋,若不瘋便等於是癲狂的另一種形式。」 藝術家果真要像個盜火者嗎?當他偷來照明與取暖的火種時,也帶來天譴的懲罰。霍洛維茲曾因練琴過度消耗,三次隱退又三次復出樂壇,到底這是折磨或成就?蘇東坡看石蒼舒的醉墨草書時慨歎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始名粗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惝怳令人愁」。恭維與調侃兼俱。蘇東坡還勸石蒼舒不要像張芝那樣臨池苦學,把一池水都染黑了,與其那樣辛苦用絹帛寫書法,還不如拿來充當被褥。即使像傅雷那樣的鴻儒,都不能看破這一點,遑論恓恓惶惶望子成龍的小市民。 所有傳記書都不脫離「教養」主題,這個傳奇人物為何會走上如此崎嶇或坦蕩的路呢?哀樂中年,我愈來愈不願用單一的成功或失敗價值觀,去品評成名人物的得與失。大衛‧赫夫考出身「猶太劫」家庭,這個印記幾乎是他求藝路上的原罪,父親的自卑情結,深遠影響孩子的教養。這個出生背景雖為殊相,但日後的小留學生和音樂比賽的種種經歷,卻是相當普遍的情境。出人頭地的明星演奏家,畢竟只是少數崢嶸者可達的願望,大部分習樂者還是退居基層的樂教工作。如果習樂伊始,便認清這個人生本相,或許整個過程不會那般扭曲,兩代的愛恨情仇能沖淡 幸好有吉莉安。我們總習於將光環全然罩在藝術家頭頂,遺忘在暗處的親友。沒有吉莉安,就沒有東山再起的大衛,她也是名正言順的盜火者。當傅聰開始談戀愛時,傅雷馬上諄諄訓示:「我一生任何時期,即使鬧戀愛的時候,也沒有忘卻對學問的忠誠。學問第一,藝術第一,真理第一,……愛情第二,這是我至此為止沒有變過的原則。」這個父親在兩個月前的信上才剛提及:「但我做爸爸的總是犯了很多很重大的錯誤……,可憐過了四十五歲,父性才真正覺醒!」 吉莉安大概會反對傅雷的告誡,倘若她依「鋼琴第一,愛情第二」這個規律,她如何忍受大衛那些比嬰兒還糟糕的「科學怪人行為」?吉莉安嫁了「丈夫」,意外得個「鋼琴家」;萬一當初嫁的是「鋼琴家」,恐怕得不到「丈夫」。願天下有情人,而不是有琴人,終成眷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