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第二卷《民權與憲法》: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結束後,日本國內要求開設議會的呼聲高漲,自由民權運動席捲全國。在此背景下,一八八九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發佈,一八九〇年,召開了帝國議會。這一時代可以說是日本現代歷史的起點,日本的國民國家和競爭社會正是在這一時代確立的。
本書從政府、民權派、民眾三極對立這一新的視角對這一時代展開描述,係作者在長期專門研究基礎上為一般讀者而作,內容通俗易懂、觀點鮮明具有衝擊力,日文版問世後在日本讀者中反響強烈。
本書特色
《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一卷於2006年出版,於2010年完成整套叢書出版。2006年出版的幾卷,目前已重印第16次,最晚於2010年出版的,亦已重印了第9次;這樣的再版情況甚為罕見,反映這套叢書在日本讀書界所受到的重視及歡迎程度。
叢書作者為1945年至1960年間出生的各大學相關學科教授,學術功底深厚,寫來深入淺,態度比較持平公允。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
① 《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著
② 《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著
③ 《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著
④ 《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著
⑤ 《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著
⑥ 《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著
⑦ 《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著
⑧ 《高速增長》武田晴人著
⑨ 《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著
⑩ 《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編
目錄
序/導讀
序
「開設國會之好時機」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四月十四日,黑田清隆率領的政府軍進入熊本城;五月二日,控制了鹿兒島縣政府所在地。雖然戰鬥還在持續,但是西南戰爭的勝負結果已定。在此背景下,《靜岡新聞》認為,「吾東洋帝國社會面貌斷然一新之大好時機」已經來臨。該報還強調,若要讓人民負擔「內亂之非常費用」,須開設國會徵得人民之同意;英國革命中查理一世「實行苛刻之法令」,未與「人民達成共識」便根據「一己之念」徵收租稅,結果「化為刑場上之朝露」;「無論為政府計還是為人民計」,「今日乃開設國會之好時機」。
如同板垣退助等人在一八七四年提出的要求設立民選議會的建議書中所寫的那樣,「負有向政府繳納租稅義務者,即具有與知及贊成或否決該政府事務之權利」,也就是說,政府向國民徵稅時必須得到國民的同意,這種國民擁有共商租稅權的想法是近代議會制的出發點。當時的現實是,明治政府在西南戰爭之後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抵制議會的開設將變得越來越困難,不僅如此,統治集團內部的裂痕也在擴大。
但是明治政府首腦只看到西南戰爭終結了反政府士族勢力奪取政權的可能,幾乎沒有認識到在這場「大勝利」背後隱藏著將會動搖其自身權力基礎的新的問題。儘管他們早就意識到制定憲法、開設議會的必要性,但是當時並沒有將其作為緊迫的政治課題,更沒有想到後來會被在野的政治力量逼入困境。
「紀尾井町事件」
一年之後,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四日早晨,明治政府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對造訪他家的福島縣權令山吉盛典說,如以十年為單位劃分明治元年後的三十年的話,則第一階段的十年是「創業」時期。這一時期雖「兵馬騷擾」不斷、疲於「東奔西走、出兵海外」,但最終總算還是安定了下來。接下去的十年甚為關鍵,為整頓內治、制民之產,本人雖不肖但仍決心盡職於內務卿。而最後的十年,乃是「守成」時期,我想到那時一切將交付給後來之賢者。
其實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大久保利通正在著手發行興業公債以推行殖產興業和鼓勵士族創業,同時正在謀劃改革地方制度以及教育思想尚未成熟的天皇。但是其理想沒有實現。這天上午八點左右,大久保利通乘坐馬車離開私宅,前往位於赤坂臨時寓所內的太政官邸上班,在從赤坂見附進入紀尾井町的一條僻靜、狹窄的夾道時(這條夾道的左右兩邊分別是北白川宮宅邸和壬生基修宅邸,前者是現在的赤坂王子飯店所在地,後者是現在的新大谷飯店所在地),被石川縣士族島田一良等六人所斬殺。
島田等人在《斬奸狀》中申討道:現在的政治「上非出自於天皇陛下之聖旨,下非來自於眾庶人民之公議,而是取決於數名獨居要職之官吏臆斷專決」。其實自明治六年圍繞「征韓論」發生政變以後,大久保利通確實身居政府之要,但他並不是一個獨斷專行的領導者,在做出決斷前他總是認真聽取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部下的意見。然而,他對於那些以暴力與政府作對的敵人毫不寬恕。對待士族叛亂自不待言,即便是對於因地租改革騷亂而起的伊勢暴動(一八七六年)他也下令徹底鎮壓。伊勢片田村原來的村長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在寬政時代,即使當農民起義軍迫近城牆時,藤堂藩政府軍的槍也只是放空槍,但是現在像要報仇一樣地殺戮人民,如此殺下去,「傲然自恣……,何以謂王政哉」。幕府末期以後一直與日本政治有關的阿耐思特.薩濤也在日記中寫道,「民眾非常憎恨大久保,所以看到他死了大家好像都很高興」。
「制度的時代」
大久保利通死後,大藏卿大隈重信成了首席參議,伊藤博文就任內務卿。大隈重信出身於佐賀藩,雖然他在財政方面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專家,但是在以薩摩、長州的藩閥佔主導的政府中屬於旁系,長州藩閥伊藤博文實際上成為政權運轉的中心。據說大久保利通沉默寡言、非必要時不說話,因而讓身邊的人惶惶不可終日,但是伊藤博文則完全不同,他待人隨和而不故作威嚴。
這不僅是兩者個性的不同,也象徵了時代的特點。在大久保利通執政時期,沒有政治、社會權力基礎的明治政府,必須一邊鎮壓守舊派士族的叛亂和民眾對於新政的反抗,一邊創設各種近代制度。例如其出台的徵兵制,以「四民平等」為前提,解除了士族的武裝,同時平民也可以被徵召入伍,結果招致了來自士族和平民兩方面的強烈反對。如果順從當時的「輿論」的話,這一制度在當時也許根本就無法確立。前述阿耐思特.薩濤的評論反映的與其說是大久保利通個人,不如說是當時的政府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孤立處境。但是,大久保利通等的執政風格確實像「有司專制」、「臆斷專決」之類的語言所形容的那樣,非常激進。
西南戰爭最終斷絕了「封建復辟」的可能性。在建設近代國家這一目標方面,民權運動和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圍繞著誰來掌握主導權,鬥爭變得非常激烈。如果說在大久保利通所說的「創業的十年」,是在和「過去」進行鬥爭的話,那麼其後「建設的十年」就是圍繞著「未來」進行鬥爭;而且在這一鬥爭中,民權運動成了引導「文明」、「進步」的強有力的旗手,而政府方面卻陷入了守勢。
與此同時,政府內部矛盾激化。已經過了二十五歲的明治天皇開始批判文明化以及薩摩、長州勢力對權力的壟斷,其親信元田永孚、佐佐木高行等人的影響力增大。右大臣岩倉具視在華族的待遇和參議的權限等問題上和伊藤博文意見對立,連明治十四年發生的流放大隈重信的政變這樣的大事,兩人也沒有進行過「合謀」。山縣有朋雖然大致上和伊藤博文步調一致,但是一直試圖將陸軍變成自己的據點。
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決策的堅定和政治運營的穩定,已經不能依靠個人的「決斷」了,唯有依靠一定的「制度」。本書的第一個主題就是,帝國憲法體制是如何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各種勢力的理念、利益中形成的。
「政府、民權、民眾」
西南戰爭後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自由民權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歷史上首次真正由被統治者來集體討論「國家的理想狀態」,並且為實現這一理想狀態而開展行動。自由民權運動在思想和社會層面的影響要比表層的「運動」、「事件」本身廣泛、深刻得多;沒有民權運動,日本就不可能迅速形成和確立國民國家。
對於民權派來說,西南戰爭之後才是他們的創業的時代。但是在民權運動興起之前,身份制度、領主割據體制的廢除,私有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等的確立,這樣一些近代國家的基本框架已經通過明治政府的努力實現了。尤其是明治政府進行了比西歐市民革命徹底得多的土地改革,通過地租改革,將幾乎所有的耕地變成了農民的私有土地。而在西歐市民革命中,那些擁有大量直接經營土地的封建領主原封不動地轉變成了大地主。民權運動是在這一基礎上興起的,它和政府之間進行的鬥爭是圍繞著政治制度和政治參與展開的。
民權派在其提出的要求設立民選議會的建議書中強調,要讓人民「與天下共憂樂」,就必須使人民「參與天下之事」。由此可見,民權運動在要求政府開設議會的同時,也在試圖向民眾灌輸一種將國家的命運和自身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我國」的意識和「國民」意識(National Identity)。沒有對於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就不可能形成政治運動,因此即使就民權運動自身的發展需要來說,民眾的「國民」意識也是不可缺少的。激進的民權思想家植木枝盛斷言,那些將本國之事當作「他國異域之事」持旁觀立場之人,對政府也好外國人也好,極易服從之,他們「實乃國家無用之人」。那些拚命逃避徵兵的民眾,也被主張民權的《自由新聞》等媒體罵為不知道「護國義務」的「懶惰懦弱」之徒。
在向民眾灌輸「國家」和「國民意識」的同時,民權派還對民眾的自發運動(如「借錢黨」、「困民黨」)進行了批評。面對通貨膨脹以及囤積居奇等所導致的米價上漲,「借錢黨」、「困民黨」開展了要求降低米價的運動;當出現通貨緊縮時,它們則要求延期歸還借款或者取消債務。民權派指責由「借錢黨」、「困民黨」代表的民眾的這種行為侵害了商業自由和財產權,是一種類似「社會黨」的行為。民權派認為人民擁有共商租稅權,以及建立在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等近代權利論基礎上的私有財產權,因而自然反對政府對於自由經濟活動的干預。同時,民權派的文明觀和國民思想也從根本上規定了他們在沖繩、北海道、阿伊努、朝鮮以及中國問題上的言行。
由上可見,以往民權運動史研究所描繪的民權派和民眾站在一起對抗明治政府、構成兩大對抗陣營的景象,是缺乏依據的。明治政府和自由民權運動的目的都是要建設近代國家,但是它們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是兩支互相對立的政治力量。但是當時在它們之外,還存在著另一支力量,那就是民眾。民眾一方面強烈反對政府的政策,同時持有和民權派不同的要求,他們是一支獨立的力量。我們應該從上述三大力量之間的對抗這一角度去把握當時的政治格局。因此,本書的第二個主題就是研究三者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民權運動和民眾之間的關係。
「兩種自由」
西南戰爭後的十多年間,經
試閱
一、竹橋事件和立志社建議書
「苛政之苦」
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一點半左右,近衛炮兵大隊近二百名軍人殺死了大隊長和一名士官後宣佈起義。這就是竹橋事件。
當時的陸軍在東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設有鎮台(地方司令部),此外,在皇宮北之丸的竹橋門附近駐有負責守衛皇宮的近衛軍。近衛軍由從常備軍中選拔出來的精英組成,近衛炮兵大隊有三百多名官兵。西南戰爭中政府軍之所以能夠獲勝,就是因為擁有近衛炮兵部隊的火力,以及由以巡查名義組織起來的各地士族組成的招募巡查隊的積極支持,就像當時人們所唱的那樣,「要是沒有近衛炮兵加招募隊,敵人就會湧入繁花似錦的江戶」。
但是,戰爭的恩賞僅僅給予了政府和軍隊的上層,普通士兵不僅戰後得不到獎賞,政府甚至以財政困難為由,將他們的津貼乃至於襪子、毛巾等配給都削減了。一名原本是堺縣(今大阪府)農民、後來當兵並參加了此次造反的士兵控訴道:「去年立有戰功者不僅沒有得到獎賞,津貼等亦被減少,且規定損壞器物必須賠償,隊中之人皆曰嚴酷」。(其口供記錄)
那些認為恩賞不公的人並非簡單地著眼於錢,就像當時的輿論對於暗殺大久保利通事件所表現出來的冷漠一樣,在這一認識背後存在的是民眾對於明治政府政治表現的強烈不滿。其實西南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這種不滿就已經存在。當時在東京的一處女子浴場中,當有人說到「這種混亂的世道到底甚麼時候才會結束?還不如德川大人回來的好」時,大家都說「是啊,是啊」。
更何況那些在殘酷的內戰中為政府出生入死的士兵,他們不可能不關心「政治」。也許正因為如此,參與起義、當兵前曾是埼玉縣秩父郡農民的田島盛介(森助)在給家屬的告別信中寫道:「近來普通百姓苦於苛政,吾願殺暴臣以護天皇、復良政,有能者指揮我等起事等等,不一一贅述」。
起義之初,近衛炮兵大隊的士兵們相信東京鎮台屬下的預備炮兵隊也會起來造反,到時候該預備炮兵隊大隊長岡本柳之助會統一指揮兩支造反的部隊。但是晚上九點過後,岡本卻下令預備炮兵隊緊急集合,然後將隊伍帶往東京北部的飛鳥山一帶,以防止兩支隊伍會合。與此同時,近衛步兵連隊的士兵也大部分站到了鎮壓者的一邊。儘管如此,還是有一百多名士兵拉著一門山炮跑出了兵營,其中九十多人來到了位於赤坂的臨時皇宮門前。但是,前來鎮壓的部隊已經在此擺開了陣勢,結果起義領導人之一大久保忠八自殺,其他人被俘。
十月十五日黎明前,參加起義的五十三名士兵在深川越中島被槍決。這些士兵大多是二十四歲左右的年輕人,出身於平民或者農民。後來,又有兩名下士被處以死刑。在這一事件中,總共有三百六十多人被判有罪,其中十三人死於獄中。岡本為何在關鍵時候阻止部下起義,理由尚無定論。日清戰爭後曾經發生過日本浪人等闖入朝鮮王宮殺害閔妃(明成皇后)的事件,這一事件的首謀者就是岡本柳之助。
「軍人訓誡」
當時的政府和陸軍直到事件即將發生之前都沒有察覺。只是到了那天下午,內務省官員才聽說「今晚近衛軍和鎮台的士兵將到皇宮放火,並將待諸官員上朝時將其斬盡殺絕」,但是當這一消息傳到軍隊首腦處時已過了晚上八點。如果那天內務省官員沒有得到消息,鎮台所屬的炮兵隊與近衛炮兵大隊會合的話,事態的發展也許會完全不一樣。事後陸軍卿兼近衛都督的山縣有朋陷入「前日之騷亂發生以來吾深受刺激,片眼朦朧雖咫尺﹝近距離﹞不能見」的狀態,絕非不可能。
軍隊的「動盪」並沒有結束。竹橋事件發生一個星期後,八月三十日,出現了一則關於鎮台預備炮兵隊將向天皇請願的流言。即使在參加過鎮壓行動的近衛步兵聯隊中,一八九七年一月好像也有人在策劃,於九月二十四日平定西南戰爭一周年時「起事」,包圍皇宮和炮兵工廠。
十月十二日,山縣有朋發佈《軍人訓誡》,極力鼓吹軍人精神在於遵守「忠實、勇敢、服從之三大紀律」;關於「聖上之事」,列舉了諸如不許批評「聖上容貌之類瑣事」等規定,並宣佈「是非朝政、私議憲法」以及「諷刺﹝批評﹞政府機構佈告等舉動」,「與軍人本分相違背」。在當時,士兵通過閱兵等活動,有較多的機會近距離地見到天皇,因此談論天皇和政治等已是平常之事。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日本近現代史卷十: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
日本近現代史卷九:後戰後社會
日本近現代史卷一‧幕末與維新
日本近現代史卷二‧民權與憲法
日本近現代史卷三‧日清、日俄戰爭
日本近現代史卷四‧大正民主運動
日本近現代史卷五‧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
日本近現代史卷六‧亞洲、太平洋戰爭
日本近現代史卷七‧佔領與改革
日本近現代史卷八‧高速增長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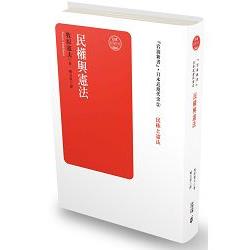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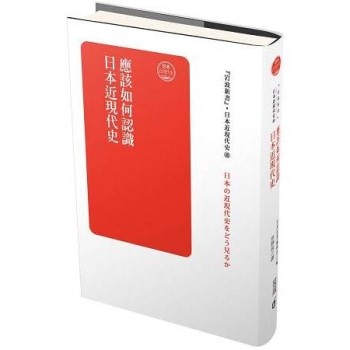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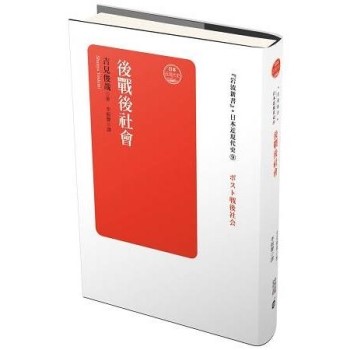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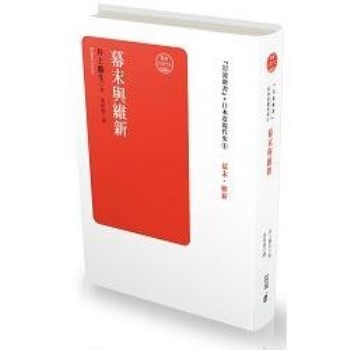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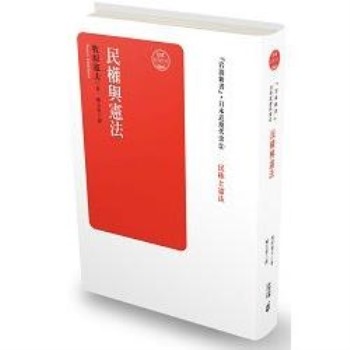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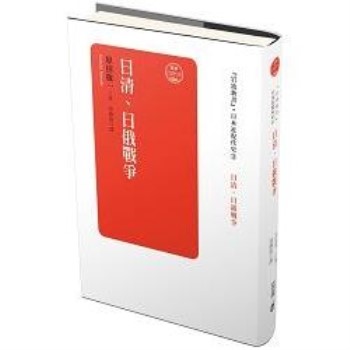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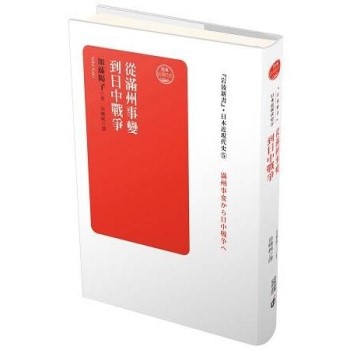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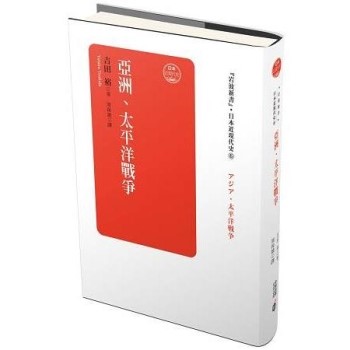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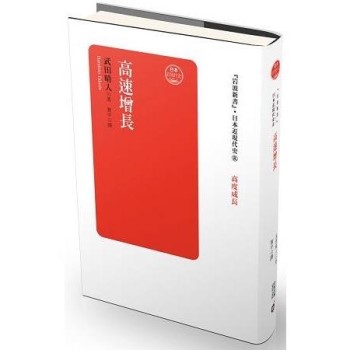


商品評價